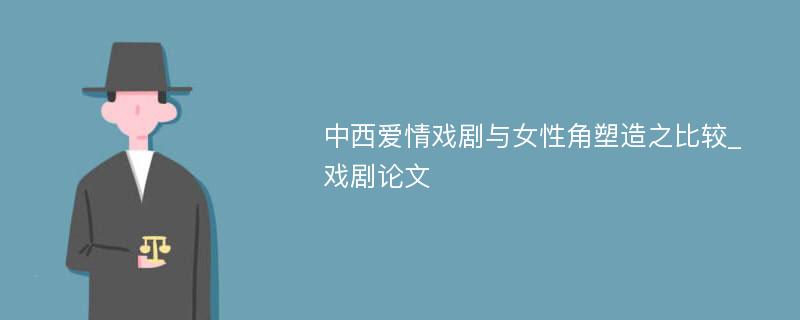
中西爱情剧和女角塑造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角论文,中西论文,爱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戏剧都有大量的爱情剧,“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中西民族的共同心理,也是中西戏剧的一个永恒母题。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的源头,《奥德赛》就写了奥德修与潘奈洛佩夫妻二人的团圆。所谓“迎合观众的心理”(《诗学》语),不就是“迎合”民族心理么?亚里斯多德想贬低《奥德赛》的“双重结构”,却无意中道出了《奥德赛》的另一种价值,这是亚氏始料不及的。荷马既是第一个伟大的史诗诗人,又是第一个伟大的戏剧诗人,这是亚氏说过的。《奥德赛》就是西方文学“大团圆”的第一部作品,从戏剧角度说,也是这样。
西方的爱情剧不乏“大团圆”的佳作。莎士比亚大量爱情剧的结局是大团圆的。《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的一个特点,就都是两对以上情人的大团圆,可称之为集体团圆的喜剧。在莎氏描写爱情的剧本中,欢乐的喜剧大大超过死亡的悲剧,这是不可不加注意的。17世纪法国高乃依的名剧《熙德》违反古典主义原则让一对冤家大团圆。莫里哀的名剧《伪君子》、《悭吝人》中的对对情人全是大团圆。18世纪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费加罗与苏珊在人间成为眷属,19世纪歌德的名剧《浮士德》中的男女主角在天上团圆。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擅写爱情悲剧的现代美国戏剧家奥尼尔,他的《安娜·桂丝蒂》的结尾也给水手一家留下一个“幸福的结局”。他的《啊,荒野》更是“有情人好事多磨——终成眷属”这一公式的典型作品。哪个作家不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包括他自己呢?奥尼尔的家庭和爱情都很不幸,使他对美好爱情的憧憬更强烈,便用戏剧表现出来。堂·吉诃德对桑丘说:“古往今来歌颂她们的诗人真有那些意中人吗?决不是的。他们多半是捏造一个女人,找个题目来做诗,表示自己在恋爱,或者有资格恋爱。”(《堂·吉诃德》杨绛中译本上册210页)。奥尼尔此剧应作如是观,他自己也这样说的:“真实情况是,《啊,荒野》是对我从来不曾经历过的一种青年时代的怀恋。”
中西爱情剧既有喜剧,也有悲剧。西方爱情喜剧的例子上面说过了,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中国爱情悲剧的例子。马致远写《汉宫秋》,不顾历史事实,让王昭君投江死了。孟称舜《娇红记》中王娇娘与申纯双双殉情。《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那对也是。孔尚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与侯方域是各自出家。黄图珌的传奇《雷峰塔》中的许宣与白娘子也不团圆。中国戏曲百分九十以上的素材来自广义的短篇小说,《搜神记》中就有《紫玉》那样的爱情悲剧作品。唐传奇中的《莺莺传》、《霍小玉传》、《任氏传》、《长恨歌传》都是写爱情悲剧。宋话本中的《碾玉观音》更是一篇爱情大悲剧。如果把《诗经》中的《氓》、汉乐府的《焦仲卿妻》视为诗体短篇小说,写爱情悲剧的作品就更多了。中国的古小说有爱情悲剧,中国的戏曲当然也有爱情悲剧,因为中国小说是戏曲的母胎。
中国爱情剧既有大团圆的,也有不团圆的,那么有没有共同性呢?有的。中西喜剧从正面直接描写了剧作家“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中西悲剧则从反面间接表达了剧作家“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除了上述的例子外,中西爱情悲剧都有“合葬”的母题也是明证。中西剧作家同情、歌颂追求真挚爱情的男女,祝福他(她)们,谴责、鞭笞破坏爱情的恶势力,这便是中西爱情剧的共性,喜剧如此,悲剧亦如此。
中西爱情剧也还有各自鲜明的特性。总的来说,中国戏曲更多地从喜剧的角度去表现剧作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以歌颂为主。《西厢记》写张生和莺莺恋爱,老夫人反对,在红娘帮助下,他们冲破礼教约束,结为夫妇。中途遭到拆散,以后张生高中,又奉旨团圆。《倩女离魂》写张倩女与王文举相爱,为母阻挠,文举被逼进京赴考,倩女魂魄离开躯体,半路赶上文举,结为夫妇。以后双双回家,梦魂仍入躯体,还是夫妻团圆。《牡丹亭》写杜丽娘和柳梦梅梦中相恋,丽娘单思而死,魂儿与柳相爱,求柳掘墓开棺,使她复生,与柳结为夫妇。这些都是以大团圆作结的典型例子。
我们的戏曲这样写是有民族文化心理根据的。孔子已提倡“中庸”,“中庸”就是中和之美,孔子说这是最高的美。悲剧就是悲哀过头了,过了头就不好,“过犹不及”不符合中庸之道。儒家不欣赏悲剧。中国老百姓大体上也不欣赏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比王国维早三百年的李渔说得更彻底:“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为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风筝误·第三十出“释疑”·尾声》)。这是他的喜剧宣言,他还有一首诗《偶兴》是这个宣言的注脚,把他的意思表达得更痛快。笠翁十种曲全是大团圆爱情喜剧。元稹的传奇《莺莺传》是悲剧,张生把莺莺抛弃了,莺莺嫁了人,谢绝见他。但董解元、王实甫就把它改为喜剧,都反映民族心理。中国大团圆的爱情剧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积极的,如《倩女离魂》、《墙头马上》、《牡丹亭》、《西厢记》,靠男女主角(主要是女主角)的努力赢得幸福。中国文学有上上品的大团圆名作,北朝《木兰诗》堪称白眉。《木兰诗》是可以作小说、戏剧看的,它先于戏曲,说它是积极倾向的喜剧的滥觞未尝不可。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不自由,男女爱情不幸者居多,剧作家要化悲为喜只有依靠浪漫主义手法。《西厢记》中的一对,可以在梦中相会。张生走了,他在梦中和莺莺相会,梦见莺莺追出城外,来到客栈,要与他“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到了《倩女离魂》,就发展为女方灵魂与男方结为夫妇。到《牡丹亭》,杜丽娘干脆死而复生,所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题词》)。《长生殿》中的明皇贵妃,还在天上重圆,嫦娥借月宫给他们成亲,所谓“天上夫妻,不比人世”(非人世可比)。这种为追求纯真的爱情,梦中可以相会,魂儿可以离体,死可以复生,天上能相见的浪漫主义手法,是中国爱情剧一个常见的艺术特色。剧作家的形象思维,有本土道教的土壤,也有西来印度佛教文学的助力,先开花于小说,后结果于戏剧。
西方的爱情剧不同,更多的是从悲剧角度去表现积极的爱情主题。其震慑人心的写法是“悲-欢-离-死”,和中国的“合”差了一字。《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一对双双死了。《阴谋与爱情》那一对也是双双死了。《欧那尼》那一对在新婚之夜双双自杀。《费德尔》中的费德尔服毒自杀。《茶花女》中的茶花女死在阿芒怀中。《大雷雨》中的卡杰林娜跳进伏尔加河死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脱与奥菲莉霞,奥赛罗与苔丝德梦娜全都死了。这个“死”又绝大多数是自杀。在西方的爱情剧中,情人魂儿离躯、死而复生的构思似乎是很罕见的,梦中相会的例子也少见。
何以如此呢?这和西方有个“二希”文化传统大有关系。古希腊的“命运”观念是很强大的,不“死”不足以显示“命运”的威力;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是很有影响的,不“死”就不是如实写出;亚氏以悲剧为“第一等”,以悲喜剧为“第二等”,亚氏的悲剧理论在一个长时期内是“独霸”,导向如此,剧作家不乐意写二流作品。以后,希伯来文化进来了,不“死”不足以表现基督教“原罪说”,费德尔不是用“死”来向丈夫赎罪么?卡杰林娜不是受宗教压力跳进伏尔加河么?到了现代,弗洛依德的心理学说对戏剧家也有影响,弗洛依德的“里比多”与“原罪说”是相通的,情欲导致死亡,那更是“死”有应得了。西方现代爱情悲剧的“乱伦”主题与此有大关系。奥尼尔尤擅此道,其《榆树下的欲望》、《悲悼》三部曲就是典型例子。受西方影响,中国现代爱情悲剧也出现同类主题,《雷雨》就是。不过《雷雨》开了个头,却无人再敢问津,《雷雨》也就成为独一无二的“乱伦”爱情悲剧至今仍镇慑住中国观众的心。
中西爱情剧都有“情”与“理”的冲突。“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属“情”,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个人爱情利益应该服从国家民族利益的主题属“理”,这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西爱情剧这两个永恒主题都有,但比较地说,西方的爱情剧侧重从个人利益角度去写爱情至上,这与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很强大有关。只有古罗马的悲剧,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如伏尔泰一些悲剧强调个人爱情利益应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中国儒教主张“克己复礼”,现代中国的思想主流与主张集体主义。受其影响,中国古今的爱情剧中“理”胜“情”的主题比较突出。在现代,郭沫若最擅于写这类爱情剧,王昭君和蔡文姬的爱情,是大义凛然的爱情,是以国家民族为重的爱情,是很有理性的爱情。即使是卓文君的侍女红萧,也手刃她的爱人秦二,因为他是一个“奴才”,经不起威胁利诱,向文君之父告发了文君私奔的计划。在古代戏曲中,明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写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西施支持以国事为重的范蠡,说“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她同意将爱情放在一边,后又毅然入吴,帮助越王勾践一举灭吴。清朝洪升的《长生殿》背景是安禄山之乱。洪升一再称赞杨贵妃的死是“为国捐躯”。孔尚任的《桃花扇》写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结尾极为警世。大法师一声棒喝:“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恨,割他不断么?”于是男女主角,一个山南,一个山北,各随师父出家。出家是看破红尘,不好,但国破家亡,山河易主,而对国家民族的大悲剧,岂能沉溺于匹夫的不幸。四个“那里”,真是警钟长鸣,给世间无数荡女痴男以震慑灵魂的启示。
下面谈谈女性角色塑造的问题。中西戏剧的两性关系大不相同,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题目。中国戏曲家喜用对比手法写女性优于男性,美于男性。这种对比实在太普遍了,已上升为两性关系的结构,体现出中国戏曲正面女性形象系统占主导地位的特色。
仅以名作为例,关汉卿笔下的窦娥,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郑光祖笔下的张倩女,白朴笔下的杨贵妃及李千金,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红娘,洪升笔下的杨贵妃,孔尚任笔下的李香君,都优于美于剧中的男性。窦娥是《窦娥冤》中唯一的正面女性形象,是全剧的灵魂。她贞节,绝不屈从张驴儿。她为了婆婆免遭拷打,宁愿屈招赴死。她临刑前把天地也诅咒到了:“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王昭君因深明大义才去和番,她投江的悲烈行动感动番王,遂使番汉和好。《梧桐雨》和《长生殿》都写贵妃之死。明皇活着,她被赐死,谁自私,谁无私,谁真爱,谁假爱?答案自明。洪升写她一往情深,实在动人。所谓“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她的形象也比唐明皇美丽多了,土地公公帮她,牛郎织女怜她,嫦娥请她听仙乐,又借月宫给她。剧作家给她披上一件神话的彩衣。《墙头马上》的李千金被裴少俊休了,李坚定于爱情,裴屈服于父亲。崔莺莺、张倩女、杜丽娘在追求爱情上都比她们的爱人大胆、主动、坚强。苦头吃得最多,代价付出最大。《西厢记》还出现了红娘这样大公无私、成人之美、代人受过、敢于和老夫人面对面斗争的优美性格。在上述剧本中,女性往往是教育者,男性是受教育者。不是汉元帝教育王昭君,而是王昭君晓以大义;不是复社才子侯方域教育李香君,而是李香君劝戒他不要收阉党的财礼使他觉悟;至于那位张生,更是经常受到红娘的揶揄,在红娘眼中,他实在不算一个男子汉。
《琵琶记》与“荆、白、拜、杀”五部南戏都以女性为中心,或写其贤孝,或写其贞烈,或写其失志不渝,或写其深明礼义。《琵琶记》中的赵五娘、《荆钗记》中的钱玉莲、《白兔记》中的李三娘、《拜月亭》中的王瑞兰、《杀狗记》中的杨氏,在每本戏里都占主要地位。她们性格爽朗、品质崇高、忠于爱情,身处逆境而意志坚一。反过来,在男性方面,除《荆钗记》中的王十朋、《拜月亭》中的蒋世隆尚能匹配外,《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白兔记》中的刘知远、《杀狗记》中的孙华,都只是一种陪衬人物,不是忘恩负义,便是行动摇摆。尤其是蔡伯喈,在最早的剧本中是“三不孝”,被雷打死。在改编本中也难以翻身。赵五娘被肯定,蔡伯喈被否定,已成文学史定论。
晚明徐渭的《雌木兰》、《女状元》更是歌颂女性的剧本。这位愤世的奇才、李贽精神上的同党干脆直说女子胜于男子:“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子汉。”“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儿。”(《雌木兰》)。
中国戏曲中确有一批“立地撑天”的女英雄,除徐渭赞美过的隋朝的花木兰外,还有宋朝的梁红玉、明朝的秦良玉。最典型的例子是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一个年轻女子占了一个山寨,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她不管封建婚姻那一套,自找配偶杨宗保。谁敢欺负她,她就把谁打个落花流水,连她的公公、赫赫有名的杨六郎也被她一枪打下马来。为了保家卫国,她退役20年后又亲挂帅印。这样的女英雄虽纯属虚构,但形象完整,艺术上真实可信。中国戏曲的这类女英雄是西方戏剧史上极为罕见的。
在研究中国戏曲两性对比结构时,绝对不能漏掉中国戏曲中的妓女形象,她们的特点是比那些善良多情专一的上层女性富于斗争性。关汉卿所塑造的赵盼儿(《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毫无疑问是首屈一指的艺术形象,因为她生前就胜利了,救出落难姐妹宋引章,斗败恶少周舍。她是一个喜剧人物,现代性格,不仅罕见于中国戏曲,也罕见于西方戏剧。焦桂英、杜十娘是复仇女性,王魁与李甲罪有应得。
中国戏曲的正面女性形象常常以“变形”的形式出现,著名的例子是《雷峰塔》的白蛇与青蛇。“女鬼”也是一种“变形”,除焦桂英、杜十娘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也一度当过“女鬼”,那是多么孤独、幽怨、美丽、执着的女鬼。晚明周朝俊《红梅记》的李慧娘也是一个。中国戏曲家独特的艺术构思来自中国志怪文学的传统,深受印度佛教文学的影响。西方戏剧罕见有“女鬼”的形象,浪漫派小说家如霍夫曼、爱伦·坡、梅里美的短篇小说中有,但非戏剧。复仇者也有,但那是爱神维纳斯的铜像,她在新婚之夜活动起来,把新郎吻死了,因为这个新郎把结婚戒指套在她铜制的手指上,又与另一个女子结婚。梅里美的《伊勒的女神》是有寓言性的,主题近于中国的小说戏曲:惩罚负情郎。但这是小说不是戏剧,是复仇女神不是女鬼。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也是著名的复仇者,但她无须成鬼再复仇,她活着的时候就手刃二子,让伊阿宋断子绝孙。
中国戏曲的两性对比结构及从变形角度塑造正面女性,实际上正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最低,最受压迫。戏曲不过是一种反写。在这里,文学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的情况恰成反比例表现出来,中国妇女在现实生活中越苦,在文学的理想世界中越光彩夺目。宋代理学盛行,“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明清两代都喊得很凶,但小说戏曲就在此时兴起,响起了对抗的声音。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中国女性的美好、苦难、愿望是由中国男作家的笔来表现的。剧作家用“变形”手法写超自然现象,是避开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借助想像的翅膀使手中的笔更自由。“反写”之所以有力,决定于剧作家的主体意识。因此,作为“艺术家的个人”,中国多数戏曲家是摈弃、反对儒家轻视、蔑视女性的陈腐观念,而代表女性说话的。在中国文学的各种类型中,中国戏曲的民主性的精华是相当突出的,尤其体现在爱情剧上。
西方爱情剧没有两性对比的结构,以莎士比亚的三十七个剧本为例最有说服力。莎氏是以塑造正面系列女性形象著称于世的,然而他的剧本中同时有一个正面男性形象的系统,同时体现着人文主义思想。我们不能说朱丽叶优于美于罗密欧,苔丝德梦娜优于美于奥罗,莪菲利霞优于美于哈姆莱脱,只能说他(她)们都是正面角色,这在“莎学”中已是定论。17世纪法国高乃依的《熙德》的男女主角同样是理性主义者,男主角唐罗狄克占主导地位,因他是西班牙的民族英雄,施曼娜不得不放弃杀父之仇而嫁他,因为君主、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18世纪德国席勒的诗剧《阴谋与爱情》、法国博马舍的话剧《费加罗婚姻》中的男女主角同样有反抗性。歌德的《浮士德》以男主角命名,我们不能说玛甘泪优于美于“自强不息”的浮士德。法国雨果的浪漫主义名剧《欧那尼》也以男主角命名,不能说爱上绿林强盗欧那尼的素儿优于美于那个强盗。西方戏剧中也有女性优于美于男性的例子。如《茶花女》、《玩偶之家》、梅特林克的《阿里亚娜与蓝胡子》、《莫纳·瓦娜》。但总的倾向是男女并重,剧作家在塑造优美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重视塑造优美的男性形象。萨特笔下的弟弟奥瑞斯忒亚,就优于美于姐姐厄勒克特拉,体现着萨特“自由选择”的积极人道主义(《群蝇》)。易卜生既写了娜拉,也写了斯托克曼(《人民公敌》。由此可见,两性审美对比结构,非西方戏剧角色系统的普遍结构。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戏剧的正面男主角,是更为典型的性格,是剧中的灵魂,是时代精神的主要体现者。众所周知,哈姆莱脱和浮士德是世界文学的典型,莪菲利霞、玛甘泪的爱情痛苦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男女双方的思想不在一个平面上。
西方爱情剧同时重视塑造男女主角,在两性关系上,多以男性为主,这和他们有“二希”文化传统也分不开。西方有英雄史诗、英雄悲剧,中世纪有中古英雄史诗、骑士传奇,男性英雄一贯是西方传统的英雄形象。普罗密修斯就是西方戏剧史上第一个顶天立地的男性英雄神。《圣经·旧约》中的耶和华,是男性神的威力的象征。上帝创世,上帝救世,在西方传统观念中是天经地义的。西方的“二希”文化以男性为主体,西方戏剧的两性关系也以男性为主体,英雄美人的爱情剧最重要的主角,自然也是男性的英雄。
至于西方爱情剧中为什么罕见有复仇“女鬼”的形象,原因有五:第一,西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永远不如东方那么严重,西方从中世纪中期起产生了“骑士精神”,尊重和崇拜女性是骑士的天职;第二,基督教讲博爱与宽恕,不主张“复仇”,《复活》中的妓女玛丝洛娃就宽恕了改好的聂赫留朵夫,茶花女也原谅了阿芒;第三,西方的悲剧传统观念是一悲到底,女性复仇却是胜利,是化悲为喜;第四,西方有“模仿说”,菲尔丁已告诫过作者少写鬼,女鬼复仇不是现实生活中有的事;第五,西方没有东方(印度、中国)的志怪文学传统,或者说,远不如东方那么源远流长。由于这五个原因,西方爱情剧便极少出现复仇女鬼的形象。
1994年2月27日于福建师大
标签:戏剧论文; 爱情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喜剧片论文; 奥德赛论文; 西厢记论文; 牡丹亭论文; 雷雨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