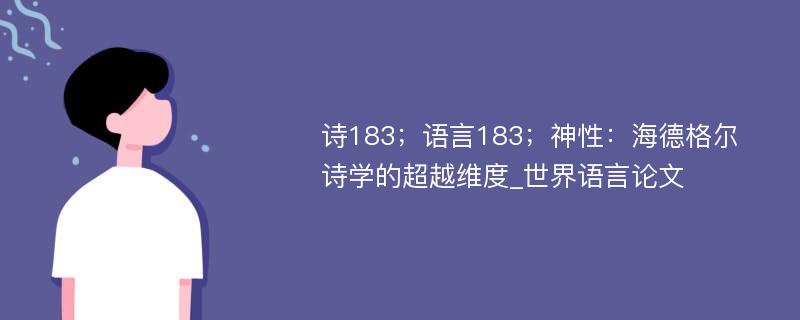
诗#183;语言#183;神圣——海德格尔诗学的超验之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诗学论文,神圣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5—0081—07
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于海德格尔诗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存在论角度入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做法的确符合海氏思想的实情,因为存在问题乃是贯穿海氏一生的思想主题,诗学问题之所以会进入他的思想视野,根本上是因为诗和艺术乃是存在的意义或者真理的一种重要的发生方式。不过,熟悉海氏诗学文本的读者想必都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海氏在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等人的诗歌进行阐释的时候,主要不是把诗与存在的意义联系起来,而是重点谈论诗与神圣、神性、诸神以及上帝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一现象昭示我们,在海氏的诗学思想中还存在着一个超验的维度,正确理解这一维度,是我们准确把握其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
一、存在之思何以接纳超验之维?
海氏的存在哲学中是否存在着一个超验或者神学的维度?这在东西方的“海学”研究中都是一个广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著名的新教神学家云格尔宣称,“自康德和黑格尔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对神学产生过他(按即海德格尔)所产生的影响”,①诸如布尔特曼、奥特等著名神学家都曾从海氏的前期或后期思想中引申出系统的神学理论;另一方面,海氏的得意弟子之一约纳斯却断言其存在哲学乃是“全部思想史上最大的亵神罪孽”。②在我们看来,这里的争议其实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个层面是海氏是否在自己的著作谈论了超验以及神学问题,另一个层面则是海氏的存在哲学客观上能否与基督教神学相容。对于后一层面的问题我们在此不予置评,本文所关注的是:超验之维是否以及何以进入了海氏的存在之思?
我们把超验一词与神学相并举,很容易让人以为我们把两者混为一谈了。事实上在我们看来,超验一词比神或者神学要宽泛一些:神学所谈论的神或者上帝固属超验之物,但超验之物除了神之外尚有某些其他形态。按照康德的划分,超验之学包括三门学问:理性心理学、先验宇宙论和先验神学,它们分别研究灵魂、世界整体和上帝,神学显然并非超验之学的全部。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之学中,灵魂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显然已经被“悬搁”了,世界整体也不再是所谓超验的实体,而成了此在生存论结构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验问题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恰好与神学成了一回事情。但事实上海德格尔除了谈论诸神、上帝之外,还把神性、神圣等置于更加本源的地位,并且与存在问题深深地契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海氏思想中的超验维度自然就与一般所谓神学有了重要的分别。
不过,贸然把超验问题作为海氏思想中的一个既成事实,显然还是一种过于轻率的做法。这是因为,超验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形而上学的一个传统话题,而海氏赋予自己的思想使命就是克服和超越形而上学,何以竟会重拾这一话题?这岂非在蹈形而上学之覆辙?从哲学史上来看,超验以及神学问题自古希腊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核心内容。众所周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创立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一门影响深远的“理性神学”,在后者的《形而上学》一书中,第十二卷就是专门讨论“神”的问题的。正是由于古希腊哲学与“神学”有着如此的亲缘关系,因此中世纪的神学家如安瑟勒姆、托马斯·阿奎纳等人才将其与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各种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对于形而上学的这一传统,海德格尔自然了如指掌,他并且敏锐地洞察到,在古希腊哲学中存在论与神学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因为“形而上学是以双重方式来表象存在者的存在状态的:一方面是在其最普遍的特性意义上来表象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而另一方面也在最高的、因而神性的存在者意义上来表象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③ 这就是说,存在论所要把握的是存在者整体的普遍性,但它所依据的表象性思维方式必然把这种普遍性把握为最高的存在者即神,这样存在论便必然走向神学。对于形而上学的这一特征,海氏抱着一种彻底的批判态度: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对于存在的遗忘”;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一位必须让人去证明其自身的存在的上帝,最终结果不过是一个说不上有神性的上帝,对这种上帝存在的证明其结果与渎神没有二致。”④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基督教的上帝只能诉诸于启示和信仰,而形而上学所谈论的上帝则只是世界存在的“自因”,“人既不能向这个上帝祷告,也不能向这个上帝献祭。人既不能由于畏惧而跪倒在这个自因面前,也不能在这个上帝面前亦歌亦舞。”⑤ 正是因此,海氏极力主张把哲学与神学明确区分开来,坚决反对在哲学中谈论神学问题。
从上述情况出发,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断言海氏思想中存在着一个神学的维度。然而问题在于,海氏自己又常常做出一些看似矛盾的宣言。他早期在致学生的信中就曾宣称自己是“基督教神学家”,在晚年又坦承“没有这一神学的来源我决不会踏上思想的道路。”⑥ 征之以海氏自己的著作,我们发现他早期的著作的确很少正面谈论神学问题,但在晚期的许多论文和演讲中,却不断地出现神圣、神性、诸神、上帝这样的字眼。那么,这是否标志着海氏晚年抛弃了早期思想的洞见,重新把哲学与神学混为一谈了呢?我们认为断非如此。事实上海氏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他在思想“转向”之后的著作《尼采》中同样宣称“基督信仰与哲学,实在毫不相干”。因此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海氏本来就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当作哲学,或者说在他看来,这乃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思想,因而与神学之间自然就不再鸿沟相隔了。具体地说,形而上学之所以与神学毫不相干,是因为其所采用的乃是表象性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是把上帝当成了一个没有神性的最高存在者。而海氏自己则抛弃了这种思维方式,转而建立起了一种崭新的思想方式,这就是那种对于存在意义的本源性的理解和领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存在意义的把握与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一回事呢?海氏对此断言加以否认:“通过对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学阐释,关于一种向着上帝的可能存在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作否定的决定。但通过对超越的揭示,恰恰赢获了一个关于此在的充分概念;而顾及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就可能追问:此在对上帝的关系在存在学上处于何种情况中。”⑦ 这就是说,对于此在生存论结构的阐释并没有对上帝的存在做出证明或者否定,但却可以为进一步确立此在与上帝的关系打下基础。那么,此在以及存在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海氏对此做了清晰的界定:“唯有神圣者才是神性的本质空间,而神性本身又只允诺诸神和上帝之维度;唯当存在本身首先而且在长期的准备中已经自行澄明,并且在其真理中被经验了的时候,神圣者才得以显露出来。”⑧ 从这段话来看,海氏显然认为此在与上帝不可能直接发生关联,而必须以神圣者和神性作为中介。具体地说,上帝以及诸神都必须以神性为前提,神性又必须以神圣者为前提,而神圣者的显现则又以存在本身的自行澄明为前提,因此,此在必须首先领悟存在的意义,而后才可能依次开启出神圣者、神性、诸神以及上帝的领域。简言之,此在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以对存在意义的领悟为前提的。正是因为这样,海氏的存在之思尽管不能直接同于神学,但却可以为神学以及信仰奠定必要的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以为海氏思想中确乎存在着一个神学之维。当然,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超验的维度,因为它所涉及的不仅是上帝,而且包含神圣者这样的超验之物。
二、超验之物何以成为诗性之源?
现在的问题是,海氏思想中的超验维度与其诗学思想之间有何关联?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一言以蔽之:超验之维在海氏看来乃是世界具有诗意的重要根源。
诗人之为诗,根本上是因为世界上本身先就有诗意存焉。然而诗意又从何而来呢?海氏的说法是:“人类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诗意的’”。⑨ 显然,这个说法来自海氏所钟爱的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氏对这句话做了明确的阐释:“‘诗意地栖居’意思是说: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并且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⑩ 这就是说,诗意的产生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神的在场和物的本质的显现。那么,神如何能够在场,物的本质又如何能够显现出来呢?这就需要弄清楚海氏对于神以及物的本质的看法。事实上,海氏对这两者的思考是相互关联的。何谓物的本质?海氏称之为“物之物性”。在传统思想中,物被看作一般的存在者,是一种被表象的对象,其本质可以通过科学认识来加以把握。然而海氏却认为,“物之物性因素既不在于它是被表象的对象,根本上也不能从对象之对象性的角度来加以把握。”(11) 何以如此?概因为科学恰恰把物变成了某种虚无的东西,从而把物之为物消灭掉了。举例来说,壶本是一物,但在物理科学看来,壶之物性在于它有容纳作用,而它之所以能够容纳其他东西,是因为壶的中间乃是虚空,这样壶的物性恰恰变成了无。而在海氏看来,壶的本质乃在于一种“倾注之赠品”,因为壶能够把倾注入其中的赠品加以承受和保持。具体地说,壶中之赠品——泉水——来自于大地,并上承于天空。在献祭的时节,壶中又可容纳着美酒献给诸神,于是诸神也便在壶中逗留……通过这种容纳作用,天、地、神、人这四方便逗留于壶中:“在倾注之赠品中,各各不同地逗留着终有一死的人和诸神。在倾注之赠品中逗留着大地和天空。在倾注之赠品中,同时逗留着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这四方是共属一体的,本就是统一的。它们先于一切在场者而出现,已经被卷入一个唯一的四重整体中了。”(12) 这就是说,在每一个物中,都逗留着天、地、神、人,并且这四者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这四者的逗留,壶才成其本质为一物。海氏把这个过程称为“物化”。
惟其通过这种物的“物化”过程,世界才具有了诗意。何为“世界”?海氏的说法是:“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我们称之为世界。世界通过世界化而成其本质。”(13) 这里所说的“居有着的影射游戏”,意思是说天、地、神、人四方中的每一方都是通过影射其他三方而居有自己的本质的,之所以称其为游戏,是为了区别于形而上学所说的对象性或表象性活动,因为这种影射活动乃是一种“居有之圆舞”,四方之间的关系不是对象性的,而是柔和、柔顺地“依偎在一起”。正是通过这种影射游戏,神以及物才得以成其本质并现身在场,从而赋予世界以诗意。
世界的诗意必然进一步转化为人类此在生存的诗意。这是因为在海氏看来,人类的生存就是一种“栖居”活动。按照通常的看法,人类的生存和栖居总是充满劳绩,因而也便是缺乏诗意的。然而海氏却秉承荷尔德林的启示,认为人类的栖居恰是充满诗意的。这里的关键显然在于对栖居一词的理解。他通过词源学的考察认为,栖居的本质乃是一种保护:“栖居,即带来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保护。”(14) 那么,何种东西在人的栖居中得到了保护呢?这就是所谓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和保护终有一死者的过程中,栖居发生为对四重整体的四重保护。保护意味着:守护四重整体的本质。”(15) 由此可见,人类生存和栖居的本质内涵,就在于守护四重整体的本质。而这四重整体的本质得以显现的过程也就是世界世界化的过程,既然这世界本身是富有诗意的,那么人类的生存不正是一种对于诗意的守护吗?正是在此意义上,海氏认为人类此在在其根基处便是诗意的。
对于海氏的这种看法,人们自然会提出质疑:既然世界以及人类的生存总是富有诗意的,何以人们仍然常常感到生活缺乏诗意呢?事实上海氏自己不也说到世界需要人的保护、大地需要得到拯救、诸神需要人们的期待吗?这不正说明世界的诗意是需要通过人来赋予甚至“创造”的吗?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人们通常认为诗是由人“创作”出来的,因而诗意也是由人赋予这个世界的。然而在海氏看来,人的创作或者生产活动并不是一种纯粹主动性的活动,而恰是一种“应合”。当然,这种应合也并不是一种纯然被动的姿态,而是一种“返回步伐”,即从形而上学以及科学那种对于物的促逼和统治,从技术对于世界的咄咄逼人的安排或者“座架”活动,返回到对于物的一种“泰然任之”的姿态,只有通过这种姿态和应合,物的本质才能显现和逼近我们,诸神和上帝也才能现身在场。然而人类却久已陷于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结果是使物和诸神的本质都不再对人显现出来,从而使世界和人的生存都失去了诗意。这是因为,物和诸神的本质都只能在一种敞开域中才能对人显现出来,而技术以及形而上学恰恰使这种敞开域被彻底破坏了:“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意见:技术的制造使世界井然有序。其实恰恰是这种井然有序把任何秩序都拉平为制造的千篇一律,从而自始就把一个可能出现秩序和可能从存在而来的承认的领域破坏了。”(16) 如此一来,世界便陷入了一种缺乏诗意的暗夜之中:“这是逃遁了的诸神和正在到来的神的时代。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因为它正处于一个双重的匮乏和双重的不之中:在已逃遁的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来的神之尚未中。”(17)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海氏的诗学思想中,诸神的在场乃是世界具有诗意的重要原因,反之,诸神的离去也必将导致世界之缺乏诗意,超验之维正因此而成为世界的诗性之源。
三、诗人如何道说超验之物?
如果说人类此在在其根基处就是充满诗意的,那么人们理应能够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直接体验和领悟到这种诗意,或者说每个人天生就都已经是诗人,这岂非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诗人了吗?更进一步来说,世界本身便是富有诗意的,我们又何需诗人的创作活动呢?
然而海氏却说,“诗人造成诗意的东西,历史性的人类以这种诗意为基础,就栖居于这种诗意之上。”(18) 似乎又在说世界的诗意是由诗人创造出来的, 这与前面的说法不正自相矛盾吗?这里的关键显然在于“造成”二字。事实上海氏所意指的并不是“创造”,而是一种“命名”,也就是说诗人并不是创造了世界的“诗意”,而是为本已存在的诗意之物命名:“诗人命名着现实之物的诗意基础并凭借其被显示的现实性才把现实之物带回‘本质’。”(19)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海氏在此似乎返回了柏拉图那种机械的“模仿说”之中,因为他明明宣称世界本来就存在着诗意之物,诗人只是为其命名而已。然而切莫小看了这一命名,因为海氏明确指出,诗意之物正是通过这一命名才得以成其本质,也就是说诗意之物与诗人乃处于一种非此不可的关系之中。诗人的命名何以具有这般神奇的力量呢?
答案即在诗人命名的方式之中。名称即是词语,因而命名便是一种语言活动,这又有何神奇之处呢?然而在海氏看来,诗人的语言与常人的语言相去何止千里:“本真的诗从来不只是日常语言的一个高级形式。毋宁说,日常言谈倒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因而被用滥了的诗歌,从那里几乎不再发出某种召唤。”(20) 这就是说,诗人的语言不仅比日常语言更加高级,而且本身就是日常语言的基础,或者说日常语言乃是对于诗歌语言的一种通俗化的滥用,其结果是使语言丧失了原有的命名力量。那么,诗人的语言何以具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命名力量呢?这是因为在海氏看来,诗人的语言本来就不是人所拥有的一种工具,或者说语言并不是一种人的活动,而是语言自己拥有言说的能力:“就其本质而言,语言既不是表达,也不是人的一种活动。语言说。”(21) 这样一种语言观显然十分怪异,因为语言活动总是需要具有某种“主体”,或者说语言总是某种主体表达自身的一种工具,一种以自身为主体的语言还能称作语言吗?即便这种语言的确存在,它和人类又有何关系呢?事实上海氏也并不是说这种语言是没有主体的,而是强调这种主体并不是人而已。那么,诗歌语言的真正主体又是谁呢?这就是诸神以及神圣者:“神圣者赠送词语,并且自身进入这种词语之中。词语乃是神圣者之居有事件。”(22) 也就是说,本真的语言并不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超验的神圣者之赠送。正是因此,在诗中不是人在说,而是语言自己在言说。当然,准确的说法是神圣者以及诸神在言说。
宣称存在着一种神的语言,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典型的玄思,这也正是海氏后期思想为人们所诟病重要原因。一个最直接的诘难就是,这种神秘的玄言存在的证据是什么呢?如果说的确存在着这种玄言的话,那么普通人为何从未听闻过呢?对此海氏的说法是,神的语言是无声的,或者说是一种“寂静之音”:“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而说。”(23) 也就是说,由于神的言说是无声的,因而常人无法分辨出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神的言说又是一种“寂静之大音”(所谓“大音稀声”)这种大音对普通人来说乃是一种无法承受的“雷霆”。那么诗人何以能够“截获”这种语言呢?这是因为诗人善于聆听这种言说,或者说作诗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倾听行为:“作诗意谓:跟随着道说,也即跟随着道说那孤寂之精神向诗人说出的悦耳之声。在成为表达意义上的道说之前,在最漫长的时间内,作诗只不过是倾听。孤寂首先把这种倾听收集到它的悦耳之声中,籍此,这悦耳之声便响彻了它在其中获得回响的那种道说。”(24)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人的命名和言说实际上是一种应合或者回答,表面看来是诗人在为诸神以及神圣者命名,实际上却是诸神在自我命名或者道说。
然而诗人并不因此而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海氏的说法,诗人们其实是“半神”,因为诗人处在诸神和人类之间,只有他们才能截获诸神的道说和暗示,并且将其传递给普通民众:“诗人之道说是对这种暗示的截获,以便把这些暗示进一步暗示给诗人的民众。这种对暗示的截获是一种接受,但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给予:因为诗人在‘最初的标志’中也已经看到完成了的东西,并且勇敢地把这一他所看到的东西置入他的词语中,以便把尚未实现的东西先行道说出来。”(25) 诗人的这种截获和暗示行为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从神的方面来说,这是神得以现身在场并与人类相遭遇的重要前提:“这些诗人们处于人类与诸神之间,对这个敞开的‘之间’来说,诗人们首先必须探索他们的本质从中起源的那个基础。惟在这个敞开域中,诸神与人类才相互遭遇,如果这样一个敞开域被发送给他们的话。”(26)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神的道说只是一种暗示,普通民众无法领会其中的含义,唯赖诗人的道说才使其不至于和人类擦肩而过。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人类需要诸神,诸神实际上也需要终有一死的人;另一方面,对于人类来说,这又是一种创建,也就是说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由诗人通过做诗才得以创建的:“由于诸神原始地受到命名,物之本质得以达乎词语,而物借此才得以闪亮,由于这样一回事发生出来,人之此在才被带入一种固定的关联之中,才被设置到一个基础上。诗人的道说不仅是在自由捐赠意义上的创建,而且同时也是建基意义上的创建,即把人类此在牢固地建立在其基础上。”(27) 表面上看来,认为人类只有通过诗人才获得生存的根基,乃是一种十分荒唐的说法,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人类的生存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然而在海氏看来,这样一种生存活动恰恰是无根基的,因为这种以技术为前提的生产活动恰恰消灭了物之物性,也使诸神不再现身在场。反过来,诗人恰好通过为诸神命名而使诸神和物的本质都得以显现出来,从而使人类获得了生存的根基。因此海氏才说:“诗是一种创建,这种创建通过词语并在词语中实现。”(28)
归结起来,海氏认为诗人之道说超验之物,乃是通过为诸神以及神圣者命名的方式来实现的。通过这一命名,诗人就把诸神的暗示传递给了人类,使得诸神与人类相遇,也因此而使人类的生存获得了根基。据此我们认为,海氏实际上建构起了一种神秘玄奥的超验诗学。
四、超验诗学背后的“两希”传统
把海氏十分玄奥的超验诗学重新置回其赖以形成的思想传统之中,无疑十分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也有利于我们为其做出客观的历史定位。
众所周知,西方思想存在两大传统:古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其中,前者主要提供哲学和科学传统,后者则提供宗教和信仰传统。征之以海氏的超验诗学,最容易分辨出的便是希伯莱的宗教传统。诸如所谓神性、上帝等说法,显然与基督教信仰有着明显的关联;当海氏宣称诗人以语词来创建人类生存之根基的时候,我们无疑听到了《圣经》创世神话的回声;当他把诸神的语言归结为一种“暗示”的时候,也让我们自然地联想到了基督教所说的“启示”;而他所谓“神的语言”与基督教所谈论的“圣言”似乎也一脉相承。正是由于有着这些密切的关联,所以天主教神学家K ·拉纳从海氏的后期思想中引申出“人是圣言的倾听者”这样的神学命题,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29)
然而就此把海氏的诗学归属到中世纪以来的神学美学传统中,却并不是一种恰当的做法。这是因为,海氏并不仅仅谈论诗与上帝的关联,他还谈到了所谓“诸神”,这显然不合乎希伯莱的“一神教”传统。他所说的诗人创建人类的根基,与上帝用语词来创造世界之间也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上帝创世乃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海氏所说的创建则并非创造,而是一种“让……成其本质”,这种“让”乃是一种接纳的姿态,它意味着从形而上学以及技术对于物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返回到早期希腊那种本源性的思想方式之中,惟在这种思想之中,诸神以及物才能够成其本质并现身在场。当然,海氏之所以能够对古希腊思想产生这一洞识,则还是由于胡塞尔现象学思想的启迪。(30) 其次,海氏认为诗人创建了人类生存的根基,并且把诗人称作“半神”,似乎也偏离了希伯莱文化的信仰传统,而与古希腊的审美主义传统有着明显的关联。(31) 对于海氏来说,尽管诗人的主要职责在于为诸神和物命名,但这种命名的目的却不是为了确立人们的宗教信仰,而是为了捕捉世界的诗性。在海氏看来,此所谓“诗性”恰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美:“美乃是以希腊方式被经验的真理,就是对从自身而来的在场者的解蔽,即对自然,对希腊人于其中并且由之而得以生活的那种自然的解蔽。”(32)
那么,西方文化的这两大传统在海氏的超验诗学中是怎样汇集起来的呢?我以为这只有通过对海氏所谓“神圣者”一词的阐释才能予以澄清。在我们看来,这个术语充当了海氏把两大思想传统沟通起来的桥梁。具体地说,“神圣者”一词显然具有浓厚的神学意味,因为它被视作诸神以及上帝具有神性的基础和前提。用海氏的话来说,“‘神圣性’绝不是某个固定的神所秉有的特性。神圣者之为神圣的,并非因为它是神性的;相反的,神之所以是神性的,因为它的方式是‘神圣的’。”(33) 这就是说,神圣者并不是诸神或者上帝的属性,相反,惟其先有神圣者在,诸神以及上帝才具有了神性。从这里可以看出,海氏其实比基督教思得更远,他要为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信仰探询其最初的本源。那么,信仰的本源究竟何在呢?海氏以为就在古希腊早期的思想之中。按照它的说法,“神圣者就是自然之本质。”(34) 这说法在现代人看来殊不可解,因为自然乃是各种存在者之总和,何来神圣之处呢?然而我们须知这样的自然观乃是近代人对于已经“祛魅”(马克斯·韦伯语)了的自然(nature)之认知,而海氏所说的却是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在古希腊人看来,自然(physis)“乃是指出现和涌现,是自行开启,它有所出现同时又回到出现过程中,并因此在一向赋予某个在场者以在场的那个东西中自行锁闭。被思为基本词语的自然,意味着进入敞开域中的涌现,进入那种澄明之照亮,入于这种澄明根本上某物才显现出来,才展示在其轮廓中,才以其‘外观’显示自身,并因此才能作为此物和彼物而在场。”(35) 从这里可以看出,古希腊人所说的自然指的是各种存在者出现和涌现的过程,是其存在得以显现和开启的过程,对于这种现象,海氏以为正是古希腊人所说的“真理”(Althetia)。更进一步来说,自然一词又与古希腊哲学的基本语词“存在”(即古希腊语的系词eimi,又译为“是”、“有”等等)有着词源学上的关联。据海德格尔的考证,该词的词干之一乃是印欧语系的“bh?”,其意思是“起来,起作用,由其自身来站立并停留。这个bh?迄今一直被按照通用的外形的看法……来解释为自然与‘生’。”(36) 这就是说,古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然其实就是存在意义的显现过程,在他们看来,这个显现的过程正是世界上最可惊讶也最为神圣的现象,而对于这个现象的思考和阐释则构成了全部希腊思想的真正源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部形而上学以及存在论哲学都导源于此。
据此我们认为,尽管海氏的超验诗学乃至整个思想都受到了希伯莱宗教传统的启迪和引发,但其思想的真正旨归却是希腊式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实际上是在以古希腊思想来为希伯莱文化奠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谓古希腊思想绝不可等同于通常所谓古希腊哲学,而是海氏从现象学的视野出发,以解释学的方式对早期希腊思想进行阐释的结果,因此海氏曾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更源始地追踪希腊思想,在其本质渊源中洞察希腊思想。这种洞察就其方式而言是希腊的,但就其洞察到的东西而言就不再是希腊的了,绝不是希腊的了。”(37) 由是观之,海氏显然并不是简单地把希伯莱文化嫁接到古希腊文化之中,而是在这两大文化传统的相互牵以之中自创一脉。仅此一点,即可见出海氏思想震古烁今的气度和胸襟。
注释:
① 云格尔:《与上帝相宜的缄默》,林克译,刘小枫选编《生存神学与末世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页。
② 约纳斯:《海德格尔与神学》,孙周兴译,刘小枫选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③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孙周兴译,《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47页。
④ 海德格尔:《尼采》,转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63页。
⑤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译,《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41页。
⑥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1页。
⑦ 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孙周兴译,《路标》,第186页注。
⑧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孙周兴译,《路标》,第399页。
⑨⑩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6页。
(11)(12)(13) 海德格尔:《物》,孙周兴译,《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67、1173、1180页。
(14)(15) 海德格尔:《筑·居·思》,孙周兴译,《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92、1194页。
(16)(17)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300、316页。
(18) 海德格尔:《追忆》,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27页。
(19) 海德格尔:《追忆》,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09页。
(20)(21) 海德格尔:《语言》,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20、8页。
(22) 海德格尔:《如当节日的时候》,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90—91页。
(23) 海德格尔:《语言》,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21页。
(24) 海德格尔:《诗歌中的语言》,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59页。
(25)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53页。
(26)(27)(28) 海德格尔:《追忆》,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78、45、44页。
(29) 参看K·拉纳:《圣言的倾听者》,朱雁冰译,三联书店,1994年。
(30) 限于篇幅,本文对此无法展开论述,可参看拙著《现象学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一书第一章第三节。
(31) 犹太民族缺乏艺术的爱好与天分,因而希伯莱文化也缺少审美主义的元素。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的一生》(粱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对此多有提及,可参看。
(32)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大地和天空》,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97页。
(33)(34) 海德格尔:《如当节日的时候》,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69页。
(35) 海德格尔:《如当节日的时候》,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65页。
(36)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1页。
(37) 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