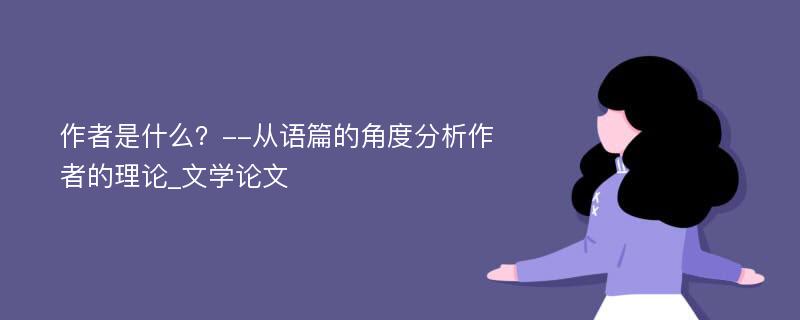
作者是什么——从话语角度浅析作者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话语论文,角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8-8717(2008)06-0048-03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一、引文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人们常常把作品和作者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因为,人们认为既然文学作品来自于作者的创作,作品的意义由作者赋予,那么,如果想要充分地理解一个文本并评价它的内容,作品的意义就应从作者那里得到解释。于是,批评家们把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作者本人的研究上,作家创作心理的挖掘成了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作者意图成为阐释作品意义的根据,传记批评成为最流行的批评方法。
可是到了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尤其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意义产生于能指符号之间的差异的理论而导向的语言决定论使得20世纪的哲学开始了一场全面的语言学转向,主体(包括写作主体)成为它的根本矛盾,“语言学摧毁了一切主体——文学研究的主体,意识哲学的超验主体,政治理论、精神分析或人类的主体……”。[1]在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作者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极大冲击。文学家和批评家们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以下问题:作者是什么?作者的功能何在?
二、“作者是什么”问题的提出
关于作者的内涵和功能的探讨很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法国的著名学者福柯发表《作者是什么》一文。福柯于1969年向“法兰西哲学学会”递交一份名为《作者是什么》的报告。他开宗明义地说他要探讨所谓的“作者”问题,“直到今日,就其在话语中的一般功能和尤其从我自己的作品来看,作者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2]
在这篇文章中,福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作者进行分析并提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一种文化中作者是怎样被个人化的;当人们在研究文本的正确性和归属的时候,人们应给予作者何种地位;为什么人们抛开文本不读,反而锲而不舍地追问作者的生平,把理解作者生平当成阅读文本和进行文学批判的关键……。他认为,就文本和作者的微妙的关系而言,作者处于文本之外,而且先于文本而存在。
福柯首先提出当代文本的特点。他认为当AI写作作的内在准则是写作不再是个人“表达”,写作不再指向自身,不再局限于其内在。写作现身于作品的外部,这使写作变成了符号的相互作用,受到能指的本质所支配。因此,写作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言词自身在自主地行动和表达,写作是在设定一个空间,人在这个空间中不断地被消解:“写作不是把主体钳入语言,而是创造出不断使写作主体消失的空间。”[2]于是,人在写作中退场了,言语活动取代了从事言语活动实践的人。这里,福柯引出了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提出的观点。
三、作者之死
罗兰·巴特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也是自60年代以来西方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巴特的《作者之死》一文写于1968年。在这篇文章中,他激烈地攻击了“作者至上”的文学观。他认为,写作不是一种人格行为,而是言语活动的表演和嬉戏,作者被吞没于言语的自理之中。
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言语的自我运行、无需他人驾驭的语言学性质早就决定了作者仅是一个只做誊写动作的现代抄写者,语言陈述的过程可以在不需要主体来充实的情况下出色地自行运转。这样,作者在写作中的重要位置就被言语活动本身的消耗而消解了。“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3]至此,巴特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作者观,成功地宣判了作者的死刑。
作者死了,在文本被构成和被阅读的各个层次消失了。于是,长久以来与作者有着“父子关系”的现代文本面临着重大变革。没有了作者,写作不再是一种记录确认再现和描绘的结果,它成了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的无起因的“性能表现”。文本失去了源头,回复到拉丁文里“文本”的本意:“由多种写作相互组合,相互竞争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原始写作的多维空间的,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3]因此,巴特认为,我们所谓的“作者写作创造文本”的事实不过是一种假象:“生活从来就只是抄袭书本,而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织物,是一种迷惘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3]
四、福柯的作者观
福柯认为文本和写作抹杀了当代作者的个性,因为作者、文本和读者间的关系已被语言和主体间的关系所替换,所以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作家或作者,不过是语言的功能本身;作者仅代表着文本话语的统一性和连贯性,而并非写作文本的个人。既然人的主体本身就是语言的构成物,今日的写作作为一种符号的交互作用,不受制于“所指”的内容,而受制于“能指”的本质,因此写作成为了不断测试、超越和翻转既有规则的游戏,其主要目的在创造一个可以让写作主体不断消失的空间。所以,今日的写作和牺牲相关,它是自愿性地自我抹消,自我不需要再现在书本之中,因为写作就发生在书写者的日常存在中。书写者被其自身的写作所抹消,作者在写作中消失了,就是福柯对“作者之死”所持的观点。
但是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福柯指出“作者已死”的这个概念所产生的后果其实仍然并没有被好好地深入探讨。他甚至认为这些概念在事实上被用来阻遏了作者概念的真正改变。为此,他举了两种命题来进行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作品”的命题。他认为人们虽然避开了书写者的个体性并避免将书写者视作“作者”,但他们却忽略“作品”的性质以及“作品”这个字其实就代表了一种整体统一的概念,因此这个字的背后其实仍隐含有“作者”的概念。第二个例子是“书写”的概念。福柯认为它虽然与写作行为无关,也与表示作者的意义无关,但“书写”把作者经验性的特征转化成为先验的匿名作者,所以“书写”的概念透过对于“先验”的维护而保留了作者的特权。福柯认为这两种观点其实都并未能够真正撼动“作者”这个概念。
福柯提出我们应该探讨作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在福柯看来,作者的名字不是一般的专有名称,而是一种话语功能。拥有作者名字的话语不是让人们用来直接消费或遗忘,而是让其作品在社会地位和接受方式上受到文化的制约,是把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从话语的内部引向外部。作者的名字存在于作品之外,又与作品形影相随,它与其他话语区别开来,显示它们的存在方式及其特征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化里,作者的名字是一个可变物,它只是伴随某些文本以排除其他文本:一封保密信件可以有其签署者,但它没有作者;一个合同可以有签名,但也没有作者;同样,贴在墙上的告示可以有一个写它的人,但这个人可以不是作者。在这种意义上,作者的作用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2]作者的名字不仅具有指出某个特定人物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更近似于一种“种类的描写”。作者的功能是要赋予社会中某些话语其存在、流通以及运作某种特征,因此作者之名的出现,是为了作为一种分类的工具。而后福柯更在将作者视为话语的一种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作者的功能”。
五、作者的功能
对于作者作为话语功能的问题,福柯主要从四个方面作了阐释。
第一,作者的功能是法律和惯例体系的产物,这一体系限制、决定并且明确规定了话语的范围。话语因而是被占有的客体,其合法的编撰多年前已经完成。把作者看作一种社会规范而提出的惩罚功能是作者功能的首要目的。因为在从前,只有当作者成为惩罚的对象,或其话语被视为是触犯刑律时,作者、作品或话语才会冠以作者的名称,人们才会去认定该言论或书籍的作者。话语最初以一种充满危险的姿态游走于神圣和世俗、合法和非法、虔诚和亵渎之间,所以当时的作者冒着极大的风险。但当所有权的体系以及著作权的规则建立之后,写作行为内在的逾越特性反而成为文学的强大驱动力。
第二,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曾经有一度“文学”的文本并不需要有作者就可以流通。福柯以“文学”和“科学”两类文本为例指出,古代的文学作品,比如小说,民间故事、史诗等,至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承认并广为传播,根本无须探究它们的作者是谁。而在中世纪,科学的文本,诸如天文、医学、地理等著作,则唯有指出作者的名字,方才显得可信度(因为担心妖言惑众)。而17、18世纪以来,科学的知识既然得到证实,其文本有无作者就变得无关紧要,科学文本不必靠作者的名字,科学话语可以单凭内容而被人接受。而文学话语却必须说明它们的作者,写作时间和其他的相关背景。即便有匿名的文本传下,读者也会想尽办法来考证出它的作者。由此可见,作者在话语中的功能,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正好颠倒过来。作者功能影响话语的方式随时代和文化形态的不同而改变。
第三,作者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单纯在话语中探究作为个人的作者来源,事实上,它是一种复杂的运动,建构出我们称之为“作者”的一种特定的理论存在,如批评家寻找作者的深层动机、独创性等的努力,其目的是为了建构出一个我们称之为“作者”的理性统一体。
第四,作者的功能因而并不是把话语视为被动的静止的材料,以从中建构一个真实的个体形象。因为文本总是含有很多指向作者的符号,它们是个人的名词、动词以及时间、地点副词的各种变化形式,对于有作者功能的文本和无作者功能的文本分别发生不同的意义。如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可以既不指实际上的写作者,又不指虚构的叙述者,相反它代表一个第二自我,这个自我与作者的相似关系从来就不是固定的,即使在同一本书中也是如此。作者的功能因而是产生并存在于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裂缝当中,是在两者的距离之间运作。这不但适合文学领域,同样也适用于绘画、音乐、科技等其他领域。
福柯接着将作者的意义扩大,他认为一个理论、传统或学科也可以有作者,他把这种作者称为占有“超话语”地位的作者。
荷马、亚里斯多德毫无疑问地扮演着这种角色,最早的数学家和希波拉克底传统的创始人也是如此。尤其在19世纪后,欧洲更出现了一种新的占据超话语地位的作者——“话语实践的发起者”——这些人不但创造了自己的作品,而且也创造了其他文本形成的可能性及规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佛洛伊德和马克思,他们不但创造出某些可供后世文本采用的相似性,也创造出差异性,他们清空出一片空间以引进与其自身相异的要素,然而这些要素仍然是在他们所发起的话语领域中。在这些发起者的作品中不会有“错误的言谈”,所以他们的作品并不是置于一种科学的关系中,但又因为发起的行动必然有其自身的扭曲,因此这种话语实践者便必须不断“回归起源”以解决构成上的疏忽,而且此种回归会转变话语实践,并会在原作者及中介作者之间建立一种有别于一般文本与直接作者之间的关系。
六、小结
较之传统的作者中心论以及当代的作者死亡论,福柯从话语的角度来思考作者的问题,把作者看作话语的功能。在他看来,话语脱离说话的主体,从而消除了自由创作的客体,因此,被视为主体的作者其实并不是话语的优先起源,尽管他作为创作者的角色被剥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消失,在话语秩序中,他依然占据一个功能性的位置,在文学活动中,他有着特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