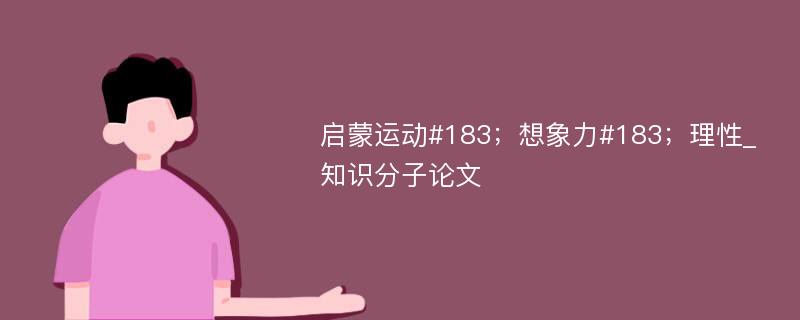
启蒙#183;想象#183;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6)03-0054-05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源自西方的多元而复杂的概念,它涵盖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不同领域含义不尽相同。在西方有关现代性概念的诸多解说中,吉登斯、哈贝马斯、福柯等人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吉登斯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社会或工业化世界,包括民族国家、民主等一系列制度性建构“意指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他认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1]22“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1]16哈贝马斯从哲学角度出发,把现代性阐释为一套源自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指出现代性乃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2]福柯则认为,现代性“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有一点像希腊人叫作气质的东西”。[3]可见,吉登斯从制度层面上来阐释现代性,突出强调现代社会行为制度与模式的建构,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的建构,福柯的作为“一种态度”的现代性实乃一种对时代进行理性批判的精神品格。尽管三位思想家关于现代性的解说各不相同,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现代性的内涵包含着人的理性精神、思想感觉方式、新社会制度的建构等。延安时期文艺理论通过强调文艺对大众的思想启蒙、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及对艺术家自由主义浪漫遐想的理性规约,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诉求。 一、劳苦大众走向现代的思想启蒙 倘若追溯西方现代性的缘起,启蒙运动功不可没。可以说,恰恰是启蒙精神催生了西方的现代性。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旨在用理性来启发人们为中世纪宗教迷信所蒙蔽的头脑,用科学知识来照亮人们的思想,消除神话、幻想,使人摆脱愚昧、蒙蔽状态,达到思想与政治上的自主性。所以,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对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摆脱。”[4]延安时期文艺理论主张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实现对大众自由、民主、平等、反压迫的现代思想意识的启蒙。 首先,强调文艺对劳苦大众的启蒙教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民族革命浪潮高涨。为发动劳苦大众投身革命,取得民族救亡革命的胜利,启蒙成为抗战的首要任务。一大批具有现代性意识的知识分子怀揣革命理想,不畏艰难险阻奔赴延安,加入民族救亡的行列。然而,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经济状况的落后及农村教育的缺失,民众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1%。”[5]民众思想意识极其落后、迷信“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6]1011面对如此情形,理论家们主张对不识字、无文化的工农大众进行一次“普遍的启蒙运动”,解放他们为封建迷信思想所蒙蔽的头脑,唤醒他们的民族自觉性、主体性,让他们“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6]1011提高他们斗争的热情和胜利信心,以取得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 为了民族救亡,文艺理论突出强调文艺启蒙功效。理论家们指出,文艺的作用“在于它能把活的事实具体地摆了出来,因此能够教育和号召全国的人,起来为抗战努力工作。”[7]601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不是要‘束之高阁’的东西,它是社会的、民族的”,“要有推动和变革现实的力量”。[7]602他们甚至认为“艺术是发动人民、团结人民,激发他们的斗争热情,锻炼他们的阶级意识,促成巨大的行动,去完成与获得人生最完美的一种成果……除此之外,艺术不为别的。”[8]显然,文艺被理论家当作了启蒙大众现代思想、激发民族意识与斗志的东西,是实现民族救亡、求得民族解放的有效手段。但由于民众文化水平的低下,文艺需要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呈现出来,方可实现启蒙作用。于是,文艺理论中关于文艺民间形式的运用与文艺大众化的呼声不断,产生了潘梓年《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林默涵的《略论文艺大众化》、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严辰的《关于诗歌大众化》等一系列文艺理论文章,主张艺术家根据大众的需要和接受程度去创造能“教育群众的文艺形式,使文艺和群众真正的结合起来。”[9]758以大众化的文艺来化大众,激发他们的现代意识。 其次,主张建构符合劳苦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美学追求。文艺大众化的发展迫使延安文艺的美学追求发生转变,文艺理论建构起一种以劳苦大众审美趣味为旨归的艺术美学追求。延安时期,因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城市,有很高的学识素养“写文章、或画图画、或演戏剧、或制歌曲,都自然而然会有城市风味、城市情调,甚至是外国风味、外国情调”这样的风味、情调与“周围农村(而且是经过了革命的农村)的环境格格不入”,[10]自然不会为民众所接受。而文艺要启蒙大众,必须要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因此,理论家们主张,要摒弃知识分子那种吟唱优雅、闲适诗意生活的艺术,摒弃那种纤细、柔弱的病态美。那些认为“大雪天出去散步,风吹的越猛越好,真有诗意”[8]的艺术美学追求在抗战语境中是不合时宜的,是不会引发民众共鸣的。“一切随着生长病和由于生活空虚而来的字句上的花饰都该在我们摒弃之列。”[11]艺术家应该关注劳苦大众的生活,描绘大众及士兵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从劳苦大众身上发掘美。“绝不能再认为女人的细腰为美,手指的纤细为美,”因为“这种美是病态的,是有钱人吃饱了饭没有事闲出来的臭美。真正的美应该是为真理、自由,为劳动的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力,创造的力,真正能够担负工作的健康的劳动者的躯体,和坚强的战士。”[8]可以说,抗战的历史现实需要知识分子放弃闲适雅致的艺术追求,赞美健康而强壮的体魄,歌颂坚强不屈的战士及他们不畏艰难坚持战斗的精神,以符合劳苦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来唤醒大众的主体性与现代意识,求得民族革命的胜利。 第三,提倡劳苦大众基于生活经验的文艺批评。延安时期,启蒙对文艺大众化的要求迫使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融入大众,向大众学习。艺术家与大众的界限被打破,大众获得了与理论家平等的评论文艺作品的话语权,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评点艺术家的作品,提出建议。如表现武装保卫耕种的《劳武合作》,有老乡针对“几个农民扛着锄头在前面走,一个民兵扛枪在后面”的画面,指出“后面的民兵也应拿把橛头,否则,前面的人好像被后面扛枪的人压迫着去生产的,而且没有敌人时还可一起翻地。”[12]868看似可笑的挑剔,实则符合情理。再如,一个老太婆指出《慰问伤兵战士的水墨画》的不合情理之处“战士打敌人负了伤,脸上发青是对的,但那来慰问的人的脸不应也是青青的,应该是红红的健康的颜色。嘴边上带点担忧的意思就够了。”[12]868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胡一川的木刻《军民合作》,许多美术家都认为是精品,但熟悉农村生活的老农却毫不客气地指出“驴儿的胸靽画得太紧了,这样驴儿会勒杀,哪还能驮子弹箱呢!松一些,弯下面一点就成了”,“赶驴的人要站在右手边,你却把人儿放左边了,这样牲口便不好牵了。”彦涵的《春耕》,老农认为耕牛少了一个木架,没有它,不能犁田,当彦涵问及该如何改时,老农沉思片刻道:“那边不是一座屋吗?……画上的远景是山脚下一个农家,画上的人招招手,口里哴哴,让家里把木架送来好了!”[13]这种基于劳苦大众自己生活经验对艺术作品的批评被文艺理论家加以肯定与提倡,认为可以纠正那些“不注意内容,只从形式或技巧上欣赏作品的旧观点。”[12]869文艺理论提倡民众对艺术的批评,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民主思想,劳苦大众被当作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虽然这些批评缺乏理论深度,但因为有丰富生活经验的积淀,从表现生活的角度来看,充满情趣,符合生活与艺术本真,值得借鉴。 二、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建构 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是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核心内容之一。美国学者安德森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4]6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生来如此”的历史宿命感,并“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从而在心中诱发出“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14]19延安时期文艺理论蕴含着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首先,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承载了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自由平等、民主富裕的想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在民族救亡激情的推动下,颇具现代性意识的知识分子将革命胜利后的民族国家想象为自由平等、独立富强的现代化民主国家。他们在对劳苦大众进行启蒙时声称,要彻底颠覆现存的“吃人”的传统秩序,打土豪、斗地主,建构一个无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平民世界”。文艺理论为配合抗战的胜利,以理论叙述的方式建构了自由平等、民主富强的现代化“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理论家指出,未来的新中国是“民主自由的乐土,是抗日的各阶级均能安居乐业,享受自由民主的幸福”[15]的国家,因此,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就是“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抗战建国)”。[16]显然,贫穷落后不是民族革命的目的,未来的民族国家是工业发达、富裕的现代化国家。“我们不能老是用毛驴运输。我们要火车、汽车和工厂,我们要逐步地实现工业化。伟大的事业在等着我们。”[17这逐步实现工业化的“伟大事业”,将要到来的自由民主、安居乐业、平等幸福的“新时代”饱含文艺理论家对全新中国的想象,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劳苦大众前仆后继、甘愿做逐日的夸父,为未来全新的民族国家去战斗,从容赴死。 其次,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使得知识分子把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关联在一起。在民族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语境和建构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中,个体的命运、情感被排除在文本叙事之外,几乎所有的叙述都成为了饱含民族革命的寓言,诚如詹明信所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8]这种寓言式的个人叙事折射出的是建构民族国家宏大的理想。譬如,冼星海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应当以工作为前提,在这大时代里我们要把一些自己所能做的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我们是渺小的,一切伟大的事业不是依靠个人成就,而是集合全体的力量而得成功。个人光荣和成功是暂时的,是虚伪的。真正成功和光荣是全人类的”。[19]可见,与民族的、国家的命运、劳苦大众的命运相比,知识分子个体命运、情感世界是渺小的、无意义的。因此,文艺要用“新现实主义”描写“今天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大众,甚至是明天建设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大众”,[20]而不是抒写个体的命运与爱恨情仇,因为,“在未来的新社会里,及在今天的新环境里,已经完全是集体主义了,只有集体才有力量,只有集体才能发展,非个人时代可代替。在诗歌上发现个人的东西,早已不再为人感到兴趣,从天花板寻找灵感,向醇酒妇人追求刺激的作品,早就被人唾弃,早就没落了。只有投身在大时代里,和革命的大众站在一起,歌唱大众的东西,才被大众所欢迎。”[21]可见,在抗战的历史语境中,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相比是不足挂齿的,企图剥离个人与民族国家的想法是错误的,脱离了民族国家与大众的个人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文艺要扬弃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与生活琐事,描写努力建设自由幸福新中国的劳苦大众。 第三,文艺理论中“新文艺”、“新文字”、“新中国”等一系列全“新”的字眼突显出知识分子强烈的同旧时代决裂的决心和对新时代、新中国的想象与向往。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充斥着全新时代的想象,理论叙述全都打上了“新”的烙印。抗战的文艺是“新文艺”,“新文艺”要使用“新文字”,要运用“新现实主义”来描写“新中国”的“新形象”,去完成时代赋予的“新任务”。“新文艺”被看成“是促成‘建国必成’的重要的条件之一,特别为奠定新中国‘文艺复兴’的基石。”[22]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新文字更加普遍实行起来的时候”,旧的形式“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被扬弃”,蜕变成“另一种新的东西”。[21]因此“要创造新的形式,如果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新的意识、思想、新的社会、新的人、新的活动的话。”[24]673这诸多“新”的表述承载着知识分子与罪恶的“旧社会”,愚昧的“旧思想”,过时的“旧内容”、“旧形式”等旧对象彻底决裂的决心和对全新时代的想象。在建构全新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与美丽梦想的文艺理论指导下,大量的文艺作品以践行理论的方式传达出共同的现代意识。《兄妹开荒》、《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逼上梁山》、《吕梁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等一系列文艺作品通过反抗压迫、追求平等、自由的主题承载着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使大众形成广泛的“认同感”,即平等、自由只有在新时代才能成为现实,从而生发出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意识,为民族独立解放、民族国家建构而献身。因此,可以说,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在“新文艺”、“新文字”的理论诉求中承载的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任。 三、自由主义文艺创作的理性规约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启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与大众文化水平、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彼此之间的隔膜日益突显出来。知识分子“感觉自己是文化人,自己从事的文化工作远高于别的工作。”[25]对老百姓不屑一顾。以鲁艺为例,有的知识分子整整四年“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与农民毗邻而居,但却“老死不相往来”。[26]知识分子“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大艺术家”,“彼此高谈阔论,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阔天空”。他们眼里的农民“没有文化,啥也不懂……身上只有虱子”。[27]于是,鲁艺的知识分子自顾自地“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5年以前,或10年以前的爱情。”[27]百姓则戏称鲁艺“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指练声),美术系不知画啥。”[28]彼此的隔膜可见一斑。这隔膜固然有民众文化水平低下的原因,但与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不无关系。 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不仅导致了与民众的隔膜,也“导致了文艺领域自由主义的盛行”,部分知识分子“拒绝任何的批评,避免集体的行动,没有明确的目标,时而这样、时而那样。”[29]甚至认为文艺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红莲、白莲、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30]这种严重脱离抗战历史语境的关于文艺自由主义的浪漫遐想与抗战所要求的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驰。面对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的浪漫遐想,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步骤地实施了整风运动,对艺术家自由主义的浪漫遐想进行适时引导与理性规约,文艺理论亦以积极、理性的姿态向艺术家自由主义浪漫遐想发出批评。 首先,文艺理论通过对严重脱离抗战现实与大众的欧化文艺的批评有意识地规约文艺创作。针对抗战初期文艺创作中严重“欧化”的倾向,理论家指出,“作家太纠缠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太沉溺于外国作品的世界了。他接触的老百姓太少了,看自己的中国看得太少了。”[31]626导致文学艺术“偏向于向外国的文艺里去学习”,这虽然是“把高级发展了的技术介绍到中国来了”,[32]但也因此脱离了历史现实语境,远离了中国民众。抗战的历史现实要求文艺“要克服那些远离中国大众的、不适当的‘欧化’”。[33]文艺发展的实践表明,“欧化”的自由主义的文艺创作是严重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以短裙舞艳的装束表演抗战舞蹈,将美国小丑的姿态赋予游击队员,这不但不能为群众所理解、所接受,即就艺术上而论也是失败的。”[34]处于抗战中的中国,民众文化水平低下,艺术接受水平局限于民族民间文艺形式,牵强地仿效欧美无益于启蒙大众的抗战现实。因此,文艺创作必须防止和反对“一步登天的‘左倾’空谈”与“慑服于困难而裹足不前的右的倾向”,要么尽唱高调,无益于实际,要么“陶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清高地’坚持自己的所谓‘艺术性’”[9]763因为,在抗战压倒一切的时代,要实事求是地“根据革命实践和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认识问题。”绝不能“凭知识分子脑子里的蓝图来设想问题”。[9]757-758文艺理论家对不切实际的“欧化”文艺的批评,有效规约了文艺创作。 其次,对艺术家轻视民众与民间艺术创作态度的理性规约。延安时期,文艺为谁服务,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不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明确的规约,《讲话》前后的其他文艺理论文本对文艺创作亦有明确的要求。在对不合时宜的“欧化”文艺进行理性规约的同时,文艺理论对艺术家轻视民间艺术与民众的创作态度发出了告诫。“我们决不能一听到‘民间的’这个名词,便存一种轻视的心思,偶然去弄一弄这类的形式时,便觉得是自贬身价,降格低就,甚至觉得是文艺的倒退而觉痛苦。”而是要“采取一场严肃的态度去研究民间形式的诗歌,去向他们学习。”[24]672-673艺术家不但不能轻视民众与民间艺术,而要甘当小学生,向广大民众学习,学习他们的生活、思想以及言谈。向丰富的民间文艺学习,“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31]621-622这才是抗战时期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有的创作态度。在全民抗战的历史时刻,文学家不应拘泥于自己知识分子狭小的圈子,缠绵于春花秋月之中,因为“时代规定了我们今天作品原则的标帜。违反这个原则的作品”是不真实的。“今天的春花是在疮痍满目中,今天的秋月是在照着中国人民受日本强盗的残酷压迫。”[35]266-267因此,文艺要“写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怎样英勇地斗争,怎样为民族的利益流最后一滴血,写我们全民族的伟大的抗敌运动。”[35]266即文艺要立足抗战现实,表现中华民族英雄的壮烈史实,激发大众民族国家认同感,取得民族独立。正如艾青所说“延安不是不需要批评”,而是“必须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抗日的、革命的立场上,却不是站在与他们对立的立场上”。[36]通过理论对文艺创作的理性规约,艺术家才在理论上、实际上认识到了解大众生活习惯、思想情感的重要性,认识到抗战历史语境中文艺反映大众生活及利用民间文艺形式的重要性,从脱离现实的自由主义浪漫遐想中摆脱开来,立足抗战现实,融入大众,创造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促进了民族民间文艺形式的发展。 总之,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在对抗战历史现实的深情体认下,向民族民间文艺形式、文艺大众化发出了深情呼唤。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性追求中,蕴涵着启蒙大众、建构民族国家、促进民族新文艺发展的现代性旨归,不仅为劳苦大众走向现代提供了可能,对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认同亦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