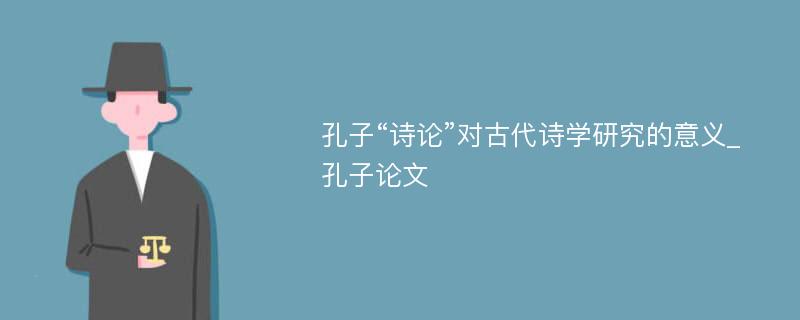
孔子“诗论”对古代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诗学论文,重要意义论文,古代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对古代诗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诗论》的出土填补了中国诗学史最重要的一环。以前我们只能从《论语》等典籍了解诸子诗学的一鳞半爪,现在读到《诗论》,才知道战国诗学达到的实际水平。正是因为有了《诗论》,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中国诗学的发展脉络,从而可以将汉以及汉代以前的中国诗学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商代以前。是中国诗歌以及诗学的起源及形成阶段,以《虞书》“诗言志”为代表。二、商周。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期,此时的诗学以采诗、用诗、编《诗》为特征。三、战国。这时《诗》已式微,然而此时在诗学上则达到了最高水平,以《诗论》为代表。四、汉代。诗学大致以《诗序》、毛传、郑笺为代表。
有原始诗歌而后有“诗言志”的表述,有商周诗之盛而后有《诗论》的理论阐发。汉以后则是《诗》作为经学的解释阶段,于《诗》之本体训诂有成就,于诗学之阐释则因《诗论》的缺失而极为艰难。
虽说商代以前的诗歌还比较原始,但《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似乎显得中国的诗学有些早熟。此时的“诗”还不一定就是后世的诗,《诗谱序》疏云:“《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然此“诗”毕竟与《诗》有别。不过“诗言志”作为中国诗歌“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则是十分确实的。
商代诗歌“不风不雅”(《诗谱序》),一是因为当时即令有风有雅,恐不为统治者认可;二是朝代更替,诗有缺佚。《国语·鲁语下》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今《商颂》仅存五篇。箕子尝作《麦秀之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与《风》相类。周代诗歌创作最为兴盛,于诗学尤可述者有二,一为采诗以观民风,二为贵族应酬之赋诗。
春秋末至战国已无《诗》的创作。《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班固《两都赋序》:“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正是因为《诗》已成为历史,于是有孔子编《诗》,有孔门弟子述先师之说而成《诗论》。
其次,《诗论》的最大特点是以儒家思想解《诗》。对此我们可以藉《诗论》中的思想用语作一简要说明。《诗论》中的思想用语可以分为三类,一、以性、情为中心,有性、情爱、爱、爱妇、悦、喜、美与恶、好与恶等;二、以礼为中心,有本、反其本、情与志、情与礼、情与独、情与善、敬与礼、贵与贱等;三、以天命、知为中心,有命、天命、受命、命与德、时、逢时、成与信、信、知、知恒、知礼、知人、知行、知难、知言、忧与思、用心、始与终等。所有这些用语全都见于郭店楚简,当然也是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常用语。仅就情爱、爱妇而言,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从而儒家“仁”的思想可以凭借《扬之水》《采葛》等诗得到更为形象生动的理解。
《诗论》解诗构思严密。例如评《关雎》等七首诗,所包含的思想模式就与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有关。《关雎》之“改”与“礼”,《汉广》之“知”,《鹊巢》之“归”与“离”,《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与“独”,很明显是始之于“性”与“礼”,而终之以“情”与“独”,“时”、“知”、“归”、“保”、“思”则在礼与独的范畴之中。《诗论》解诗,深刻透彻而又奔放洒脱,充满了圣知的光照,体现了形象与思辨的完美结合,前无古人,后继者亦难以望其项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说,《诗论》是真正的诗的哲学。
由春秋末至战国,是《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最初阐释阶段。孔门先师与七十子阐释《经典》,大都是为了依据经典完成各自思想的构建。孔子修《春秋》,微言大义在其中,已使《春秋》超越了史官记史的王官史学。《易传》的产生,则使《易》从此具有卜筮与哲学的双重意义。《礼记》乃诸子所述之“礼”,瓶子是先王留下的,里面的酒则是缙绅先生新酿的。《乐记》述乐而又释之以礼,乐与礼一内一外,从此音乐之“乐”与思想之“乐”血肉相依,不可分离。至于《书》,春秋以降,天子也好,诸侯也好,无新作之礼,亦无新创之例。若视诸子著述为《书》之变异,有如汉儒谓孔子学说为素王法,要当不诬。《诗论》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思想解诗的特征,与当时儒家解经的风气是完全吻合的。
《诗论》的这一特点,既区别于王官之采诗用诗,亦区别于《诗序》。
再次,《诗论》为《诗序》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机。《诗序》究竟产生于何时,是诗学研究的难题。在《诗论》之前是否有更早的《诗序》?其一、官学背景可以排除学人自作“诗序”的可能。其二、如果王官学作有《诗序》,那就只能理解为由国家颁布的有关《诗》的定评。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春秋赋诗断章,对诗的理解是可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看来并不受某种定评的限制。王官学定乐歌是合情合理的,定《诗序》则很难给予合理的解释。“诗序”的流传与《诗序》的编定不是一回事,看来有必要把这二者区别开。窃以为“诗序”最初是口传的,诗歌的流传客观上会将某些诗的作诗缘起与本事同时传下来。《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歌曰”以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候人歌》之序。若《候人歌》被孔子编进《诗》三百,那么这一段文字将成为《诗序》之所本。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这类口传“诗序”在孔子的时代尚未成编,七十子至孟、荀,是否有人将其编之成册,无从实证。至汉代则实实在在地将口传“诗序”编定,并为毛、郑解《诗》之所本。
《诗论》与《诗序》的传承应该看作是并列的两条线,而不宜理解为一条线的先后相继关系。《诗序》尤其是《诗大序》纵横捭阖,超凡脱俗,其立意必有受之于先师者。然而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体例看,《诗序》均与《诗论》有别。是作《诗序》者受之于子夏而有新创欤?拟或“儒分为八”而各得“性与天道”之精髓欤?是有待于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