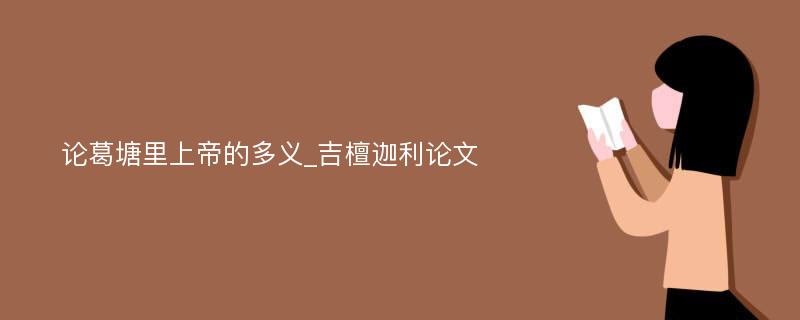
论《吉檀迦利》中“神”的多义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义性论文,吉檀迦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印度传统的“梵我同一”思想并不是《吉檀迦利》中“神”的内涵的全部。诗集中的“神”作为一种诗歌的意象,更倾向为一个象征或称谓,它的实质是美与创造,真理与理想,抑或观照世界的自由心灵。
关键词 观照/象征/意象/自由
中图法分类号 Ⅰ106.2
英译诗集《吉檀迦利》(以下简称《吉》)使泰戈尔蜚声欧洲,并获得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西方读者将诗人看作宗教虔诚诗人和神秘主义哲学家,由于《吉》的影响太强烈了,以致于把他的爱情诗集《园丁集》也看作神秘主义的宗教颂歌。
为了解除这一误会,著名诗人庞德不得不呼吁读者“自由地和完整地读这些诗歌中的每一首诗,忘掉对诗歌所含意思的追究”。〔1〕
在印度当代著名评论家、自称是泰戈尔和泰戈尔所创造的文化最为熟悉的那些人之一的圣·芨多教授的专著《泰戈尔评传》中,他也指出把泰戈尔想象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秘宗教诗人是一种偏见,因为没有一个诗人比他更热爱大地、热爱生活。圣·芨多教授是这样评价《吉》这本诗集的:“这些散文诗所描写的无非是人对神的崇拜这些非常古老的题材。这些观念是很简单的,这些形象也是很熟悉的,几乎已经到了老一套的地步,但是这部诗集却仍能妙语连珠,处处充满着奇思妙想……这种质朴是通过各种思想感情和形象的迷宫般的盘根交错才达到的。”〔2〕这一评价对《吉》艺术性的分析是中肯的, 对它思想上的分析则过于简单。笔者认为,在《吉》中,泰戈尔所渴求与交流的神并不仅仅是若干世纪来在印度一直为人们熟知的那个形象,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揭示出它的全部意义,有助于我们对泰戈尔和他的诗做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吉檀迦利》的创作背景
泰戈尔一生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20世纪初他退出群众反英运动止),可以他的故事诗为代表。《被俘的英雄》是其中的名篇,诗歌歌颂了反对莫卧儿帝国统治的锡克族英雄,塑造了般达的高大形象。这时期的诗不仅指出了“祖国呵/它现在风雨飘摇,软弱无力/它任人宰割,破碎支离”的现状,而且呼吁“尊贵的、卑贱的,婆罗门和锡克团结成一个。”
由于泰戈尔注重在农村摘一些实际工作而不是空想着自治,由于他更强调发展印度技艺的必要而不是忙于焚烧外国货,由于他不仅谴责英国,也抨击种姓制度的罪恶和印度的贫穷,无知……他和自治运动其他领袖的关系开始冷漠下来了,这个自治运动的先锋战士退隐到圣地尼坦潜心文学教学的研究,进入了他的创作中期。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一些最为神秘的作品——戏剧《暗室之王》、《邮局》和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泰戈尔的朋友C.F.安德鲁兹说:“它们标志着他一生中伟大的转折。那时,诗人对民族的渴望已经融汇在宇宙之中了。他曾试图——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善尽美地表现生活的丰富’。”
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同样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有歌颂爱情与儿童的《园丁集》、《新月集》,哲理格言式的《飞鸟集》,还有直接回答时代问题,关注民族前途的长篇小说《戈拉》。
泰戈尔对安德鲁兹谈及自己将“尽善尽美地表现生活的丰富”是1882年的事情。在1882年,也许更早一些,诗人18岁时,他得到了一个伟大的启示。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他谈到了这种感受:“我的经验的世界似乎豁然开朗了,那些以前彼此分离的,朦胧模糊的事实,形成了一种意义上的伟大整体。”关于这一启示,他在《人的宗教》一书中有更完整的阐述:
我突然感到某种长久以来笼罩着的迷雾,似乎一下子在我眼前消失了,世界脸上的曙光,似乎放出了一种内在的欢乐的光辉。在这种感受中,令人难忘的是它的人类信息,是我的意识在人的超越个人的世界中的突然扩大。
正是获得了这一启示以后,他对安德鲁兹说自己将‘尽善尽美地表现生活的丰富”。可见这一转折在1882年便已完成,而且以后一直指导着泰戈尔的整个创作和思想。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吉》诗是1911年诗人病中及赴英国途中作为消遣从自己的几部诗中选译出来的。他并非为了宣告自己完成了“伟大的转折”。在印度国内,《吉》的反响并不如在西方那样强烈。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吉》并不是泰戈尔退隐时期所谓神秘主义思想或宗教崇拜的代表作,在《吉》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他的创作早期就已形成并贯穿他一生的哲学思想——人的宗教。
二、泰戈尔“人的宗教”思想
泰戈尔彬彬有礼而天性倔强,人们劝他信奉基督,他说:“我们自有宗教。”作为一代名士的幼子,家学渊源,东西文学哲理兼收并顾,且相信科学的他思想来源十分复杂。通常认为他创作中期的诗歌,思想上追求人神合一的神秘主义。这个说法比较含混,因此有必要将泰戈尔的哲学思想略作论述。
叶芝在《吉》序中指出,泰戈尔诗的魅力正在于“肉的呼声与灵的呼声是合二而一的”,〔3 〕他引用一位印度人评价泰戈尔的话说:“他是我们的圣人中间第一个不厌弃生存的,他倒是从人生本身出发来说话的,那就是我们所以敬爱他的缘故。”〔4 〕这正是泰戈尔的神与其他一切宗教不同的所在。在《人的宗教》一书中,他写到:“我想到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宗教——人的宗教,在这种宗教中,无限在人性中变得有限,并与我逐步接近,于是也需要我的爱恋与合作。”
对人的认知力的肯定一方面归功于他的天赋与才华而得到的那个伟大的启示;另一方面还得到现代科学的佐证。在他学习到的科学知识中,有一点使他感触很深,即生命并不意味着一种细胞的聚合,而是意味着这些细胞的内部有一种奇异的统一。虽然支配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事物所固有的,但是对这种规律存在的认识却是精神的;是精神观察了事物并发现了统一它们的规律。在一次与爱因斯坦的会晤中他说:“……假如说有某种真实,它与人类的精神既无感官上也无理念上的联系。那末,只要人类还存在,它就永远是虚无的。”
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话明确指出人的身上有两重性。“在外部的思想,感情和事件的背后还有内在的人,然而却很少被人了解或引人注意,但是在这一切之中,作为生命进程中的一个要素,他是不能被忽略的。”
他在强调人需要神的同时更强调神需要人。这些哲学思想在诗歌中集中地体现为吉范—德瓦塔的核心形象。它一方面指有限的自身渴望通过“内在的人”认识宇宙,一方面指无限通过人与万物表现着自己。虽然现实的琐碎的世界可能只是幻象,但绝对的美正是通过这个世界来表现自己的。这便是泰戈尔在生与死,是与非,静止与运动,无限与有限之间信奉和谐统一之韵律的缘由。人只有克服贪欲和自私,在科学哲学文艺工作中实现灵魂的解放,才有人格可言,这便是他宣扬“爱”、“互信互助”的缘由。
以上便是泰戈尔“人的宗教”思想的一个简述。
它与基督教、佛教不同。在那些宗教中,神专为饶恕人的愚蠢,体察人的渺小而在,专为昭示来生而在。
它与古印度哲学中“梵我同一”的思想亦有区别。黑格尔认为那种将“意识与自意识以及世界内容和人格内容都消失掉”,以达到“绝对无知无觉的冥顽空无境界”的“梵我同一”,“不是想象和艺术的对象。”〔5 〕泰戈尔在戏剧《桑亚西》中也明确地否认了禁欲苦行的修炼方式。在《游思集》—23中,在戏剧《桑德拉》中,苦行的修士都因着人世的召唤而放弃了无所事事的独坐冥想。即使在他退隐期间,与《吉》创作于同年的歌词《印度的主宰》呼吁印度的独立和富强,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被选为国歌。这可作为他的“人的宗教”面向现实区别于传统的又一明证。
但是他的哲学承继了印度传统的泛神主义诗。黑格尔把印度诗作为泛神主义诗最早的例子。他认为真正的东方的泛神主义强调的是“在一切现象里观照太一实体和抛舍主体自我。”主体通过抛舍自我,“意识就伸展得最广阔”。通过摆脱尘世有限事物,就获得完全的自由,结果就“达到自己消融在一切高尚优美事物中的福慧境界”。〔6 〕泰戈尔的人与自然、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思想正与此息息相通。在他的一些最纯净的诗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如黑格尔所说的“凭想象使自己进到事物灵魂里去分享其中同样的平静统一的生活……和一切值得赞赏的喜爱的对象,一齐享受最幸福,最欢乐的自得的内心生活”〔7 〕这样的境界。如《流萤集》—4, 春天吹得纷飞的花瓣/并非为了将来的果实而生/只是为了一时的兴会/—31:白的夹竹桃/同粉红的夹竹桃相见/用不同的方言/谈笑得兴高采烈/—50:池水从幽暗中/高高擎起百合花/那是池水的抒情诗/太阳说,它们真好。
这种泛神主义或许就是圣·芨多教授所说的“古老的题材”、“熟悉的形象”,它无疑是《吉》中“神”的起源与内涵之一,但在诗集中表现得并不显著,而且也绝不是它的全部内涵。
三、《吉》中“神”的多种内涵
内涵之一:天神与情人
孟加拉有一种古老的宗教联谊会由波尔歌手们组成。他们拿着单弦竖琴,来往于乡村之间:唱着对天神的爱情之歌。歌手们称天神为Maner—Mannsh,意即“我的心上人”,他们崇拜天神,把天神当作情人和朋友,例如,他们唱道:“啊,我到那儿去找他,找我的心上人?/唉,自从我丢失了他,/我穿过远远近近的地方,/到处漂泊寻找他。泰戈尔对这种农民歌手唱的歌儿很感兴趣,他自己写的歌曲里也回响着他们的情绪。〔8〕
泰戈尔继承了印度传统泛神主义诗的思想。在《吉》中,这一“神”的内涵可以第84首为典型:是这分离之苦/它弥漫寰宇/在天涯无际的天空里产生形象无数。是这分离之愁/它默默地通宵凝望繁星/又在七月阴雨的天气里,/在簌簌作响的树叶之间变成抒情之诗……诗歌展示了神的无所不在,而人通过万象来感知神。这样的诗还有第6首、 第75首、第81首等。
由于从民间文学吸收了营养,在这部诗集里,上帝或天神,便是诗人的或诗人假托的一个妇女的“心上人”,这种诗歌意象,使得诗在字里行间充满深情。所以叶芝在《序》中说:“情人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低吟这些诗篇,就会发觉这种对神的爱是个魔法的海湾,他们自己的更为痛苦的热情,可以在其中沐浴而重新焕发青春。”
诗集中大部分诗篇都采用了这样的形式,如第7首,第13首, 第17首等等。诗歌通过追寻爱人的艰难与苦痛抒发对神的渴望。如第22首结尾写道:“啊,我唯一的朋友,我最亲爱的人儿,我家的门户都是洞开的——千万别像梦一样的过门不入啊。”
但这只是诗歌思想的一个表象,一种艺术形式,他所追寻的神的内涵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内涵之二:美、真理(理想)
在动人的诗歌意象背后,诗人所渴求的“神”拥有丰富的人类意蕴,其主要指向是美与真理,及在此之中的理想境界。
关于灵魂可以超越自身观照宇宙万物,发现美与真理的表述,最早可见于《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一个人如果随着向导,学习爱情的深密教义,顺着正确次序,逐一观照个别的美的事物,直到对爱情学问登峰造极了,他就会突然看见一种奇妙无比的美。他的以往一切辛苦探求都是为着这个最终目的,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
…………
请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有运气看到那美本身,那如其本然,精纯不杂的美,不是凡人皮肉色泽之类凡俗的美,而是那神圣的纯然一体的美,你想这样一个人的心情会像什么样呢?〔9〕
这个境界与泰戈尔获得的启示多么神似!书中还提出“心灵的生殖力”的说法,亦与泰戈尔“人身上的两重性”的思想相一致。泰戈尔也相信终极的美,正如柏拉图所说的神圣的纯然一体的美:“在一圈复一圈的/永恒的舞蹈的核心里/中间是寂然不动的。”“世界是浮在寂静之海海面上的/那经常变化着的泡沫。”(《流萤集》第184、80首)
《吉》中的神具有鲜明的与众不同之处,它存在于现实尘世之中:“这是你的足凳/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生活的地方/便是你歇足之处。”(《吉》—10)“神在农民翻耕坚硬泥土的地方,在筑路工人敲碎石子的地方。”(《吉》—11)这样我们可以发现,“神”作为诗歌的意象,具有丰富的人类意蕴。它只是一个称呼,如同我们对“造物”的称谓。诗人所赞美与渴求的神,没有姓氏与教义,主要地象征着美与真理,和建立在此之上的理想之国。
让我们以开篇第1 首为例:“你已经使我臻于无穷无尽的境界/你乐于如此”……“你翻山越岭、越过溪谷带来这小小芦笛/用它吹出永远新鲜的曲调。”这里的“你”,正可理解为泰戈尔思想中一切运动与静止、存在与湮灭的中心——和谐、统一的韵律之美,它滋生了宇宙万象生生灭灭的美的具象。
再读一读第12首:“我跋涉的时间是漫长的,跋涉的道路也是漫长的。”……“到达离你最近的地方,道路最为遥远;达到音调单纯朴素的极境,经过的训练最为复杂艰巨。”/“旅人叩过了每一个陌生人的门,才来到他自己的家门口;人要踏遍外边儿的大千世界,临了才到达藏得最深的圣殿。”/“我的眼睛找遍了四面八方,我才合上眼睛说道:‘原来你在这儿!’”……
王国维将稼轩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举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10〕的最高境界。作为《吉》诗集中追寻美与真理的艰难历程的代表诗,第12首的意境与之多么神奇地吻合着。
既然“神”的本质象征着美与真理,我们就不难理解诗人将对爱人的怀念和对童心的赞叹也奉献在这位神的脚下。而由此衍生出的更显著的一个涵义是理想人性与理想乐园的描摹。在《吉》—36中,泰戈尔追求着理想的人性:“我的主啊,这是我对你的祈求——请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赐我以力量,使我轻易地承受欢乐与哀伤/……赐我以力量,使我永不抛弃穷人,永不向威武屈膝/赐我以力量,使我的心灵超出于日常琐事之上。”在著名的《吉》—35中,这种追求表现得更为深远:
在那儿,心灵是无畏的,头是昂得高高的;
在那儿,知识是自由自在的;
在那儿,世界不曾被狭小家宅的墙垣分割成一块块的;
在那儿,语言文字来自真理深处;
在那儿,不倦的努力把胳膊伸向完善;
在那儿,理智的清流不曾迷失在积习的荒凉沙漠里;
在那儿,心灵受你指引,走向日益开阔的思想和行动——
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进入那自由的天堂吧!
这无疑是完美的印度、完美的世界和人类的理想乐园。
内涵之三:观照世界的自由心灵
《吉》—102全诗如下:
我在人前夸口,说我认识你。他们在我的一切作品中,看到了你的画像。他们来问我:“他是谁?”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我说:“真的,我说不出来。”他们责备我,鄙夷地走掉了。而你坐在那里莞尔微笑。
我用你的事迹编成不朽的诗歌。秘密从我的心里喷涌而出。他们来问我:“把你的命意告诉我吧。”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我说:“啊,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笑,万分鄙夷地走掉了。而你坐在那里莞尔微笑。
一般认为,《吉》的103首诗歌具有完整的结构。第102首属于结尾部分,概括了诗集的内容和意义,说明他的诗不为常人所理解,只有神自己明白,表现了诗人的神秘主义思想。
这一说法好象说诗人自己宣称了自己的神秘主义。实际上,泰戈尔对自己的“人的宗教”阐述得十分明确,并无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这里的“你”绝不是抽象的、与人对立的神。一方面它可理解为集美和真理于一身的造物,另一方面也可将它视作观照世界、自由创造的心灵。
美变幻不定,真理扑朔迷离。每个追求缪斯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可以在心里获悉她的秘密,可以在作品中透露她的讯息,可要说出“所有的意思”是难上加难的。
苏轼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11〕诗人在第102 首诗中写出的正是这一事实,他表达了对自己能具有认知造物的自由心灵的一种惊奇、自信与感激。正如苏格拉底所说:“要想找到一个人帮助我们凡人得到这样福份,再好不过的就是爱神。”〔12〕爱神并不存在,具备认知能力的还是人自己的自由心灵。在这幅生动的图景中,诗人想象的“莞尔微笑”的“你”正是自己不为别人理解的心灵或灵魂。可以用一句唐诗做个形象的比方:“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哈拉德·雅恩为泰戈尔作的《颁奖辞》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的神祗崇拜,可说是一种美学的有神论……如果我们愿意说,这可说是一种神秘主义,但这不是那种把个人的人格抛弃、以求取被纳入“一切”——而这“一切”又近乎“无有”——的神秘主义,而是秉具灵魂的一切才能,修炼它们,以期达到最高境界,而热切地迎向一切造物之父的神秘主义。〔13〕
确实,神就是诗人灵魂祭起的一面神奇纯净的镜子,流转观照,敛人与吐露一切美好和谐的事物与情感。它通过诗人心灵的翱翔得以在整个世界穿梭停驻。鲜花和果实,季节的变异,印度的暴雨与河流,海洋和天空,妇人的手指和儿童的心灵都得到诗人的凝视与描绘。小我延展至无限的大我,在这些可见的形象与可感的声音中,往往在“这一个”上凝聚着人类相通的情感智慧。这大我的光芒使生活中最琐细的事情和自然中最平凡的物体萦绕着一种奇异的气息,这便是他所感悟的神与我们所读到的神秘。泰戈尔诗歌中的“神”具有丰富的人类情感和哲思的意蕴,《吉檀迦利》中“神”的多种内涵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收稿日期:1997—04—08
注释:
〔1〕《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871页。
〔2〕S.C.圣芨多:《泰戈尔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本文其他未注出处的引文均引自该书。(泰戈尔诗歌除外)
〔3〕〔4〕叶芝:《吉檀迦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6月版,第9、3页。
〔5〕〔6〕〔7〕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 1979年1月版,第86—87、89页。
〔8〕吴岩:《吉檀迦利》(译者后记),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6月版,第132页。
〔9〕〔12〕《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1 月版,第251—252页。
〔10〕王国维:《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8月版,第2页。
〔11〕《诺贝尔文学奖全集》,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12月版,第9页。
〔13〕《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版, 第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