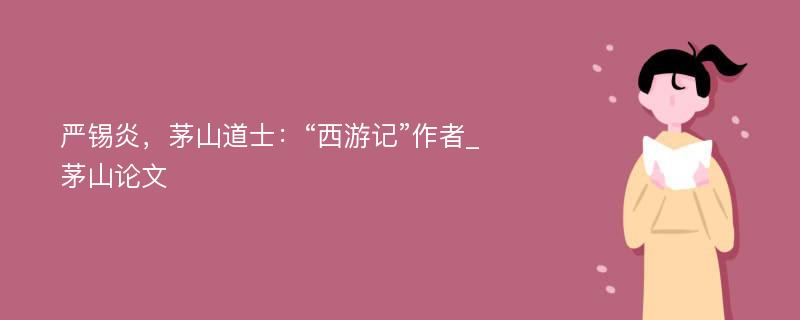
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今本《西游记》定稿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茅山论文,西游记论文,定稿论文,师徒论文,道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20(2002)04-0034-04
笔者根据对全真教秘史和《西游》评论史的一些考察,曾提出作为今本《西》书之祖本的《西(平话)》,与全真教创始者之一的丘处机(道号长春真人)关联甚密,它其实是丘的弟子史志经等人在华山撰成的;托名丘撰,其意在更有力的宣扬全真教义[1]。本文将进一步说明,今本《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人也是明万历时江苏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道士。
在我们目前见到的百回本《西》书古代版本中,最早者是明代万历20年(1592年)金陵(今南京)世德堂(现已知此书坊主人是唐光禄)版《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书无撰者姓名,仅有陈元之序,并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研究今本《西》书的作者及主旨,无论如何不能无视这个最古版本的这种特殊格局。近年有研究者指出,其中,陈元之情况不详,但不可能是撰者;唐光禄也非撰者;倒是“华阳洞天主人”令人生疑。据研究,此处的“校”字,意指“善校”,“其广义实为编撰之工”,因此,此“华阳洞天主人”应为《西》书最后定稿人[2](P188-194)。在我看,这是有道理的。如果再考虑到陈序透出《西》书的道教旨趣,以及《西》书出版时定稿人面对的复杂形势使之不愿公然露出真姓实名(见本文后述),那么,“华阳洞天主人”即《西》书最后定稿人之断,就显得更有力。《西》书作者之谜的求解,应集中力量于此“主人”之搜寻[3](P152)。本文是先投石问路。
(一)“华阳洞天”只属于茅山道教,与其它宗教无关。“华阳洞”本是江苏金坛及句容市内的一个溶洞,风景极佳,后成道教胜地,周围称“华阳洞天”,为道教“第八洞天”。汉晋以还,道教中一些真人宗师常修炼于此。其中,西汉时期陕西咸阳三茅兄弟(注:茅盈,茅固,茅衷。其高祖茅濛,曾修炼于华山,于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升“仙”。始皇为纪念他,把腊月改为“嘉平”。参见樊光春《陕西道教两千年》第146页,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从陕西来此修行、传道并施医,深得当地人爱戴,被尊为神,此地遂有“茅山”之称[4](P87-89)。但茅山之最大溶洞,为何被命名为“华阳”?
“‘华阳’作为地域概念出现甚早,《禹贡》、《尚书,夏书》、《周礼·职方氏》及《汉书·地理志》、《三国志》等均曾涉及,以华阳为古梁州范围内的一个具体地域”;“山之南为阳,秦岭山脉以南(此处尤指华山之南——引者),为《禹贡》梁州地界。故《禹贡》云:‘华阳黑水惟梁州’”[5](P78-82)。从战国时期秦国有“华阳军”(《史记·周本纪》)以及“华阳太后”(《史记·吕不韦列传》)等称呼看,当时“华阳”往往主指陕西华山之南的地域,所谓“华山之阳”是也(陕西有县在华山北,曰“华阴”,显然是其对举)。唐代长安还有华阳观,纪念华山神君(白居易诗中有多处诵此观)。唐人储光羲更有诗《题茅山华阳洞》:“华阳洞口片云飞,细雨濛濛欲湿衣。玉萧遍满仙坛上,应是茅家兄弟归”。由此诗看来,茅山“华阳洞天”之命名,显然是三茅兄弟所为(明代《乾元观记》碑文有“三茅所称华阳洞天”及“独以茅氏三真君得名”两句可证,见新编《茅山志》第372页),盖因其祖修炼于华山,闻名天下,其人又来自“华阳”(注:有资料显示,秦时此洞似尚无“华阳”之称。其中台坛被称为“句金之坛”或“金坛百丈”,见新编《茅山志》第268页。今金坛市名应源于此。)。后来,南朝道士陶宏景隐居茅山40余年,尊奉三茅为祖师,号“华阳隐居”;唐代道众施肩吾又自称“华阳真人”;南宋时,吴兴道士沈善知穴居华阳洞中,自称“洞主”,等等;此外,唐宋尔后又有人在此地建“华阳馆”、“华阳观”及“华阳道院”等,使“华阳洞天”名播宇内。道教典籍《云笈七签》又把“华阳洞天”列为道教的“第八洞天”。唐宋以后,文人骚客笔下的“华阳洞天”,往往是茅山道教风景区的标志或代称。元代著名诗人萨都拉《送刘云江还茅山》云:“八十华阳洞里仙,朝回剑履御阶前”。明人诗则曰:“试看喜客泉头日,别是华阳洞里天”(陈凤梧《登大茅山》)[4](P392);“大茅峰头鹤唳,华阳洞口龙吟”(夏言《游三茅漫句》)[4](P394),皆是此意。
要之,“华阳洞天”早已成茅山标志;它最初在文化深层与陕西以及华山道教有着千絮万缕的“血缘”关系。
(二)明代“青词宰相”李春芳在《送袁一斋归茅山》诗中写道:“汝是萧闲第几仙,乘云何日下瑤天。洞有华阳人不远,井闻葛稚药须诠”[4](P393)。从中,人们悟不出此君尚以“华阳洞天主人”雅号自称的蛛丝马迹。否则,其诗不会如此写“华阳洞天”。但不知怎的,沈承庆先生却引吴承恩《赠李石麓(即李春芳——引者)太史》诗中“移家旧居华阳洞,开馆新翻太乙编”两句,又引刘荫柏、苏兴等力主《西》书为吴承恩著的学者见解,竟凭空认定李春芳即“华阳洞天主人”(注:见《话说吴承恩》第191-192页。据此书序者说,由吴承恩之诗推出此见,也是上世纪40年代有关学者的旧说。)。另有学者则引吴承恩《德寿齐菜颂》关于“帝奠山川,龙虎踞蟠,建业神皋,华阳洞天”的韵句,说此文是写给李春芳的,也得出同上结论,实在令人不敢苟同[6](P126)。既然“华阳洞天”当时已成茅山景区的标志或代称,且明人有关“华阳洞天”的诗句也并不少见,那么,由吴承恩“移家旧居华阳洞”一句,怎么可以轻易断定李即“华阳洞天主人”呢?既是“主人”,为什么又在送友人诗中写出“洞有华阳人不远”之句呢?这岂不是“主人”“辞职”吗?批评吴承恩系《西》书作者之据是“孤证”的人,自己又犯更孤更悖的逻辑和推理错误,怎能自圆其说?照此逻辑,前引明人陈凤梧和夏言皆应被称“华阳洞天主人”,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华阳洞天主人”决非李春芳。沈老先生此断难成立。其实,如再考虑到当时华阳道众种种复杂的内外处境(见本文后述),这位李官人也绝不会给自己起这么一个惹麻烦的“道号”的。
(三)明万历20年前后的“华阳洞天主人”,只能是茅山道士中的全真派。
最早,元代皇室虽在北方对全真教大加扶持,但在茅山却支持道教南派正一教。元大德八年(1304年),元成宗封第38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茅山等三山符箓[4](P82)。从此,茅山成为正一道场。这一点,又随着明室对全真教的长期压制而日益定形(参见本文后述)。直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闫希言从陕西南下,住进茅山乾元观,全真教及其龙门派才逐渐在茅山立定脚跟,并在道众中传播。当时,正一教与全真教在茅山的确是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在万历年间形成了“五观”传全真而“三宫”尊正一的格局(“五观”即乾元观,玉晨观,德祐观,仁祐观,白云观;“三宫”指九霄万福宫,元符万宁宫,崇禧万寿宫)。其中,乾元观和仁祐观道众属于闫希言开创的龙门“分支岔派”即“闫祖派”,其余“三观”则传“龙门正宗”(参见新编《茅山志》第82-83页)。“五观”传全真局面的形成,是与万历后全真龙门派在江浙一带的中兴联系在一起的(注:参见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论稿》第70-77页,巴蜀书社2000年版;又可参见张文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第189-191页、第1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在此之前,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室在茅山设“华阳洞正副灵官”各一名,正为六品,副为从六品,掌领茅山教事,全从正一道士中挑选[4](P17)。终明一代,正灵官计有15人[4](P139)。在《西》书于金陵出版的前一年(万历十九年),华阳洞正灵官杨存建在茅山还树立了《明重建元符万宁宫万寿台记碑》[4](P375),实际上也是向在茅山全真道士示威显权。全真道士在被明室轻视的各“观”争夺道众,包括“乾元观自明嘉靖以后,由道教全真派道士主持”[4](P416)。闫希言当时就以此观为“根据地”,并培养出了一些很有水平的门徒如舒本住,江本实,以及王合心、李教顺等[4](P129)。江还撰有《华阳真海》一书(注:也有人说此书为闫希言本人撰,参见新编《茅山志》第133页、第93页。)。“华阳真海”,意谓华阳洞天是全真教的海洋也。从书名也可看出,当时全真道士力争成为“华阳洞天主人”。在这种两派斗争的格局下,如《西》书定稿者是正一道士,他或他们尽可以抬出“华阳洞灵官”的大招牌来吓人,不必以“华阳洞天主人”自称。可以设想,当时以“华阳洞天主人”自称者,只能是全真道士,其称含有抗衡“灵官”之意。已成全真领地的白云观,门前对联的上句说“此地是华阳故里”,也可为一证[4](P408)。如再考虑到这种含糊的隐称一方面是向“灵官”们示威,另一方面也不必暴露真实姓名(见本文后述),那么,此论断成立的可能性很大。
(四)闫希言师徒很可能就是作为今本《西》书定稿者的“华阳洞天主人”。这是因为:
(1)在万历20年前的茅山全真道士中,只有闫氏师徒具有这种可能性。一来,当时只有他们是公然敢于与“华阳洞灵官”斗争的全真道士中的领头者和佼佼者;二来,闫希言“来自终南”,其徒江本实后又归于终南[7](P76),他们与三茅“华阳洞天”更具亲和力,自称其“主人”在情在理;三来,当时的茅山只有他们的文艺修养堪当此任。《华阳真海》不仅从书名上露出“华阳洞天主人”的消息,而且也是闫氏师徒堪当此任的书证之一。还有资料显示,闫氏师徒不仅言行脱俗(闫本人“不巾栉,身着粗布夹衫,有履而不袜,人目之为‘闫蓬头’”,“盛暑辄裸曝日无汗,严冬凿冰而浴”。新编《茅山志》第133页),而且精文墨,有著述,多才多艺,包括舒本住还擅长绘画,有画作《仙山楼观阁》存世(注:参见江苏句容道教协会办《茅山道院》2002年6月第六期《萨都拉与茅山》一文。);至于江本实放荡不羁,洒脱张狂,重演“活死人墓”故事,在茅山也尽人皆知。据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七说,明亡之后,江本实“散家财弃妻子,入终南学仙”,可见其确已超脱世事,别有“华阳”的情天恨海。说真的,他们编撰《西》书,比吴承恩那个“老夫子”合格多了。四来,在茅山,除闫氏师徒外,“龙门正宗”的第六代宗师沈常敬也住乾元观,并在此观培养了孙守一、闫晓峰等。但沈氏师徒在茅山时,已距万历20年较久,《西》书已经印行,故他们不可能是《西》书所署“华阳洞天主人”。
(2)以上立论成立的一大铁证尚在。现在茅山乾元观尚存《乾元观记碑》,是闫希言于明明万历16年(1588年)逝后,其徒江本实、李合坤等人于万历十八年(1590)所立。其中有段碑文是:
余观三茅所称“华阳洞天”、“金陵地肺”,盖天下第一名山,而得道之士如展上公、魏元君者甚众,独以茅氏三真君得名耳。……而观(指乾元观——引者)创于宋时,则因真宗祈胤生,仁宗而主教事者朱自英也。乾元之设旧矣,其待希言而兴乎者[4](P372)。
这段碑文形成于《西》书付梓前夕,在我看来,它实际是对闫氏师徒即“华阳洞天主人”的一种暗示。对《西》书作者研究,它相当重要,至少超乎天启《淮安府志》。鉴于它的刻成比《西》书梓行仅早一二年,所以,它的价值就更值得注意。碑文开头即述“华阳洞天”,然后马上“缩景”于乾元观,说明“其待希言而兴乎者”;对于当时“华阳洞灵官”把持且势大财粗的“三宫”,则只字未提。在这里,乾元观是“华阳洞天”的标志。乾元观兴,则“华阳洞天”兴,这不是暗示着闫氏师徒为“华阳洞天”的“新主人”而何?
作为此段碑文含义的佐证之一,乾元观至今尚存“闫祖派”第五代传人钱永成为乃祖江本实所立墓碑。碑文曰“皇明重兴乾元祖文谷姜公墓”[4](P375)。“重兴乾元祖”头銜,与上引碑文“其待希言而兴”遥相对应,均隐含着“闫祖派”誓作“华阳洞天(新)主人”的祈愿。
(3)据明人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闫道人传》说,闫希言初到乾元观时,此观“仅有门及丙舍。道人游金陵,化公卿间,汇赀成诸殿阁”。其徒舒本住即金陵人氏,助闫希言共同化缘,共同修观。“观内原建有正门和西便门,进正门是灵官殿,殿之两侧为东西拜楼;进西便门有小山门,后为太元宝殿,殿后为玉皇殿,殿东侧有李明真人炼丹井,旁有陶弘景炼丹碑,西有客堂、祠堂、库房和西花园,最后一排殿堂自东向西有东拜殿、东岳殿、三清殿、西拜殿、住宅楼、住持室、斗姆楼和三层宫殿式建筑的松风阁,以及道舍、斋堂等等”[4](P97)。如此巨量建构,耗资巨大,可见闫氏师徒等在金陵化缘之功甚巨。
可以设想,金陵世德堂本《西》书的出版,正是以闫氏师徒在金陵化缘募资作为契机和经济支撑的。明代文艺史和宗教史上的事件很多,但象茅山闫氏师徒在南京筹巨资这样的事情却很少,《西》书的定稿者因此便大大缩小了范围。
(五)在明代嘉清、万历时期,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大发展,随之使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各种文艺思潮大碰撞,民间文艺包括话本艺术也日益普及推广[8];另一方面,中国各派宗教势力,特别是民间道教力量,也尽力利用当时大普及的民间文艺形式(如话本、说唱等)力求广泛传播本教派教义,吸引教徒。例如,在嘉靖、万历时期盛行于河北一带的民间道教——黄天教,便创作了《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和《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太阴生光普照了义宝卷》、《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神宝卷》等许多通俗文艺作品,在其教传播普及中起了很大作用(注:参见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第八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比《西》书刻印时黄天教的这种传播手段,闫氏师徒编撰整理《西》书,以播全真教义,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西》书一面世,论者异口同声把它解为道书,确非空穴来风。
收稿日期:2002-08-30
标签:茅山论文; 茅山道士论文; 西游记论文; 道士论文; 道教门派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吴承恩论文; 禹贡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