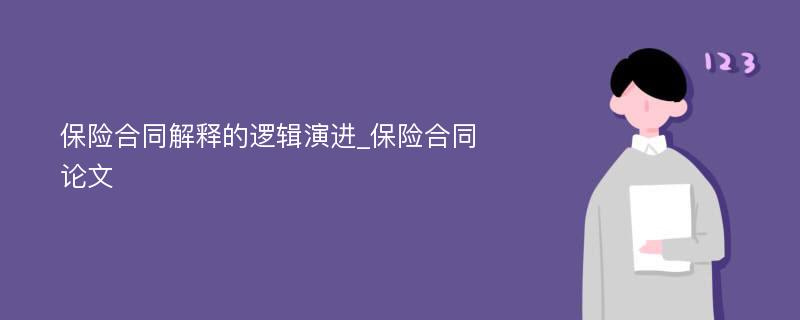
保险合同解释的逻辑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险合同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合同为当事人间的合意,而合同解释涉及合意是否存在以及合意内容的确定。因而如何对合同进行解释是合同法的重要议题。在保险领域,合同解释的重要性由于保险合同的附合性、技术性以及公共物品属性而更为彰显,直至成为“保险合同的灵魂”。①但我国法院对保险合同的解释活动却处于失当和无序状态。在合同解释的指导理念上,许多法院割裂了一般合同解释与保险合同解释的共性关联,将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障视为合同解释的终极目标与判断结果正当性的唯一标准;②在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顺位与范式上也显得相当混乱,体现为对文本解释方法的轻慢,对目的解释方法的任意扩张,以及对不利解释规则的误用与滥用等。即便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相关案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种非理性的、与合同解释基本法理相背离的倾向,③因而学界亟需对此作出回应。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在于尝试建构一种均衡考虑合同共性与保险特性需求的、更为规范与清晰的解释活动的指引框架,以回应保险营业技术性对解释结果一致性与可预测性的内在需求,而不会停步于对具体解释方法的论证。 一、保险合同解释的原点:解释活动价值基础的确定 (一)保险合同解释的层级递进 狭义的合同解释主要包括含义的释明与漏洞的填补。但是,对解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也是合同解释隐含的必要过程,此即所谓“公平解释”与“诚信解释”等类似方法的实质。④在保险领域,合同解释活动通常与漏洞填补无涉,因为条款是由专业从事风险经营的保险人起草的,出现漏洞的概率不大。况且合同中有承保事项和除外责任的规定,二者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确定了保险人的承保范围。因此,保险合同解释客体包括争议条款含义的阐明和对不适法结果的修正,解释过程也就相应地表现为这两个层级递进的阶段。就争议条款的阐明而言,主流观点认为应首先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解释理论,⑤这意味着需要在合同法共性的维度内分析解释活动背后的基础性价值构成,确定实现价值的技术方法。因为任何法律都包含价值与技术两个层面,前者表现为抽象法律原则,后者体现为原则指引下的具体法律规则。⑥与此同时,保险合同仍有独特属性需要予以考量,即实现保险法维度内的独特价值取向也会影响解释规则的选择与适用。而第二阶段则是要确保解释结果符合上述价值基础,特别是应满足保险法维度内的价值取向需求。毕竟,前一阶段的解释规则主要源自于合同法共性价值的推演。概言之,确定合同法共性与保险法特性下解释的价值基础是保险合同解释的原点。 (二)合同法共性维度内解释活动的价值基础 意思表示具有双重功能:它一方面是一种决定性的行为,表意人的意思似乎对法律后果具有关键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表达出来的东西,性质决定了其应为他人所知。⑦当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与表示出来的意思不一致时,应以何者为优,这一争论贯穿了大陆法系合同解释理论的历史。及至今日,方逐渐步入“以表示主义为原则,以意思主义为例外”的阶段。英美法系合同解释也有相对应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分,虽然自近代古典契约法理论形成以来,对应于表示主义的客观主义成为正统立场,但其同样承认当事人在遭受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时有撤销或变更合同,以维护自身真意的权利,因而两大法系的解释理论并无实质的不同。究其原因,就意思主义而言,如何确定作为过去心理事实的表意人的主观意愿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意思”的确定必定仰赖于客观外在证据,所谓表意人的意思只能是被客观推断出来的意思。因而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在方法论上并无实质差异,差别仅在于证据选择,一为表意人之证据,一为受领人或第三人之证据。⑧再者,意思主义本身存在逻辑悖论。它奉个人意思自治为圭臬。然而,合同中的自治始终涉及双方当事人,一味地依循表意人的意思而无视受领人的自治,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而表示主义主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从意思表示受领人立场去认定之‘客观表示价值”’。⑨它强调表示本身具有不受表意人内心意思影响的客观意义,并赋予此种理解以法律效力,确立了“规范意思”,因而被视为有利于保护受领人的合理信赖,以维护交易安全。 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演变的实质是合同解释活动价值基础的转换,它主要体现了表意人自治原则与受领人信赖原则之间的角力。⑩不过,价值基础的彻底转换会导致对一种价值的过分贬损,因而最优选项应是在相互妥协中寻求价值实现的平衡。毕竟,表示主义同样存在困惑。为何受领人的规范意思可转而凌驾于表意人意思之上?在寻求受领人信赖保护时,亦应兼顾表意人的自治利益。(11)在此,需要引入德国法创设的可归责性原理,通过对双方当事人可归责性的比较、权衡加以确定。这表现为,合同内容应根据处于受领人地位的理性受领人的合理理解来确定,同时,该理解须为处于表意人地位的理性表意人所能合理预见。前者考察的是受领人的信赖是否具有合理性。能预见到对方的意思就不应在该意思之外产生信赖,否则即具有可归责性——受领人对表意人内心意思的预见程度与其对规范意思的信赖程度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后者则考察表意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其对受领人理解的预见程度与可归责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这一标准下,受领人只要足够谨慎,他的理解就不会背离法官的解释,其缔约目的因而可以实现。表意人通常能够预见理性受领人对自己表示的理解,如受领人的理解与自己的意思不同,表意人应当通过信息沟通消除前述分歧。如果这种理解差异超出了谨慎的表意人所能预见的范畴,则合同不会依照受领人的理解解释。(12) 然而,效率原则、给付均衡原则也是指引合同解释活动的基础性价值,进而可修订上述结论。依据前者,如果表意人与受领人均不具有可归责性,此时,对合同的解释已经脱离了当事人的意志进入了一个客观状态——风险分配领域。解释已经变成了风险分配问题,谁能以最小成本移转和削减风险就应认定其具有可归责性。在个别磋商缔结的合同中,当事人的能力被假定基本相当,效率原则于此无适用余地。合同可能会被解释为未成立,当事人互不承担责任。(13)但对于格式合同情形显然不同。格式条款制定方对于此类风险的控制成本明显为低,这一结论导致了不利解释规则的引入。再者,格式条款起草者的预见可能性程度、风险规避能力、交易能力等明显占优,可能造成利益失衡。因而给付均衡原则要求在格式条款解释中,受领人信赖合理性较之表意人可归责性标准居于优先地位,对受领人而言的矫正只适用于极罕见的例外情形。此时可归责性标准实际上是按照处于受领人地位的理性第三人的理解确定合同内容的客观标准的另一种表达。(14) (三)保险法特性维度内合同解释活动的价值基础 保险营业存在鲜明个性,这决定了保险合同的解释除需遵循合同法的一般解释原则外,仍需受保险法维度内价值取向的影响。 1.保险营业的技术性要求在解释合同时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首先,保险是一种移转和削减不确定损失风险的机制。消费者将自己面临的风险移转给保险人,保险人则通过集合与分散的方式将风险损失确定化,随后又以收取保费为对价将补偿承诺销售给消费者。保费数额不得少于经保险精算得出的、预期自己将为特定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失额。(15)因而准确测定主体风险水准是保险营业维持的关键。为此,亟需增强解释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就要求构建一种更为规范和清晰的保险合同解释框架。其次,承认各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相对的适用位阶,规范其适用范式也是十分必要的。最后,在解释规则与解释原则之间,应优先采用具有严格逻辑结构和适用要件的具体规则,避免直接诉诸最一般的原则性方法去寻求正当决定。毕竟,后者缺乏统一适用标准,易导致裁判结果的不统一,影响保险人对风险的评估。 2.保险作为公共物品的属性要求其尽量满足被保险人对获取保障的合理期待。在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保险产品开始被赋予公共物品属性,“它不仅是一种经济补偿和社会再分配的手段,也不仅是以物质财富保障为中心,而是逐渐转向以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为中心。”(16)它能将个体所面临的难以承受的风险在共同体成员间进行分摊,帮助被保险人应对未来的不测,完成其对日后生活的合理规划,维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此外,获取保险赔付对于利害第三人,如被保险人不当行为的受害者也具有相当的意义,它甚至是构建强制责任保险的首要动因。因而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取其所需的保险产品就成为一项公共政策。将满足合理期待作为保险合同解释原则,有助于法院贯彻前述政策,充分发挥保险机制移转风险、分散损失的功能。 3.保险市场存在结构性利益失衡,这表明在解释合同时应适当倾向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以达成真正的给付均衡。保险商品的实质是风险移转服务,具有无形性,消费者的交易判断几乎完全仰赖于保险人一方提供的信息。保险商品还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消费者难以了解条款的真正含义。前述特性与交易契约定式化的结合使得保险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相比,交易弱势特点更为突出。再者,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被保险人(17)缴纳保费的义务是确定的和在先的,而保险人给付义务并不确定,时间上亦具有滞后性,这种不对称强化了保险人的结构性优势,也使得保险监管难度加大。况且,监管机构对保费水准和保单条款的审核无法避免不公平情形的出现,许多被保险人是因为保险人的不当营销方式而产生了对承保范围的误解,其甚至在合同缔结前无法获得保险条款,更遑论对内容的了解。这种结构性利益失衡使得各国在解释保险合同时更加关注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如《欧洲保险合同法原则》(PEICL)第1:104条就要求“依据文本、语境、目的和比较法背景对《原则》予以解释,且须考虑促进公正交易、合同关系的确定、法律适用的一致以及充分保护保单持有人”。此一特性不仅凸显了给付均衡原则对选择保险合同解释规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还印证了合理期待原则的重要性。毕竟,市场结构性利益失衡使得穷尽现有规则也可能无法确保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因为规则援用需考察个案情形,满足前提要件。而合理期待使得法院可以摆脱具体合同内容的束缚,将视线投向保险市场的本质或特定种类保险必须实现的目标,甚而去填补行政机关对保险业规制的空白。 综上所述,保险合同解释既需遵循合同解释的一般性原则,如意思自治原则、信赖原则、效率原则,以及给付均衡原则,(18)同时也应考虑保险营业特性,保护合理期待,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以及适当倾向于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保险合同的解释过程首先表现为主要遵循合同法基础价值指引下的一般技术规范,探寻处于受领人地位的理性第三人对合同内容的理解,以此阐明争议条款的含义。若解释结果有悖于前述价值基础,则应予以修正。 二、保险合同解释的展开:意图探寻技术规范的运用 (一)意图探寻中的文本主义解释论与语境主义解释论 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而确立了以探究理性第三人的理解为内容的客观解释论。(19)《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此处的通常理解,即是依照合同法中理性第三人标准具体化的、普通的被保险人对争议条款的理解。(20)在此,我国合同法遵循了英美合同法的一般做法。(21) 然而,在客观主义的基础上,英美法尚存在文本主义(形式主义)解释论与语境主义(功能主义)解释论的进一步区分。(22)前者植根于古典契约法的完全合同理念,后者则建构于新古典契约法的不完全合同理念。古典契约法的形成主要源自于对法律确定性与简明性的追求。它认为行为人在作出决定时,通过将所有未来的收益和成本折算为现实价值,能够理性地将其主观预期效用予以最大化。签字即意味着行为人已经阅读、理解并接受交易条件。因而除非存在欺诈等特定情形,否则合同“明示条款必须遵守”,不允许以合同缔结前或与之同时存在的其他证据更改业已成立的合同。而新古典契约法则认为,古典契约法未曾考虑到当事人社会行为的复杂性和经济权力的不公平分配,因而需要将当事人利益置于交易背景和社会价值中考虑,将当事人未约定的“社会标准”引入契约关系。(23)故而协议不仅表现为合同中的语言文字,还体现为此前的交易履约过程以及交易惯例等其他相关情形。(24)据此,在文本主义下,合同文本被视为决定性的解释依据,而语境主义则将解释资源扩展到文本之外。(25)一般认为,语境主义较之文本主义在解释的精确度上为优,但成本却高于后者。(26)而没有任何解释理论能证明,投入无限的资源提升解释精确性是正当的,(27)特别是在成本的承担不仅涉及当事人,还关乎法院之时。因而完全脱离语境的文本主义与无边无际的语境主义皆非合理选项。对此,现今多数美国法院采取的是将文本与语境结合,优先适用前者的方法。(28)笔者认为,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保险,而且其合理性更为充分。因为它能在更大程度上契合保险营业对法律适用确定性的需求。 (二)文本主义下的探求真意方法 在文本主义下,法院主要通过文义解释规则与体系解释规则探求当事人的真意。首先,对保险条款的含义应当按照其普通含义加以理解,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基本方法。合同条款皆由语言文字组成,当事人所欲设定的权利义务也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因而其是证明当事人意图的最直接、最简便的证据。“保单应首先依照其所使用的条款加以理解。条款本身将依照其使用的语言文字首要的、本质的、普通的以及流行的语义加以理解。保单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含义是一个具有通常智力水平的普通人所理解的含义。”(29)所谓普通人,是指一个在法律或保险营业方面未受过特别训练的理性第三人。具体而言,是指格式保险合同的可能订约者。(30)例如,对于“坠落”一词,不具有专业知识的保险消费者通常将其理解为自高海拔向低海拔的下行运动,这种运动并不限定于绝对垂直降落。(31)其次,需要将特定条款置于保险合同整体背景下进行体系理解。合同是一个整体,要理解其整体意思,需理解各个部分的意思并确定彼此间的关系。反之,要理解特定条款的含义,也需将其置于整体合同中理解。正如《法国民法典》第1161条所言:“契约的全部条款得相互解释,以确定每一条款从整个行为所获得的意义。”适用体系解释方法时,应尽量采用使各个条款之间相一致的解释。对仍可能发生的条款之间的冲突,英美判例法总结出了多种规则,包括个别协商条款优于定式条款,手写条款优于机打条款,机打条款优于印刷条款,背书条款优于保单正文等,均值借鉴。(32)此外,英美保险法中与体系解释相关的技术规范还包括同类解释与限制解释。前者是指若保险合同列举的事物属于同一类,紧接列举事项后的用语所表示的含义系指同类,而非他类事物。例如,依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条款》(2009年版)第4条第1项的规定,金银、珠宝、钻石及制品、玉器、古画、艺术品等珍贵财物不属保险标的物。此处的“等珍贵财物”应解释为与前述列举事物同类的物品,如珍贵邮票,而不能解释为包括土地使用权。后者是指保险合同的限制性用语紧接在概括用语之后,在前的概括用语不得按其原先含义解释,应受在后用语限制。如前述《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条款》(2009年版)第2条第1项规定,保险标的包括“房屋及其室内附属设备(如固定装置的水暖、气暖、卫生、供水、管道煤气及供电设备等)”,此处的室内附属设备应解释为固定设备,而不包括可移动设施。 (三)语境主义下的探求真意方法 “当语境清楚地表明词句不再具有普遍流行的含义时,这一(优先采用普通含义的)规则就不再适用。”(33)语境主义下的解释规则主要包含如下三项:(1)专业解释。对于具有特定技术含义的词语,可能需要按照专业含义加以理解。采取这种规则的前提是,这种技术含义已经成为行业惯例,或者其他外部证据表明应作此种理解。概言之,语境既可以赋予某个经常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词语以特定的技术含义,也可以剥夺其技术含义,使之回归普通含义。例如,保险单中的“暴雨”时常被界定为气象学上的专业术语,意指1小时降雨量达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达30毫米以上,或连续24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但如果保险人在交易过程中对其作了与普通理解一般的界定与说明,则发生纠纷时应按普通含义解释。(34)(2)历史解释。即应当借鉴合同缔结前的事实与资料以及缔结合同时合同文本外的事实与资料来解释争议条款,如购买保险时的电话记录、保险公司的宣传材料等。(3)习惯解释。即按照保险交易习惯或惯例明确争议条款的含义。总之,要援引语境事实作为解释依据时,主张方应承担举证责任。 (四)目的解释方法的适用领域 目的解释事实上也可归入超脱于文本的语境解释范畴。我国保险法学者多赞同将之引入。但实践中对其的盲目扩张却令人担忧。(35)许多法院将目的解释理解为应对存疑条款作有利于当事人缔约目的实现的解释。然而,被保险人的缔约目的就是获取保险理赔,这意味着若依此规则,一旦发生纠纷,保险人即应承担责任。这显然在利益衡量上过分倾斜于被保险人。保险人自本质而言是风险共同体成员所缴纳基金的管理者,允许保险人为个别成员本不应获赔的损失承担责任,事实上是允许该人从最终归属于全体共同体成员所有的保险基金中不当得利,将其应承担的责任转嫁于无辜的共同体其他成员。因而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发生纠纷时,“彼此应立于整个共同团体之利益之观点……判定双方之权利义务归属,须不时以共同团体内其他成员之利益为出发点。”(36)再者,目的解释方法在技术上也存在困惑。适用上述语义的目的解释不可能在结论上得出两个以上的结果,这将在事实上排除《保险法》规定的不利解释规则。后者依法才应当是判定居于被保险人地位的理性第三人对争议条款理解的终局性规则。因而笔者认为,应将目的限于“设定争议条款的目的”,而非“购买保险的目的”。即目的解释的对象是争议条款或词句,而非保险合同。因为前者可能存疑,使不利解释规则有适用的空间。后者则是清楚和唯一的,没有解释的必要。例如在一个案例中,保单将未依法取得驾驶证、驾驶证审验未合格、依法应当进行体检的未按期体检或体检不合格,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产生的赔偿责任列为除外责任。而根据机动车管理规定,大型客车驾驶员应在每个记分周期结束后15日内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在一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一年内未提交的,注销其驾驶证。被保险人在超出15日、未到1年时发生事故,而后提交体检证明,保险人因此拒赔。被保险人认为,列举上述免责情况的目的在于防范驾驶员在不具有驾驶资格的情况下使用机动车,从而增加危险程度。因此,未按期体检的行为也应导致丧失驾驶资格。即“按期”应理解为一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一年内。保险人认为,约定免责情况的目的,并不是单一地避免驾驶员在不具有资格的情况下驾驶车辆,还应该包括对具有驾驶资格的驾驶员的身体条件的要求,因而“按期”应理解为一个记分周期结束后15日内。(37) 综上所述,在探求理性的被保险人意思的立场上,仍存在文本主义解释与语境主义解释之争。前者在效率与确定性上更具优势,因而应优先适用。文本解释的方法包含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但是,在当事人提出合同文本外的证据证明争议条款具有他种含义时,法院应采用语境解释方法,通过专业解释、历史解释或习惯解释的方法确定其真实意思。至于目的解释,应将其限定于争议条款设定的目的。在文本解释与语境解释之间虽然存在适用顺序之分,但这两类中的具体规则无此区分。因为每种解释方法都可能从其他方法中获得一些要素,它们之间是相互交叉的,(38)例如历史解释方法与习惯解释方法。 三、保险合同解释的继续:不利解释适用范式的规整 当对信赖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的权衡无法确定唯一的解释结果时,效率原则的适用有助于导出最终的结论。这集中体现在不利解释规则的引入。一般认为,不利解释规则是指当格式合同的语句有歧义时,应采取对拟定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39)该规则虽已为各国普遍采用,但各方对其适用范式的争论却从未平息。(40) (一)不利解释适用范式的排列组合 决定是否适用不利解释规则时,首先需要考虑保单用语是否存在模糊性(歧义)。对此,一种标准是仅审视“一个条款可否被视为存在两种以上合理的解释”,另一种标准则审视“保险人是否原本能消除条款含义的不确定性”。(41)依据前者,只要条款存在歧义,法院就应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即便保险人事实上无法合理地削减这种条款含义的不确定性,因而其是一种严格责任。后者不仅要求法院判断条款是否存在歧义,还要求判断保险人是否能更好地对保险条款予以表述。如无此种可能,法院就不应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故其属于过错责任。 适用不利解释规则的第二步是评估被保险人在多大程度上信赖与歧义条款相关的保障确实存在。此处也存在惩罚性与合理性两种标准。依据前者,被保险人有权获取争议条款所涉及的保障,即便绝大多数被保险人不认为存在此种保障(或不愿在保险精算的基础上购买此类保障)。这意味着被保险人无需证明其对获取此种保障存在合理信赖,或者无须证明自己因该条款存在歧义而遭受了损害。它暗含着对保险人控制条款起草权但又未能消除歧义的惩罚。而依据后者,如果该承保事项不是被保险人所合理期待的,则不得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得不利解释规则的适用出现了以下四种可能的排列组合:(1)过失责任与合理性标准;(2)严格责任与合理性标准;(3)过失责任与惩罚性标准;(4)严格责任与惩罚性标准。 上述第一种范式能提供最为明确的规范性指引。它将责任承担与条款完善性结合,向保险人指明了规避自身风险的路径,即尽力消除条款歧义。此外,它还表明绝大多数被保险人希望获取争议条款涉及的保障——即便保险人未就此收取相应保费——进而促使市场着手提供此类产品。(42)但这一组合向被保险人提供的保障程度也是最低的。第二种范式与第一种范式的区别在于,它并不要求调查保险人是否能将保险条款更为清楚、准确地表达出来。采取严格责任事实上切断了条款完善可能性与承保范围获取之间的联系,能够削减条款完善性审查的诉讼成本。第三种范式完全涵盖了第一种范式,并力图在提供完善条款的规范性指引与削减成本之间达成平衡。第四种则是实践中最常见的一类。它最明显的优势是削减了对言语完善可能性与期待合理性的审查成本,因而是一种简单、直接和高效的方法。它还能为被保险人提供最充分的保护,避免其因歧义语言误导而造成损失。此外,它能将其余组合中被保险人面临的无法获得救济的风险全部转嫁给保险人,而后者显然具有更强的风险控制与承受能力,因而更加符合效率原则。但另一方面,这一范式使所有被保险人都能获得争议条款涉及的风险保障,即便绝大多数被保险人不愿购买,或者该被保险人事先也未期待获取此类保障。这将导致不利解释的规范性指引功能无从发挥,贬低了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也有悖于合同解释中的可归责性原理。此时,保险人可能被迫提升保费,甚而认为避免这一风险的最佳途径是将此类条款从保单中剔除。最终的结果是,被保险人必须在付出更多保费购买那些超出其需要的保险产品与无法获得保险产品之间作出两难的选择。 (二)我国法中不利解释适用范式的规整 不利解释规则在国内遭到相当程度的滥用与误用。前者表现为法院在案件不涉及条款内容理解争议之时适用该规则。其中,有的是双方所提交的合同不一致,有的是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承担合同约定之外的损失,还有的是当事人就案件管辖权发生争议。这明显损害了给付均衡原则,威胁到保险营业的维持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也与《保险法》第30条确定的合同解释应以意图探寻为先的规定不符。再者,误用不利解释的情形也相当普遍,表现为一旦被保险人对条款提出不同见解,法院即直接适用该规则,而不管异议是否合理。(43)如前所述,适用不利解释首先应识别保单用语是否存在歧义。这表现为法官从普通理性的被保险人(可归责性标准中处于受领人地位的理性第三人)角度出发认定文本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44)这种模糊性既可以来自于条款词句本身,也可以源于合同的结构缺陷。在此基础上,法院需要决定应否考量保险人的过错与被保险人的意图。这仰赖于对价值基础的权衡。 笔者认为,采用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问题的本质是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均不具有可归责性时如何确定损失风险的分配。此时,保险人的意思自治与被保险人的信赖具有对等程度的正当性。对合同的解释已经脱离了对当事人的意志考察,进入了风险分配领域。效率原则将在此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最终决定无过错责任是更为妥当的选择。一方面,保险人作为专业从事风险经营的商人,较之于被保险人显然具有更强的、对于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仍无法消除的语言歧义风险所导致成本的承受能力。这种成本的施加也不会过分影响保险人改进条款的动力。因为保险人是否已尽到合理的努力去消除歧义,即判断保险人过错的有无并无确定的标准。对保险人而言,将消除歧义的注意义务程度确定在较高水准的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差异不大。况且对风险的识别与控制能力本身即是保险营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通过此项能力的提升,保险人从市场竞争中可获得的利益可能远远大于无过错责任向其额外施加的成本。另一方面,适用过错责任可能导致司法成本的增加。被保险人不仅仅要证明诉争条款合理地存在两个以上含义,而且需提出更适合实现保险人设定该条款目的的替代性表述。保险人则要证明该替代性表述将使含义更加含糊,或其不能与保单上的其他用语和谐并处,从而将法律问题转换成事实问题。这既是一个困难的、成本较高的举措,也必定是一个个案判断的、缺乏统一标准的过程。 在下一层面,法院还需考虑保险人适用歧义条款的行为与被保险人因该条款适用而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的关联性。在合同法语境下,对歧义条款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被视为是向被保险人提供的、对获取保险赔付的期待利益的救济。那么,假如被保险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损失不会获得理赔,立法应否允许作出这种解释呢?持肯定态度学者的理由是,在合同法中,被保险人很难证明自己对歧义保单提供的承保范围存在信赖。(45)但是,通过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移转可以轻易消解前述难题。如由保险人证明被保险人知道自己的损失不在承保范围内,或者绝大多数被保险人在类似情形下并不存在对争议条款所涉承保范围的期待。此时,被保险人的理解与绝大多数被保险人通常合理之理解并不一致,其所主张的解释也与绝大多数被保险人对承保范围的客观合理期待不符。所谓信赖不具有合理性,依据可归责性原理,此时保险人的自治利益显然为优。作出这一选择还有助于控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发生。概言之,笔者倾向于采取上述第二种范式。 综上所述,不利解释的正当性源于效率原则,其本身并非探求真意的方法,而仅具有工具理性之目的与价值,是一种风险分配工具。它仅在探求真意规范无法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时方可采用,是可供依靠的第二位的解释工具。我国《保险法》在2009年修改时对此特别予以明确。因而在适用该规则时,首先需确定诉争条款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释义,保险人不得以自己对条款歧义的存在并无过错为由主张免责,但应允许其以被保险人的期待不具有合理性为由进行抗辩。 四、保险合同解释的终点:基于解释结果的价值评判 保险合同解释的终点是对遵循解释规范得出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确保其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这主要是通过援引作为解释活动价值基础的法律原则来实现的。一是经由规范的逻辑演绎结果存在背离作为推论前提的价值基础的可能;二是主要基于合同法共性解释规范得出的结论必须满足保险营业的特殊需求。此类矫正性原则主要包括给付均衡与合理期待,特别是后者,最集中地体现了基于社会现实的一般公共利益需求。 (一)合理期待原则的制度内涵 保险法上的合理期待原则勃兴于美国。1970年,基廷发表了《保险法中存在的与保单规定相冲突的权利》一文,明确主张保险人不应通过保险交易获得任何不当利益;且投保人与未来受益人的客观合理期待应当得到满足,即使通过深入细致(“painstaking”)的研究发现保单条款其实并不保障他们的期待。(46)之后,多数美国法院都乐于以此“时髦理念”为据作出裁判,希望敦促保险业整体诚实信用地行事。(47)但由于彼此所持的形式主义或功能主义的司法立场不同,导致其对制度理解不一,法官按照自己的认知与意愿演绎出了不同形态的合理期待。(48) 1.弱化版合理期待。即当诉争条款存在两种以上合理释义时,法院应依照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确定含义。这在学者看来与不利解释并无区别,“它是一种假合理期待之名而采取的最为审慎的解释方法。除了提供额外的正当性,即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它等同于不利解释……采用这种版本的州在处理案件时,也完全等同于那些拒绝采纳(基廷提出的)合理期待的州,都主张合同语言对于判决起决定性作用。”(49) 2.折中版合理期待。即在被保险人由于保单语言不明确、保单存在结构性缺陷,或因交易实践而产生了对承保范围的合理期待时,法院应满足此种期待。它的核心目标是确保保单条款与交易程序公平。其主要适用于程序性不公平与结构性不公平。前者是指使被保险人不可能阅读,更无法理解保险语言,从而产生与保单规定相悖的承保期待的情形。如通过自动售卖机销售航空保险和通过电话销售机动车保险。后者是指除外责任条款以较小字体印刷,或未作突出显示而令被保险人难以察觉。保险人则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推翻前述期待:(1)修订保单用语和结构,使期待不再合理;(2)在缔约时采取措施,确保已经就限制承保范围的条款向购买人进行了充分解释。(50) 3.强化版合理期待。其是指当法院认为若严格执行合同条款将导致被保险人(不仅针对诉讼中特定被保险人,还包括绝大多数购买类似保险的被保险人)购买保险的目的落空,或者使那些非被保险人的第三人,如被保险人不当行为的受害者无法得到充分赔偿,则不管条款如何清楚、明确,法院都可否定其效力。这一版本不允许保险人通过解释和修改合同来阻止合理期待的适用。此时,法院不仅关注争议条款的实施是否导致了不公平的结果,还期望充分发挥保险机制移转分散风险的功能,确保受害人获得赔偿。(51) (二)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范式 在上述合理期待含义的各个版本中,弱化版与折衷版均建立在合同文本之上,只不过后者更加宽松,仅仅针对语言晦涩或内容令人惊奇的情形。弱化版合理期待的功能完全可以为不利解释规则中的合理性标准替代。因为特定被保险人实际的主观期待优先于一个假定处于同样情形下的理性被保险人的推定客观期待,故而一个实际了解合同情形、知道自己并未获得特定承保事项的被保险人不能声称自己对获取保障存在合理信赖。此时,可归责性原理要求优先满足保险人的自治利益。而折衷版合理期待也可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所替代。说明义务有助于将抽象无形的保险产品转化成更加直观的、能为当事人理解的普通消费产品,如此一来,一个从保险人处获取充分信息的被保险人将无法证明自己主观期待的合理性。(52) 与那些直接或间接建立在合同文本上因而受其限制的解释工具不同,强化版合理期待能超越具体纠纷,在更高层面上确保基础价值的实现。保险市场的结构性利益失衡使得穷尽一切规则也可能无法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因为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包含假定、处理与后果。对其的援用需满足前提要件。而强化版合理期待使法院可以抛开具体合同条款与当事人具体情形的限制去贯彻与文本规定相悖的司法政策,实现了对作为整体的被保险人利益和保险市场需求在更高层面上的考虑与衡量。(53)其中的合理期待应被视为一国范围内的被保险人的共同合理期待。(54)从长远来看,强化版合理期待还能控制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障水平,将其限制在整个保险行业所能承受的范围内,避免对保险业的财务稳健造成严重影响。例如,法院显然不应受理被保险人对于因空气中PM2.5超标所遭受损害的理赔请求。再者,强化版合理期待也可以指导各个规则的适用,消弭其冲突,因而值得采行。 作为一种矫正市场失灵的司法机制,强化版合理期待主要适用于若司法不施加干预,会导致消费者系统性地缺乏相应保险产品,或者免除保险人责任就个案而言并非不公平,但在保险业整体层面上使保险人攫取了不当利益的情形。前者如在健康保险中,保险人对“疾病”范围的严重限缩与消费者寻求更多的疾病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后者如在被保险人因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人得依据风险不可分原则免除全部责任,而非依比例进行赔付。(55)适用方式是还原合理期待作为指导和矫正规则的上位法律原则的本质,将之视为引导保险合同解释的理念。具体而言,合理期待不仅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真意探求规范,而且在适用顺位上也应居于末位。它应作为保险合同的兜底性条款,仅在穷尽一切手段仍无法达致给付均衡和确保保险产品可获取性目标时方可适用。事实上,基廷使用的“painstaking”一词也表明它是适用顺位最为靠后的解释工具。(56)许多国家已然作出了这一选择。(57) (三)合理期待原则与给付均衡原则的并行 除合理期待原则外,给付均衡也是矫正解释结果的价值准则。可能成为未来欧洲统一保险合同法蓝本的PEICL第2:304条第1款规定:“非经个别商洽确定的条款,如……依据其所属保险合同之特征、该合同中其他条款以及该合同订立时的情形而认定,(条款)导致保单持有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合同权利义务显著失衡,损害其利益,则此条款对保单持有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具有约束力。”此时,应以理性的当事人在缔结保险合同时,如果知道不公平情形之后可能会约定的其他条款来替代前述条款。(58)许多国家的立法中都有此种规定。(59) 虽然给付均衡原则与合理期待原则均力图达成公平的损失分配结果,但二者无法相互替代。首先,给付均衡原则始终关注法院面前的具体当事人的认知能力和对条款的理解。因而对其的援用受到具体案情的限制。其次,合理期待原则还有维护保险产品公共物品属性的追求,因而在某些情形下,即便保险人拒绝赔偿并非不公平,法院仍得依据合理期待原则强制保险人承担责任。(60)最后,二者可作用的范围不同。依据给付均衡原则,消费者可以要求对保险条款的公平性进行司法审查,但这种审查具有局限性,主要是不及于核心给付条款。(61)因为市场竞争机制通常虽不能作用于附随条款,但能作用于核心给付条款,(62)况且各方对核心给付条款的外延存在严重分歧。对此,有英国学者认为:“那些清楚地界定与描述保险合同所承保的风险以及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属于审查范围。”(63)而诸如除外责任与保证这些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都是界定和描述承保风险的,它们在确定保险费率时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其属于核心给付条款范畴。(64)英格兰与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对此也不持异议。(65)但是,“《德国民法典》第305~310条适用于向投保人施加义务的条款,因为这些不属于……界定保险合同核心内容的条款……保险合同中核心给付条款被认为相当狭窄,只有那些简短描述所承保的风险与应支付的保费的条款才属于免于审查范围。”(66)而合理期待原则的审查却不受前述限制。爱尔兰法律改革委员会就指出:“(免于审查的核心)条款必须满足下列两个关键要求:(1)必须以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达……(2)不违背消费者的合理期待。”(67)这种对免于审查范围进行额外限制的做法反映了保险背景下矫正结构性利益失衡、适当倾向于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合理期待原则与给付均衡原则也不会发生冲突。因为原理与规则不同,不是要么充足,要么不充足,而是被期待尽可能地充足。它承认就同一事项而言都具有妥当性的原理之间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互相补充。(68) 五、结语 保险营业的技术特性显示,有必要构建一个相对规范与清晰的、指引保险合同解释活动的框架,以增强解释结果的一致性与可预测性。保险合同解释应在合同法共性与保险法特性维度内的基础价值的共同指引下完成。解释活动包括文义释明与结果校验前后两个阶段。解释体系中的各种方法存在相对位阶秩序,其逻辑上的层级递进可作如下概述:确定居于被保险人地位的理性第三人对诉争条款的理解是保险合同解释的基本方法,对之通常应先作文本解释,次之为语境解释。若仍然存疑,则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在适用不利解释规则时,保险人对存在条款歧义的主观过错无需关注,但被保险人对承保范围的信赖程度却是需要考量的要素。而结果的矫正主要是通过合理期待原则与给付均衡原则完成的。二者居于解释体系的末尾,仅在穷尽一切手段仍无法达致给付均衡和确保消费者可以获取必要保险产品这一公共政策目标时,方可适用。 注释: ①See Robert H.Jerry Ⅱ,Insurance,Contract,and the Doctrine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5 Conn.Ins.L.J.55(1998). ②参见杨小勇、李晶雪:《保险的法律困境与出路》,《法律适用》2008年第1期。 ③例如,在杨树岭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宝坻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中,一审法院无视合同中对家庭成员含义的明确界定,以家庭成员和亲属具有法定含义,不包含来与当事人登记在同一户籍内的直系血亲为由、认为原告之母不属除外责任中的家庭成员。参见《杨树岭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宝坻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11期。 ④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89页;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37~538页。 ⑤See David S.Miller,Insurance as a Contract:The Argument for Abandoning the Ambiguity Doctrine,88 Colum.L.Rev.1849(1988); Raoul Colinvaux,The Law of Insurance,Sweet & Maxwell,1984,p.32. ⑥参见叶金强:《合同解释理论的一元模式》,《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2期。 ⑦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5页。 ⑧同前注⑥,叶金强文。 ⑨参见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第1册,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78页。 ⑩参见叶金强:《私法效果的弹性化机制——以不合意、错误与合同解释为例》,《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1)对受领人信赖的保护同样可转译为对自治的尊重。因为保护信赖表现为依照信赖者通常合理之理解来解释合同,而谨慎的信赖者的内心意思会与该理解一致。此时,其自主选择意义上的自治就得以实现。故当事人间的对抗实为各自自治利益间的对抗,按照何者的意思来解释合同,决定着谁自主选择意义上的自治可以得到实现。 (12)同前注⑩,叶金强文。 (13)如德国法中著名的“菜单案”,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2页。 (14)同前注④,李永军书,第548~549页。 (15)参见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16)田玲、徐竞、许潆方:《基于权益视角的保险人契约责任探析》,《保险研究》2012年第5期。 (17)严格来讲,应当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缔结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但被保险人与投保人时常为同一主体,在财产保险中更是如此。因此,英美法系保险法通常用被保险人指代投保人,而对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情形作例外规定。当然,这一做法也与早期的保险合同皆为为自己利益合同有关。为便于论述,本文也将遵循这一做法。 (18)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的整个意义脉络、双方共同承认的合同目的以及双方共同想象的合同利益状态”。它内含的是全部的法的价值,是一项技术性原则,而非价值性原则。因而本文未将之列入解释原则。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0页。 (19)同前注④,李永军书,第549页。 (20)参见樊启荣、王冠华:《保险格式条款“通常理解”之解释——以我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为中心》,《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6期。 (21)See Nicholas Leigh-Jones,John Birds and David Owen,Macgillivray on Insurance Law,Sweet & Maxwell,2008,p.293; [美]小罗伯特·H.杰瑞、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李之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邹海林:《保险法教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22)See Peter Nash Swisher,A Realistic Consensus Approach to the Insurance Law Doctrine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s,35 Tort & Ins.L.J.729,747-758 (2000). (23)参见刘承韪:《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以英美契约法为核心的考察》,《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 (24)See John E.Murray,Jr.,Contract Theories and the Rise of Neoformalism,71 Fordham L.Rev.869 (2002). (25)See Shawn J.Bayern,Rational Ignorance,Rational Closed-Mindedness,and Modern Economic Formalism in Contract Law,97 Calif.L.Rev.943 (2009). (26)参见周建涛、博科、周明生:《法院审理保险合同案件的两种解释方法比较》,《保险研究》2009年第1期。 (27)See Alan Schwartz & Robert E.Scott,Contract Interpretation Redux,119 Yale L.J.926 (2010). (28)See David Charny,The New Formalism in Contract,66 U.Chi.L.Rev.842(1999). (29)同前注⑤,Raoul Colinvaux 书,第32页。 (30)参见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31)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18271号民事判决书。在本案被保险人行车时,车沿坡路滑下落入河中。保险人以坠落仅指垂直降落,不包含倾斜角度下落为由拒赔。 (32)同前注(22),Peter Nash Swisher文,第740~741页。 (33)同前注⑤,Raoul Colinvaux 书,第32页。 (34)同前注(21),Nichotas Leigh-Jones、John Birds、David Owen书,第300~301页。 (35)同前注②,杨小勇、李晶雪文。 (36)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37)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 (38)参见[美]肯尼思·布莱克、哈罗德·斯基博:《人寿与健康保险》,孙祁祥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39)参见孙宏涛:《保险法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北方法学》2012年第5期。 (40)See James M.Fischer,Why Are Insurance Contracts Subject to Special Rules of Interpretation?:Text versus Context,24 Ariz.St.L.J.995(1992);曹兴权、罗璨:《保险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二维视域——弱者保护与技术维护之衡平》,《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 (41)See.Jeffrey W.Stempel,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Law and Strategy for Insurers and Policyholders,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4,p.186. (42)See Owens-Illinois,Inc.v.United Insurance Co.,650 A.2d 974(N.J.1994). (43)通过“北大法宝”检索可知,在2009年至2011年间,共有57件案件涉及不利解释规则。被保险人胜诉的有47件,占82%。其中,不涉及条款理解争议而涉嫌滥用的有30件,占64%,其余17件中也有13件存在误用。典型案件参见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平民三终字第628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2009)临民初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0)杭萧商初字第2150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0)芷民二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书。 (44)See Kenneth S.Abraham,A Theory of Insurance Policy Interpretation,95 Mich.L.Rev.546(1996). (45)同前注(44),Kenneth S.Abraham文,第531、536页。 (46)See Robert Keeton,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s(Part Ⅰ and Ⅱ),83 Harv.L.Rev.963,976(1970).该原则对普通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学者也纷纷主张引入此一制度。参见孙宏涛:《保险合同解释中的合理期待原则探析》,《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樊启荣:《美国保险法上“合理期待原则”评析》,《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李利、许崇苗:《论在我国保险法上确立合理期待原则》,《保险研究》2011年第4期。 (47)See Kenneth S.Abraham,Judge-Made Law and Judge-Made Insurance:Honoring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67 Va.L.Rev.1151,1153(1981). (48)See Mark C.Rahdert,Reasonable Expectations Revisited,5 Conn.Ins:L.J.107,112-114(1998). (49)See Stephen J.Ware,A Critique of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56 U.Chi.L.Rev.1468 (1989). (50)同前注(48),Mark C.Rahdert 文,第113~114页、第128页。 (51)有观点认为,合理期待造成了裁判结果的不确定,对保险人精确测定承保风险水准造成了困扰。笔者认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合理期待的规则化”,即法院将之作为优先适用甚至唯一适用的解释方法。而作为原则的合理期待的例外适用所引发的不确定是极为有限的。再者,确定性的追求不应被赋予绝对意味,利益的衡平要求同时关注被保险人的诉求,而给付均衡原则无法完全达致前述目标。况且,通过保险机制分散风险并向受害人提供赔付也是必须考虑的价值目标。因而合理期待有必要以矫正原则的面目继续存在。这也是多数美国学者的观点。See Kenneth S.Abraham,The Expectations Principle as a Regulative ideal,5 COnn.Ins.L.J.64 (1998); William A.Mayhew,Reasonable Expectations:Seeking a Principled Application,13 Pepp.L.Rev.270 (1986); 同前注(22),Peter Nash Swisher文,第729页。 (52)同前注(41),Jeffrey W.Stempel书,第321页。 (53)同前注(40),James M.Fischer文,第1004页。 (54)See Robert E.Keeton & Alan L Widiss,Iusurance Law:A Guid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Legal Doctrines,and Commercial Practices,West Publishing,1988,pp.617-618. (55)See John Lowry,Whither the Duty of Good Faith in UK Insurance Contracts,16 Conn.Ins.L.J.97,115 (2009).不实告知固然使保险人无法精确地承保特定风险,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存在不实告知的投保申请都是不可承保的。每一个因重大过失而实施不实告知的被保险人也并非都会提起索赔,例如当保险事故未发生时。因为其不存在骗取保险金的意图。在事先无法确定不实告知的被保险人会否遭受损害时,事后行使解除权的自由使保险人可以保留那些未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同时拒绝向遭受损害的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进而在整个体系层面合法地获得了超出其损害范围的补偿。 (56)同前注(22),Peter Nash Swisher 书,第733页。 (57)See C.Brown,Insurance Law in Canada,Thompson Carswell,2005,pp.8-12. (58)See Jürgen Basedow,Project Group "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Th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 (PEICL),European Law Pub,2009,p.118. (59)See Hugh Collins,Harmonization by Example:European Laws Against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47 Mod.L.Rev.147(2010). (60)同前注(47),Kenneth S.Abraham 文,第1184~1185页。 (61)See The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cottish Law Commission,Consumer Insurance Law:Pre-Contract Disclosure and Misrepresentation,December 2009,p.48. (62)参见[日]石川博康:《契约的本性的法理论》,有斐阁2010年版,第28~29页。 (63)See The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cottish Law Commission,Insurance Contract Law:Misrepresentation,Non-Disclosure and Breach of Warranty by the Insured,A Joint Consultation Paper,June 2007,p.44. (64)同前注(21),Nicholas Leigh-Jones、John Birds、David Owen书,第244页。 (65)同前注(61),第47~50页。 (66)See Rühl,Common Law,Civil Law,and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for Insurances,55 Intel.Com.L.Q.879 (2007). (67)See The (Ireland) Law Reform Commission,Insurance Contracts Consultation Paper,December 2011,pp.145-146. (68)参见解亘:《格式条款内容规制的规范体系》,《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标签:保险合同论文; 保险法论文; 合同条款论文; 合同风险论文; 技术合同论文; 保险价值论文; 合同目的论文; 信赖利益论文; 法律论文; 契约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