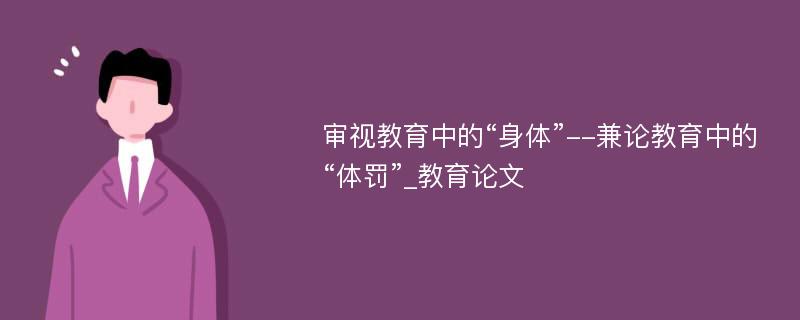
审视教育中的“身体”——兼论教育中的“身体惩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06)03-0009-06
在论及“教育的人的制约性”或“教育必须适应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时,一般探讨的都是人的“心理”发展对教育的影响,“身体”并没有真正进入教育理论的视野。身体在教育理论中本应该具有更基础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人的身体,人的自然性、生物性,本来应是教育的出发点与基础,但在教育理论的探讨中却不断地遭遇到了尼采意义上的“遗忘”而退入到了教育活动的幕后,成了存而不论的背景。教育学对人的身体的关注,正是将人的动物性存在从形而上学的理性中唤醒,是对人作为一种完整性存在的正视。第二,教育中的诸多问题都涉及到人的身体,但人们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教育理论研究无法回避身体这种教育的基本前提与重要内容,教育通过引导人运用身体,使社会性身体与生物性身体相互调节、修饰与形塑。第三,身体是最真实的存在,排斥身体及其感觉的教育,绝不是完整的人的教育,甚至可以说是虚幻的教育,因为它无视个体的真实性——“我的本质主要取决于我的特殊身体,这个身体同其他社会表现者的身体不同。”第四,随着“身体”成了反思传统观念、传统思维方式的最重要的突破口,“身体”也成了反思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理想的一个基本范畴,通过审视身体在教育中的地位与意义,可以寻求到身体的那种既抽象又具体、既冲动又沉寂、既顺从又反抗品性的教育学意义。第五,提倡身体视角的教育研究,并不是要对传统教育进行颠覆,而是进行补充,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和谐的完人教育,并为构建一种以“身体”为核心概念的“体”“现”教育学及其实践意义。
一、“匮乏”的身体与教育的可能性
1.人的未完成状态与教育的保护性
人的未完成状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一,人是“早产儿”,人在尚未完成的时候就提前来到世界。人最重要的未完成,就是脑的未完成,新生儿的脑只达其成年时期的23%。其二,人是一种本能匮乏的生物。动物的生命由其生物组织及其机能所规定,特定的行为方式和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性是动物生命的秘密——“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人则因“发育不全”而成了“易遭危险的生物”。教育存在的理由,其一就是给过早来到世间的人提供一个生长、生活的环境。教育所提供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环境的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养成人的群居的习性和与人打交往的惯习,并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群体的力量。其二,教育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活动,它实际上进行的活动是把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整合到大脑中,实现脑和文化相互印刻,从而进行文化再生,使文化亦获得某种意义上的“遗传结构”。其三,在任何历史形态中,教育的直接目标就在于培养人的生存能力及如何更好地生活的能力。
2.人的未特定化与教育的双重解放
动物器官的结构及其机能能适应特定的生活条件,这种专门化、特定化的效力和范围就是动物本能的集中表现。而对人而言,自然没有规定他应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茫然不知所措——尼采所说的人是“尚未被确定的动物”,指的就是人是一种未特定化的存在。这是人在生物学上的一个缺口,但正是这个缺陷便成了人向世界开放、使人成为“有活力”的生物学的基础。
“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就是学生的可塑性。”——人的可塑性,这是教育的前提。人的可塑性就来自于人的未特定化。人的未特定化意味着教育使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走向文化。文化规定了人应该做、可以做些什么,文化的教育学意蕴就在于通过教育给人“卸载”——作为开放性存在的人,必然处于极度的超载状态,因而,追求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存在状态的人,从一开始就必须学会如何有效地在集体中生活,从而为自己卸载。动物的自我完善实际上就是一种“充盈”的自我封闭,而人的开放性,则使人处于一种可能性世界的“虚空”状态,因而,人可以进行自我造就。
另一方面,人的自我造就则正是使人走向封闭性的起点。人在解放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远不止是补偿了其“匮乏”,“智人”在运用其理性的过程中,逐渐要求“为自然立法”,人在宇宙中的连续性被隔断了。因而,教育必须要使人从自我造就的封闭中解放出来,重新走向开放。在教育中重提生物性,就是要使人意识到人与世界的同源性、同质性与统一性。同时,教育应使受教育的人都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黑格尔称教育的绝对规定就是解放,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真是睿见。
3.幼态持续与教育的保护性
缓慢的身体发育是人的生长过程中的一个特点,生物学上称之为“幼态持续”。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儿童本身所获得的就是人类情感的保持、深化与扩散化。种种诸如爱、依恋、友谊等原始感情都应成为教育的条件,也是教育应予以保护的珍贵的人类财富,这些在儿童的教育世界中应得到展现与重视。漫长的身体发育期的教育是形成个体的“历史性”——对人类文明与文化历史性的继承及自我的历史性的形成——的重要基础。儿童在此期间可以学习传统、智识与技能,接受文化的陶冶,并形成个性。通过自由的教育,对儿童个性发展的保护,是为了实现文化的复杂性与个性的差异之间的相互锁定与共同促进。教育的个性化不仅仅具有个人意义,亦具有社会学与人类学意义。这一过程之后,人将是“通过自然形成的文化生物,因为他是通过文化形成的自然生物”,这是一种互融。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社会文化选择所确定的内容,在适应儿童的身心生长的节奏与规律的前提下引导、帮助儿童生长并走向成熟,这一阶段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斯普朗格所说的“对发展的援助”。在此过程中,家庭教育非常关键。但令人遗憾的是,家庭教育的地位正在削弱,有意识、有效果的家庭教育越来越少。事实上,家庭教育无论在儿童的精神世界、身体发育、社会化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高素质的母亲是儿童发展、甚至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庞贝夫人对拿破仑“法国最缺少什么”的回答是“母亲”,高素质的母亲!
二、教育传统中身体的缺席与功用化
1.“扬心抑身”的教育传统
从总体上说,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扬心抑身”的思想基调、价值取向与二元的方法论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成了西方教育最重要的思想与世界观基础。在教育中的表现即是:注重的是人的灵魂、精神、理性与神的信念,人的感官、肉体、欲望本身是不受重视,甚至是受压抑的。而重视道德、理性(与知识)及神性的塑造,便都是“心”的表现。尽管在古希腊时曾发生过道德素质和理智品质的转换,但教育总是属于精神性的事业。
教育在于培养德行。苏格拉底强调“美德即知识”、智慧即德行,教育首要任务就是培养道德,而自制是“一切德行的基础”;洛克认为绅士最重要品行的顺序是德行、智慧、教养和学问。他的一个关键词汇“训练”同时适用于身体与心灵:身体的锻炼被用来增进儿童体质,并使身体处于精神的绝对控制之下,所有的欲望与动机都应服从于理智。赫尔巴特则认为,“教育的惟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要养成内心的自由、完善、仁慈、正义与公平的信念。教育在于发展理性。在理性人类学看来,只有理性才是使我们成为人,人的真正特殊性在于他的理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康德、启蒙理性及现代科学主义教育,无不体现了教育对理性的追求。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灵魂转向”。亚里士多德那儿,强调健康、健全的身体,目的是要产生一个健康的身体以健全清醒的头脑。笛卡尔尽管他承认身体比任何其他物体“更真正、紧密地属于我”,但“我思故我在”的“我”是灵魂的“我”,“我”可以无头而存。康德所发出的启蒙理性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科学主义教育更是注重理性之心的教育。
教育在于培养对神的信念。源远流长的犹太教基督教禁欲主义思想,加上一千多年的教会控制教育的历史事实使得“原罪”观念深入人心,身体的禁欲苦行成了获得救赎的最重要的工具与途径。禁欲主义与笛卡尔的世俗理性主义二者是相互印证的,有着某种文化相容性。禁欲主义的作用在于把灵魂从身体设置的诱惑当中解放出来,那种诱惑源于人类身体体现的局限性,对身体的约束和戒律其目标在于“创造和建立免受身体感官奴役灵魂或精神的自由。”宗教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教育给信仰带来便利,而不是为了知识与真理,于是,教育把普通知识限定在它的兴趣和教义固定范围内,人们随时准备接受教会的权威解说,“当教育没有把我们引向真理时,则必须使我们易于接受由教会解释的真理。”
2.教育中的功用性身体
教育就算是重视身体,也只是重视身体的功用性,而不是重视作为本体的身体,不重视身体的自我享受与自我呵护,从而不能使人在最真切的意义上感受到自我。
“战斗”的身体。训练(教育)新生一代谋生,这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一项事务。首先,通过教育的身体训练是为了生存。斯巴达教育的全部特征是由追求军事效力的愿望决定的,斯巴达人实行严格的体检制度就是为了提供优秀的军士苗子;女子教育一方面是为了生育健康的子女,另一方面是为了防守本土。其次,身体训练是为了表演与娱乐。如骑士七技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于是,身体教育要么是生产性的,如竞技体育的过度表演性,实际上是“战争”的转移;或者是消费性的,如健美。
认识论中的身体。在教育史上,不乏关心人的身体,人的感官者,如洛克、卢梭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者们,他们相信科学,强调人的感官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就是因为知识来源于感官。洛克强调,“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知识归根到底导源于经验”,而感觉经验是认识的第一步和第一阶段;卢梭强调通过个人的感觉经验去认识外界事物,目的在于避免盲目服从传统偏见和权威,并在教育史上首次详细论述了如何训练儿童的感官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艺术的极大发展,促使教育开始关注人的感官与身体的教育。
“礼乐教化”:承载社会秩序的身体。“社会‘秩序’问题最终取决于身体顺从与逾越的问题”,那么,社会传统如何在个体身上烙下印记?基本途径就是“社会记忆是与身体实践分不开的,社会通过身体实现记忆”。在古代,最重要的教育方式就是年轻人进入成人集团的纳入仪式:以稳重的行为规范来尽早地教导青年一代。这些仪式针对的都是身体:在隔离生活期间,要经受的严酷考验主要是身体的,如冲浸、禁食、鞭身、敲牙、断指、割礼等,对身体的这种规范就是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中国传统社会“教化”的实质就是“由礼而走在仁的途中”,而“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身体的不同安置来表现了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中国人的‘身’是由人伦与社群的‘心’去制约的,因此,‘个体’并不是自己‘身体’的真正主人。”这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气质的影响是直接的,因为一个人“是否激进的实质在于身体的激进;是否激进的实质是自身存在的激进性”。于是,身体的教养就成了文明的标志,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身体行为来表现的,而此时,“身”实际上就已经受到了“心”的“照顾”。
身体惩罚与教育的合法性。在传统教育中,东西方都非常强调借助于身体的强制技术,如体罚,这种赤裸裸的权力运用,从而确保教育的效率。尽管体罚有可能暴露教育活动的权力运作的实质,但由于教育本身的权力运作的隐蔽性,反而强化了教育本身的合法性。于是英国学校的九尾鞭、小学教师的棍子或古兰经教师的长把尺子、中国的“夏楚二物”都成了教师合法地位的象征。通过权力运作,教育中暴露出的权力关系反而成了合法化的象征。
三、教育的格局与体育中身体的失真
在论及教育时,人们习惯把德智体美四育并论,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模糊。王国维所倡导的“完全之人物”的教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逻辑描述:教育包括培养身体之能力的体育与培育精神之能力的心育,而心育又可依西方心理学知、情、意的三分法分为智育、德育、审美教育。从形式上看,身体之教育“势单力薄”,但在其他几育中也在进行着身体的教育。如智育中认识论的身体,德育中“发乎情性,止乎礼仪”、审美教育中注重审美感受,注重培养“有音乐感的耳朵”和“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都是在进行着身体的教育。在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体育也并不是身体教育的全部,体育是“根据人体适应与变化的自然规律,有意识地用人体自身的运动来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的科学方法,是社会的一种文化教育活动。”而身体教育则可以包括生理学知识的教育、性教育、健康教育等方面内容。但以增强体质为本质的体育是身体教育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其目的在于促进身体的成长与保养。但令人担忧的是,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出发点不再是身体,其目的也不再是保养健康与身体的自我享受,而迷失了其方向。
不说竞技体育是一个不科学的名词,起码它是一个成问题的概念,因为现今竞技运动中的教育意义已远远未及其经济意义、意识形态意义,我们倒宁愿直接称它为竞技运动,即应把作为教育的体育与作为表演与竞赛的运动分开来看,不能因为他们都使用了身体而混淆二者。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主要已不在身体方面了,而在于民族精神、国家伦理与商业利润:在各类赛事中,种种幕后交易丑闻不时暴光;团队精神进一步加强,领跑屡禁不止,花样翻新重出;对冠军及破纪录者的重金“悬赏”及在世界媒体露脸与被炒作机会增多所引起的广告效应,诱使运动员不断地冒险服用兴奋剂。“那些体育明星再也不愿在比赛中拿他们的名声冒险,以维护自己的金钱价值,它也成为事前协商好了的运动。”在竞赛中富有教育意义的公平、友谊等高尚风格与运动精神已黯然失色,“教育”缺席于竞赛运动之中,因而,此种竞技体育已不再是体育了。
学校体育是最应具有身体关注的身体教育形式。但学校中的体育目前也发生了一些偏离现象值得引起注意:一是体育成了为智育服务的补充;二是体育过程中的竞技化。在扬心抑身、身心二分的教育传统中,人的智慧被认为源于灵魂,因而教育重视灵魂而轻视身体;随着科学的发展,脑成了智慧与学识的来源,于是开始注重脑功能的开发,智力成了教育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而劳逸结合、有张有弛成了智力发展中必要的措施,在此情形中,锻炼身体的目的就在于保证旺盛的脑力,体育就成了服务于智育的调节剂。学生的课间体操的目的只有一个:有了好的身体才能使学习有保障。身体本身的健康却没人关注了。指导这种教育观念的仍是那种身心二元的世界观。另外,学校体育的竞技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体育以健身为本,是要实现学生的身体合于生理的生长,并振作学生的精神。学校体育的竞技化一方面使学生注重动作的标准化,另一方面使学生只关注胜利。蔡元培先生针对这种现象的评论既形象又深刻:“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上有妨害,且成了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体育的价值了”;在心理上亦受到恶的影响,“胜者,于己骄矜,于人蔑视;负者,于己愧恧,于人忮忌”,这些都是恶德。因而,学校体育应使“学生彻底明白体育的目的,只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不是在比赛争胜上”。当然,这并不是说体育中不要竞赛,但体育中的竞赛不能抹杀其游戏性质,学校体育中的竞赛更应是一种轻松的游戏,体育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那种综合性的“乐”。
大众体育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才是真正的体育,在此,人们以健康、以增强体质为目的。全民健身运动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教育形式。SARS的肆虐更加增强了这种形式,这是来自具有复杂性自组织特征的自然意志的教育,这种生物性的追求似乎比人类有意识设计的说教更见效果。值得强调的是,大众体育更具有游戏的性质。人们在游戏中轻松地嬉戏,自娱地对抗,身心投入而又身心放松,真是怡然自得,这才叫生活世界。当然,大众体育中也有竞赛,但这种竞赛并不以输赢为目的,竞赛的人本身也不受输赢所累赘,只是娱乐而已!体育除了回到游戏,回到体质以外,似乎还可以回到最早使用“体育”一词的卢梭时代。卢梭认为人的所有的官能中,理性是最后发展的一个,因而,如果像以平常的教育所做的那样,无异于教育是从终点开始;而首先成熟的官能是感官,首先就进行感官的锻炼。卢梭倡导在儿童期进行“消极教育”的理由就在于此。适合儿童期的正确的教育是通过身体的活动。尽管卢梭说,“要学会思考,就需要锻炼四肢、感觉和器官,因为它们是智慧的工具。”因此,教育不仅是感官训练的工具,进行感官训练的同时也是在进行判断力的培养,是在进行思想免疫力的陶冶。卢梭给我们的教导是:体育绝不仅仅是体育,同时亦是身体智慧的训练。
四、被规训的身体与教育中的身体惩罚
1.体罚的是是非非
目前很多国家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禁止体罚,如英国、法国等,一般而言,“体罚”在教育学领域及社会科学领域内都是一个贬义词。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体罚应该被禁止,而惩戒应保留,但由此而引起的关于体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鉴于本文的基本意图,即重新思考身体的教育学意义,因而,我们首先对“体罚”进行还原,即在“身体惩罚”这一中性意义上理解“体罚”,并思虑身体惩罚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第一,教育中的伤害:来自身体的与来自心理的。一般认为,体罚指的是对学生给予身体上感到痛苦或极度疲劳的惩罚,并造成学生身心健康损害的侵权行为;而惩戒是指“施罚使犯过者身心感觉痛苦,但不以损害受罚者身心健康”为原则的一种惩罚方式。体罚和惩戒都涉及身体,二者的区分就在于一个“度”:体罚损害了受罚者的身心健康,惩戒越过了度就是体罚,就违法,因为它造成了事实的身体伤害。
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动机上,教师并不是虐待狂,也不是变态狂,因而,对学生的体罚绝对不是以“损害受罚者的身心健康”为目标的。因而,应该把体罚和故意的身体伤害区分开来。且不说把变相体罚中的一些诸如“心罚”的内容归诸于体罚是否合理,单就不涉及身体的惩罚与体罚谁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而言,现在的口号是“心罚甚于体罚”、“语罚猛于体罚”,谨防教育中的“软暴力”等,似乎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体罚是否造成身体或精神上的民事或刑事责任,应该由相应的民法或刑法来裁定,即教育中体罚的度已有法律进行认定,教育中实在没有立法禁止的必要。现在我们把“法”看成了解救不完善的根本性力量,动不动就要立法,法制成了惟一的希望,但我们是否理解哈耶克所作的“法治”与“法制”的区分的真正意蕴?
第二,一无是处的身体惩罚?尽管体罚属于违法行为,但在教育实践中,体罚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是少数,但总有部分学生、家长、教师对体罚是认可的。当然,正如一贯强调的,不能用事实的“证明”来代替“缘何”的合理性的解释,但这种理论与实践中的差距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体罚或许只是学术团体之间的一种抽象争议,但却给教师与家长的教育实践出了道难题。在对教育的人文性的强化过程中,在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的反复宣讲中,教育对儿童的态度就只能是人道主义式的爱护。于是,家长们被震住了——体罚孩子的家长被认为是失败的家长;教师们同样也束手无策,问题并不在于教师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管理教育学生,而在于学生们的有恃无恐与嚣张;也不在于这种嚣张对师道尊严的打击,而是实在已经涉及到了人格的侮辱。教师们的权利谁来保障,因为我们是教育者,我们就得用我们的权利与尊严为代价去培养、教育、感化他们?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认为,如果在正常的家庭与学校教育场合中,体罚适时、有度、有据、有情、得法,会使孩子更好地受到教育。这其实也是很多家长与教师内心里的想法。对于体罚的夸大其辞的结论,如“会使孩子成为狂暴易怒的孩子”、“会使孩子郁郁寡欢、野蛮粗鲁”等,美国儿童科学研究院作了低调处理,1996年的一次关于惩罚的研讨会上,主持人斯科恩伯格教授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一个家长轻视孩子的长大会成为罪犯,或成为愤世嫉俗的暴徒。这也是美国部分州没有进行立法禁止体罚的重要原因。
第三,体罚的传统。体罚的生命力亦来自于体罚的传统。象形的“教”字就意味着教育中身体惩罚的伴随性质,在《学记》中亦有“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说法。传统教育中最具有体罚象征意义的就是先生手中的戒尺(又称戒方),当然,体罚对孩子的伤害程度并不严重:“轻则学长以戒方打掌,重则罚跪于圣人前”,这在强调师道尊严的儒家传统中,应该是一种很文明也很科学的处罚方式,跪于圣人前意味着师道尊严的重塑,而打手掌(现在家长常打屁股也一样)则起到了疼痛刺激但又不伤人筋骨的教训作用。西方教育亦有体罚的传统,如斯巴达、雅典的教育中就很明显。但体罚最严厉的要数教会教育时期,这与宗教的原罪观念与救赎观念有关,因为欲望的身体偷吃了知识之树上的智慧之果,对身体的责罚自然就成了解脱的最重要的方式,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就是榜样。奥古斯丁允许把鞭笞作为一种刺激因素和驱逐邪念的手段,鞭笞纪律是获取知识和增长才智的方法,各种戒律须靠鞭笞打入他们的记忆和品德之中。体罚的教育传统肯定有其合理性,至于这种合理性的条件与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还存不存在,这就要具体分析了,但从教育实践来看,似乎体罚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其合理性,其中最深层的原因可能就是人性的因素了。
2.再思身体惩罚
学校中的惩罚很多都是直接以身体为对象的,不以身体为对象的也有很多顺便“劳其筋骨”,因而,身体惩罚在教育中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第一,反对身体惩罚,本身就是扬心抑身的传统的体现。身体在扬心抑身的教育传统中没有合法地位,只有工具或功用性价值。通过身体本身的教育来达到设想的教育目的,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现代教育也倡导这种“心育”,要通过观念、知识、说服等来进行教育才是真正的、有效的教育。通过身体惩处进行的教育似乎只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因而,身体规训在教育中是个贬义词,但福柯的研究给我们的身体规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教育人学的身体视角已向我们打开了身体规训与身体教育的积极作用。
第二,身体惩罚是惩罚序列中的一级。现在的家长并不是不懂教育儿童,他们知道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倒可能是只从人道主义、哲学或精神分析的思想家们忽略了现实中的真实的儿童。家长、教师们首先“劝”,进行说理,对儿童进行遵守契约的教育——接着再“哄”,也可以说是“求”——接下来就“骗”或“诱”,如以好吃或更好玩的进行引导——再不成就“吓”,对儿童进行威胁,如不让儿童干他想干的事——最后一招,“揍”,运用武力直接解决当下的难题。如果从学理上来讲,这种惩罚序列就表现为:说服—诱导—合格权威—合法权威—武力的威胁—武力,其中隐含着的就是权力的公开程度以及对权力的反叛程度。当所有的惩罚手段都不能解决问题时,有必要使用武力。尽管使用武力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是一种暴力,它的行使意味着权力关系的彻底破灭,但同时,它又重建并巩固了这种权力关系,并通过武力摆脱了既有的不得不破灭的权力关系。因而身体惩罚从权力体系来看是不能取消的,体罚的消逝意味着权力体系的崩溃。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洛克尽管批评了文法学校中的体罚传统,但亦认为:鞭笞是最坏的一个,因而也是最后的一个教育方法。当然,作为惩罚序列最终端的身体惩罚,只能“偶尔”为之;而且还得注意度:身体惩罚的限度就在于身体惩罚不能演变成身体暴力,否则就构成犯罪。
第三,禁止身体惩罚的人性悖论。惩罚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必要的秩序,而教育中的种种秩序基本上都是在自然基础上设计与衍化的,因而这里必须考虑休谟所提出的政治制度设计的最基本的原则:无赖原则,即“把每个人都当作无赖”,这一方面是从可能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另一方面则亦是对人性本恶的肯定。身体惩罚作为最后教育的一道防线与保障,在维持教育秩序中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而禁止体罚的前提预设是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显示的是对作为“人”的儿童及其权利的尊重,相信儿童潜在的人性本善。因而二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人性可能有善恶二端,但恶的一面对于善的一面具有优先性,这可通过权力对于权利的扩张性能证明这一点。因而,要调和这种紧张,惟一的策略就是承认身体惩罚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第四,当众的身体惩罚具有生产性。一般认为,身体惩罚是一种否定性行为,即对违纪者本人进行一种制裁与补偿;但身体惩罚又不仅仅是一种终止孩子不端行为的非口头方式,当众的身体惩罚有些像福柯所讲的是一种仪式,在此过程中,身体惩罚进行着生产,即生产出一种符号,使“违规—惩罚”这一观念偷偷溜进每一个学生的大脑,从而产生了防范性的预防作用。于是,每一次身体惩罚就成了一则寓言故事,这可能是纯道德的功利,但亦是更现实的功利。事实上,在学校中,使用更多的也是这种身体惩罚的象征意义及由此而产生的身体惩罚的威胁,而不是具体的、真实的身体惩罚。在这一点上,应该记住涂尔干忠告,对惩罚的恐惧并不是惩罚的主要理由,惩罚的本质功能不在于赎罪,也不在于恐吓,而在于维护良知,在于产生对正当规范的敬重。另外,罚学生值日、扫地、劳动等,刚好吻合了福柯所称的惩罚经济学性质与追求,这种身体惩罚在进行着另一种生产,即“生产性劳动”,用这种“生产性劳动”来代替纯粹的身体惩罚,不知是不是一种进步?
第五,身体惩罚使学生本人通过其身体而成为真正的责任承担者。在“你认为哪些行为属于恰当的惩戒范畴”的调查中,家长所赞同的前三位分别是:口头警告处分;向同学或学校道歉,甚至罚款;增加作业量。暂且不论增加作业量属不属于变相的身体惩罚,在这里,主要是想针对罚款作一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学生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针对学生的罚款肯定会发生转移,转移到家长身上还是好事,若转向其他渠道则可能会令所有的人担心。如果家长向学生提供这种罚款,不知这是不是在纵容自己的孩子?尽管家长可能会很生气,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教育,但不知采取何种有效的方式?可否把这种经验向教育界给予反馈,并借鉴?做错了,就应该承担后果与责任,但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能支配的、能用以承担后果最真实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就是他们的身体。可能这种“切肤之痛”才能让儿童获得最明确的责任意识。当然,这并不是倡导身体惩罚,而只是进行分析。或者说,只是提出身体惩罚作为终端而存在的可能性。
第六,教育可能管得太多,导致身体惩罚的概率增多。教育中纪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教育正当运行的秩序。打个比方,学校中的纪律应该如同现在所倡导的国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作用一样,只是作最低限度的秩序维持,其余的事交由自由竞争去完成。现在教育中的很多身体惩罚,是因为学生没有完成家庭作业,或者作业做得不对,或者考试没有考好而发生的,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教育管得太多了,尤其是在学生的学业上。教育中的纪律与惩罚应把注意力放到学校秩序、教育秩序的维护上。这并不是说不注重学生的学业成就,而是说要通过有效教学与引导,把学习交给学生自己,通过学生学业之间的竞争来促进学生学业的进步。现代教育承载的责任实在太重了,人们对教育期望的太多了,教育也自我陶醉了,于是行为就出格了,这真是“恨铁不成钢”!当然,教育可以通过奖赏、激励等方式进行引导,可以在学生需要的时候应提供帮助,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教育促进每个学生最大程度的发展,通过的主要途径就是竞争,而不是教师对每个学生进行全面的干预,这是微观教育实践中的“政府行政模式”。而且,也正是在“竞争最大化”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实现学生的自由发展与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