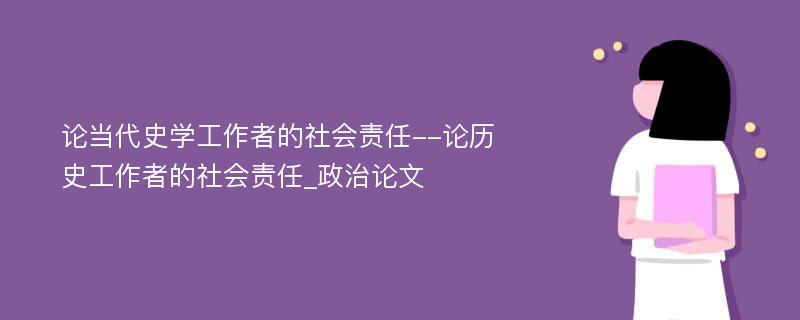
“当代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笔谈——再谈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工作者论文,责任论文,社会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应《历史教学》之邀,笔者完成了一篇访谈录:《兴趣和责任——专业研修的动力》,其中“责任”二字,稍有分量。委实如此。多年前我选择历史专业,而后徐徐走来,除了就业选择和兴趣之外,就是在履行自己作为史学工作者的职责。稍有缺憾的是,笔者久忝学界,却很少从理论上探究此事。而自己的责任意识,是在工作中,凭着本能,逐步增强的。
责任心的动力不止一端。笔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幼年时曾欢欣鼓舞,讴歌新社会。后又经历不少政治风雨,对历次侵害人权的政治运动深恶痛绝。这种心境激发笔者做职业性的反思。1976年笔者留校工作时,阴霾低垂。单位停电半年,我晚上读书,常对着昏暗油灯苦思。幸好,翌年全国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启动,高校重现生机,笔者有幸成为首届世界史专业研究生。读研不久,有师友问:你为何舍弃有一定基础的俄语和中国史,改学英语、世界史?为何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英国两党制度史作为研究方向?我沉默良久未作解释,可心情并不轻松。一则,刘少奇惨死的消息刚从小道传出。堂堂的共和国主席,竟殁在出了包青天的古都开封,真是对宪法的莫大讽刺!二则,回想自己在“大跃进”、“自然灾害”和“上山下乡”时的感受,在“文革”中的风风雨雨,怀念自己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几位师友,常常陷于痛苦和思考。我深知中国多年个人崇拜盛行,灾难连连,源自专制主义的祸害。国内运动不断,在于过分的阶级斗争说教,欠缺宪政、法治、自由和人权。而中国史的教学中又甚少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时,我想通过对世界史的专业研修,了解和介绍不列颠政治史的曲折历程,从中领悟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这种责任感,是激励我在以后几十年,始终坚持研究英国政治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职业的选择,我终生无悔。
然而,所谓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意识,践行起来并非易事。多年来教条主义理论的浸淫,一些貌似正确的思想原则和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也使我形成了思维惯性。好在自己早有矫正心态,欲对某些陈腐的学术观点加以清理。这就促使自己在教学和研究中:坚持科学、客观和正义的立场,坚持专题研究方法和态度,客观适度地评判历史问题,保持辨伪校正的勇气。
科学、客观和正义的立场,就是求真。对此,当代一位学者说得好:历史学家就是做镜子的。工匠在做镜子时,必需注意质量,要使镜子清晰透真,不可轻易迎合某种心态,将之制成变态走形的哈哈镜。为此,笔者就不迷信权威了,多了独立思考,在承担较多教学工作的同时,围绕世界史的热点问题,撰写一些论文,陈述自己的基本观点,并在课堂上加以阐述。这里略述一二。
一是关于断代史的分期。即世界“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开端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将之绝对化,断言“五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生产方式”是划分各个历史时期的标准。其阐释是:所谓“古代史”,是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历史;“中古史”是指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代史”主要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并开始衰落的历史;而“现代史”的开端则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划分方式言之凿凿,可最大的弊病,是把表示时间概念的断代史与表示社会性质的政治发展史紧紧挂钩,将两类不同的概念混淆,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典型的历史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将灵活的问题用僵硬的教条主义来解释。甚至在21世纪初,仍有官方人士扬言:历史分期是“政治性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在课堂上与学生一道质疑该分期标准。1981年,我写了《论历史分期的相对性》一文,强调划分历史各阶段的标准不是“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而是“时间”的远近,其参照系是“现代人”。即是说,凡是距离我们现代人比较久远的,属于古代史;不太久远而又非多数现代人所能经历的,是“近代史”;距现代人颇近、又由部分世人所亲身经历的,是“现代史”。例如,俄国十月革命曾经离“现代人”很近,应是现代史开端;可目前这一事件离我们比较远些了,就归入世界近代史了;再过数百上千年它肯定还要归入古代史,尽管十月革命的社会形态属性没有改变。又如755年的“安史之乱”,对于亲身经历了的杜甫而言,是现代史;对于唐末李商隐而言是近代史;相对于我们来说则是古代史。尽管这一事件始终发生在封建社会的唐朝。此文先后投向多家报刊,均被退回。有编辑回函:论文的观点是对的,国内通行的分期方法是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但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不能发表。直到1993年,方在我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研究通讯》上非正式地印发。而它正式发表在《史学月刊》,则是1998年的事情。此文前后17年的遭际,说明我国史学中教条主义根深蒂固,各家报刊总有一股政治阴影,也说明了倡导学术自由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
二是关于世界近现代时期国际共运史的难点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共运史教学和研究一直走下坡路,其中近代国际共运史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可许多高校讲义和中学课堂还在重复着旧观点,对于“议会道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中产阶级”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等,动辄鞭笞。这种理论滞后的情状,给教学带来了诸多不便,学生听课兴趣索然,甚至公开质疑。鉴于这种情况,我于2005年年初,发表了《国际共运史: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模糊性》(《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集中阐述了我对近代时期国际共运史中几个“敏感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对世界近现代史教材和教学中一些教条主义的陈腐观点,如过度宣扬共运史中的内部斗争、过度强调狭隘的阶级立场、过分贬低中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公等,加以辨析。文章发表后,迅即被多家出版物全文转载,一些学界同仁来函来电表示赞同,其观点至今还屡被提及。
英国政治史在世界史中占有突出地位,它一直是笔者的研究重点。朝着这一目标,笔者循序渐进,在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7册书,理清了一些历史问题。其中《英国政党政治史》、《英国政治制度史》、《英国贵族史》和《英国政治思想史》等,成为一些高校世界史和政治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书。另为多家刊物写出了一些论文。为完成这些作品,我前后费时30余年,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该系列的目标之一,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其中,笔者有意揭示了一些易被学界忽略的历史启示。
譬如,针对国内学界所谓共和国肯定优于君主制的断言,笔者结合克伦威尔军事独裁的史实,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中指出:“英国近代政治史的特色之一,是专制政体仅仅出现于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并且使用了共和国的名义……仅此可见,社会的安定与动荡和国民自由的多寡并非总与政体形式有关。此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历史一再地证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又如,针对某些国家危害深重的个人崇拜,书中写道:“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民主法制观念的成长还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观念,削弱降低政界头面人物的作用。纵观‘光荣革命’后的历史,可知不列颠政界罕见主宰国运的伟人,上层政要的活动大多要置于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干预之下,普通国人对政界名流常常会敬而远之,甚至冷嘲热讽。英国政界缺少叱咤风云的强者,以及民众对政要所表现出的冷漠轻视,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同上书,第6~7页)
比较而言,在笔者的英国政治史系列中,政治思想史的论作属于更高的层次。其中不仅介绍探究了英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思想演变,揭示出不列颠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特征和趋势,还激发笔者关注中国现实社会,做深刻的反思和委婉的评判。这又牵涉到史学工作者责任观的又一方面:关注现实社会,行使评判职能。
从学理上说,关注现实和行使评判能力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还是最起码的权利,是体现历史研究的价值要素。因为,历史学者研究某历史问题时,不仅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还身处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有着判断现实社会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能在陈述和解释具体历史问题时,联系较近的社会现象,展示自己的基本看法。可在中国,由于某些原因,对西方历史问题的解释不仅曾受到较多的制约,在评判某些人物、组织和事件时,还有着太多的清规戒律,而且要时时谨慎,尽量不去联系本国历史和现实,否则会与某些所谓原则相抵牾,有影射的嫌疑,甚至招惹是非和祸端。像我这样的年龄,此类教训所见多矣。也正因如此,史学论著中,浅薄和曲解屡见不鲜。鉴于此,我提醒自己:若只是就史言史,回避现实,就很难体现专业研究的难度和深度,很难赢得读者,自己也会逐渐失去研究兴趣。随着形势的变化,我在研究英国政治史时,不仅注重客观求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有意联系国内相关问题,加以评判,并因此养成了一定的学术毅力和勇气。
笔者在研修英国政治思想史过程中还发现,对于著作等身、政治影响较大的思想家,学界关注较多;而对于个别昙花一现思想保守的思想家,人们很容易不屑一顾,或简单批判了事。并由此形成积习。17世纪英国保王党思想家罗伯特·菲尔默及其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就有类似遭际。人们只是在谈到约翰·洛克的思想时才会偶尔提到他,可对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却长久欠缺,甚至低估了此类思想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针对这种情形,笔者写道:
我们可以相信,在十七世纪,菲尔默的理论肯定不代表社会思潮的主流;更谈不上顺应历史方向。他的诸多著作,很难得到赞同者支持者,却容易遭受批评。但人们不应忽略的是,专制主义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领导专断、个人崇拜等,即便是那些没有读过菲尔默著作的人,也会得心应手无师自通地显示出来的。甚至到了现代后期,某些显赫人物还是易于采用不同的声色,演唱独断专行的剧目,诱导芸芸众生歌颂权威,而一些官场人物也善于利用民众的崇上心态,营造出可歌可泣的感人场面。他们若要有所作为,可能是为了展示政绩,谋取利益;他们若能得到下属的奉承,则会自奉贤明,洋洋得意。可这种做派的代价总是格外深重的。就此来看,菲尔默实际上代表了政治思想史上最有持久的一种学说(《英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也许,如此的评论,短时间内领悟者寥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理解的人会越来越多。
再如,笔者纵览18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上层阶级政党之间政治宽容的大量史实,对照法国、德国、美国党派之间和苏联党内残酷惨烈的党派斗争,有感而发:该时期英国政治宽容的启示是,一个没有宽容的社会是病态的、变态的。只有容忍和鼓励反对者和批评者表达自己见解的社会或国度,才是健全的国度,因为宽容、和平和妥协等是政治文明的真正本质。2008年发表在《世界历史》第1期的论文《近代前期英国政党关系宽容化述论》,肯定赞扬了政治宽容做法。文中指出,二百多年来,之所以英国的政党之间和政党内部,没有个人权利的侵害和人格羞辱,是因为该国以议会政治为中心的党派斗争,始终是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的。
在英国政治史研修中,笔者发现了中国学界“阶级立场”的一种偏差:充分肯定下层阶级政治斗争的作用,但缺乏对统治阶级上层群体历史作用的中肯评估。国内关于英国贵族阶级的历史作用,长期侧重于对17世纪所谓新贵族的研究,而对其他时期的活动或一笔带过,或慨然否定。实证研究不足使中外学界的研究有着明显的距离。为此,笔者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搜集材料,先后写成了《论英国贵族政治权势在近代的延续》、《论20世纪英国世袭贵族的衰落》等论文,最后形成两册专著,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英国贵族阶级的历史作用及贵族文化的深远影响。在《英国贵族史》中,笔者强调:英国贵族群体有着强韧的生命力和政治连续性。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善于协调自身与王权、宫廷的关系。即便在资本主义时代,他们也能在维护既得利益的情势下,较老练地处理本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他们既是王权的追随者、服从者、合作者和维护者,又是王权的对抗者、挑战者、监督者和制约者,是《大宪章》、《权利法案》等重要历史文件的制定者,“光荣革命”的发动者。他们与别国权贵的不同点,是在政治斗争中,善于捕捉有利时机,把握斗争分寸,运用群体力量,援引历史先例,发挥创造精神,采用法制手段,与国王达成了较为切实可行的契约关系,最早创立和逐渐完善了议会制度,率先获取了从事合法斗争的组织机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不列颠贵族更是稳居国家权力的中心,精心营造了以大地产者为核心的贵族寡头体制,把多种权力运用到极致。他们长于政治防守,又不放弃必要的退却,能够较为及时地掌握政治主动权和社会领导权,步步为营地缓和社会矛盾(《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笔者在读书写作时,一再为不同国家之间所发生的类似事件的差异而感叹。当我读到其他国家实行温和有序的土地改革历史时感叹不已。我油然想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大陆推行的土地改革,本来已经具备了和平进行的条件,但还要对土地所有者实行过度的剥夺和暴力侵害,乃至对当事人野蛮处决。这种滥用暴力的做法,源于过激的阶级斗争理论,贻害无穷。而且,暴力行为的扩大化,不仅彻底摧毁了财产私有法则,还彻底摧残了原有乡绅阶层的权威和人格,甚至在以后几十年里虐待他们的后人,在农村建立起低层次的“阶级专政”,败坏了世风。还有,当我们看到眼下中国许多具有官场背景的人迅速暴富,回想到那些曾经奋斗了几代,方有少许资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急剧消亡,难免会问:既然如今,何必当初?
史学工作者又一责任:坚持做史学的普及工作,襄助中学历史教育,并利于世界历史知识的传播。
应该说,在中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尤其是中国史,通俗读物,俯拾皆是;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胜枚举,赏心悦目。但比较而言,世界史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通俗易懂的作品依然不多。仅有的一些国别史著作,还存在着重政治史、忽略其他方面的缺憾,这是其一。其二,国内的中学历史教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依然滞后,甚至不比国内高校教学,影响了青年人的知识结构认知。为此,笔者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于2001年春季,完成了《英国史》。该书40余万字,其中采取了中国史学典籍中“纪事本末”体的写法,注重可读性,兼顾了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科技史等多方面的内容,可做教材和一般读物,问世后一再重印。再是应《历史教学》编辑部之邀,面向中学历史教师,先后撰写了20余篇有关英国历史的文章。这批作品比较简短,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兼顾学术性,既注意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注重通俗可读性,发表后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不觉之间,笔者年岁见长。但以后还会笔耕不止,在完成现有研究计划的同时,写出一些通俗性普及性作品。这也是笔者继续体验专业研修乐趣和人生意义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