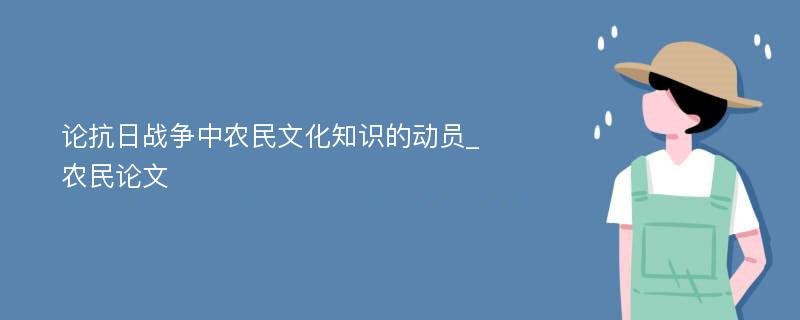
论抗战中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界论文,中文化论文,动员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化知识(注:本文从最宽泛的含义上使用文化知识界的概念,它大体上包括学者、乡村工作者、文化和艺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等知识团体和个人,故这一概念与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同一意义。文中也杂用知识分子、文化知识界人士等语词。)界自觉担当起农民动员的重任,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由战前的一般性号召瞬间走向高潮。这个高潮,将1930年代抗日爱国、农村农民和知识分子三大社会热点聚焦到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上,使作为时代先驱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基本力量的农民群众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相结合,构成全民族抗战中富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双重意义的奇观盛事。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考察这段史实,对于重现知识分子对民族救亡的精深思考和自觉担承,理解民族抗战对社会关系、民众心理和民主政治的深刻影响,深化民族抗战史和战时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学术界对知识分子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研究较多,成果丰富,故本文将论述的范围侧重放在国统区。
一
抗战爆发后,全社会对农民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倚重,与农村农民慌乱、漠然和散漫的现实状况,构成巨大的反差。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抗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口号与要求”。文化知识界人士率先奋起,自觉地承担起动员农民的时代重任。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奋起的民族解放战争。根据中日两国军事、经济力量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我国在战争初起时,即在中共倡导下,结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地确定了全面、持久抗战以制胜的战略与策略。这一战略策略的主要根据,是我国广大农村拥有源源不竭的人力、物力和广袤的地域条件,足以成为长期抗战的力量源泉,而最终战胜国度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侵略者。因此,中国农民被历史猛然间推到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受到全国各政党团体和全社会的一致推重,抗战的最后胜利“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成为社会的共识。
知识分子最富有民族精神、国家观念和民主意识,对抗日救亡事业积极主动,表现出前驱和先锋的群体特性。战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文化知识界已明显呈现转向关注和诉求农村农民的动向,并在一二九运动后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抗战爆发后,文化知识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对农民在抗战中作用地位的认识,达到空前的高度。他们认为,“在全体总动员中,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抗战力量,是最主要的工作。战区农民之能否与军队合作,帮助前方将士作战;被陷区域内,农民之能否蜂起,扰乱敌人的后方;以及后方农民之能否踊跃参加‘征兵’,补充前线的损失,努力生产,供给战时粮食的需要,皆成为决定战事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今日不欲抗战则已,若欲抗战,就非立即组织全体农民,发动农民广大的抗战力量不可。”(注:姚克夫:《怎样发动农民参加抗战》,薛暮桥等著:《抗战与乡村工作》,生活书店1938年发行,第33页。)当时作为战地记者考察华北抗战的徐铸成,针对社会流传的华北民众是一盘散沙的说法,在介绍“前方民气的沸腾”后指出,这散沙的每一粒全是铁沙,他们具有天然赋与的强壮的体格,直率的性情,将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能将铁沙化成铁块,就“是一座国家的长城”。(注:铸成:《第一次对外抗战》,《国闻周报》第14卷第33-35期(战时特刊合订本,上),1937年10月4日出版。)这说明,文化知识界对于战时农民作用的认识,不但具有思想高度,而且也十分准确。他们的言论,对于端正全社会的认识至关重要。
但是,农民具有巨大作用是一回事,能不能将农民的巨大作用发挥出来,又是一回事。事实是,当时农村农民的现实状况,与农民在全面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及全社会对农民的推重,构成极为强烈的反差。由于自然经济下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农民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弱点。农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比较薄弱,既有朴实、忠厚的特点,更有根深蒂固的散漫、认命、顺从和冷漠的特性,要将他们动员成为自觉的强大的抗日力量,决非易事。全面抗战爆发时,农民还处在无准备无号召也无组织的散乱状态,并不明白民族抗战的意义和抗战与他们的关系,虽然确实不乏奋起反抗侵略和主动支前者,但麻木不仁者、惊恐慌乱者、束手待毙者乃至因各种原因而公然附敌者,也所在多有。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线,许多紧急调动中的军队,因为无暇埋锅做饭而往往整天挨饿,大量军需找不到民夫帮助运输。师长宋希濂等说,作战中“最使我们痛苦的是民众没有组织。我们军队开到之后,能帮助我们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汉奸”,以至电话线屡遭破坏,军情被密报日军,作战十分困难。将士们普遍与北伐战争时相比,认为民众对军队的支持远不如北伐之时,因而深感不可理解。(注:胡子婴:《在火线的后面》,《抗战三日刊》第7号,1937年9月9日出版。)有人专门调查后指出,抗战到来后,农民依其心理状态可分为4类,即满足于有地有食、安分守己而不闻天下事者,为贫困所压迫而怨天尤地者,胆怯怕死者,具有抗敌思想的“好事”勇敢者。调查者认为,农民“对于此次民族抗战意识,理解十分模糊,或竟莫明究竟,此种民智呆滞之现象,如不再急速加以训练,而欲求民族解放持久抗战胜利,实有些南辕而北辙。”(注:黄士英:《持久抗战与组织农民义勇军之建议》,《申报》,1937年11月7日。)当时投身抗日救亡工作的孙冶方,在淞沪抗战前线也写下《从汉奸之多谈到乡村工作》,疾呼“扩大乡村工作,发展农民运动”。这类现状,通过文化知识界人士的笔端,被披露到全社会面前。它们深刻地说明,即使是在全面抗战的民族大义之下,农民的力量也不可能自发地爆发出来,而是还存在着对他们进行充分解释、动员和组织的严重任务。“把农民组织起来,已成为抗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口号与要求。”(注:恽逸群:《组织农民的主要问题》,《抗战三日刊》第9号,1937年9月16日出版。)
谁去动员和组织农民?谁来担当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弥补国家需要与广大的分散农民之间事实上存在的裂口?于是成为继起的急迫而尖锐的问题。“知识分子就有着发动民众力量的极大责任”(注:仲持:《知识分子当前的责任》,《抗战三日刊》第7号,1937年9月9日出版。),文化知识界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意识,勇敢地承担起动员和组织农民的时代重任。1937年8月,胡绳向文化界发出紧急建议,立即散开到全国的每一个小城市、小乡镇中去开展文化运动,以提高全民族的抗战情绪,凝聚全民族的一切力量,(注:胡绳:《战争时期的文化界》,《抗战三日刊》第4号,1937年8月29日出版。)正是这种自觉意识的典型表现之一。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将去农村动员和组织农民,作为个人为民族解放战争所应尽的责任。
二
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与全面抗战几乎同步发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直接从事农民动员,以抗战初期最有声势和最为集中,呈现出集中性、团结性、大众化和自律性等鲜明特征。他们以自己的激情、知识、才能和精神,接触并感动着广大农民,描绘并丰富了全民动员的壮观图景。
(一)时间集中,围绕着淞沪战役、华北抗战和武汉会战等大战役,形成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一个个高潮。淞沪战役打响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口号响彻云霄”(注:吴一民:《农民的政治训练》,《抗战三日刊》第19号,1937年10月19日出版。),集中在上海的众多文化知识界人士,或踊跃到战区农村从事战地服务和农民动员,或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发起的“还乡工作运动”中,纷纷返回故乡参加抗日宣传动员。华北抗战时,由平津学生组成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几万名队员,晋冀鲁豫各地流亡学生组织的“动员剧团”,以及山西牺盟会、战区动委会包括上海来的救亡剧队等,如潮水般的涌向农村。特别是武汉会战前,武汉成为东南沿海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文化知识界的聚集中心,“文章下乡”,“工作下乡,唤醒民众”,更被知识分子当成“针对着这次全民抗战长期抗战的药方”和“保卫中华的先决课题”,(注: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巡回施教队:《救亡团体下乡太少》,《抗战三日刊》第85号,1938年6月29日出版。)而纷起身体力行。据孙晓村当时的估算,下乡的知识分子在1938年初已不少于十二三万人。因此,知识分子直接到农村去的活动,在武汉战役时期达到最高潮。
(二)团体众多,知识分子或自己组织,或参与政府、军队的战地服务团队,围绕着抗日救亡的目标,手携手的在农村共同奋斗。由社会团体组织者,例如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深入松江、镇江和河南等地农村。由政府、军队组织者,例如有政府出面组织的各种战地服务团、巡回演出队,著名的如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应青年学生的要求,组织4千名青年学生分赴75县农村,进行为期半年的发动和训练农民工作;(注:详见:《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159页。)各战区长官部“动员民众委员会”征求文化知识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分派到乡镇进行农民动员,著名者如山西牺盟会和第二、第九、第四等战区动委会,均组织了很大规模的深入乡村活动。
更多的还是文化知识界自己的组织。如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会,1937年10月发起“农民抗战教育”运动,在湖南招收平津沪流亡大学生,组成农民抗战教育团,分赴各县农村。他们怀抱“广大农村正是我们马革裹尸的沙场”的坚定信念,白天口讲笔书宣传抗战,晚上演出抗日短剧,四乡农民举着火把涌来观看。(注:谢尚品:《曾被誉为”世界十大伟人”之一的晏阳初》,《炎黄春秋》,1997年第12期。)同年底,湖北各级学校战时服务总团组织30个乡村巡回宣传队,深入各县做“普遍抗敌宣传工作”。次年1月,湖北文化界领袖孔庚、邓初民、马哲民、梅龚彬等发起组织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制定8条工作纲要,集中各地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唤醒民众,支持抗战。而全国各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救亡协会和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更是知识分子下农村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
知识分子地位有别,来源不一,政治倾向更不尽相同,其中许多分属于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但他们自动团结起来,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对动员农民工作不但认识相同,而且热情高涨。《新华日报》载文称赞说,抗战以来,“无数的乡村救亡工作团体,在政府主办或个人自动组合之下,不断地建立起来;无数的救亡宣传队,战时服务团,以及军队中政训工作员等,一队队的涌往农村去,大家手携手的在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奋斗。”(注:新华日报:《怎样展开农村救亡工作》,《抗战与乡村工作》,第24页。)此情此景,充分显示出知识分子的崇高境界和凛然大义,确实令人感佩。
(三)内容丰富,注重大众化形式,适合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传播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和文化知识,激发农民的抗战热情和爱国精神,使其在抗日致胜目标下组织起来。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动员,主题鲜明,形式活泼,其活动既有培训干部、组织自卫队等政治军事训练,也有演讲、戏剧、歌咏、图画等抗日宣传,在战区农村的还有难民收容、战地救护等工作,在城市的则有针对农村问题的理论著述、刊物宣传和文艺创作。一位在赣东农村从事动员的人士说,他们在贵溪、广丰的一个半月中完成了九项工作:各学校、部队的歌咏、戏剧、漫画两周训练;妇女战时常识训练;成立妇女战时服务团;小学教师座谈会;成立小学生联合宣传队;小学生集中训练;出版宣传文件9种;发行画刊一种;平均每周举行宣传会一次。同时,他们还做了农家访问、筹备一个半月下乡巡回宣传及其他训练工作。(注:周君实:《浙赣工作六个月》,《抗战三日刊》第74号,1938年5月23日出版。)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工作不但内容实在,而且也十分紧张和繁忙。
在农村动员中,戏剧和歌曲被作为传输民族精神、凝聚民众情感、激励意志信心的大众化形式,成为最有影响和成效的武器。特别是那些针对农民所创作的作品,在农村受到极大的欢迎。话剧中在各地演出最多的有反映抗日救亡的剧目《放下你的鞭子》、《毒药》等,演剧队搜集前方军民抗战事迹编成的剧本,“下乡到境内各区镇去公演,每次乡民围拢来看的均达四五千人”(注:叔羊:《救亡运动在山西》,《抗战三日刊》第44号,1938年2月9日出版。)。歌曲也是这样。一首《抗敌四季歌》,以其古风的意味,从农民的内心深处勾起其民族传统精神:夏季里,日正长,征衣换上别爷娘。勇敢从军去,为国为家乡。秋季里,稻上场,大家联合打东洋。身体虽辛苦,精神百倍扬。(注:《抗敌四季歌》,《战时民众》,第2卷第11期,1940年12月10日出版。为省篇幅,春冬季歌词未引。)又如以锄头歌调创作的《打日本歌》,短短三句,朗朗上口:拿起了枪杆打日本呀,打走了日本求生存呀!武装了民众打日本呀,日本的鬼子没法儿凶呀!抗战到底打日本呀,最后的胜利属我们呀!(注:刘良模:《打日本歌》,《抗战三日刊》第31号,1937年12月26日出版。)丰子恺谈及由浙江经江西、湖南到汉口的一路见闻时说,沿途各地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偏的小山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竟是“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景况。(注:潘文彦等:《丰子恺传》,《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第253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战时农村动员的规模和程度。
(四)经受磨难,增进感情,在动员农民中注重自身锻炼,表现出可贵的自律精神。“脱掉长衫,同赴战地!一面唤起民众,一面教育自己。”这是淞沪抗战时著名文化人钱亦石创作的战地服务歌的头两句歌词。它深刻地说明,知识分子去农村,并不是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先知先觉者,而是对自身的局限也有足够的认识,自醒到自己也要在农村、在战争中经受教育和锻炼。因此,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过程,也是自身经受锻炼和成长的过程。艰辛跋涉,耐得劳苦,食得粗粝,住得简陋,成为下乡者的常事。10多位从上海到浙赣农村工作的知识青年说,他们每天在乡村流动工作,最初的4个多月中,经过了12个县城,60多个乡镇,“上海的经费接济早已断绝,每天和饥饿寒风做朋友,衣履褛褴,一般人把我们看作难民”,“可是由于四个月的锻炼学习,我们已经渐渐地熟习如何运用工作方式,认识和适应内地的环境,十几个工作员便结成了一架灵活可用的机体”。(注:周君实:《浙赣工作六个月》,《抗战三日刊》第74号,1938年5月23日出版。)农民在接触中日益亲近知识分子,“他们和我们亲密得如同一家了”;知识分子在动员农民中自身经受锻炼,“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学到了不少在课堂里念课本所学不到的学问”,(注:非伶:《寒假下乡宣传回来》,《抗战三日刊》第52号,1938年3月9日出版。)成为农村动员中十分感人的画面。特别是,在农村工作中,还有的知识分子献出了宝贵的鲜血和生命。
1939年后,由于国民党实行防共反共政策和新县制等加强了对农村的控制,以及后方秩序逐渐稳定,大中学校完成迁移并相继开学,文化知识界在国统区的大规模到农村活动逐渐结束,小规模的活动虽未中断,但被完全纳入政府的组织和主导中。而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直接到农村去则仍然方兴未艾,他们与农民群众日益紧密的结合与融通,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最为鲜活的内容之一。
三
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的另一重点,是与乡村民主政治相联系,体认农民疾苦和反映农民愿望,呼吁实行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现状、激励农民奋起。这类工作,在1939年大规模到农村的活动基本结束后,尤其成为文化知识界关注农村、动员农民的主要形式。在国统区,知识分子成为农民利益的坚定代言人。
没有农民的投入和牺牲,不可能取得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是各党派各阶层乃至中外人士共同一致的认识。但是,怎么样才能赢得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奉献牺牲,却有着不一样的主张和认识。对此,文化知识界人士在与农民的接触中,相当集中、深入和尖锐地提出了他们的主张。这些主张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他们不满基层政权的作为,要求改良农村政治和行政机构。农民眼中的国家,就是作为其代表的基层政权。因此,知识分子们也在这个层面考察基层政权的状况及其与农民和农民动员的关系。其结果是对区乡政治的批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陶百川主办的《血路周刊》第二期刊文,分析区乡政治的现状,认为现在一部分区乡长人格卑污,大部分的区乡长纵不为恶也只知道做官,此外尚有一些较好的区乡长,也只能做传达公文的工具(注:沙扬:《动员千百万农民参加抗战》,《抗战与乡村工作》,第15-16页。),如此区乡政权不会去关心和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分析各地农民动员不起来的问题,指出“原因是充当区长、保长、甲长的,十之八九都是土豪劣绅,他们武断乡曲,欺压平民,乘机敲诈,无恶不作。此种分子如果不更换,民众抗战的情绪便永远不会提高起来。”(注:仲实:《鄂省策进民训办法》,《抗战三日刊》第47号,1938年2月19日出版。)也有人根据动员实践,对中上层政治提出批评,如县政的混乱和县长的无知(如湖北某县县长面对下乡的众多知识分子,不但神气活现官架十足,而且不准他们扩大抗日宣传和唱歌演戏),以及部分地方当局阻碍农民动员的政策,有的还直接批评缺乏民众动员和表面花样繁多实则内容空虚的民众工作,是造成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注:赓雅:《广州失陷的教训》,《申报》(香港版),1938年12月6日。)。因此,知识分子们普遍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善地方政治,认为要想真正把广大民众动员起来参加抗战,“只有彻底改革下层行政机构才行”。有人甚至提出了要人民爱国,必须先使人民感觉到“国”之可“爱”的严峻问题。知识分子因其特性,对现实政治具有天生的批判性,他们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批评,固然有的可能过于绝对,但总体上不但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而且所针对者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其根本点在于要求改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他们在特殊环境下实际上成为战时国家农村权力的批评者和监督者。
第二,关于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他们要求禁止地主豪绅借抗日而剥削压榨农民,动员当地知识分子起来改良农村社会环境。下乡人士发现,农村中的绅权相当大,大大小小的“绅士”、“先生”们与保甲长相结合,垄断农村的事务,主宰农民的生死。抗战时期,地主豪绅除了对农民直接的土地上的经济剥削外,在税捐和兵役上的不公行为最为知识分子所愤慨。章乃器指出:“在社会方面,新旧土劣把持后方工作及保甲制度,以为个人乘机渔利的工具的,也所在都有。如制裁汉奸和抽调壮丁,便在许多地方成为土劣敲诈平民的口实”。(注:章乃器:《抗战时期的民主问题》,《申报》,1937年10月22日。这样的言论当时很多,如周君实指出,他们在农村工作6个月来,同别的战时服务团一样,觉察到很多令人不痛快的事情:保甲制度的不健全;强迫执行征工征兵;民众生活的艰苦非常;无钱的出钱,无力的出力;还有发救国财的官吏。“这些令人齿冷心寒的事实,仍旧一幕一幕在串演。”(周君实:《浙赣工作六个月》,《抗战三日刊》第74号)。)章乃器将他们称之为“一班自私自利不知羞耻的棍徒”,对国家在抗战中如何需要民众的奋起既不了解也不肯计及,是国家意志和权力不能达于下层以致削弱抗战力量的障碍。由于地主豪绅与保甲长、乡村政治紧密相连,知识分子们因此提出,要从建立乡村民主入手,动员当地的知识分子(全国乡村中当时仅小学教师有几十万人),尽力联络推动乡村上层分子,至少做到禁止土豪劣绅借抗日而剥削压榨农民。不少人还建议实行保甲长甚至乡镇长由农民直接选举,以此改变地主豪绅主宰农村的现实,实现农村政治的开明。从理论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农民动员,要求动员农村中的一切阶级一切力量,即包括愿意抗日的地主富农士绅等等,共同投入抗日的洪流中。但实践中,一方面,知识分子们对这部分被称为农村上层、精英的人物,在观念上有所鄙视、感情上有些格格不入,因而不够重视,也未能进行具体分析(未对其中一部分人的爱国意识和抗日热情给予足够的估计和肯定),是有些失误的;另一方面,这些农村上层人物,掌握或控制着农村的政治与经济生活(这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架构有重大甚至本质的区别),他们将农民动员视为对既定秩序及其既有利益的威胁,也基本上没有来自上层政权的强有力制约,因而他们中的相当比例的人对知识分子的农民动员不甚欢迎乃至从中作梗、破坏,也导致知识分子对他们更为严厉的抨击。
第三,关于农民的意愿与权益,他们直接反映农民的需要,要求当局给农民以实际利益。知识分子在农村中深深地感受到农民的痛苦和无助。由体察农民的痛苦进而了然他们的内心需求,并向当局和社会发出呼吁,成为文化知识界人士农村动员工作的一大特点和优点。长期从事农村农民问题考察研究的阎若雨,根据农民的愿望,归纳出战时农民的十大需要,即需要切实优待军人家属,需要公平抽征壮丁,需要军官与新兵共甘苦,需要刻苦耐劳领导群众的县长,需要统一税收,需要良好的保甲人员,需要织布传习所,需要合作金库和合作社,需要农产品推销处,需要知识分子。(注:阎若雨:《农民的十大需要》,《现代农民》第2卷第6期,1939年6月10日出版。)陈翰笙则认为,合理征收、提倡合作和调整保甲,是“目前农村中最起码之要求而急乎办到者”。(注:陈翰笙:《农村与抗战》,《中国农村》第6卷第10期,1940年9月1日出版。)孔庚等提出的8条纲要,也涉及到乡村自治、自卫、发展经济、减轻负担、普及教育、培训干部等内容。所有这些言论,涵盖了兵役、县政、经济和文化知识等直接影响农民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农民最实际的利益和最迫切的要求,因而也最为农民所欢迎。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们还提出了组织和武装农民,以及要求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去争取改善生活、解除痛苦和维护利益的问题。而这一点,显然更具有根本性。
文化知识界人士所以如此关注农民利益和农村政治,既源于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正义的意识,更缘于他们的深入农村、接触农民和了解实际。他们当然是从民族利益的全局来思考和阐发问题的。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在要求农民为抗战作出贡献时,也要考虑农民的实际利益,让他们减轻长期经受的压迫、剥削与困苦,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实行一定程度的农村社会的解放(改善农村政治)和农民的解放(改良农民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动员农民起来抗战的先决条件、根本条件,希望由此更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的爱国热情,进而为保障抗战胜利提供源源不竭的物质和人力源泉。他们也承认,这些工作应在国民党当局的领导下并在完善保甲制度的框架中进行。他们的呼吁,有的固然也曾为国民党当局所重视,但因其不少涉及国民党的农村基层政治体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本质上与国民党的办法难以相容,而与中共的主张更为接近或者说更相吻合,因此在国统区大多未能成为现实。
四
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富有多方面的成果和意义。他们在走向农村中,唤起了广大农民群众,促进了自身思想的升华,带动了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实际发挥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和基层政权的制约者等多重作用。他们为民族抗战的胜利和中国政治的更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有效地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觉醒和社会关系的变动,相当程度地动员和组织了农村的抗战工作,促成农民投身抗战并作出巨大贡献,无疑是文化知识界农民动员的最大和最为直接的成果。“抗战将知识分子大批带到乡村去”,在当时即被认为是抗战中最令人兴奋的事。它一方面,为落后分散的农村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新鲜的活力,促成了战时农村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的动员和组织,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促成农民超出传统经验的局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看世界、国家及身边的一切,而对抗战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白了抗战是什么一回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大家非一致起来不行了(注:新华日报:《怎样展开农村救亡工作》,《抗战与乡村工作》,第25页。类似记载,如“凡军队所过的乡村,现在决不会发生找不到老百姓的现象”,因为文化知识人员的经常下乡和宣传戏剧团体的巡回工作,“使乡村中文化的水准,一般的比抗战前提高了不少”(张西超:《战时乡村工作诸问题》,《中国农村》第6卷第5期,1940年2月16日出版),也屡屡可见。)。广大农民真正成为支持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正如亲身经历抗战的新闻记者冯子超所说,要把散漫的、无知识的农民组织成一支抗日力量,原本是一件费力的事;但他们一经组织起来,加以教导,灌输抗战知识,所形成的力量可以说比任何阶层都坚强。因此,他在1946年出版的有“历史实录”之誉的《中国抗战史》中,特别肯定了知识分子农村动员的作用,指出抗战初期农民的英勇抗战故事,“正是那些时代先驱、爱国的知识分子在艰辛中教导,启发了他们以后的对抗战有益的正义的表现”。(注:冯子超:《中国抗战史》,1946年版,作者自序第4页,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确实,在广大农民的伟大贡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身后的那些爱国知识分子的身影和作用。
继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实现大规模的与农民相结合,奋起关注农村农民的现状与利益,也锻炼促成了自身思想的升华,是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的另一个重要成果。知识分子是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都与农民不相同的社会群体,促成他们走向农村、关注农民的中心动力,是强烈的民族精神、责任意识和自律意志。没有这种精神、意识和意志,如《申报》记者所言,不要说“深入”和“久入”农村很难,就是“浅入”和“暂入”也不易(注:《汉市近郊农村一瞥》,《申报》(汉口版),1938年6月27日。)。正是这种精神、意识和意志,使作为时代先驱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基本力量的农民群众,继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相结合,构成全民族抗战中富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双重意义的奇观盛事。在农村中,农民朴直忠厚的性格让他们感动,贫弱无助的困境让他们激愤。他们也曾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和不足,但更显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群强有力的战斗员”的风貌。他们既“在沉寂的乡村中播下了救亡的种子”,也坦承自身经受了教育和锻炼而有了“很大的进步”。(注:非伶:《寒假下乡宣传回来》,《抗战三日刊》第52期,1938年3月9日出版。)特别是,他们在农民动员的实践中,不但实现了不同思想倾向者在农民动员事业上的紧密团结,提升了自己的视野、思想和品性,而且奋然承担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民众文化的组织者和基层政权的制约者等多重角色。因此,有论者指出,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是抗日战争期间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发生的一个深刻思想变化,也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大创造。(注:李侃:《抗日战争与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最后,增进了对中国现实和政党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中国政治态势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共两党对知识分子去农村及其对农民问题的呼吁建言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国统区,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去农村最初表示支持,蒋介石也看到了知识分子在动员农民中的巨大作用而发出过号召(注:如蒋介石1939年1月19日致全国各地士绅和教育界通电(《现代农民》,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10日出版),号召各地知识分子各回乡邦发动全民力量,开发各种资源,以供抗战需要,认为如此,“没有不能战胜小小日本的道理”。),但各地阻碍和不合作的事实严重存在。对知识分子的呼吁,则基本上没有真正重视和接受,虽曾下达过禁止强拉民夫、壮丁和完善保甲制度之类的条令,并曾处决过个别强拉壮丁和虐杀壮丁的人(注:如1945年4月处决强拉3名壮丁的四川省资简区壮丁队长王平章,13日处决虐杀6名壮丁的接兵连长肖鸿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31辑第56、61页)。),但到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已无力抑制在全党弥漫开来的严重的腐败之风,不愿也不可能实行知识分子所期望的农村社会变动,不愿牺牲其乡村统治基础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愿触动和改变其农村政治与社会结构,除新赣南、龙泉等少数几个地方外,对地主阶级和地方豪强事实上也已难控制。因此,在国统区,农民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广大农民是在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为民族抗战大业作出贡献和牺牲的。这一点,最让知识分子感动,他们明确地肯定“农民们在抗战上的功劳太大了”(注:《保守我们的田地》,《现代农民》第1卷第1期,1938年10月10日出版。);也最让知识分子产生对执政党及其政权的不满,进而日益扩大地影响到他们对国内政治的观感和对政党的选择。与国统区的情况相反,知识分子的期望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被一一见诸实践。由于注重并较好地解决了动员农民与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及相应的经济利益,根据地农民对抗战的支持,更多的是或者说更带有自愿的性质,抗日的负担比较公平地落实在农村所有人口而不仅仅是贫苦农民身上。所以如此,在于知识分子的这类呼吁和期望,本来就与中共的政治主张相吻合,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有的本身就是中共党员)的言论,实际上反映的便是中共的政策思想,至少也是深受其影响。国、共两种区域出现的不同情况,在知识分子看来,显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成为其后知识分子与农民两大群体对国共两党产生不同的倾向性认识与选择的重要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