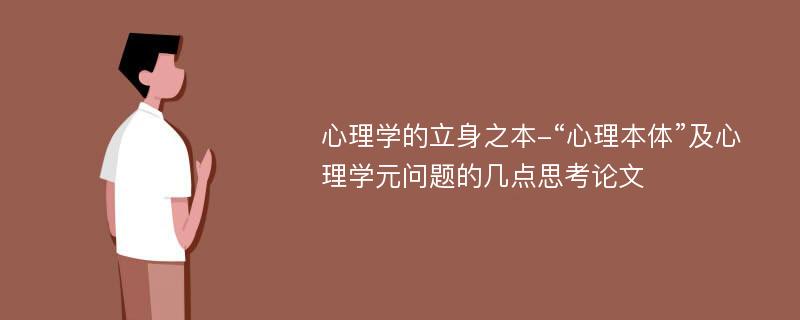
●本期特稿
编者按: 李其维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心理学会会士、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心理科学》主编、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长)。他多年来根植于发展心理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对我国皮亚杰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儿童认知发展、现当代智力理论及智力的测量与训练、具身认知等领域也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
本文针对与心理学有密切联系的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人文社会科学展开层层剖析,从心理学学科性质、心理学研究对象及双重研究取向与心理学的关系等角度,对最核心的心理学元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是对当前处于所谓热点光环之下的心理学的深度解读。
作者不仅向读者揭示了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强势挤压背后可能导致的还原论弊病,中国本土文化心理学等在貌似“思想正确”实则仍处于外围因素、较低层次研究路径等种种问题,更迫切于对心理学“安身立命之本”的“心理本体”的探寻——心理学必须走出原始、中庸的“心理现象”研究,走出模棱两可、众说纷纭的“心理对象”研究,而应定位于“心理过程与机制”,唯其如此,心理学方能立于不败。皇皇大论展现了中国学者不满于百年学科进程中唯有输入之弊陋,而期待通过独立思考渴望对心理学知识体系输出的责任与担当。
心理学的立身之本
——“心理本体”及心理学元问题的几点思考
李其维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摘 要: 在心理学备受国家及社会层面的支持的今天,对心理学的学科自身现状留一份清醒的自省意识显得非常有必要。脑与神经是心理的“亲密有间”的兄弟,但不能为心理活动提供因果解释,若企图从生理的角度对心理作因果说明,会导致还原论立场。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是朋友兼对手,“科学”与“人文”并非对立,而是已踏上融合之途。如何从现实中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的、带有一般心理机制意味的概念、范畴、理论,是中国心理学家的职责所在。在面对神经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人工智能等多面挤压时,心理学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心理活动的过程和机制”,做一些“以问题为导向”的现实合作项目,拿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其他学科难以取代的成果。
关键词: 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人文社会科学;心理本体;心理机制
当前国家层面对心理学的支持声频仍,沐浴于期盼已久的心理学春风中的心理学工作者一片欢呼。不过,兴奋之余,对心理学学科自身现状留一份清醒的自省意识或非多余。用大跨度的历史观审视,多少年后回顾,或许我们今天走过的路或欲前行的路,未见是全无弯道的。于是想到几个问题,借论坛之便,斗胆说说我的看法——因为只是书面发言,人未到场,胆子可能有点大了。所言咎误不当之处,敬请有识者重重打板或一哂了之。
一、脑与神经:心理的“亲密有间”的兄弟
如今国内的心理学研究,已到言必谈“脑”和“神经”的地步。不谈脑,近乎没脑子;不谈神经,仿佛神经有点不健全。
以前(2008)我曾撰文表达过“第二代认知科学”中的4E,即具身的(embodied)、延展的(extended)、生成的(enactive)、嵌入于环境中的(embedded in the environment)之看法,认为它们既有可能合作而消解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但也可能使争论的余波继续荡漾——这是因为有的E本身潜在地偏好不同的走向——如果它们彼此不能主动迎合对方的话。现在我则更欣赏“生成的”(enactive)的观点,因为它有可能较好地兼容两个“主义”(我不是从生物学或演化学来理解的,而是从认知或心理的“形式-内容”的角度来理解的——后文还会有所涉及)。
(3)实验教学和工程实训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对于力学性能的测试方法,包括硬度测试、冲击韧性测试和拉伸测试等,可安排学生到实验室观摩和操作。对于材料的铸造、热处理和机加工过程,可安排学生到工程实训中心进行课程实习。使学生更容易“掌握机械工程材料的特性及选用原则,掌握常用工程材料的热处理方法及工艺规范”。
由于人的地位的特殊性——它既是物,又是非物的有生命且有反思能力的“人”(暂且这么称它吧),所以两种文化必然深刻地反映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并且会演变为两种取向之争——这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
在心理学大视野中,心理与脑和神经结合得最为有声有色的当属认知神经科学,特别在所谓低端认知过程(如感知觉、记忆等)。国内几个重要的心理学单位的同仁们,均有出色的研究成果刊行于世——无论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基本训练是心理学的还是神经科学的。其他各种闪亮登场的“某某神经科学”或“神经某某学”(恕不一一列举了),现虽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未来“接天莲叶无穷碧”之景象应可期待。
但也请各位记住:这里有个重大问题似不可不辨,即脑与神经的研究虽为心理学的“兄弟”,却不是与心理学“连体”的。对心理而言,有心理活动,就有相应的生理活动,这何奇之有!这些生理层面的研究是为心理的研究服务的。说它们是好兄弟绝不为过。但是兄弟虽亲,却未及“无间”。将来是否可能“无间”,那是将来的事,所以要留有一份清醒(是否“无间”可能涉及某些心灵哲学的观点,此处不议)。之所以存在“有间”之芥蒂,根子在于它们只能作为心理活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发挥作用。我们不能也不应指望它们为心理活动提供因果解释。有时,我把这种“因果”称为“从生理到心理的反向决定论”。
心理学对脑与神经好兄弟的期待是:必须能为我们构建某种心理层面的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论(或哪怕只是小小的某种“观点”),发挥启示和反哺的作用——最低限度,它须有助于验证或确认心理学所提出的某种研究结论!我以为,目前凡是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结合得好的研究,它们无不是坚守了这些原则而非不当且过分地赋予神经科学难以承受的“因果解释”之使命。生理的变化只是心理活动特殊的、细化的外显指标(与行为指标具有同样性质),并不是心理本身。我的上述观点,多年前业已著文提出,至今未尝有变,所以总是习惯性地以此观点阅读凡有脑与神经研究相伴的心理学文章,看看它们离简单的“生理机制”的水平到底有多远,是否够得上前述之“验证或确认”的最低要求。
很遗憾,现在多数情况是“验证”(确认)尚嫌不足,“启示”(反哺)更近阙如!
前面说到的“某某神经学”之类,其中虽不乏“验证”和“确认”意义上的研究所得,但总体而言,大多只是成了某种标签、包装或点缀!趋之有众,不也乐乎!更有甚者,某些研究似在有意无意间步入了颠倒心-身关系的误区。
现在心理学家们多以有神经机制方面的数据相伴而觉得自己的研究仿佛一下子高大上了。可惜,技术虽高端,意义解释却很骨感。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仅获得浅显的“旁证”,有点不值得。目前整体而言,多数还只停留在“印证”阶段,即对心理-行为表现的某种或大或小的所谓规律性的研究结论,在神经层面予以证实。这已经很不错了。但它仍属于生理机制的低水平。更高水平的生理机制应该是通过这些神经数据启发我们构建新的心理活动的规律的认识(理论),使得生理-心理达于一种良性的、更富有成效的相互塑造的合作之环。当然,这些数据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学用武之处”,不妨保存下来以待后用——这一后用时机何时能到来只能寄希望于心理学自身研究的深入。
一言以蔽之,我认为:与心理学无关的生理学(脑的各层级)研究,生理学家们尽管去探索好了,而且越深入越好,因为它们还另有非心理学的价值,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不牵扯到你什么心理学!),比如医学诊断、疾病治疗、优生优育、特殊岗位从业人员的选拔,等等。但若你要把它们与心理学相联系,对不起,它们就必须恪守为“心”服务的本位!因为一旦这类研究想与心理学挂上钩(这种挂钩常常不是人家生理学家们主动为之,而多是心理学家一厢情愿靠上去的),特别当你企图用它们对心理现象作因果解释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不与心理学联系,这些研究是各自舞台上的主角;而一旦与心理学相联系,那就要恢复这些研究在心理学舞台上的配角身份。因为,即使你把上述那么多层级的生理(脑)机制都研究透彻了,你所获取的仍然只是心理的“生理(神经)关联物”——尽管总有一天,我们对它们的机制几可穷尽其妙,那也不能角色颠倒。因此,如果这种生理的解释仅是“相关”说明,或哪怕被视为“必要条件”的话,那也无妨;但若企图从生理的角度对心理作因果说明,把生理的结构与功能作为“充分条件”或“充分且必要条件”对待的话,那么还原论就会在前方等着你。因为我们无法期待心理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仅在生理层面就能得以解决。
把所有关于“心理现象”的研究都纳于心理学的旗帜之下,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而且我认为,它是现今“多元范式的心理学”之间互不服气、互打棍子,彼此谈不拢的根源所在。但或许换个角度看,它也可能是希望所在。因为,如果最终在心理学研究对象上取得一致,那么那些心理学史上缠斗百多年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科学取向和人文取向),不就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殊途同归,迎来和解的一天了嘛!
详细论述身心关系涉及心灵哲学的许多问题。但二元论历经百余年的“拷问”之后,现又在某种程度上“名誉有所恢复”是不争的事实,其成果就是出现了若干新的非笛卡尔式实体二元论的样式及相应的多种研究路径。我觉得,企图彻底磨平身、心的界限,对心理(特别是有意识心理)之产生的问题追随那种所谓彻底的自然主义-物理主义心灵哲学立场,至少在目前看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它几乎等同于取消了“心-身关系”问题,认为心理现象就是生理现象,甚至“还原”是应该的。实际上,更多的心灵哲学流派主张:生理证据并不能直接描述或解释“心”,包括心的感觉、心的创造、心的思维和想象。那种认为“人类心智状态的每一实例均等同于一个大脑状态,即心智状态等同于大脑状态”是不可接受的。
遗憾的是持这种显然为还原论立场的仍大有人在。这种立场视心理只是神经活动的副产品或副现象(epiphenomenon)。如遗传分子密码的共同发现者克里克(Francis Crick)甚至认为:“你,你的快乐与悲伤、记忆与渴望、你对人格同一性与自由意识的感觉,事实上只不过是数量众多的神经细胞及其相关的分子的集群行为。”还有一位著名人物(美国神经科学家莱顿克斯(Joseph Ledoux,其人以“恐惧情绪”的研究著称于世)说过一句名言,“你,就是你的突触”,它把什么环境因素、社会影响之类都纳入于突触的改变之中了,生理还原论莫此为甚也!
现在,大多数人工智能科学家实际从事的是“用电脑去模拟人脑进行的思维、决策、学习等活动,以完成以前人脑才能完成的任务”,其间既可使用也可不使用到人脑进行这些活动的机制。因为这时电脑的实际工作模式(状况)是否已经达到“与人相同”的机器人或钢铁侠水平,并不是人工智能及其设计者和工程师们所在意的。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达到这种水平,因为连人对自己的智能机制的了解目前仍还属初级水平呢!
纳入标准[3-4]:家属及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临床资料齐全;完成随访;经CT、MRI等检查确诊的复发脑恶性胶质瘤。排除标准[5]:凝血功能障碍;严重肝、肾、心等重要脏器功能异常;有手术禁忌证;临床资料不全。
以上所言,如果给大家留下李某反对生理(神经)研究的印象,那真是天大的误会!心理与生理之联系那是永远割不断、从来就是相伴而行的。李某之陋见只不过强调在这种相伴中应增强心理学自身的自主性,别忘了自己的任务所在而已。“大脑并不思考,而是我们思考大脑”(尼采)这句耐人寻味的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当然,也不必视还原论为“不可接触者”。还原论是“污水”,但“污水”中有“孩子”(宝贵的实证研究数据)。要留下孩子,把“污水”换成“清水”(对数据作非还原论的解释)。否则,现在心理学家们非常热衷的那些神经科学研究的范式,其意义和价值岂非大大降低了!或许你会批评这种“换水”之举乃是一种变相的“还原”,不如还是把它正名曰“心理的神经关联物”更为贴切,因为你最多只能“还原”到心理的“机制”而非“内容”层面。比如你丢钱,心中懊恼,它一定会出现相应的脑变化。这种变化会在各色人等中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但你无法“还原”到你是丢了人民币还是美元?是丢了一百元还是二百元(差别太大可能有所不同),是在路上丢的还是在某个公共场合丢的?只要涉及思维的具体内容层面,绝对的、生理和心理严格一一对应的还原是不可能的。未来国内外的各种脑研究计划也绝对不会、也不可能把所谓“阐明学习、记忆和思维等脑高级认知功能的过程及其神经基础”引向这一方向。
安全技术方面,五建以“用技术和装备,让世界不再有危险的工作”为使命,首先从“标准化”入手,总结、提炼、开发了适用于工程建设现场HSE标准化的成果和实践,成为中石化标准化工地建设和安全实操仿真培训基地的行业标准。之后在“可视化”着力,与高校和科研单位合作开发,形成了“安全眼”和“立体定位”为代表的系列安全硬件产品,基本实现了“施工现场可视化”的目标。近期又开始在“智能化”聚焦,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开发智能化安全产,力争成为工程安全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成就高科技及安全领域先行者。
二、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朋友兼对手
国家“脑计划”中在“认知脑”之外还有另一重要部分即对类脑计算与脑-机智能的研究和开发(所谓“智慧脑”的建构)。我们一般以“人工智能”来概括之,其内容显然也与心理学关系密切。这就要说到当前心理学面临的另一热闹场景:人工智能呼啸而至,大有凌驾于人的智能之势。是否存在那种与脑和神经相连的具身心智并列且具有同等智能水平的、非人的离身心智呢?这是个问题。
人工智能对心理和心理学的关系,与其说是“帮忙”,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啻是一种颠覆——因为它要去掉“人的心理”中的“人”字,即把人的心理非人化!
其实,人工智能向心理学的入侵,最初的那扇门是心理学家特别是第一代认知科学家们自己主动打开的——谁让你附和某些心灵哲学家们也去高喊什么“认知即计算”“心理即计算”呢!其实,抛开计算不谈,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的关系其实是一种非对称关系。因为在对心理活动之过程及其机制的解释上,人工智能与脑和神经的解释力乃是半斤八两,也是帮不上“心理”多少忙的。但他们随着各自技术上的进步,又都自恃有能力继续向心理“挤压”。如人工智能得益于两大进步: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超大数据集的实现,人工神经网络系统就可更有效学习,于是出现了“深度学习”等新技术。本质上,人工智能是机器技术力量的外显化。至少在目前,它还不是什么新的物种或什么新的生命形式。人工智能要说有“灵魂”的话,那就是人给它配备的“程序”(数据与算法)。它根据程序行事,但它“自己”并不知道是在“行”某事。因此,你可以让人工智能不去做“下棋”这样高雅的事而去“杀人”,但这时恶劣的不是人工智能(智能机器)而是躲在其背后“指使它”(即安装了“坏程序”)的人。
现在大谈“人工智能已不满足于工具层面,而有实现与人类智能画等号的野心”,多半是既非计算机学者也非心理学家的一类人喊出来的。遗憾的是,有些著名人物如霍金也是此类中人。他认为长期或未来而言,人工智能可能不被人类控制,甚而“终结”人类在地球的存在。不过,幸运的是这可怕局面若想成为现实,则显然必须建立在强人工智能水平上。恰恰在这一点上,至少在目前,实乃多虑了。
所有的生理(神经)层面的研究,它们只是广义的或曰细化的行为外显指标,而不是心理本身;或曰,它们只是心理的生理相伴物——我们赞同心智和躯体不可分割的立场,应以这种“不可分割性”来改造二元论,但同时又要警惕还原论。
因此,现在需要对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的“朋友”关系作新的思考,其关键仍在“计算”概念。电脑上的计算与血肉之躯人脑上的“计算”(如果它也可“计算化”的话)有何不同?人脑的“计算”中是否有比算法更多的东西,或者说人脑的心理活动中在“计算”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不可计算或不是按算法进行的、我们尚未挖掘出来的成分?
仅从“经验”这一简单视角,两类“智能”的差距即可立判。
人工智能是否有经验?似乎有,不过更确切地说,它们只是某种经历:前面的计算留下可被再使用。所谓“深度学习”不就是如此学习的嘛!
人工智能的计算程序为什么叫“经历”更合适呢?因为它可避免把计算的操作程序理解为“主体体验”的错误。试问:操作程序的丰富、复杂化,最终会导致人工智能的“主体”产生,乃至使“经历”可升级为“主体体验”吗?还是,真正的“主体”另有来源(社会性的相互作用、主体间性的发展等),在“主体”发展形成之前,操作程序就只是“经历”而已?塞尔的“中文屋”实验早就论证了我们无法使机器获得真正的主体意识。
在此,让我们稍稍提及阿尔法狗(Alpha Go)系列所引发的有关人工智能的热议——心理学界对此反应似乎不大。我的看法是:阿尔法狗的胜利只能说是计算机工程师的胜利,是数学和逻辑的胜利。它说明在某些特定领域的数学计算和逻辑推理方面,工程师们制造的机器胜过人类的大脑。这就像人造的汽车比人跑得快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你可以说人的智能在某些方面输给了人所制造的某类机器,但并不是输给了什么更高一筹的“智能”!而且,未来这种输赢在很多方面将是常态,人类完全用不着忧心忡忡。
阿尔法狗走每一步棋接受的是计算机程序设定的“命令”。“命令”体现了命令设计者的意图。意图的核心是“合目的性”。电脑没有自己的“目的”,但电脑工程师有——赢棋就是电脑工程师的目的。赢棋了,电脑工程师的目的达到了,其为电脑设计程序的行为实现了所谓“合目的性”。电脑的每一步“行棋”没有这种“合目的性”,只是在执行一个程序软件所采用的算法。“合目的性”只有人有。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阿尔法狗的胜利,其“智慧含量”甚至远远比不上李世石走出的一步“臭棋”。因为电脑只是被动地执行算法,因而它并不是真的对围棋之妙有悟性之“感”,把下围棋当作一种艺术享受。在心理的各种“感”的方面,机器远远不如人类。破解这些“感”之奥妙,不仅电脑(人工智能)做不到,目前人脑(人的智能)也尚未做到——这些属于所谓“强认知”范畴,但它们正是心理学研究的职责所在。
再者,关键在于,李世石赢了电脑一局以后,高兴得很;但阿尔法狗赢了四局,请问它高兴吗?——这就是要害所在,即人有“主体性”,有“自我”,有图灵50多年前就说过的一系列他认为机器(电脑)永远不具备的诸如“仁慈心、幽默感、是非观、友好态度、犯错内疚心理以及恋爱心情”;甚至“享受草莓和奶油的美味”的主观感觉体验也在此列(图灵的话我在多年前某篇文章中曾引用过)。说句笑话,人在实在斗不过电脑的情况下,作为有主体感的你可取最下策:拔去无主体感之电脑的电源或取出电池。除非电脑它也具有主体感了,能识破你的意图与你怒目相对,并与你争夺电源和电池的控制权!
至于强认知与弱认知或曰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对立,对心理学家而言,不在于是否认识到这种强弱之分,而在于是否承认这种区分最终可被跨越,即认可上述这些电脑“不能之处”会越来越少直至最终实现人工智能对人的智能的完全模拟如同亲手制造了一个与自己“等能”的亲兄弟?于是,“心-身”关系在人工智能横插一杠的情况下,又演变成了某种“心-物”关系。
人工智能若想升格成为与人的智能“等能”的兄弟面临着两条路的选择,即一条还是走“类身”之路,使机器变成人脑或无限接近脑,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功能);另一条则是走“非类身”之路。
在返程之前,我们专门来到格罗布尼克汽车世界。这条赛道的设施自然是比不上那些国际级赛道,但赛道旁小吃店的意式浓缩咖啡的味道极佳。如果你也希望沿着我们的路线享受这样一段跨国之旅,那么这里非常值得一试。
先说第一条路。有人认为未来可以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的统一,两种智能将成为智能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员,甚至认为“不认可统一是一种唯心论而不是唯物论”。其“唯物”的逻辑依据是:人类智能的出现说到底是自然进化之功而不是神创;既然不是神创,那么总有一天科学家会探尽进化其妙,压缩时间,使进化速成于一时——不仅机能可以速成,机能赖以依靠的身体(特别是脑)也可以速成。
于是,实现统一似乎又有两条分路可行:一条是走“软件”分路,即通过算法的不断提升使冰冷机械持有的人工智能也与血肉之躯具有的人的智能达于一致,不管它是否具有“人形”。这条分路的前提是计算及其算法能够使非人的机器获得前述的“主体性”“自我”“合目的性”等人之特质。于是,离身心智的说法成立了;再于是,上帝也就存在了。这条道是否走得通,请各位自辨。
或者走另一条制造“硬件”的分路,即通过首先制造人工生命,继而在这个人工生命上实现人工智能。这意味着智能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也可以人工合成、制造,这似乎避免了神创智能的陷阱。对此,且不说它是否走得通,即便走得通,你现在连个毛毛虫都不能制造,连两个神经元之间的信息如何联系都不甚了了,现在就谈什么经由人工生命达成的人工智能,不是有点像神话故事吗?
目前比较多的具有中庸特色的说法是:两者会越来越近,但不会最后重叠。不能重叠的部分,也许就是某种“自然机制”——它既不能被算法程序化,其进化过程也不能被压缩化。
当然,我们不排斥两种智能未来在“自然机制”以外的“可计算化的非自然机制”部分,可以有很长一段合作之路同行,用不着担心前方有什么“计算危机”。于是,对人工智能学家来说,特别在软件方面,如强化学习、深度学习及其策略网络和估值网络等,不妨对人的智能(心理学)的研究保持某种开放的姿态,或许从中可得到某种启示以完善自己的设计。
再说另一条所走的“非类身”之路。
选取了2017年2月到2017年12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48例膝关节炎病患,随机分成了治疗组、对照组。治疗组:病患24例,男性病患16例,女性病患8例,年龄在42-74岁,均龄49.32±5.72岁,患病时间持续1-8年,均值4.97±2.21年;其中9例左膝患者,15例右膝患者。对照组:男性病患15例,女性病患9例,年龄在41-73岁,均龄为50.21±4.32岁,患病时间持续2-8年,均值为4.52±3.46岁;左膝病患共有9例,右膝患者15例。
William Bernard Jones用四句话(四个“视角”,六个话题和一个从属话题)阐述了本场辩论的总话题(“干预叙利亚”)拟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叙利亚贫民所面临的大屠杀问题。
人工智能完全可以独自上路,不必依赖于人脑,不必考虑向人的智能看齐。尤其在硬件的纯技术方面精益求精,如分布式计算技术、支撑着运算的CPU和GPU质和量,你可以继续去开发、升级,使计算机的计算水平远超人类,特别在所谓“弱认知”的领域——正像当下计算机科学家们如火如荼所做的,因为制造如此的非人“超人”甚至比制造人还要容易。正如司马贺(1986)所指出的:“计算机能模拟人的智能活动,但计算机和人脑不一定按相同的原理(注意:指的是原理,而不是硬件)进行活动,所以计算机不是模拟人脑的真实活动,而是实现人脑活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反过来推断人脑进行的心理(认知)活动的原理与计算机运行的原理相同。这实际上说明了以计算机运行的“计算”原理作为认知活动原理的逻辑不能成立。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人工制造的非人的智能”。同样,这条“非身”之路,是否在无心理学帮助的情况下,最终可以实现从“弱认知”向“强认知”的跨越,我们现在并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
这种对立的实质依我简单化的理解是“人”与“物”之争,反映的是当时某些人对所谓“粗俗的物(自然科学)‘霸凌’高贵的人(人文科学)”的不安和恐惧。这种霸凌趋势今天无论人文学者们如何不满和抵御,其风更盛那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虽然两种科学都有了飞速发展,但它们的发展不可同日而语且性质完全不同,因为说到底,世界是“物”领先于“人”的,是人诞生于物,而不是物诞生于人。至于对“人”的最终说明,物的科学(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人文科学)孰为主导,各自作用何在,作为“人学”的心理学应扮演何种角色,处于何种地位,这些争论将长久存在。
刘红杰等[16]分别采用水蒸气蒸馏法、超临界CO2萃取法、石油醚超声提取法及石油醚微波提取法制备广东艾叶挥发油,并比较了各种提取方法的得油率及化学成分种类,结果显示,石油醚微波提取的得油率最高,是水蒸气蒸馏法的3倍之多;但水蒸气蒸馏提取的艾叶挥发油中所含化学成分最多,石油醚超声提取的挥发油化学成分最少。仝燕等[17]比较了水蒸气蒸馏法与超临界CO2萃取法对香薷挥发油提取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虽超临界CO2萃取提取的挥发油总量较高,但水蒸气蒸馏提取的香薷挥发油中活性成分百里香酚、香芹酚的含量是超临界CO2萃取法的3倍。
也有反对上述观点的,其论据是:人的整体布局和把握的能力不同于简单地运用符号和规则。计算机不能模拟意识活动,因为有意识的思维是不符合算法规则的。要使计算机有人的思维和智能,其结构必须类似于人的神经系统,并主张从低等生物功能的模拟入手。于是看来还得回到第一条“类身”之路上。
我的立场倾向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的滞后,人工智能或机器人的研究在保持对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开放态度的同时,更要习惯于自己在路上摸索前行。人工智能要实现真正的与人的智能等同化,即强人工智能假设的要害之处在图灵所说那些“感”上。当然,只要暂不碰触这些难啃的硬骨头,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还有一段很长的合作之路可以携手同行。这段同行路,不妨仍以“计算”为导引的旗帜。因此,我们也许应该重新认识“计算”前方的认知“悬崖”,它们的出现(到来)尚十分遥远,甚至不排除某一天人类真的能证明“终极计算”的出现!
对那些主张“应当而且可能”以人工智能来实现人的智能的心理学家(第一代认知心理学家)来说,不仅可以专心致志地进行“可计算化的非自然机制”的研究,你还可以与计算机科学家一起,尝试把计算用于“自然机制”的研究上,在双方的合作中寻找共同语言,利用人工智能已有的基础(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结合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自动化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对人的心理活动(尤其是情感、意志、性格、创造等)全面进行人工机器模拟。国内沈模卫教授团队在“强认知”领域就已做了不少出色的研究。
至于对回归“具身”立场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家而言,保持定力,埋首于深入进行强认知及更高层次的情、意和人格层面的心理学研究,这方为正道——尽管非常之难。因为人工智能(电脑)与人类智能的学习方式是不同的。如何将后者融入前者,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现在,最强的人工智能也比不上几岁幼儿的学习能力,因为它们的学习方式不一样。
第二代认知科学有别于经典人工智能那种依赖于符号推理和逻辑架构的路径,它采取直接知觉理论或生态心理学这个思路,首先在让机器人拥有“生态自我”心灵(即恰当的自主运动能力)着力,这或许是强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新希望所在。
生态自我概念来自吉布森的认知理论。我认为吉布森意义上的“生态性自我”概念,是目前为止心理学所能贡献于人工智能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前面谈到的“优生进化”目标的实现就有它的功劳。
吉布森的理论完全不同于心理表征计算的认知理论,它采取了一种具身的认知理论,认为身体在认知活动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是一种非大脑(或心灵)中心的认知立场。它以简单的“知觉即行动”原则来解释动物获取事物、躲避天敌,以及对环境的各种适应的行动等。动物能够通过视觉,直接拾取到环境中的光流,这些光流所组成的光线陈列提供给它们的知觉-行动耦合可能性的信息。动物所栖息的地方,就是基于提供给它们的各种行动能力的环境特征集合。吉布森以所谓“动允性”(affordance)来概括其“知觉-行动”观。
人类或许可以通过吉布森的认知理论,有一天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让机器人拥有“生态自我”的心灵(即恰当的自主运动能力)。按照这种理论,我们的意识并非完全来自大脑,而是来自包括大脑的整个身体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从与环境进行交互以便获得生存资源并能区别自身与环境的差异的角度看,“自我”概念中最基本的一个模块应是吉布森意义上的“生态性自我”概念。至于其他什么“主体间自我”(与他人相区别的能力)、“延展性自我”(时间上不同的自我能够进行统一认知,具有各种知识的自我)、“私有性自我”(具有第一人称私密的感受性、情绪、意向和信念等)、“概念性自我”(能够认知自己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及具有上述四种自我概念的所有功能),这些等级的“自我”如何在计算机上实现,只能逐步探索其路。至于当下,我们还八竿子打不着它们呢!
三、科学与人文取向:跨世纪缠斗
谈心理学两种取向似应从“两种文化”说起。数十年前斯诺(C.P.Snow)提出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说。他认为两种文化的对立全方位地渗透于人类社会与精神生活,对人性和人心领域表现出某种隔阂、误解、相斥和敌对,可不仅限于心理学。
现在的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研究的最新动向是:把“优生进化”即智能机器的自主心理发展作为新的目标。所谓“自主心理发展”就是它有一套“自主发展程序”,有了这程序,计算机的感受器和效应器就可实现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使计算机的“心理能力”得到发展。据说,有心理发展的机器人的原型已经制出,如Danwin V和 SAIL。
公路桥梁养护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为了提高公路桥梁养护工作的开展效率与开展质量,就必须要加大公路桥梁养护工作的经费投入。首先,有关部门要设立专门的公路养护经费管理中心并让专业人员对公路养护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根据公路桥梁养护的实际建设情况与加固维修状况进行资金的划拨,以此保证公路桥梁养护后续工作资金的充裕性;其次,公路桥梁养护工作需要不断引进高科技维修设备,以此保证公路桥梁养护工作的高效开展;与此同时,公路桥梁养护工作还需要引进具备较强技术性的专业人才,以此保证公路桥梁养护工作的正常运行[8]。
正因为心理学学科的特殊性,心理学成为两种文化缠斗的主战场那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本来的“自然科学文化与人文科学文化”的文化分歧,变成了“科学取向与人文取向”两种取向。它们在学术价值观、知识的基本来源、具体研究方法和分析水平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对立。(顺便说到:两种文化在心理学中的起源,我觉得咱们别老拿冯特说事。冯特未见是两种文化的始作俑者。也许,当年冯特以《生理心理学原理》和《民族心理学》两书开创心理学之际,其脑中所想的只是区分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或者他认为心理应从这两个角度去探索,而不是区分什么两种文化:前者是科学主义,后者是人文主义。他当时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后人从“群体心理”有意地走成“人文”之路那是另一回事。另外,把布伦塔诺说成心理学的人文始祖,似也未尽然——后文还会有所涉及。)
我还想对“科学”与“科学取向”的区别说说自己的看法。
在现今谈及“科学取向”的语境下,其中的“科学”常常指的是自然科学。
坤二少爷自幼聪颖,三岁能背唐诗百首,四岁呤诗作赋,乡人谓之神童。只憾张神童生逢乱世,读至县立麟山中学时,尚未完成学业学校停办,便辍学回乡。适逢老父过世,长兄张铁头闯荡江湖,油坊无人打理,便子承父业,年方十六做了油坊主。
从表1结果可知,浮选金精矿中主要有用元素为金、银,可在后续浸金工艺中回收,铅含量为3%,达到了综合回收的要求。
我意在与人文学科对应时,还是明指“自然科学”为好。斯诺时代的自然科学受限自身的发展水平,尚不能真正染指人文科学,故把它们在两种不同“文化”的旗帜下集结是说得过去的。今天时代不同了,再把“科学”与“人文”对立,我觉得似未见妥切。
这主要基于两点思考。
其一,人文学者你可以拒绝自然科学(是否拒绝得了那是另一回事),但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科学”的对立面呢?“科学”非自然科学所独享。难道“人文”的研究不讲科学性吗?“科学”二字不也常缀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后嘛!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只要是科学,就有科学的属性。科学是人文科学的上位概念。心理学的人文取向更得讲科学,不应该自我放逐于科学之外——此恐也非人文心理学家之本愿吧!“科学”并不与“人文”对立,它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只与“非科学”——或说得更具体点——只与迷信、巫术、臆测、妄想对立!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假设可能并不像“硬”科学那样容易通过实验进行验证或推翻。这里的关键是“实验”,而不是“证实”或“证伪”的目标。打个比方,你的“身体”(科学性)必须要经过体检,这是必须的,至于是通过什么手段:X光机透视还是CT扫描,抑或中医的望、闻、问、切手段,那又当别论。
其实,所谓人文取向的心理学并非没有实验。社会心理学中的“刻板印象”系列的著名实验研究众所周知。当然,相对而言,实验方法并不受到人文-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取向的心理学)的青睐,因为人类行为非常复杂,不可能通过实验去全面验证人的行为或解释为何出现这些行为。实验方法在人文-社科中还受到伦理的约束。
在我回办公室的路上,张大爷跟了过来,悄悄问:“大夫,能过这个年不?”每次面对家属的这类询问,我只能抱歉地笑笑,“我们得看病情的发展,现在看阿姨之前拍的CT,两侧肺病变都很严重,预后特别不好……”李阿姨之前的CT显示高密度的结节影像棉絮一般遍布双肺,“而且还有胸腔积液,我们只能尽量做,但不敢保证能活多长时间。”
同理,“人文”似也不宜为“人文取向的心理学”所独占。至于有些学者甚至悄悄地把“人文”二字有意无意地换成了“文化”,继而实际上把“科学取向”逐出“文化”范畴,认为凡做自然科学心理学研究的,都是不够“文化”资格的,文化外衣似乎只能披在“人文”取向的身上。这就更不足取了。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现今的两种进路已踏上融合之途。有学者(李恒威等)呼应斯诺当初曾提出的“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根据认知科学已深深涉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很多领域的现实,敏锐地指出认知科学可成为“再启两种文化的对话”的渠道。如前所述,两种文化交织于心理学(认知科学)乃是由于心理学研究的是“人”这一特殊性所决定的——“人”既是“物”,也是“心”!这样的“再启对话”历史使命,舍我心理学其谁!
主要从植物群落的外貌特征、景观结构、空间特征、游憩利用现状4个方面对样方进行调研。详细记录各个样方地理位置、植物种类、数量、特征数据(高度、冠幅、胸径、多盖度等)、生境条件等。同时根据植株干、枝、叶的生理性状评估树木的生长势,描绘样地平面图,并拍摄照片以作为其平面分布和竖向景观的有效补充。
国内很多学者(朱滢、韩世辉、周晓林等诸位——请恕所列不周)在社会神经科学领域的坚实的实证成果在这一对话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引学界瞩目。当然,这些研究若从“证明了某些社会心理的神经基础”上更进一步,跳出纯生理机制的层面,对心理与生理的融合做出统一的机理解释,那就更完美了。其他领域的神经科学研究似也面临类似的状况,即为我前面所说的“启示”与“反哺”的不足。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因创立情绪神经科学而声名远播的达马希奥(Antonio R.Damasio)的工作。他认为“躯体识别机制”(Somatic marker mechanism)和外部环境经过感知在脑中形成的表象一起,相互协调而决定个体行为。而且情绪引起躯体标识机制是先于我们的高级思维在进化中形成的。这一思想我认为已超出生理机制的一般解释水平,它对以人文学科最引以为豪的“情感”而论,其对两种文化之争的最终结局的意义不言而喻!
两种文化或两种取向的融合将因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诞生而步入新阶段。如果你承认“认知神经科学”是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结合,因此,当认知心理学有变了——从以“计算”为基础的第一代认知心理演变为以“具身”为主要特色的第二代认知心理学,那么,它们相结合的认知神经科学当然就是第二代的了!至少后者在选择研究问题和研究方向上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上应会有新的不同视角。
我就从这说起吧。不可否认,当今心理学研究几乎与脑及神经须臾不相分离,称它们为心理学的“兄弟学科”绝不是套近乎。在研究心理时,脑、神经层面的相关探索无疑大有裨益,怎么深入都不为过(我这样说不是怕当什么“对立面”,而是真心体认如此)!它们使心理学能与时俱进换了容颜,功不可没!而且甚至可以说这类研究现在尚属起步阶段——因为诸如大规模皮层的动态活动、神经回路、神经元、突触及其神经递质、膜及其离子通道、生物化学、基因-遗传学,乃至分子生物学、分子及其自组织、化学键等多层次对心理学之作用的机理挖掘,以及ERP、fMRI、fNIRS(功能性近红外光谱脑成像)、PET、MEG等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心理研究的助力,当下或许只算刚起了个头呢!
当然,自然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当涉及到“人”时。但,此时请不要夸大其“软肋”——尤应避免对其妖魔化,用平克(Steven Pinker)的话说就是“视(自然)科学为敌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只要是科学,它就与“真”有关。求真是“科学”之根本的、核心的属性。我将之称为任一“科学”所应必备和必然具有的“认识论属性”——尽管人文-社会科学还有“善”与“美”的任务,但它们并不排斥“真”的任务而且要求联系三者通力合作去展开研究。
对心理学的“任务”而言,这就要在更深层次上明确心理学的学科属性。
在心理学的性质与对象问题解决并取得共识之前,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谈及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依李某愚见,说“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属性,又有社会科学属性”是一种懒汉思维,说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也等于白说。请问:它的哪一部分有自然科学属性?——请不要把不属于你的神经科学硬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哪一部分又是社会科学属性的?——请不要把自己的手伸到人家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的口袋里!心理学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有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有对象,双方的手才不会乱伸。不能笼统地说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现象不只是心理学一家去研究的,但其他学科对心理现象研究的进路或角度与心理学不同。
可能会有人指责我的观点陈旧,认为这一立场乃是基于常识或基于“名声不佳”的二元论。的确,还原论碰触到了严肃的“身-心关系”问题。心理学家不能不察。
在心理学中,“两种取向”之争的说法要比“两种文化”的说法更准确些。它们是否能够“并肩同行”,端赖心理规律(与我在下一节要谈的“心理的过程与机制”有关)的普适性是否取到共识,即两者能否在“心理学到底研究什么”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对人文取向者可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是一种“转向”:从主要以心理内容为研究对象(它们常以所谓“影响因素”的面貌出现),然后才能思考何种取向才是真正朝向这一目标前行的。我的观点可能有点偏:如果对象(目标)不一致,永远最多只能形成统一战线或是两条同向而行的两条平行线而已——只不过不时地将自己的研究所得相互印证(友好地)或相互炫耀(非友好地),而不可能成为同一支队伍!
为什么要坚持“早上四点起床”呢?这是为了在上午完成上司交给你的工作,然后在下午开始铺垫新工作。能否灵活运用一大早时间,是能干的人与不能干的人之间的分水岭。对上班族来说,充分利用早晨尤为重要。半天干完全天活,人生的顺逐就从早晨四点开始。关键并不在于“早起”,而是重新审视“早晨的灵活用法”。
遗憾的是,在当前国内心理学界似乎有那么一股风,它有意无意间把上述“取向之争”上升为“文化之争”,又以“文化”与“科学”的对立,继而假“文化”之名,抬高“人文取向”而贬低“科学取向”,特别强化后者对心理研究的无能。它貌似推崇“人文取向心理学”,实际伤害的是整个心理学。这种挤压甚至比神经挤压、人工智能挤压还要强势,因为它似乎常常伴随着某种所谓的“思想正确”。
在“文化”的大纛下,站在科学心理学之对立面的不仅有“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人马,还集结了来自其他欲染指心理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他们形成了对有确定研究对象的科学心理学的挤压。我把它称为“泛文化的挤压”。如今,心理学家谈文化也是一件很时髦的事。不谈文化好像显得很没文化。我之所以用“泛文化”一词,是基于凡是从社会、历史、国情、本土,甚至阶级、民族等角度对心理的思考,某种程度均可纳入“泛文化”的影响范畴。
文化思考不是坏事。以上各种角度的研究也是绝对必要的。但我对文化或泛文化的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或在什么角度上,影响到了心理,有些疑惑(这将自然会涉及“心理本体”的概念,下面再谈)。我认为心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超文化性,这说到底仍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关。“科学心理学”并不拒绝文化,而是应以自己的特有对象,来搭建研究的整体框架或以之为指导思想,将文化和泛文化融入于己,就像中华文明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吸纳外来文明一样(纯粹是比喻)。否则,心理学势必消融于其他什么各种学了!
下面我主要从文化或泛文化对心理学的影响谈谈粗浅的看法。
在座年岁稍长的同志一定记得“文革”前的“葛(铭人——“革命人”,姚文元化名)陈(立)之争”,以及那些诸如“大粪是否香丑”之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心理学的干扰。现在人们不再提这类近乎脑残的问题了。但它们在换了某种看似“思想正确”的马甲之后,仍依稀可见其身影。
文化对心理的影响我认为主要反映或积淀在“主体间性”上。主体间性因我读书少,理解浅,我认为它说到底不是悬浮在空而会在具体的个人心理的加工层面反映出其特征来的。
那么,是否有中国文化下的中国人特有的心理加工层面的规律,我不敢骤下断语。我只是希望不要把心理学变成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
现在有不少人呼吁建立中国文化心理学。我认为,从创立真正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心理学到一般地承认心理学存在文化影响或文化烙印,这其间其实存在不同的层次。粗粗分析,大致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所谓的中国文化心理学,它有自己的独特范畴体系,甚至独特的研究对象。极端情况是连西方的现有的知、情、意、人格等范畴都不用——不仅是不用这些范畴词,而且连它们所指向的对象本身也有所不同,甚至大不同(注意:是“对象”不同哦!),即其内涵都要重新厘定。
如此,这样一种中国本土文化心理学,如要与西方心理学进行交流,则必须通过某种转换才能进行。换言之,你要说明:中国心理学中讲的某某东西,就类似于外国心理学中的什么东西。注意:是“类似”,而不是“是”哦——因为你的“心理”与人家的“心理”不一样,只能做到大致对应。为什么只是“大致对应”,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对象本身”有别。目前我们似乎还拿不出这样的基于中国文化的本土心理学。是否真有这样的“中国文化心理学”,我不知道。而且,中西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真的是那么对立吗?究竟有无共性的、普适的东西存在?在现代之中、西人的身上,其心理机制、加工过程的差别多大?或共性多大?文化本身在变,因此浸润其中的人的心理自然也在变(内容大变,机制小变)。但这种变是“轨道”(火车线路)不同,还是轨道相同(比如走的都是京沪线)只是列车不同(你乘的是用电的高铁,我是烧煤的绿皮车)?
在所谓“文化”对心理的影响只在“心理内容”的层面发表各种高论,我无话可说。但是,这有使心理学混同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一定风险。至少,它不应成为心理学的主体部分。因为本质上,强调“文化”的心理学是一种关于心理内容的心理学。我的立场很明确,心理学是关于心理形式的心理学。
概括一句话,心理内容有其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甚至阶级的、民族的制约性,但心理的形式未见有这些“性”。对现今人类来说,其“心理形式”如同一个“工具库”,大致上人人皆有(无关人种、民族、文化、社会、阶级、群体等),区别的只是因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一句话,因经验的不同而有的工具用得多,有的用得少,因而导致其使用效率或使用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工具(“心理形式”)的总类并无大的区别——至少没有某些热衷“文化”者设想的那么大。我想起几年前周有光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各自持有的关于中西文化“双文化论”和“河东河西论”的著名之辩。虽然他们谈的是文化,但对我们思考心理形式的普遍性很有借鉴意义,有兴趣的同志不妨参阅。季先生的观点因其暗合人们民族自豪感的高涨和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因而附和者众。但坦率地说,我赞同周先生的观点。当然,因文化或泛文化因素致使“工具库”内的工具种类有别(一如前面说到的所谓“机制小变”),尽管这不足以构建另一炯然不同体系的心理学,但这种差异也不应忽视。
第二层次:研究对象与西方心理学一致,如知、情、意等(注意:不是指知、情、意“这些词”一致,而是指这些词所指向的“对象本身”一致),但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即你把它们叫作知、情、意,而我们则用别的什么范畴来指称它们。
这里,可以稍提及佛教中的“唯识学”。我不知道“唯识学”是否属于这一层次还是上一层次,但至少可能达到了这一层次。要把唯识学的佛学概念(据说它有丰富的心理学内容,特别在认知领域)改造成现代人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心理学范畴,不妨先从构建“唯识学认知心理学”开始。
唯识学是一座蕴藏丰富心理学思想的富矿。国内曾有著名学者半开玩笑地说过:如果康德看过玄奘所写《成唯识论》一书,也许其《纯粹理性批判》就不必动笔了!因为距今1300多年前的玄奘大法师就达到当时哲学思维最高峰,涵盖了哲学所讨论的几乎所有最重大问题(北大辜正坤教授)。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心理学界对此是认识不足的(尚不及国外的如瓦雷拉(F.J.Varela)这样的有识之士),特别是相应的实证研究更是长期缺乏。但近年来状况有所改变。以唯识学为纲的具有完整体系的心理学(哪怕仅限认知心理学)似乎目前尚未面世,但国内有一些学者做了一些令人称道的开拓性工作,如李庆安、彭彦琴教授们的工作。彭彦琴教授等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比较了“现象学心理学与佛教心理学”两者之互补性及反传统心理学的“意识自然化”共同立场;以佛教五蕴系统为基础,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信息加工模型;从中西方的“惟我”与“无我”之别,论证自我的不同发展阶段;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注意力训练为“正念”的核心机制等研究;李庆安教授等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例,分析唯实学之“精进”的结构与功能并编制可实用的测量工具等,均难能可贵!但也许我们对唯识学寄希望过高——尽管它富含心理学元素,但它是否足以支撑整个心理学科的大厦,尚属未知。
第三层次:对象与范畴仍然高度一致,但每一范畴都有中国文化的解释,即有所谓中国文化的烙印。如人格特质,你可以仍然用人格特质这个概念,但不是大五人格了,而是其他中国心理学家研究出来的人格结构了。如王登峰的七个维度、张建新的六因素、许燕的三因素,等等。
因此,我认为,现在我们谈论所谓中国文化心理学,恐怕还仍然停留在这第三个层次,因而谈不上是真正的中国本土文化心理学。对现存的心理学研究,它到底具有西方文化属性还是东方文化属性,哪怕我们不能一个个加以说明,但如果要使人信服你的本土文化心理学的话,至少应该以典型的研究为例,为它们分别贴上“这个研究属于西方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那个研究是属于东方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之不同标签吧!或者如一时从中难觅到“属于东方文化心理学”研究的话,那请告诉我们这些研究该如何按“东方文化心理学”的规范去做?——这并不难,打开任何一本国内心理学刊物,逐篇进行检查、改写即可。不过要知道,以三层次视角来看,“属于东方文化心理学”与“用心理学研究东方人的心理”两者可不是一回事哦!因为,前者是第一层次,后者仍可能为第三层次的研究。
因此,在以上三个层次中,对创立中国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现实可能性来说,第二个层次最具操作性。我们应该向第二个层次努力。
目前在第二层次,话语权似乎还在西方心理学家的手上,因为现在心理学的范畴体系是人家提出来的。我们不妨也在这方面学学人家如何善于从现实中提炼这些范畴的,或许对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建构有所借鉴。
几年前我在天津师大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说过,我看过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为北师大王芳同志),其中讲到所谓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发展历史的“双生性”,即“当我们梳理美国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主题更替脉络时,毫不意外地发现其与同期的社会发展历史宛若双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们针对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你不能说它们只是西方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人家自己也不把它们添加上“西方文化”的标记。
以下是某些典型的“双生”: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种族主义、攻击、政治宣传、群体士气(“社会认同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刻板印象、偏见、歧视;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服从与反服从、少数派影响;9·11事件、恐怖主义——存在焦虑应对、恐惧管理;如此等等。这些概念虽源自西方社会,但你认为它们不具有跨文化性吗?文化的多元不应该与心理机制、心理规律的普遍性相对立。而且我认为,这种“双生”现象不只出现在社会心理学中。与人的不同实践领域对应的各种心理学,都可能有类似的“双生”现象,如教育心理学。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时代变迁的大环境中,首先提炼出若干属于教育心理学的普遍性范畴,继而也梳理出某种“双生”。
其实,所谓“普遍性范畴”,也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提出足堪统领整个学科领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尚有困难,不妨可在前人已提出的现有范畴基础上,退而求其次提出自己的次级范畴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就像Benoit Monin和Dale Miller,在研究刻板印象和决策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时,发现“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效应那样。后者同样具有原创性,并且引领了后续大量的甚至跨领域的研究。
回到社会心理学上来。中国社会心理学家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很多,但为什么中国社会心理学家还较少地从中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的、带有一般心理机制意味的概念、范畴、理论呢?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我了解有限,所知浅陋,有些研究还是值得称道的。如金盛华教授提出的“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及后续系列研究、乐国安教授关于“集体行动整合性模型”和“网络集群行为分类框架”的设想、俞国良教授关于国民幸福感在社会转型特殊阶段的“震荡与变迁”的观点、许燕教授关于自我和谐作用的论述等等。可以说它们有的已具有上述“次级范畴”的意思了。有的——恕我直言——若以是否提出“既为原创,又能开启后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甚至诞生新的学科分支的核心范畴”之尺来度量,似仍嫌不足,尚处于待提升之“临门一脚”的临界点上。
目前,这种提出原创的、可以开辟出一片研究天地、引领后续研究络绎不绝跟进的“普遍性范畴”的局面似不多见,即使在喊声最响的所谓文化心理学领域亦如此!这是因为中国心理学家不够聪明,还是另有深层原因?我虽然对此设问,但因自己就在“不够聪明”之列,因此我也不知道。
四、心理本体:能否为“心理”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以上分别从神经科学(“脑理学”)、人工智能(“脑外学”)、人文社会科学(“心里学”)以及心理学自身学科弱势现状的角度为心理和心理学所作的某种“维护”。我知道这种维护是无力的,因为它们更多是从“心理学不是什么”的角度所发的议论。那么,到底心理学该是什么样子呢?这就涉及所谓“心理本体”问题了。关于“心理本体”的想法,在我脑际已萦绕多年。它一直伴随我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哪些问题属于心理的“本体问题”?一般指:意识是否可等同于或有资格成为心理的本体?如何跳出早期心理学对“灵魂”“意识”的本体执着?心理学作为一门“人性”的科学,其人性之性质体现在何处并如何有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心理的本质、源头、存在的平台、活动的场所到底存在与否?这个场所到底是否有别于生理场所和内容场合而有其独特性?心理的运作是否就是心理加工的过程与机制?如此等等。
前面谈“文化”时所提到的“心理形式工具库”之想法自然支持“心理本体”概念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前我在很多场合曾经常谈及它。“心理本体”之说李某不是第一人。远的不说,稍早就有李泽厚先生的“心理本体论”——它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心理学的探索,其核心是“从文化解释心理”,认为“心理是文化无意识的积淀”,于是形成“文化心理结构”。“积淀”确是一个好概念,前面再加上“无意识”,更使其增加了方便施用的领域:维果斯基的历史-文化学说、福多(J.A.Fodor)的“模块论”等归根结底似乎都得借助于它。当然,福多的“模块论”较之李泽厚的“积淀说”既有共同之处,但所指之时间跨度也有区别,前者历时更为长久,它涉及史前的进化;而后者仅与文化人类学的历史相关。就总体而言,两者都是大跨度,也都属于“意识前史”。
心理学家可以接受“积淀说”,但不能止步于此——因为心理学家与哲学家的兴趣焦点不一:心理学家既对如何积淀本身感兴趣(由进化心理学和比较心理学研究之,其具体目标是对前述关于文化导致的所谓“内容大变、机制小变”中的“机制小变”提供细节的说明——这是难度很大的纵向研究,因为它有赖于文化人类学的援助);更对积淀之产物在人类(人)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如何实际运行的感兴趣(这是当下各心理学分支正在进行的横向研究)。仍以“工具库”类比,纵向研究是研究工具如何入库的(文化如何积淀),横向研究则是研究已入库的工具如何被拿出来使用的。
在“心理”或“心理活动”层面,是否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可分性?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是否存在相对脱离心理内容的心理形式?这一问题又可换一种说法,即是否在心理的生理机制和心理的内容两端之间存在着一种“既不研究生理机制又不研究内容的中间科学,即心理学”?的确,如果不承认心理学的这种“中间性”,尤其是不肯做心理形式和心理内容的相对切割,那么各种丛生的心理学就会变为各种社会-人文科学,如社会心理学变成社会学,管理心理学变成管理学,教育心理学变成教育学,如此等等。
当我们说“心理的形式与内容”不可分时,实际指的是任一研究者当下所进行的某项研究,它总是具体的,当然不可能是纯抽象形式。但是,该项研究的目标又应该不是指向内容的,而是指向“心理的过程与机制”的,即通过内容而实现对心理形式的关注。因此,它是一项心理学研究而不是内容所属的其他某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心理本体”当然得建立在“心理存在说”之上。你可以批评这种观点陈旧、庸俗如民间心理学。你的批评或许有道理,但至少难以否认这是我们与民间心理学友好的根本原因(民间心理学并不像其名称所示,如“民间物理学”等那么庸俗——此处不做详细分析)。100个心理学家(常人更是如此)的心里也许有100种关于“心理”的说法(模样)!那么,哪一种模样与哪一种心灵哲学更为合拍呢?继之,又是哪一种合拍才是更合理的呢?如今为“心理学”找个安身立命之所(或者用时髦的话说“工作的平台”)真的很难。这本质上还是与确定心理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有关。很遗憾,这项“找对象”的工作如今并未成为心理学从业者们的共识,虽然在心理学大旗下汇聚并端着心理学饭碗者众且其乐陶陶。某些所谓的心理学研究,连当年认知主义革行为主义命时的水平都谈不上,因为没有对心理过程的揭示,走的还是简单的S-R老路。
当然,说“心理存在”,不是说在脑中有一个虚空的平台,然后让心理加工在它上面进行;而是说,这些加工及其所形成的“网络(结构)”本身就是平台!平台是加工所构成之物!
去年(2018)理论心理学年会前,河北师大的闫书昌教授曾来电邀我与会。我乘便向他建议理论心理学界的同仁们不妨从“心理本体”的角度,梳理史上和当今心理学大家(师)们的观点,看看他们各自是“视心理为何物”的,并且选择适当的维度(如“本体”指向的清晰程度、形式化的不同层次等)将其排序或归类。
一般而言,心理学史上各家理论、流派,对“心理本体”并没有明晰指明,只谈“对象”而无涉“本体”。而且所指“对象”,也多粗略说到“经验或直接经验”“灵魂”“意识”等。把心理本体简单归为“意识”“灵魂”这是刚脱离哲学母体之襁褓时期心理学所普遍携带的印记。
要能为心理本体彻底解决“居无定所”的难题,心理学的确应在诸多心灵哲学理论派系中,寻找到合适的可相互依靠的同盟军。在过往心理学自身的发展史中,一切偏重于心理的形式方面的理论,我认为都是我们今日可为“心理本体”寻找安身之所的希望之地。比如,格式塔的完形甚至并未得到认可的“感觉元素”等都是有可能重新解释赋予新义的有用遗产。
再如,布伦塔诺心理学思想尽管从意识出发,但能鲜明地提出心理学不研究意识的内容,而从“动”(过程)的角度来探讨心理现象,实属不易,闪烁先知者的智慧光芒。我觉得这一思想对我们探讨“心理本体”有极大的启示。布伦塔诺的这一思想的科学引领作用有点被后人低估了。他以意动心理学的创立名世。何谓“意动”?简洁回答就是“意识的动作”。他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我非常欣赏的观点是:意识的动作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意识的内容(意识所承载的)则不是——尽管它们不可分离。可以说,布伦塔诺是主张心理学属于形式类科学之第一人——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无此意识(抑或不同意)。
布伦塔诺的意动概念,必然引发另一重要的后续问题:“意”为何动?对此的回答,势必又会引出“功能”和“意向性”两大核心概念。它们都与心理的动力机制有关。人文主义的传统也许是由此而确立的。是无心插柳还是其本意?抑或只是“意动心理学”可能演变的走向之一?
不能因为布伦塔诺强调对内省经验(实际是迥异于感知经验的体验)的重视就称其为人文主义的开山鼻祖,千万不要轻视他对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意动)加以区分的重大意义。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人文之祖,不如说他是最早明示心理学未来真正研究方向(本体)的先知者!
布伦塔诺对心理现象以“心理活动本身”与“心理活动的对象”作时间上的过程之分,这也许是今日时髦的意识的阶次之分(对象意识和高阶意识)的最早源头。
“意动”非“体动”,乃指内在的意识之动,是心理层面的运动(这里又得提防极端物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责难了),某种意义上它是虚动而非实动。它与皮亚杰的“动作观”虽风马牛不相及,但虚动是否也会如皮亚杰所强调的会经由动作之间的“协调”而产生新质?我不知道,这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探讨。
回到心理本体问题上来。我认为探讨心理本体的第一步是要明确“心理现象”并非只是心理学一家研究之禁脔之地。
如与“幸福”相关的问题,你不可否认它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心理现象,但你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划清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的界限呢?它们的聚焦点肯定是不一致的。类似的,这种多学科共同作战的心理现象还有很多。
心理学研究幸福感的问题应在“感”字上做足文章,这才是心理学家之职责所在。推而广之,一切有“感”之处,才是心理学用武之处;力气用在其他地方,都是荒废了主业。如前所述,心理学家的真本事只有在揭示各种“感”(除幸福感之外,从低级的各种感官的“知觉感”到高级的“道德感”“责任感”“美感”“负疚感”“自豪感”“崇拜感”“敬仰感”等数不胜数)之奥秘,心理学才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当然,在这项艰巨任务中,神经科学确可助一臂之力,但请切记,后者只是某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于是,首要的一步是必须在心理学到底研究“心理现象”中的什么部分或从什么角度研究“心理现象”上达成共识。我认为,心理学只研究心理现象的心理加工和操作的“过程和机制”,即便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也应如此!我提出“过程与机制”,只不过是不忘当年第一代认知心理学的“初心”:研究心智的内部结构和心理过程。第一代认知科学无论多有什么不当,这一传统总没有错;第二代认知科学无论有多少条新进路,这一目标也不应丢。否则,那就不是心理学了!
心理既有内容,又有形式,但本质上,这些过程和机制属于心理形式。尽管对“形式”的研究须通过“内容”之平台进入,但它本身不是着眼于对心理内容的研究。心理学其性质类似于逻辑、数学等形式类学科。2加2等于4,既可以用于“苹果”相加,也可以用于“非苹果的任何东西”相加;三段论的有效式、命题演算的永真式(重言式)自然可以应用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思维推理之中。同样,所有的心理活动的规律(具体表现为各种过程与机制)都可以承接不同的心理内容。记住什么,有赖于不同的经验(其他学科可以由此介入),但记住的过程和机制是一致的。悲伤的对象可不同(其他学科也可以由此介入),但其过程和机制也是一致的。幸福感的内涵可能不一(同样,其他学科也可以由此介入),但其“感”是相同的。过程和机制不是认知的专擅领域,也不只是与基础心理学有关,甚至人格也有其形式的一面,人格研究也应重视心理过程:注重其动态发展及实际发生的心理操作,应避免只是对已成型之人格特征的静态描述。从人格视角出发的心理的过程与机制是否存在某种特别之处,或者,简言之,人格中是否存在有别其他心理领域的过程与机制,我不知道,但信其有。我个人认为在人格的结构、动力、发展这三方面的研究上,可在“发展”和“动力”方面多下功夫,如婴儿的气质是如何发展成为特质的;生活事件、动机、目标、文化等因素是怎样塑造人格的——注意,是“怎样”!再如Walter Mischel的认知-情感人格系统中的“人格基本单元”(大量的“如果……那么……”集合)和Edward L.Deci和Richard M.Ryan的“自决理论”(它在自主、胜任、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中,注入了动机要素)都富含指向心理过程和机制的“形式成分”。
但是,如何使自身研究真正做到目标指向心理本体(心理加工与操作层面),对许多心理学分支来说,并非易事。从问题的确立到设计方案的确定,恐要付出艰难的思考——当然,也许设想很丰满,实际操作却很骨感。
最近在与西北师大的年轻学者舒跃育同志的微信交流中得知,他近年拿了个国家社科基金,就是探讨心理学本体论和方法论关系的。我非常为他高兴,视他为思考“心理本体”路上之同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所强调的“心理本体”与他的“心理学本体”有何异同。直觉上感到我们思考的角度不尽相同。他可能是从心理学史中各家之说的角度梳理其理论与方法如何相适与统一的,并不以对各家“心理本体”本身(如果有的话)之臧否为侧重。不过,我倒希望他能在论述时兼顾我前述向书昌教授的建议。今天我想再次明确我所指的“心理本体”的内涵:所谓“心理本体”就是“心理活动的过程和机制”!它既不是生理机制,也不是心理内容,更不是提供、制约心理内容的其他什么外部的因素。
因此,现在或可鼓起勇气说了:凡不是聚焦于“心理活动的过程和机制”的研究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不回归到“心理活动的过程和机制”这一正道,未来没有前途,也绝拿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其他学科难以取代的成果!当下,心理学需要一场清理门户、廓清战场的“正名”之举!只有如此,在面对前述神经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人工智能等多面挤压时,才能胸有底气,心中不慌!
顺便提及,如今“影响因素”之类的研究频见于各种心理学刊物。请问,影响什么?须知,影响指向的对象才是目标。只涉及影响因素仍是外围作战,它不能替代对目标本身的探究——尽管“如何影响”自身的过程和机制研究也很重要且有价值,但它是另一角度的、处于从属地位的过程和机制。
机制与过程有所不同,它偏重于原理的概括及对所涉因素的因果联系揭示。阐释事物发展背后的“机制”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目标。“机制”作为现代科学的核心观念,甚至有取代“定律”“逻辑”“因果”等范畴的趋势。对心理学研究而言,这是一种对心理活动背后规律的理论表述。不过较之其他学科,其“粗糙”的机制易得,“精细”的机制难觅。现今的不少名曰心理学的研究真正指向“过程与机制”的,并不占多数。即便有些研究似乎表面上表现得对心理操作的规律有所自觉,但受制于设计的简单、粗糙,所得结果仍然还只是静态的几个相关因素相互连接的图示,离内部规律的揭示尚有较大距离,这不能算是真正的“过程与机制”研究。“过程”谈不上,“机制”也不够格。
至于前述两种“取向”,由于它们主要采用的方法毕竟有所不同,因而所谓“科学进路”似更有利于专注心理的“过程与机制”;而人文社科进路虽然也研究心理,但专注的是心理外或心理后,即心理活动的产品而不是其产生的过程和机制。我不否认对前者的偏爱。在我任《心理科学》主编时,曾仿《科学》杂志庆祝其创刊125周年列出未来125个重大问题的做法,在我们庆祝《心理科学》创刊50周年时,也推出了心理学科具有前瞻性的“50个问题”。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每个问题又包含有数个小问题,而其中的核心问题乃是围绕着“过程与机制”之研究主题的。
心理的过程与机制自然有文化烙印。人的心理层面的加工过程和机制受文化的影响,自然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这何奇之有!当然,如前所述,关键看这种文化影响到“心理加工的过程和机制”达什么程度。我不排斥其中可能部分地已达于“硬件”变异的程度,但不宜夸大,甚至夸大到与各种文化下“共同”具有的部分相对立或相并列的地步!
值得提及,目前有些“心理机制”的研究,常常用到“结构”一词——那些由各种连线相接的“模式图”之类,大概也算是一种粗略的结构图。但应指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结构”概念被滥用和误用了,因为静态的所谓“结构”不能相比于动态的建构。结构是建构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根据皮亚杰,结构是建构过程本身的刻画!静态的所谓结构,其实并不符合结构的要义,因而也不是真正的结构,更遑论建构的过程了。
心理本体不能止步于仅指出“过程与机制”,还要为过程与机制落实更具体的存在形式——不管它是实在(真实的)抑或是虚空的。人人“有”心理,人人“说”心理,但若不为它在过程与机制之后落实其存在形式,那就问题很严重。因为势必要落入或是“功能”的陷阱,或是遭遇持极端物理主义心灵观者们的无情判决:一切所谓心理之物都是无稽之谈,它们只不过是一堆神经元的活动而已!
进一步分析“过程与机制”必然会遇到前已约略提及的“心理形式与心理内容”的可分性和“表征及其加工”的概念。前者涉及“过程与机制”的存在基础;后者是“过程与机制”的次级范畴,正是它们才构成了一个名曰“心理”的平台。心理学家的主要工作应是在这一平台上劳作——不管你是哪个领域(门类)的心理学或何种取向的心理学研究。但囿于本人的知识局限,以下的分析均以认知心理学为例。所引成果或显“老化”,但对说明我以下观点来说或足敷使用。
关于“心理形式与心理内容”的可分性,我们以著名的四卡问题进一步说明之。
思维必有内容,但心理学并不研究思维的内容,研究思维内容那是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各门具体学科的任务。四卡问题典型地受到外延逻辑中难以避免的所谓蕴含悖论的影响。如果熟悉数理逻辑,采用真值表方法,并且熟悉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区別,这一任务是容易解决的。对他们来说,心理学问题被逻辑知识所掩盖了,换言之,他们解决此类问题时并未进行常人所经历的心理过程,而直接运用了形式逻辑知识——当然这也有心理过程,不过这是另一类型的心理过程。但是,对一名非形式逻辑学家的普通人来说,他们解决此类问题的过程则可能遵循如下规律:他们或表现出证真偏向而不采用证伪的思路;或产生错误的思维定势,倾向于选择命题中提到的项目;或混淆了条件命题的单向性,产生前后项的所谓“换位效应”;或不当地激活了头脑中已有的概括性的知识,如允许图式(把“如果,则”等同于“只有,才”)、义务图式(把“如果,则”等同于“如果,就应该”);或者,主体受内容促进效应的影响,使得问题显现的抽象性程度也作为一个变量而导致通过率的差异。如此等等,它们都属于解决四卡问题的心理层面的一般规律。
我们说这些反应是心理规律乃是它具有概括性和一般性的性质。因为我们可以以不同的外显形式呈现这一问题。换言之,四张卡片上可以换写成不同的符号、图像、数字、字母,只要保持问题的基本结构仍是要求被试去检验“如果x1,则y1”命题的正确性即可(当然,必须同时呈现另二张卡片x2,和y2,并且使x1与x2有上层类,y1与y2也有上层类)。
如果把上述这些不同的符号、图像、数字、字母等也理解为内容,似乎说明心理学也研究内容,这未尝不可。形式与内容是事物的两个属性,它们是密不可分、对立统一的。它们是作为统一体成为心理的加工对象的。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所谓纯形式也是心理的对象。沃森(P.Wason)的原创研究所使用的E,K,4,7等符号本身就是相当抽象的符号,并没有多少生活的意义。当然我们可以按照四卡题的结构要求,把问题换成有具体现实意义的命题,这时的解决过程可以呈现不同的特点(所谓内容促进效应)。但心理学研究的着眼点仍是内容对过程的影响,而非内容本身。什么是这时的“内容本身”呢?依笔者之见:如果命题的内容涉及的是不同实践领域或知识领域的知识,那么对不同身份、地位、专业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效应,这就是内容本身的研究而不是四卡问题本身加工机制的研究。如果要说它也有心理规律存在,那是另一性质的心理学研究。
上述的四卡问题的心理层面的规律需要证实,这种证实只须在心理层面上进行即可。只要各种解释与数据资料相符合,那么我们就应承认这些解释的合理性。这时其实并不需要神经科学的帮助。当然,这绝不是说这时没有神经的、生理的活动。但神经的、生理的活动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的。生理的活动与心理的活动或许是同时进行的,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在同时之中,主导方面是心理活动,是心理活动引导、决定了生理活动。绝不可能是先有了不同的生理活动,然后才有(对不同主体来说)不同的心理操作——表现为对四卡问题的不同趋向(证真偏向、匹配偏向、换位效应等)!那么,生理的研究作用何在呢?应该说,它们也有用武之地,也可为心理学助一臂之力。因为说到底,心理层面的规律是研究者从行为数据中主观提炼出的,它们只是理论构想。它们若能得到生理层面的相应说明则更有说服力。如能得到生理的“同构说明”则更好。具体地说,最好能得到与上述不同解释相对应的并且彼此可以区隔的生理模式,而不能仅仅是生理模式而已。因为有心理活动必有生理活动,仅仅绘制出生理活动的各种景象,那即使你绘制得再仔细、再深入,那也无济于事!
四卡问题与其它心理问题,特别在思维、决策领域的问题具有同构性。详细分析此处从略。
在为“过程与机制”落实更具体的“形式”时,借助于“表征”概念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思考方向。于是,我们首先得把“表征”概念从已被某种程度“污名化”的“计算”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心理学通常把心理表征视为心理的概念单元(conceptual units)。在具身与计算的关系上,我持“弱具身”的观点,不认为它们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第一代认知心理学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得感谢以研究认知过程为己任的认知心理学。认知活动的心理过程就是认知过程。在当代第一代认知心理学的话语体系中,所谓认知过程,涉及两个主题:信息如何存在于心理以及被怎样加工的。如果把信息的存在方式和加工方式统一于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就是所谓表征系统。表征系统具有表征和加工这两层含义。认知心理学“表征”概念的提出为心理本体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视角和分析的把手。表征本身不是客观存在,是研究者主观设想的东西,当然研究者认为它们是与心理本体相一致的。两者的关系类同于智力与智力资源(如因素,过程、格式等)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当代认知心理学者提出了多种表征系统。其中著名的(同时也是成熟的)表征系统有:命题表征系统、类比表征系统以及说明性-过程性表征系统等。它们恰巧对应于知识的不同形态或信息的不同种类:类比表征对应于具象信息,命题表征系统对应于抽象的语义(意义)信息,而说明性-过程性表征系统则与另一类特殊知识——人的技能活动有关,即过程性表征对应的是熟练技能中所使用的知识,说明性表征对应的是非熟练技能中所使用的知识。上述各种表征系统(不限于这几种系统)各有所指,各司其职,共同构造了“心理”(不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心理本体,而是研究共同体认可的心理本体)这一平台,以各自的方式回答“信息是如何在脑中(心理上)表征的”这一问题,具体言之,就是回答各种知识(信息)是如何存在和怎样加工的。表征系统的好处十分明显,没有它们,我们显然不能对心理本体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谈到表征和表征系统时,有一个问题常常不为心理学家所重视。那就是:知识在主体表征(存储和加工)之前,对该主体而言,那还不是知识,也谈不上是什么信息。知识或信息是离不开认知主体的。没有主体,外物的存在只有本体论意义而不具认识论意义,因而认识的对象就无从谈起。知识(信息)是在认识主体对之进行心理上的表征的过程中才成为认识对象的。心理学的介入使原来的认识论问题——所谓认识的主体性问题,有了科学的根据。认识(信息)在人脑中(心理上)通过多重表征方式得以表示,即展现其不同的数据结构以及在此数据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操作,从而实现主体对外部世界——被表征的对象的反映。一言以蔽之,认识发生在心理上的表征过程之中或之后,而不是之前。
指明表征系统在形成认识之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为说明心理本体的客观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心理本体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了,在认知心理学的视野下,它们就是表征系统,对信息的表征和加工是心理本体发挥功能作用的两个侧面。
我认为,认知心理学家对表征系统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心理本体的研究,它所揭示的工作机制就是心理层面的规律。这个规律既不是关于引发心理活动的内容层面的规律,如见到美丽的花朵,哪些人在哪种特定的情景下会产生何种情感(情感是基于认识的),这或许是不尽相同的。严格说来,这须进行社会学、文化学甚至伦理学的分析。它们不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研究一般的表征和加工机制。当然,另一方面,这个规律也不是生理层面的规律:神经系统是怎样活动的。
那么,就基本认知加工而言,哪些研究成果属于心理层面的规律呢?
对此,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认知心理学已构建了多种表征系统模型,如属于命题表征系统的特征比较模型、信息分层存储模型、语义网络的激活扩散模型、概念依存性理论及原语说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它们都涉及对意义的表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原语元素,它们似乎都蕴含着动作因素,以这些富含动作因素的原语元素来表征意义,这与皮亚杰以动作及其转换来说明逻辑-数学知识的构成有着相通之处。另外,框架、图式-信息包、程式等都是可以用来解释思维、记忆、语言、推理等问题的更高级表征系统。属于类比表征系统的重要理论及模型则主要有柯斯林的表层-浅层表征说,谢泼德等人关于心理旋转的内部表征系统模型,等等。类比表征系统都认为外部物体的空间结构可以被某种程度地保存下来即被表征出来,因此,它们(表征物)与被表征物保留了某些特性的类似,故它被称为类比表征。
从符号的角度分析,心理层面上的表征系统,它们都是某种模型而已,它们不是事物本身(具象的物或抽象的意义)。表征系统的这一属性帕尔默对之曾有清楚的界定。它似乎距离我们的常识也并不遥远。大雁在眼前飞过,常识告诉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大雁在我们头脑中飞过,但为什么我们又能感到大雁飞过呢?因为我们在心理上对此进行了类比表征,并且似乎一些更具体的点阵的模型能很好地反映这一过程。这些规律就是心理层面的规律。今天我们由于受到了认知心理学的深入浸淫,对心理过程的描述语汇都是表征、加工等一套术语。因为它们有效,能解释许多认知的特点和规律,所以成为了当前心理学家共同体普遍接受的范式。但我们也应该为其他的范式保留存在的权利。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找到更好地刻画心理层面现象及其规律的概念系统,它们不再使用表征、加工之类的说法而换成了另一套说法。事实上,某种意义联结主义心理学就是不同于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另一种心理学。判断孰优孰劣,似乎不易仅凭一时之短长,还应放眼于长远。我们的观点是:不管黑猫、白猫,能说明心理过程之特点与规律、能为“心理本体”提供扎实平台的理论就是好猫,就是好的心理学。
心理学目前面临的危机似乎并不是来自上述之“内忧”——不同表征系统或心理学本身的不同范式的主导地位的争夺——其实,这种所谓的内忧,确切地说,那是“内喜”。第一代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地位的动摇,可能标志着心理学“过程”研究未来新的繁荣。如前所述,危机似主要来自于“外患”:有些人热衷于跳过心理层面而径直向生理层面挺进。本来认知神经科学自有其兴盛的充分理由,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在认知活动的同时,我们脑的生理本体是怎样工作着的。它有助于我们对心理层面规律的理解和建构。但是,生理规律不能代替心理规律。生理本体不能代表心理本体。如果可以代替,那么心理学还剩下什么呢?
我们说生理层面的活动不能代替心理层面的活动,因为从心理到生理又经历了一次转换,又成为了另一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从实体(外物)到心理本体的对应物(表征系统)再到生理水平上的物质活动(神经活动,甚至生化活动),三者之间的确存在对应的关系。两次转换,也可以说是两次编码:把外物在心理上编码;为保证心理上的编码得以进行,又须以生理上的物质活动予以保障。生理上的活动也是一种编码,于是成为某种形式的能量传递。两次符号转换也好,两次编码也好,并不能说明还原论的正当性。因为它们各自存在自己的规律。除非存在一个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它可以作为全部活动(社会性的、心理的、生理的、生理的又分为细胞水平的、分子水平的、原子水平的)的解释机制,如计算哲学和计算理论所宣称的——世间万物的活动都是计算,甚至存在“终极计算”,于是全部科学都变成了计算理论统率下的某个分支!这是一种彻底的还原论。 如果放弃心理学自身的主体性,势必会走上这条路。多年前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并视其为心理学的危机。今天则立场松动,原因在于我们对“计算”的理解可能有误。即便有危机,正如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说到的,那是遥远未来的事——远得就像说地球总有一天会消失而无甚意义。
五、基于学科自信的跨学科合作与根植于学科成果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口号频出是目前心理学界的又一热闹场景,它也是心理学家们喜欢戴的时髦帽子之一。之所以如此,这与心理学自身不强故而希冀得到其他学科外补的强烈欲望有一定关系。
李某现在有点心情纠结:既有对心理学学科一定程度的“学科自信”——这种自信不仅仅来自高层权威人士的讲话。我的自信源自于以下基本认识: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只要心理现象存在,心理学这门学科就永有存续的理由。它不受人的喜好所左右。
但又有些学科恐惧:因为目前心理学能够提供的堪称为心理规律的东西,在去掉前面提到的神经、脑和文化等绚丽包装之后,可拿得出手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实在太少了!长此以往,恐怕又会遭到社会大众的误解,甚至白眼。“哎呀,心理学就这些东西啊!”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担忧而无奈的前景。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自然值得提倡。但问题在于,你心理学拿什么去跟人家“跨”?蒙学水平能与学者水平“跨”吗?那只能跨着、跨着,把自己跨丢了!跨学科研究犹如合资办公司,你出资太少(没有心理学的干货),就不会有多少发言权。于是,挂名是“某某心理学”,却还是在人家“某某学”的屋檐下。主旋律还是人家“某某学”奏响的,心理学只是添加了几个装饰音而已。
有人说我前面所论是在“双拳出击”,左打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入室侵犯”,右打脑-神经科学的“喧宾夺主”,(双向)拒绝的结果不是自我孤立嘛!这是误解。心理学不拒绝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在确保自身有独立存在根基之前提下的合作,即要有为共同关注的问题之解决贡献本学科的力量。
只有把“心理”之研究强根固本了,才能更好地进行跨学科的合作。这不仅是心理学自身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为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使有效合作可持续。例如,使脑研究更好地、有针对性地为心理学做出解释;使人文社科更好地着眼于人,发挥更有效的人文作用。总之,如此合作才有价值,心理学才能在合作中不被边缘化。
如,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让·皮亚杰对儿童思维、乔瓦尼·维柯对古代思维,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在我看来,都有共同的或潜在共同的立场,即人的思维在个体身上的发展过程与在整个种族的发展过程具有相似性。看来,视群体思维与个体思维同构,皮亚杰并非是位孤独的行者,还有另两位同道。事实上,三人中的后者皮亚杰在其关于发生认识论的诸多论述中就处处体现了他的合作精神。
关于学科融合,可以“教育神经科学”为例。学界共识,教育神经科学是心理学、神经科学和教育实践进行深度整合的产物,是构筑在后两个学科之上的桥梁(A bridge between brain science and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ractice)。目前,不能说这座桥梁已完全建成,甚至有学者(如J.Bruner)指出:这是一座“过于遥远的桥梁”(Education and the Brain:A bridge too far)。但无论如何,它正在建造之中。最终这座桥梁建成和稳固与否,全赖心理学(或认知神经科学)能否为教育(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教学实践)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心理学(或认知神经科学)是这座桥梁的主体部分或桥墩。
在我看来,它仍未脱离相关学科“相交”而非相融的初级的合作阶段。根据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小泉英明的形象说法:“相交”(Inter-disciplinary)具有静态性,可用平面的二维的相互重叠的文氏图表示。而“相融”(trans-disciplinary)则具有动态性和发展的方向性,他以“超学科矢量”这一概念来表示这种方向性。因此,二维的平面图不能说明这种融合,必须以一个从底部起即有待整合的多学科而逐渐旋转上升(即相融的过程)的三维空间圆锥体方能表示——直径越来越小,乃至最后“融而合一”,这才意味着新学科的最终形成,其标志是有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原来参与融合之各学科范式的新范式。以此标准衡量,心理学与其他学科所形成的跨学科多数尚不够格吧!
万事皆有度。不能为标新立异而跨,或为跨而跨。在新学科未全面融合之前,采取问题导向的研究体制是最合适的:既联合作战,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从不同的侧面去合力攻坚。目前,心理学还是应多做一些“以问题为导向”的现实合作项目,别忙着宣称“某某心理学”的诞生为宜。
强调心理学的应用现在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请问,拿什么去应用,咱的心理学!?靠那些离心灵鸡汤或“人生练达”的生活心理学常识不远的东西吗?它们堪负此重任吗?心理学家们不去花大力气、老老实实对心理本体做深入的、其他学科不能取代之研究,心理学这棵树是结不出自己硕果的!一个羸弱的心理学如何去“应用”呢!
在心理学的应用潮流中,有一种相反的“自大”倾向也值得注意。随着心理学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青睐,致使有些心理学的从业人士自我感觉良好,甚至飘飘然视心理学为万能,不当地把那些尽管与心理学有些许相关但根本无力解决且也不属于心理学研究范围的任务,扛在自己肩上。我理解这些同志努力使心理学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和紧迫心情。低估心理学的价值要不得,但也请不要夸大心理学的功能,尤其不要越俎代庖,自以为通过心理问题的解决即可使本属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法律的、伦理的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这就有点因果倒置,陷入另一认识误区了。本质上,这也是一种学科混淆。
如,和谐社会与创新人才是现阶段我国心理学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任务,心理学家自然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施展身手的急迫心情。但另一方面,心理学家对心理学在社会发展和为其服务的系统工程中所应当扮演以及能够扮演的作用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对某些夸大的说法不以为然。
使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幸福,达于国泰民安之境,如何才能实现之,心理学自然有用武之地,但起关键作用的角色恐非心理学吧!
举个也许不太贴切的例子:若赋予心理学对罪犯改造有多么大的作用,因而认为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甚或主要贡献,说重了,那就是个笑话!社会治理讲到底,其决定因素是政治、是经济!心理学只是配角而已。
再比如,说“个人有幸福感才能使社会安定”,这是一个典型的越界问题——从心理学越界走向政治学、社会学了。“才能”两字是要害——心理学不能承受之重!把“才能”改成“有助于”或“促进”尚可接受。之所以越界,乃是倒置了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心理学问题,它属于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伦理学、经济学问题之列。心理学应该研究幸福感的过程本身(加工机制);自然,相应地,也要研究“不感到幸福”的过程(加工机制)。在此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建言献策。我一直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对心理学有挤压,致使心理学家丢失了本我,模糊了自己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典型的一例;是心理学,具体说是社会心理学向上述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屈服。
当然,我们不是说心理学的研究不能为政治服务,而是要明确:你——心理学应该拿什么为政治服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这种服务。
请不要轻率地越出了心理学自身要解决的问题的边界。归根结底,如前所述,要明了心理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在研究什么?当前,心理学家对自己到底应该在何种方向上发力似乎还没有找准,甚至对“心理”和“心理学”的内涵在心理学家共同体中尚未形成共识,这是上述所有问题、难题和尴尬处境之根源所在!
总之,不要说大话,说什么21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心理学春天的真正来临还须费以时日,强烈的社会需求不一定就能使它马上到来。这不是一件可以“大干快上、立见成效”的事。想想人类多么希望攻克癌症的强烈愿望吧!揭晓心理秘密之路还长着呢!
借此机会我想说说应用工作做得较好的决策心理学。决策问题有点特殊性,它既具有基础心理研究的属性,同时正因为其基础性,于是它又在管理、社会、经济行为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甚至几乎渗透于所有人的活动领域。
关于决策中的有限理性研究,心理学占据重要地位,心理学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极大提升了其在经济、管理等的应用价值。这是有目共睹的。
西蒙算得上是研究“有限理性”的鼻祖(可别轻视他对这种天天、时时、处处发生的现实中的平常存在所作的四字概括之功劳!),随后的泽尔滕、卡尼曼及最近的塞勒也不遑多让,好像都得到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奖,顺便也使咱们的心理学跟着露了脸啦!特别是塞勒(Richard H.Thaler),他基于有限理性,提出“心理账户”理论,继而又揭示了心理账户具有禀赋效应、自我控制不足及公平偏好等后续的次级概念(亚理论),为决策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其功厥伟!
国内李纾教授足以厕身于当前有限理性研究中之佼佼者之列。他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有别于无限理性和规范性理论的“齐当别决策模型”。它在众多决策理论中以其简洁而有效的特征独具特色;后续展开的一系列检验与证实其合理有效的研究也值得称道!
我为何在此多花了点笔墨说到决策,特别谈及“有限理性”这一人们司空见惯却又蕴含丰富心理学内容的现象,除了因为决策理论的应用性特别广泛有作为典型推广之价值之外,实在说,略有点私念。因为它与皮亚杰的“心理逻辑学”概念之与“形式逻辑学”的关系太具有同构性了,即“标准理性(完美理性)”类似于“公理化形式逻辑”;“有限理性”类似于“心理逻辑学”。必须指出,我们类比的是“关系”。正像“有限理性规律”支配实际决策行为那样,“心理逻辑”刻画的也是实际思维的逻辑过程。它们都远不是标准化或公理化的。
决策与逻辑思考其实是一回事,都是思维,只不过穿了两件不同的马甲而已。它们都是在人遇到问题时,研究实际思维活动是如何进行的。所谓“实际思维”是与“正确思维”(保证此时的推理形式在命题形式的公理化系统之内;或保证其决策过程符合无限理性要求)分属两个系统,是两回事。
我是一名思维广义论者。任何认知活动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内隐或外显地与它有关。人的所有理性活动都具有决策属性,也都有心理逻辑的参与。人对社会环境、物理环境、人文环境的适应,其本质就是不停地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决策、就是“奉心理逻辑行事。”
但令人遗憾的是,“心理逻辑”在思维研究中的命运,显然没“有限理性”在决策研究中的命运好。后者人才辈出,前者则门庭冷落。两者后续研究的规模和影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四卡问题算得上有点心理逻辑学的味道,但与之比肩者,又何其寥廖!
我有时在想:心理逻辑如果傍“有限理性的热点与人气”,改称其为“有限逻辑”,或许可改变点当下状况吧?是否也会像决策研究这么热闹呢?
六、余论
本文重点在第四节论及心理本体的文字,其余部分某种意义都是铺垫或多余的话。但对心理本体之过程与机制的揭示依赖于实证的研究,尤其是实验方法。基于此,我以为,心理学从业者至少应具备如下基本能力:
首先,应能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发现或确定要研究的方向性问题;
其次,把此方向性的问题再进一步转换为具体课题(科研项目申请通常由此开始,一般而言,此时研究者已有初步的结果预期和理论模型的设想);
再次,把课题变身为具体的任务(这时,如使用实验方法,就需要对可能所涉变量和研究范式作初步考虑);
第四,基于统计技术和行为实验设计技巧,设计出正确的完成操作任务的程序;这一环节涉及具体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我想多说两句。
由于各心理学分支有其特殊性,故似不能一概而论排除非实验方法。有的心理学分支,如发展心理学,甚至因时间的“单向”特性,所以无法进行把“时间”作为变量处理的实验研究,因而无法从此类实验中真正获得关于“发展”的信息。因此,发展心理学面临的心理过程与机制似乎有两种:一种是纵向的发展过程和机制;另一种是操作当前任务的横向过程和机制。
当然,发展心理学并不完全排除实验法——这倒不是因为它本身有“非发展”的问题,而是即便对“发展”而言,我们在获取各年龄段所谓“非时间所控制的静态画面”时(这时并不是以年龄—时间为变量,而只是据此而取样),实验方法仍是可以出力的,而且它们对最终形成“动态的发展过程”是有用的。当然,实现从静态向动态的超越需要某种综合、概括和理性思考。应该承认,如此所得到的关于“发展”的结论只是间接的推论,而不是直接的发展事实。
我非常同意辛自强教授在“发展心理学并非实验科学”一文中表述的观点及对皮亚杰研究方法的肯定;而且我很奇怪,如此重要的观点为何竟未在发展心理学的圈子中引发应有的更大反响呢?
以上四步是一项研究逐次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第五,根据所获数据修改原初设想的理论模型或建立某种新模型。这是一个使研究反向地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概言之,上述基本能力是所有以“心理的过程与机制”为主旨的实证研究而非理论思辨都需掌握的。它可简化为五个主题词:问题、课题、任务、程序、模型。它们如何被实际运用支撑着你的整个学术素养。因为,从问题开始向其后的每一次转化,都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选择——如何选择,则决定于你的水平,也决定了你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级高度。
当然,你同时还要熟悉采集数据的各种instruments的原理及其具体操作,以避免被这些instruments牵着鼻子走而只是获得一些无效的数据。
关于论坛,再絮叨两句:希望今后的各种心理学的论坛,越办越多,越办越好。“好”的最简单的标准就是要让参与者在论坛上有交流,甚至有交锋。此乃学科发展动力源之一,是思想与理论得以锤炼和建树之正途。如此,论坛才有生命力。否则,论坛就是个换了叫法的报告会而已了!
比如今天的论坛,我就不认为我的发言是什么“非主流声音(观点)”。它只是多种声音中的一种,只不过因其对错之处斑驳其间,因而可能反对者比赞同者更多而已。
最后,我还想再次提及皮亚杰。学界共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为具身取向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源头之一。而且,皮亚杰堪称一位杰出的心理学行为研究大师。他所研究的是货真价实的“心理的过程和机制”——别看它们戴着“认识论”的帽子!布鲁纳(Jerome Bruner)曾谓皮亚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心理学家之一”(He is one of the two towering figures of 20th century psychology,Time,1999,March,29),另一位是弗洛伊德。把这俩人并列意味深长,他们似乎各自据守着健全人性(心理)的两翼(根据潘菽老的“两分说”)。有诸多理由使我们可以期待(用不着一一列举),仅就发生认识论关于“理解即发明”(To understand is to invent——注意:是invent,而不是discover!)的深刻思想以及随着对创新思维、创新人才强烈的时代吁求来说,皮亚杰及其理论一定会“被再次再发现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皮亚杰在美国曾有所谓“被再发现”)。对此,我深信不疑!
以上有点冗长的文字,若有人耐心听(看)完,则李某幸甚。这已属奢望,不敢再有什么“嘤求友声”的过分之想了。“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忧、求之间,听命于识者之判吧!
本文根据在深圳大学“心理学科高峰论坛”之“圆桌会议”(2018-12-20)上的书面发言稿整理修改而成;魏威博士协助整理,谨此致谢!
The Foundation of Psychology :A Meta -Discussion on “Psychological Ontology ”and Related Issues
LI Qi -wei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acceptance and recognition on governmental and social levels,the subject of psychology has enjoyed rapid growth;thus,it is crucial to stay informed on its current state of development.Its close-yet distinctively different-neighbouring subjects of brain science and neuroscience often fail to provide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for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the causal mechanism of which would result in reductionist arguments if examined from a physiological perspective.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intelligence are both friends and enemies,and that science and humanity are ceasing to be opposites,rather embarking on a path towards integration.At this point,Chinese psychologists are task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extracting from reality those concepts,categories,and theories with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pertine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gener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In dealing with the pressure from competition with neuroscience,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artificial intelligence,etc.,it is critical for the subject of psychology to develop its own clear research objectives,focus on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s of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and examine issues oriented to solving real-world problems while producing results;psychology’s unique contribution is irreplaceable by other disciplines.
Key words :neurosci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psychological ontology;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作者简介: 李其维(1943— ),男,江苏滨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终身教授,主要从事儿童认知发展、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现当代智力理论及智力的测量与训练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 B8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68( 2019) 03-0001-21
收稿日期: 2019-07-15
DOI: 10.19563/ j.cnki.sdjk.2019.03.001
[责任编辑:江 波]
标签:神经科学论文; 人工智能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 心理本体论文; 心理机制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