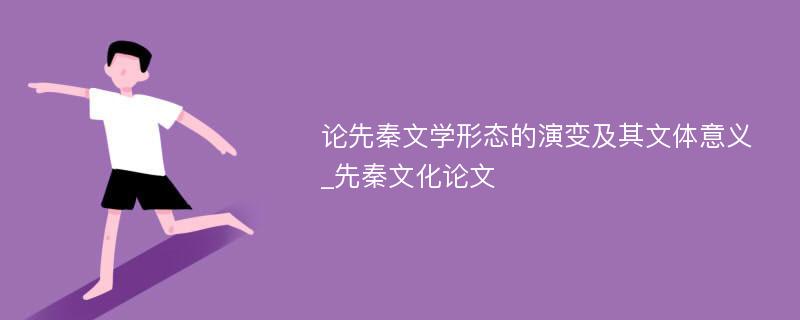
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文体论文,形态论文,文献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一系列出土文献的发现,证明“语”是先秦时期盛行的一种文献,这种文献的大量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重言风尚和记言传统。作为一种起源非常古老的文献,它在上古漫长时段中其形态经历若干重要的演化。近年来,人们对于先秦语类文献的文体形态进行了一些讨论,通过这些研究,不难看出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强调“语”是先秦时代一种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①有的主张“语”在形式上大致可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类;②有的认为“语”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直到《国语》成书后才完备起来,“国策”、“事语”是“语”发展的一个分支,而格言警句以及谚语、俗语一般是从“语”中提炼出来的,③等等。诚然,先秦“语”体存在讲述故事的现象,但并非所有“语”体都是如此,如当时流行的各种格言谚语,《论语》中绝大多数言论等,这些“语”是故事所不能涵括的,也就是说,主张“语”是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这一见解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用来概括先秦语类文献的整体文体特征则是片面的。同样,先秦语类文献有叙事的成分,特别是“事语”这一形态,但是,正如下文要讨论的,“事语”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言,记事只是为了引出议论,所以,将重在叙事作为“语”的文体形态之一种在根本上就否定了“语”体之成立的根本条件在于其记言这一本质特征。至于说格言警句、谚语、俗语是从“语”中提炼出来的这一说法,则是没有清晰认识到先秦语类文献演变的过程。
由此看来,这些研究虽然接触到上古语类文献形态的若干阶段性特征,然而由于缺少对先秦语类文献形态做整体性、历时性的关照,即语类文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成、演化这一动态化的过程中去把握其文体形态的生成和特征,因此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语类文献在上古时期其文体演化与特征这一问题。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图在论述上古语类文献生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体形态及其演变。
先秦时期是否存在一个记言传统,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就早期文献的记载来看,大都认为记言传统是客观存在的。《礼记·内则》记载三王时代“乞言”的情况,“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④这则记载说明上古社会有一种史官叫惇史,他们在五帝时代负责记载老人善行,到了三王时代,除载录老人善行外,还载录其善言。值得注意的是《尚书·皋陶谟》载有“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的说法,柳诒徵分析指出,“《皋陶谟》所谓五典五惇,殆即惇史所记善言善行可为世范者。故历世尊藏,谓之五典五惇。惇史所记,谓之五惇。”⑤这说明惇史负责载录的言行资料已形成文献。《大戴礼记·保傅篇》载录一种司过之史,他们负责记载太子的过失,“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⑥所谓“过”,其范围当不限于行为,也可能也包括言语之“过”,譬如《史记·晋世家》载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认为这是戏言,但史佚指出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需引起注意的是,《礼记·玉藻》提出“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观点,即认为上古社会史官存在记言、记行分职传史的现象。《汉书·艺文志》进一步指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⑦即认为《春秋》、《尚书》是记事、记言传史的结果。后来杜预在《左传·隐公十一年》“宋不告命”句注释中指出,“命者,国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辞,史乃书之於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⑧现代学者据此将上古史官的传史方式概括为“承告”与“传闻”。所谓“承告”是指别国史官以书面的形式前来通报本国事件,所通报言辞是经过谨慎选择的,符合当时的书法原则;“传闻”则是史官通过非正式的文告所得来的信息,其内容涉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等,其中也可能包括史官个人的态度和评判。⑨这两种传史方式中,“传闻”为“言语文辞”,孔颖达指出:“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⑩上述这些例证表明上古社会确实存在记言的传统。此外,一些文献还载录记言的个案,《鲁语上》记载臧文仲准备祭祀爰居,被展禽谏止,事后臧文仲说:“‘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筴。”(11)筴即简书,展禽对于臧文仲的一番谏辞当时即被记录下来。《吕氏春秋·骄恣》载齐宣王为大室,春居谏之,宣王召掌书“书之”。(12)《论语·卫灵公》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13)即是说子张将孔子的言论记录在绅带上。《孔子家语》也多次提及载录孔子言论的情况,如《弟子行》、《六本》、《入官》、《五刑解》等。
从上述这些例证来看,记言传统在先秦社会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一传统,从而促使语类文献的生成。吕思勉尝谓记言之史“以其初本以记言辞;又古简牍用少,传者或不自记录,而以口耳相授受也,则仍谓之语。……《史记》本纪、列传,在他篇中述及多称语。可知纪传等为后人所立新名,其初皆称语”,(14)俞樾《湖楼笔谈》卷二也认为:“疑古史记载自有语名,《牧野之语》乃周初史臣记载之书也。左丘明著《国语》,亦因周史之旧名。”(15)应该指出的是,语类文献只有到周代才大量出现,这主要是由周代文化决定的。西周以来的文化较此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王国维认为殷、周之变革实乃“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并进而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体。”(16)据此可见“德”的观念“是殷周之际宗教意识形态之变迁最核心而且是最具特点的内容”。(17)这种观念表现在政治上,便是以“德”行政,因此周人非常重视明德、敬德、务德。正是基于这种重德观念,当时形成“咨政”、“规谏”风尚,《国语·晋语八》载叔向说:“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型,而访咨于耈老,而后行之。”秦穆公也说:“询兹黄发,刚罔所愆。”(18)无论是“访咨于耈老”,还是“询兹黄发”,都是突出政治实践中要向老人讨教或接受其规谏。正是在这种重德观念下,大量“善言”被载录,从而促使语类文献得以大量出现。
作为一种起源非常古老的文体,“语”在先秦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成、发展过程中其文本形态经历了若干变化。通观先秦语类文献,其文体形态大致可以划分为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三个类型。先来看“格言”体式。
所谓“格言”,是指富于教益、短小精悍的话语。这一形态在文献上常常用“言”来指称,比如《尚书·盘庚上》:“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19)《泰誓下》:“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20)《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21)《秦誓》:“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22)有时也用“谚”、“语”,比如《左传·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23)《大戴礼记·保傅篇》云:“鄙语曰:‘不习为吏,如视已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24)为什么先秦文献喜欢用“言”来称呼这些富于教益、短小精悍的话语呢?按《诗经·大雅·公刘》毛传云:“直言曰言。”所谓“直言”,就是独言的意思,也就是指一个人言说。这种独言在形式上表现为怎样的特征呢?我们不妨通过分析“乞言”仪式来寻找其答案。《礼记》中的“乞言”,虽然有向老人请教的意味,但呈现的仍是老人独自的言说。可以想见,在“乞言”这样的场合之下,这些独自的言说,在体式上应该不是长篇大论,而是短小精辟之言。《晋书·王祥传》载:“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25)这里提到“乞言”,只是史官用“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概括王祥的言论,很难看出这些言论在形态方面的特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具体记载王祥的言论:“帝乞言于王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乎!’”(26)这就清楚显示王祥言论的格言特征。通过这个例证,可以推断“言”在形式上主要是一些富于教益而又短小精悍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格言”体式的语类文献称为“言”体。
格言体式的“言”在先秦流传下来的文献中表现形式极为灵活,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一些归纳工作,指出言类之“语”可归结为散见之“言”与结集之“言”两类。(27)这一分类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可惜的是没有进一步考察这些散见之“言”与结集之“言”各自的多元存在形态,即没有详细考察这些“言”内部具体演变的情况。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格言体在先秦的发展形态及其文体意义。
散见之“言”常见的体式有“有言”、“建言”、“谚曰”、“语曰”等,它们往往是一些零碎的却富有一定意义的言论,这些不同称谓在实质上体现引用者所关注的重心有所区别,从而它们所反映出的文体意义也不太一样。“有言”的格式,如《尚书·盘庚上》:“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28)此处引用的是一个具体人物迟任的言论,这一格式反映引用者不但重视言论的意义,也关注此言论的主体,也就是说,在引用者看来,无论是话语的意义还是话语的主体对于他的表达都拥有同样的意义。《论语》中单纯载录孔子言论的“子曰”体式就是继承这一传统。但是,有时候引用格言并没有点明其出处,只是泛泛引作“古人有言”,如《泰誓下》:“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秦誓》:“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29)这些地方的“古人”虽然常常被理解为古代的圣王,但毕竟难以指实,这就意味着引用者已不太关注言论所自出的主体,也就是说,用“古人”这样一般化称呼来作为其言论的主体,这意味着这些言论已成为公共资源,同时也表明人们关注的是话语本身所呈现的意义,至于是谁的言论在引用者看来已并不重要。称呼的改换所表现出来重视言论自身意义的倾向,有可能使引用者用其他名目来替代“有言”的体式,如《老子》第四十一章的“建言有之”,建言即设言,意谓通常如是说。这里,引用者并不关心“建言”之后的言论是谁说的,他引用这些言论的目的不在于突出话语的主体性,而是关注这些话语自身所包含的意义。这种情形进一步的发展就出现“谚曰”、“语曰”,《左传·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30)《战国策·韩策二》作“语曰:‘怒于室者色于市。’”(31)《大戴礼记·保傅篇》云:“鄙语曰:‘不习为吏,如视已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32)贾谊《新书·连语》作“周谚曰:‘前车覆而后车戒。’”(33)同一句话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呼,此处称“谚”,彼处称“语”,这些现象说明:这些富有教益的话语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已为当时社会所普遍认可,它本身自足的意义使他不需要依赖其他方式而为人接受;此处的“谚”、“语”之类的称谓主要起着指示的作用,有着很清晰的文体意义。
结集之“言”,一般可以理解为是对散见之“言”的整合,其形式有如下几种:
其一,汇集某一具体人物的言论。史佚是周初很有影响的史官,《左传》、《国语》多次征引他的言论,如《左传》僖公十五年:“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文公十五年:“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昭公元年:“史佚有言曰:‘非羁何忌’”(34);又《周语》:“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亊莫若咨。’”(35)从这些引用史佚言论的方式来看,与《盘庚上》所引迟任的话语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左传》成公四年引用《史佚之志》,其文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6)对于此处所提到的《史佚之志》,应是汇集史佚言论而成的。又《左传》襄公三十年所引《仲虺之志》与《史佚之志》具有同一性质,为汇集仲虺的言论。这里需补充的是“志”的性质,《周礼·春官》提及“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这“说明古代自王室至诸侯都有为史官所掌之‘志’”。(37)这种“志”在内容上表现为记言或记事,但就《仲虺之志》、《史佚之志》而论,当属于记言体例。这种汇集某一人物言论的《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春秋以降“家语”文献的编纂,典型的如《论语》、《孟子》。
其二,汇集无主名的言辞。虽然汇集的材料源于“语”、“谚”,但在编辑时,已经削去“语”、“谚”等指示性标志,而成为格言集。同第一种情形比较,这些篇目基本上不再是某一具体人物言论的汇集,而是广泛收集、聚合“语”、“谚”,这种聚合并非纯粹堆积材料。也就是说,若干“语”、“谚”材料聚合在一起共同说明某一主题意义,这种方式避免资料散漫、混乱之现象,带有专题化倾向。《逸周书》之《铨法》、《周祝》和《王佩》是纯以格言组成的文章,如《周祝》收录的是王者训民的戒语,“通篇悉为韵语,似铭、似箴,盖直开老氏道德之先”。(38)与《周祝》等篇处于类似地位的还有其他一些例证,其中需加以注意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书·称篇》,此处的“称”,并非度量之义,而是“言”的意思,所谓“称”,实际上是指“语句的汇集”。(39)《称篇》与《周祝》在文体方面很接近,“是把许多格言、谚语式的词句串联集合在一起”,(40)此外《语丛》四篇,以及《说苑》之《谈丛》,在性质上与《称篇》、《周祝》相近。
其三,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中,汇集的主要是某个具体人物的言论,而第二种情形虽然汇集的是不同的格言谚语,但组成的多是单篇的文章。与此不同的是,存在这样的情形,即吸纳“语”、“谚”资料,进行整合,使之融入一个超乎篇章的有机整体之中,这在《老子》文本上表现非常明显。简本《老子》的发现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过程。与帛本、通行本比较,简本《老子》在结构上基本上还是一些琐碎的“自然章句”,呈现的是语录状态,后来经过章序调整、合并等一系列编辑工作,才“逐渐完成了从琐碎的‘自然章句’到相对整齐、规则的‘章’,从松散无序的章序到严谨、‘有机’的结构布局,从零散的材料到真正严整的‘书’”。(41)
散见之“言”与结集之“言”各自内部所经历的形态方面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上面已经做了相关论述,需补充的是它们这种变化之间的联系。“有言”体式反映的是人、言并重,其中的“人”有时是具体的某个人,有时泛指“古人”;“古人”虽然还体现重视人地位身份的倾向,但由于这种“古人”的称呼已经趋于泛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与“语”、“谚”这样的指示语没有多大的差别。这样,散见之“言”可以划分为具体的人物言论和无主名的言论两种,对应这种划分,结集之“言”就出现纂集某一具体人物言论和纂集无主名言辞两种形式。至于像《老子》这种撰作方式可以视为纂集无主名言辞这一形式的扩展,这样看来,散见之“言”与结集之“言”之间就存在一种对应关系。
其次,所谓对话体,是指语类文献中载录富于教益的人物对话的一种形态。这种对话体一般是以结集的方式存在的。就对话体这种语类文献而言,它的内部也存在若干差异,大体可以划分为原生态和次生态两种文本类型。当然,与格言体一样,对话体是用现代术语去指称古代的文体,其实,文献中常用“语”体来指称对话体式这一文体。《诗经·大雅·公刘》毛传云:“论难曰语。”这就是说,“语”是指与人交谈、对话,所以,“语”作为文体,最初用来指对话体。后来,“语”体又被用来指称“善言”这一文体,其范围就不限于对话体。在本文中,为了论述的方便,用语类文献来指称“善言”文体,而“语”体仅用来指称语类文献中的对话体。
原生态文本是指这类文本载录的只是纯粹的对话。在《尚书》典、谟、训、诰、誓、命六体中,典、命记事成分较多,而谟、训、诰、誓载录的主要是对话。《逸周书》也有记言体,据学者的分析,它可以分为对问体、教令体、谏诤体、训诫体和格言体等几种情况。(42)其中格言体在上文作了讨论,除此之外,对问体的完整体式由问、答、谢构成,如《小开武》、《大聚》、《大戒》等篇。在这种标准体式中,双方平等对话,答语成为整篇文章的重心所在,答语大都充满道德训诫意味。教令体虽也有双方在场,但两者的处境并不相同,一方处于主动的地位,发布训令,这些训令包含道德训诫;另一方不参与对话,只是训令的接受对象,常处于听的位置。这类篇目如《程典》、《文儆》、《商誓》等,从文体形态及其性质方面来看,《逸周书》中的教令体非常接近《尚书》的“训、诰”体。谏诤体主要是臣子规谏君主而形成的一类文体。至于训诫体,罗家湘说:“当对问体、教令体、谏诤体文章中那些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的训诫部分独立出来后,就构成了训诫体。”(43)这也就是说,训诫体与对问体、教令体、谏诤体三者并非是从同一层面划分而产生的文体现象,而是单独进行归纳的结果;但就这些文体来看,其形态主要还是表现为对话。同样,《论语》的记言现象也非常突出,这些记言大体可分为格言体与问对体两类。其中问对体在《论语》中的表现形态很丰富,分析起来有这样几种:一是典型的问对,即有问有对;二是有提问的指示,但没有记载具体的问话;三是不是具体的问答,而是孔子对弟子话语或行为的评论;四是孔子先做出评论,接着是他人就此提出问题,然后是孔子的回答。这些形态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话形式是非常明显的。此外如《孟子》、《荀子》、《墨子》等也载录一些对话文献,吕思勉指出:“《论语》者,孔子及其门弟子之言行之依类纂辑者;……亦不惟《论语》,诸子书中,有记大师巨子之言行者,皆《论语》类也。”(44)这样看来,它们也属于原生态对话文本。
与原生态文本不同,次生态对话体文本除了载录对话之外,还有其他的附加文本。此形态以《国语》文本最为典型。周代盛行规谏风尚,《国语》文本载录的主要是谏辞,但是,《国语》除了一些文本只是纯粹载录谏辞外,大多数文本在载录谏辞这样的核心文本之外,还存在附加文本。《国语》的附加文本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三段式”,一是“谏辞+君子曰”,比如: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45)
在“三段式”文本中,除了谏辞原文本外,还有规谏的起因和结果。上述这段引文,起因是密康公随同周恭王游泾水,“有三女奔之”。针对这一事件,密康公的母亲规劝他放弃,以免遭致危险,这一层次构成规谏的过程,即谏辞部分。但是,密康公并没有听从母亲的话,以至于一年后被周恭王灭掉,这是结果。就《国语》文本而论,一般情况下对于“规谏”不接纳的,在文本上大都具备这三个层次;至于“纳谏”的,大都只具备前两个层次,有时也叙述其结果,但与不纳谏相比,其结果往往是好的。就《国语》文本整体而言,其规谏结果或“君子曰”大都是后来补录的,这是不难从“一年,王灭密”的叙述中看出来的。
据上所述,对话体语类文献在形式上大体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尚书》、《逸周书》、《论语》等文献,一是《国语》。前者大都只是纯粹载录对话,而后者除了对话之外,还有其他成分。所以,尽管《尚书》、《逸周书》、《论语》、《国语》都是经过编纂的,但《国语》文本中的附加文本显然是有意识编纂的结果。
再来看“事语”体。
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时使用了“事语”这一类材料,但没有对它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同时由于刘向在整理时又使用其他的材料,现在很难分清《战国策》中哪些文本出自《事语》。这样,虽然有些学者对《战国策》的“事语”进行一些分析,但其看法带有推测性质。比如郑良树指出《事语》属于记言类,主要记载游士的言论;(46)何晋主张《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六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指出游士的策谋言辞表现了当时的军政大事,这番言辞记录下来便是《事语》。(47)按照何晋的看法,所谓“事语”,即在形式上呈现为对话,而这些对话又承载一定的事实,也就是说,“语”是形式,“事”是内容,“事”蕴藏在“语”中。这一有关“事语”文体的看法是否符合实际呢?按《管子》收录有“事语”,刘向在《管子书录》中说:“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48)据此来看,刘向校理《管子》时只是做了“除复重”、“定著”的功夫,很可能没有涉及篇目名称等内容方面的改动,那么,《管子》中的《事语》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明确以“事语”名篇的文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分析“事语”的文体特征:
桓公问管子曰:“事之至数可闻乎?”管子对曰:“何谓至数?”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49)
按《管子·事语》收录两则“桓公问管子”,它们的结构体式一致,因此这里只抄录一则作为代表。从上述引文来看,它在形式上呈现为桓公与管子之间的对话,就此而言,它与前面所分析的对话体(“语”体)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个例证同时也表明何晋关于“事语”的看法有其合理性。
但是,《春秋事语》表明“语”体与“事语”体之间在文体形态方面还是存在区别的,张政烺在《〈春秋事语〉解题》中说:“‘语’这一类的书虽以记言为主,但仍不能撇开记事,所以又有以‘事语’名书的,刘向《战国策书录》叙述他所根据的底本共有六种书,其中第四种就是《事语》,其书虽已不可见,但估计它的形式和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近似,即既叙事,也记言。”(50)张先生强调“事语”的一个很显著的文体特征就是“既叙事,又记言”,这一判断是很准确的,但叙事与记言是如何结合的,它们之间的地位如何,则仍需做一些说明。
《春秋事语》共16章,有些章残缺,但参之其他文献,可以推知大略。从文体方面来说,此16章的根本特点是强调对史事的议论,如《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整理者说:“此章事见《左传》僖公三年及四年(前657年及次年),《左传》只有叙事,没有士说的议论。”(51)这一特点具体表现在结构上,呈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史实+评论”型:如第1章虽残缺颇严重,但显示的结构很清晰,其史实为“□□□□□杀里克”,此后是“□□曰”的评论,整理者说:“《春秋》僖公十年(前650年)夏,‘晋杀其大夫里克’。此章所记当时人的议论,别的古书没有记载过。”(52)这一结构在16章中仅此一例。二是“史实+评论+征验”型:《春秋事语》15章均为此类型。如《吴伐越章》:“吴伐越,复其民。以归,弗复□□刑之,使守布舟。纪□曰:‘刑不□,使守布舟,留其祸也。刑人耻刑而哀不辜,□怨以伺间,千万,必有幸矣。’吴子余祭观舟,阍人杀之。”(53)文中前两句叙述史实,接着是对此事件的评论,最后载录其结果,可以视为对评论者话语的印证。
在这两种形式中,《春秋事语》的核心文本是“史实+评论”,这一结构即是张政烺所说的“既叙事,又记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叙事”与“记言”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在《春秋事语》中,“事语”是“事”与“语”的结合,并非“事”蕴藏在“语”中。由此来看,“语”体主要是对话,而“事语”侧重于对史实所进行的评论,这就意味着二者之间是存在区别的。进一步来说,“事语”中“事”与“语,的结合是编纂的结果。因此从文本结构来看,《春秋事语》虽与《国语》很近似,但两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在《国语》“三段式”文本中,规谏者针对某一行为——这一行为可能未发生,如《国语·周语上》载“穆王将征犬戎”;有的则已发生,如上述密康公纳三女。——进行规谏,这就表明规谏起因与规谏过程是同一历史事件,这样,它们就构成同一个文本;而《春秋事语》中史实与评论则是两个文本。当然,《国语》与《春秋事语》也存在文本一致的地方,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语》中的规谏结果与《春秋事语》“史实+评论+征验”型中的征验在功能方面是相同的;一是《国语》中“谏辞+君子曰”与《春秋事语》的核心文本“史实+评论”也存在一致的地方。这些表明作为次生态的对话体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语”体向“事语”体的过渡。
上面对先秦语类文献所涵括的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三种类型作了分析,其中也涉及文体的演变,这里再补充探讨这三种形态之间的承继与演化关系。从整体上来看,先秦语类文献形态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向演进的:一是格言体内部的散见之“言”向结集之“言”的转变,一是对话体(“语”体)向事语体的演变。
散见之“言”主要包括具体人物的言论与无主名的言论。无主名的言论意味着我们已经不清楚它的出处,这种情况表明引用者或像我们一样不清楚这些言论的作者;或清楚这些言论的作者,只是在引用时忽略它的作者。倘若是后一种情况,表明引用者关注的只是这些言论本身的意义,而不太重视它的来源。前面已经论及,早期的史官群体不但承担记言的职责,同时也负责整理这些记言文献。那么,对于散见之“言”中具体人物的言论与无主名的言论这两种形式,史官会按照某个具体人物来编纂他的言论,如《仲虺之志》与《史佚之志》;或者收集格言谚语编纂成格言集,如《逸周书·周祝》、《黄帝书·称篇》、《语丛》、《说苑·谈丛》。这两种方式深刻影响到后来诸子文献的编纂,《论语》主要收录的是孔子的言论,这是沿袭史官汇集具体人物言论的编纂方式,《晏子春秋》、《孟子》同样是如此;至于《老子》,则是沿袭史官汇集格言谚语的编纂方式,谭家健、郑君华在所著《先秦散文纲要》中说:“《老子》吸收了大量来自人民群众的格言谚语。……《老子》把这类东西吸引过来,加以改造融化,纳入自己的体系,论证自己的哲学和政治观点。”(54)这个论述是准确的。
先秦语类文献演进的另一路向是对话体(“语”体)向事语体的演变。从文本来看,《春秋事语》有些历史事件和议论不见于《左传》,甚至也不见于其他古书,这表明两者确实存在差异。但是,《春秋事语》16章除第一、二、三章外均近于《左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部帛书虽然记有《左传》所没有的事(如子赣见太宰嚭)……但是所记的有关历史事实则大部与《左传》相合。”(55)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春秋事语》“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56)今本《左传》包括记事和解经两部分,解经有解释和评论的分别,评论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在记事下用“礼也”、“非礼也”加以批评;二是“君子曰”、“君子以为”、“仲尼曰”;三是“凡例”。同时,《左传》的记事文体也有三种情形:一是文字较简短,有日月,应出自史官记事;二是一般的记事,包括零星故事,一般无时间记载,多半出自各国私人记载;三是长篇大论,类似《国语》。(57)刘知几认为《左传》文本的形成是受原史“言事相兼”的传史方式影响的结果,在刘氏看来,《春秋经》的文体特征是由史官言、事分记引起的,“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58)《左传》采取“言事相兼”的方式,避免《春秋》记事不记言的不足,“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59)也就是说,《左传》作为编年体史著,不再像《春秋》一样只是单纯记录事件,而是在记录历史事件时也关注历史人物的言论。《春秋事语》“既叙事,又记言”这一文本特征的生成应该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也就是说,事语体的生成,即对话体向事语体的演变,是由于先秦史官群体“言事相兼”传史方式的结果。
注释:
①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②(27)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
③王青:《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④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5页。
⑤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⑥(24)(32)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55、55页。
⑦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⑧⑩(23)(30)(34)(3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8、1405、1405、360、818页。
⑨过常宝:《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第4期。
(11)(35)(4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0、114、8页。
(12)陈奇猷:《吕氏春秋》,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405页。
(13)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65页。
(14)(44)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5、215页。
(15)俞樾:《九九消夏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91页。
(16)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1页。
(17)郑开:《德礼之间》,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81页。
(18)(19)(20)(21)(22)(28)(29)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70、232、280、380、569、232、280页。
(25)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43页。
(26)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7页。
(31)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21页。
(33)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5页。
(37)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20页。
(38)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20页。
(39)(40)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8、301页。
(41)宁镇疆:《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42)(43)罗家湘:《逸周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8、95页。
(46)郑良树:《战国策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第141页。
(47)何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
(4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32页。
(49)戴望:《管子校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357页。
(50)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51)(52)(53)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年第1期。
(54)谭家健、郑君华:《先秦散文纲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55)唐兰、裘锡圭等:《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年第9期。
(56)李学勤:《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
(57)赵光贤:《亡尤室文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58)(59)浦起龙:《史通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3、34页。
标签:先秦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论语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老子论文; 读书论文; 尚书论文; 逸周书论文; 国学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