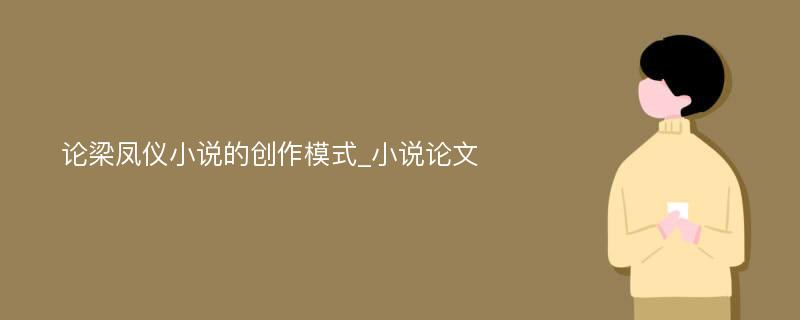
论梁凤仪小说的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梁凤仪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梁凤仪的小说,大多有同样的背景、相仿的人物、一个个不同的恩怨相交的故事。而这三者,共同构成其小说的模式。小说的外壳是:一个美艳女子在与若干男人的恩怨纠缠中,由最初的哀怨走向自立,而后终于成为商界中擎天一柱的女强人。这“外壳”包含三个因素:一是人物。大多数主人公是美艳女子;二是背景。大的背景基本上是商品社会中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商界,小的背景是男人;三是恩怨情仇的故事。小说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充满了理想色彩,对激发女性振作、奋起,争取美好的生活和平等的权利有一定的意义。作者所编的故事,情节复杂,引人入胜,可读性强。作者以男性为陪衬,给女主人公以超越一切苦难的力量,所向披靡的气势,战无不胜的手段,陷入狭隘的女性群体意识,淡化了女性解放的社会性矛盾冲突。
【关键词】 梁凤仪 小说 模式 美艳女子 恩怨情仇
1
读梁凤仪的小说,会产生紧促感。其小说情节大起大伏的节奏,人物辗转曲折的命运,以及故事背景那变幻莫测的商界,在作者短句式的叙述语言下,强烈地牵引着读者,令人不由得跟着那烽烟四起的感觉,一口气将故事读完。掩卷之余,方敢唏嘘、莞尔。
作者尤长于演绎故事。她的小说,有较为稳定的思路和显豁的脉络,在某些方面,显出与一般的流行小说迥异的烙印:在相当数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背景、相仿的人物、一个个不同的恩怨相交的故事。而这三者,共同构成其小说的模式。小说的外壳是:一个美艳女子在与若干男人的恩怨纠缠中,由最初的哀怨而走向自立,而后终于成为商界中擎天一柱的女强人。这“外壳”包含着三个因素:
一是人物。绝大多数的小说主人公都是美艳女子,她或者出身低贱,如《花魁劫》中的容璧怡;或是“难民”,如《红尘无泪》中的方子昭;或是富商巨贾之女,如《谁怜落日》中的汉至谊,《洒金笺》中的方心如,《誓不言悔》中的许曼明;或者是商界中人,如《世纪末的童话》中的孙凝。无论她们的出身如何各不相同,她们却都拥有美丽绝伦的外貌、聪明睿智的头脑,以及过人的胆识,不羁的性格,尤为突出的是女性迷人的魅力。她们或者锦衣玉食,或者虽然在物质上贫匮,精神上却胜似拥有整个世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必遭巨变,在生活中遇毁灭性打击,由不堪其苦、不甘其辱而走上独立之路,由籍上无名而脱颖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经济的女性企业家,似火中凤凰,涅槃而新生。而男主人公,对她们而言,往往非友即敌。敌者罪不可赦:他们毫不心软地、非常自私和可恶地抛弃多情可人的女主角,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爬向更高层的生活;友者如救世主般:他可以包容那个落难女子的一切,并倾其所有资助美人儿。
二是背景。大的背景基本上是商品社会中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商界,特别典型而常置于小说中的是股票市场,一个非常适合表现主人公大起大落命运的背景。小说的另一个“小背景”很特别,是人,是男人。在这些小说中,很少有从根本意义上具独立存在价值的男性形象;他们的或善或恶,都太具痕迹地关联着女主角的命运,从而成为女主角活动的“背景”。
三是恩怨情仇的故事。恩怨情仇,是梁氏小说的经线,人物在其间穿梭,较量在其间展现,起伏在其间显端倪。个中有美艳绝伦的女子与风流倜傥的男人的斗智斗勇,有财雄势大者的斗气斗财,有怨怼女子对负心男人的复仇,也有孤身嫁入豪门之后面对整个大家庭的冷眼而挣扎,更有身负家族血海深仇而杀向商界,以复兴家族、报仇雪恨的。小说的情仇,是以两性间的对立来写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绝色人物、商界背景、恩怨情仇,成为构建梁氏小说的三个基本因素。
2
三个因素中,“绝色人物”是最活跃、最具份量的。小说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充满了理想的色彩。
小说中的女主角,都是些美貌与智慧并重、内外兼修的出色女子。她们大多置身豪门华族的商贾之家,过着千金小姐阔少奶的生活,其才华往往掩盖在对当前生活满足的消磨中,端的“养在深宫人未识”。即使出身寒门,也沉醉于所拥有的爱情,甘作小女人。忽然之间,风云突变,似股市大泻,这些女子或遭情郎背叛,或被丈夫抛弃,或遇世交变仇人的变故,或遭金堂玉马变作一贫如洗的打击。痛定思痛之下,方才顿然醒悟,从而走上发奋之路。尔后必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中一展峥嵘,终成商界女豪杰。巨变,成为她们的人生转折、新生契机。最受女读者青睐的《誓不言悔》中的许曼明,便是这样一位在苦难中涅槃的女性。由于遭受丈夫遗弃而力挽不果,美丽傲慢的许曼明一改以往少奶奶慵懒的生活习性,抛却从前的幻想以及幻灭的痛苦,转而投入商界,几经奋斗而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独立个性、独立经济的企业家。《谁怜落日》中的汉至谊则由于家族惨变而无所依傍,由从前置身商业大家族中享尽千金小姐之福的境地一落千丈。凭着复仇的意志,她侧身金融界,在重重波折中显出不凡身手,终至复兴家族,报仇雪恨。个人的生命价值,便在这场复兴中得以体现。《世纪末的童话》中亮丽动人的孙凝,美丽非凡,原是公司白领,总是尽职尽责地工作,屡创佳绩,却被心术不正的上司恣意多方刁难。深思熟虑之下,她另觅它路,开拓自己的事业,一举而成名震四方的女强人。《红尘无泪》中的方子昭,更是艳光迫人。她曾经拥有青梅竹马的男友,在患难中,曾数次拼死救男友于水火之中,自忖拥有一份无怨无悔的爱情。岂料男友丛树康在生死关头,以出卖女友,去换取自由与前程。绝望之余,她发誓报仇雪恨。个中艰辛,不能与人言。先卖身,后学艺,再以美色与绝艺博得一巨贾之欢爱。此后借巨贾的财力,进入商界,很快地成为生意场上的强手,以至无人能在财力与手段上与之匹敌。最后以身相殉,将怨敌绳之于法。连瓷娃娃般的冷美人高彩元(丛树康之妻),也由踏入社会而终于有勇气正视自己婚姻的实质。写得比较深刻动人的是《花魁劫》,女主角容璧怡,原为温柔怯懦的小妾,二十余年来在巨富贺敬生设就的金丝笼中生活。虽因大妇的凌辱而需委屈求全,但她是颇满足的:“这些年来,自问最大的喜悦,就是备受敬生的爱宠,因此,就直觉地认定女人至大的幸福,无非建筑在阴阳协调、鹣鲽情浓之上”。然而,当丈夫溘然长逝,遗下生意、财产、以及大妇和大妇子女的刁难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笼中鸟的地位,才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于是,她冲破重重罗网,亲自打理丈夫遗下的生意。凭她的睿智与胆识、兼容与练达,在家族危机中挽狂澜于既倒,不但赢得大妇一干人的感恩与敬重,还赢得了新生的爱情。由笼中鸟而成女豪杰。作者写出了她的困境,写出了她走出困境的艰辛与机智,清晰地呈现出她由从属他人走上自主之路的历程,人物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这部小说比较见功力的还有人物心理的丝丝入扣,大场面描写的气派与时代色彩的逼真和谐,以及融在人物塑造之中的大至对人生的顿悟,小至对人物事件的剖析,都包含了作者对生活、对世事的独特体察与感受。
梁凤仪小说涉及艺术创作,尤其是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女性从困境中走出,在寻找自我中实现自身价值。“女性要收复她为人类丢失的一切,不再仅仅充当生命的源泉、人类的根和父权社会的合作者”[①]。小说中的女性,原来的处境,如同过去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的其他女性一样,往往处于一种从属、依附的地位。她们是社会的、男性的附属物,并无独立的人格价值可言。她们既无独立的经济,也没有自己的事业,即使在她们视为依傍的两性关系中,也处于被动的地位:被宠爱、被占有、被遗弃……男人才是操纵者。自我意识的隐匿,令她们面对生活,没有创造,而只余责任感,只有乐于天命之心,只安于空虚的物质享受。生活对于她们,不是一种生命的追求、幸福的体验。因此,当她们那建筑在砂砾之上的“幸福”世界,在冷酷现实的冲击之下轰然倒地时,她们才有切肤之痛。重新的自我审视成为必然,追求独立、自尊、自信,便成为她们新生活的主旋律。她们倔强地摆脱从属的地位与心态,凭着不比男子逊色的才能——小说中那远胜于男子的才能,去开拓自己的事业。这些可敬的女性,在走出了误区、挣脱了枷锁之后,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宽阔而丰富的生存空间。她们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实现的充实,感到了创造性的生活乐趣和满足。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从传统的从属地位移向主体地位,追求自主的精神意识,使作品呈现出耀眼的理性之光。梁凤仪笔下的女性无疑具有这样的认识与审美价值:女性要摆脱从属的地位,要避免受制于人的局面,就必须投身社会,在自我开拓中寻找人生的真谛,在男人统治的社会中显示女性的实力,在创造性的生活中实现自我存在的社会价值。
比之大陆的女性文学,多强调知识女性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趋向理性化与贵族化而言,梁凤仪小说呈现着通俗的、日常性的市民文化特点。在她而言,将女性作为叙述焦点,是她把握以自身为中心的客体和现实世界的角度。然而这种把握有时由于作者对女性神活般的成功期望过于强烈而产生偏颇,我们尤其可以从小说对男性角色的程式化的处理中,看到这种偏颇的折射。
3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商界,是上述女强人一个个串演一出出亦悲亦喜的人生戏剧之大舞台。这些绝色女子,人人身负重创,不得已而背水一战,因此,凝聚了所有的智慧与力量,在商业领域中玩得风生水起。梁凤仪凭借自己浸淫商界多年的经验,将熟烂于心的豪门内幕、财经股票知识、种种经营设想与手段,赋予这些女主角,使之个个长袖善舞、战无不胜,好生痛快。这是梁氏“财经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论家多有评说,此不赘言。
在这一系列的“财经小说”中,男人似乎是以“人文景观”的身份进入故事的。他们作为一道活动的背景,影衬出无数红唇巾帼的英雄业绩。这些男人,无论在情场上还是商场中,都彻底地败在曾经从属于他们的女性手下。
不少评论及作品介绍,都提及梁氏小说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确,爱情故事在这一系列小说中,往往是支撑小说的骨架。然而,除《花魁劫》写得比较委婉缠绵之外,贯串于小说中的更多的是刚豪之气。或者说,故事本身可能很缠绵,但作者并没有太多的笔墨落在营造这种缠绵上,更多的是借爱情故事的波折,去表现女主角的特殊命运。女主角性格中最光亮点,往往由爱情的变故而产生或激发。而她们身边的男人,往往就略逊一筹了。那些与她们演义爱情对手戏的男性,其实并没有能力做她们的对手,尽管总是男人惹起事端,挑起战火。这些男人,要么突兀而不太合情理地背叛娇妻爱侣(那是一定会有报应的)。如杨慕天之弃庄竞之(《今晨无泪》)、金信晖之背方心如(《酒金笺》),丁松年之绝许曼明(《誓不言悔》);要么完全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如赵善鸿之于庄竞之,童柏廉之于汉至谊(《谁怜落日》),贺敬生之于容璧怡(《花魁劫》)。这一类的背叛与拜倒,成为女主角的戏剧人生推波助澜的行为。而且这些男性形象,常常缺乏前后统一的性格,而人物在小说中成为女主角的陪衬。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过是女主角活动的一种特殊“背景”。
在作品中,作者表现两性关系,往往突出上述两极取向:男子或背叛女子,或宠幸美色。作品在叙述这种背叛行为时,将男子的决绝写得相当狰狞而无人性。《今晨无泪》中的杨慕天对庄竞之的背叛,未能从性格上、心态上写出这一背叛行为的基础,使人物为背叛而背叛,不合常理。首先,杨要背叛庄不是件容易 事,因为这个女子视他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曾数次舍命救杨慕天于危难中,小说的前一部分一直渲染着这对情人相爱之真诚与不渝;纵然劣根性使杨慕天在生死关头“不得已”以庄竞之换取自由;那么在自由之后,他完全有条件去解救恋人。然而他没有,甚至没有试一下去争取。杨慕天后来对那几位与其有夫妻之名或肌肤之亲的女性,都只有利用,而无真正的感情。那时的他,已是流氓大亨的心态,倒不足为奇。然而他的不解救庄竞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作者对这种极端行为的描述,未能在人物心理上给予充分的展现,以至人物行为缺乏心理依托,令小说呈现这样一种意味:男人根本就是恶棍,天生是女性苦难的制造者。作者的失败显现在于没有为杨慕天的背叛行为找一个有说服力的借口。故事的发展的确令人发指:因为男人的背叛,庄竞之被卖到妓院,历尽人间折磨。小说对杨慕天性格的描写,也有失误。两人青梅竹马之时,杨慕天的性格是懦弱而无主见的,倒是庄小姑娘“每临大事有静气”,杨慕天总是生活在庄竞之的庇护之下:饿了她去觅食,病了她去寻医,溺了水还是她以命相救。然而,成人之后的杨慕天,却以刚愎强硬的姿态出现,在商场中叱咤风云,与从前的胆小懦弱判若两人。判若两人的性格没有内在联系,似乎从前的懦弱,是为衬托庄竞之的义勇;后来的雷厉风行,是成全庄竞之旗逢对手之必须;又因为杨慕天能与庄竞之匹敌,庄竞之因此而旧情依然。这一切不是不可以如此,而是作者没有写出人物“何以”如此?人物就难以有鲜活的生命力。而《誓不言悔》中的丁松年,其性格也有这种不统一的地方。在婚变之前,他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气度、相当通情达理的谦谦君子;纵使背叛了妻子,也万分内疚地忍让,冷静地处理事情,是个凝重的绅士式的人物。对比之下,其妻许曼明的刁蛮、霸道就很有点咎由自取的意味了。但当许曼明在新的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可以体现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之后,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丁松年,却是那么一个自私、小气、猥琐的男人,那么的一无是处。在无任何转化因素的情况下,换了个行头,以反衬获得新生之后的女主角。如果这种转化,是以许曼明的视觉作为轴心,反观丈夫的为人,或者会写出许曼明人生态度的转变与境界的提高,并塑造一个真实的丁松年。但作者显然将情感的天平倾向女性,而导致了这一类失误。我们看到作者笔下的两性世界是对立的,而非互相映照。作者的选择,很明显地出于这样的目的:贬抑男性、崇扬女性。然而,偏执的选择,实际上是女性对男性意识——抑女扬男——刻意求同的一种心理折射。抑男扬女与抑女扬男,在本质上具有其文化心理的同一性。
至于赵鸿善对庄竞之的宠幸有加与倾囊相助,童柏廉待汉至谊倾情爱恋且斥资相救,很大程度是出于爱恋美色。他们先是惊艳,继而欣赏她们的聪颖,进一步认同她们与自己的意气相投。女主角正是看准了男人贪恋美色的弱点,而倚仗美色为所欲为。上述两位女子都并不爱她们的恩人,其肌肤之亲也非完全出于报恩,有时更是一种手段,一种征服男子、利用他们以达目的的有效手段,庄竞之尤甚。
男人永远地败在她们的手下,无论是情场中,还是商场上。他们如果背叛女主角,那等于给她们敲响一记石破惊天的警世钟声,宣告她们新生命的即将到来,被抛弃的感觉便是那诞生的阵痛;他们如果爱恋女主角,不计前嫌,不求回报(求什么回报呢?坐拥美色,已然是最大的回报),更是锦上添花,为女主角走向人生的辉煌铺就金灿灿的大道。就是在商场上,素来雄霸天下的枭雄,也失色于女强人的手下。易祖训、易君如败给汉至谊,洋行大老板列基富成为女强人孙凝的对手(《世纪末的童话》);贺家大少贺少聪则是父亲遗下的小妾“三姨”令他一败涂地又网开一面,才有活路(《花魁劫》);至于赫赫女将庄竞之,更把杨慕天玩弄于股掌之上。作者是太爱她笔下的女性了,她给予她们超越一切苦难的力量,给予她们所向披靡的气势,给予她们战无不胜的手段,给予她们一座座辉煌的殿堂。然而,这只能是“世纪末的童话”;对两性关系的偏激选择,对男性形象的简单化、程式化的处理,导致了这种“童话”色彩的存在。
从作品中传递的两性对立的情绪,我们感觉到了女权主义“首先假定男女是对立的”这个前提的存在。如果以性别来分野社会阶层,以两性构成生活矛盾的双方,而男性首先充当女性所有不幸与灾难的发源,之后又充当女性征服的对象,那么,社会的真正矛盾就会被淡化,女性走出命运的沼泽地之途将更为漫长。上述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由于男子对女子的不平等行为而产生的两性之间的矛盾状态。作者似乎陷入了狭隘的女性群体意识,以“性沟”作为女性的最大障碍,从而淡化了女性解放的社会性矛盾冲突。对人类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现实的表现本身,本来具有相当的社会的、认识的价值,尤其是在这种不平等发展到极端的华人社会,这种文学表现,就更具现实意义。但是,如果只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女性意识,把女性的一切苦难归罪于具体的男性,并且以这种归罪来促成女性的崛起,却是非理性的。两性的不平等的起源和形成,具有其长期而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当今女性的苦难,来源于两性不平等的观念。因此,要摆脱女性的不平等地位,要使女性由从属走向自主,由束缚走向自由,不是打败男性,而是推翻旧观念,铲除不平等观念滋生的土壤;更不是征服男性,而是战胜自身的弱点,以与男子同样的自信与才能存在于社会,建立和谐的两性世界。
只有真正的男性和真正的女性才可以组合为和谐的人类世界。把男性与女性对立,无论是抑女扬男,还是抑男扬女,往往只有扭曲了的男人和女人。对于男性,无论是把他们贬为敌对者、被征服者,还是视为恩人,都背离了事情的本性,背离了女性人格独立的本义。只有将男性作为一种有价值的人生参照,反映出的女性之光才更真实而更富于内涵。
4
在通俗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安排,是封闭型的,它不像纯文学。纯文学的小说情节,只是一种结构手段,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刻划人物才是关键。而通俗小说,故事情节本身就是目的,人物是第二位的。因此,要使故事具有较大娱乐成分的可读性,就必须在情节的安排上多作文章,以故事本身的精彩性、传奇性吸引读者。
恩怨情仇,是梁凤仪系列“财经小说”的中心情节。其小说的故事情节安排,无疑依循了通俗小说以情节取胜之道。故事的起伏,全在“恩怨情仇”之间。恩,可重如山,无以回报;怨,会绵如雨,漫漫无尽时;情,必深似海,纵有怨亦无悔;仇,当大如天,永恒于心,无法弥消。这四者交织在一起,波澜四涌,传奇的色彩由此而生,作品的可读性因此而强。在这千变万化中,我们依然可以寻到作者构建故事的砖砖瓦瓦:施恩的,多是富甲一方、称雄一时的男人,他们所施之恩,不是寻常人家有助人之心就可施以援手的;生怨的,总是女性,或是弃妇遗孀,或是受人欺压凌辱的弱女子;情,偏是那何以堪之情——庄竞之不能忘情于杨慕天这无耻之徒的惨烈之爱,小云的爱贺敬生之委屈求全,汉至谊因家族的血仇而不能爱其所爱之凄苦、许曼明在新的感情来临之时,惊觉自己仍然深爱的是那个自私而不负责任的丈夫……这“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切,是如此地令人扼腕,令人深感完美之无处可寻;仇,相当错综复杂,纠缠不清,有因爱成仇的,有因得罪小人而惹祸的,有由于经济上的利益而互相残杀的。这四者,相互交错,恩怨并存,情仇相交,与传统的通俗小说的恩怨分明有别。
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故事处理成有恩的报恩,有仇的复仇,怨得以伸,情有所托,最后是完美的大团圆结局,那就没有什么“特别”可言了。作者的特别在于,写出了事情的复杂性,让人性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凸现。
我们从梁氏小说的复仇故事中,看到了复仇者的两难:仇深似海,报亦有难,罢亦不甘。复仇的行动每走一步,痛苦就多一分,因为最恨的人却又是最爱的人。庄竞之大仇将报,覆水难收之时,这样痴心地自我拷问:“自己会不会报复了一个其实始终深爱着自己的人?”,这一心态令报仇失去了全部意义。复仇的结果,不是获得胜者的快意,而只有失落;不仅是失落,更是一种假如从头开始,依然会是如此无可选择的人生。一种悔亦不能的痛楚,把主人公永远地定格在无可奈何中。
在这些恩怨交加的复仇故事中,作者同时倡导另一种以德报怨的人生态度。对非正义者的讨伐,当然是伸张正义的最直接手段。但事实上,在复仇的过程中,往往伤及无辜,使手执正义之剑者,留下种种遗憾。更何况,怨怨相报,后患无穷。因此,“有风使尽舵”是作者所鄙视的人生态度;胸襟广阔,识大体,有大气,“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作者赋予她心爱的主人公的一个较突出的美德。从容璧怡、周宝钏(《誓不言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闪光点。连复仇心切的庄竞之,对仇人以外的其他人,总是表现出宽容之心。
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既借恩怨情仇构建了故事,又对恩怨情仇的关系作出积极的思考,对这古老的主题给予多角度的观照,从而使历尽艰辛的人物在大团圆的结局之下,依然带着隐隐的苦涩,令人释卷之余,尚作回味。
5
梁氏小说以香港风云变幻的商界为背景,将财经知识、经营手段等因素融于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之中,塑造出一系列时代女强人形象,而形成独特的“财经小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财经”到底只不过是小说的框架,是故事的背景,赢得众多读者的,是那些传奇般的故事,是人物的命运,尤其是贯串于小说始终的、女性对两性不平等的反叛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带有偏颇性。传奇故事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曾遭遇不幸的女主人公翻手为云的成功,将普通人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理想,在小说中延续、实现。作为流行小说,它们已经具备了通俗文学的几个美学特征:大众性、通俗性、娱乐消遣性、传奇性以及教喻性,更兼有纯文学严肃主题的探索。因此,尽管“模式”对一般作者而言,往往很难满足他们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别具匠心的艺术表现,“模式”往往成为创作者的桎梏。然而梁凤仪似乎有意在这种桎梏下舞蹈,她笔下的故事的丰富性几乎成为她创作的全部。因此,她作品中的人物或有相似,经历却不相同,她总是给读者不同的故事。丰厚的商战经验,是她创作的得天独厚之处。她在一篇题为《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散文中,说过一段大意如此的话:本人在商界多年,所见所闻异常丰富繁复,只要以电脑组合的方式,将它们再现出来,就会是一部部精彩的小说。这种创作方式本身,决定了小说的通俗性。
因此,读梁凤仪,请读她的故事,读商界中那些长袖善舞的女子。
注释:
①钱荫愉:《女性文学空间》,见《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