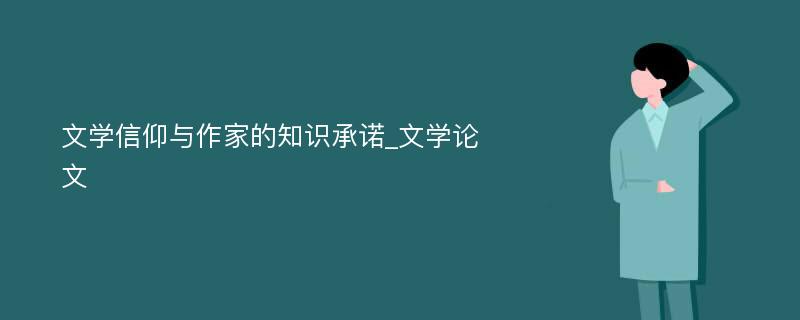
文学信念与作家的知识分子承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信念论文,作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5)06 —0063—07
一、来自余华的启示
1992年12月和1995年12月,余华分别发表了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近十年来,仅在南海出版公司,这两部小说就重版了二十多次,发行数10万册之巨。2004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余华作品系列”十二种,《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亦名列其中,一年之后,再度发行9万余册。除此之外, 它们还先后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日文等,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出版,并进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兰登书屋。
与此同时,《活着》还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1998年),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1994年),香港“博益”十五本好书奖(1994年),第三届世界华文“冰心文学奖”(2002年),并且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2000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被列为中国百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2005年7月,沉寂十年之后的余华再度出山,他的长篇新作《兄弟》(上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20万册,一周之内便发行告罄。
余华的这几部小说既没有多少时尚的元素,也没有十分强劲的市场炒作,更没有获得过国内权威的文学大奖,但是,在很多人都认为文学已经不断走向边缘化的时候,它们却制造了中国当代小说在读者中的一个奇迹。
那么,在这个奇迹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吸引了广大读者?
倘若从审美接受上来探讨这个问题,答案可能会很多。譬如,这几部小说的故事都很简单好读;譬如,它们的主人公命运都跌宕起伏颇有悬念;譬如,它们的悲剧色彩都很浓郁让人回肠荡气……但是,我以为,这些并不是它们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核心因素,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这些都不是难以企及的艺术目标。
事实上,真正让读者引起长久共鸣的,是余华对生存苦难的深切关注和体恤,对日常生活中许多人性温馨的重新发现,对生命中最本质的善与真的敬畏。余华曾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1](P145) 正是这种“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使他轻松地绕过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口号迭出的文坛表象,直接将审美理想建立在对苦难的深情体恤、对生命的无限敬畏之上;也正是这种“展示高尚”的坚定的写作信念,使他在面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时,总是能够有效地激活大众的共同情感,让人们在同情和悲悯的浸润中感受到生之不易,就像福克纳所说的那样,“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2](P368)
“帮助人们挺立起来”,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充满了道德色彩的伦理口号。然而,当它植根于作家的灵魂之中,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追求,它就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化的命题,而是一种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基础的文学信念。这种文学信念一旦被确立,将会使作家对人类的生存苦难保持一种高度敏锐的姿态,并在同情的眼光中获得精神追问的深度,在展现人性丰饶和复杂的同时,使文学真正地回到对人类生命尊严的关注上来。
二、信念的边缘化
遗憾的是,在当代文坛中,这种坚定的文学信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崇。尤其是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价值观念的不断变化,很多作家都非常简单地认同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正在走向边缘化。而且,在这一认同的背后,还潜藏了另一种自给自足的理由:这种边缘化了的文学现实,注定将很难产生伟大的作品。
我对这种“边缘化”的看法一直持以怀疑的态度。其主要理由有二:第一,倘若我们的文学真正地边缘化了,那么边缘化之后的文学虽然不会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热点,但它却能够有效地剥离附着在其自身内部的许多非文学功能,使它更进一步完成艺术的自律性。如果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考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文学艺术与政治、哲学、科学和历史一样,只有拥有相对完整的科学的自律空间,它才有可能更加健康地发展。第二,真正的文学边缘化所产生的严峻现实,将会自然而然地淘汰那些功利性作家的写作行为,因为它不可能让作家们在短时间内满足一些世俗的愿望。这种严峻的现实,将会促使文学远离那些急功近利的浮躁表达,回到纯粹的精神生活中来,回到那些因内心的需求而写作的人群中来,从而有效地保障作家队伍的纯粹性。
不可否认,这两种情形在当今的文坛中也确有体现。譬如,有些作品就非常自觉地逃离各种庸俗的功利表达,并在艺术本体上不断地展现作家独特的审美追求;不少作家也因为社会身份的危机而销声匿迹,作家队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净化。但是,从文坛的整体格局上看,我们还不得不承认,虚浮苍白且焦躁不安的功利性写作依然广泛地存在着;借助各种反自律性的表达手段,通过暧昧性的感官迎合,让作品谋取市场利益的情形依然屡见不鲜;尤其是一些新崛起的青年作家,精神格调与审美眼光普遍不高,创作热情却是异常高涨,感官化、粗鄙化、表象化的率性之作大量涌现。这种看似热闹实则平庸的创作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表明了某些作家为了重新谋求社会核心价值代言人的身份或世俗化的物质利益依然在进行各种突围表演,而并非是真正边缘化了的作家在艺术自律性上的自觉努力。换言之,它并非是一种文学走向的边缘化,而是作家信念的边缘化。
针对这一创作现象,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最近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文学与整个世界文学的格局一样,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边缘化,只是作家们缺少一种恒定的文学信念,“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3]。为此, 他极力倡导所有中国作家都应该建立起“伟大的中国小说”之信念,并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3] 尽管这个宏大的信念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理想,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终极目标,但是,只要大家都朝着这个信念去努力,只要这个信念始终统摄着我们的文学创作,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就会出现,我们的文学也就不会显得“众声喧哗”却难觅精品。
表面上看,哈金的这一思考似乎显得有些陈旧,因为创作主体的“宏大意识”、“同情心”以及让有感情、有文化的读者从中找到“认同感”,不仅是一位优秀作家的必备素质,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作品的精神深度与艺术高度。对此,中外文学的无数经典作品早已作出了证明。但是,倘若我们仔细省察当下观念驳杂、价值取向十分紊乱的创作现状,潜心思考庞大的作品数量与精品寥寥的尴尬现实,尤其是面对人们简单地认同文学边缘化之后所体现出来的复杂心态,我们就会感到,重提“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一信念,让同情心、高尚情操和宏大意识重新复活起来,就绝对不是多余的了。
有例为证的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坛一直不缺乏各种标新立异的写作口号,从“新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冲击波”,从“新体验小说”到“个人化写作”,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写作”……所有这些口号看起来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呈现出及物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特征,充分展示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精神禀赋,也道出了作家在艺术表达上的多向度审美追求。从文学发展的自由空间来说,这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在这些极度纷繁的“及物性”口号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却始终没有一个口号能够直面“伟大的中国小说”,没有一个口号能够从根本上触及某种带有形而上的终极意味的文学信念,也没有一个口号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强调了创作主体精神品格与艺术胸襟的自我建设问题。作家们总是不断地向各种形而下的现实世界行注目礼,而对形而上的理想世界,却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模糊姿态。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众说纷纭的口号之中,从审美趣味到精神趣味,很多作品都出现了大面积的价值分野。很多人认为,这是文学多元化的一种体现,表明我们的文学创作正在进入“众声合鸣”的繁荣格局。我觉得,这种“多元化”的表述不仅值得商榷,而且具有某种诡秘的遮蔽作用——它不仅催化了文学价值标准的不断失范,使作家们在为所欲为的自由颠覆中拥有了看似合理的理论依据,而且使我们心安理得地省略了对创作主体精神本源的追问,也忽略了对文学信念必要性的思考——尤其是对同情心、高尚情操和宏大意识的恪守。
其实,并不只是哈金意识到了文学信念的重要。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略萨从一开始就谈到了“文学抱负”,并认为它是“作家必要的起点”。略萨所说的文学抱负,与哈金所强调的文学信念,其实是同一个命题,即,都是针对创作主体的精神信念。但是,略萨更加侧重于推理性的论述。在他看来,文学抱负是一个作家的精神起点,而对现实世界的批评与拒绝则是文学抱负的起点,“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4](P6)。正因如此,对作家来说, “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4](P6)。事实上,有了终极性的文学信念,有了远大的文学抱负,有了超越于世俗利益的审美追求,一切庸常的现实秩序及其价值体系,将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家的拒绝目标和消解对象。因为理想之所有存在的理由,就是现实不可能提供而人们又心向往之,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因果关系。无疑,这也表明了文学抱负(文学信念)在创作主体精神内部的核心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创作主体精神本源的自我追问,是每一个优秀作家都不容回避的存在处境,也是我们检视作家艺术精神和审美眼光是否卓越的重要方式。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宏大的精神胸怀,缺乏相对恒定的、具有共识性和终极性的文学信念,就会直接制约他的创作所能抵达的精神高度,也会直接影响他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力度。余华曾说:“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恶习分开。在现实中,作家可以谎话连篇,可以满不在乎,可以自私、无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严肃认真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1](P185) 这是余华对一个作家“诚实”和“向善”的基本品质的自我设定,也表明了“同情与怜悯之心”对于作家作为一个精神劳作者的不可或缺,强调了悲悯情怀在写作中的价值意义。
现代管理学上有一句名言:思想影响行为,行为影响习惯,习惯影响性格,性格影响命运。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作家的思想境界不高,心中缺乏一种高迈恒定的文学信念,就会直接导致他的审美视野不会宏阔,艺术胸襟不会高远;而视野的不宏阔,胸襟的褊狭,又会导致创作主体面对现实世界时,拒绝和批评精神的严重缺席;这种拒绝和批评精神的缺席,必然使他们产生审美趣味的滑落,对各种世俗欲望持以简单的审美认同和价值迎合,由此而导致的最终结果,便是作品的审美格调普遍不高,艺术的震撼力与思想的穿透力都会不强。我们的创作之所以日显平庸,作家的心态日趋浮躁,质疑精神、批评精神、原创精神日渐贫乏,虽然可以总结出很多客观原因,譬如大众文化消费模式的转变,商业性出版行为的加剧,传媒信息的误导,等等,但是,从主观上来分析,高迈恒定的文学信念的缺席,向“伟大作品”冲击的文学抱负匮乏,乃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
惟因如此,强调建立某种共识性和终极性的文学信念,强调创作主体内部有关高尚、尊严、人道等普世价值的自我建设,并以此来重新统领作家们日益涣散的精神姿态,使不同的艺术探索、审美价值和个性风格,都能够沿着各自的有效方式,朝着我们共同认定的伟大作品逼近,这样,不仅会促使作家们自觉地形成一种向形而上的理想高度不断攀援的创作态势,而且也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整个民族文学的发展气质。人类因梦想的存在而伟大,文学因梦想的存在而辉煌。离开了伟大的梦想,离开了高迈脱俗的理想,我们的文学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脱离低俗的欲望,而只能是人们庸常欲望在话语上的复制、迎合和鼓噪。或许,哈金对“伟大的中国小说”所下的具体定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商榷,但是,他所强调的“宏大的意识”却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这种终极性的文学信念的存在,小而言之,可以有效地消弭所谓的文学“边缘化”给人们带来的焦灼不安和失落情绪,并引领作家超越现实生活的羁绊和制约,深入到纯粹的、理想的精神世界之中,从而遏止作家主体精神不断下滑的趋势;大而言之,则可以有效地整合在“多元化”的口号掩饰下所涌现出来的审美价值逐渐失范的创作格局,阻止当下的文学作品在数量与质量之间严重失衡的情形,并进一步制约作家以自由的名义在庸俗的温床上肆意叫喊的创作现状,使不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个性沿着高度自律的艺术空间发展。
三、重返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
既然恒定而高迈的文学信念,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亟待建构的一种精神本源,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探讨,如何才能使作家们自觉地关注这一精神本源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重新强调作为作家所必须恪守的基本职责和使命。因为任何一个信念的形成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人对自我角色的准确认识,基于人对自身信仰和理想的深切理解,基于人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清醒体察。如果一个作家对自身的角色定位非常模糊,对自己肩负的使命不甚清晰,那么,他就不可能确立恒定而高迈的文学信念,而只能使自己的写作随波逐流。
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面对物质化的生存现实,面对利益阶层重新分配的社会秩序,面对伦理体系不断被颠覆的人性场景,我们的不少作品都陷入了某种迷惘与失衡的精神空间。它们要么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要么是对公众聚焦的简单临摹,要么是对低俗欲望的尽情宣泄,缺乏对人们内心焦灼的深度追问,缺乏对现实苦难的深层思考,也缺乏对生存困厄的真切体恤。作家们都在不断地强调个人化写作,强调对个人心灵的绝对服从,但是,却将作家的个体生命与现实苦难隔离开来,从而导致写作的使命感不断衰退,自我中心主义四处泛滥,甚至犬儒主义也开始大行其道,文学在很多时候成为个人情感的分泌物。
对真正的生存苦难失去体恤的情怀,对人类共同景仰的价值谱系自觉回避,这种“躲避崇高”的写作倾向,不只是作家丧失高迈信念的一种表现,也意味着他们对自身角色——尤其是知识分子角色失去了最基本的省察。任何一个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应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点,从知识分子诞生的那一刻便得到了确认。1894年,法兰西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受控“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被法国军方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一年后,法国情报机关擒获一名德国间谍,审讯中意外发现德雷福斯是清白无辜的,但是军方以“国家尊严和荣誉高于一切”为借口,虽经重审,却仍拒不纠错。著名作家左拉惊悉此事之后便拍案而起,奋笔疾书万余言,欲以公民的名义,替这个与他素昧平生的小人物讨回公正。1898年1月13日,这封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以《我控诉》为题发表在《震旦报》上。第二天,《震旦报》上又刊出了《我抗议》,在这篇极力支持左拉行动的短文下面,署有法朗士、普鲁斯特等一大批法国“文学士”和“理学士”的签名。由是,左拉的身后开始迅速出现了“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茨威格语),他们包括:《震旦报》主编克雷孟梭,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纪德,以及俄国作家契诃夫等3,000余人。
这便是世界思想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知识分子群体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左拉的“控诉”也因此被视为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宣言”。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种启迪:一是知识分子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作家息息相关。或者说,正是左拉、法朗士、普鲁斯特、纪德、契诃夫等著名作家的存在,才催生了知识分子群体力量的出现。其二,这一重要事件,不仅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公正、真理与真相的执着追求,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生命尊严高于国家利益、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的伦理观念,还体现了他们对弱势群体的承担姿态,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自觉关注。它说明了作家作为一种精神劳作者,他的核心身份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艺术上的“知识分子”或“专业分子”,他拥有自身十分清晰的伦理信念,并且为维持自身的信念而随时准备出发。
明确了作家就是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定位之后,那么,当我们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创造性、质疑性和批判性时,强调他们对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建构与承担时,强调他们对人类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道义、良知、操守的强力维护时,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家必须行使知识分子角色中所包含的这些使命。事实上,作为现代社会体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都与现实生活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这也意味着,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们在追求独立人格的同时,并不只是沉迷于纯粹的个人化精神空间,与社会保持着某种决绝的伦理姿态,而是以自身独立的、不受任何意志左右的价值准则来对现实秩序进行有效的判断,从而在实践的意义上凸现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表现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他们必须时刻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地参与到一切和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秩序中来,在弘扬自我艺术良知和职业精神的同时,为维护社会文明中的一切正义、真理、尊严、操守等伦理秩序而努力,并通过他们的作品给人们以救赎的勇气和复活的力量。所以,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明确地说:“我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共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5](P16—17) 萨义德的这段话无疑也表明,一切现代知识分子都必须时刻保持自我的公共属性,即他们必须承担自身的社会伦理化使命,代表“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而奔走、呼告和吁请。任何一个以人类精神表达为职业的作家,当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时,他绝对不只是针对自我的处境,而是针对社会群体性的处境,是直面现代社会在文明程度上的进步性,他是在拷问中将问题引向深入,在质疑中揭开问题的真相,在明确的伦理化诉求中告诉人们努力的方向。他们不仅要向社会提供值得信赖的观念和思想,而且要以自己特有的艺术方式,唤醒那些在平民社会中被日益腐蚀麻痹的心灵,让它们由异化变为正常,在困厄中获得坚持的力量。
尽管我们的大多数作家都不会怀疑自己是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是,他们对于自身作为知识分子所必须恪守的伦理信念却不甚明确,对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也推诿殆尽。尤其是面对重大的公共事件,面对集体性的生存苦难,面对现实内部的各种尖锐痛楚,我们常常听到的,都是一些大众传媒的声音,各种专家和学者的声音,却很少听到作家的声音,听到那些振奋人心的作品的声音。作家们很少能够自觉地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它们及时而有效地作出艺术上的承担。最明显的例证之一,就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作家们尽管也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诗歌等作品,但是,除了附庸风雅的话语“作秀”和廉价的情感表演,我们实在看不到有多少作品,对那些置身于恐惧中的人们在灵魂上给予了何种安慰,更看不到它们对这场公共危机的有效思考。可以说,作家们在这场重大灾难中的表现,甚至远远不及大众传媒。
不注重艺术思考的实践性价值,不强调自身在公共领域中的现场作用,不突出自身作品对公众苦难的深切表达,其实是当下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生存心态,是他们缺乏恒定而高迈的文学信念的突出表征。它所折射出来的,就是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严重缺席。它看似维护了自身精神上的独立性和艺术上的自律性,实则是瓦解了作家所必须承担的知识分子伦理体系,抛弃了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学信念。如果深而究之,我以为,学者王彬彬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中就曾非常清晰地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在这篇文章中,王彬彬通过反右时期的“吕荧事件”,毫不含糊地道出了中国作家面对历史的蒙昧而表现出来的圆滑、世故和吊诡。他们看起来是为了明哲保身,为了委曲求全,实则是弃正义与公理于不顾,是借用“难得糊涂”的中庸思想来逃避知识分子的伦理职责。久而久之,盲从替代了思考,麻木替代了质疑,信念出现大面积的缺失。但是,就文学艺术而言,没有警惕就没有怀疑,没有怀疑也就不可能有发现,而没有发现就不可能进入事物的核心地带,不可能揭示真正的生存真相和存在本质,更不可能显示出一个作家作为精神劳作者的独特品格。
因此,面对当下种种日趋麻木的精神处境,要彻底改变各种近乎无聊的自我表演式的创作情趣,我们必须重提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这意味着:作家们一方面必须以直面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来道出民族内在的缺陷,展示历史潜在的本质,披露大众的苦难根由;另一方面,还要有一种对大众苦难的体恤情怀,对人性劫难的悲悯胸襟。一个作家,只有拥有了这种信念,才有可能穿透所有世俗的迷障,写出真正内涵宽广而又能“帮助人们挺立起来”的作品。
收稿日期:2005—08—06
标签:文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作家论文; 信念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许三观卖血记论文; 活着论文; 读书论文; 边缘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