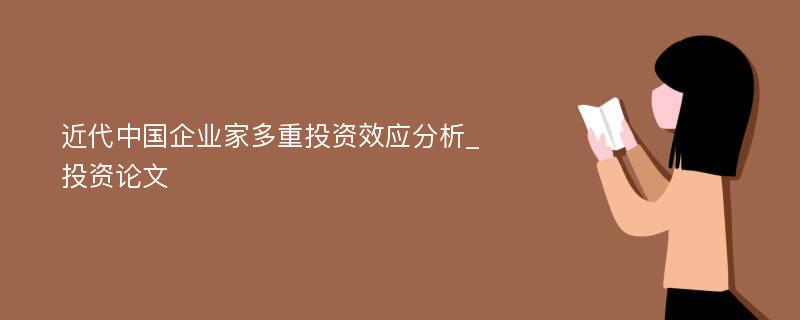
近代中国企业家多元投资效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效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3)11-065-074
一、学术回顾:以往的研究是从企业集团的视角切入
以往研究近代中国企业家多元投资的论著,多从企业集团的视角切入。徐新吾、黄汉民主编的《上海近代工业史》总结了六个企业集团的情况:在棉纺织和面粉两个行业中均处领军地位的荣氏企业集团;在火柴、水泥等多种工业行业及商业领域投资的刘鸿生企业集团;卷烟行业中的佼佼者简氏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经营百货业进而投资纺织业的郭氏永安集团;从面粉业发展到工、商、金融一体化的孙氏通阜丰集团;完成从缫丝到织绸一体化的莫氏企业集团。①在上海未作投资的企业集团并未包括在内。黄汉民和陆兴龙在另一部著作中总结了企业集团的三种类型:一是横向专业生产型企业集团,即基本上都是由生产同一产品的多个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团,如申新纺织公司、福新面粉公司、阜丰面粉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二是纵向全能生产型企业集团,即由从原料制造到产品制造具有有机联系的多个生产环节的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团,如美亚织绸公司、大中华橡胶公司等;三是工商联合型企业集团,即由在生产上和销售上存在着业务联系的多个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团,如五洲药房公司。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本身是从纺织到印染的纵向一体化生产企业,而该公司又是由永安百货等联号企业投资创立的。②
对于每一个涉及多元投资的企业集团,包括上文没有提到的,实际上都有不少论著论及。为了避免给人报流水账的感受,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马伯煌主编的《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研究了企业集团多元投资的目的,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为了防范风险,如永和实业公司的创办人叶钟廷、叶翔廷说的“多品种、多门类生产,则在某一种产品受到阻滞甚或被迫停产时,其他产品仍能照常开工”,或如刘鸿生说的“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是说,所有我的资财都是分开投资的。如果一个企业组织亏损了,其余的还可以赚到大量利润”。所以,永和的化工、医药、文教用品、橡胶等投资并不一定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刘鸿生的火柴、煤炭、毛纺织、搪瓷、银行等产业也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另一种则是为了获得产业互补或互助的好处,如荣氏企业的粉棉互补、大隆机器厂的棉铁互济、永安联号的以商养工等。③宋美云认为,企业家组织企业集团,是“通过规模扩展,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有利条件”,她所举的多元投资的实例有周学熙利用启新、滦矿的资本积累投资创办纺织、玻璃等新企业、范旭东以久大精盐公司的盈余支持创办永利制碱公司。④
以往学者在研究企业集团时,几乎没有引入经典的企业史理论,对于多元投资避险趋利的实际效果更流于表面的积极认定,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关于企业集团的说法,王颖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家族性联号企业:一种非企业集团的中间性组织》中提出了商榷性意见,她引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企业史理论,认为通常被称为“企业集团”的近代中国家族性联号企业,实际上与威廉姆森和钱德勒等人关于企业集团的理论特征有重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没有发展出控股公司作为企业群运作的中枢或核心;其二是联号企业间以血缘纽带作为主要的联结方式;其三是在联号企业间,由大家长的权威机制导致的关系性契约成为主要的契约方式,而由市场决定的个别性契约则处于次要地位。⑤
王颖的观点未必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她的商榷性意见对于我们深入讨论近代中国联号企业的性质是有益的。实际上,可以讨论的并不局限于企业的性质,多元投资的实际效果是大家谈得很少的。而且,即使在谈到实际效果时也很少运用企业史的经典理论。我们在阅读美国著名企业史专家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时,还不是十分明白他所总结的美国企业管理革命的具体针对性,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则是说得非常明白了。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一书中多处指出:他所总结的美国、英国、德国的现代企业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诸方面取得企业组织能力的革命性进展是指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后者来说,“大的综合企业只有很少的竞争优势”。⑥他还运用了西蒙·库兹涅茨在《各国经济增长》一书中的统计成果:库兹涅茨将美国制造业的38个分支分成4个组,分别统计出它们在1880-1948年间的增长速度,第一组是汽车、电机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增长特别快,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先锋工业;第二组的增长率稍低,是出现稍早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第三组的增长率则更低一些;至于棉纺织、面粉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被列入第四组,也就是最后一组,在这一组中的行业不仅“份额急剧下降”,而且“大工业公司从来没有起过重大作用”。⑦有人分析说,美国经济具有“二元结构”:经济的“中心”是一些大的卖方寡头垄断产业群,经济的“外围”是一些小的、竞争性结构产业群。后者的活动大部分在市场上进行,而前者的活动大部分在企业内部发生。⑧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还没有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的阶段,因此企业纵向、横向、混合兼并及多元投资的实际效果不能尽如人意,应是合乎历史逻辑的事情。本文拟在这方面尝试作一初步的探讨。
二、近代中国企业家多元投资:原因、结构和模式
多元投资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第一种,为了某种社会理想;第二种,为了产业的关联互补;第三种,为了风险防范;第四种,为了融资需求。
张謇在南通的多元投资是为了他地方自治的社会理想。大生集团在不到30年的发展中致力于多元投资,扩张成为拥有近60家工、农、商以及金融、交通、服务等各种企业的庞大企业群,纺织业和农垦业是这个企业群的两大核心支柱。⑨张謇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对实业的惨淡经营,表现了“地方自治”的理想,即通过实业、教育、慈善等途径,经营地方自治,奠定立宪的基础。⑩
像张謇这样的理想主义实业家影响很大,但人数很少,更多的情况是产业的关联互补促成了多元投资。荣氏企业主要投资于纺织和面粉两业,这两业是关联互补的。申新纱厂所织的棉布供面粉厂制袋之用,1917年申新棉布产量的97.9%供制袋用,1918年这一比例为93%。(11)而面粉则是纺织生产中的重要辅料。(12)严裕棠、严庆祥父子的严氏企业主要投资于棉、铁和房地产企业,就棉铁两业来说,大隆机器厂生产的棉纺织机器可供苏纶、仁德等纱厂使用,这在大隆方面获得了销售市场,而在纱业方面则获得“品质实可与外货并驾齐驱,售价亦较外货特廉”的纺织机械。(13)类似的案例是比较多的。
风险防范是多元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理由。上文刘鸿生讲的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就是这个意思。安徽寿州孙氏家族创办的通阜丰联号企业相互关联度不大,除了天津中孚银行外,在实业方面有上海阜丰、山东济宁的济丰和河南新乡的通丰等三处面粉联号企业,在北京创办通惠实业公司,在烟台创办通益精盐公司,在哈尔滨创办通森采木公司等。(14)1932年8月,中国征信所的调查员在调查中孚银行时,发现该行经营稳健,1917-1931年共盈利达292万元,孙氏实业中“最著成效者,如滦州矿务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上海阜丰面粉公司、北平通惠实业公司(现已迁沪)等,皆资本雄厚,年有进展,而与该行均有甚深之关系,互相维系者也。其营业宗旨,主张稳健,故虽无突飞猛进之现象,但循序渐进,历来营业顺利而行基日益巩固”。(15)这类跨行业投资大多是为了规避系统性风险。孙氏企业不求高速扩张,是多元投资做得最好的。
融资需求是多元投资的一个共同理由。可以发现:大多数企业家的多元投资都会包含金融业。大生联号中有一家淮海实业银行,只是成立稍晚(1920年),可能是张謇对此觉悟较晚。到1921年为止,张謇还投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5000元,大生纱厂沪账房主任吴寄尘投资该行1万元,张謇是上海银行1919年至1922年的董事,张謇的哥哥张詧是该行1919年至1926年的董事,吴寄尘则是该行1919年至1923年的董事,1922和1923两年并任副董事长。(16)荣氏兄弟对金融业的投资远比张謇数量大,荣家以申新纺织总公司的名义在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有大量投资,投资中国银行25万元,投资上海银行45万元。荣宗敬在这两家银行都担任董事。荣宗敬还以个人名义投资于钱庄和银行,其中有投资额可查的,在1931-1932年间,有信康等5家钱庄和统原银行,投资额共在25万元以上。1919年,荣宗敬参与创办正利商业储蓄银行,1920年荣参与创办大丰商业储蓄银行,同年又与虞洽卿一起创办了劝业银行,1923年参与创办江苏华大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又参与创办正华银行,1931年荣是新成立的中和商业储蓄银行和宝丰保险公司的董事。(17)通阜丰联号的孙多森于1916年在天津创办中孚银行,额定资本200万元,实收102万元,1921年收足150万元,是一家颇具实力的银行。(18)刘鸿生于1921年发起创办煤业银行,并担任董事,(19)1931年创办中国企业银行,并担任董事长。(20)
融资需求中用于正当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是主流,但也有用于投机活动的。申新总公司在1934年以前的四年间的巨额亏损,主要不是因为市面不好,而是因为投机:在国外的小麦、棉花、外汇市场上做投机共亏损1227万元以上(包括1926年的外汇投机亏损75万元)。(21)上海房地产富商程霖生是衡吉、衡余等好几家钱庄的大股东,程氏做标金投机失败,便向自己投资的钱庄借钱,企图翻本,结果越陷越深,标金期货的本没有捞回来,钱庄也被拖跨了。(22)1929年底程氏共欠42家钱庄、6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公司等债务达2037万两。(23)若非上海钱业公会竭力维持,一场金融风波恐不可避免。
近代中国企业家的多元投资,尽管都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进行的,但各自的结构特征仍互不相同。有的已有了相当规模的主业,主业有一个的,如郭氏的百货,(24)刘氏的火柴;也有两个的,如张謇的棉纺与农垦,荣氏的棉纺与面粉;更多的则主业并不明显,每业的投资规模都不够大;还有的分散于证券和银钱业各部门。当时缺乏实业基础而跨行业投资于金融和房地产,或金融和商业,或在金融业各行中作跨行投资的人所在多有,其投机性较为明显,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如:1921年底孙铁卿等在上海创办信通商业银行,资本仅20万元,“利用华商证券交易所之存款经营得法,获利颇巨”,1923年该行同人“将历年花红储蓄,与银行合资,以二万元代价,购得华商证券交易所第十号经纪人位置,号牌为信通证券公司,号址即附设行内,代客买卖证券,中国、交通、四明等银行公债交易,其时大都由该公司经手,业务颇呈蓬勃气象”。(25)总行在香港的嘉华银行系粤商创设,“股东中以经营地产者居多,故大半与南华地产公司有关系,在申设立分行,以便利在沪粤人经营地产为宗旨”。(26)华东商业储蓄银行的股东大致由平湖和苏州两大帮构成,这两大帮以经商为主,但实力并不十分坚强。(27)
近代中国企业家多元投资的管理模式尚未达到钱德勒分析美英德现代大企业时所总结的控股公司、层级制和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发展阶段,主要仍是以家族权威人物为中心的管理,但也出现了若干企业管理层从血缘和同乡发展到非血缘和非同乡的进步,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刘鸿生曾设立中国企业经营公司对他的多元投资实行集中管理,他所选定的中国企业经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是非刘姓的华润泉。(28)1926年代表广东人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上海总商会会员的,竟然是一个浙江慈溪人陈才宝;而湖南长沙人陈沧来代表北方资本久大精盐公司的上海支店成为上海总商会会员;代表宁波叶家老顺记五金号参加上海总商会的是一个江苏嘉定人项如松;而代表安徽系资本中孚银行上海分行参加上海总商会的则是一个上海人谢芝庭。(29)根据1921年的调查,大生系统的华成盐垦公司,在总协理、会办、监察共5人中,有1个浙江绍兴人,1个四川富顺人,江苏人虽有3个,但只有1人是南通本地人;总会计处共有6人,其中1人来自四川成都,1人来自安徽婺源,另外4个江苏人中也只有1个是南通人;工程处7人中有2个安徽人和5个江苏人;工料处6人中有浙江、四川、安徽籍各1人,其余是江苏人;北闸工程处8人中有湖南籍1人;各乡管理27人中有浙江3人、安徽4人、湖南和四川各1人,其余都来自江苏各地;窑务处经理是北京人;闸务草务渔务总稽查是1个直隶新城人;盐务处也有1个直隶人。(30)甚至这样一个盐垦公司的主要管理部门,按理最应该与乡土特色相维系的,却也吸收了不少外乡人。
在企业的组织架构方面,虽然持股公司未能成功出现,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也未壮大到足以引领企业的管理革命,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改变。如:五洲制药公司原来只有一个皂药厂,一个银公司,管理比较简单,但随着业务的迅速扩展和工厂、营业店号的不断增设,公司管理也有了进步,根据职能部门分为生产、营业、财务和管理四个系统,下面再设科、股,分别执行具体业务。(31)申新企业原来是无限责任企业,由荣宗敬一手掌控的,但一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个别人的精力、经验和权威是有限的,不再能实行有效管理;二是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冲击后,荣氏兄弟实际上已不能承担财务上的无限责任,因此便酝酿将无限责任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但在改组过程中在管理权限上未能取得协调一致的意见,于是出现了一个公司内部分立成三个系统的局面。(32)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是将生产厂的业务分成三大块:一是家用化学品厂,二是橡胶厂,三是油墨厂。这三大块的业务是分而治之的。(33)这有点像事业部制的萌芽。至于刘鸿生的尝试建立持股公司,更是一种在西方理论指导下的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了。
三、多元投资的实际效果之一:高速扩张的陷阱
多元投资是为了“寻求最佳经济效益”,或为了避险等等,但实践的结果,凡扩张过快的,就会落入陷阱,走向与当初的愿望正好相反的命运。在这方面,张謇的大生企业系统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大生企业系统的扩张速度惊人,到1922年底,企业总数近60家之多,资本总额2483万两,其中纱厂4家,资本总额770余万两,盐垦公司竟达约20家,资本总额1238.7万两,比纱厂的资本总额还多。(34)盐垦地在改造的过程中大量投入,却少有产出,常以纱厂的资金援助盐垦,如1922年盐垦各公司欠大生一厂的债款达133.4万两之多。(35)可以说,盐垦公司是把大生系统拖入扩张陷阱的主要问题所在。
盐垦事业需要大投入,可是这些盐垦公司成立时并未征召足够的资本,原因是怕资本多了,股东的利益会变薄:“始当集资之时预计股东之利,资多则利分,资少则利厚,非不知集充分之资而事易办,实欲厚股东之利而资宁少,则事大而资少,资少而贷债。”资本少了,借债当然就多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能够速收多元之合利:“继欲股东之速收,促工垦之并进,百事同兴,需款难继,不得不贷债以竞其功。”可惜“终因天时灾欠,颗粒无收,债息须还,累积无算”,把整个大生系统拖入困境。(36)
在盐垦事业刚刚兴起、规模尚小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通海一带“人浮于地,故争携订守[首]来佃,来佃者率有少数资本,固将以此为生也,于是深沟加泥,培草肥地,地因易熟利因易获,佃利而公司亦利也”。在盐垦规模小的时候,佃户带资承佃,积极改良土壤,效果甚佳。但盐垦公司越来越多,盐垦地越圈越大,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公司为了获得劳动力,“定优待之章以广招徕”,许多承佃者不是通海的当地人,他们无订首,或只缴很少的订首,没有改良土壤的资金却承佃大块土地,“欲广种而多利”。遇到天灾,这些未经改良的土地无产出,公司不仅收不到租,反而需要对这样的大批佃户“抚恤赈济”。(37)
到1922年的时候,通海盐垦“各公司负债约六百万[元]”。本来,在过去的若干年中,盐垦公司的困难都是由纱厂系统帮助解决的,但1922年中国棉纺织业因扩张过快发生“棉贵纱贱”的困难,大生诸厂“亦同处困难而乏现金”。通海各盐垦公司股东提议:将各公司借款时“指备还债之地拟共划出一百万亩……每亩作价十二元(顶首多寡均归纺织自收),合共银币一千二百万元,除填给股票以抵债额外,应找出现金五百万。此项拟由纺织分为三年按期交付以备工程各用”。考虑到“纺织缺乏现金”的状况,“拟将通海一带之布厘纱税力向政府请免十年(每年布厘纱税约在四十万左右),即以此税为借款五百万保证之基金,作移助垦荒河堤建闸之用(此专指辟治卖出之百万亩),其余各地工程尚待另筹”。将借款担保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政府免税可能性上,而且,在因贪大求速而遇到莫大困难时,还在描绘一幅更大更速的盐垦计划,说什么淮南盐垦计有荒地430万亩,各公司之地加上民荡更共有1500万亩—1600万亩之谱,待开垦完成,政府每年可多收税费百万元以上,“而沿海千余万无告之穷民亦可得资生活,诚一举而数善焉”。(38)
这份意见书反映了盐垦公司股东的投资心态,也反映了大生系统决策层的投资心态,他们对投资前景的考虑过于乐观,过分理想化。让政府免税,当然不可能是通海投资人所能一厢情愿地决定的,最可行的还是求助于银行。但即使像张嘉璈这样的当时中国银行业的顶级精英,对于大生系统的过度投资和过快扩张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反而受盐垦公司影响,把银行拖入了大生系统多元高速扩张的漩涡和陷阱之中。
1921年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率银行业十余人到通海盐垦各公司实地考察,参观了“已垦之地”和“所备即时可垦之地”各50万亩,共100万亩,通海方面负责接待的吴寄尘介绍说,这100万亩“每亩平均价格三十元,计值三千万,现在四公司(按:指大有晋、大豫、大赉和大丰)股款四百八十万,如举债五百万,合计未超过一千万”,希望能以土地抵押发行公司债筹资。张嘉璈在去通海考察之前,就已有“邀集中国银行团协商从垦务公司入手”发行公司债,“借以展拓社会经济”的先入之见,到通海实地视察后感到“尤为满意”,决定着手进行。(39)
张嘉璈后来成功地组织了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40)决定发行两期公司债:第一期300万元,第二期200万元。条件是两项:第一项是银团方面要求得到“酬红地”作为发行债券的回报,五公司董事联席会“公决在华成公司北余区内购出地三万六千亩为五公司第一期三百万债票酬红地,通告银团派员勘定”。(41)3.6万亩是个不小的数字,但似乎银团方面还不满意,所以最后的数字是4万亩。(42)第二项是公共试验场的开辟。即银团在五公司地产范围内挑选一块地建立一公共试验场,“为改良种植起见”,在每年经常费用三万元中,五公司津贴一万元。(43)
应该说,这是两个不怎么厚道的条件,五公司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别无选择。但可惜的是,发行公司债所募得的款项,并没有像先前预想的那样用在农田的改良工程上,银团“第一期债本三百万元之接济,仅敷偿还旧债一部分,而对于经营地亩各项工程,仍未有所设施。且当债票发行之年,各公司骤遭灾歉,故订定偿还之本息,即多数未能按约履行”,银团只能一再展期。(44)迁延至1931年,各盐垦公司已呈瘫痪之势:“各公司益陷困顿,甚至经常费用,亦难筹措,主持无人,各事停顿,不复顾惜信用,更无论清理债务。”(45)
高速扩张常以理想条件为预期,一旦条件改变,高速扩张就会变成陷阱。大生的盐垦系统是如此,荣氏的申新系统也是如此。申新系统从1932年起所遭遇的财务困境,是与它在这之前的十年中高速扩张,因此债台高筑密切相关。(46)另一个例子是上海的房地产富商程霖生。程霖生的主业是房地产,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忽然大举进军钱庄业,他所投资的钱庄先后有鼎元、衡泰、成丰、吉昌、衡吉、泰昌、达源和衡余等8家,1925年1月退出鼎元,与程氏有关联的钱庄还有7家。这7家钱庄,有的是他独资盘下的,如衡吉,其他则是第一大股东的身份。这样近于豪华的金融业投资,似乎为程氏构筑了铜墙铁壁似的保护,然而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程氏的钱庄全都好景不长,从1927年起接连倒闭,大致到1930年全部停歇。倒闭的原因是程氏向这些钱庄的过度借款。(47)程氏自恃有强大的金融后援,无惧地涉足标金期货投机而难于自拔,向自己的钱庄大量借款,结果将这些钱庄一一拖倒。(48)1929年他的负债总额高达2037万两,须把程氏的房地产全部拍卖才能勉强了结债务。(49)
四、多元投资的实际效果之二:以丰补歉的实施条件
以丰补歉是多元投资的宗旨之一。这看起来符合逻辑,但实施起来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实施条件至少有以下三个:第一个条件:以丰补歉必须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上,若单向帮助,则不能持久;第二个实施条件:“歉”的程度若太深,“丰”的企业不愿意介入;第三个实施条件:因为没有控股公司的产权约束,家族权威的意志在这一点上是有限的。
张謇的通海盐垦事业,初期规模小的时候效果尚可,但规模一旦放大,就似乎成了往里投钱的无底洞。大生纱厂对通海盐垦的帮助是单向的。而当大生纱厂自己遇到困难时,盐垦系统不可能帮上忙。郭氏的永安联号企业也是这样,大致上是香港和上海的两个百货公司单向帮助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从1923年到1930年,上海永安公司调拨给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的资金多达750万元,甚至超过后者的原始资本600万元的数额;到1933年底,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结欠香港永安公司的债务余额为607.3万元,结欠香港永安公司银业部的款项另有108万元,两者合计715.3万元。但这种单向的帮助是不可持续的。从1934年起港沪两地的百货公司营业日渐低落,资金周转困难,从银行已很难增加借款,在这个时候,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并不能帮助这两家永安百货公司。权衡之下,郭氏认为只有牺牲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来保证两家百货公司渡过难关,因此不惜以低价抛售“永纱”,来归还对两家百货公司的欠款,结果使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濒临破产。(50)
荣氏的粉、纱两业原是比较理想的互补型投资,但实施的结果并不理想。1922年以后,茂新和福新面粉系统少有扩张,而申新棉纺织业系统却高速扩张,到了30年代前期,二者的境遇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从1922年到1931年,面粉系统总体上仍能盈利。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美国实行“杨格计划”,先后贷给国民党政府小麦60万吨。国民党政府便把这些小麦分配给各粉厂代磨,麦价比市价便宜,磨成的面粉则照市价结算给国民党政府。经办此事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和美国人贝克。凭着实力及与陈光甫的密切关系,茂新、福新和阜丰等大厂获得了大部分代磨权,茂新和福新系统得到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是该系统在粉业普遍困难的时候还能获利的根本原因。(51)据统计,单就福新系统的面粉厂而言,1932-1936年共盈利达672万元。(52)而申新纺织系统则面临搁浅清算的风险。所以,“银钱业中人多主张以粉厂之余,补纱厂之缺”。但当时荣宗敬虽为茂福申新总公司总经理,但福新面粉系统实际是由创办人之一的王禹卿掌管的,荣、王之间存在分歧或隔阂,王以为荣氏纵子投机,损失达千万元之巨,是造成申新系统困难的主要原因,损害了股东权益,因此不愿过多地卷进申新的债务中去。而荣氏认为粉厂系统也是主要由他们兄弟俩创办的,理应帮助纱厂渡过难关。(53)
事实上,粉厂也不是没有支援过纱厂。1927-1931年,汉口的申新四厂每年都从福新五厂借钱,1931年达到226万元之多。(54)1934年6月7日,申新纺织公司向中国、上海两银行押借280万元,借主为荣氏兄弟,而福新粉厂系统负责人王禹卿担任保证人;荣宗敬以福新一、三、七厂合同议据向中国、上海两行押借100万元,款项用于纱厂,而王禹卿则用粉厂资金归还约30万元;另外还有用福新二、四、八厂押借款项用于申新纱厂系统的。(55)长期分管经营福新面粉厂的王禹卿、王尧臣兄弟及福新其他非荣姓股东,害怕荣氏以粉补纱的战略会把福新拖垮,所以商议决定,将福新系统从茂福申新总公司中分离出来,另立福新总公司,由对外信誉好于荣氏的王禹卿任总经理。(56)
当然,荣氏仍是福新的最大股东。福新的分离,说明茂福申新总公司本来就不是一个持股公司,同时也说明以丰补歉的多元投资战略,还只是少数人心目中的理想状况。在实际运作中,如果“丰”的一方对“歉”的一方的长期发展没有信心,不愿冒险卷入债务漩涡的话,它采取的策略很可能就是自保。1935年1月,荣氏兄弟提出议案,要求以福新盈余帮助申新、以福新二厂道契向麦加利银行押借200万元,并以面粉生产的“下脚”收入担保支付这200万元借款的利息等,遭到王氏兄弟等竭力抵制。王禹卿对先前为荣氏借款所作的担保,也无意继续,甚至要求银行方面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荣氏,称“如逾期不为审判上之请求,鄙人即免担保之责”。(57)
以丰补歉的多元投资战略本身即带有战略制定者的主观意愿和家长权威在内,虽然符合大家长的整体利益,但对丰方和歉方的其他股东而言,这种交易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型交易。肯定有一部分人(丰方)的利益受到了伤害。而这部分受伤害的人并不认为他们今后能有机会得到补偿。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会抵制家族企业大家长的意志。
五、多元投资的实际效果之三:金融业难以做到保驾护航
实业家们在多元投资的时候,往往少不了要投资于金融业,他们投资了金融业,以为有“财神爷”护驾,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克服困难。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财神爷”反过脸来,有时会变成“索命”的“判官”。企业与银钱业之间在顺境时的融洽关系也不复存在。
1924年2月,张嘉璈鉴于通海盐垦各公司的困境,建议“再募集二百万”,即照原计划履行第二期公司债的发行。这一建议遭到银团其他成员的拒绝,正如盛竹书所言:“续借一层恐不可能之事,盖债票信用早已完全丧失,且每届付息还本终不能如约应付,如言续借非根本整顿另订办法不可。”(58)
1924年通泰盐垦已无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运作的气象,各公司,特别是境况稍好一点的公司,不愿再同其他公司连在一起,相互负无限责任,主张“分立办事”。(59)应该说,从彼此负无限责任到“分立办事”,银团方面的利益是受损的,但当时已无合适人选有能力整体主导五公司,所以分别签约是不得已的办法。银团方面加紧催缴作为土地产权凭证的“部照”(这是土地抵押必须实行的规范手续),却发现“大豫公司已将担保地卖出”归还其他债务,引发了一场债务纠纷。(60)收缴“部照”的事拖延了好几年没有结果,后“自十八年起,几经交涉,且为之筹垫款项,始将所有部照领齐保管,较之徒恃契约,似聊胜一筹”。但这时各公司情况越来越糟:“不独对本团债票本息无从措理,甚有私将原为本团抵押田亩,擅自转抵,或出售,冀得现金周转者,种种违约举动,不一而足。虽经本团一再严重交涉,亦无适当解决办法,此则各公司已至山穷水尽,纵欲顾全债信,亦不可得矣。”银团见此情形,便于1928年间将发行300万元债券的“酬红地”4万亩接收,“组仓自管”,1929年联合南通兴丰银团“组织维持会”,共管大丰公司,同年又与华成公司订定代管协议,1930年组织委员会执管大豫公司,1933年执管大赉公司担保地。大有晋债额最少,就没有实行执管。自执管以后,“略事整理,已获相当成效”,但综合各公司担保地亩的全年收入,即使是丰稔之年,所余也有限,灾年则“形支绌”。关键是土地未经改造,产出自然就十分有限:“多数地亩,均属草荡,如不设施工程,则天然进步固微,而碱潮冲击为害尤巨,非谋积极进行,难收桑榆之效。所虑者担保地虽经执管,而地权仍属公司,进行固多窒碍,筹款亦自不易,地权不能解决,工程亦无由而实施。”银团为保证自己利益,对土地实行“执管”,但同样不愿投入进行技术改造的资金,盐垦公司的问题至此已成死结。
荣宗敬对金融业的投资热情是当时实业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所投资的中国、上海等银行及多家钱庄也确曾给荣氏企业帮过很大的忙,1929年-1930年期间,中国、上海两银行还为争做汉口荣氏企业生意而彼此产生矛盾。(61)但在荣氏企业的财务困难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上海两家实力雄厚的大银行对他们的大股东兼董事会成员荣宗敬却并没有法外开恩,而是采取一切措施追偿欠款,控制申新企业,使荣宗敬破灭了金融业是他坚强后盾的幻想,使他知道,他一直以来在这方面的苦心经营到头来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正是因为中国、上海等银钱业债权人对荣宗敬父子的不信任,才导致荣宗敬在1934年7月间的一度被迫辞去企业的总经理职位,(62)后虽复职,但银钱业债权银团对申新的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先是仅“由银行派员驻厂监督资金的支付”,后来发展到“银团参加部分企业的经营管理,直接控制企业的生产业务,而损益则归企业负担”。(63)实际上,银团这么做并不过分,这有点类似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在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时,主银行可以接管企业。(64)荣宗敬对银团在进货渠道等方面的严格控制非常不满,他在致陈光甫的信中发泄不满情绪,说“弟与台端相识多年,交谊亦尚不薄”,为什么银行方面如此限制申新采购原料?还说申新如果搞不好,“则不幸者不独敝公司已也”。(65)荣家甚至有舍弃中国、上海两家银行,另觅交通银行支持之意。但过往的历史和沉重的债务岂能一刀割断?钱新之代表交行回复荣家:交行与“中国、上海两家关系已深,如合力扶助,极愿分担一分子;若舍两家而单独为之,似交情上不免为难”。(66)
1935年1月,申新一、二、五、八厂与中国、上海两银行及永丰钱庄所订营运借款补充合同满期,银团对继续垫款营运提出条件,要以银团为主体管理工厂,而荣宗敬认为银团只能监督财务,不能过问厂方生产。争论双方相持不下,最后折中:银团继续按原订合同垫款营运申新一、八厂,申新二、五厂停工,四千工人失业。(67)
应该说,申新所遇到的困境,主要是因荣宗敬的过快扩张、过度负债的盲目乐观的经营方针所致。他不应该不知道产业周期的道理。他所投资的银钱业似乎可以为他提供取之不竭的资金,但事实不可能如此单向的慷慨。1934年6月底,申新纺织公司的资产总额是6899万元,而负债总额(不包括资本和股东其他权益)高达6376万元,照此计算,此时股东权益仅余523万元,而申新系统1932年的自有资本是1802万元,(68)可见已大大缩水。中国、上海两银行对申新的扶持可谓已达极致,如1933年底,上海银行的纱厂放款总数计2254万余元,约占全行放款总数的17%;各厂中以申新的数额居首,计1322万元,占纱厂放款的58.6%。(69)也就是说,对申新放款占上海银行放款总额的10%。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比例是高得惊人的,因此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银钱业对股东滥借行为的负面后果是有所觉悟的。1923年2月28日的上海钱业内园年会通过了“同业股东与本庄往来案”,对股东的借款行为进行限制。该议案规定:股东“与本庄往来,应以存款为标准”。(70)就是说,股东与他自己投资的钱庄的关系,应该是在钱庄里存钱,而不是向自己的钱庄借钱。程霖生事件发生后,钱业对股东借款更加警惕。在1930年7月2日公会的一次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钱业领袖秦润卿提出了改革钱业的5项办法,其中第一条是:“股东在本庄往来应有存无欠,即其联号往来如有欠款,其总额亦不得超过该东所占股份。”(71)银行业出于支持国货工业的民族主义信念,还没有意识到贷款集中度太高带来的风险,但他们在企业财务状况恶劣时对企业的干预和接管行为并无不妥。荣宗敬等企业家应该丢掉幻想:投资金融业不等于给自己上了保险。
六、结论:多元投资效果差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反映
近代中国企业家多元投资的效果不佳,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管理革命尚未出现,企业组织能力的发展有限。近代中国产业发展还停留在棉纺织、面粉等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层面,资本密集型产业还刚刚起步,而根据钱德勒的研究,像纺织之类的劳动密集产业,“大的综合企业只有很少的竞争优势”,其横向兼并及多元投资所“产生的成本利益则远远少于在资本密集工业中的成本利益”;“在劳动密集的工业里,许多单一工厂的小企业继续取得成功”。(72)申新系统由于搞兼并,其生产总量的增长率居华商同行业之首,但并没有数据表明,它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居华商同行业前列的,或者它的成本是最低的。
第二,由汇率、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政治性周期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往往是整体性的,不分行业的,很难通过多元投资来调节。近代中国的各个产业都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发展期,并没有形成自己特定的产业特点和产业周期,还没有形成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基础的产品创新周期基础,虽然中国经济自身也会出现一些类似周期的因素,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的产业大发展及1922年起数年的产业调整,但主要的产业风险是由汇率、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的政治性周期带来的。(73)由这些因素所带来的产业风险往往是全方位的。那位信奉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刘鸿生,在1933年至1935年间他的“各项企业”都“遭受很大的损失”,“这些企业毫无例外地正在经历一个十分危急的时期”。(74)事实证明,放在几个篮子里的鸡蛋是有可能同时倾覆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时,纺织业和面粉业的情况都不好,荣氏面粉业只是因为获得代磨美麦的特许业务,才在整个行业的萧条背景下独得一线生机,也难怪王禹卿不肯拿粉厂盈余过多地去支持纱厂了。当政治性周期处于政府大力发展公营事业的时期时,民营企业不管属于什么行业,都会遭遇困境。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实业家的多元投资受到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而避险和获取范围经济的成效并不显著。
①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154页。
②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74页。
③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240页。
④宋美云:《试论近代天津企业规模化发展路径》,载刘兰兮主编:《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5页。
⑤王颖博士学位论文:《近代家族性联号企业:一种非企业集团的中间性组织》,上海财经大学,2007年。
⑥(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张逸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⑦同上,第242—245页。
⑧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王珏、李淑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⑨详见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并可参阅卫春回:《张謇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0页的表2.1和表2.2。
⑩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208页。
(11)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12)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第238页。
(1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45页。
(14)郝秀清:《清末明初的“通阜丰”实业集团》,《安徽史学》1993年第1期;杨金:《寿州孙氏家族与阜丰面粉厂》,《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并参阅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附录。
(15)中国征信所第169号报告,1932年8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以下简称“上档”):Q275—1—2288—3。
(1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0、51页。
(17)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239页。
(18)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1933年刊印,相关各页。
(19)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1页。
(20)《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B84页。
(2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398页。
(22)成言:《房地产富商程霖生、程贻泽》,载政协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3)程氏债权银团会议录,1929年12月27日。上档:S174—1—37。
(24)也可以说,郭氏的主业有两个,即百货业与纺织业。但纺织业在郭氏企业中的地位远不如百货业。
(2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于信通商业储蓄银行的情报第6447号,1934年10月23日调查,1934年11月19日发出。上档:Q275—1—2227—1。
(2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1088号调查,1933年1月30日。上档:Q275—1—2227—2。
(2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情报第1857号,1933年5月4日调查,5月5日发出。上档:Q275—1—2227—2。
(2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3页。
(29)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517、525页。
(30)华成盐垦公司调查报告,1921年。上档:S442—1—4。
(31)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第48—51页。
(32)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第54页。
(33)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第55页。
(34)卫春回:《张謇评传》,第156—157页。
(35)南通市档案馆、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留学生部江南经济史研究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I》,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36)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整理盐垦公司刍议”,约1921—1922年间。上档:S442—1—7。
(37)同上。
(38)通海股东提议盐垦固本轻累意见书,1922年。上档:S442—1—8。
(39)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关于辛酉年五盐垦公司发行债董事会、股东会、董事联席会议案,1921年。上档:S442—1—11。
(40)通泰盐垦五公司系指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和华成等五家。
(41)辛酉年夏历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五公司董事联席会决议,1921年。上档:S442—1—11。
(42)沈元鼎致银团各成员函,1924年12月1日。上档:S442—1—15—35。
(43)辛酉年夏历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五公司董事联席会决议,1921年。上档:S442—1—11。
(44)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报告,1933年8月。上档:S442—1—3。
(45)同上。
(46)参阅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86页。
(47)杜恂诚:《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89页。
(48)成言:《房地产巨富程霖生、程贻泽》。
(49)程氏债权银团决议录,1929年12月6日;程氏债权银团会议录,1929年12月27日。上档:S174—1—37。
(5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126—128页。
(51)《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74页。
(52)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122—123页。
(53)《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08页。
(54)《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77—278页。
(55)《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94页。
(56)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124页;《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77页。
(57)《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94—495页。
(58)经募通泰五公司债票银团会议录,1924年2月28日。上档:S442—1—1。
(59)经募通泰五公司债票银团董事会议录,1924年4月5日。上档:S442—1—1。
(60)经募通泰五公司债票银团董事会议录,1924年6月20日。上档:S442—1—1。
(61)《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73—276页。
(62)《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12—413页。
(63)《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42页。
(64)青木昌彦、休·帕特里克主编:《日本主银行体制》,张橹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9页。
(65)《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44―445页。
(66)《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45页。
(67)《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66—467页。
(68)《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04—405、280页。
(6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513页。
(70)上海钱业公会内园年会会议录,1923年2月28日。上档:S174—1—1。
(71)上海钱业公会执委会议事录,1930年7月2日。上档:S174—1—4。
(72)(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规模与范围》,第41页。
(73)关于中国近代经济的政治性周期,请参阅杜恂诚:《中国近代经济的政治性周期与逆向运作》,《史林》2001年第4期。
(74)《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28—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