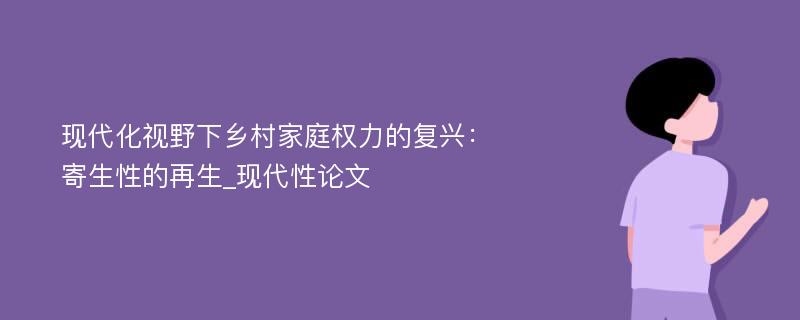
现代化视野下村落家族势力的复兴:寄生性的再生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落论文,势力论文,视野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村落家族势力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家庭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迄今为止,家族势力仍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得到国家政权的扶持,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家族势力作为一种秩序基本上稳定。从本世纪开始,中国村落家族势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动荡分化的时期,消长趋势间替。然而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文化悖论: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发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的家族势力却重新复兴起来。这股“回流潮”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一
家族,又称宗族,它是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古代社会中,家族常表现为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聚居在某一区域,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合成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注: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 页。)。家庭是家族的基本构成单元,家庭借助于血缘关系扩展成家族。从关于家庭的文献著作来看,学者们对家族的解释一般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家族看成是以血缘为中心的封闭性的、具有现实的社会经济功能的体系;另一种是把家族看成是家庭之上的虚体或纯粹的意识形态和认同感。笔者认为,家族势力的含义既具有“实”的一面,即社会的外观形态;又具有“虚”的一面,即表征意义。
长期以来,家族势力在农村逐渐成长为一种自在的秩序。然而自本世纪初以来,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家族势力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是对立的两级,是一种完全的取代和被取代关系。然而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发展的实践却表明这种观点是有局限性的。在中国农村,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产生了一种刺激——反应模式, 或称为“互以为力的双元体”(注:
"Japan:the Continuity of Modernization",in L.W.Pye and SindegVerba,PoLitical Culture&Political Development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Word.)。 家族势力作为传统性的一大因子的复兴表明,在中国农村传统性和现代性并没有处于相互排斥的极端状态。其实,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性,相反,现代化进程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适应的过程(注: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年版,第18页。)。
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家族势力的复兴的。人民公社和10年“文革”的政治风暴使中国的行政触角几乎涵盖了整个农村社会,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又使广大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虽然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比较松散,但我国已绝不是那种“只有‘边陲’而没有‘国界’”(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的传统国家了。 从总体而言,我国正处在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糅和的阶段,家族势力作为我国传统性的重要一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程中努力寻找自己的落脚点,虽然有点杂乱,但总体还算有序,从而在外观上表现为“回归”或者“复兴”的趋势。
笔者把这种“复兴”称作“寄生性的再生长”,之所以称其为“寄生性”,是考虑到下述两点:一是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糅合中,现代性在总体上占优势,并且优势递增;二是传统性的韧性和穿透性使其表现出新的外观和内涵,并对现代性起着阻碍和推动的双重作用,其中推动的作用尤为引人注目。
二
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互动的背景下,从家族势力的结构和功能入手,我们可以发现,家族势力在80年代以后的“复兴”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1.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家族势力对现代性的穿透力度,也是现代家族势力复兴的深层次原因。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施以控制所需的科学和知识等资源尚相对不足。我们不妨从两个向度来分析生产力水平对家族势力消长的影响。第一个向度是内外互动向度,即刺激——反应向度。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了现代化力量对家族势力渗透的国度,也决定了国家与社会两重力量在农村的复合度。第二个向度是家族势力内部互动向度,即内部机制。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所有制形式时曾指出: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再生产出来,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马克思的看法用来分析今天的家族势力仍然适用。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使很多农村地区家族势力的根本特性未受到冲击,如血缘性、聚居性和封闭性等,从而使其内部机制以血缘关系决定的权力等级变更不大。
从根本上看,只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从而使现代性在和传统性结合而成的二元复合体中不断增强,才是从根本上消灭家族势力的真正武器,而仅凭外科手术式的风暴疗法是不可能奏效的。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前的时间里,“文化大革命”曾一度席卷了农村,各种“左”的思潮从根本上冲击了村落家族势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打破了血缘关系和家族的伦理纲常,压制了依据血缘关系划分亲疏的传统,甚至在父子、兄弟姐妹间也大搞阶级斗争,既对家族势力的外观文化表征进行肃清,又对家族组织形式和结构进行改造。如在福建省安溪县美法村,所有的家族仪式、社区内部传统的互助行为,均被列入“四旧”加以批判,社区的公共祭祀全部被禁,原来对族内辈份、房份关系的清楚界定被搞得派性混杂,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的无规则化(注: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 第59页。)。再如福建省南部的塘东村,到1976 年时当地的庙宇已荡然无存,祠堂被改造成仓库,家谱被烧毁者高达90%(注: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6页。)。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扫荡是极其表面性的,家族势力的外在文化表征虽然遭到破坏,但其内在文化关联却损伤不大,只是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压抑,并没有终结。如1978年后塘东村蔡氏家族的大部分庙宇已得到翻修,祠堂已焕然一新,祖先和鬼怪的祭祀大为流行(注: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8页。), 甚至在“文革”期间,胶东半岛的村落家族成员还冒着政治风险偷偷摸摸地开展祭祖活动,并组织人编写宗谱(注:辛显龄:《少年天才》,青岛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2.国家行政力量的弱化和社会机制的残缺使家族势力获得了生长的空间,使现代性在和传统性的共生中不占优势。
应该说,中国农村行政力量的薄弱由来以久,而国家与社会是一种你进我退的关系,国家力量的萎缩必然导致家族势力这一重要社会力量的复兴。
在西方文明中,家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它在中国却生生不息。这一方面与文化的特质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特殊的家—国关系有关。中国是一个宗法国家,从西周开始,家族内部的等级序列就和国家政治统治的行政序列合二为一,宗主就是国君,血缘关系就是统治者内部的政治关系,家即国,国即家。家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经历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大部分国家家族制度的历史命运。长期以来,家与国不但没有紧张的对立,而且家居政坛之上,家国不分,和谐融洽(注:刘广明:《宗法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第2—3页。)。
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利用农村中的家族势力进行行政控制,在农村中家族秩序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至民国时期才被打破,国民党推行保甲制度,试图加强对农村的乡政控制。到了人民公社和“文革”时期,行政力量在乡村的延伸达到了顶峰,但由于这种延伸并不是以物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所以,随着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行政力量在农村大大弱化,国家在农村社会中的很多权力归还了社会。
与国家行政力量弱化相对应的是社会体制的离散,从而使有效的社会控制在信息传递等方面增加了操作的难度。
3.家族势力的复兴充分说明,家族制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发挥着某些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
我们可以把复兴的家族势力解剖成如下几个层面:一是群体行为的复兴,表现在建宗祠、修宗谱、开庙会等形式上;二是家庭内部成员互动行为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互助关系、权力关系等内部关系范式上;三是家族文化、观念等意识形态、范畴的复兴(或者说显性化了),这是一、二两点在思想上的反应。家族势力在上述三方面的复兴是与其所发挥的功能分不开的。
首先是家族势力所发挥的互助功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强化了村落家庭的功能,农户家庭的生产性功能重新处于决定性的地位。中国的家庭不同于西方的家庭,费孝通认为,西方家庭是“生活堡垒”,而“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民族性的了”,“为了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从费孝通这段话中,我们看出了两点:一是家庭扩大成为家族,家庭的观念是家族势力复兴的酵素;二是要经营各种事业就离不开家族内的互助。笔者所关注的是第二点。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集体劳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正式的合作制度与互助形式及民间社会关系网络的衰落,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力量的撤出,政府对农村经济合作和公益事业的直接干预也随之撤出,而农村的小户经营特点又使很多事情单凭一家的力量无法完成,关系资源十分重要。
互助关系的复兴又强化了血缘这一家族势力的本质规定。根据调查,血缘关系仍是农村最重要的可利用的互助资源(注:沉石、米有录:《中国农村家庭的变迁》,农村读物出版社,第93—94页之图表。)。下表是对福建省塘东村30个住户进行的社会互助抽查结果。通过该表可以看出,在农村互助中血缘关系仍起着主导作用,友缘和业缘尚处于次要地位(注: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2页。)。
互助类型 财政支持关系支持劳力支持 信息支持
堂亲48%
41%78% 42%
姻亲25%
34%14% 29%
朋友27%
25%8%
29%
家族成员间的合作与互助,不仅体现在生产和劳动上,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的家族内部关系整合成一种非正式的地方性制度进入了功能再现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这种互助合作实际上也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动力支持,如福建、广东等地很多家族成员内部联合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办企业。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寄生性共存在这里找到了最佳的诠释。
其次是家族势力发挥了一种情感满足和社区认同的功能。这一方面是改革以前长期被压抑的心理和情感势能的释放,一方面也反映了新时代下农民精神上的浮躁和不安。处在现代社会中的农民,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乏力感成为普遍的心态,精神上漂泊不定,找不到泊位(注:王晓毅:《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与此同时,中国不同于西方,中国是礼俗社会,而西方是法理社会(注:费孝通:《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中国人对祖先十分敬奉。改革开放后农村各地出现的建宗庙、修家谱以及家族组织的各种节庆,反映出传统仪式的不可替代的情感功能。
第三点是家族势力仍履行着一定的维持功能。村落家族需要以一定的方式来维持其内部秩序,这一点也与中国社会是礼俗社会有关。家族讲究“家丑不可外扬”,家族事务最好关起门来自己处理,而上告到法院,无疑会给家族脸上抹黑。费孝通曾经这样论述道:在礼治社会中,子女教育由家庭完成,“子不教,父之过”,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儿子做了坏事,父亲也跟着丢人,打官司也是一种可耻之事,表示教化不够(注:费孝通:《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第101页。)。同时,维持功能的保持还与现代性力量的薄弱有关, 社会体制不能充分取代家族秩序。
传统家族势力的功能很多,其中有的逐渐式微,而有的却不断强化,除了上述三个功能外,家族还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保护、绵延、教育等功能,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
4.家族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因子,辐射力极强,家族文化特质的存在,甚至构成了我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即儒家式现代化。
家族文化不仅涉及家族势力,而且构成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固有成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子,是以家族势力的存在为前提的,其基本价值取向与家族势力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复杂,然而其共同的中心点就是忠和孝,忠就是忠君,孝就是孝亲。围绕忠和孝,又衍生出许多新的文化特质,因为忠,所以对家庭和国家要尽忠尽责,不辱使命;因为孝,所以要显扬父母,光宗耀祖,力争上游,并且要尊敬父母,尊敬长辈;因为忠和孝,所以才念旧崇古,趋向保守(注: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375—376页。)。 而上述的许多传统文化特性恰恰正是家族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忠和孝正是血缘在观念上的反映。所以,没有家族势力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家族文化,而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面目全非了。
家族文化从远古的群体劳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萌芽,逐渐成长为我国的主导文化,并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为其所同化和感染。即使在现代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家族文化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努力为自己定位。如在与基层政权的关系中,家族组织都积极地谋求合作而不是对抗,并且很多家族成员已经意识到需要从法律的角度为自己的一些宗族行为寻找依据(注:钱杭:《当代农村宗族的发展现状和前途选择》,《战略和管理》1994年第2期。)。在此, 笔者想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个概念来形容这种定位,即“穿透力”,家族文化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这是当今我国现代化水平所无法阻挡的,这样就产生了寄生性的再生长。
剔除掉一些消极因素,如家族械斗和血并等,家族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这种“寄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益的。文化具有很强的绵延性和历时性,在这个意义上,家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有时显著些,有时压抑些。如此,80年代以来家族势力的复兴便再也不奇怪了。
三
以上,笔者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互动的框架下简短分析了家族势力复兴的几个原因,并强调指出了在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和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的家族势力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但是,无论如何,当前的村落家族势力已远不是一个规范和完整的体系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几次大冲击:农村土地改革、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使村落家族势力发生了很大的嬗变: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家族内部互动关系发生变化,家族成员可获取资源渠道的广泛化以及相关的家族内部权力关系的变更;家族内部结构的离散化和功能的逐渐削弱;农村中国家行政权威地位的上升和理性、法律观念的增强,等等。
家族势力的相对式微是不容置疑的总趋势,但正如上文所述,我们也必须重视家族势力中的“合理内核”的强大寄生性和附着力。“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化,是打破传统的各种程序,即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但是社会的稳定又是现代化的保障,可以说,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现代化”(注: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这样,一个严竣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即如何才能实现家族势力和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对接,尽量实现“文化软着陆”,并慢慢地消除家族势力的不利因素,从而减少“摩擦性”震荡。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着深刻教训的。1949年后,我国曾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等激进方式对家族势力等所谓的封建迷信进行扫荡,然而事实证明,这种“风暴疗法”只能引起农村秩序的混乱和现代化中断。
毫无疑问,只有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真正对家族势力形成冲击,但同时也必须加强制度引导和制度建设。中国人“认同感”很强,认同基源于历史传统,要想全部抛弃是不可能的(注: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我们可以加强制度上的强化、约束和指导,运用制度的力量逐步引导农民把理性思维和现代意识转化为他们的“新认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冲击家族势力的内部机制,弱化家族成员对家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