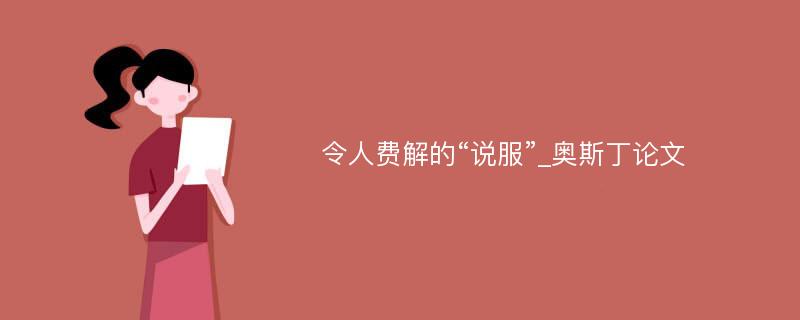
令人纠结的“劝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劝导》(一八一八)是英国女作家奥斯丁(一七七五-一八一七)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叙事围绕自幼丧母的女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一段人生悲欢离合展开。 当年,十九岁的安妮堕入情网,与年轻的海军军官弗雷德里克·温特沃斯私订终身。温特沃斯出身寒门,两手空空,安妮的父亲沃尔特爵士自然不赞成这件婚事。不过,真正下力气出面劝阻并最终促使安妮取消婚约的,却是如慈母般关心她的近邻拉塞尔夫人。自那以后,安妮在小小乡村世界里再没有爱上任何人。她拒绝了本地一位地主少爷的求婚,在伤心和隐忍中渐渐香消玉殒。 由于沃爵士一味讲究排场、追求浮华,渐渐入不敷出,七八年后不得不举家迁往巴思城,将乡下祖宅凯林奇大厦出租。安妮听说承租人竟是温特沃斯的姐夫,不禁百感攻心,意识到难免要经受与初恋爱人重逢的冲击和折磨。对于那桩梗在心头的陈年旧事: 她们(安妮和拉塞尔夫人)并不了解彼此的观点,不知对方的想法是一如既往还是早改初衷,因为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提起——不过,安妮到了二十七岁,想法已经和十九岁大不一样了——她曾经接受拉塞尔夫人的劝导,为此她既不怪拉塞尔夫人,也不责怪自己;可是她觉得,若是现在有哪位年轻人处境相似,她绝不会给人家出那样的主意,让人遭受无可逃遁的眼前苦痛,却未必能得到缥缈虚无的长远裨益…… 假使让安妮·埃利奥特开口,她该有多少雄辩说辞——至少,她会理由十足地支持少年人的炽热恋情和对未来的乐观信心,反对过度的谨小慎微,因为那简直就是对奋斗的羞辱和对神意的不信任!——她年轻之时被迫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随着齿龄增长反倒逐渐习得了浪漫的心性,这是不自然开端的自然后果。(I.4)① 这是小说首次明确点出“劝导”母题。 有不少西方评论家从此节及类似文字中读出了浪漫取向,认为此时奥斯丁“前所未有地深入了个人情感且饱含同情”,更多地站在了个人、情感和欲望一边,更接近所谓“美国立场”,②表达了对来自他人特别是家长的说服指导的抵制态度。有人甚至揣测作者在借此辩驳认为她反对浪漫情愫的议论。③然而这类判断与该节叙述全貌以及小说中许多相关内容有抵触。这些学者将注意力聚于对拉夫人早年劝导的批评,忽略了其他多元化的信息,并且或多或少把小说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感受过度解读为作者的主导话语。 引文出现在上卷四章,其中叙述者和女主人公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微妙而灵动。前一段文字有综述色彩,远非满负荷地传达安妮的心思,但是叙述与她的心态及表达方式的重合度已明显超过此前三章。后段中“假使让安妮·埃利奥特开口”一句径直切入女主人公的视角和语气,一连串波折号更是传神地呈现了且想且说的沉吟情态,仿佛在同步直播正徐徐生成的思绪。准“剩女”安妮的内心独白不仅毫不含糊地表达了针对拉夫人所认同的世俗主流婚姻观的直接批判,也痛切地揭示出横亘于两代人之间的深刻隔阂。由于往事留下的伤痛,由于难以弥合的观点分歧,也由于绝不愿伤害对方的殷殷顾念,这两个往来密切、情同母女的人竟无法袒露胸襟、彼此沟通。考虑到安妮在虚荣而势利的家人中形单影只的处境以及她在本地乡绅交往圈里格格不入的感受,再联系到小说中醒目出现的“疏远(estrangement)”、“间离(alienation)”等极具现代气息的字眼,女主人公与她最亲近友人之间的这种心理距离便更加惊心。如坦纳指出,安妮所置身的社会处于“道德及话语高度分崩离析的状况”,她时时被“飘零无根”之感缠绕,小说中充满“(人与人)彼此隔绝的氛围(atmosphere of disconnectedness)”。④可以说,“劝导”之所以成为必须辨析的问题,与人际关系纽带的瓦解和女主人公作为孤独个体所具有的鲜明“现代性”⑤处境密切相关。对于安妮们,来自权威长者的劝导不再理所当然。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安妮的思索委婉、迂折而缜密。她的态度包含不能回避的内在矛盾:即虽然认定拉夫人当年的劝阻是错误的,给年轻人带来了莫大伤害,却仍然强调自己不怨、不悔。也就是说,她对那一轮伤筋动骨的“劝导”既反对又有所认可。而且,她思考问题时遣词造句十分考究,整饬的巧智对仗(“年轻之时”对“齿龄增长”、“眼前苦痛”对“长远裨益”,等等)以及温和的反讽口气都映现出女主人公的修养和气韵。严谨和讲究说明这场绵延的思考在内心酝酿了多年,浓郁的自言自语风格则提示读者,女主人公是如何在有话无处说的漫长孤独时光中把对个人悲欢的反刍部分地转化成对普遍原则的追问,把怨艾升华为修辞的艺术。 男女主人公各自经过千思百虑,似乎都已有裁断,但那段往事仍然盘结在他们心底。女主人公情不自禁反复思量,理还乱、剪不断,所谓理性反省实际却更是对旧情肝肠寸断的一步一回望。对于大英皇家海军舰长温特沃斯来说,恋人悔婚留下的创伤仍隐隐作痛。他愤恨地认定安妮顺从长者是“优柔寡断”、是顶不住“芥末小事的无聊干扰”,所以,当邻家少女路易莎宣布自己“才不那么好说服呢”(I.7),他毫不迟疑地表示赞赏。然而后来的事态却动摇了他的自信。路易莎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和坚决,不听劝阻从莱姆镇海堤的陡峭石阶上贸然下跳,无端受了重伤,也让众多亲友陷入惊恐忧扰。这一任性表演无意间成为主人公们再次检点往事的契机。全力安排救助伤者的安妮不由自主地分神猜想:这下温特沃斯是否会意识到“坚定的性格也应该有个分寸和限度”、“容易被说服”并非全然不可取(I.12)。如有的学者指出,两人在久别重逢历程中的这些情感发酵、思想调整等“内在动作”构成小说真正的情节主线。⑥然而在这一阶段他们俩有关“劝导”的言说和思考,虽然无不以对方为“目标”和潜在对话人,却似被无形绝缘体屏蔽,彼此没有直接交流。 直到分手八年的恋人终于重修旧好,他们才得以当面锣对面鼓地认真讨论“劝导”。温特沃斯表白道:莱姆之行使他最终信服安妮的方式更靠谱,承认“有必要区分原则坚定和一意孤行”。安妮则告诉他: 我一直在思考过去,想公平地明辨是非……我当初听从朋友的劝告,尽管吃尽了苦头,但还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对于我来说,她处于母亲的位置。请不要误解,我不是说她的劝告没有错误……我说的是听她劝是正确的……因为(若不那样)我会受良心的责备。 安妮力图冷静地、条分缕析地将劝告内容和劝导行为区别对待。她充分承认“劝告”举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拉夫人虑及少女一生的平安,出于责任感和爱心拦阻一见钟情的冲动订婚无可指责;而尽量听从也是年轻人顺乎责任和良知的选择——“我当年肯听劝,因为我认为那是义务”。与此同时,她又认定拉夫人的劝告本身是错误的,那位乡绅遗孀太过庸俗地看重门第、财产和外表风度,依据错误的原则导出了褊狭、势利而又短视的结论。温特沃斯进而坦承这一次自己准备再度求婚之际,其实仍对拉夫人“劝导的威力”心存余悸,安妮便立刻表示“情况大不相同了,我的年龄也不同了”,对方应该明白她如今不会再盲从。经过岁月的磨砺,当年的小姑娘已经有了主心骨。当拉夫人大力举荐安妮远房表亲即她家祖业和名位的继承人埃利奥特先生作首选联姻对象、甚至动情地表示希望安妮能继她母亲成为凯林奇大厦女主人时,她已经不能左右安妮的决定。虽然就地位和财产而言,埃先生肯定会远远超过仅仅在海上冒险生涯中发了些战争财⑦的温舰长,但安妮已事先断然排除了仅只为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而结缡的选项——“假如我嫁给对我无真情厚义的人,就可能招致各种风险,而违背所有的责任”(II.11)。 换言之,安妮认为,以她当年的思想水平和具体处境,服从拉夫人理由充分;而如今审慎拒绝同类劝告更义不容辞。必须承认,在这个“由书名宣示出的核心问题”上,女主人公所提供的最后“答案并非没有含糊歧义”,⑧相反以深刻的自相矛盾以及繁多的限定条件为最鲜明特征,比如要考虑权衡具体事项、劝说者的用心和被劝者的成熟度等等,简直可以说复杂到等于没有确定结论。 在奥斯丁的世界里,对“劝导”感到困惑的不仅是安妮和温特沃斯。《傲慢与偏见》(本八一三)中的达西和伊丽莎白也曾就此“短兵相接”地辩论过。该书一卷十章有这样一个场面:达西在亲友面前挖苦好友宾利做决定草率却又耳根软,听别人劝几句就改弦更张。那时伊丽莎白正在找茬和达西斗嘴,便挺身而出为宾利辩护:“难道达西先生认为,若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就可以把前面的鲁莽粗率一笔勾销了吗?”达西说这是强词夺理地把他没有的想法强加于他,同时强调“没有信服就盲目顺从,对劝导和被劝导双方的判断力都不能增光添彩。”不料伊丽莎白却转而抨击达西“好像不赞成友谊和感情可以有影响力”,逼问他为人随和、乐于顺从友人意愿又有什么不好。达西回复道:这要先确认“友谊亲密到什么程度、那意见是否可取”。至此,舌战已经进入抽象思辨的领域,达西明确地主张要针对具体问题做周详的具体分析——而这,可以说是与安妮的思考遥相呼应。 劝,还是不劝;听劝,或者拒绝听劝;显然是没有固定答案的疑题。 奥斯丁为什么对“劝导”(包括发生在平凡琐细家庭生活中的七嘴八舌议论)如此重视呢? 对于这个疑问,《劝导》一书提供了很多指向答案的线索。 细究起来,“persuasion”(包括同词根动词和形容词)曾出现多次,除了偶尔取其他义项(比如“信念”等),多数情况下意指人际间用语言进行劝导、说服,其中拉夫人劝安妮退婚是最重要的一例。不过该词也出现在其他不同场合。比如:紧随开篇的上卷二章记述了拉夫人和管家合力说服沃爵士出租凯林奇大厦一事;第六章展示了小妹玛丽和妹夫分别说服安妮的尝试(前者希望二姐相信她饱受疾患折磨,后者则企图证明妻子是无病呻吟);下卷一章呈现了路易莎摔伤后安妮如何引导大家协力救人善后的过程。此外,下卷五章细细描写了拉夫人如何赞扬埃利奥特先生、力劝安妮把那位远亲列为最优先考虑的夫婿候选人。在上述几例中,玛丽夫妇的行为出于小小私心私见;拉夫人劝婚可说是重蹈覆辙、再次开出错误的人生处方。但是另外两次劝告则或是言之有理,或是极为必要且出于仁爱和公心。也就是说,小说中“劝导”一词的使用是中性的,被用来指称大不相同的行为——有的可赞,有的可笑,有的当疑,有的当斥。 书中另有两场没有直接用“persuasion”标出的劝导重头戏。一是安妮的女友史密斯太太心怀“个人盘算”⑨揭发埃利奥特先生昔日劣行、游说安妮帮助她自己。史太太的口头“突袭”强化了安妮对埃利奥特原本持有的某些保留和怀疑,从而成功抵消了拉夫人力挺埃先生的说辞。安妮意识到,若没有女友介入,“她本来是有可能听人劝说嫁给埃利奥特先生的……她完全可能被拉塞尔夫人说服!”(II.9) 另一场“劝导”对情节推进更为关键。那就是下卷十一章里安妮与另一位海军军官哈维尔在巴思旅店里的精彩对谈。 哈维尔谈起一名年轻同僚正在为未婚妻过世而伤心欲绝,却突然爱上了路易莎。安妮说,男人原比女人易变,女人生活平淡,更难舍旧情。对此,哈维尔指出:书上可不是这么说的,所有的历史记载、故事、散文韵文、歌谣谚语,都说女人朝三暮四。一向低调而节制的安妮此刻脱口反驳道:“请不要引书里的例子。男人比我们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可以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受过的教育比我们高得多,笔捏在他们手里。我不承认书本能证明什么。” 这一章和其后作为全书收尾的十二章是由初稿中一章修改拓展而成,而且初稿和改稿都保留了下来。研究者们注意到,原稿有些匆促地奔向喜结良缘的大团圆结局,而修改稿放慢了节奏。⑩修改的最重要效果是使安妮得到了长篇发言的机会,突出了她作为意见发布者的身份。她敏锐分辨“他们”和“我们”,一语道破“笔”和“书”的性别属性,确实构成一种思想突破。她言及男人的“持笔”特权时口风犀利,不被儿女私情所拘限,是辩论者立场鲜明的发言和成熟女性的深思熟虑的创见。难怪她的这番议论被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关注女性问题的读者和评者反复引用和论证。谈话不仅体现了安妮作为婚姻伴侣的质量,更投射出一种远远超逾当时淑女规范的新形象。我们有理由认为,她最重要的美德更多体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这种勇敢突围,而并非麦金泰尔所强调的忠贞(constancy)。(11)安妮其实并不曾主张或赞美对男性的无条件忠诚——更不必说盲目的从一而终。她说女性容易固守旧情不值得羡慕,因为这很大程度源于她们相对狭隘的生活。她的“忠贞考”与其行动可互为佐证。我们看到,这位沉静的女主人公不但没有不假思索一概拒绝接触其他男性,相反曾努力拓宽交往圈,只不过她一直坚持从容而明慎地考察判断,一直忠于内心与外在的真实。也就是说,选择忠诚于初恋是安妮在思想和生活中谋求突围的结果,而不是将对特定男人的崇拜与忠顺作为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安妮作为思想者的分量超过了奥斯丁的其他女主人公。 不过,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安妮谈话在叙事中的另一个重要功用,即向温特沃斯传达信息。小说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她开口前已经决定要暗度陈仓。但是读者明确得知:她当时已欣喜地判明了温特沃斯的心态,而且正在考虑该“如何打消他的嫉妒心……如何让他了解到她的真实情感”(II.8),还留意到他怎样借打牌一事申说自己“没怎么改变”(II.10)。换句话说,彼时彼刻安妮最最挂念的就是寻找机会向意中人表白心迹。 当时旅店客厅里还有其他一些人——坐在沙发上的两位妇女正大声议论年轻人的婚姻,温特沃斯在书桌旁埋头写信。其中一位太太是温特沃斯的姐姐,她发表意见说,如果年轻恋人不具备成家的经济条件便率然订婚,实为不智,父母理应尽力阻止。安妮听见,“她的眼睛本能地朝远处桌边望去,只见温特沃斯停了笔,抬起头,凝听着,随即,他转过脸,迅疾而忐忑地瞥了安妮一眼”。旁听者的反应揭示出室内诸人的空间距离都很近、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更近,而且他们时时刻刻都被对方的意识“雷达”锁定。 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安妮来到窗边开始和哈维尔谈话。讨论热切地进行,一个轻微的声响转移了交谈者的目光。循声望去,他们看见温特沃斯的“笔掉到了地上”,“安妮发现他离得比原来想的还要近,不觉心中一凛。她怀疑那笔之所以会跌落,是因为温特沃斯专注于他们俩,想听清他们的话。可是安妮觉得他其实根本听不清。”这一次作者安排女主人公直接忖度有关距离的问题,读者便不得不意识到,安妮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聚焦于那表面上的局外人,而温特沃斯其实是参与谈话的沉默第三者。(12) 作为十九世纪初年的大家闺秀,安妮不能径直走到温特沃斯身旁打开窗户说亮话。然而此刻爱人近在咫尺。她即使没有预谋,也不可能对机会毫无感知,更不愿再一次与幸福失之交臂。因而,她后来的言说,包括“笔”握在谁手的议论等等,既是与哈维尔说理论争,也是在向温特沃斯倾诉衷肠。联系到她赋予“笔”的象征意义,笔的掉落似乎暗示着恋人之间主导权的瞬间转移。平素寡言的安妮一反常态地侃侃而谈,说到最后心中五味纷陈:“女人的全部特权是……爱得长久,即使生命不再,或者希望尽失。” 如有些评论指出,该节对话“从结构上看是戏剧性的而非论说性的”,安妮的发声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为女性整体奋争,而是向温特沃斯倾诉衷曲的冒险一搏”;(13)“面向哈维尔的雄辩之论构成了女主人公向旁听者温特沃斯的爱情剖白”。(14)后者听罢便立刻写信再次求婚,证明安妮旁敲侧击的劝导十分成功。当然,坦陈一已心意与为女性整体代言两者并不必然冲突,完全可以一举两得。 奥斯丁曾把“劝导”和“影响”(influence)当作近义词相提并用(15)。归纳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劝导行为,不难看出在作者心目中“劝导/说服”作为有目的交流,乃是人际关系甚至人类生存的根本形式之一。小说结尾时安妮对“劝导”的多角度论说,虽然是人物之言,却也承载了奥斯丁关于这个问题的忧思。 通过对“劝导”的聚焦,奥斯丁揭示了人际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两面性——它可是束缚、陷阱,但更是个体最根本的生命支持系统之一。 在与《劝导》同时问世的《诺桑觉寺》(一八一八)里,persuasion或其同根词也频繁出现。其中有两段很耐人寻味。一是上卷十三章里自私的伊莎贝拉·索普用甜言蜜语恭维新结识的少女凯瑟琳,说她“心肠软、脾性好,最乐意听从亲朋好友之言”,企图借此哄骗后者任自己摆布。另一段出现在下卷四章,讲述的是天真的凯瑟琳要求亨利·蒂尔尼劝阻他哥哥追求伊莎贝拉,被更通晓世事的亨利当场拒绝了。亨利告诉她:“说服人可不是想有就能有的事”,而且他压根“不会去尝试说服(他哥)”。两段对话的语气都拿捏得极好,活灵活现体现了人物特征,又从不同角度入木三分地展示了各色人对“劝导”的理解和态度。《曼斯菲尔德庄园》(一八一四)另从其他方面丰富了对“劝导”的探究。那部小说中成功的劝导或是发生在半恩师半兄长的埃德蒙及其小表妹范妮之间,或是发生在事事插手的诺里斯太太和她慵懒退缩的妹妹贝特伦夫人之间。自然,更为一言九鼎的是姨夫托马斯爵士对范妮的种种居高临下的指点——“他用的词是‘劝告’,然而那却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劝告(advice of absolute power)”(II.11)。(16)这类事例清楚地告诉读者:劝导方和被劝者之间常常由于地位、财产、年龄、性别甚至个性差异而形成某种“势位”差,私人劝导行为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也存在丝丝缕缕的关联。此外,奥斯丁还点出了非语言行为的劝导效应。比如亨利·克劳福德在朴茨茅斯港的表现就比他的表白言辞更具说服力,几乎使范妮“相信(persuaded)”他确实有了改进。 把这些生动片段如拼图部件那样组合起来,便可大致看出作者对“劝导”多方位考察的全貌。在奥斯丁看来,不论行劝还是听劝,都必须持审慎态度,必要时可以批判劝者动机,可以抵制劝言主旨,就像安妮裁定拉夫人的价值观有错误。但是,形形色色的劝说时刻流转于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影响是人际纽带的必然后果,本身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完全去除。确实,即使安妮当年拒绝了拉夫人之劝,也并不意味着她就精神上“独立自主”了,相反只表明她可能是更多听信了温某人。(17)安妮最后把拉夫人当作唯一可贵的亲友郑重推荐给温特沃斯的姿态,连同她接续与史密斯太太的旧谊以及结识海军界新朋友的尝试,共同构成了打破小说开篇时的原子化孤立个人生存状态、重建人际关系的自觉努力。 奥斯丁小说书名中不时有抽象名词出现,如“傲慢”、“偏见”、“理智”、“情感”等,但是其中唯有“劝导”与动词关系密切,较多体现了作者所服膺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乎行动”(18)的理念。哈·布鲁姆考证说:“劝导”是“抽象概念”,“来自于拉丁语的‘劝告’或‘敦促’……本源可以追溯到‘甜蜜’或‘愉悦’”。(19)对西方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读者都知道,从亚里士多德起到奥斯丁生活的年代,伦理哲学一直与愉悦或快乐纠缠不休,也常常很不脱离群众地讨论“趣味”、“友谊”之类与形而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奥斯丁“敏锐检视当世种种现象并权衡其利弊,这绝非局限性的征象,而是表明她与休谟和吉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她对“劝导”的深度剖析可说是就谋财逐利商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本质和危机进行的饱含痛感的“哲学探究”(20)。不论“劝导”一词最终出现在书名里是奥斯丁本人的决定还是她去世后由家人做出的选择(21),围绕那个关键词进行的反复辨析印证了作者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正是由于对社会变化以及传统人际纽带崩解的现实做出了敏锐而及时的回应,奥斯丁小说才能够在两百年后仍然吸引着、慰藉着同时也拷问着全世界的读者。《劝导》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安妮对个人情感的忠诚与坚守;同时又强调她“是无私的,有群体关怀的”(22)。然而,小说最见笔力之点,不是对主人公私人美德的赞颂,而是展示、探讨个人主体与他人共在的生存方式本身,是坚持让不可删除的人际关系得以“显影”并得到重视和思考。 ①引文出自Jane Austen:Persuasion,Cambridge UP,2006,ed.Janet Todd & Antje Blank,括号内标出的是引文所属的卷(罗马数字)、章(阿拉伯数字),此后其他引文均照此处理。译文参照奥斯丁《劝导》,孙致礼、唐慧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②Thomas Edwards,"Persuasion and the Life of Feeling",in Bridget G.Lyons,ed.,Reading in an Age of Theory,Rutgers UP,1997,p.121. ③见A.Walton Litz,"Persuasion:forms of estrangement",in John Halperin,ed.,Jane Auten:Bicentenary Essays,Cambridge UP,1975,p.231;另见司各特《一篇未署名的评论〈爱玛〉的文章》,朱虹选编:《奥斯丁研究》,第10-2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④Tony Tanner,Jane Austen,Macmillan,1986,pp.218,220-221. ⑤见Litz,p.222。 ⑥R.S.Crane,"A Serious Comedy"(1957),in B.C.Southam,ed.,Jane Austen NORTHANGER ABBEY AND PERSUASION:a Casebook,Macmillan,1976,pp.188-182. ⑦当时英帝国海军状况是近年有关奥斯丁的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参看Edward Neill,The Politics of Jane Austen,Macmillan,1999,pp.124,129-130; Janet Todd & Antje Blank,"Introduction",in Jane Austen:Persuasion,Cambridge UP,2006,pp.xxxiv,xlv-xlviii. ⑧D.W.Harding,"Introduction",in Jane Austen:Persuasion,Penguin Books,1965,pp.12,13-14. ⑨见Elizabeth Jean Sabiston,Private Sphere to World Stage:from Austen to Eliot,Ashgate,2008,p.47。 ⑩Sabiston,pp.36-37. (11)Alasdair C.MacIntyre,After Virtue,Univ.of Notre Dame P.,1984,Ch.16,见《追求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2)见Stuart M.Tave,Some Words of Jane Austen,The Univ.of Chicago P.,1973,pp.267-268。 (13)Mary Waldron,Jane Austen and the Fiction of Her Time,Cambridge UP,1999,pp.152,154. (14)Todd & Blank:"Introduction",p.lxxxii. (15)Jane Austen,Mansfield Park,Cambridge UP,2002,III.Ch.5. (16)见Claudia L.Johnson,Jane Austen:Women,Politics and the Novel,The Univ.of Chicago P,1988,pp.101-102。 (17)见Neill,pp.121-22。 (18)Terry Eagleton,The English Novel:an Introduction,Blackwell publishing,1988,p.106. (19)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第196页,江宁康译,南京:译文出版社,2005。 (20)见Rebecca West:"this comic patronage of Jane Austen"(1928),in B.C.Southam ed.,Jane Austen:the Critical Heritage,Vol.II,Routledge,1979,p.290。 (21)见Claire Tomalin,Jane Austen,Vintage Books,1999,p.272。 (22)Alistair M.Duckworth:The Improvement of the Estate:A Study of Jane Austen's Novels,The Johns Hopkins UP,1971,pp.182-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