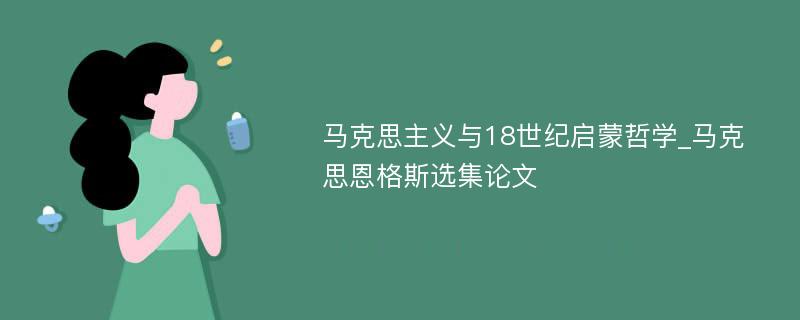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与18世纪的启蒙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各个角度逐渐加深了对它的认识。作为一个严整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孕育于19世纪的西方社会中,它扬弃并且融合了各种相差异和对立的思想成分,这种融合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增添了某种复杂性。我们很容易有时强调某些成分,有时又会偏重另一些内容。到了8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诸如对科学性的批评和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以及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认同等等。这些理解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参考和借鉴。但是,我们还应看到,这种种理解往往只是站在20世纪文化的立场上,只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局部的东西,未能全面地、本质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理解中有许多词汇表面看来似乎相同,但在20世纪和19世纪的不同文化背景中其实是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相信,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因此,要想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将其放在19世纪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工业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思想武器,是在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成长壮大的。对于这个包容了多种成分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进行观察,但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与18世纪启蒙哲学的关系。自然,在字面上,我们也不会忽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批判资产阶级启蒙哲学的抽象的理性和他们的机械唯物主义,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更广的视野,即从欧洲18 世纪到19 世纪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来重新了解这种关系。欧洲从18世纪到19世纪并不仅仅是通常想象的一种连续和发展,而是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差异和断裂,以至这两个世纪在政治、文学、哲学乃至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在这种世纪的过渡之中,马克思主义也表现出复杂的方面,即一方面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某些成分,同时又处处表现出19世纪的风格和对18世纪启蒙哲学的批评。这种批评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而是整个19世纪的潮流,不过马克思主义是站在最高峰。而且,这种批评尽管和20世纪的许多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毕竟是属于不同的时代。
将马克思主义放在与启蒙哲学的关系中去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许多内容,像主体性、历史主义、客观性和辩证法等等。一种理论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正面的论述,而且也体现在与它所否定的对象的关系中,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真正历史的态度。此外,假如我们从当代中国的思潮演变来看,这种回顾也许就尤有意义,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最有影响的也许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启蒙哲学思潮了,不仅是现实的政治,而且在根本的思维方式、对历史和文化的基本态度上,以及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中,都无不深深体现着它们的影响,体现着它们的联系、差异和冲突。
二
18世纪的法国社会表现出复杂的方面,尽管封建专制日益严酷,各种社会矛盾在酝酿积累,但除去一些零星的骚乱,它在总体上是稳定和平静的,工商业飞速发展,科学和文化欣欣向荣。恩格斯指出,“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情况’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04页)经济的发展创造出大量的财富,文明、 优雅和享乐之风笼罩着这个时代,法国的巴黎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文明从这里向世界扩散,这就是18世纪的状况。这个时代尽管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苦难,但在文明的光辉的映照下却似乎隐没不显了。在这个时代中出现了它的精神代表,即启蒙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启蒙运动尽管反对现存的制度,但在本质上是属于18世纪的,体现了18世纪的风格和特点。E.卡西勒说,“18世纪思想的着重点日益从一般转向特殊,从原理转向现象”。(《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它沿着17世纪以来的道路进一步扩展了对于经验和世俗世界的兴趣,它相信理性不再是人和神共有的“永恒理性”的王国,不再是先验的“天赋观念”,而是一种人类的能力和力量。它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去歌颂人类文明的美好的一面,歌颂理性和科学的进步,并将中世纪的基督教作为野蛮和黑暗的东西而抛弃了。“伏尔泰年轻时从不知悲观主义为何物。他拥护纯享乐主义哲学,这种哲学的真谛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享受人生的一切乐趣”。(同上书,第143页)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类似,都带有某种贵族化的特征。启蒙思想家生活在帝王的宫廷和贵族夫人的沙龙里,他们成为欧洲贵族和帝王的导师,充分感受到了文明生活的美好和优雅的一面。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那种种贵族化文明和优雅随着巴士底狱的被攻克而被颠覆了,欧洲从此陷入了战争和动荡之中。在旧的稳定和秩序崩溃以后,那在文明的盛期被压抑和隐没不显的许多狂热和非理性的东西都浮现到了社会生活的表现。在战争和动荡中,权力和财富在急剧地转移。它们给人类带来了焦虑和痛苦,人们不再崇尚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一种浪漫主义的热情和对形而上学与宗教的渴求笼罩了欧洲。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这是一个忧郁多幻想的时代。19世纪的思想家不再简单地歌颂理性、文明和科学的进步,而是正视社会和民众的苦难;19世纪的生活和思想不再是18世纪的贵族式的,在浪漫主义中,我们看到了普通民众的情感,在空想社会主义中,则看到了各种改革社会和救助下层民众的方案。“在18世纪人民是旁观者,到了19世纪他们变成了演员。社会主义在启蒙运动时期是少数个别人的一种文学上的一种乌托邦,如今成了一种世界的因素:起初是一种思想,后来成为一个党派和一种改革,最后成为一种世界观。”(保罗·亨利·朗格:《19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马克思主义即诞生在19世纪的氛围中,当它产生的时候,浪漫主义的热情和黑格尔式的哲学思辨已经衰退,时代的潮流已走向唯物主义和实证科学。在反对普鲁士专制政权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法国唯物主义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19世纪的产物, 它对启蒙运动的继承只限于对现存专制制度的批判,从其根本的思维方式上来说,则和启蒙运动有着根本的区别。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他们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社会。“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市民等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失,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7-408页)
之所以在这里引证恩格斯的这段较长的论述,是因为它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创立时所面临的现实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启蒙运动,或者说19世纪不同于18世纪之处。这不是一幅理性、文明和进步的美好图画,也没有启蒙运动的那种乐观和自信。启蒙思想家把目光放在一切优秀和杰出的人物身上,认为“英雄”的意志决定历史的发展,他们是鄙弃劳动群众的;而马克思主义却把目光放在正在成长的工业无产阶级身上,这并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注定受难的阶级,而是注定了它要在未来的历史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的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社会历史的。它不再像启蒙运动那样仅仅看到表面的辉煌,而是要从表面的辉煌后面看到真实的存在,从笼罩着一个社会的宗教、法律和国家制度等后面转移到那处于下层和基础的物质生活的关系。这些物质生活的关系可能不够高雅和体面,但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和真实的存在,正是这些事实才构成了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实际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19世纪的许多思潮,浪漫主义、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等,也都把目光转向辉煌的文明背后的东西。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19世纪,是因为需要机器去生产大量的面向普通民众的必需品,而在18世纪贵族化的文化氛围中,却只需要那些为有闲阶级服务的奢侈品。18世纪的思想家不关心民众的苦难和现实的恶,而19世纪却不一样了。美国作家梭罗不喜欢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他看到了在那些华丽的寺庙后面,是贫苦阶级的酸辛和苦难,所以他更喜欢让石头放在原来的地方。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贫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三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崇尚理性的同时,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思想家沿着17世纪以来的道路,日益摆脱那些宗教和形而上的成分,并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放在现实和世俗化的、微小和局部的事物上,世界整体的联系被割裂了,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确定、有序和静止的,这和他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是一致的。他们以一种乐观的情调把理性和文明世界作为普遍的标准,以至把一切过去的历史作为黑暗和野蛮的东西而抛弃了。18世纪的思想家无法感受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也无法真正地理解历史。马克思主义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在本质上却决不同于18世纪的思想家。恩格斯说,“了解了以往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2页)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是崭新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的运动变化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之点,历史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与那种盲目的乐观和自信不相容的。19世纪的思想家面临着的是一个动荡不定的世界,他们多少都能在不同的程度上去理解历史。浪漫主义曾经在中世纪的民歌中,恢复了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至于黑格尔的哲学,则贯穿着一种巨大的历史感。而马克思主义,则相信无论自然和社会,都是处于一贯的历史的发展之中,我们经过和面临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同上书,第60、422页)在人类的历史中,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中的一些阶段,每一个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必然的,在当时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在历史的变化中,不存在任何普遍和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暂时和特殊的。
启蒙思想家如吉本等,他们在歌颂文明、理性和科学的同时,把中世纪的基督教看成完全的野蛮和黑暗。但是,恩格斯却和维柯等人一样,相信基督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自然和必要的,“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 页)恩格斯相信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的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基督教是在罗马文明解体时期,作为罗马文明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最早的基督徒来自受难的下层民众。此外,对于日耳曼蛮族的征服,启蒙思想家认为是野蛮毁灭了文明;而在恩格斯看来,促使欧洲返老还童的,正是德意志民族的野蛮状态和氏族制度,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总之,是罗马人所丧失的一切品质,……只有这些品质才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了新的国家,养成了新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52页)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文明不再是单纯地直线进展,而是有上升也有下降。同时,在历史的变化中,文明和野蛮、善和恶也不再是像启蒙运动所理解的外在的对立,而是一切都是辩证地相互依赖和转化,贪欲和权势欲像黑格尔所说的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杠杆。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科学和艺术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同上书,第173页)在文明时代中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对立面, 都必然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同上)但是统治者却以伪善把自己同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以习惯性的伪善来掩藏这种矛盾和对立,“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同上书,第174页)
四
20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往往有一种倾向,即喜欢逐渐排除马克思主义中客观必然性的和本体论的一面,而片面强调其中的主观能动性的成分。诚然,这种理解有着其历史背景,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确实相当强调历史的变化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是,我们还应看到,20世纪的文化与19世纪的文化有着重要的差异,20世纪的一些人所理解的那种主体性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中的那种主体性是相当不同的。20世纪的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意味着一种普遍性和绝对性的解体,时代的潮流日益趋向某种经验主义的、特殊的、偶然和多样的东西。19世纪的思想尽管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和变化,但这种变化中却始终渗透着一种热情、力量和冲动,在特殊性中包含着一种普遍性,一种对形而上的整体的感受与憧憬;19世纪的思想是辩证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40年代,尽管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哲学的思辨已经衰退,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消失,一切毕竟在过渡之中;这个时代之被称为“思想体系的时代”不是偶然的,对体系的兴趣和对普遍性与整体的渴望是一致的,即使像孔德这样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者,也要去发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斯宾塞则更是创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批评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的虚妄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也保留了对辩证方法的运用和对客观必然性或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的尊重。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主观能动性等,和20世纪的有些思想家所理解的是有相当差别的。
在这方面,20世纪的一些思想同18世纪的启蒙精神倒有着较多的共通之处。启蒙思想家在夸大自己的理性的普遍性的同时,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偶然和任意的世界,帝王的某一个怪癖都可能导致世界战争,而且,启蒙思想家也相信意见可以支配世界,世界似乎可以按照人的意愿去安排,他们都很难相信有什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的力量,这和他们的较为乐观的情绪和对个人的尊重是一致的。而马克思主义在谈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却始终强调一种客观的方面,他的主观能动性带有德国文化的特色和影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 页)这里重要的即是那种“客观的活动”。马克思尽管相信人类历史是一个一贯包含着上升和下降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马克思决没有像18世纪的人那样简单和乐观,也不像20世纪的一些人那样走向虚无。马克思心目中的历史并不是偶然和任意的,在历史中始终存在着必然的成分,这就是物质生活的关系,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启蒙运动过分强调了人的理性的能力,而忽视了潜藏在联系背后的,或者说是超出理性范围而决定理性的东西。因此,尽管他们提倡理性和启蒙,最后却导致法国大革命及以后的社会动乱,历史往往并不理睬人们的善良愿望。恩格斯说:“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却“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而且,马克思主义尽管强调人的解放,但他所说的人是被包含在阶级和社会的整体的运动中的人,而不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或现代一些思想家的意义上的人。“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
无论怎样,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关系虽然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方面,但也仅仅是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毕竟也继承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当我们从某一个角度去进行观察的时候,可以将某些方面凸现出来,但它永远不等于真正和完整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毕竟是19世纪特定时代的产物,后代的人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进行理解,但在内容上不可能完全一样了,历史和空间的距离必然会带来理解上的差异。更何况,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受难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而当代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带有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情调,他们当然不会也不可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完整地理解。不过,从另一角度说,或者在真正的历史的意义上,片面的理解也许其本身就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们正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表现和内容。
五
对于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来说,西方文化中对它们影响最大的也许就是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了。不仅是中国,在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也往往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一些人那里,马克思主义正是作为对启蒙运动的对立和补充而出现的。在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80年代的文化热,对启蒙的憧憬始终激动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这不仅表现在现实的政治中,也表现在对东西方历史、哲学、文化的理解以及诸多人文社会学科中,不仅西化派是如此,许多新儒家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承认启蒙的重要。启蒙的理想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也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沾染上了18世纪启蒙哲学特有的局限性。在西方,自从浪漫主义产生以后,浅薄的启蒙运动一直是一个流行的口号。在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越来越对五四时期及80年代文化热中所表现的许多表面和浮躁的东西有了更多的认识。许多人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一样,对科学、文明、进步和人类的历史作了过分表面和乐观的理解,他们往往只看到文明的辉煌的表面,而对文明的变迁中那相反和辩证的方面,对辉煌的后面所隐藏的黑暗缺少足够的认识,这样,他们也就不能以真正冷静的态度去正视文化的内在的生命。在对西方历史的理解中,他们将西方文化简单的看成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进步的历史,而对这个过程后面的基督教的背景和非理性的力量却作为野蛮和落后的东西而忽略了。在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中,他们或者对传统作了片面的否定,就像伏尔泰嘲笑中世纪的教会那样,或者是从历史中找到某些成分并按照启蒙的模式去加以赞美,例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这样,他们也就和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一样无法真正地理解历史。到了80年代以后,许多人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上,尤其喜欢强调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中启蒙的成分,至于他们对启蒙的批评却视而不见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许多人之所以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反异化、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的成分,除了受到西方某些流派的影响外,在某些名词的背后,不能忘怀的仍然是那种启蒙的情结。
每一种社会思潮都是特定的历史的产物,当18世纪的启蒙哲学走到它的顶点时,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了,我们应当在这个角度上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出现的重大意义。当然,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又远远超出了19世纪,它作为严整的科学体系,对人类历史又具有深远的普遍的意义。然而在当代中国,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启蒙精神的根本差别仍有现实意义。80年代的一些人,往往站在启蒙的立场上,宣称要重新发扬五四运动后被中断的启蒙精神。实际上,假如他们能稍稍正视一下当时的下层民众所受到的苦难,就会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20年代以后的中国迅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的现实政治,也为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打开了新的视野,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不过,在这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内在精神也被一些人在僵化的词句中表面化和教条化了,这也许就如恩格斯所说,“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个个别场合和每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不管怎样,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哲学的关系仍然是相当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尽管继承了一些启蒙的原则,但更多的是对它的扬弃。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辩证的理解,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对历史和客观规律的尊重,都足以对我们在许多学科和领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盲目的乐观和热情提供某种思考和借鉴,对于重新振兴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标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法国启蒙运动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科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