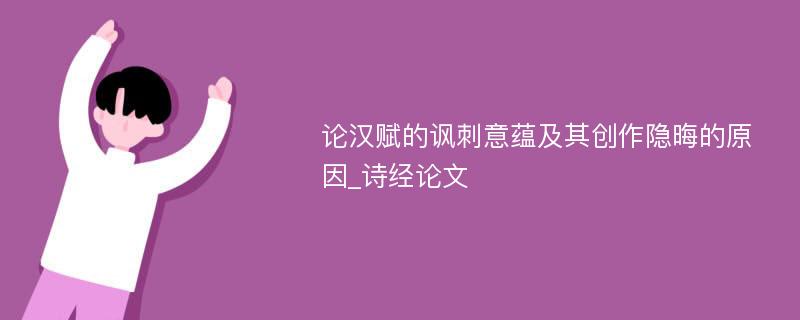
试论汉赋的讽谕意图及其在创作中隐没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意图论文,试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汉赋原是以“古诗之流”的身份出现的,作为《诗经》“美刺”精神的继承者,它不仅有“颂美”的功能,还兼具着“讽谕”的意图,但由于汉赋采用“谲谏”的方式,通过“推而隆之”,由极见反的归谬法来讽谕,造成了讽谕意图的隐晦;更由于汉赋创作中必然的“尚美”倾向的冲击,其讽谕的意图进一步消隐下去,而只表现出“逞辞”、“媚谀”的面貌来。
关键词:讽谕 美刺 谲谏 推而隆之 尚美 隐没
一、汉赋本具“美刺”的双重使命,讽谕是其题旨应具之因素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卓荦独立于两汉的无疑是汉赋,钟嵘所谓“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正说明了汉赋的独盛。但汉初的赋作不过是承屈宋骚体之余绪,直到枚乘、司马相如的出来,真正意义上的汉赋——大赋才产生。对这些宏章丽辞的篇什,班固在《两都赋序》谓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指明了它们既可“通讽谕”,又能“宣上德”,从而具有“讽谕”和“颂美”两方面的功能。但后人,尤其是近世以来的学者,多只看到汉赋“颂美”的一面,以为它是奉命的文学,是以谀媚颂德为目的的。其实,汉赋自产生之时便具有“美”与“刺”的双重使命,“讽谕”是其题旨应具之因素。
首先,汉代的文学思想决定了汉赋应有“讽谕”的意图。汉继秦火燔书之后,其文化的重建是建立在对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的经典的整理、阐释的基础之上的。其中又尤以《诗经》最为重要,汉儒在对其不断的研究、阐述中逐渐形成了“诗教”理论,它至《毛诗序》而臻于成熟。“诗教”理论的核心在《毛诗序》中鲜明地表露出来:“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在此实指感家国兴衰而生之心绪),“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强调的是诗歌的功利教化作用,这把先秦以来重视文学的政教功用的主张推到了极致,以至于“汉儒言诗,不外美刺两端”(程廷祚《青溪集·论诗十三·再论刺诗》),说诗无往而不关教化。不仅如此,是否具有“美刺”功能,还成为汉儒评价《诗经》以外一切典籍和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汉赋也正成形于儒术独尊,“美刺”思想主宰文学之时,它以“古诗之流”自任(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文心雕龙·诠赋》:“赋自诗出”),固然有其攀附正统之意,而也表明了要承传《诗经》“美刺”精神的雄心。而“美刺”为何?《毛诗序》释“风”、“颂”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明白地说,刺是“下以风刺上”即“讽谕”,“美”是“美盛德之形容”之美,即“颂美”。
而汉赋家们也是自觉地以“讽谕”为目的来进行创作的。如扬雄“奏《甘泉赋》以风”(《甘泉赋序》),“上《河东赋》以劝”(《河东赋》),“聊因校猎赋以风”(《羽猎赋序》);班固《两都赋序》指出汉赋创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目的,其作《两都赋》是为了“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令之法度”,表白自己对迁都的看法及守法度戒侈靡的政治见解;王褒在《洞箫赋》中述乐声之化人而赞其“感阴阳之龢,而化风俗之伦”……这些都明显地表述了作赋目的。而又有一些汉赋,虽未明说是为了讽谕,但一些史乘记载点明了它们的讽谕意图。如司马相如的三篇骚赋,据《史记》、《汉书》的本传,《哀二世赋》是从武帝过宜春宫时所献,赋中哀叹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是对武帝的很好鉴戒;《大人赋》是他针对武帝的好神仙而进献的,扬雄说“往时武帝的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自序传》),指出了他的讽谕的意图。由骚赋的创作也可反证相如大赋创作的严肃性,司马迁说:“《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有其原因的。再如《后汉书·傅毅传》载:“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如所言确实的话,则许多类似题材的赋作中,或许有的也隐藏着讽谕的意图。
汉赋的讽谕意图在赋作的格式中也可见出一端。《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扬雄语曰:“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其对赋的评价虽刻薄,却真实地勾勒出汉赋的格式来:先是极力铺陈夸饰,百般赞扬,是为“劝百”,最后再指出前面做法的弊处,进行讽谏,这是“讽一”,便是“曲终”所奏之“雅”,而正是它向我们昭示了汉赋的讽谕意图。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末尾假托天子之口说:“此大奢侈”,而以“解酒罢猎”、垦地为田,发仓救穷诸种施指改正侈靡之习,达到了“天下大悦,向风而听,随流而化,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的境界,这是从正面写戒奢侈、行德政的理想境地以召引欲德化尧舜的帝王;赋作还从反面写“终日驰骋”、“务在独乐”的劳民伤财,民遭尤而离心的危害——“非所以继嗣创业垂统”——对帝王进行告诫。观其意旨,与孟子见梁惠王而倡“仁政”几无二致,相如讽谕之心可见矣!
再者,汉人(包括赋家)对赋的评论中也可看出汉赋确存讽谕的作用。《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具要归引之节俭,此于诗之风谏何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指出汉赋有“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两方面的功能,在《汉书·叙传》中又称相如赋“寓言淫丽,托风终始”;扬雄认为“赋者,将以风之”(《自序传》)而发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崔骃也说:“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于劝也”(《七依》),蔡邕虽否定赋作,也称“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从以上引述可知汉人是把“讽谕”作为衡量汉赋价值的一个标准的,即使是持否定的态度,也不得不承认汉赋虽“劝百”,而毕竟有“讽一”的作用。
二、汉赋讽谕之旨隐而不显之原因分析
汉赋既然有着显明的讽谕的意图,讽谕又何以在作品中隐而不显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汉赋的讽谕意图是源于《诗经》的“美刺”,但时代决定了它不同于《诗经》的“刺”,而只能采用“谲谏”的方式。《诗》三百篇,特别是风诗,是采集而得,在这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民众的情感真实地流露出来而不加掩饰,“美”诗不必说,就是“刺”也是直捷了当,无所顾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言《诗》“刺”者多端:“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词以讽者,亦有全篇皆美而实刺者”,但由于诗篇情感洋溢,且作者少顾虑,虽是“微词以讽”和“全篇皆美而实刺”的诗篇,也可轻易见到其揶揄和讥刺,更不用说那占绝大多数的“直言以刺”的篇什了,象“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邶风·雄雉》)、“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小雅·巧言》)于句中直刺,而《魏风·硕鼠》、《小雅·节南山》则是整篇的鞭挞了,都是直指人心。总之,《诗经》的“美刺”单纯得很,直率得很,美则美之,刺即刺之,绝不闪烁其词。而汉赋就不同了,这些作品多为应诏之作,或是赋家为某种目的而进献于君王的。在那王权进一步强化,动辄得咎的专制气氛中,赋家们定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唯恐忤触帝王。就连以教化为己任的儒士们也不提倡切谏了,《毛诗序》释“风”,主张“主文而谲谏”便是因其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妙处。而什么是“谲谏”呢?《说文解字》释“谲”曰:“谲,权诈也。益梁曰:谬欺天下曰谲”,则“谲谏”显然有别于“直刺”,它要把自己讽谕的意图隐藏起来,用欺人耳目的方法从别的方面着手引人入彀而达到讽谕的目的。至郑玄也是如此,其释“赋”、“比”、“兴”曰:“赋之曰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此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春官·大师注》),虽也看到了直陈善恶的“赋”法,但他又说:“诗者,弦歌讽谕之声……及其制礼,尊君卑臣……于是箴谏者希……于是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毛诗正义·诗谱序正义》引),认为诗的讽谕不同于有书契之后的“目谏”(即面刺直谏)的,它要注意到君臣的尊卑。这样在讽谕的手法上他必定更重婉转的“比兴”。王符论诗赋应“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潜夫论·务本》),也强调的是表达方式的委婉。在汉儒诗教理论的指导之下,汉赋的创作也相应地要注意措辞的委曲,力求把讽谏的意图隐藏得深一些,做到“谲谏”。
为了达到“谲谏”的目的,汉赋采用了“连类相及,推而隆之”的手段,赋家先并不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欲抑先扬,而是把帝王所好的事物集中在一起,加以夸饰,张扬,极赞颂之能事,顺着帝王的喜好方向和思维逻辑往前推衍,直到“隆盛极点”而显示出其荒谬的一面来。因物极必反,事物美善到极致,又自然地让人想到为之而要付出的代价,最后,作者再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点明自己的讽谕意图,可谓水到渠成。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依次写了上林的方圆,其中的川泽、水产、山峦、草木,各方之异兽,苑中的宫馆,四季的美果芳草,树上的异鸟珍禽,还有天子校猎的仪仗、场面和收获,校猎之后的宴乐,在铺述中力求巨细靡集,描摩入微,文章通过铺陈、排比和夸张,竭力要渲染出各种场景的壮丽迷人,以显示帝国的声威和天子的气派,明处看是用“美”的手法颂扬帝王和帝国,天子自然乐于披览,但隐藏在铺陈颂美后面的是苑囿大则民不得耕,宫馆丽而财费必多,校猎壮则士卒必劳,宴游独乐而民心也失,最后作者再点明它,以达到讽谏的目的也就自然而然了。再如班固的《两都赋》“极众人之所眩耀,”将西都形胜的壮观、宫室的华靡写得无以复加;而于东都却重于写光武帝对西都制度的纠正,明帝时的典章制度,至于田猎、宫室也无不从合于制度入手;写田猎是“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写宫室则强调“奢不可逾,俭不能侈”。此乃“今之法度”也,相形之下,西都虽壮丽、华美却不合法度,这样作者提倡节俭,守法度,反对迁都的讽谕意图也就达到了。由此可见赋作讽谕意图的幽深隐晦。
从以上的阐述中,我们还可以说那种认为汉赋“劝百讽一”,其讽谕只是画蛇添足的看法是不当的。显然赋中“劝百”是为“讽一”作准备,“讽一”才是文章题旨所在。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赋作“劝百”与“讽一”的严重失衡,多少又使得汉赋讽谕意图在赋作中显得微小和无足轻重。
三、汉赋“尚美”倾向的必然性直接冲击了汉赋讽谕的功能
从教化功能评价,汉赋“不免于劝”,其背离讽谕意图的原因,除了它采用“推而隆之”的“谲谏”方式,使其讽谕意图隐晦难明外,还由于受到了汉赋“尚美”倾向的直接冲击。“美”与“刺”在诗教理论原本是“颂美”、“讽谕”两方面的统一,但由于汉儒过分强调诗的功利作用,更由于诗教理论初创的汉初,承秦之敝,需从多方面革除弊端,使得诗教理论从一开始就更侧重于对“讽谕”的鼓吹。如前面所引司马迁论相如赋“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于诗之风谏何异”,《汉书·艺文志》称枚、马之徒“竞为侈丽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及扬雄说赋“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其中的“风”(讽)都指的是箴谏的“刺”的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赋忽略,摒弃“美”,恰恰相反,因文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汉赋大大发展了《诗经》的“美”,使之由“美盛德之形容”的仅仅对德行的颂美(《诗》中也不乏对容貌的描写,但仍是为了衬出人物的德行的,否则,貌美而无德就成了“刺”了,如《鄘风·君子偕老》)而发展到讴歌功业,赞美河山,追求辞藻华美,追求文气丰沛,赞美新鲜事物诸方面,形成了“尚美”的倾向。统言之,“尚美”包括对“大”,对“丽”的两方面的追求。“大”是立意大体制大,要“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语);“丽”是辞采的华美,描摹的精微,是“丽词雅义”(《文心雕龙·诠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精心组织。以下多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汉赋“尚美”倾向的必然性。
(一)文学的发展总是由简而趋繁,由质朴无华而到注重绘饰的。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意味着自那时起优美的文辞就成了文士的自觉追求,至战国便出现了许多富有辞采的著作来,如《庄子》。楚辞,汉赋承其风绪,追求辞采的华美也是自然的。
(二)汉赋家与纵横家的渊源,也使汉赋必重辞采。纵横家对赋家的影响,前人已经清楚地阐述了,从汉初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赋家的身上尚可发现纵横家的影子。纵横家的特点诚如章学诚所论,“欲文言以达旨”,“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文史通义·诗教上》),其“文言以达旨”,“揣摩”而“腾说”的行文方式正与汉赋“主文而谲谏”的讽谕方式相契合,受其恢奇敷张的文风的影响,汉赋也追求铺陈、夸饰,以期气势雄张而打动人主。
(三)帝王喜好汉赋辞采的审美娱乐作用,影响所及遂成风气。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爱促进了汉赋的繁荣。但帝王好赋的原因是什么呢?《史记·司马相如传》载“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观《子虚赋》并无讽谏之辞,则武帝所好的大概是相如所赋诸侯之事“足以观”;再看“上既美《上林》之事,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因上《大人赋》欲以讽,而帝“飘飘有凌云气”,足见武帝所好乃赋作之靡丽。而宣帝的观点就更加明白了,《汉书·王褒传》载其论赋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虽也强调赋的讽谕作用。但并不掩饰他好辞赋的“辩丽可喜”,将之视为“贤于倡优博奕”的娱乐手段。上之所好,下之所趋,又兼以相如诸人以文“侈丽闳衍”见召,扬雄因“文似相如”被荐等实例的刺激,更将煽扬汉赋的靡丽之风。
(四)汉帝国为巩固统治的一系列措施,也利于汉赋“尚美”倾向的发展。汉统治者自建国之初就着力于消除不利其统治的内忧外患,至武帝文功武治,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人们的意识形态趋于一致;政治上,武力与“推恩”兼施,消除了藩王的威胁,安抚各方的少数民族,使帝国空前的统一;军事上,击匈奴,平朝鲜,定南越,使得大汉的疆域空前广大。国家的统一,政治的清宁,军威的显赫,疆域的广大,及丰饶的物产,绮丽的山河,不仅给了汉人安逸生活和新鲜的眼界,更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自豪及对新奇世界的神往。对现实的肯定,使汉赋家乐于形之于笔端,而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系列文化措施,正迎合、促进了这种要求,赋家们腾踊笔墨,讴歌帝国的声威与壮美,展想新奇的世界,以“美文”赞“美世”,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时代的需要。
(五)汉帝国的雄强富庶则为汉赋的“尚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史记·平准书》的记载充分反映了汉武之世的富足:仓廪皆满,库余财货,钱取之不尽,粟食之不竭。但物质的极大丰富,及汉人对未来的充满自信,又势必造成享乐主义的盛行。《三辅黄图》称汉的宫殿“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青琐丹墀,左磩右平,黄金为璧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然也”,又记商人“衣必文采,食以粱肉,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可见西汉社会自上而下的奢侈;东汉也是如此,张衡作《二京赋》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后汉书·张衡传》)。侈靡的世风自然要影响到汉赋上:丰富颖奇的物产,精彩纷呈的娱乐方式,穷奢极欲的欢娱场面,都为汉赋提供了充实的内容,而对更靡丽美好的事物和生活方式的向往,又为汉赋的联想、夸饰准备了宽裕的空间。刘永济先生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论汉赋风格时说:“于时天下殷实,人物丰阜,中于人心,自然闳肆而侈丽”,正说明了富庶的物质生活导致了汉赋的“尚美”倾向。
(六)汉赋体式的模式化和讽谕内容的单一,也使得赋家向“尚美”方向倾斜。由于汉赋的发展到司马相如而成熟,后来赋家的创作多为对相如赋的模拟,就形成了汉赋作品采用人物问答,先“劝百”后“讽一”的模式;又因为汉赋作品进献的对象是君王,作家多是一些脱离社会实践的宫廷文人,它的讽谕内容就总是集中在“戒奢侈,倡节俭”上,脱不出儒家老生常谈的论调,这客观上就迫使赋家把创作精力转到文辞及所写对象的“闳衍巨丽”上。这方面扬雄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创作都明白地说明了讽谕的意图,也自称“少好相如之赋”,并常“拟以为式”的,从他的《甘泉赋》看,与相如赋的格式及讽谕内容并无大异,想来不至太费神。但桓谭《新论》载:子云亦言,成帝时……与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足见其于文辞上费心之苦。
总之,汉赋的“尚美”倾向具有必然性。而“尚美”在创作中不外是追求文辞和所写内容两方面的壮美、华丽。但矛盾出来了,从讽谕的意图来看,对事物、场景的极力夸饰铺陈是要突出其奢靡,为讽谕作好铺垫,这就要求作家对所描绘的持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但汉赋正产生、定型于汉帝国最盛隆之时,其铺陈的一切正反映汉赋家们的心态,即对帝王功绩的赞美,对帝国声威和富庶的自豪和对新奇世界和美好未来的神往。这是一种对现实认同、赞赏的态度,而这必然地决定了讽谕意图的软弱无力:自己都赞同的又如 何能劝服别人反对它呢?同时在铺陈之中,赋家们为追求文辞之美,极尽想象、夸饰和堆砌之能,务求无所不集,无所不丽,为之殚精竭虑。然而“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文心雕心·夸饰》)过分追求辞藻美客观上将冲淡汉赋讽谕的意图。又因为汉赋作品讽谕的方式和内容的单一化,评价赋作优劣与否的标准便主要依靠作品是否“恢廓”、“靡丽”,这又促使赋家有意识向“尚美”的方向发展,而忽视汉赋的讽谕意图,使讽谕意图成为作品的点缀,汉赋便进一步表现出“逞辞”的面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