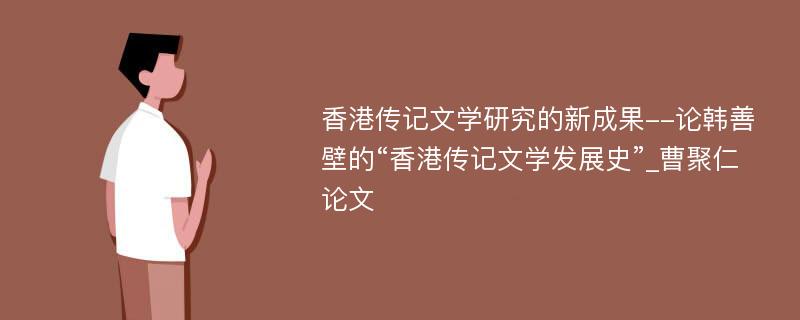
香港传记文学研究的新创获——评寒山碧《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寒山论文,传记论文,文学论文,发展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06)02—0007—06
当代香港传记文学是在商潮迭涌中开绽出的一朵奇葩。50多年来,香港的传记作家们以自身不懈的努力,在大众文化中求生存,谋发展,为中华传记文学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这是有目共睹的。遗憾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香港的传记文学却“被文学史家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成了花果飘零的一个弃儿。”[1](P415) 坊间出版的多部香港文学史,如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潘亚暾、汪义生的《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1997)、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和施建伟主编的《香港文学简史》(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等,都没有探讨传记文学的有关章节。这些著作大同小异,无外乎是谈香港的小说、通俗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和文学批评等,“鲜有人把传记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究其原因,“这可能是因为不少传记文学政治性太强,故分类时常把它当作政治读物。又由于这些传记非常敏感,一些研究者只好绕开走。”[2](P557) 令人欣喜的是,寒山碧先生继主编厚近600页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特色及其影响》(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0年11月初版,繁体竖排本)之后,又推出厚达760 余页的皇皇大著《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1月初版,繁体竖排本)。可以说, 这部《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有力地矫正了先前所有《香港文学史》(含《概观》)忽视传记文学的弊病,填补了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一大空白。它的出现,标志着香港传记文学学科的不断成熟,不仅是对中国传记文学学科的普及,更是对香港传记文学这门学科的总结与提高。
寒山碧先生是资深香港传记作家和著名学者,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会长。他本名韩文甫,海南文昌人,1938年底生于一个华侨家庭,1962年秋毕业于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68年10月移居香港。在香港30余年他笔耕不辍,一直致力于文化传播和20世纪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传记写作,并不遗余力地推动香港传记文学前进的步伐。他先后写过《邓小平评传》(共四卷,1984—1993年)、《毛泽东评传》(1987年)、《蒋经国评传》(1988年)和《中共四大家族》(1996年)等,其价值“明显是通过具体真实的历史细节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与反思,对中国现在与未来道路的殷切思考与关注。”[3] 1999年,在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下,寒山碧创办《文学与传记》杂志,邀请两岸三地的传记文学作家、学者,出席他主持召开的“香港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香港传记文学发展特色及其影响》。
《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系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之研究计划项目。因限期完成,寒山碧先生“经八百个日日夜夜,奋笔疾书”,[4](P3) 终成此书。这部40余万字的新著,凝聚着著者多年来的心血结晶。它从追踪香港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中,描摹了香港传记文学的斑斓景观,展示了香港传记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让我们管窥到香港传记文学的流变走向,可谓创获良多,功德无量。
创获之一:视野开阔,纵横交贯,资料翔实全面。
在我看来,写“传记文学发展史”,首先应该有扎实的资料考索和个案研究的经验,然后才能有统摄全体而写史的条件。因为只有弄清传记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产生与发展、嬗变与演进、曲折与停滞、精致与辉煌等,这才能真正进入“发展史”的写作。1999年,当我读到陈兰村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时,便不禁为该著扎实的资料考索、精彩的个案研究以及对中国大陆传记文学发展规律的辛勤探索而叫好。如今又读到寒山碧先生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更让人坚定了对“发展史”写作的这一看法。《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论及的传记作家作品,其时限始于1949年10月1日,截止于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之后发表和出版的传记,作者说留待将来的研究者去撰写《香港特区传记文学发展史》了。关于作家作品的取舍标准,著者在《后记》中说:“本书非以作者国籍为取舍标准,而是以传记出生(初版)地为取舍标准,作者只要是华人,其著作中文初版在香港印行或发表,我们皆视之为香港传记文学。侨居各地之作者,所持护照虽然不同,但其文化传承则一,其所关心之事物也一样,他们的中华心是相同的。”[4](P735)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种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视野,使“香港”这一特色更为鲜明。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华洋杂处、中西交汇的地区。无论地理上或政治、文化上,香港都是一个边缘之地,对不同体制和意识形态,既始终有一种潜意识的关注,却又有拒绝宰制的自由,因而在交相纠缠、迎迎拒拒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景观。事实上,香港是沟通海峡两岸文学的桥梁和纽带。诚如著者所言的那样:“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不能流通之书籍资料,香港可以自由查阅;海峡两岸不能撰写之现当代人物,香港可以自由臧否;海峡两岸不能发表和出版之文章,香港可以自由披露,是以造就了香港传记文学之辉煌。”[4](P2) 这种说法,无疑表明了寒山碧传记文学史学批评的文化视野与艺术眼光。
为取得丰硕成果的香港传记文学写史,著者构架研究体系时言明:“无论传记、自传、回忆录,本书皆以政治人物为主,文化人物次之,其他人物又次之。”[4](P735) 并采用了全新的纵横交贯、紧密结合的方式。全书正文除导言外,还有十六章,另有附录一、二。在“导言——自由孕育和造就了香港传记文学的辉煌”中,著者从纵向总述了香港传记文学的“辉煌”成就,高屋建瓴地对香港传记文学的兴起、发展与演变、特色及影响作出了相当科学的、学理色彩相当强的说明。在第一节里,他从“文史不分是中国的传统”,说到《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并进而说到西方的史特拉齐、卢德威克、莫洛亚、罗曼·罗兰等传记大家,以阐发传记的文学价值。第二节谈“五十年代香港传记文学兴起的机缘”,第三节谈“六十年代人文杂志与传记文学的兴起”,第四节谈“七十年代香港传记文学大丰收”,第五节谈“八十年代寒山碧的政治人物传记”,第六节谈“九十年代政治人物传记”,第七节谈“作家、学者传记的研究与评介”,第八节谈“富豪传记的兴起与演变”,第九节谈“香港传记文学的特色及影响”。作者的创新之处在于,从文化学的大视野,考察了传记文学与民族文化、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大众传媒和受众群体等诸因素的联系,使读者清晰、明确地了解和掌握极富中国传统和香港特色的“香港传记文学”的发展脉络,给人以系统感和整体感。“导言”之后的16章,依次为“回忆录百花齐放的五十年代”,“曹聚仁和他的传记文学”,“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六十年代张国焘、萧瑜、李璜三部回忆录”,“六十年代‘文革’资料的搜集与政坛人物的研究”,“军人传记及回忆录”,“六十年代的回忆录与传记”,“七十年代政治领袖传记大丰收”,“七十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研究”,“香港富豪传记的发展与演变”,“寒山碧《邓小平评传》及其他著作的价值与影响”,“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研究”,“港台作家传记研究”,“八十年代的政治人物传记”,“九十年代的政治人物传记”,“九十年代香港共产党人的回忆录”等。从大的“章”来看多是纵向的,但从“章”下的每一“节”来看又多为横向,史著始终注重在香港传记文学的总体背景下,探讨文学思潮、不同类型的作家(作者)创作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期的分流与整合,演化与变异,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香港传记文学历史图像。
寒山碧十分熟悉香港传记文学。他自196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当代史,又长期担任编辑出版工作,创作过大量人物传记,并与香港作家学者多有联系,因而由他写作这第一部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真是适得其人。作者在对大量零散的文献史料进行细密剖析和详尽占有的基础上,于卷帙浩繁的传记作品中披沙拣金,做深入研究,使人感到全书所论大多言之成理,落墨有据,这从书中各章之后的总共约 700条规范而详尽的注释中便可见其一斑。著者对传记作家(作者)的介绍,资料翔实全面,举凡籍贯、出生日期、学历履历、创作经历等等,多有较详细的说明;面对少数作者资料不详,著者也加以解释,不妄加猜测。对传记作品的内容及版本有关问题,也多娓娓道来,如开本多少、页码多少、篇幅长短、章节内容、前后书名、出版经过等等。这样一来,论从史出,一切分析、判断与结论都来源于较扎实可靠的史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在扎实可信的史料叙述的基础上,还精心配置了两百余幅作家照片和书影(从封面、封底至内文),这不仅为正文提供了视觉上的参照对象,使文字与图像相互补充,相互生发,而且还诱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调剂了阅读的节奏,让人有目不暇接、爱不释手之感。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使用如此大量有些甚至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当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创获之二:直率犀利,评价具体,力求客观公允。
古人写史,讲究史德、史识、史才,著者对此亦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一部文学史的真正价值,就看这位史家所保持的公正程度,一手固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的。”[4](P128) 著者在书中引用曹聚仁的这段话,其用意在于勉励自己,在撰写《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时,坚持说真话,下笔“力求公允”。[4](P3;P736) 通读全书,我以为寒先生正是秉承曹聚仁的精神写史,他对在书里提到的传记名家,包括曹聚仁、司马长风、丁望、余思牧、刘以鬯、郑义(胡志伟)、李立明、冷夏等,无论是前辈、师长、同辈友侪或晚辈后进,都大加臧否,绝不畏缩;凡提到的文章、著作,他必定评点一番,好则说好,糟则说糟,无所顾忌,表现出一种独立的品格。如他论及李立明的《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时,细数成绩:一是“数量大,人数多”,二是“作者基本上是站在中立的知识分子立场,考虑某作家是否人选时,排除党派之见,纯从其知名度和文学成就出发”,三是“依姓氏笔画而编,方便查阅”;同时又指出它某些地方有“很大的随意性”、“取舍标准相当混乱”和存在“史料错误”等缺失。再如1996年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作家传略》,这是香港自开埠154年以来,内容最完备、资料最详尽的香港作家传记集。著者将其与同类著作相比,认为它有三大特色和优点,即“资料翔实准确”,“资料相对齐全”,“内容丰富”,但同时又指出该书存在的不足之处,认为“此书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统一的取舍标准”,显露出一位传记文学批评家不偏不倚的方略。又如对大陆读者十分熟悉的冷夏、夏萍二人的富豪传记,作者辟出两个专节来写。一节为“冷夏的富豪传记吹捧成风”,真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寒山碧认为,冷夏的《何鸿燊传》“吹捧太甚”,《金庸传》“避重就轻”,而《包玉刚传》则“平实可取”;一节为“夏萍的《李嘉诚传》和《曾宪梓传》”,著者认为《李嘉诚传》“书中的资料全部是由传主提供的,书中的话,也全是传主想说的话。作者只是有闻必录,最多是加上自己一些感性的赞叹之辞”;《曾宪梓传》为尊者讳,明显存在着“回避传主的过失”的毛病,而“‘隐恶扬善’正是富豪传记的共同特点”。这种观点鲜明、议论直率犀利的特点,充分展示了香港学者的学识素养和写作风格。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写作于1950年代的香港,被学界视为香港传记文学在五十年代最重要的收获,其影响遍及两岸三地。在国内外数十种关于鲁迅的传记、评传中,曹著的《评传》是最具个性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作者说,他写鲁迅既不仰望,也不俯视,而把鲁迅视作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的人。曹氏通过对鲁迅心路历程、文艺观、思想政治观的述评,剖析他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鲁迅。寒山碧对曹聚仁情有所钟,不仅在“导言”里扼要介绍了曹氏的《鲁迅评传》,而且用专章长达40页的篇幅论述“曹聚仁和他的传记文学”。这一章共两节,一节为“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一节为“曹聚仁的回忆与自传”。寒山碧论及《鲁迅评传》,条分缕析,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方面一一细数其特色:“定位正确,立志颇高”,“准备充足,材料丰富”,“勾勒神貌甚似”,“了解鲁迅颇深”,“探索鲁迅的精神世界”,“持论较公允”,最后还集中探讨了“《鲁迅评传》的成就与价值”,知人论文,深中肯綮,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针对古远清先生的一种说法,著者也直截了当加以批评。书中写道:“古远清说‘曹聚仁的鲁迅研究尽管有谬托知己的失误或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的研究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处‘谬托知己’?何处‘不尽如人意’?古远清语焉不详,实际只是为了寻找缺点而强说‘失误’,是不足以取信的。”类似这种商榷体现出的直率与较真,亦是一种史家精神的体现。
我很高兴地读到史著第十一章“寒山碧《邓小平评传》及其他著作的价值与影响”。著者将自己独列专章,剑走偏锋,卓尔不群,显示出独树一帜的学术探索勇气,体现了分析评述时的一种价值判断,即以在香港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评价作家和传记作品,而当仁不让,这是以往文学史绝不敢做的。这难道不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心理现象吗?它体现了著者的一种豁达、自信、坦诚、大胆。这与国人一向推崇的谦让的传统风格全然不同。俗话说,孩子总是自己的好,有时也的的确确是真的好,但又有几人能不避嫌(唯恐为人诟病),敢对自己的作品叫好或说三道四呢?但寒先生不一样,他襟怀坦荡,让人敬佩。2005年12月,笔者由墨尔本考察回国,有缘在香港与寒先生见过一面,此前此后E-mail往来不断,深感先生快人快语,为人极其率真坦诚。事实上,曹聚仁、司马长风、丁望、寒山碧、郑义(胡志伟)等作家,都堪称香港传记文学的大家,正是他们杰出的作品,构成了香港传记文学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铸就了香港传记文学的辉煌。
像寒山碧历经15个春秋完成的四卷《邓小平评传》,便在海峡两岸和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全传约100万字,启笔于1970年代末,完成于1990年代初, 备受学界好评。“《邓小平评传》无疑地成为世界瞩目的畅销书。”[5](P114) 寒著《邓小平评传》销量庞大(含日文译本),盗版本更多,对于这样一部给自己带来巨大国际影响的传记作品,寒山碧除在书中详述他写作与修改《邓传》的经过,并在此基础上用专节谈了“寒著《邓传》的特色”,其写作的特点表现为:“规模宏大”,“去伪求真,史料丰富精确”,“自由意志,秉笔直书”;还用专节谈了“寒著《邓传》的写作手法”,即“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议论和评判是点睛之笔”,以及“作家学者对寒著《邓传》的总体评价”等。须知这些评价并非著者王婆卖瓜,而是选自中英文各种评论寒著《邓传》的文献资料,凿凿有据,这有中国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学者以及美、英、澳、日汉学学者的评论为证。此外,著者也不讳言来自学界的“不同意见与批评”,对学界提出的一些不足之处,他也一一录下,立此存照。实际上,由于《邓传》每一次印刷都作一些修改,所以有些批评刊出之前或刊出不久,作者已经作了补充或纠正。对于寒山碧其他传记著作,像《毛泽东评传》、《蒋经国评传》、《毛泽东情史》、《中共四大家族》等,著者坦言,“这几本都远比《邓小平评传》逊色,无论资料的搜集,人物形象的勾勒,述事与分析都比不上《邓传》。究其原因,是因为不如写《邓传》那样用心,也就难免露出粗糙的痕迹。”[4](P508) 这“几本传记都只属一般水平,参考价值和影响力是有一定局限的。”[4](P515) 我们认为,著者的这种自我评价是客观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创获之三: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富有理论创新。
广东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张振金教授在评论《邓小平评传》时曾说:“韩先生在香港这个中西交汇、多元并存的文化环境中,对于中西文化有所坚守,有所吸纳,有所融合,有所弃除,使自己的‘史德’和‘史识’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的传记文学内容扎实,涵容深广,有史诗的大气慨与魄力,文笔舒卷自如,简洁明快,人物性格鲜明,见解独具,让人从中了解历史,又受到文学的感染。”[6](P109) 我以为将这段话移用作为对《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评价,也是十分恰当的。
这是一部充分显示了著者个人学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史著。著者充分论述各种类型的传记文学产生的复杂因素,不仅对地域、自然、人文诸环境因素作了观照,而且对整个大中华包括海峡两岸传记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呼应,以此考辨源流,寻绎承传,揭示和彰显出了香港传记文学的发展规律(如对香港富豪传记的发展与演变的论述便尤见功力)。全书不仅语言富丽,叙述生动,富于感染力,书中的议论也每带有激情,或冷峻或幽默,可以说史家的理性与诗家的感性在书中是共存的。书中有许多具有历史深度的分析,对有些作品的解读亦很有历史感,如分析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的写作背景、价值意义时说:“曹聚仁早在三十年代就搜集资料,就准备为鲁迅写传,延宕至五十年代初来港定居后才动笔,除了因为抗战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台海两岸都未具备可以为历史人物自由写传的环境。香港虽然十分细小,文化气氛也不浓,但却能兼容并蓄,拥有充分的自由。以曹聚仁固有的学养、器识、视野,写起来流畅自然、淋漓尽致,自然不同于台海两岸那些奉命文学,或带有严重偏见的鲁迅传。”[4](P111) 书中进一步分析作者和传主之间的关系:“要绘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必须对他有深刻的了解,而这不是生活在他身边就能做到的。因为只有冷静观察,才能达至深刻的了解,而要作冷静观察,就必须保持一定距离,太近了就会产生许多视而不见的死角和盲点。曹聚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既不是鲁迅的学生,也不是鲁迅的密友,他跟鲁迅虽时有交往,但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能够看得真切。”[4](P113) 这是少见的具有真正历史深度的分析。多元价值观念的交织显出了研究者历史视野的开阔,因而在评说作品和人物时,便能自由挥洒,格外鲜明生动。
作为一个传记文学研究者,我还激赏寒山碧先生在这部史著中不时抒发的一些关于传记文学的真知灼见。这些见解,虽是结合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却源自作者的内心和创作经验,有感而发,富有理论创新,无疑将启人心智。请允许我抄录几段以飨读者:
“要写好一部历史人物传记,除了要有扎实的文字基础和表达技巧(即‘史才’)之外,还要掌握丰富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史识’和‘史德’。所谓‘史识’就是要求作者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使自己能够站在高处观看历史长河,并把传主放到历史长河中评估。所谓‘史德’就是要秉笔直书,忠于史实,不贪财富,不惧权威。只有具有足够的‘史才’、‘史识’、‘史德’的作者,才不会仰视或膜拜传主,才可以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史家的立场,对传主作平视的观察和描绘。”[4](P55—56)
“人物传记第一个要素是‘真’,必须符合历史真实。如果作者捏造史料,刻意作伪,或者只是夸大偏颇,即使你有生花妙笔,辞藻华丽,也失其价值。”[4](P111)
“传记文学跟其他文学体载有很大不同,……作者不能幻想,不能创作,不能任意发挥。因为传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大众熟悉的人物,他的事迹大家也耳熟能详,没有作者随意发挥的空间。作者只能根据传主的原本面貌来勾勒描绘。这就存在作者自身的定位问题,你到底是要当美化传主的化妆师?还是想做丑化传主的涂鸦者?抑或要当一个写出历史真实的史学家?”[4](P107)
“婚姻子女似属于隐私,似乎也跟国计民生、香港前途无关,但一部传记却必须了解上述种种,才能了解传主完整的人格,才能勾勒出传主的真面貌。传记作者如果只依传主的意思来写,只展览传主光鲜亮丽的一面,只说传主想说的话,那么他就只是传主的录音机、摄像机,或者只是传主的宣传部主任,而不是能够独立思考具有独立意志的传记作家了。”[4](P456—457)
几点不足与商榷
《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不愧为一部难得的学术专著。作为第一部香港传记文学史,虽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还有一些可议之处。
因限期完成,时间紧迫,全书布局尚未完全均衡,对某些作家作品的介绍存在篇幅过多或偏少的问题。作者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后记”交代了附录一、二中的“香港艺术家的传记”和“香港清末民初的掌故和传记”的写作经过。原来这些文字均出自方宽烈先生之手,因“不符文学史的规范”,只好经整理后“当作附录,列于书尾”,[4](P736) 而给人一种急就章的感觉。
书中有的观点似乎也难以让人信服,如说“近五十年来,香港传记文学成果之丰硕,成就之高,以及在国际上之影响,远远超越海峡两岸。”[4](P28) 又说:“近五十年,大陆和台湾可以为中文世界供应小说、诗歌等文学读物,也可以供应通俗消闲的读物,但无法供应人物传记,特别是当代政治人物的传记。”[4] (P54) 这种论断似嫌武断。说“香港传记文学成果之丰硕,成就之高”,以及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这无疑都是正确的。但若硬要将两岸三地传记文学分个高低,排个座次,愚以为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至少在目前),因为祖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传记文学各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和个性。即以寒先生所说的大陆当代政治人物的传记而言,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应该承认它的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正视它与时俱进的发展现实。实事求是地说,当代大陆政治人物传的写作,虽历经坎坷,但发展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它以其新的实绩证明了它无愧为中国传记文学中一个有独立审美品格的大类。笔者在撰写《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一书时,曾专门用“领袖传记”、“将帅传记”和“反派人物传记”三章的篇幅,来描绘这几类政治人物传记的发展轨迹,评说了近20部代表作品的成败得失。[7]
此外,我还想指出一点的是,香港的当代政治人物传记(含自传与他传),虽出现不少好的或较好的作品,但也有一些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严重错误。由于作者身份的复杂性,加上他们中的有些人或远离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或加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对资料的占有也不够,在概念、术语上有歧解,使得有些结论与事实不符,如把中共党内的斗争一概看成权力之争,如披露的所谓“秘闻”、“内幕”等等,寒先生书中似乎也批判得不够。这些缺失,假如《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今后出修订版,希望能够有所补充和订正。
随着香港顺利地回归祖国,香港传记文学已正式纳入中国传记文学的整体研究领域之内,这给源远流长的中华传记文化必将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我欣喜地得知,寒山碧先生现已荣任香港特区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主席,我们期待着他的《香港特区传记文学发展史》早日问世。
收稿日期:2006—02—20
标签:曹聚仁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香港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人物传记论文; 鲁迅评传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