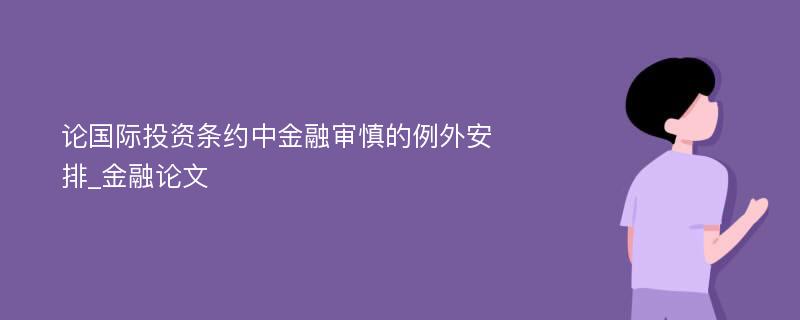
论国际投资条约中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审慎论文,条约论文,国际投资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97(2013)04-0131-09
金融审慎措施的基本含义是指基于审慎原因所采取或维持的合理措施,包括:(1)保护存款人、金融市场参与者和投资者、投保人、索赔人或金融机构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的措施;(2)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健、完整或其财务责任的措施;(3)确保缔约方金融体系完整性和稳定性的措施。这种措施始于国际贸易体制对于金融服务的规制,典型的实践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14章(金融服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金融服务附件。从投资条约的角度看,美国2004年BIT范本和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率先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引入专门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这一做法逐步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缔约实践,构成国际投资法的一个最新发展。
一、在投资条约中纳入金融审慎例外安排的基本背景
(一)金融审慎例外安排产生的一般背景
应该承认,金融审慎例外对于美国而言并不陌生,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寻求将服务业纳入多边条约框架,以适应其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转换趋势,即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的比较优势日益转向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优势则转移到新兴工业国家,而发达国家仍然具有重要比较优势的知识型或高科技型产业和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却被长期排除在多边框架外。作为一项自由化程度极高的区域性贸易协定,NAFTA把传统上被认为涉及国家主权最敏感领域之一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规制范围,部分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开放[1]。其中,NAFTA第14章规定了金融服务的相关规则,不仅包含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基本原则,甚至涉及金融机构的设立、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监管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致力于金融领域的自由化,NAFTA第14章还是规定了金融审慎例外,这一做法同时影响到《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件第2.1条的规定。
由于NAFTA第14章关于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之一为“商业存在”,因此,该章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投资规则。然而,NAFTA专门规制投资问题的第11章却未出现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并且外国投资者在金融领域设立“商业存在”的行为及其经营也非适用第11章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NAFTA投资体制对金融审慎例外的规定并不充分,而事实上这也是美国、加拿大在投资自由化驱动下的必然选择。但是,此后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阿根廷政府被外国投资者频频诉诸国际仲裁的惨痛经历,促使一些国家意识到,有必要将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引入国际投资条约,以便在投资(包括金融服务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维护东道国正当的规制权。在此情况下,极力鼓吹投资自由化但同时极为注重维护本国主权的美国,以及在NAFTA体制内频频被美国投资者诉诸国际仲裁的加拿大及时地“改弦易张”①,在投资条约中率先规定金融审慎例外。
(二)金融审慎例外安排产生的特殊背景
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并未包含专门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在晚近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尤其是阿根廷应对2001年经济危机诱发的大规模投资仲裁案件中,被诉东道国通常援引根本安全例外条款作为金融管制措施的抗辩。例如,Continent公司案的仲裁申请人认为,阿根廷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限制汇出、重新安排现金存款、美元存款比索化等,损害了其在阿根廷的投资权益。针对这一指控,阿根廷提出的基本抗辩依据是1991年美国—阿根廷BIT第11条,即根本安全例外条款。该条规定:“本条约不排除任何一方为维持公共秩序采取的措施,为履行与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义务,或保护自身根本安全利益所采取的措施。”阿根廷据此认为,根据该条规定,应完全或部分免除针对所指控的违反条约义务行为承担的赔偿责任。ICSID仲裁庭最终接受了阿根廷的抗辩,其基本的裁判逻辑是:对根本安全利益应采取广泛界定的做法,它不仅涉及地理、战略以及国防的利益,还包括缔约方在面对社会、政治、严重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确保国家安全的措施。②然而,东道国援引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经常受到制约,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总体而言,投资仲裁庭对于根本安全例外条款采取严格解释的方法,从而导致在类似案件中出现截然不同的裁决结果[2]。例如,在涉及阿根廷的一系列投资仲裁案中,虽然仲裁庭普遍同意根本安全例外包含经济紧急情况,但紧急情况要达到何种程度才可以使东道国免责,不同仲裁庭的裁决意见并不一致。一些仲裁庭甚至将根本安全例外等同于习惯国际法中的危急情况,从而进一步限制了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3]。例如,CMS公司案、Enron公司案和Sempra公司案等案的仲裁庭即认为,虽然阿根廷面临着严重危机,但危机尚未导致阿根廷经济与社会崩溃,尚未危及到国家的存在,因而不能援引美国—阿根廷BIT第11条的规定。③
第二,根本安全例外主要针对特定的、极其严重的国家安全事件或情势,这一点是国际投资仲裁庭共同承认的。换言之,根本安全例外条款适用十分严格的标准。然而,这与东道国在投资自由化进程不断深化,尤其是在金融服务成为日益重要投资形态的背景下维护金融公共利益(如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客观需要并不符合。有效地维护金融公共利益不仅要求东道国在出现严重金融事件或情势时采取有力措施,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管理中通过审慎措施预防严重金融事件或情势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适用根本安全例外显然十分困难[4]。与此不同,NAFTA以及GATS的实践表明④,相关措施只需满足最低标准,仍有可能被认定为构成金融审慎例外。
二、投资条约中金融审慎例外安排的实体内容
(一)主要内容
与1994年BIT范本未针对金融领域的投资制定专门的规则不同,美国2004年BIT范本增加了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并在2012年BIT范本中延续了这一做法。美国2004年和2012年BIT范本采用的共同模式,是把审慎例外安排规定在金融服务条款中,进而规定特殊的争端解决方式、严格的透明度要求等。然而,该模式导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东道国所采取的金融审慎措施影响到非金融领域投资时,东道国政府能否援引金融审慎例外作为抗辩。这种将审慎例外安排纳入或局限于金融服务的做法,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赋予东道国宽泛的金融规制权的顾虑,以及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商业组织在BIT范本修改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反对态度,因此其安排未必是充分合理的。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投资分会在美国2004年BIT范本颁布前的评论中表明了这一点,该机构指出,它的一些成员认为:“金融领域应承担与其他领域相同的BIT项下的义务,审慎例外安排会成为缔约方政府违反条约义务的保护伞,从而导致美国投资者承担巨大的风险。”[5]与美国的做法不同,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将金融审慎例外规定于一般例外中⑤,允许缔约方基于审慎原因采取或维持合理措施,据此,金融审慎例外被延伸到非金融领域。其结果是,在相关金融审慎措施(如适用于宏观经济的金融调控措施)影响到非金融市场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只要它们满足金融审慎例外的构成要件,就不会被视为成员方违背依协定本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
加拿大BIT范本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将金融审慎例外适用到资本汇兑与转移条款。从传统来看,投资条约中的资本汇兑与转移条款旨在平衡两个目标:一是赋予投资者与投资相关的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的权利;二是赋予东道国一定的灵活性,推行其货币和财政政策。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投资条约中的资本汇兑与转移条款只强调“缔约方应当允许所有与合格投资有关的资金自由、迅速地汇入或汇出其境内”,“允许以按照市场最高价换算出的自由使用货币形式进行转移”⑥,但没有包含用于处理严重国际收支失衡及其他情况的例外条款。其原因可能在于,缔约方并不认为限制转移是处理国际储备短缺的最佳选择,相反,在发生危机时,对国际转移进行限制反而会加重投资者的焦虑情绪,从而想方设法去规避这些限制。美国2004年和2012年BIT范本甚至强调,金融服务(显然包含金融审慎例外)不影响缔约方在“资本转移”和“实绩要求”项下的义务。⑦
但是,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曾经建议,投资条约应当对资本自由汇兑与转移施加限制。例如,Anderson指出,美国BIT范本中的相关规定已经过时,严重制约了政府推行维护国家金融体系稳定的政策或导致这些政策的实施不够充分……事实证明,控制资本流动是避免投机资本泡沫和恐慌性资本外流的极少数有效工具之一[6]。作为效力于美国政府的政策研究中心全球经济项目主任,Anderson的建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如,美国国务院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流动的暂时限制对于防范和缓和金融危机是必要的,而短期资本输出入的规制尤其如此[7]。遗憾的是,可能受到着力推动并维护投资自由化的商业界的影响,这些建议在美国2012年BIT范本中并未获得采纳。与美国踯躅不前的情形不同,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已经对金融机构的资本汇兑与转移作出明确的规制。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第14.6条规定,为了保护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定、完整及其支付能力,缔约方可以禁止或限制某一金融机构将资金转移给其分支机构或者与该机构相关的人,但该措施的适用必须是公平的、非歧视的以及善意的。
(二)晚近采取金融审慎措施可能诱发的投资争端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传统上奉投资自由化为圭臬的发达国家频频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采取一些非常态的管制措施,这种情况在金融领域尤为突出。布雷顿项目组织(Bretton Woods Project)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国际投资仲裁中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结构出现转向,即来自于南方国家的投资者更有可能对发达国家政府提出仲裁指控[8]。Aaken和Kurtz也认为,由于政府在救助危机时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与其他国际经济法领域相比,短期内国际投资法领域更容易产生法律诉讼。⑧它们主要包括政府在发生危机时的政策介入,比如对流动性的支持、购买银行资产、对银行间同业借款的支持以及给予零售银行的存款担保等。由于这些救助措施一般只适用于国内金融机构,而外国投资者不能享受到同等的非歧视待遇,因此大多存在隐性投资保护主义的倾向[9]。例如,美国《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授权财政部通过“问题资产解救方案”(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收购问题住房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其救助的对象限定为在美国有“重要经营”(significant operations)的金融机构。虽然该方案并未排除外国银行受惠于美国救市计划的可能,但实际上美国的国内银行占据了绝大多数。
诚然,由于美国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多采用“补贴或津贴包括政府支持的贷款、担保和保险”的方式,它们属于美国2004年或2012年BIT范本第14.5条规定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豁免范围,因而外国投资者难以根据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条款获得补偿。并且,由于政府针对金融市场的救市政策通常因势而动,不断调整,要界定这些措施的性质并非易事。但是,第14.5条并未提及公平和公正待遇,因此,投资者仍然有可能以未获得与美国银行相同的救助计划为由,根据公平和公正待遇条款提出指控。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已经出现过类似措施引发的投资仲裁案件。比如,Saluka案仲裁庭认为,捷克政府在处理银行业的坏账问题时,不能提供合理的理由证明为什么对日本银行在荷兰的子公司给予差别待遇。捷克本国的四家大型银行在面对坏账问题时处于类似的情况,投资者存在合理的预期,认为救助计划也会涵盖Saluka公司,但捷克政府的做法显然让投资者的合理预期落空。⑨
三、金融审慎例外争端解决的特殊程序安排
在WTO体制下,涉及金融服务的争端只能通过WTO成员方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解决。与此不同,20世纪90年代后缔结的国际投资条约普遍规定了投资者—国家间仲裁机制,据此,投资者往往可以不受国家(东道国和母国)限制直接诉诸该机制。对于传统上仅适用于当地救济的金融服务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发展,但同时也给主权国家尤其是东道国带来严峻的挑战。对此,无论是NAFTA还是此后的美国、加拿大BIT范本,一方面规定了投资条约中通常采用的投资者—国家间仲裁和国家间仲裁程序,另一方面则借鉴了在维护东道国主权时同样敏感的税收措施的处理模式,即将缔约方之间主管部门的协商作为争端解决的主要方式之一。例如,以强调独立裁判和承认投资者诉权著称的NAFTA,对金融审慎例外设置了特殊的由金融服务主管部门磋商的规则,并承认它们的共同决定对仲裁庭具有约束力。更早一些的《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甚至排除适用仲裁的方式,规定涉及金融服务的争议只能由加拿大财政部和美国财政部通过协商加以解决。⑩此后,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BIT范本,涉及金融审慎例外的仲裁机制都既不同于一般的国际商事仲裁或公法意义上国家间的国际仲裁,也有别于ICSID体制下的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
例如,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第17条规定:当投资者向国际仲裁庭提出诉请而被诉方东道国以金融审慎措施和合理的阻止或限制资本转移措施为由进行抗辩时,应先由缔约双方的金融主管部门进行磋商,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或通过另设国家间仲裁小组的方式,准备一份书面报告,该报告对仲裁庭具有约束力。仲裁庭在收到该份报告前,不得就前述条款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投资者的诉请构成有效抗辩作出审理。反之,如果仲裁庭在收到投资者诉请的70天内,既未收到两国另设仲裁小组的请求也未收到来自两国金融主管部门达成共识的书面报告,仲裁庭即可直接对前述问题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定。其中,承认主管部门间书面报告约束力的意义在于可以更好地反映缔约方的真实意图,避免由仲裁庭白行任意解释条约而影响到缔约方金融安全的情形发生,而时间上的限制则可避免仅由缔约双方协商出具报告时缔约双方的久拖不决。简言之,仲裁庭对于投资者单方提出的东道国金融措施“不合法”侵权的诉请,享有较为直接的管辖权、审理权和裁决权,而不仅仅是主管部门协商程序的延伸[10]。
在投资者—国家间仲裁解决争端方面,较之加拿大较为保守的做法,美国的缔约实践则显得较为激进。事实上,美国2004年BIT范本颁布前的草案曾经规定,当双方金融主管部门未能就金融审慎例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作为有效辩护决定的情况下,被申请方可以请求设立国家间仲裁庭对金融主管部门的未决问题作出决定。但是,这一程序的设置遭到代表投资者利益的国内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抱怨认为,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首先是两国主管部门的联合决定,如果被诉国要求,还将进入没有时间限制的国家间仲裁,这种冗长、重复的程序设置降低了仲裁效率[11]。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2004年和2012年BIT范本都规定,如果双方金融主管部门在收到请求后120天内未能作出正式决定,仲裁庭应当认定该问题未能由缔约双方适格的金融主管部门解决,并适用投资者—国家仲裁的程序。同时,美国2012年BIT范本还设置了更严格的时间限制,该范本第20.3(e)条规定,如果两国金融主管部门没有作出联合决定,仲裁庭应在30天内就主管部门的未决事项形成报告,以解决被申请方(东道国政府)是否能够援引金融审慎例外的问题。由此可见,虽然美国BIT范本还保留着国家间仲裁程序,但它与投资者—国家仲裁是彻底分离的。这种模式维护了投资者在金融服务争端解决中实质性的地位,从而降低了国家间仲裁对投资者保护的弱化,强调了投资者通过投资者—国家仲裁途径寻求救济的权利。
四、中国投资条约中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及其完善
目前,在投资条约中包含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已经成为国际投资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对中国而言,这一安排显然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中国是传统的投资输入国,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向对外投资大国转变。(11)这种转变同时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增加,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例如,中国平安集团诉比利时政府案表明,中国的投资实践实际上已经涉及金融审慎例外问题。作为首起中国内地企业诉诸ICSID解决投资争端的案件,该案备受关注。2007年11月,平安保险集团斥资238.74亿元购买富通银行4.18%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但富通银行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陷入困境,比利时政府通过对该公司进行国有化及变卖资产的方式提供援助,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平安保险集团最终累计计提损失达227.9亿元,2012年9月,平安保险集团诉诸ICSID申请国际仲裁[12]。对此,比利时政府抗辩认为,在2008年富通集团面临整体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有责任及时采取措施保障该实体继续经营,其购买富通银行股权并将75%的股权转售给巴黎银行,是为了保障存款人和客户的利益以及富通集团在比利时境内雇员的就业[13]。由于中国—比利时BIT(1984)中并无根本安全例外或金融审慎例外的规定(12),比利时政府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该行为属于非补偿性的管制措施而非间接征收。国际法上虽然承认非补偿性政府管理措施的存在,但未对两者的区分予以明确阐述,且仲裁庭在实践中更倾向于关注这些措施对财产所有人产生的影响而忽视规制措施的目的[14]。
单就本案而言,中国—比利时BIT中没有包含根本安全例外或金融审慎例外条款对中国企业可能是“因祸得福”,比利时政府无法以该措施的目的是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稳定为由成功抗辩。尽管如此,从中国兼具重要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的双重身份看来,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欢呼雀跃”。例如,WTO争端解决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目前,涉及GATS金融服务附件的案件共有4例(13),全部指向中国,这也凸显了中国将金融审慎例外安排作为金融领域(包括金融服务)开放安全阀的重要性。因此,在我国缔结的国际投资条约中设计恰当、合理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金融规制权,同时又避免过度限制或损害对外投资者的利益。
(一)实体性条款
就我国的缔约实践而言,除中国—哥伦比亚BIT(2008年12月签订)、中国—加拿大BIT(2012年9月签订)外,金融审慎例外安排还出现在《中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中国—东盟国家投资协议》)、《中国政府、日本国政府及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以下简称《中日韩投资协定》)、《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等投资条约或协议中。
1.金融审慎例外
在设置金融审慎例外安排方面,我国签署的投资条约并没有遵循统一的模式,甚至对于是否将金融服务纳入投资协议还存在着一定的顾虑,体现为相关条约或协议签署时的语焉不详。例如,《中国—东盟国家投资协议》第3.5条规定,投资待遇(公平和公正待遇)、征收、转移和利润汇回、损失的补偿、代位和缔约方与投资者间争端解决,经必要修改后应适用通过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贸易。同时,该协议第16.2条针对金融服务,允许GATS金融服务附件第2款(国内规制)经必要调整后并入。但对于何为“必要调整”,至今都没有明确界定。《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既无专门的章节涉及金融服务,也未对金融服务的内容作出专门规定,却在第2条(适用范围和例外)第6款规定,一方可以基于审慎理由采取或维持与金融服务相关的措施。
此外,即使是明确地将金融审慎例外纳入调整范围的近期投资条约,其规定也不尽相同。中国—哥伦比亚BIT在第13条中明确指明“金融部门的审慎措施”,《中日韩投资条约》第20条的标题为“审慎措施”,但在具体内容上将其界定为“涉及金融服务的措施”,而中国—加拿大BIT则把金融审慎例外规定在一般例外中。本文认为,虽然将金融服务单列的方式有利于强调对金融服务纳入投资条约保护范围的重视,但较之中国—加拿大BIT而言,在具体适用时缺乏周延性,因为后者更有利于东道国政府利用金融审慎例外安排维护金融主管部门在非金融领域的规制权。
当然,美国、加拿大的BIT范本对于金融审慎例外的实体性规定也颇为笼统,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法中“审慎”一词和“例外”存在密切关系,与此不同,国内法中的“审慎”往往被视为金融监管的原则之一。审慎例外的敏感性使得各方在此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分歧不小,因此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与之相类似,在规定金融审慎例外的判断标准时,GATS金融服务附件第2条同样存在着模糊性问题。对此,欧盟曾建议适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对“审慎”一词进行补充解释,但因为WTO成员方对上述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代表性有所质疑,该建议并未获得广泛支持。(14)实际上,就各国规制金融业的法规和政策来看,其中多数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审慎考量,如果不进一步区分,审慎措施将等同于各国的金融法规和政策,从而导致推行金融服务领域的投资自由化努力沦为一纸空文。
由此可见,审慎原因的界定以及审慎措施的标准和范围缺乏明确性,会导致其在适用中的困难。如果提交投资者—国家仲裁,很可能是承认了仲裁庭对这些模糊问题的解释权。对此,美国国务院关于修改2004年BIT范本的一份报告曾经提出,针对第20.1条的金融审慎例外,应当加入类似于根本安全例外中采取的“自裁决”(self-judging)的措辞。(15)因为基于历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其是否危及国家生存只有当事国最为清楚,当事国应最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无论是发生金融危机或者为防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审慎措施都是如此,而置身事外的第三方的事后判断无法取代当事国在当时的决策。(16)
本文认为,虽然投资条约尚未将金融审慎例外设置为“自裁决条款”,但从美国金融危机后对投资条约的反思以及对国内金融市场利益加强保护的实践来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此,在我国签订国际投资条约时,如果能把金融审慎例外规定为“自裁决条款”,将有利于为自身保留更灵活的政策空间。当然,为了避免金融审慎例外的模糊性赋予仲裁庭过于宽泛的裁决权,有必要针对争端解决作出特殊规定,从而确保缔约国金融主管部门可以有效参与甚至主导此类争端的解决。
2.资本汇兑与转移例外
1996年12月,我国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并开始了资本项目的开放。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加快了资本项目改革的步伐,直接投资领域实现了基本开放,而证券投资领域则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重要时期[15]。此后,我国外汇管理局不断推出取消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审核权限及管理措施的通知,在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的同时,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转移。由此可见,从长远来看,中国将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汇兑与转移,因此,有必要在投资条约中规定相应的资本汇兑与转移例外条款。
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国际投资条约实践来看,早期资本汇兑与转移条款一般仅规定“在满足其法律要求的条件下,各缔约方应允许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实现款项的汇出,并且不应不合理地迟延”,2003年中国—德国BIT议定书第5条甚至前瞻性地提出,如果相关手续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不再被要求,BIT中“投资和收益的汇回条款”可以不受限制地适用。2004年5月,中国—乌干达BIT第7.4条首次规定了资本汇兑与转移中的金融审慎例外,允许一旦发生严重的收支失衡或外部融资困难或存在这样的威胁,缔约任何一方可以暂时限制资本转移,前提是该限制应被立即通知缔约另一方,与IMF协定的条款相一致,限制在商定的期限内,并根据公平、非歧视和诚实信用原则而实施,此后,中国在部分BIT中陆续加入了类似规则。
但与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不同,我国投资条约中针对资本汇兑与转移事项规定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主要适用于严重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17)对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予以完善:首先,中国—韩国BIT第6.4条增加了“在例外情况下,资本转移引起特别是金融和汇率政策方面的宏观经济管理的严重困难或有上述困难之虞”,其范围较之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仍较为狭窄。因此,特别是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的初期,我国应将资本汇兑与转移例外放宽到“为保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完整”,扩大其适用范围。其次,在极少数BIT如中国—法国BIT第6条中,资本转移限制措施实施的时间被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长于6个月”,这样的约束虽然有利于保证投资者在金融危机发生时也能尽快转移其资本,但对于东道国的政策制定显然十分不利。因此,我国未来签订的国际投资条约应尽量采用中国—韩国BIT的措辞,即“临时的并在条件许可时被取消”。
(二)争端解决
在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上,最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的方式当属协商。在协商解决争议的过程中,争议双方地位平等,方法灵活多样。正因为如此,对于涉及国家主权核心的领域,争议国家往往不愿采用法律的方式,而更倾向于协商。然而,相互协商程序只能要求相关国家的主管部门设法就争议的解决达成协议,并不是必须达成,其结果容易因主管部门无法达成共识而使争端得不到有效解决。因此,在目前的国际投资领域,通过仲裁解决争端已经成为发展趋势。虽然将涉及金融审慎例外的投资争议置于国际仲裁之下,可能会导致外国投资者滥用诉权以挑战东道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权,东道国政府基于审慎监管追求特定公共政策目标的能力有可能受到抑制,但在金融市场全球化、WTO明确了对金融服务进行规制的背景下,投资条约将金融审慎例外彻底摈除于仲裁解决之外,并不可行。
因此,中国—加拿大BIT针对金融审慎措施合法性的认定,采取了特殊的处理方式,即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仲裁庭不享有裁决金融审慎措施合法性的管辖权:首先,仲裁庭应向缔约双方寻求关于此问题的书面报告。投资者—国家仲裁庭只有在收到此报告后方可继续仲裁程序,或在设立国家间仲裁庭的情况下,只有在收到此国家间仲裁庭裁定后方可继续仲裁程序。其次,如果争端各方的金融服务主管部门未能在规定的期限(60天)内联合作出共同决定,则任一缔约方可在30天内将争端提交给缔约国间的仲裁庭解决。
由此可见,该程序的设计是调和传统的金融服务争议由东道国国内管辖与投资者寻求国际仲裁之间矛盾的产物,其试图在解决金融审慎例外问题上实现尊重东道国对国内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与维护跨国投资者权益之间适当平衡的目标,但仍然属于相互协商程序的延伸。应该说,由于有后续国家间仲裁程序的压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缔约国双方主管部门积极主动地尽最大努力通过此前的相互协商程序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以避免启动后续的仲裁程序,从而提高双方主管部门间相互协商程序的效率。即使双方主管部门不能在前置性的相互协商程序阶段经过谈判解决争议问题,通过后续的具有第三方争端解决性质的国家间仲裁程序,也能够使妨碍主管部门间达成协议的未决问题获得仲裁裁决。
国际投资条约历来被认为是强有力的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工具,然而,例外条款的存在表明,对投资者的保护不适用处于极端风险中的危机情况或其他特定情形。例外条款为缔约方设置了一种免责机制,缔约方可以在例外情况发生时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而不承担违反条约义务的责任,从而合理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权益保护关系。由于晚近投资仲裁实践暴露出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在抗辩外国投资者诉求方面的不足,金融审慎例外的出现具有其必然性和现实性,有利于通过肯定东道国的规制权来应对投资自由化带来的风险。对于我国而言,金融审慎例外安排还有其特殊性:作为资本输出国,我国需要关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以金融审慎为由实施的市场干预措施和救助措施,这些措施存在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有可能导致金融审慎例外异化为投资壁垒;作为资本输入国,我国则应尽可能通过金融审慎例外安排的合理设置,在国际投资规则谈判中充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收稿日期:2013-03-25
注释:
①截至2011年12月,美国被诉14次,成为全球第十大被诉国,而加拿大被诉17次,是全球第六大被诉国。(参见:UNCTAD.Latest Development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J].IIA Moniter,2012,(1):17.)
②参见: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Claimant) v.Argentine Republic(Respondent),ICSID Case No.ARB/03/9(2008),paras.162-165.
③参见:CMS Gas Transmission Co.v.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ICSID case No.ARB/01/8(2005); Enron Corp.Ponderosa Assets v.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ICSID case No.ARB/01/3(2007);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The 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2/16(2007).这3起案件后来都进入撤销程序,CMS公司案的撤销委员会认为,仲裁庭将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必要条件与习惯国际法中危急情况的必要条件相等同是错误的,但最终认定该裁决没有明显越权而未予撤销。Enron公司案和Sempra公司案的撤销委员会都作出撤销裁决的裁定,理由是仲裁庭未适用根本安全例外,由于没有正确适用法律,已构成明显越权。
④构成金融审慎例外的条件要比根本安全例外宽松。在金融审慎例外中,通常采取的措辞是“为保护……”,而非根本安全例外中的“必需”、“必要”等。对于后者,只要存在一种可行的替代性措施比现有措施更有助于实现目标,现有措施就会被认为不符合必需要件;对于前者,即使存在更优的替代性措施,但只要现有措施满足最低标准,仍有可能符合金融审慎例外的要件。
⑤参见: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第10.2条。
⑥参见:美国2004年BIT范本、2012年BIT范本第7条。
⑦参见:美国2004年BTI范本、2012年BIT范本第20.2条。
⑧其原因主要在于,国际投资法中涉及金融审慎例外的内容显然比国际贸易法如WTO规则更为宽泛。同时,与WTO的争端解决在政府与政府之间进行,容易引起针对对方同类型措施的报复性诉讼或贸易报复不同,国际投资领域允许私人投资者发起投资者—国家间的仲裁程序,从而弱化了政府间争端解决的政治考量。(参见:Anne van Aaken,Jürgen Kurtz.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G]//Simon Evenett,Bernard Hoekman.Trade Implications of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risis.Washington:World Bank Publication,2009:9-10.)
⑨参见:Saluka Investments BV v.The Czech Republic,UNCITRAL,Award(Mar.17,2006).
⑩NAFTA第1415.2条,《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第1704条。(参见:Anna V.Morner.Financial Servic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A Comparative Snapshot[J].Law & Business Review of the Americas,2001,(Fall):67-68).
(11)201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60.11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746.5亿美元,其中金融类投资为60.7亿美元。(参见: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三部门发布《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B/OL].[2012-12-07].http://www.gov.cn/gzdt/2012-08/30/content_2213920.htm.)
(12)2005年6月签订的中国—比利时BIT在发生国有化时还未生效,即便如此,2009年12月生效的中国—比利时BIT也未包含根本安全例外或一般例外条款。
(13)这4起案件分别是中国-影响金融信息服务和外国金融信息提供者的措施案(DS372,DS373,DS378),中国-影响电子支付措施案(DS413)。(参见:Disputes by Agreement[EB/OL].[2013-01-14].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agreements_index_e.htm? id=A8#selected_agreement.)
(14)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Special Session,Report of the Meeting Held on 3-6 December 2001,S/CSS/M/13,Feb.26,2002.
(15)例如,《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第22.2条的脚注2就特别提出,当一成员方按照第10章“投资”或第21章“争端解决”提出根本安全例外的仲裁程序时,仲裁庭或专家听证程序应适用该项例外(即属于“自裁决”的内容)。
(16)自裁决条款一般取决于条款本身的措辞,缔约方可以通过明确的条约措辞来体现某一条款具有自裁决性质,反映其真实的意图,以影响仲裁庭的评判标准。(参见:韩秀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自裁决条款研究——由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引发的思考[J].法商研究,2011(2):17-24.)
(17)例如,中国—加拿大BIT第12条、中国—西班牙BIT议定书第6条等。
标签:金融论文;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审慎监管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投资论文; 金融服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