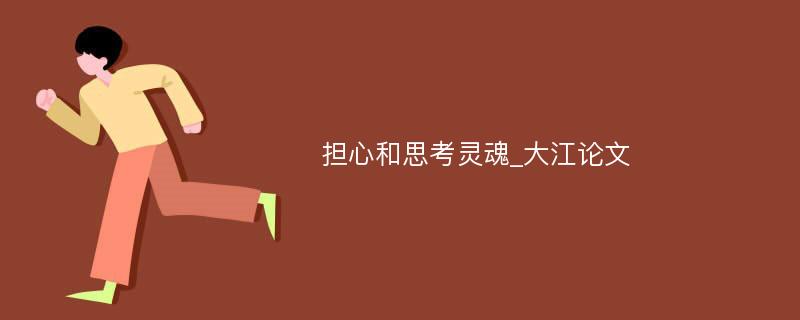
关于灵魂的忧虑和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虑论文,灵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信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在大江健三郎晚近的作品里,“灵魂的问题”愈发成为作家关注的重心。比如,在去年推出的长篇小说《空翻筋斗》(新潮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的封面上,大江就明确宣布,自己的创作目标是“在小说里创造一个建构灵魂的场所”。而在最近发表的关于冲绳的系列随笔中,他也清楚表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传达冲绳的‘灵魂’所发出的声音”。(《朝日新闻》二○○○年五月十八日)熟悉大江作品的读者会清楚,这样的思想倾向和写作意识,并非作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晶。“灵魂”,是大江的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语,也是指引我们进入大江的文本世界的重要标识。本文就是想沿着这一线索,对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和文学发展的脉络,做一些梳理和阐释。
从词语到主题
如所周知,所谓灵魂问题,常常和宗教观念有一定的关联。在大江的文本里,“灵魂”作为一个重要词语被使用,就是和《圣经》联系在一起的。他于一九六四年发表的系列随笔《广岛札记》第五节引述了《圣经·创世记》中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灵魂”、“拯救”等词语也在这段文字里出现。这透露了大江对《圣经》的初步兴趣,虽然在同书里他谦虚地说:“我对于《圣经》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随后,《圣经》显然成了他经常阅读的书,一九七三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仅从篇名就可以看出,灵魂和洪水,已经不是作家信笔使用的词语,实际上成了大江文学世界的重要意象和思考主题。
《洪水淹没我的灵魂》的标题所包含的典故,当然和《广岛札记》引用的诺亚故事有关,但更直接的来源是《旧约》里的《约拿书》(注:《约拿书》第2章第5节约拿向耶和华祷告的话里,有这样的句子:“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的灵魂。”)和《诗篇》。尤其是《诗篇》中“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一节,深深地打动了大江的心,他说自己由此而充分体味到灵魂浸在哀伤里的焦虑和对获救的强烈期望,而在他的笔下,这节诗则像主题曲一样,回响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洪水淹没我的灵魂》描写的是一个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鲸鱼和树木的代理人、名叫大木勇鱼的人物。他断绝以往的一切社会联系,和白痴的儿子躲进可以抵御核辐射的避难所,过着隐居生活。但早在《个人的体验》(一九六四)时期就已经确立的这种父亲与残疾儿子共同生存的故事模式,在这部长篇里有了新的发展。小说特别写到,被认定为白痴的儿子,“眼睛深沉而澄澈,听觉敏锐超常……至少可以辨识出五十种野鸟的叫声”。对于致力保护自然环境的大木勇鱼来说,儿子敏锐感受到的其实是被破坏的自然发出的哀鸣和呼救呐喊,他不仅由此获得新的信息,也获得生活的勇气。后来大木走出隐居地,参与到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组成的“自由航海团”,在向团员们发表演说时,他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人物的话说:“我们要特别爱护孩子!因为孩子像天使一样纯洁,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感动,使我们的心灵净化,是对我们的一种指教。”在这里,残疾儿不再只是需要看护的对象,同时也是鼓励健康者生存的积极的存在。这无疑是大江文学主题的一个积极的深化。无需讳言,小说描述白痴儿子感悟启示的场面,不无神秘色彩,但作家并没有以此遮盖或改变另外一条写实性线索,“自由航海团”和代表国家暴力的警察机动队发生冲突,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总体说来,大江尽管借用了《圣经》典故以至故事框架,但他真正关注的并非纯粹的基督教神学问题,而是人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仍然是关于和残疾儿共同生存的叙事,到了系列短篇《新人呵,醒来吧》(一九八二),大江为什么把阐释的参照转向了诗人布莱克。这位十八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先驱者的诗作里的意象,虽然很多都“来自基督教圣经旧约”(注:参见王佐良《英诗的境界·布莱克》,三联书店,1991年7月。),但他秉持的信念的思想来源其实相当庞杂,“立足于从基督教到密教的传统上”(注:参见大江健三郎系列短篇小说《新人呵,醒来吧》中的《被禁锢的灵魂》。)又通过诗歌艺术,独创了“一套神话体系”(注:参见张德明《论布莱克诗歌的神话原型形式》,《外国文学评论》1990第1期。)。布莱克的方法,显然很容易引起同为文学家的大江健三郎的共鸣,尤其是布莱克通过儿童天真纯洁的灵魂透视人的本性、生命的本质的思考,更给予大江以直接的启发。头部患有疾病的儿子身体在成长,但智力却犹如幼童。他的灵魂深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这样孱弱的生命,怎样才能在社会中生存?这是大江在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不停思索的问题,《新人呵,醒来吧》则是这种思索的形象记录。这部由七个短篇组成的系列小说,主要叙述“我”和残疾儿子义幺共同生活中经历的艰难、辛酸、欢乐和哀伤,情节和作家的实际生活接近,颇有些类似日本文学中传统的自叙传体“私小说”。但在叙述义幺故事的同时,作家还设置了一条“我”阅读布莱克的线索,两条线索映照交织,不仅把传统的“私小说”改造成了复调叙事,更重要的是,把描写残疾儿成长的过程升华为探讨人的灵魂奥秘的过程。
在这部系列小说里,布莱克的诗句不仅预示着义幺故事的发展,还是引导人们进入义幺灵魂世界的桥梁。第一篇《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写道,“我”到国外旅行期间,留在家里的义幺突然表现异常,举止乖戾,说出的话也不可理喻。他不相信母亲说的“爸爸没有死,下个星期就回来”的话,坚定地反驳说:“即使是那时候回来,现在他也已经死了。”归国之初,“我”也认为儿子发了疯病,甚至从他面孔和眼神里看出“发情的野兽在内部吞食着他”。但随着对布莱克诗作的理解加深,根据自己童年时代也曾有过的“死去的人还能回来”的想法,“我”终于明白:义幺幼稚的念头,或许因为他发育迟缓的智力还停留在儿童阶段,但他考虑父亲死后的问题,说明这颗天真的心灵也在成长。而他的乖戾举止,则表明他“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由是,“我”真正领会到,义幺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巨大的痛苦。但那不是绝望无告的表情,而是为了慰藉他人的悲伤,像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吟诵的那样:“他坐在我们身边/呻吟着,直到我们的悲伤逃走。”
从残疾儿不合常理的话语中读出意识深层的声音,在其常被从轻蔑意义上称呼的“天真”(=白痴)的灵魂中发现独特的力量,是贯穿《新人呵,醒来吧》的主旋律,也是大江在此之后直到九十年代初继续探索和表现的文学母题,《环火鸟》等作品,都可视为这一思考线索上的产物。在这些作品里,“灵魂”成为经常讨论到的话题,但略加考察就可以看到,这些讨论很少围绕宗教信仰展开。而在描写残疾儿的意识世界和某种特殊能力的时候,大江虽然会表现出对一些超常现象的迷恋,但最终总会或明或暗地做出合乎理性逻辑或艺术逻辑的解释。如《环火鸟》的结尾,一向处于被父亲保护地位的儿子,在父亲昏倒的时刻突然转化为父亲的保护者,而他已经丧失的对野鸟叫声的记忆,也在那一瞬间恢复。这情景当然有些神奇,但这与其说是神秘主义的渲染,毋宁说是浪漫主义的艺术修辞,而让读者受到强烈震撼的,也并非超自然的“奇迹”,而是残疾儿子和父亲相濡以沫的人间情怀。
忧国与忧虑自我的灵魂
就这样,在以上论及的小说里,对“灵魂问题”的探索,作为神话层面上的故事,不断地向写实层面的残疾儿故事投射进色彩斑斓的光束,丰富和提升了后者的意义蕴含,也为大江的文学带来了独有的特色。但大江并不认为自己因此获得了特别成功,尤其是宣布停止小说创作以后,回顾近四十年的文学历程,他甚至认为,恰恰是小说叙述,妨碍了对灵魂问题的彻底探究。因为对于职业小说家来说,即使未能对问题做出透彻解释,也可以将其付诸文学表现。表现完成了,但问题却遗留了下来,这正是大江最感遗憾的。所以,他决定由小说转向斯宾诺莎,直接去面对终极的灵魂问题。而那时候,大江的思考也有了更具体的所指。他说:在有限的余年里,我不能不忧虑自己的灵魂(注:参见大江健三郎《我的小说家的历程》第10章,新潮社,1998年4月。)
大江之所以做这样的决断,主要出自两方面的考虑。第一,这是他思想和文学发展的一个自然归宿。从《新人呵,醒来吧》到以后的续作,他始终把以自己儿子为原型的残疾儿的内心和生活作为描写重心。其主要目的,是想给缺乏表现能力和交流能力的残疾儿做个代理人,借助通用的语言媒介,将其灵魂世界展现给社会。但当儿子创作的音乐被广泛理解和接受之后,大江认为自己的代理者作用已经变得多余,剩下的时间,应该用来考虑自我灵魂的问题了。第二,大江的决断,也是针对他所置身的社会现状做出的反应。他写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些并没有做成什么事业的历史学家、文学研究家和掌握了国家艺术机关权力的作家,到了晚年,发表忧国言论,居然大为畅销。其实,这些人所谓的忧国之思完全是谎言。他们的言论,不过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无缘结出果实的证明。大江甚至直接对他们发出质问:难道没有比忧国更重要的事情?难道你们不更应该忧虑你们自身(虽然还谈不到你们的灵魂)?(注:参见大江健三郎《我的小说家的历程》第10章。)
参照日本社会的政治状况,可以知道,大江的批判锋芒,直接针对的是以作家石原慎太郎、“自由史观研究会”等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九十年代以来,他们利用日本社会因冷战体制解体、泡沫经济崩坏而产生的心理恐慌,鼓吹国家主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一时在媒体上大行其道。他们把向遭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道歉的政治家称为“亡国之徒”,把知识界反省日本侵略历史的努力称为“自虐史观”,而这些观点居然被无批判地接受,所谓的“自虐史观”,甚至在青年学生和市民中成为“最新的流行词语”(注:参见小森阳一等《超越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5月。)。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江特别提出“自我”,来对抗右翼势力膜拜的“国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大江的用意,并不是要躲进封闭的自我天地,他解除自我禁令之后创作的《空翻筋斗》,和此前的《燃烧的绿树》(一九九三——一九九五)都表现出他深广的社会关怀。两部作品都写到具有某种超常功能的人被视为神或救世主,被推为新兴宗教的教主,而当他想要放弃神的身份时,却不为信徒所容许。因为他们需要神来保证“灵魂的安宁”,常有论者提到这两部小说和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关系,其实还可以说,这两部小说也隐喻地浓缩了近代以来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绝对权威的形成,潜藏着作家对国家主义复活的担心和对国民所陷入的精神危机的忧虑。同时,小说里也包含着作家对自我灵魂的深刻剖析。大江在谈到《空翻筋斗》时说: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他“把自己心灵深处易于被神秘主义所吸引的部分全都暴露出来,并一一加以清算”(注:大江健三郎《致苏珊·桑塔格》,1999年4月。)。
经过这样的清算,大江对灵魂的解释和形容也退去了神秘,而变得更加朴素。在《燃烧的绿树》里,否定自己创建的教会的格兄用水滴和大地的关系比喻灵魂和上帝,认为要“建构真正的灵魂”,不应依赖教主和宗教组织,而应像水滴渗入大地一样,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祈祷和主直接相通。这之中无疑寄托着作家的理念。而在普通人中发现“真正的灵魂”,本来也是大江所坚持的信念。从六十年代以来,他风尘仆仆地赴广岛,到冲绳,则是这种信念的实践。多年坚持反对美军基地的冲绳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他解释了灵魂的含义:“它藏在人格的深层,即使肉体受伤,精神受伤,它也不会损失。”(注:《朝日新闻》2000年5月18日。)而身负原子弹爆炸创伤而顽强生存的广岛人,更一直给予大江以关于灵魂的启迪。他甚至认为,广岛人不仅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人类的灵魂。九十年代初,他已坚定了这样的认识,但当把这认识发布于世的时候,却遭遇了困难。一九九○年,大江和一个电视摄制组一起到韩国访问著名诗人金芝河,谈话的题目是《世界记着广岛吗?》金芝河是大江的老朋友,当年,为营救被韩国军人政权迫害的金,大江奔走呐喊,甚至退出国际笔会日本分会以示抗议。但现在,金芝河却向大江发出严肃的批评:这个电视节目的题目错了。毋宁说,应该问的,是“世界记着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人吗?”“记着战争中牺牲的一千万亚洲人吗?”……大江端正地坐在金芝河面前,认真地接受他的批判。后来,他不仅让电视清楚地放映这一场面,而且,还写进自己的文章里。他知道,灵魂和人格,都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而非抽象的存在。大江和金芝河的对谈场面,不仅反映了沉重的日本现代历史给大江带来的巨大困境,也记录了一个“真正的灵魂”自觉背负起十字架所经受的磨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