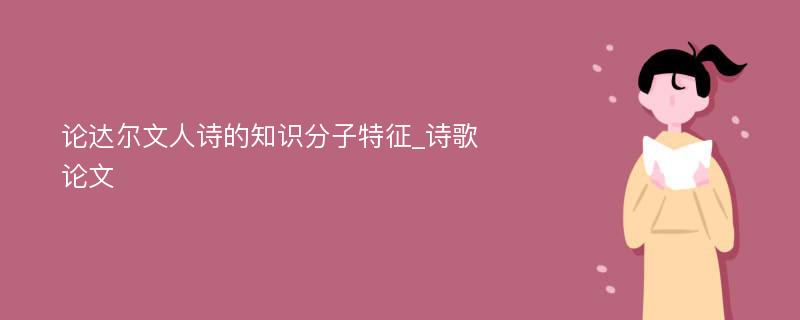
论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的知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斡尔族论文,知性论文,文人论文,诗歌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3)06-0084-06
清代以降,达斡尔族的文人诗歌①创作肇始,敖拉·昌兴的出现将其引入较高的发展层面,此后达斡尔族诗歌创作蔚为大观。面对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新的诗歌现象和庞大的诗歌数量,概括分析其诗歌品质就成为必然。只冠以“民族性”显然失之宽泛。笔者认为,“知性”或许是达斡尔族诗歌区别于其他民族诗歌的关键所在,也正能揭示出达斡尔族诗歌独特的精神构成与诗歌质地。
本文所使用之知性属于诗学范畴。对于“知性”为何,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而言,知性是指抽象的、概括的、综合的精神能力。具体到诗歌领域,知性诗歌除了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更应该在哲学的或日形而上的层面去理解,并且哲理性的内核应该是知性诗歌的重要构成,即该类诗歌偏重理性思考,具有玄学色彩;但哲理性并没有妨碍诗歌的诗美,由于理性的介入,这些诗歌往往由清明的理性节制着感伤与激情。诗歌此时就成为现实和哲思的融汇:现实指其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哲思表现为敏感多思、机智,具有对现实人生折光和抽象的能力,因之这类诗歌往往能把握人生和宇宙的真相,对生存有深刻的思辨。
达斡尔族诗歌的知性特征有其基础。达斡尔人的学校教育开始于17世纪70年代,至晚清,各地达斡尔农村已经普遍出现满文私塾,到光绪末年则兴办起大量汉文私塾,此外各地的八旗学堂也培养着知识分子,因此从历史上看,达斡尔人的受教育程度就极高。而达斡尔诗人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诗人往往也是学者。从达斡尔族文学的宗师敖拉·昌兴开始到钦同普②,再到当代诗人孟和博彦③、孟德苏荣④等都是如此。诗人们的知识储备足够令其诗歌涵容最大的智慧内核并承载相应的哲理异趣。
如前所述,对知性诗歌而言,诗歌的内在支撑是潜在的哲理,具体到达斡尔族诗歌这里,则反映为如下主题:从自然中获得启悟,从日常境界中体味哲理,省思历史,等等。可以说,很多达斡尔诗人都致力于以诗句表达人生甚至是宇宙的觉识,复杂深沉的精神内蕴构成达斡尔族文人诗歌创作规律性的东西,并因其从近代(清)到当代的时间跨度而显示出某种笼罩性影响,或者说,形成了创作传统和资源,从而具有了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一、从自然中获得启悟
人类一直直接或是间接地从自然中获得生产生活资料,虽然曾经出现过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思潮,但在很多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少数民族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共生的,自然同人一样拥有生命。因此表达人与自然万物的亲近、将自然人化或是崇拜自然等都是各族文学很普遍的主题,像蒙古族文学中的马赞就异常发达。同样,虽则经历数次迁移,但达斡尔人的生活范围却从未离开大河大山与原始森林,表达对自然的礼赞也顺理成章。其特殊之处在于,诗人们更进一步,从山水中获得智慧和启发,山水也成为精神的体现物。
额尔古纳河是达斡尔族的母亲河。在诸多描写额尔古纳河的诗篇中,金荣久⑤的《观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感》就将诗歌的精神核体放到由观河而获得的启悟上。诗人首先感慨江河的流动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流注灌溉湖沟时毫无间歇、永不懈怠和没有疏漏是其表现,而“一切流量与流向/都似有自己特定的节奏”、“其调度的流速与流向/都似有自己的原故”则更让人惊奇大自然超越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这里,激赏江河“不变”中所享有的自主标示着,作者已无人类中心意识而有更为阔大的宇宙关怀。此外,水还象征历史变易和沧海桑田。诗人则表述为,“自古留下之遗迹/如水一样清澈/古代留下之江河/今日深浅变化谁能测”,其中包含着物是人非的体验,而流水“变易”与“不变”的双重属性更在于,多年前流水如何走向,今天也很难把握:“古代留下之江河/今日深浅变化谁能测”,若再作更深一层考虑,这种现象却又正如历史本身,在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变迁中,只留下人们对于历史的阐述,但历史本身已经不可追回地逝去。最后,诗人的诗思从历史转向了现实。比如诗歌写到最清廉的衙门,在其为政过程中事事明晰,“其清者也莫过于水”;最精明的商人,在顺势而为、变动不居这一特点上,“其精者也莫过于水”。所以如果衙门从政和商人经营若能从“水”中获得教益,则在其事业开展的过程中自然会如水般顺畅:“若能似水样清/便不会被抛弃/若得水之鉴/便不致有失意。”全诗行文至此既有鼓励之情,又有警世之义。这里,对水的哲理性观照来自于达斡尔人对人与自然关联性的认识:既然人和人生都是自然的一个部分,那么自然当然可以成为人生的象征或是隐喻。
因为生存之地河、水和泉的丰富,这些自然物象还在达斡尔文人哲理性观照的视阈中,成为自我存在甚至是人类存在的镜像。例如孟和博彦就以《小泉》叩问人的生存困境。小泉落在丛生的杂草间,河道规定着它的流速和走向,这便是小泉的“生之困境”,而这也是人类的“生之困境”——我们的生存,从来都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规定。诗人问“举止文雅、安详,心性平和、恬静”的小泉,“这一切似乎在表明,你对生的困境安之若素?”其实也就替读者问出了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问题,那看来文雅、安详甚至有些呆滞的外表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异化和逃避?
当然,人生存的意义还在于对个体自身和周围环境的积极反抗,这也正彰显了生命的力量。在诗歌接下来的部分,波澜暗生。或者说,诗人发现了小泉的另外一面:“在你幽邃的心底,/却蕴蓄着永不枯竭的热能。/你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地贡献着自己的/辛勤劳动。”而这也是达斡尔人甚至更多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以水滴石穿的平静与踏实应对生命的坎坷苦难,于无声处听惊雷。并且在赞扬小泉反抗生的困境的同时,诗人开始辩证地思考小泉的生存:那是一种带着镣铐努力起舞的状态。小泉在动和静、沉重和轻盈、柔弱和锋利、被动和主动这矛盾的两极之间回复往返:“你性格沉稳,/但却不时地为雄伟的森林之曲,/伴合着悦耳的奏鸣。/而你那涓涓的细流,/则又像把锋利的剑,/它披荆斩棘。”恰恰是在对矛盾对立的几重因素的统一协调中,纤细的小泉在困境当中奋发有为,而且柔韧不屈地达到了目标。生命体味与哲理思考借由小泉获得了定形,更重要的是,两者构成一个严谨完整的抽象思辨与形象感觉的抒情世界。
除了江河,山、鱼、各类植物也都成为意象,散布在达斡尔诗人的诗歌中,助益诗人哲思的表达。从敖拉·昌兴的《四季歌》、《百花诗》到钦同普的《捕鱼歌》再到孟和博彦《春的使者》,孟德苏荣的《山》,苏华⑥的《致向日葵》,晶达⑦的《白马》,慕仁⑧的《蹄音与嘶鸣》等等,自然启悟诗人的心灵,也凝聚着他们对生存的思考:当严冬也不过是“大地从容换新装”,其后是诗人对四季轮回不曾变易的认知;兴安杜鹃“怡然”地傲雪开放,内里是诗人对生命生生不息力量的赞许;山的岿然不改一再被孟德苏荣强调,源于它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特点,比如恒常和坚定,这表明诗人在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上把握住了山,而山此时也超越了物质生存层面的意义,成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在对“被动而无奈地等待日出”的向日葵的批判和对“驮着展翅的思想”的奔马的赞美中(《白马》、《蹄音与嘶鸣》),诗人表达着对自由自主的生命强力的热望。在达斡尔诗人笔下,自然山水作为客观对应物,为诗人的现实感悟和哲学沉思赋型。
二、从日常生活中体味哲理
与个体生命发生最深切、最长久联系的,往往是平淡日常的事物。李广田曾谓,“诗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现象中……那在平凡中发见了最深的东西的,是最好的诗人”⑨。近现代的达斡尔诗人也乐意于从生活中体味哲理,而日常生活情境笼罩在诗人沉思的观照中,化作诗人潜思生命万物的结晶。
比如玛玛格奇⑩的《赴甘珠尔庙会》和《在齐齐哈尔城看戏》,写的是达斡尔族生活中赶庙会、参加集会的事件。作为叙事诗,仅仅描绘庙会上的盛景就完全能让这两首诗成为达斡尔族社会生活的生动摹本。但诗歌的指向在更远更深处。《赴甘珠尔庙会》的超拔处在于写出进庙观礼所受之震撼与思考。诗歌首先详写甘珠尔庙的壮丽以及诵经声、海螺声所造成的威仪,如此情境之下,信众们甚至孕妇都虔诚到叩头进庙。但诗人紧接着就对信众的顶礼膜拜提出了质疑:人们对佛祖的礼拜和敬畏都源于对其有所求,抑或是弥补自身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反过来说,万物在被创制时,就已经有了差异参差,如果相信上天存在和万物被创制,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实是“容貌之美丑/岂能随愿得”!由此,诗歌显示出独立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于生活在藏传佛教极为盛行的时代和地区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也将诗歌的精神内涵推向了更为深邃的层面。《在齐齐哈尔城看戏》也独出机杼:在“看戏”的题目之下,诗人更多关注的却是观众中一个异常美貌的女子和她多舛的命运。当诗人感慨女子的配偶是一个放浪形骸之人时,发出的也就是青春所遇非人的深重感慨,并且这种感慨也并非只是针对着一个女子而言,当诗人无奈地说“如此命乖之女子/岂止她一人/试问天地间/般配的有几个人”时,就将个体遭际上升为人类性的普遍现象,而这种人性的或者说人类性的关怀,才是整篇诗歌诗意叙述中的精髓,命运对美好的捉弄亦让这首诗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达斡尔族的经济是多样化的,又因清朝时曾被编为打牲部,狩猎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构成。艰苦多险的生活催迫其思考自身和人类的命运。比如《狩猎诗》(金荣久),除了书写狩猎生活和经验,作者更在探寻达斡尔人奋力狩猎的目的和意义,并且由对达斡尔猎人狩猎目的的追索而转向对人生遭遇不同、结局不同的嗟叹。由狩猎中毫无猎获者“纵然不辞辛苦/也难免穷困/虽然一样劳累/也难免厄运/因为无所获/令人心寒而难振”而联系到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均是如此,付出未必就有回报:“阴差阳错者比比是/想样样达到等同/不知会到哪一世。”必须指出的是,与农耕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收获有关,农业文化培育出来的诗人恐怕很难有这种感慨,恰恰是狩猎的不确定性让诗人有如此思考。并且诗人的思索已经不仅局限于狩猎之事本身,而是深入到对人生其他事相的把握。这种穿越表层的思考让本诗把握到的不止是狩猎生活的实质,更是生活的实质。如此,这种感慨就跳脱出一己的悲欢而转向对世界上更多有类似遭遇的人的同情与悲悯,其忧伤也就深广悲怆。
读书在达斡尔人的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这个民族坚信能从知识当中获得哲理,《读书篇》(钦同普)就是一个确证。作为长篇叙事诗,该诗可谓作者的“上学记”,诗歌除了书写上学的事宜和心得,更在人生与存在的层面上考量知识的意义与作用。在诗人看来,人生是充满坎坷的,而在这路途中,“有富有穷/福祸相连/磨难重重”,尤其是如果踏上吸引无数人趋之若鹜的名利之途,就更是走上了“磨难丛生之险路”,难免摔得头破血流。但有了知识(四书五经),便有所不同:“若是学到了知识/可以防患于未然/若是精于此中理/应付自如免遭难。”可以说,“明哲保身”的最初意义即获得智慧而保全自身这一观点在这几句诗中得到了发扬。而当读书被放在应对生存的层面而非获得功名利禄的层面(如“书中自有黄金屋”)考察时,诗人的诗思也就获得了超越常人思考的深刻性质。并且,还必须指出的是,虽则其中可以看到儒家典籍对达斡尔人明显影响,但在这里,其功用已经被再造:如果说文化知识对儒家来说是“立德立功立言”的桥梁,那么近代的达斡尔诗人则是从存在的角度肯定知识与人生的联系。并且重要的是,在接受者对影响者的重释中,固然显示出某种联系,但更能见到由于不同民族的经验和智慧(包括面对生活不同)所造成的歧异。这种歧异值得珍视在于,它一方面揭示着达斡尔诗人精神思想的独特性,同时也标志出其思考的路向和深度,恰恰是这种歧异,才让诗歌呈现出属于达斡尔族文化特点的独特面貌。
三、反思民族历史
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现在都牵系其深长的历史。很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里都有英雄人物作为某段历史的界标,或成为标示该民族精神特质的象征。以诗歌书写民族英雄并进而追索民族历史、张扬民族精神是各少数民族诗人常见的诗学选择(11),达斡尔族文人诗歌也如是。在对历史人物的书写中,深潜着诗人对历史具有现代性的思考与认识。
当代诗人乐志德(12)是这一创作路向用力最勤者。他常用沁园春和念奴娇等词牌回望达斡尔族充满苦难和悲情的过往。比如《沁园春·祭桂古达尔人》,重现的是达斡尔人以弱抗敌的历史。执弓箭的桂古达尔人“为中华沃土,当年血战沙俄哈寇,寸土相争”,但沙俄侵略军拥有的却是枪炮等武器,不敌之下,自然渴盼作为中央军队的清兵相助,因为在其心中,中华一体。但“天兵何处,湖南征战”,居然无暇顾及外敌和外敌对达斡尔人的屠杀。诗人写及此、读者读至此一定是充满义愤的,然而,所有的愤怒仅化成了“只有烟云”四字。1500人的城寨只突围出15人,如此惨烈的民族战争往事用“只有烟云”概括时,也就字字千钧:其中既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悲愤,也有站在今天回望已经无法改变的历史的达观。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同样复杂难言的民族情感也隐约现出。接下来的两句“气贯长虹,光齐日月”与“天地悠悠难为春”是豪气与悲慨并举,但因其“难为春”,也才突出了桂古达尔城人宁死不屈、义薄云天的可贵。这里,诗人观照民族命运时,所居的文化立场既是本民族的,同时又有大中华的,执著中有开放而不困守;同时在看待民族历史时,则不以成败论英雄,超越了胜负的简单与狭隘。
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达斡尔诗人来说,反思民族历史仍然是他们的审美选择,但思辨性是其突出特征。比如高志军(13)的《啊!达斡尔族》,民族的苦难与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民族成长的关系被如此表述:“正因为撞碎过善良/才知道有比狐狸还狡猾的动物/正因为经历过曲折/才把嫩江汲成母亲的乳汁/正因为咀嚼过苦难/才把柳蒿芽当作佳肴美味……正因为孵化过希望/才祖祖辈辈在狼烟烽火中繁衍生息”——这里,诗人看待历史时的辩证思维以及由这辩证思维所生成的豁达深沉的情感成为诗歌的内在结构和主体情感,从而构筑出雄健的诗行。
而苏勇(14)《隆起的颧骨里》当中,思考则更为深邃,诗人深深忧虑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性格的丰富性被外界单一化:“有时显得多么单调,白桦树和木库莲只是一代人的背景”,诗人甚至直接宣布:“我们的形象不应该总是粗犷豪放,/一如我们绵长的故事。”挣脱“他者”——他民族甚至是整个世界对某一民族历史和现在的符号化、片面性的理解,这种问题意识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达斡尔族,其普遍性与现实性在于,它是世界上很多民族不断遇到的问题:总是被简单化地想象和揣测。并且对这一问题的书写其实来自于自身民族认同的焦虑甚至是民族身份的焦虑。而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其实从来都不是某一个民族自身的问题,它们往往与“他者”的理解、认同相关。这是诗人不断在诗中使用“我们”的原因:“他者”的价值体系以及如此尺度下的价值判断始终存在于诗歌当中,尽管诗人按下未表。在与“他者”判断趋同和求异的过程中,“我们拒绝的也接受了,不拒绝的也接受了”。但很可能与此同时,真正自觉的民族自我意识和形象也才在“总是粗犷豪放”的“误读”中建立起来,正如诗人最终意识到:“走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路……”这里,具体的困惑中讲述的是普遍性的问题,而诗人思考历史,则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如此,本民族作为具体形象的“接受”遭际延伸出广大的概括领域和漫长的历史跨度,诗歌内蕴因而具有了深广度和概括性。
四、冷峻的诗歌风格
对历史和宇宙的沉思赋予达斡尔族知性诗歌以冷峻的风格。这正符合中外知性诗歌的一般特点:经验的传达和思想的成分(对事物的凝视、思考和解剖)驱除了以情绪为诗歌中心的趋向。
其诗冷峻首先源于,达斡尔族文人诗歌多带着生活本身的生动和沉重。与中国古代玄言诗谈空说有的渺远不同,达斡尔族文人诗歌从本民族的生活和大地上茁长起来,其哲理思考与民族的现实及历史互为表里:自然山水、捕鱼、养马、狩猎、商贸等生产生活活动包括宗教崇拜都与个体的生死、命运和际遇息息相关,因此这些物事激发的不是诗人波澜起伏的情感,而是明澈深邃的理性思考。并且与达斡尔族人口较少、长期与他民族、他种族杂居或是相邻而居的生存现状相联系,这种思考所指向的,往往不是个体的际遇和悲欢,而是带有明确的族群意识。《赴甘珠尔庙会》中,“众人”一语时常出现,而对“当地蒙古人”和“库伦蒙古人”脸型、举止的描绘也揭示出诗人的归属感。钦同普的《读书篇》、《酒戒》、《色戒》、《气戒》等诗中,其预设的读者都是“世人”、“活在尘世的凡人”等。而“达斡尔”也成为很多诗人写作的共名。这一共名也让诗人落笔时自然带些肃穆的气度和客观化的语气,诗歌凝结的自然就不是个人情感的颓丧自白,而是充满理性的人生沉思。
知性诗歌并非无情之诗,而是其情感抒发和表现形态有自身特点。这正是很多达斡尔文人诗歌中的情感:不是浓烈繁华、倾泻而下,而是和哲理融成一片,蕴藉而出。在表达时,诗人常以理智节制情感,形成冷静的情感类型。与蒙古族的勇武剽悍不同,达斡尔族的性格特征更多表现为坚韧强劲。因为所居地理位置的特殊,他们数次迁徙流离,而在与沙俄政权和清朝政权周旋的过程中,则忍辱负重。因而诗人表达悲欣时有一种不事张扬的隐忍和世事洞明的豁达,文字上便喜怒不形于色。另外,近现代的达斡尔文人诗歌亦是可以传唱的文人乌春,乌春的调式较为平缓自然,为配合演唱,也会潜在影响诗人的创作,像《捕鱼歌》(钦同普)就言“编成歌儿供君知”。当然,儒家典籍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对儒家诗教哀而不伤的认同也易造成静定之气。可由于与达斡尔族生活几乎是血肉般的联系,达斡尔族文人诗歌中没有儒家传统诗教下易出现的超脱出世之风,而是带着大地般的凝重忧郁,当贡貂的艰难、大旱的焦虑、跋涉的艰辛、世间的不公、民族的悲情、战争的酷烈等成为诗歌的背景、底色乃至诗本身时,也就造就了诗歌的质地和张力。而这种有别于其他民族诗歌的冷峻,以及造就其冷峻的理性和沉思,也就标志出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的个性特征。
当然,言达斡尔诗歌具有知性特征并不意味着达斡尔族文人诗歌是知性诗歌。如将其放到近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乃至世界知性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就能发现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知性可能是很多达斡尔族诗人自然和自觉追求,但不一定是非常成熟的创造。尤其是思考复杂深邃的人性内涵和存在意识,探究生命个体潜意识等内宇宙空间的诗歌还不多见。而某些知性诗歌常见的主题,如孤独、爱与死、个体的挣扎等也只有少数诗人如孟大伟(《樱桃红了》)和晶达(《润土》)涉足。此外,就诗歌艺术手法而言,隐喻、象征往往是创造知性诗歌的重要手段,如何通过比喻和联想让哲理在与象征意象的联结中暗示出来,而非“卒章显其志”式地表达,仍是达斡尔族诗人在诗艺上需要关注的。但如诗人郑敏所言,“诗歌可以浓妆艳抹,也可以凝练隽永。只要它能将人的心与宇宙间万物沟通起来,使他领悟天、地、自然的意旨,有一次认识的飞跃,也就得到了审美的满足。这样的诗就是我心目中的好诗,因为它将我封闭狭隘的心灵引向无穷变幻的宇宙。”(15)这恰好说明了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的基本特征和价值。
①这里的文人诗歌作为书面文学与民间传唱的乌春相区别。
②钦同普(1880-1938),目前可认定有《捕渔歌》、《伐木歌》、《耕田赋》、《读书篇》、《酒戒》、《色戒》、《财戒》和《气戒》等文人乌春8篇。
③孟和博彦(1928-2006),诗人和评论家。有《孟和博彦评论集》及《孟和博彦文集》行世。
④孟德苏荣(1932-2004),也写作门都苏荣,诗人和学者。有《北斗星》、《万年灯》等诗集出版。
⑤现存《狩猎诗》、《观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感》和《即兴诗》等都是金荣久的代表作。
⑥苏华(1957-),女,笔名娜迪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开始创作。
⑦晶达(1986-),女,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2003年开始发表作品。
⑧慕仁(1966-),笔名静欣。1988年开始诗歌散文写作。
⑨参见李广田的《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载于《诗的艺术》,第71页。
⑩玛玛格奇,也写作玛莫格奇,约为清代同治到光绪年间人。
(11)如蒙古族叙事诗《嘎达梅林》、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等。
(12)乐志德(1935-),诗人和达斡尔族文化研究者,有作品集《万里雪飘》(民族出版社,2005年)。
(13)高志军(1962-),诗人,中学校长,诗歌多次获奖。
(14)苏勇(1960-),1982年开始创作,有散文诗集《木库莲声》(远方出版社,1995年)。
(15)参见郑敏的《探索当代诗风——我心目中的好诗》,载于《诗探索》,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