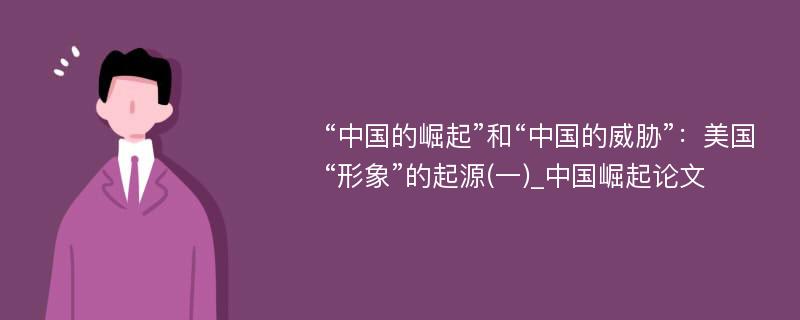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美国论文,由来论文,中国崛起论文,中国威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国崛起”伴生而来的“中国威胁”,常常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和不满。为什么“中国崛起”在美国必然产生“中国威胁论”,这不能简单以美国人有敌视中国的情绪或者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来进行解释。“中国崛起”不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从理论到实践都必然产生的深刻历史问题。“中国崛起”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崛起如果继续的话,将是21世纪世界最重要的趋势”。(注:Nicholas D. Kristol, "China's Rise," Foreign Affairs,Vol. 72,No. 5 (November/December 1993),p.59.)正是由于“中国崛起”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其背后又存在广泛而又深邃的理论、政策、观念和价值问题,才使“中国崛起”的过程会不断催生各种看法和争议,并带来各种政策反应和战略性的调整。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今天国际权力结构中唯一的主导性国家,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的本源不在于美国特定的政策传统,而在于它和崛起中的中国在国际关系系统结构中的特殊关系。(注:有关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崛起的中国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关系的最新理论论述,参见Barry Buza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 G.John.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John J.Mearsheimer,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 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然而,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image of China threat)远比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主义解释要复杂得多。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形成和发展,客观上是一个价值驱动、政策驱动和利益驱动“三合一”的过程。
本文在综合各种文献研究、政策分析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力图能对“中国崛起”伴生而来的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并从国际关系基本的理论争论、价值和美国人“中国观”的内涵出发,对“中国威胁”论的思维特点和结构进行探讨,以期提供中美关系及中国与世界互动过程中我们认识外在世界的一种方法和理解。
一 “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伴生的基本原因分析
对中国崛起的最大争论是这一崛起过程是否会对地区和世界造成不可避免的威胁,从而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并引发难以控制的大国冲突、甚至战争。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结论并不是由“中国经验”产生的,而是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来的,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和认识权力关系的基础内容。“中国崛起”如果能够真正走出一条和平的道路,显然,这代表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经验的颠覆。正因为如此,中国崛起才具有如此重大的震撼力,从而使得围绕着这个命题的争论可能还仅仅是刚开了一个头。
中国崛起的另外一个争论的动因,是美国强烈感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对其现有霸权地位和利益的冲击。这种利益驱动的关注远比理论驱动的争论复杂和尖锐得多,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当政者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应,也涉及到西方政府在价值上对中国的排斥。因而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争论背后,有着出于保护私利需要而对中国未来的警觉的难以掩饰的价值动机。
1993年围绕着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PPP)标准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出现的中国经济实力排行世界第三位的报告,以及欧佛霍尔特(William H.Overholt)对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的断言,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波的中国威胁论。(注:William Overholt,China: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3).也有人提出,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亚洲的经济产值将超过欧洲和北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参见Urban C.Lehner,"Belief in an Imminent Asia Century Is Gaining Sway?" Wall Street Journal,May 17,2003.)最开始的这两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都对中国的未来持积极的看法。(注:例如,Overholt强调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将对世界经济政治都有建设性的贡献,而不太会成为潜在的危险。William Overholt,China: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pp.351~354.)但《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Kristof)在1993年《中国崛起》一文中,提出了两个理论性的命题:一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必然要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更多的权力;二是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内在特点不稳定的国家,如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很强,但一直深受西方伤害,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一直有被排挤、欺负和受伤害的“巨人的痛苦”(annoyance of a giant)。(注:Nicholas D.Kristol," China's Rise," Foreign Affairs,pp.70~72.)克里斯托夫的结论仍然认为中国将来不太可能是一个“侵略性的、不负责任的国家”。
然而,世界银行报告的惊人数据、欧佛霍尔特对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大胆预言和克里斯托夫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在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三份材料最大的震慑力,是它们描绘了一个将在经济实力、甚至整个国家能力上与西方“平起平坐”、在同一力量水平上竞争的中国。这使陶醉在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的喜悦中的美国,突然要面对一个“历史远远没有终结”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美国朝野在“政治倾向”层次上产生的“中国威胁”看法,成为主导90年代美国有关中国问题辩论的最主要的分野。(注:为何在美国“政治倾向”会产生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如何主导“中国威胁论”,请参见Denny Roy,"The 'China Threat' Issue: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Vol.71,No.12(December 1996),pp.758~771; Thomas 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but not Buck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 (Spring 2001),pp.1~34.)
在1993年,“中国崛起”还并非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只能说是中国发展的强劲势头所带来和展示出的某种潜力。“中国威胁论”接踵而至,最重要的原因是受1989年“六四事件”的影响,美国的“中国视角”普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六四事件”使中美两国人权和制度对立问题在美国的中国政策中尖锐化和模式化了。虽然老布什政府在“六四事件”之后仍竭力想要推行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但美国国会、媒体和人权组织都强烈要求白宫说明人权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基本定位。(注:参见Harry Hading,The Fragile Relationships:US-China Relations since 1972 (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2),pp.58~65; Robert Mann,About the Face; Roger W.Sullivan,"Discarding the China Card," Foreign Policy,No.86 (Spring 1992),p.21.)人权问题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中国威胁”论也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多样化的利益背景和多元化的利益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常常在中国问题上有相当不同的看法,美国国会又需要不断制造理由来干预白宫的中国政策,美国舆论更是把中国问题视为表达美国人民看法的重要领域。中国威胁论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必然产物。(注:有关9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对中国政策的作用,请参见Robert G.Sutter,U.S.Policy Toward China:An Introduction to the Role of Interest Groups (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lishers,Inc,1998); Kenneth Lieberthal,"Domestic Forces and Sino-U.S.Relations," in Ezra F.Vogel,ed.,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st Century (New York:Norton,1997),pp.254~276.)
其次,很多美国人、包括政治精英都对中国所知甚少。美国公众和政治人物的对中国的看法经常在两个极端上摇摆。要么是尼克松访华后在对苏冷战的时刻,美国人突然对中国有一种多了个“帮手”的天真、简单的同情和好感,要么就是1989年后一边倒地认为中国是一种“邪恶”。这种对立的、非常极端化的中国观直到90年代中期都没有改变过。(注:有关美国人的中国观念的两极对立,请参见Nancy B.Tucker,"China and America,1941~1991," Foreign Affairs,Vol.70,No.5 (Winter 1991~1992),pp.75~92; David Shambaugh,"Patterns of Interaction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eds.,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97~223.)大多数美国人之所以不了解中国,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并不重要,以至于中国问题在向来以功利主义著称的美国没有多少需要曝光或者认真看待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从一开始,在美国人看世界的“余光”中,中国就是一个落后、神秘、古怪和另类的国家。这种印象几乎根深蒂固。(注:专门介绍美国人中国观的专著,请参考Herald R.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John Day,1958); T.Chr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美国人总是自以为是地按照西方的制度原则和社会结构来判断和衡量中国,按照美国人所认知的“常理”(conventional wisdom)来认识中国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偏见很深的人士就直接叫嚷“中国威胁”,而严肃的学者至少认识到中国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中国能否顺利进入“后邓小平时代”、平稳渡过权力交接,到中国的内在社会关系紧张将如何克服,以及中国未来做什么样的政策选择,等等。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并不必然就是“威胁”,但“威胁”至少是很有可能的一种结果。(注: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参见Richard Baum,"China After Deng:Ten Scenarios in Search of Reality," China Quarterly,No.145 (March 1996),pp.153~175; Robert G.Sutter,China in Transition:Changing Condi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Washington,D.C.,CRS Report no.93~1061 S,1993; Maria Hsia Chang,"China's Future:Regioanlism,Federation,or Disintegr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September 1992,pp.211~227;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S.Ross,The Great Wall and Empty Fortune (New York:Newton,1997); Ezra Vogel,eds.,Living With China (New York:M.E.Sharpe,1997).)他们从西方学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角度出发,同样难以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准确和积极的勾画与预判。如沈大伟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磨损”,犯罪直线上升、年轻人异化、知识分子反叛及“拜金主义”盛行,国家权威的下降和道德水平的堕落是根本原因。(注:David Shambangh,"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2 (Fall 1996) ,pp.180~196.)然而,这些问题事实上也可以解释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个人权利自由和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不同的政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内局势的判断。
从对中国抱有偏见角度出发,这些变化不仅被视为是中国政局和社会动荡的表现,更是中国对外政策有可能受国内危机影响而变得更具有“威胁性”的前兆。为此,鼓吹“中国威胁”的有些学者甚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要么认为国内关系的紧张将使中国崩溃在所难免,所以一个“即将”崩溃的中国的威胁性也就自然降低了;要么从中国的强大的“威胁论”转向中国“衰落”的“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崩溃同样将给世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至少中国未来的前景存在很大脆弱性,中国对世界的威胁始终都难以消除。(注:David Shambaugh,"China's Fragile Future," World Policy Journal,Fall 1994,pp.41~45; Gerald Segal,"China Change Shape",Foreign Affairs,May 1994; David S.Goodman and Gerald Segal,eds.,China Deconstructs (London:Routledge,1994); Gerald Segal and David S.Goodman,China Without Deng Xiaoping (Melbourne and New York:ETT,1995 ).)在这些人看来,即使没有可靠证据显示“中国威胁”,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威胁论”也被夸大,但并不等于中国不是“威胁”。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最好的结果无非是成为一个“二流的中等强国”(second-rank middle power)。(注:Gerald Segal,"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Vo.78,No.5 (September/October 1999),pp.24~36.)西方国家不需要太把中国当回事,只有这样中国才会认真实行“西方希望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注:参见Gerald Segal,China Changes Shape,Adelphi Papers,No.287,London:IISS,1994.)这种从所谓西方人的“常理”出发来认识和判断中国问题,当然难以避免扭曲和偏差。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指出,美国人要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最好是首先改变他们所通常认为的“常理”。(注:Yasheng Huang,"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 Foreign Policy,Summer 1995,p.68.)
90年代中国威胁论观点的第三个特点、或者说是第三种状况,是基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展不确定的现实而产生的“威胁意识”。这是一种立足于美国自身利益、需要寻找到美国和西方世界面临的下一个敌人,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能更好地有所准备而在思想上做出的必然反应。在美国冷战后将要面对的不确定世界所产生的新威胁中,无论是在安全理论上还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新定义上,中国都是一个不可能漏掉的、最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威胁的对象。
冷战结束后,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美国来说有太多不可知因素。因为冷战结束得太快,美国还来不及为国际体系的过渡做好准备。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言,“冷战的结束,把美国推到了一个似乎还缺乏存在一个重要的敌对大国的世界,很明显这也给美国人提出了谁将是美国最重要的敌人这样一个只有少数人准备好回答的问题。”(注:George F.Kennan,Around the Cragged Hill: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W.W.Norton,1993),p.180.)在1992年美国大选中,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是美国政治评论员诺曼·奥斯坦因(Norman Ornstein)提出的问题:“什么应该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在一个已经不再有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世界上应该做的事?”(注:Norman Ornstein,"Foreign Policy and the 1992 Elec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1,No.3 (Summer 1992) ,pp.1~16.)在只有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世界里,美国的战略终究应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困扰美国的话题。这种困境正如基辛格所言,“失去了需要与之奋战的敌人之后,美国就像‘飘荡在新世界汪洋中’,比曾经历的20世纪任何时期都要安全,但却没有了要去完成的使命。”(注:Henry Kissinger,"At Sea in a New World," Newsweek,June 6,1994,pp.6~8.)
为此,美国一方面积极着手制定冷战后新的全球战略,继续维持与巩固美国在单极世界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则开始寻找新的“敌人”。在相当一部分人美国人看来,无论是拒绝民主化进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特点,还是缺乏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军控与裁军制度的热情,中国都是美国潜在的最重要的“敌人”。虽然在官方政策上,美国仍然维持了对中国一种模糊的“非敌非友”的关系,(注:对90年代初中美之间这种“非敌非友”关系的论述,参见Harry Harding,The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S.-China Relations since 1972.)但美国的东亚地区安全战略的调整,很快围绕为了防范和遏止中国这个最有潜力的“敌人”而进行的。
首先,在地区安全方面,美国认为“后霸权时代”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出现一个在区域层次上对美国利益的直接挑战者。随着两极体系的崩溃,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两极体系的崩溃导致美苏全球战略对抗结束的同时,在区域层次上留下了新的权力真空。如果出现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那样的地区性扩张国家,不仅排斥美国的利益,而且也将实质性地伤害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这种新挑战者出现的过程,就是美国的战略研究者们所说的“地区层次上的多极化过程”。如果美国无法对这个过程加以有效遏止,新的活跃的地区力量将必然把挑战的矛头指向美国。即使不和美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地区性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过程,也必然是损害美国既得利益的过程。(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最有代表性成果有:Thomas J.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 (Spring 1990),p.168;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 (Summer 1990),pp.5~56; Richard Ullman,Securing Europ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美国的基本对策是一方面在全球进行战略调整。由于不再需要面对前苏联的战略压力而保持前沿战略力量对峙,美国开始减少在欧洲的驻军,撤走在欧洲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关闭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降低在亚太地区的驻军规模。另一方面,美国继续保持和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体系,维持前沿驻军,加强对如中东地区的全球战略节点地区的军事存在,通过重新对欧洲和亚洲承担安全义务的方式,一方面继续保持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网络体系,保证美国能随时介入和干预地面冲突,继续实行冷战时代能够同时打两场战区战争的防务力量配置;另一方面,用威慑和防范新的地区安全的挑战以防止出现针对美国的地区层次上的军事和战略挑战。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重组过程中,中国是美军主要的防范对象。而在东亚,中国更是美国军事和战略力量的首要对象。现任美国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助理的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兰·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90年代初就曾断言,美国是否能继续成为亚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能继续将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投射在亚洲地区。(注:Aaron 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 (Winter 1993/94),p.7.)
自克林顿政府起,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开始确立为防止出现一个新的如前苏联那样和美国具有同等竞争力的军事力量,并能与美国在同一层次上较量的“同辈竞争者”(peer competitor)。美国认为,中国不仅是最具有潜力成为这样的战略竞争者,而且与西方或东方同样具有潜力的竞争者相比,中国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国家。例如,在后冷战时代有关欧洲政治走向问题的探讨中,多数学者都反对欧洲将重新回到不稳定的多极时代的论点,认为欧洲国家特点的变化、欧洲一体化进程所形成的欧洲传统大国之间制度化的紧密联系,以及战争在成本和收益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使欧洲即使继续强大,但也不会让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重新堕入强权竞争的多极化的、不稳定的过去。因为这些欧洲大国都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典范,有着成熟的权力制衡机制,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已经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欧洲联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注:对欧洲新战略和政治特点的研究,参见Stephen Van Evera,"Primed for Peace: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3 (Winter 1990/91),pp.7~57; Robert Jervis,"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3(Winter 1991/92),pp.39~73; Jack Snyder,"Averting Anarchy in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4,No.4 (Spring 1990),pp.5~41; James M.Goldgeier and Michael McFaul,"Core and Peripher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 (Spring 1992),pp.467~491; Stanley Hoffmann and Robert Keohane,"Correspondence:Back to the Future,PartⅡ: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ost-Cold Wa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2 (Fall 1990),pp.191~194.)这些欧洲变化的新因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通常也被称为是“非结构因素”,它们同样能说明强国的兴起并不必然导致不稳定和冲突。
然而,当美国的学者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审视中国问题的时候,却无法得出他们对欧洲冷战后未来的同样结论,也无法将亚洲与冷战结束后的欧洲等同。换句话来说,美国学者对欧洲和亚洲进行比较研究,对亚洲所得出的结论相当悲观,认为冷战后支撑美国对欧洲有乐观看法的经验和理论依据完全无法适用于亚洲。(注:这一方面的典型论述,请参见Aaron 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Robert Jervis,"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Gerald Segal,"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96; David S.Goodman and Gerald Segal,eds.,China Rising:Nation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London:Routledge,1997); "How Insecure is Pacific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2,No.2 (April 1997); "The Asia-Pacific:What Kind of Challenge?"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Routledge,1998).)因为在一个两极体系对抗的主导因素突然消失的亚洲,地区各国必然为了财富、威望和权力展开新的权力角逐,包括进行军备竞赛、在领土问题上威胁诉诸武力而极可能引发新的地区冲突。(注:Richard K.Betts,"Wealth,Power,and Instability: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 (Winter 1993/94) ,pp.34~77; Robert Taylor,Greater China and Japan:Prospects for an Economic Partnership in East Asia (London:Routledge,1996),pp.178~184.)失序的东亚局势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种本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这时面临着要么“选边”、进行干预性的战争,要么随着地区强权的崛起、面临着自己被“逐出”亚洲的命运。而这两点都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避免这种困境出现,美国必须继续维持在东亚的驻军和军事同盟关系,通过在战略上遏止中国威胁”和重新承诺对东亚的地区安全责任。
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向冷战时代过渡,从一开始就是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尽管美国和日本在贸易摩擦和经济竞争上存在冲突,但美国认定日本是一个“瘸腿”大国,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及宪法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限制,让日本无法单独发展成有效制约中国的独立战略力量。特别是中国基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对日本的“不信任”,一旦美国无法对所谓“中国崛起”保持美国一马当先的战略戒备,美国在东亚战略势力的弱化将会直接引起中日之间的冲突而使美国面临更大的消极后果。(注:对于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战略分析及由此而对美国东亚战略的影响,参见Steve Chan,East Asian Dynamism:Growth,Order and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Region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 Aaron 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Thomas Christensen,"Beijing's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Vol.75,No.5(September/October 1996) ,pp.37~52.)而美日在价值、制度和利益上的高度一致,更让美国认为日本是其在亚洲保持战略利益的“命定的帮手”。但由于日本的军事崛起无法得到亚洲邻国的认同,因而除中国外,美国在东亚找不其他潜在的、有份量的战略对手。(注:Gerald Segal,"Coming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orld Policy Journal,Vol.10,No.2 (Summer 1993); Denny Roy,"Hegemon on the Horizon: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 (Summer 1994),pp.149~168.)美国所关注的朝鲜和台湾问题也都和中国直接或间接有关。中国不仅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军事力量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工业支持,而且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似乎表现出了“侵略性”的势头,因而被美国解读为“既有对外动用武力的力量和意志”、又能让亚洲邻国对其动用武力而保持“沉默”的国家;(注:Michael G.Gallagher,"China's Illusory Threa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 (Summer 1994),pp.169~194.)并且,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安全努力从根本上就是要排斥美国的存在和打击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注:David Shambaugh,"China'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urvival,Vol.34,No.2(Summer 1992),p.89.)冷战后中国在东亚战略结构中地位总体上升的趋势和中国的“反美”战略意图,而被美国称为“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东亚霸权国家”。
通过把中国定义为美国在东亚最大的“战略性威胁”,对美国政府来说至少有4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说服东亚民主国家继续团结在美国的周围,维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使美国在东亚继续保持强大的前沿驻军,保证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侵害和排斥;二是保证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避免被任何东亚国家或者东亚国家的联合而“边缘化”,甚至逐出亚洲。这就需要美国在战略上遏止中国这样的“地区强国”;三是符合美国冷战后继续在东亚和全球推动民主进程的需要,在对中国保持强大的战略和政治压力的同时,通过鼓励中国的经济开放实现中国政治向民主转型的目标;四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凝聚美国公众的价值和意愿,减少美国东亚政策在国内政治中所受到的批评。说到底,“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充分反映出美国冷战后的东亚战略重建需要首先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战略要求。“如果美国无法清晰地划定敌人和阵营的区别,任何战略的调整都无法完成”。(注:Michael Cox,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Superpower without a Mission?(London:Chatham House Papers,1996) ,pp.100~101.)
二 中国威胁:国际关系理论“问题”?
由于“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根源是所谓大国崛起必然带来权力转移及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论证的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变化必然导致冲突的结论,90年代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在讨论“中国威胁论”这个命题的时候,一直是一个矛盾和争论的过程。但这些具有学术和理论特点的认识,同样是美国“中国威胁意象的基础。不了解这些认识,客观上无法了解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的形成和发展。
1.制度/结构论
美国人无论是从民主意识形态还是从冷战的经验,都自然而然地认同那些和美国人一样摆脱专制和享有自由的国家,而冷战的体验又使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像斯大林式的苏联和法西斯德国那样具有侵略性。因此,他们将“六四事件”的中国与这些国家等同起来,相信所谓的中国“制度决定论”的侵略性。这种制度决定论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典型逻辑是一国政府“在国内如何对待其国民”就会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注:Jim Hoagland,"Simply China," Washington Post:National Weekly Edition,June 12~18,1995,p.28.)即使没有实际的事例证明中国是一个会“侵略别国”的国家,但他们也这样相信。这是基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认识而产生的典型的“中国威胁论”的依据。(注:Ezra F.Vogel,ed.,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Norton,1997),p.29.)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毫无例外地都将中国视为是一种“威胁”,但至少大多数美国人根据民主与否的标准在意识深处不认同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的事实,为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土壤。
站在西方立场上认为中国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特征必然对西方构成挑战,并很可能引起未来与西方冲突的最具极端观点是亨廷顿(Sammuel Huntinston)的《文明的冲突》。他认为未来“文明—意识形态”差异将是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原因。(注:Samuel Huntington,"Cr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2,No.3 (Summer 1993),pp.22~49.)这种用冷战对立模式在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观点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中国究竟是对邻国的威胁、还是变成美国的敌人,从而成为全球秩序的“系统性的挑战”,这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注:David Shambaugh,"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 p.180; David Shambaugh,Political Dynamics in Transitional China: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arlisie Barracks,Penn:U.S.Army War College National Strategy Institute,1996),p.23.)在这一波的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中,中国国内状况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关注的重点,而只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及政治结构特点的主观臆断。谈论中国威胁的,大多是美国研究中国外交和国际政策的专家,很少有专门从事中国内政研究的学者。(注:有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状况的学者,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将使中国的外交政策趋向温和。Michael D.Swaine,China: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Santa Monica:RAND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1995 ).)而一些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的美国人,更是从他们对中国的肤浅认识出发,提出“中国最有可能采取的制度形式是一种“集合性的(corporatist)、军事化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在相当程度上类似于墨索里尼统治时期的意大利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那样的法西斯国家。”(注: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n," Foreign Affairs,Vol.76,No.2 (March/April 1997),p.29.)
与此同时,有部分美国学者相信,中国“非民主”的政治制度不仅源自所谓“一党专制”的意识形态,也来自于中国威权体制背后的政治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皇权至上”等封建思想和中国人的政治理解都会继续让中国维持一种“帝国式”的权力统治的方式,而不是去追求建立在鼓励社会力量多元化和个人权力基础上的多元主义的民主政治。中国依然还有2/3的地区被少数民族、而不是被汉族居住的现实,更让中国维护“帝国式”的统治方式非常必要。(注:Ross Terrill,The New Chinese Empire:Beijing's Political Dilemma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Basic Books,2003 ).)他们认为,90年代上半期中国面临权力交接的问题,而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来看,权力交接和接班人的选拔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政权更替”将会像前苏联那样将中国的政治结构“拖入到”新的权力争夺的漩涡,从而进一步阻止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种认为中国政治结构的特点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观点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非常普遍。(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参见Arthur Waldron,"China's Coming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Obis,Winter 1995,pp.19~35; David M.Finkelstein and Maryanne Kivlehan (Armonk:M.E.Sharpe,2003).)而另外一种对中国制度的分析是,中国的民主化会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而中国的政治精英没有意愿、也害怕承担民主化进程所招致的权力和威望的损失。(注: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Vol.76,No.2(March/April 1997),pp.26~29.)在他们看来,民主和平论对解释中国的未来战略动向几乎毫无用处。另外一种极端的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理解是,权力斗争使中共权威受损,军队因而会重新成为权力的实际中心,历史上的“军阀”割据将重新上演。至少,军队可能会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单位。(注:Arthur Waldron,"Warlordism versus Federalism:The Revival of a Debate?" The China Quarterly,March 1990,pp.116~128; Michael D.Swaine,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Leadership,Institutions,Beliefs(Santa Monica,CA:The RAND Corporaion,1993); Arthur Waldron,"China's Coming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7,p.25.)
另有学者则从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来解释中国政治威胁的理由。他们认为,经济改革已经使得中国出现了“去中央化”或者“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过程,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抗拒正在扩大。中国政府为了保持权力控制,继续不断地加强干预和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其结果是中国经济不仅不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不会真正走上西方想要看到的“政治自由化”的道路。(注:Margaret Pearson,Joint ven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 Hornik,"The Muddle Kingdom? Bursting China's Bubble," Foreign Affairs,Vol.73,No.3 (May/June 1994),pp.28~42; Jack A.Goldstone,"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Summer 1995,pp.35~52; David Zweig,"Developmental Communities' on China's Coast:The Impact of Trade,Investment,and Transnational Alliances," Comparative Politics,April 1995,pp.253~274.)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特殊的结构形式,让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会带来尽快的民主变化。
从上述对中国国内政治发展所持的极端主义观点来看,中国是一个“强大”但“不稳定的、不满意现状的、常常在国际共同体之外行动的修正主义”性质的国家。(注:Gerald Segal,"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5 (September/October 1999),pp.24~36.)即使在温和的学者看来,由于中国国内政治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显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此期间国内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内在紧张,有可能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导致中国对外行动的攻击性。此外,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是高度集中的、缺乏有效的信息提供和高高在上的(insularity),因此,常常在“真空”里决策,幕僚及利益集团的作用都被压缩到最小限度,缺乏灵活的政策选择。(注:David Shambaugh,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s,p.201.)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一外交决策机制难以保证其政策选择是温和和务实的。美国前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erald Brown)认为,未来中国究竟是一个“合作性的角色”(cooperative player),还是国际关系中“愤怒的民族主义的破坏者”(angry nationalistic disruption),这取决于未来中国领导制度的性质。(注:Herald Brown,"Preface," in James Shinn,ed.,Weaving the Net: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1997),p.x.)
2.理论/经验论
有美国人提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历史上大国的经济发展毫无例外地都带来了政治影响的扩大,并进而通过追求军事力量的强盛来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如英国于1588年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取而代之成为此后300年间国际关系的新霸主;法国的崛起也产生了拿破仑战争,德国在19世纪后期的崛起则将世界带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国主义的日本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的强大把世界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对峙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两国在战争中迅速膨胀的国内经济和军事力量。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FK Organski)根据现实主义分析方法,将这种大国的力量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会扩散到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历史经验,概括成了“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理论。(注: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 (New York:Knopf Publishers,1968).)这一理论后来经奥根斯基教授和他的学生一起共同进行了修正和发展,成为解释国际关系中大国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扩张性的权力追求、进而产生新的权力冲突,并导致不稳定、甚至战争的基本理论。在理论的层面上比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更为彻底、更有说服力的对大国崛起的不稳定、甚至战争作用的解释,是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该书是从体系结构的角度说明为什么国家间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很可能招致大国冲突的最权威的作品之一。它从理论上总结了崛起的大国为何会成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挑战将以何种方式进行、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如何应对、现有的国际合作要素为何难以阻止“挑战者”与“主导者”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注: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相对来说,吉尔平的理论在结论上要乐观得多,他并不认为国家间为了权力、威望和财富的纷争完全无法避免最后的冲突和战争。为此,他随后潜心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就是要通过了解权力追求与财富追求之间动态互动来找到破解非和平方法解决国际冲突的路径。(注: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在吉尔平看来,经济民族主义是引发国际经济系统中权力分散化,进而威胁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注: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406.)
如上所述,大国崛起的非和平历史、国际关系理论中大国崛起必然导致新的权力分配从而引发冲突的观点,是一些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解释现实和未来“中国威胁”的一种普遍的理论和历史依据。
3.能力/意图论
“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论据是所谓中国挑战美国的能力和意图问题。在能力问题上,美国人的直觉是“中国崛起”给中国带来了可以挑战美国的“能力”,因此“中国崛起”等同于“能力崛起”。无论是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积极、温和立场的分析人士还是对中国的发展非常有偏见、甚至敌视的观察家,都普遍相信,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带来其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必然将使中国在自己的边界之外追求和行使权力。问题是在于,中国究竟以什么方式在更大的权力基础上扮演自己的国际角色?这种不确定性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例如,有美国学者认为,一个脆弱的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不可能承担战争所需要的经济代价。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开始有能力追求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中的海外投掷力量,这就构成了可以挑战和威胁美国的能力基础。虽然多数学者不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足够挑战美国的能力,(注:Robert S.Ross,"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Vol.76,No.2 (March/April 1997),pp.33~44;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W.W.Norton,1997); Michael O'Hanlon and Bates Gill,"China's Hollow Milita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0.)但美国“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认为,首先,中国现在没有能力威胁美国,但并不等于未来没有;相反,中国发展的势头证明中国未来这样的能力是可以期待的。其次,从美国利益出发,美国只有“坚实地拥有经济的超强地位和金融的强大,美国的霸权才不会受到任何真正的威胁”,即使中国崛起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削弱美国霸权的能力,这样的中国同样也是一种“威胁”。所以,从能力角度出发的“中国威胁”论非常敏感,其采取的对策从美国继续加强在东亚地区的驻军、加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巩固军事同盟与伙伴关系,一直到美国从经济上强化出口控制机制、阻止所有敏感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美国国会设立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就中美经济合作是否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进行评估、美国国会要求五角大楼每年提交中国经济力量的评估报告,到2005年修改能源法阻止中国石油公司并购美国能源企业等诸方面。
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分析上,美国的看法是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而改变。有学者认为,中国是要通过军事扩张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还是愿意认可现有的秩序和游戏规则进而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很难预测。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但对“相互依存、对国际制度和规则仍然相当抵触”。(注:Michael Oksenberg,"The China Problem," Foreign Affairs,Vol.70,No.3 (Summer 1991),p.10.)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愿意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但只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不会是一个“规则的接受者”。中国的领导层对西方官员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高傲和无知非常地憎恨。(注:Kenneth Lieberthal,"A New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Vol.74,No.6 (November/December 1995),pp.38~42.)中国对外政策强调“强权政治”(realpolitik),追求力量和力量间的平衡是其基本理念和手段。(注:Charles Krauthammer,"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July 31,1995,p.72; Alastair l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Thomas J.Christensen,"Chinese Realpolitik.")特别是基于历史上对日本的不信任,中国一定会大力发展军事力量来应对日本的重新武装,并在台湾问题上出于民族自豪感对台独倾向继续采取军事威胁的方法。虽然这种“强权政治”的思想并不能说明中国必然有挑战美国的“意图”,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美国观察中国“意图”的一个重要视角。美国的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未来的“战略意图”是“可变的”、“流动的”。(注:Robert S.Ross,"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Vol.76,No.2 (March/April 1997),pp.33~4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存在很强的反美主义,其长远的战略意图就是要将美国“赶出”亚洲。(注:Arthur Waldron,"Deterring China," Commentary,Vol.100,No.4 (October 1995),p.18; Kristof Bernstein and Robert Munro,"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美国即便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也必须追求“稳定的安全区域”,以应对通过经济上把中国吸纳进国际社会的政策却未能使中国变得更加“温和”的局面。
为此,有学者提出观察中国国际行为、进而判断美国是否对中国实行“接触”还是“遏止”政策的十项原则,包括中国不得单方面对外进攻性地使用武力、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尊重国家主权、航行自由、对军事力量发展采取克制态度、军事力量的透明度、不扩散、贸易与投资的市场准入、合作解决跨国问题及尊重基本人权。(注:James Shin,ed.,Weaving the Net:Conditional Engagement,pp.2~28.)也有学者提出以台湾问题、市场准入及不扩散问题为判断中国国际行为的准则。(注:Audrey Cronin and Patrick Cronin,"The Realistic Engagement of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Vol.19,No.1 (Winter 1996),pp.141~170.)这些原则和问题都成为判断和衡量中国国际意图的标尺,其基本结论是中国如果有能力和意图对外扩张、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或公然挑战美国的安全利益,那么美国政府就应迅速地从对华“接触”转向对华“遏止”。
4.社会/文化论
有关中国社会状况与其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也为“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提供了一种依据。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建立起多元民主所需要的文化板块,因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仍然是“绝对化的”(absolutist mentality);中国的社会状况依然固守在消极和内省型的传统上,缺乏对公共生活的热情和政治变革的勇气。中国社会依然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外观,团体利益远远超越于私人利益”,“高傲的精英常常蔑视外交政策规划的重要性”。(注:Lucian W.Pye,"China:Erratic State,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Vol.69,No.4 (Fall 1990),p.54.)美国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问题学者白鲁洵(Lucian W.Pye)提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儒教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因素”。这种政治文化让中国政府认为“有权干预私人生活,有责任帮助人民改善其生活状况,”结果是公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地位。这种政治文化不仅阻碍中国发展个人权力保障基础上的民主参与,而且让中国政治的民主进程非常缓慢。(注:转引自Richard Hornik,"The Muddle Kingdom:Bursting China's Bubble," p.48.)也有学者提出,中国人世界观的心理基础是强烈的“自卑感”,因而总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具有更加优越的权力地位,或者整个社会心态是要改变落后,甚至不顾规则地想要强大。这就为所谓中国国际行为的“危险性”提供了心理基础。(注:Jianwei Wang,"Coping with China as a Rising Power," in James Shinn,ed.,Weaving the Net: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pp.133~174.)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极端分析也制造了另外一种“中国威胁论”的依据,即所谓“即将到来的中国的崩溃”。(注:Gordon G.Chang,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Random House,2001).)这种观点认为崩溃后中国所产生的难民、跨国犯罪及武器安全等问题,将给世界带来严重威胁。
除此之外,美国学者颇为注意研究中国在对待外部世界问题上的基本心态。他们认为,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帝国,这种历史的征服和战争欲望在今天中国的国际行为中依然还可以见到其无法割裂的联系。(61)另一方面,美国学者注意到了自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西方侵略与奴役的历史,认为对这一段屈辱的历史记忆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根源,而民族主义激情往往会激发其寻求强硬的对外对抗性行动。他们认为,中国“受伤害的民族主义、总是萦绕在心头的历史的屈辱感和对外国人的强烈的不信任”,以及中国政府对这些“扭曲”情感的操纵和利用,将推动中国采取“进攻性的、大规模的”对抗性的对外政策,至少会继续将美国视为“敌人”。(注: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7),pp.34~53; Stephen Yetz,"Don't Comprise even if the Embassy Bombing,"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Belief,No.221,May 1999.)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威胁论鼓吹者重点关注的对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进攻性和排外的特点,这是将中国的对外政策引向冒险和扩张及阻挠中国与世界接轨重要的国内诱因。(注:Allen S.Whiting,"Assertive Nation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sian Survey,August 1993,pp.913~933; Muqun Zhu,"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Post-Deng Era," China Strategic Review,vol.2,No.2 (March/April 1997),pp.68~83; Suisheng Zhao,"We are Patriots First and Democrats Second: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In Edward Friedman and McCormick,eds.,What if China Does Not Democratize? (Armonk,NY:M.E.Sharpe,2000) ,p.1~22.)正如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所总结的,美国人担心一个经济上不断强大、但又有着强烈民族主义诉求的中国会给美国带来很多的麻烦,例如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交易与运送、以市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环境、人权等其他问题的国际规范问题。(注:Robert Sutter,"China's Rising Power:Alternative U.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CRS Report 96~518F,June 6,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