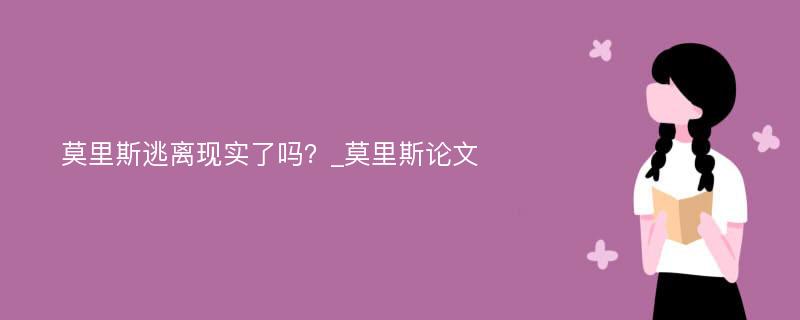
莫里斯逃避现实了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里斯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的诗歌成就在我国学界一直未曾得到足够的重视。不久前问世的《英国19世纪文学史》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书对莫里斯的诗歌未置一词。这一情形可能跟西方学界的有关评论不无关系。不少西方学者或贬低莫里斯的诗作,或笼统地称其为逃避现实之作。例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经断言“莫里斯的诗歌大都较弱”(R.Williams 155);另一位著名的“莫学”专家布里格斯虽然在他编纂的《莫里斯选集》(William Morris:News from Nowhere and Selected Writings and Designs,1962)里收录了不少诗歌,但是认定莫里斯的“许多诗歌都是特地为逃避现实而作的”(Briggs 13)。直到两年前,托德·奥·威廉斯在评论莫里斯的早期诗作时,还引用并默认了露丽(Margaret A.Lourie)的这个定论:“指责莫里斯逃避现实的许多批评家是相当正确的”(qtd.in T.O.Williams 103)。然而,莫里斯的诗歌(包括他的早期作品)果真是逃避现实之作吗?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莫里斯的相关作品,并考察其文化语境,就会发现它们并非高蹈隐逸之作。这也是本文以下需要论证的观点。
一、传奇题材与现实关怀
从题材上看,莫里斯的后期诗作显然没有逃避现实的嫌疑。他的激情组诗《社会主义者之歌》(Chants for Socialists,1883-1887)是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讴歌;他的叙事长诗《希望的香客》(The Pilgrims of Hope,1885-1886)以巴黎公社的斗争为主题,两者都是作者热情入世的产物。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莫里斯的早期诗作。原因在于它们大都取材于古代故事和中世纪传奇,如《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The Defence of Guenevere and Other Poems,1858)的主要题材来源就是马洛礼(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85)。此处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选用中古传奇故事作题材,就一定意味着逃避现实吗?
被最频繁地引用以证明莫里斯“逃避现实”的诗行出自史诗《地上乐园》(The Earthly Paradise,1868-1870)卷首的“歉词”(Apology):
我无力歌唱地狱赞颂天堂,
也不能减轻你们恐惧的重负,
我不能缓解迅速飞来的死亡,
也不能唤回逝去年代的幸福,
我的词句不能把希望恢复,
也不能把你们的眼泪驱走,
我是个空虚时代的徒劳的歌手。
沉重的灾难、无穷的操劳忧烦
把挣面包为生的我们压制,
徒劳的诗句无力挑此重担,
所以,让我唱古代难忘的名字,
他们已不在人间,但永远不死,
漫漫长年也不能把他们冲走——
而离开空虚时代的可怜歌手。②
此处叙事人(其实也代表莫里斯本人)似乎在哀叹自己是徒劳而可怜的歌手,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唱古代难忘的名字”,沉溺于“逝去年代的幸福”。不过,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段“歉词”其实为整首诗歌埋下了一个伏笔:它暗示诗中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对照物,即19世纪英国所处的“空虚时代”,以及它所见证的“沉重的灾难、无穷的操劳忧烦”。这种对照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介入和批判。
上述对照在《地上乐园》的“序诗”(Prologue)中更为明显:
忘掉伦敦四周那浓烟笼罩下的六郡,
忘掉喷鼻息般的蒸汽和活塞的击撞,
忘掉丑恶城市的蔓延和扩张;
回想当初靠驮马运输的城乡,
梦想伦敦小而白净,又清爽……
(Morris,The Earthly Paradise I:69)
这几行诗句明显地捕捉住了19世纪的英国社会现实:“浓烟”、“蒸汽”和“活塞”等意象无疑指涉工业化及其后果——与这些意象搭配的“笼罩”、“喷鼻息”以及“击撞”带来的噪音只能唤起不愉快的联想;与工业化相伴而行的是城市化进程——“丑恶城市的蔓延和扩张”。尽管叙事人接连用了三个“忘掉”来表明远离丑恶现实的愿望,然而此处的排比句式恰恰凸显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其中的悖论以及鞭挞时弊的含义不言而喻。诚然,《地上乐园》中构成了全诗主体的24个故事不是来源于古希腊神话,就是以中世纪挪威等地的传说为题材,看似远离了19世纪的英国现实,但是有了“序诗”和“歉词”中的现实图景,等于从总体框架上给那些传奇题材设置了一个参照体系,时时提醒读者把不乏英雄的中古时期和19世纪那“空虚时代”两相对比。
即便脱离了直接展示的现实图景,传奇题材的使用也不意味着莫里斯的逃遁。《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就是一例。该作品没有像《地上乐园》那样直截了当地用现实图景作铺垫,而是讲述了美丽的王后吉尼维亚与亚瑟王麾下最英武的骑士兰斯洛特之间的爱情,以及其他同样以中世纪为背景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所遵循的是一种梦幻逻辑,展现的是一个个梦境,不过都不是舒适安逸的美梦,而是离奇怪诞的梦魇,其基调时而忧郁时而恐怖,其场面常常充满血腥和暴力,其事件常常缺乏因果链的支撑。显然,这样的梦境并非遁世的好去处,说莫里斯借此遁世不免过于牵强。
可是莫里斯为什么要选择那些中古传奇和神话故事作题材呢?这些离奇怪诞的故事本身跟现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伊莎贝尔·阿姆斯特朗(Isobel Armstrong)在这方面发表过独特的解释,值得我们借鉴。她认为《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等诗歌是莫里斯捕捉现代人意识活动的一种尝试。而且对莫里斯来说,对于中古传奇和神话故事的想象最能体现现代人的意识活动。阿姆斯特朗的观点有一个认识前提,即文学艺术是一种劳动形式,而这种形式“在实质上取决于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人们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和性质”,因此莫里斯的诗歌实际上是要“探索19世纪社会的工作形式和性质如何对现代诗歌形式和意识产生重大影响”(Armstrong 235)。
比上述观点更值得重视的是,阿姆斯特朗把莫里斯笔下的怪诞故事跟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有关怪诞艺术的论述作了比较。罗斯金在“哥特式建筑的特性”③一文中高度赞扬了中世纪哥特式建筑所体现的怪诞艺术,他立论的基点是工匠/艺术家的创造性在这些建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虽然中世纪的工匠们身处被奴役的状况,但是他们在具体的个体劳动过程中有足够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而不像19世纪大机器工业背景下的工人们那样,被剥夺了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一切权利。哥特式建筑中那些怪异的尖拱、肋棱拱顶、飞扶拱及其相伴的图案往往让人始料不及,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这正是工人们匠心独运的结果。也就是说,哥特式建筑那千奇百怪的形状其实是工匠们用以再现自身生活状态的手段——那些雕凿出来的形状和图案虽然丑陋或恐怖,却是工匠们想象力纵横驰骋的产物,是劳苦大众实际生活的写照。跟中世纪的工匠相比,19世纪工人的境况更惨。后者所从事的机械劳动使他们处于“完完全全的被压迫状态”,以致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根本得不到发挥”(Armstrong 238)。阿姆斯特朗这里所说的情形,其实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说”来解释更为透彻:异化劳动意味着主体(劳动者)和客体(劳动对象/机器)之间关系的颠倒,原本应该在劳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反被客体所奴役,因而陷入了一种“最令人绝望的精神状态。它是一种完全不真实的人类存在,一种完全真实的非人化存在,一种绝对的拥有——有的是饥寒交迫,有的是疾病、罪行、堕落和愚钝,有的是非人的怪诞”(Marx and Engels 42)。这种“非人的怪诞”缺失了中世纪怪诞艺术所拥有的、人的自由想象。不过,没有自由想象的能力,并不等于没有自由想象的愿望,也不等于没有想象,只是这种想象受到了空前的遏制或扼杀。这种愿望与能力之间的鸿沟正是莫里斯所要捕捉的精神现实。因此阿姆斯特朗强调,《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等诗歌“试图展示在工作和劳动影响下现代人意识活动的形式,展示其如何观察体验事物并产生愿望,展示其想象的产物以及凭借神话从事想象的过程。这一尝试的预期目的是揭示现代人在想象过去时的意识活动方式,而不是把过去当作分析的工具”(Armstrong 236)。言下之意,莫里斯诗作的重点不是传奇故事本身,也不是与这些故事相应的历史时代,而是对19世纪英国社会现实——尤其是精神现实——的关怀。
确实,一旦我们透过那些传奇故事来追寻19世纪大机器工业背景下人们意识活动的轨迹,就会比较接近莫里斯诗作的主旨了。前文提到,那些故事所遵循的是一种梦幻逻辑,展现的画面往往呈破镜状,事件与事件之间缺少因果链,象征符号与所指之间常常发生错位或断裂。例如,《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中的“关于黑肤色的杰弗里·特斯特”(Concerning Geffrey Teste Noire)一诗,从讲述如何伏击大盗特斯特开始,但是叙事人很快就开始离题——一位名叫约翰的伏击者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骷髅和头骨,于是他开始根据这些尸骨的形状推断并想象死者生前的故事和死因。如对其中一具女尸的揣测:“她那细嫩的喉咙被箭射穿,/她的右腕骨破裂,于是我明白/她为何要把战袍穿,/她和情郎的故事分明在眼前”(Morris,Selected Poems 48)。接着约翰想象了这位女子的情郎冒死救援的动人场面。这些片断式的想象还夹杂着约翰的一些回忆,如小时候跟随父亲目睹的一场杀戮,以及他父亲在发现一些女子尸骨时的恐惧,等等。事实上,这首叙事诗一而再、再而三地偏离了伏击主题,而且偏离主题的事件和场面所占篇幅远远超过了伏击大盗的故事。可以说,叙事结构的因果链已经破碎不堪,断裂的画面犹如梦幻。这种情形正是莫里斯的苦心所在:破碎的故事正好说明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连贯想象的能力。中世纪题材只是供现代人通过想象力来重新组织的素材,而由于长期受机械劳动和机械式思维的影响,现代人的意识被禁锢了,因此想象出来的画面必然是支离破碎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莫里斯的早期诗作折射了现代人意识受到囚禁,想象力受挫等精神现实,但是这并不代表莫里斯相关作品中全部的现实关怀。笔者以为,那些中古传奇故事除了折射上述精神现实之外,还具有折射19世纪英国文化焦虑的意义。相对弥漫于莫里斯作品中的总体文化焦虑,阿姆斯特朗的研究显得过于狭窄。有鉴于此,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
二、文化焦虑
应该承认,禁锢的意识和受挫的想象力是19世纪英国文化现状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焦虑也就是文化焦虑的一部分。然而,仅仅从夭折的想象力这一角度来探讨莫里斯所表现的文化焦虑是不够的。为把这一问题说清楚,我们有必要先来界定一下本文所说的“文化”这一概念。
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研究,莫里斯所处的19世纪见证了“文化”概念的重要演变,即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总体生活方式的观念得到了明显的增强。更具体地说,莫里斯跟稍早于他的卡莱尔(Thomas Carlyle)、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罗斯金(John Ruskin)等人一起,促成了一个有关文化的假说,即“一个时期的艺术必然跟该时期普遍流行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其结果是审美判断、道德判断和社会判断都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R.Williams 83-130)。除了威廉斯所说的以外,“文化”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在19世纪还经历了另一个重要的演变,即多了一层“现代性焦虑”。这一点已经由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说得非常清楚:“到了穆勒、阿诺德和罗斯金的时代,对于文明的肤浅及其悖逆自然的效应的焦虑开始赋予‘文化’一词新的价值含义”(Hartman 207)。虽然哈特曼没有提到莫里斯,但是对于现代文明的焦虑无疑也是莫里斯文化观的核心部分。他在“我怎样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一文中发表过这样的声明:“我一生的主要激情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为对现代文明的仇恨”(Morris,“How I Became a Socialist” 380)。所谓“现代文明的焦虑”,是指社会转型期的焦虑。莫里斯的一生见证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迅速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思想、情感和文化方面的危机。这些危机的主要特征是工业主义和机械主义盛行,因此卡莱尔把那个年代称作“机械时代”(Carlyle,“Signs of the Times” 169)。继卡莱尔之后,阿诺德、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和罗斯金等人先后在各自的文艺创作和批评作品中表达了对于“机械时代”的焦虑,形成了一种文化批评的语境。这一语境又经莫里斯之手得以扩充和发展。对此笔者曾经在“乌有乡的客人——解读《来自乌有乡的消息》”一文中作过较详细的探讨④,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莫里斯的早期诗作也必须放在上述语境中加以审视,或者说从文化焦虑的角度来理解。
换言之,19世纪的英国文化染上了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等病毒,而《地上乐园》和《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等诗歌是这一疾病的有力见证。这一疾病不仅仅表现为人的意识和想象力遭到了禁锢,更表现为异化劳动、人际关系堕落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等症状。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莫里斯是如何揭示异化劳动的。本文第一小节中已经谈到,阿姆斯特朗所举的一些例子实际上可以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来解读。例如,莫里斯笔下的蒸汽、活塞、城堡、塔楼和布匹等许多物品同时也是劳动产品,但在诗歌中却看不到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者。后者的缺席意味着创造物和创造者被无情地分割。用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点来分析,我们在诗歌中看到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和错位。关于这一点,阿姆斯特朗实际上已经有所论及,遗憾的是她未能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来深入地分析。她曾经注意到《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中“手”意象的频频出现,并对此作了以下评论:
……手也是工具符号和代理符号,因为诗中的手总是操纵着物品,经常摆弄杯子和衣服之类的消费品,或者握有盾牌和利剑,而且总是跟身体分离,让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里的‘手’当然指称19世纪的工人。城堡、塔楼和花园的建造都要依靠工人,但是在莫里斯笔下,作为建造者符号的工人全都被不祥地清空了……清空得如此彻底,以致构成了一种揭示工人遭受压制这一状况的怪诞技巧。现代怪诞艺术无法再现工人,因为工人除了缺席以外,再也没有再现自己的手段了。(Armstrong 241)
鉴于阿姆斯特朗只是笼统地提到了“手”意象以及身手分离这一情状的重要性,我们不妨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在《地上乐园》里题为“十一月”(November)的篇章中,叙事人突然打破叙事框架,要求读者跟他一起“看一看外面的真实世界”,结果他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寂寞这符号亮得让我眼花缭乱,/漫无止境的恐怖啊,怪得荒诞。/空洞的恐怖耐久无边,可容得下这躁动的心脏?/狂热的双手向外伸出,可它们的位置又在何方?”(Morris,Selected Poems 96)
此处“狂热的双手”处于整个篇章的最后一行的“压轴”地位。更须一提的是,此处的手是单独呈现的,跟这些手有关的身体的其他部分,整个篇章未置一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陌生化处理。类似的处理方式在莫里斯的诗篇中比比皆是。譬如,《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中“夫人礼赞”(Praise of My Lady)一诗,在形容那位忧郁的夫人时聚焦于她的手腕及其血脉:“静脉沿着她的手腕蠕动,懒懒地死去”(Morris,Selected Poems 79)。把手腕的细节刻画得如此生动,无疑突出了“手”意象在诗中的地位。同一诗集里“洪水中的干草堆”(The Haystack in the Floods)也有强化“手”意象的倾向,如关于女主角珍黑妮那双手的描写:“我那软弱的双手试图回忆起壮汉们如何游泳”(Morris,Selected Poems 48)。这里,手竟像脑袋那样有了回忆的功能,这显然也是一种陌生化处理。在“吉尼维亚的自辩”一诗中,“手”意象出现了不下十次。例如,吉尼维亚在和兰斯洛特亲吻时,两人的“手都被留在了背后,被拉向远方”(Morris,Selected Poems 26)。这样的描写意味深长,显然又给人以身手分离的感觉。如此奇特而反复出现的“手”意象可以看作语言学家通常所说的“型式化”(patterning),即某一型式(pattern)或某一类同结构(parallel structure)通过重复而构成了语篇的凸显的部分,或者说是语篇前景化(foregrounded)的部分,用以突出语篇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就莫里斯的诗歌而言,经过前景化处理的“手”意象当然也承担着传递主要信息的任务。我们似乎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手”意象虽然没有跟19世纪的劳动场面直接发生关系,但是凭借“型式化”巧妙地折射出了异化劳动的惨状——19世纪的英国工人只能通过“狂热的双手”、“懒懒地死去”的手或“被拉向远方”的手来再现自己。这样的手已经无法以劳动果实来为劳动者服务,因而呈现出种种荒诞乃至恐怖的情状。
莫里斯早期诗作折射的还有人际关系蜕变这一现实。19世纪英国的“文化病”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卡莱尔当年所说的“现金联结”(cash-nexus),即人际关系蜕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经济关系,社会成员之间只剩下了以现金支付为唯一联结的经济纽带(卡莱尔,《文明的忧思》54-55)。这种情形在“吉尼维亚的自辩”一诗中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吉尼维亚与兰斯洛特发生了婚外情,这被以高文为首的一大批骑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把吉尼维亚推上了法庭,欲置之于死地。高文等人貌似正人君子,然而他们要维护的“道德”(其评判标准其实代表了典型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即排斥人的自然情感,机械地拘泥于某些条例)恰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吉尼维亚与亚瑟王的婚姻是一桩买卖婚姻。面对高文等人的指责,吉尼维亚给出了这样的辩词:
……那时亚瑟把我购买,
他名声显赫,却没有爱,
难道我必须为此放弃真正的爱?
难道我必须为了一纸婚约,
放弃那让万物生辉的情爱?
为那言不由衷的婚礼誓言
永远生活得像冰冷的石块?
(Morris,Selected Poems 24)
莫里斯此处讲的是中世纪的故事,但是其弦外之音不容质疑:吉尼维亚和亚瑟王的买卖婚姻是19世纪“现金联结”的生动写照,虽然是曲折的写照。关于《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英国著名批评家汤普森(E.P.Thompson)曾经有过一段比较笼统的评论,但是仍然值得我们参考:“《吉尼维亚的自辩》诗集中的人物——如……吉尼维亚本人——往往受激情的驱动,他们那高尚而强烈的情感可能超过我们的情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自己跟他们情感相同的部分。他们行动的外部条件可能对我们很陌生,但是他们行动的后果所遵循的逻辑跟我们自己生活中所体验到的逻辑并无二致”(Thompson 118)。同样,吉尼维亚的悲剧其实就是19世纪英国普通人的悲剧:现金逻辑主宰了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甚至主宰了最私密的两性关系。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道德的成了不道德的,不道德的反而成了道德的。莫里斯借古讽今的意图,不可谓不明显。
把早期莫里斯说成逃避主义者的观点有一个立论基础,即他的早期诗歌和后期诗歌的两相对比。由于他的早期诗作大都选用中古传奇题材,而后期诗作则采用现实题材,甚至采用革命题材,因此不少人认为莫里斯的思想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汤普森是这一观点最有影响的传播者。他在《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者》(William Morris: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1955)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影响力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观点,即莫里斯的文学生涯经历了一个由浪漫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脱胎换骨的过程。按照这一思维模式,汤普森和他的追随者把莫里斯的早期诗作划入浪漫主义的范畴,并且认定此时的浪漫主义“已经不再是一场反抗的运动,而是一种寻求补偿或逃避的转移”(Thompson 118)。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证明,莫里斯的早期诗歌里涌动着深深的文化焦虑,倾注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还须特别强调的是,莫里斯前后期作品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而似乎可以看作一种顺理成章的发展和补充。如果说他的早期诗歌表达文化焦虑,后期诗歌则旨在摆脱文化困境,那么二者虽有不同,却并行不悖。
事实上,莫里斯的文化焦虑的确在后期诗作中得到了延续,一种积极的延续。他的文化之旅最后通向了社会主义。露思·季娜(Ruth Kinna)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莫里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大贡献——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在于他对文化的欣赏,以及他对文化变革的欣赏”(Kinna 17)。我们不妨反过来说:莫里斯的文化焦虑把他引向社会主义,使他在社会主义理想中找到了归宿。具体地说,在《社会主义者之歌》和《希望的香客》等作品中,他直接向前文所说的“机械时代”提出了挑战,并开出了治疗文化疾病的药方。例如,他在“工人们在行进”(The March of the Workers)一诗中号召穷苦工人们加入社会主义“大军”,推翻剥削制度。诗中有一段对剥削者的质问:
是他们织你的衣,种你的粮,盖你的楼。
是他们化苦为甜,开发荒地,填平山沟,
为你干个不休。什么是给他们的报酬——
直到大军向这儿行进?⑤
这几行诗句像莫里斯早期的一些诗句一样,揭示了劳动异化现象:穷人们“干个不休”,劳动果实却为富人们占有。此时的莫里斯已经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消除文化焦虑的根本出路在于社会主义,所以他以巴黎公社的斗争为题材,写下了
长诗《希望的香客》。诗中不乏对未来的憧憬,姑引其中的一个例子:
那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降临巴黎:邪恶的侏儒发狂,
举刀一砍,想要摧毁巴黎,却不料刀断人亡;
巴黎自由了,城里再无敌人和白痴,
而今的巴黎,明天会变成全部法兰西。
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心在说:“不消多久,整个地球……”
终于来了那盼而又盼的一天,我知道了生命的价值,
因为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整个民族人人欢欣,
我这才知道我们常说的未来前景,
自己曾在悲伤和痛苦里宣传过,但心里也曾怀疑,
不知道这是产生于对当今的绝望还是对将来希冀——
而现在我亲眼看到了,实实在在,就在身边。⑥
这里,“整个民族人人欢欣”的景象其实是人类走出文化困境以后的景象,此时的人民“知道了生命的价值”。但是,在莫里斯对未来的憧憬的背后,文化焦虑仍依稀可见。
总之,文化焦虑伴随莫里斯走完了诗歌创作道路。无论是早期的莫里斯,还是晚期的莫里斯,逃避都跟他无缘,有缘的只是焦虑。
注解:
①2006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②参考飞白译文。见《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241-242。
③原文为“The Nature of Gothic”,最初是《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1851-1853)中的一章,后来莫里斯把它析出,单独印刷成册。
④参见《外国文学》3(2009):40-48。
⑤参考飞白译文。见《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256。
⑥参考王佐良译文。见《英诗的境界》(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212-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