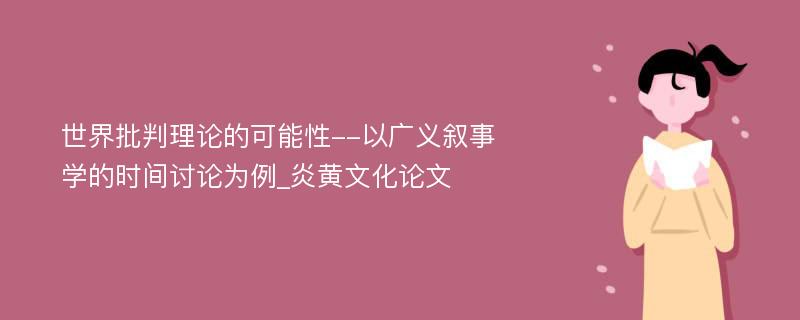
世界批评理论的可能——以广义叙述学的时间讨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广义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921-(2010)07-0002-08
1.为什么是“批评理论”?
关于广义叙述学的主要框架,笔者曾在几所学校做过演讲,也在叙述学的专业会议上做过发言,但得到的反应却是一片沉默:没有人赞同,也没有人反驳,更不用说著文支持或驳斥,似乎这个议题中没有任何值得争论的内容。但是对小说叙述学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西方学者已讨论多年,中国学者的争论也很热烈,争论的中心似乎是:谁对西方理论的理解更正确?对这种局面只有一个解释:中国学界还没有准备好把批评理论变成世界批评理论,最大的雄心也只是用中国古籍把批评理论“中国化”,而这种做法对于建立一个现代批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一百年来的两难之境不是接着西方人说,就是自言自语。难道中国学界至今缺乏提出全球性新课题、思考全球性新课题的能力或雄心?
世界批评理论的出现,取决于非西方学界对自己工作的基本态度。创立一个世界批评理论,首先要求我们不排外,把全部批评理论(而不只是19世纪末之前的中国文献)当做“自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等着接受批评理论世界化,这个前景需要我们积极参与才能实现。
中国的大学必开的三门课程是《中国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前两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同是文学,却成为完全不同的学科。分开它们的鸿沟有两条:首先它们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批评语汇,互相不能兼容;其次它们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学说:《中国文学理论》讲到19世纪末为止,至多到王国维结束,没有“20世纪中国文论”;而《西方文学理论》虽然从古希腊讲起,重点却在20世纪。《文学理论》课则不是前两门课的综合,而是将两者分别陈述。但是该课程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中西合一的批评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我们正在做的。因此,笔者在这里提出开设“世界批评理论”这一学科,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承认事实,只不过是提出了几点新的看法。
首先,这门学科应当叫什么?古代汉语中没有“文论”这个双声词,但这个“文学理论”的缩略语却在中国学界广为接受。1960年代以来,这门学科的重点已从文学转向文化,“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已经使“文论”面目全非。“Literary Theory”一说已不适用,不仅文学批评已多半是“文化进路”,而且研究对象也是整个文化。近四十年来,文学系、艺术系、传媒系、比较文学系,乃至哲学系,都转向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各国学界为如何命名这项全球性新课题伤脑筋时,中文却以一个模糊双音词安之若素,“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都是“文论”。可见,“文论”本身的发展,让中国学界得了这个缩写词的便宜。
最近十多年,情况又有发展:这门学科目前又在溢出“文化”范围,把有关当代社会演变及全球化政治等课题都纳入关注的范围。因此,近年来这门学科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这一名称原来一直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称呼自己理论的专用,直到最近,其指称意义才开始一般化。中文倒是可以避免这一混乱: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及其发展译为“批判理论”,而把广义的Critical Theory译为“批评理论”。这个名称在中国也开始为学界所接受,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①。
的确,这次改名是必要的:该理论体系及其应用范围已覆盖并超越了文学/文化的领地。先前各学科至少界限比较清楚: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因研究对象不同而界限分明。比较文学在全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跨学科研究的推崇,反而促进这种界限的模糊化。当代文化的急剧演变,以及这个理论本身的急剧演变,迫使这个理论体系改变名称。批评理论的目标学科宽泛得多:文学基本上全部进入。当然过于技术化专门化的文学研究不算;文本源流、考据训诂等传统学术依然是语文学科的核心,不属于批评理论的范围。
各种文化领域(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美术、戏剧、电影、电视、歌曲、传媒、广告、流行音乐、各种语言现象、时尚、体育、娱乐、建筑、城市规划、旅游规划,甚至科学伦理(克隆、气候、艾滋等)——的研究都是批评理论目前讨论最热烈的题目。同样,对广告等进行专业技术的讨论则不属批评理论。只有当它们成为批评对象时,才进入讨论的视野。
而文化领域之外,政治经济领域却越来越成为“批评理论”的关注点。全球化问题、第三世界经济受制宰问题、“文明冲突”、意识形态、世界体系、第三条道路问题、贫富分化、穷国富国分化、东西方分化、弱势群体利益、性别歧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批评理论特别关注的目标。而要用一种理论统摄所有这些讨论,则这种理论一方面不得不接近哲学的抽象,例如德勒兹(Gille Deleuze)的以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与资本主义对抗的解放哲学;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不得不越出“文化”的非行动界线,如近年的性别政治论(Gender Politics)。
因此,在许多同类的文集、刊物、课程提纲及教科书中,我们会发现所选内容大致上三分之一为文学理论,三分之一是文化理论,还有三分之一与人类问题有关的哲学(福柯称为“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这样看来,“文论”(哪怕是文化理论)这一名称也已经不合适这门学科了。
2.批评理论的基本体系
20世纪批评理论有四个支柱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卢卡奇(Georg Lukacs)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基本完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可以说,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保持了当代文化理论的批判锋芒。反过来,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从文化批判角度进入政治经济批判的。
20世纪的批评理论的第二个思想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phenomenology/existentialism/hermeneutics)。这个体系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哲学之延续,他们一再声称结束欧洲的形而上学,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传统顽强,所以需要努力来结束。从胡塞尔(Edmond Husserl)开始的现象学,与从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开始的现代阐释学,本来是两支,却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利科(Paul Ricoeur)等人手中结合了起来。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80年代的著名的“德法论争”显示了较严谨的哲学思辨与解放的理论态度之间的差别。
当代文论的另一个思想体系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这一支的发展一直陷入争议,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只是这一派的“性力”出发点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过于对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对西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巨大,但其陈意多变,表达方式复杂,在中国的影响较为有限。
当代文论的形式论(formalism)体系是批评理论中重要的方法论,可以说是“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产物。但是语言转向至今并没有结束,“文化转向”就是其延续方式之一。符号学(semiotics)与叙述学(narratology)本应是形式论的分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成为形式论的代称,它们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推进到文化。当代文化的迅疾变形使形式研究出现了紧迫感:一方面形式论必须保持其分析立场,另一方面它必须扩展到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分母”。
在当代,流派结合已成惯例:对当代批评理论作出重大贡献者,无不得益于这四个体系相互间的结合。1970年代前,两个体系的结合已很常见,例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从法兰克福学派独立出来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主要就是糅合精神分析,如拉康从事的是符号学式的心理分析;利科的工作重点是把阐释学与形式论结合起来。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用结合体系的方式向新的领域推进,如克里斯蒂娃用符号学研究精神分析,展开了性别研究的新局面;齐泽克则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推进到全球政治批评。
当代批评理论的新发展往往都以“后-”的形态出现。结构主义发展到“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但后结构主义者原来都是结构主义者,这证明结构主义有自行突破的潜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研究当代文化和当代社会正在发生的、足以决定历史的重大转折;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则反映当代世界各民族之间——尤其是西方与东方国家之间——文化政治关系的巨大变化,以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新形式;如果把女性主义(feminism)与后起的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看作原本“理所当然”的男性霸权主义文学之后的学说,那么60年代之后的批评理论的确有“四个后”主要分支。
说批评理论有四个支柱,其余都是延伸,自然是过于整齐的切割。笔者只是想指出:现代批评理论已经覆盖了整个人类社会文化触及的所有课题。只要我们能时时回顾这四个基础理论,就完全不必跟着西方“最时髦理论”奔跑,也就能摆脱“不是跟着说,就是自言自语”的两难之境,就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对一个世界性的批评理论作出独特的贡献。
说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是“西方”的,就迄今为止的主要参与者而言,确实如此。四个支柱理论体系和四个“后-”体系的创始人和主要发展者,甚至今日的主角人物,都是西方学者。
其实在英语世界,整个批评理论体系常被称为“欧洲大陆理论”(Continental European Theory)。在主要的批评理论家中,德语(德国、奥国)和法语(法国、瑞士、比利时)的思想家占了大半,英语国家、东欧及南欧的思想家比较少,这与其幅员版图和高等学校数量相比正好相反。英国美国受经验主义传统之累,高校再发达,也只能起鼓风作浪的传播作用。欧美之外对批评理论起过重大作用的人主要是“后殖民主义者”。这一派的几个领军人物都是在英美受教育、并在英美大学执教的阿拉伯人和印巴人。无论如何,这个批评理论并不是一种“西方理论”。
第二个原因可能更重要,即批评理论需要一个体制作为批评对象,现在批评理论的对象是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但是这个体制正在向全世界扩展,因此这个批评理论也就是针对正在向全球延展的西方式体制(如符号经济;又如社会泛艺术化)的批评理论,这从反面证明它不是一种西方理论。
3.批评理论需要更加普适
批评理论是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思想回应。西方批评理论是20世纪初在欧美的许多国家没有经过任何人际族际协调而发展起来的,例如,弗洛伊德不了解马克思、胡塞尔不了解索绪尔、雅克布森不知道瑞恰兹或艾略特、皮尔斯不知道索绪尔,因此批评理论的第一代奠基者之间没有可能发生有意识的相互应和。20世纪初,这些思想者都发现有必要从现象后面寻找深层控制原因:葛兰西在阶级斗争后面找到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弗洛伊德从人的行为方式后面找到无意识中里比多的力量,胡塞尔从经验与事物的关联中找到意向性这一纽带,而索绪尔与皮尔斯则分别看到人类表意符号的规律。这样一个不约而同的“星座爆发”是文化气候催生的产物。正因为它们是对同一个文化发展进程的思想应对,它们对表面现象持同样的不信任态度。这种共同立场也为它们日后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批评理论的确是在欧洲文化土壤上长出来的。20世纪初的欧洲出现了现代性的挑战,学者普遍感到了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压力。那时在世界其他地方尚未出现这种思想的压力。早些时候(19世纪),欧洲学界存在文学理论、文化思考和哲学探讨,但学科之间并没有构成一个运动。“批评理论”(这个名称是近年才形成的)的突然出现的确是现代性首先对欧洲思想施加压力的产物。
由此,我们可以辨明另一个问题:既然19世纪的西方还不存在批评理论,那么19世纪的东方(例如中国)没有这种理论也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需要进行自辩。等到现代性的挑战成为世界现象时,翻译已经发达,国际学界交流已成常规,大学成为思想融合的阵地。此时东方(包括中国)的批评理论已不可能与世隔绝单独发展,我们可以大胆预言:批评理论今后的发展目标必然是“世界批评理论”,因为东方学者不得不回应现代化进程提出的各种问题,从而不再“学着说、跟着说”。
预言批评理论将世界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东方民族的文化遗产已开始进入批评理论的大体系。近三十年来,人们渐渐在全球范围内认同一整套新的价值观,如多元文化、地方全球化、弱势群体利益、环境保护意识、动物保护意识和反无限制科技等等。很多新价值观的提倡者声称,他们是在回应东方智慧。对生态主义的西方信徒来说,道家经典是他们的圣经,道法自然是他们的响亮口号;反对“科技无禁区”的人则一再重提老子关于过分智巧的警告;动物保护主义则与佛教的众生有灵思想有显然的对应;关怀残疾人和弱智者,这更是佛教式的悲悯;至于对老年人权利的保护则当然与中国的儒家传统一致。至少,这本是我们固有的思想。东方人对这些新价值观应当并不陌生,甚至应当有自然的亲和感。
结论是什么呢?在不远的未来,非西方民族将会对批评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不会完全用一个东方化的理论取代它,而是把它变成一个真正世界性的理论。批评理论已是整个人类的财产,而当代东方的文化气候已开始召唤这样一种世界化。也就是说,批评理论的当代化与“批评理论世界化”在同时进行之中,不久后我们就会相信,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命题。
这不是向“普适主义”投降,因为任何理论的适用性都不需要预设,需要的只是在批评实践中检验某个特定理论的有效性。我们更需要发展理论,因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任何理论都还远远不够成熟。所谓“发展”,并不是在现成的理论框架中填充中国材料。恰恰相反,理论之所以仍需发展说明理论总体尚有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发展理论不是证明理论“非普适”,而是证明理论“不够普适”。
下文就以我们对叙述学中的时间问题所作的探讨为例,说明中国学界能把某种理论推进得更具普适性。如果靠我们的努力可以把叙述学世界化,那么整个批评理论都可以在中国学界的努力中得以世界化。
4.叙述三环节中的时间向度
任何叙述流程毫无例外地含有三个基本环节,即叙述行为、被叙述出来的文本和叙述文本的接受②。本文将要讨论的,是贯穿这三个环节的“内在时间”。
叙述与被叙述的关系是一种“抛出”,即叙述把被叙述之物抛出叙述人③所在的世界之外。格雷马斯认为,叙述的最基本特征是“分离”,即叙述人向自身之外投出各种范畴,形成“创造性的分裂”:“一方面是陈述的主体、地点与时间的分裂,另一方面是陈述的元表现、空间表现与时间表现的分裂”(Greimas & Courtes 1982:76)。“抛出”形成的叙述世界与被叙述世界之分裂是叙述的前提。叙述人主体与被叙述的人物主体不可能同一;叙述人所在的空间时间与被叙述的空间时间也不可能同一。叙述本身就是在讲另一人(可能是叙述人自己)在另一地点和另一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情。诚然,这种“抛出”有远距与近距之分。在最贴近的叙述中,例如病人向医生讲述当下的症状,“抛出”几乎难以觉察,但是依然存在。莫妮卡·弗路德尼克(Fludernick 1996:252)提出:“不可能同时既体验一个故事,又对这故事进行叙述,也就是说,不可能把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讲成故事”。叙述可以叙述任何事件,就是无法叙述叙述行为本身,因为叙述行为是元叙述(格雷马斯上引文中称为“元表现”)层次的操作。叙述与被叙述合一,从而取消了叙述本身。的确,叙述与被叙述之间的时间差是保证叙述进行的条件,但是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叙述,而不是读者/听众对叙述进行的时间重构,听众完全可以认为被叙述的事件正在发生,例如医生必须把病人的主诉视为正在进行的情况加以诊断。
因此,本文讨论的时间向度不仅是叙述时间,不仅是被叙述时间,也不仅是被理解的叙述时间,而是叙述的三个环节之间的时间关联。一旦把叙述的三个环节联合起来讨论,叙述“抛出”形成的时间向度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联系。本文试图讨论的就是叙述文本“意图中的内在时间向度”。
对于时间这一困惑了哲学家数千年的难题,胡塞尔(Husserl 1991:16)认为时间的三维实为意向中的存在,对过去,意识有“保存”(retension);对此刻,意识有“印象”(impression);对未来,意识有“预期”(pretension),意识由此而组织成一股“时间之流”,而这个时间之流穿过形式的渠道,“维持这一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之流的形式结构”。而利科(1985:6)则提出,胡塞尔所说的“意识时间之流的形式”就是叙述。没有叙述,意识中就没有内在时间,意识本身就无法存在。他在三大卷《时间与叙事》(1983-1985)中详细讨论了意识如何靠叙述组织时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没有叙述,意识就无法把握时间。该书第一卷开场就声明,“关于时间的思考,只能是无结论的思索,只有叙述才能给予回应”。
但利科并没有明确回答本文讨论的问题:叙述的三个环节对时间的理解并不一致,那么到底是叙述(行为)、被叙述(文本),还是叙述的接受(理解),构成我们意识中的时间之依据?利科(1988:241)有时似乎认为文本更为重要:“没有被叙述出来的时间,便无法思考时间”。他(1985:181)还认为意识用三种不同的模仿来处理时间的三维:“从情节顺序之预构(prefiguration)出发,通过情节化(emplotment)来进行建构(constructive configuration),达到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冲突的再构(refiguration)”。利科把胡塞尔的经验对时间三环节处理方式具体体现到叙述中。但在他的实际讨论中,叙述行为依然扮演主要角色。
胡塞尔讨论意向中的时间三维似乎假定经验主体是合一的,而利科则落实到叙述。这样难题就出现了:显然,利科说的时间预构、建构以及再构,依靠的是不同的主体。笔者的看法是,我们很难描述叙述的发出主体,也控制不了接受主体,文本是唯一可以验证的依据。当叙述文本具有本质上不同的形式时,它的“全部意义”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在有关主体的意识中引发不同的时间意识?广义叙述学的关键就在于文本体裁与时间意识的这种关联。
5.叙述的定义
体裁研究是形式-文化的综合讨论,是文化中形成的表意和诠释默契,是超出个体意识活动之上的认知模式,时间向度既是叙述人的意图,也是叙述接受者的意图,体裁保证一种叙述形式能够把相应的时间构筑方式变成“交互主体关系”中的时间向度意识。
邦维尼斯特(Benvesniste 1971:10)在《一般语言学诸问题》中提出,语态(moods)的三种基本方式具有传达表意的普世性:“任何地方都承认有陈述、疑问和祈使这三种说法……这三种句型只不过是反映了人们通过话语向对话者说话与行动的三种基本行为:或是希望把所知之事告诉对话者,或是想从对话者那里获得某种信息,或是打算给对方一个命令”。这三种“讲述”讨论的不是讲述内容,更重要的是讲述人希望讲述接受者回应的意向,是贯穿说话人-话语-对话者的一种态度。他没有说这是三种可能的叙述形态,也没有说这三种句式隐含着不同的“时间向度”,但是他已经暗示了支撑讲述的是主体关注,是一种“交互主体性”④的关联方式。
本文通过探讨各种叙述类型及其表意方式,发现叙述人能够把他意向的时间向度用各种方式标记在文本形式中,从而让叙述接受者明白如何回应这种时间关注。三种时间向度在叙述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没有对这三种时间向度的关注,叙述就无法对经验提供组织方式。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对叙述的定义进行“扩容”,以涵盖所有的叙述。而西方学界至今仍在坚持一个观念,即叙述必须是对过去(或假定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进行回溯:过去性是小说叙述学的立足点,而要建立广义叙述学,就必须打破这条边界。亚里士多德就强调“叙述”(diegesis)与“模仿”(mimesis)的对立,也就是史诗与戏剧的对立,因此在西方传统中,戏剧不是叙述。排除“正在发生的”戏剧,也就排除了影视这个当代最重要的叙述样式,更不用说尚未发生的叙述,如广告。
西方叙述学界(无论是“经典叙述学”,还是“后经典叙述学”)至今坚持这一传统观念。普林斯(Prince 1988:58)提出过对叙述的简单定义:“由一个或数个叙述人,对一个或数个叙述接受者,回述(recounting)一个或数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但是他马上提出附加条件,即必须是“重述”,“台上正在发生的”戏剧不是叙述。新叙述学的领袖之一费伦(2007)则斩钉截铁地表示,“叙述学与未来学是截然对立的两门学科。叙述的默认时态是过去时,叙述学像侦探一样,是在做一些回溯性的工作,也就是说,是在已经发生了什么故事之后,他们才进行读、听、看”。另一位新叙述学家阿博特(2007:623)也强调,“事件的先存感(无论事件真实与否,虚构与否)都是叙述的限定性条件……只要有叙述,就会有这一限定性条件”。
要建立一个包容一切叙述的广义叙述学,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定义叙述,取消普林斯这个“回述”条件。笔者建议,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思维或言语行为,都是叙述:
1.叙述人把一个或一组卷入人物的事件组织进一个文本;
2.这个文本可以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内在的时间向度。
概言之,能用任何媒介把事件“组织”成文本即可构成叙述,该事件不一定发生在过去。
叙述必是一个涉及“人物”(不一定是“人”)参与的事件的符号文本,但是这个文本必须靠读者注入时间关注,才成为叙述;在读者加以“语境扩展”之后,文本才获得必要的内在时间向度。按照上述两条最宽泛的定义(事件构成文本、文本具有时间向度)来理解叙述,不难发现,在人的生活经验中充满叙述,叙述无所不在。
6.按叙述体裁划分三种时间:未来时
上节的讨论挑明了叙述的必要条件是时间。而叙述的贯穿性时间意图在体裁上留下的标记最明显。观察当今文化中各种叙述体裁不同的内在时间向度,大致上可以作出以下的划分:
过去向度叙述:历史、小说、文字新闻、档案等;
现在向度叙述:戏剧、电影、电视新闻、行为艺术、互动游戏、超文本小说、音乐、歌曲等;
未来向度叙述:广告、宣传、预告片、预测、诺言、未来学等。
未来向度叙述的体裁标记比较清楚,因此先从未来时间向度叙述谈起。上述三类叙述的时间区别不在于被叙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就被讲述的事件而言,各种体裁甚至可以讲同一个故事,例如“小贝秒杀弯刀救主”。它们的区别在于叙述关注的时间方向。新闻说的是昨晚的球赛,广告则以过去的故事诱劝可能的购买者。下面是Nike运动鞋的一个电视广告:
在一艘大船的船舱里举行了一场足球赛,船舱壁上画出一个方框作球门。穿Nike鞋的足球明星连续传球,脚法令人眼花缭乱,最后贝克汉姆临门一脚,打到船舱壁上的方框之中,进球,钢板破裂,大船下沉。
广告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只有“完全可能发生过”的特质,才能获得非真实的实在性。虽然故事或许是“过去性”的,但在广告制作者的意图中,未来向度非常明确:拥有一双Nike鞋吧!穿上后,你甚至可能像贝克汉姆那样“成功”。更重要的是,接受者关注的是未来。广告研究者(Williamson 1978:56)告诉我们:这种意义不是广告灌输的,而是由观众(爱好运动的少年)的意识构筑的。他们急需用幻想中的未来以实现自我的转换。而广告叙述必须构筑明确的未来向度,几乎所有广告受众都不会被一个关注过去与此刻的广告成功左右。
未来叙述的最大特点是承诺(或反承诺,即恐吓警告),这是叙述行为与叙述接受之间的意图性联系,而叙述的故事倒是灵活多变,往往从过去延伸到现在,再进一步延伸至未来。请看下面这一则常规的文字广告叙述:
在众多的楼宇中,我为什么选择了名粤花园?因为她……
唯一感到不便的是紧贴广州大道、离地铁出口太近,因为亲朋好友会轻易找上门来。
唯一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是意想不到的升值,因为她坐落在广州市重点发展区中心。
唯一缺少的东西是污染,孩子认识的第一种颜色将是绿色,因为数百亩受重点保护的果树园林环绕周边,教人不看也难。……
这就是名粤花园,令人神往的花园!集别墅、住宅、写字楼、商场于一体,宝石蓝玻璃幕墙、快速电梯、自动扶梯、送IDD电话、空调器、抽油烟机;每平方英尺仅357元起价,一次性付款85折优惠(15天内有效)……
用过去的经历(我已经选择)预言将来的图景。广告的语言说到过去无妨来点幽默,但是希望接收者清晰理解的向度是未来,因此必须说到商品本身,而且必须显得实实在在。两段之间明显的文体断裂(这是许多广告的共同特征)表明了修辞的意图。
未来型叙述都具有强烈的“意动性”(conative)。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在他的“语言学与诗学”一文中提出符号表意的“六因素对应六功能”论,其中“信息指向接收者的倾向,是其意动功能”(1990:176)。广告叙述人明显的意图是要求叙述接受者进入他尚未采取的行动——购买商品、加入运动、回报爱情、接受馈赠等等——因此明显是意动性的,也就是邦维尼斯特所说的“祈使语态”。雅克布森说他指出的六个因素在任何讲述中都存在(同上:189)。这也就是说,任何叙述都有意动性,都有让接收者采取某种立场和某种行动的功能。浪漫小说催动爱情,寓意小说启示前景,“现实主义”小说教导对世界采取某种解释。只是“意动性”为主导的“未来型”叙述明显地让接收者感到叙述者催动的意愿。雅克布森没有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符号表意中的意动性会被前推为主导因素。本文认为这种“意动标记”主要是体裁特征,即体裁的文类标识,例如广告与产品的连接,让读者/听众能识别出广告内含的未来时间向度。准确地说,叙述者看到面对的叙述是一份广告,就产生程式性的未来意义期待⑤。
“此时此刻”的叙述承继前文,并且不断向前延伸,就构成了现象流的“内在时间意识”(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Husserl 1991:16)。利科指出:“(胡塞尔说的)‘意向方式’变化的要害,是意向方向的变化,而不是意向对象的变化……因为意向方式在行进中总是被不断破坏,从而划分了不同的意向平台”(参见尚杰2006:79)。的确,叙述的对象(事件本身)不是决定性的,意向方向的变化(例如指向未来)是在叙述体裁这一文化程式提供的平台上形成的,这是本文再三强调的最主要问题。因此,无论广告做得如何艺术、无论文辞如何诗化、无论制作者如何巧妙地掩盖生意目的,广告都无法逃脱商品的主导,根本原因是因为叙述接收者很难摆脱广告解读程式,不可能把它当作一首诗来欣赏。
7.现在时叙述的“此刻在场”性
现在时叙述是最难辨析的,而这是叙述学走向广义的一个关键点。上文已经说过三种语态与三种时间向度有对应关系,未来时叙述与祈使语态对应,过去时叙述与陈述句对应,现在时叙述则与疑问句对应,后两者的区分比较细微。雅克布森(1990:179)说,“陈述句与疑问句经常可以互相转换,祈使句却不能。例如奥尼尔剧本《泉》中的主人公说:‘喝!’,明显是意动,是命令。而陈述句‘他喝了’,却可以转化为疑问句‘他喝了吗?’”相应的,陈述本质的过去叙述与疑问本质的现在叙述,给人可以转换的印象,例如过去时的小说可以“自然”地改成现在时的戏剧或电影。
很多人认为小说与电影叙述时间性相似,因为它们叙述的事件似乎一样,但两者的内在时间向度很不同。过去叙述给接收者“历史印象”,典型的体裁是历史等文字记录式的叙述;现在叙述给接收者“即时印象”,典型的体裁是戏剧等演示性文本。
由于电视电影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中最重要的叙述体裁,所以我们先来讨论影视的现在时间特征。电影学家阿尔贝·拉菲(Laffay 1964:18)提出:“电影中的一切都处于现在时”。麦茨(1996:20)则认为,这种现在时印象的原因是“观众总是将运动作为‘现时的’来感知”。画面的连续动作给接收者的印象是“过程正在进行”。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持不同看法,如戈德罗和若斯特(2005:135)认为电影是预先制作好的(已制成胶卷或DVD),因此“电影再现一个完结的行动,是现在向观众表现以前发生的事”,所以电影不是典型的现在叙述。他们认为“(只有)戏剧,与观众的接受活动始终处于现象学的同时性中”(同上)。但是最近也有叙述学家(费伦2007:624)认为,戏剧电影都是“重述”过去的事,它们与小说不同之处只在于“戏剧和电影不是一个故事的表现而是再现,这个故事作为手稿、脚本、小说、历史、神话或一个想法而现存于人们的头脑之中”。
看来,戏剧或电影与小说在时间性上的区别是个理论大难题,有关学者一片混战至今未休。在此,笔者的观点很清楚:第一,因为戏剧与电影都是演出性叙述,在意图性的时间方向上与小说等典型的过去叙述有本质的不同;第二,戏剧与电影之间,在叙述行为的方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从文本被接受的方式上看,内在时间向度没有根本的不同,都具有“现象学的同时性”。
说两者不同的学者认为,戏剧的叙述(演出)如口述故事等,叙述人(演员)有临场发挥的可能,下文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电影是制成品,它缺少这种不确定性。但是这种区别只对了解影视制作方式的人有用,观众的直接印象是两者相同。在叙述展开的时段中,接受者始终被印象中的共时性控制。而直觉印象对现象学的时间观念来说至关重要。
戏剧与影视的对比与口头叙述和广播的对比类似,口头叙述的现场展开是多渠道传达。宋元平话、明清弹词、今日的说书、相声,所有这些现场表演式的口头叙述都有各种“类文本”特征(姿势、声调、伴奏),有叙述人与听众的应和互动,叙述人有特权作临场发挥。但是听口头讲述得出的时间印象与听收音机广播没有本质的不同。哪怕听众知道广播里放的是事先制作好的录音,不是现场广播,“正在进行”的感觉印象却一样强烈。
各种演示叙述时间概念的关键是“不确定性”,是“事件正在发生,尚未有结果”的主导印象。演示就是不预先设定下一步叙述如何进行、情节如何发展。正因如此,在演示性叙述中,一切意义必然是即时现场实现的,随时可能被后来的事件所修正。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戏剧反讽”(dramatic irony):观众因为一路看过来了解前情,因而比角色知道得多。观众胆战心惊,看着角色正在犯错误,爱莫能助扼腕顿足,而角色因为不知情而越发理直气壮地、几乎傲慢地卖弄自己的无辜,一门心思犯千古大错。
如果演示性叙述文本不具有这种“现在在场”的时间特征,不能给观众强烈的“眼看着某种情况正在发生”的感觉,戏剧反讽就不可能出现。只有看起来灾难性后果尚未发生,才会令观众觉得如果让他们参与——例如朝台上大喊一声——便可设法扭转局面。观众的内心冲动也经常表现为看球赛时的捶胸顿足、狂呼尖叫等行为。舞台上或银幕上的叙述行为,与台下叙述接受之间,的确存在异常的张力。小说和历史固然有悬疑,但是因为小说的内在时间是回溯的,不管什么情节,一切都已经写定,已成事实,已然结束。读者急于知道结果,会对结局掩卷长叹,却不会有似乎可以参与改变叙述的冲动。今日网上的互动游戏与超文本(情节可由读者选择的动画或小说)更扩大了不确定性。接受者似乎靠此时此刻按键盘控制着文本,在虚拟空间中,“正在进行”已经不再只是感觉,而是切切实实的经验。
康德称这种现时性为“现在在场”(the present presence),海德格尔引申称之为“此刻场”(the momentsite)⑥。在现象学看来,内在时间不是客体的品质,而是意识中的时间性。叙述现在向度不是叙述的固有特征,而是特定叙述体裁固有的接受程式,是接受者构建时间的文化约定方式。
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新闻现场转播的时间性:绝大部分所谓现场转播、新闻广播和电视讨论都是预先录制并经过编辑处理的。极个别节目如足球赛之类才是真正的直播,因此才会出现诸如黄健翔“出格”的讲解;某些“选秀”节目为了现场与手机互动,只能直播,也会出现柯以敏式的不当评论。但是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预录与真正的直播效果相同。社会学调查证明:绝大部分观众认为新闻都是现时直播的(Feure 1983:12-22)。
现在回到本文开始时说到的时间性这一现象学的中心议题,胡塞尔着重讨论的是主体的意识行为,讨论思与所思(noetico-noematic)关联方式;利科着重讨论主体的叙述行为,讨论叙述与被叙述(narratingnarrated)关联方式。而叙述的接受如何相应的重现意图中的时间,成为他们留下的最大的理论困惑。利科在三卷本巨作临近结束时声明关于时间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time)与关于意识的时间(time of consciousness)实际并不可分:“时间变成人(human)的时间,取决于时间通过叙述形式表达的程度,而叙述形式变成时间经验时,才取得其全部意义”(Ricoeur 1988:52)。新闻实际上是旧闻,是报道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这一点在文字新闻报道中很明显,而电视播音的方式则给过去之事一种即时感,甚至如现场直播一样给人“因正在进行而不可预测结果”的感觉。电视新闻冲击世界的能力就在于它的现在时间性,它把叙述形式变成可以实现的时间经验。
“现在在场性”误导听众最有名的例子发生在现在看来很“假”的广播剧中。1938年10月30日晚上,WABC广播公司根据威尔斯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现场报道”火星人入侵,引起纽约市民大规模逃亡。虽然说得清清楚楚是广播剧,中间还插了三次气象预报,但是现场时间解读程式依旧占了上风。
这段尽人皆知的往事可能匪夷所思,因为今天的听众可能对媒体的态度成熟多了。但是当今媒体对电视的利用也比当年老练多了。“现在在场”是许多的公众关注的重大群体政治事件背后的导火线。电视摄影机的朝向使叙述的意图方向本身如此清晰,以至于意图叙述的事件果真按照叙述意图在现场发生。此时,叙述人(全球影视网的叙述者)、叙述文本(处于政治事件中的被叙述者)、叙述接收者(所有的观众,包括上述叙述者与被叙述者自己),全被悬挂在一个貌似不确定的空白之中,像升到顶的过山车,在下一刻似乎朝任意方向泻落,而这个方向实际上已是自我预设好了。
今日西方叙述学界依然把叙述看成是个古瓶,把“事件的在场实现”这个妖魔锁在过去中。一旦把叙述广义化,这个瓶塞就被拔开了:时间的在场性就把预设意义以我们的内心叙述方式强加给当今,“新闻事件”就变成一场我们大家参与的演出:预设意义本来只是各种可能中的一种,在电视摄影机前,却因为我们自己的集体自我注视,而将在场实现于此刻:在“现在时”叙述中,我们在被迫叙述我们自己。
8.世界批评理论的可能
以上是一个不算太简短的实验,意在验证我们能否不跟着西方学界走,也不依靠中国古籍(19世纪前的中国古人显然不可能预料到当代叙述范围的扩大,不可能为我们准备好精神遗产),为建立具有普适性的批评理论作一点贡献。
结果证明,我们多少能作出一点特殊的贡献。西方叙述学界至今守住亚里士多德的区分,不愿意承认叙述可以“非回溯”,不承认戏剧是叙述,这样就使叙述学不能处理当代最重要的叙述体裁电影、电视新闻、广告、游戏等,也无法处理传媒时代带来的许多问题。只要我们不盲从,就可以看到,西方学界被动词时态绊住了,反而是动词没有时态的中国人,容易看到这种时间束缚是没有必要的。
经过当代文化的“叙述转向”,叙述学就不得不面对已成的事实,即既然许多新体裁已被公认为重要的叙述体裁,那么叙述学必须自我改造,最终实现不仅能个别应对传统叙述,也必须有能总其成的广义理论叙述学。事实证明,各种体裁的叙述学绝不是“简化小说叙事学”就能完成的,许多体裁提出的叙述学问题,完全不是旧有叙述学所能解答的。
叙述固然无法叙述叙述本身,但是叙述接受对叙述的内在时间进行重构就使叙述意图中的内在时间得到彰显,叙述就出现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之分。而这个分野可以从批评理论的四个支柱得到支持。本文得益于形式论,也得益于现象学与阐释学,包括邦维尼斯特的“泛语态论”、胡塞尔的“内在时间论”以及利科的“叙述建构时间论”。这正好和笔者的看法相呼应,即只要坚持回到“四个基础理论”,我们就能独立地创新。只要思维创新,在说出与西方学界不同的看法时,我们完全不必犹犹豫豫。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能作出的一点贡献并不是把批评理论更加“本土化”。在这个时代的批评理论中,强调“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机会主义,除了自我炫耀恐怕达不到其他目的。既然我们面对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共同的,既然广义叙述学要处理的电影、电视、新闻、游戏等新的叙述方式是全球共享的形式,我们要帮助建立的理论就自然具有世界性的品格。这样一门批评理论,肯定有本土性的因素,不会彻头彻尾是普适的。但是只要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没有逆转,批评理论的普适性也就只会增加。
注释:
①例如Hazard Adams主编的著名的巨册文集兼教科书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从1971年初版以来,已重印多次,中国也有重印本;如王一川主编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又如张颐武的论文“全球化时代批评理论的新空间——简评《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第三、四卷”(《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以及周小仪的“批评理论之兴衰与全球化资本主义”(《外国文学》2007年1期)。
②中国大部分文献中,“叙述”、“叙事”混合使用,不加区分;或是过于做文章,认为这个区分大有讲究。谭君强译米克·巴尔的专著Narratology: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时,有意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将标题译为《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利科的名著Tempsetrecit,英译成Time and Narrative,汉译成《时间与叙事》。但是本文结尾会讲到,利科的重点恰恰不是文本,而是叙述行为。在本文中,笔者坚持用“叙述行为”与“叙述文本”两个说法,无非是令自己行文统一。
③本文用“叙述人”一词,因为“叙述者”常用于小说文本分析中,而“叙述人”在本文中指任何叙述行为者(agent of narration)。
④胡塞尔(参见倪梁康1997:858-59)对“交互主体性”的认识是“我们可以利用那些在本已意识中被认识到的东西来解释陌生意识,利用那些在陌生意识中借助交往而被认识到的东西来为我们自己解释本已意识……我们可以研究意识用什么方式借助交往关系而对陌生意识发挥‘影响’,精神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纯粹意识的相互‘作用’”。
⑤乔纳森·卡勒在他的成名作《结构诗学》中首先阐述了体裁引出的“期待”(expectations)在释义中的巨大作用。他讨论的是诗。其实各种题材有不同的期待。弗劳恩德《读者归来》(Freund 1987:108)一书中,称卡勒的著作“提出了一种阅读理论”。
⑥此词德文原文为Augenblicksstatte,参见Heidegger 1999: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