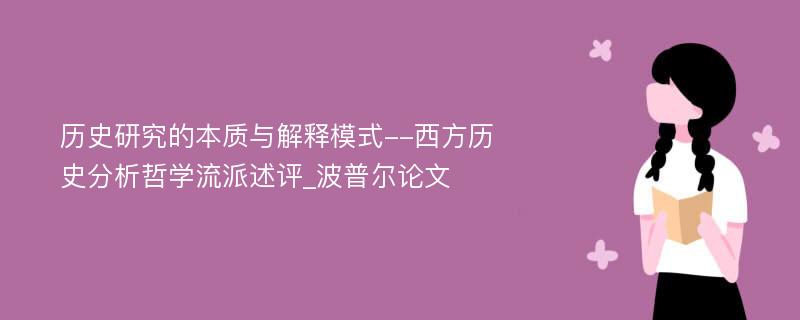
解释在历史研究中的性质及其方式——西方分析历史哲学流派观点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述评论文,流派论文,性质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是20世纪西方史学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从狄尔泰(Dilthey)1883年发表《历史知识导论》(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家们就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历史写作的形式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讨论。其间出版了许多专著。到90年代有关分析历史哲学的著作仍不断出现。这场讨论对西方史学在20世纪的革新和历史写作领域的拓展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仅是对这个重要史学流派的兴起、背景、研究主题和意义做一初步评述。
分析历史哲学或批判历史哲学,是作为思辩历史哲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分析历史哲学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性质及其方法。而思辩哲学则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力图对人类历史过程的宏观结构、目的及其意义作出猜测性的解释。(注:据认为W·H·沃尔什在其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中首先使用批判历史哲学一词,指那些区别于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索罗金等人的历史哲学著作。关于分析历史哲学何时出现西方学者有争议。明克(Louls.O.Mink)认为其开始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38年发表的《历史哲学导论》,而阿瑟·丹图(Arthur Danto)则认为其始于1942年亨佩尔(Carl.G.Hempel)发表的《一般定律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分析历史哲学的出现一般应推至狄尔泰。这是因为狄尔泰不仅对分析历史哲学的目的及其后来所要探讨的那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论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狄尔泰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注:狄尔泰宣称他打算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做那样,在历史知识中找到康德在现象知识中所发现的超越时间的理解范畴,从而使历史知识具有实在的基础。)虽然早在1874年,英国历史学家布伦德莱(Bradley)在其《关于批判历史学的若干初步意见》一文中,就对分析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但他的著述在当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布伦德莱提出历史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所有历史著述都是评判性的。因为我们选择史料和事件。过去是独立于历史家而存在的,历史家因而不能完全主观地写作历史。但是随着社会经验的增长,不论有没有发现新的史料,每一代人都重写历史。因而一切历史著述都是当代史,即从该时代的角度观察过去,从而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著述是人类历史思维的记录。任何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都是复杂现象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其复杂性是难以分析的,只能靠批判的理解。静止的现象,不变的关系可以用所谓规律来描述,如社会结构。但是关于社会发展动力和过程却不可以用规律去描述。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是新生的、具有质的差别的有机阶段。我们因此不能预见未来发展趋势。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布伦德莱的这些思想在后来的几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如狄尔泰、克罗齐、科林伍德和奥克夏特等人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布伦德莱的论文在当时英史学界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这位英国的狄尔泰才被科林伍德发现。科林伍德称该文相当于史哲学中的哥白尼革命。(注:见布伦德莱:《关于批判历史学的若干初步意见》(F·H·Bradley,"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刊载于其Collected Essays,牛津,1935年出版,及科林伍德:《历史想象》(R·G·Collingwood,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牛津1935年版。)
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同20世纪初欧洲社会政治危机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新潮流的影响有联系。但它主要还是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当时面临的深刻危机有关。19世纪后半叶是兰克史学方法逐渐成为西方历史研究主要范型的历史,兰克史学强调原始史料及批判考证原始史料的重要性。此外,兰克还主张通过课堂讨论班的形式把这些原则方法传授给学生。这种理论与实践适应了当时历史家希望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愿望,以及历史学刚开始成为大学一门学科对明确的方法论的需要。另一方面,兰克史学方法又是与西方史学自修昔底德以来的主流是相一致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这种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修昔底德—兰克传统区别于希罗多德著述所代表的社会文化史传统。这两种历史编纂模式又同中世纪神学史有根本差异。修昔底德所代表的这种史学编纂传统描述世俗的事件,以叙述为主,历史被视为文学,注重修辞,其目的在于在批判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客观地重建历史真象”。贯穿这种史学的基本观点是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历史解释是通过理解人的动机。同这种人文主义历史观相联系的又是一种贵族的世界观。历史被认为应主要描述杰出的,特别是统治阶级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国家政治发展是贯穿历史叙述主要线索。18世纪以伏尔泰为首的法国启蒙史学力图打破这种狭隘的历史视野。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以文明发展为主题。德国的哥廷根历史家们也尝试写社会史,包括人口、经济和其他非欧洲社会的历史。然而这些努力并未能打破欧洲主流史学传统。
兰克在研究与写作欧洲各国的近代史中认真地、大规模地运用了他的原则方法论。此外,兰克更进一步把他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原则传授给大批学者。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观念包括关于历史真理的客观性,事实优于理论,历史事件具有独特性,政治发展是历史叙述主体等因而获得广泛传播。19世纪后半叶,兰克的史学方法论包括其著名的通过课堂讨论引导培养学生批判考证史料的方法被首先介绍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培养历史学博士的方法。在法国,兰克类型的研讨班也同讲授课一起成为历史教学的主要形式。在英国,由于斯达布思(William Stubbs)的努力,兰克史学方法被引入牛津大学。斯达布思运用兰克方法批判考察了大量政府文件、法律和教会记录写出了《英国宪政史》。在剑桥大学,希利(Jonh.R.Seeley)教授宣称兰克使历史写作成为一门科学,主张按兰克方法来建设历史学科。(注:见哥德斯太恩:《牛津剑桥的历史研究——兰克的影响和历史研究的专业化》(Doris Goldstein,History at Oxford and Cambridge-Professionaliz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Ranke"),载于伊格尔斯和波维尔编《利奥波德·冯·兰克与历史学科的建立》(Georg.G.Iggers and James.M.Powell,ed.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1990),第142页。)
19世纪末,关于历史研究已成为一门科学的乐观情绪因而流行于西欧。历史家们相信运用德国历史家所发展出来的史料批判方法,历史家能客观地重建历史真相,并发现人类进步发展到西方社会经济、道德状况的过程。剑桥教授埃克顿(Acton)和伯利(J.Bury)的宣言清楚地表明这种乐观情绪,埃克顿宣称“鉴于欧洲档案的开放,全部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历史问题都将可以解决,终极完善的历史学已为期不远了”。伯利也认为19世纪史学的再一次飞跃使其与客观地研究自然现象的各门科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史学已是不折不扣的科学。(注:见斯太恩编:《历史写作的类型》,(Fritz Stern,ed.The Varie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Macmillan,1956),第189-190,210-223页。)
然而到20世纪初,历史家却开始讨论“历史主义的危机”。一场批判旧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运动在英美法都出现了。西方史学内部的这种深刻自我反思除同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潮有关,其主要还是归因于兰克史学方法的一系列根本缺陷。首先,由于兰克派史家强调历史写作必须始于掌握了原始史料,特别是档案中发现的文献证据。历史学日益成为一种文献研究。其次,兰克史学又同一种唯心历史观相联系,认为每一社会的行为后面都有一套复杂的目的和价值。因而历史只能通过研究人类行为的思想动机而得到理解。这种观点同19世纪正兴起的以孔德、博克尔(Buckle)和泰恩(H.Taine)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相冲突。后者认为历史解释必须依据概括性定律和历史发展规律。而历史主义则认为历史主要涉及人的行为的目的和意义。因此只能通过理解而不能通过抽象的公式去把握。第三,兰克史学从启蒙史家那种具有宽广视野的社会文明史退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大量领域被排除于历史编纂之外。历史写作集中于决策者及社会精英的意识。一般社会生活、文化、广大群众被忽视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兰克史学的认识论。兰克最著名的论断是历史家的职责在于重建历史真实。因此历史家应避免进行价值判断和运用理论。在兰克看来,历史事实本身会说明历史真相。兰克的这种观点同当时历史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日益深入的理解是背道而驰的。只需要列举与兰克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家,如德国历史家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特罗伊森(Johann Droysen)对历史事实或历史真相的理解便可看出。在兰普莱希特看来,历史研究像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必须首先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及对该问题解答的某些假设,然后历史家才开始考察资料,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他认为科学研究集中研究个别、孤立现象的时代已过去。历史家应从描述事件,转向更为概括的探索。那种认为可通过严密考证原始史料,建立历史事实,而不用解释的方式已过时。特罗伊森也提出任何历史著述都是历史家所处环境(社会制度、习俗、常规、思想方式)及遭遇(过去的遗迹,诸如纪念碑、资料等)的产物。历史家因而是创造性地,批判性地,但却有控制地重建历史过去。(注:见伊格尔斯:《20世纪历史编纂学,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Georg l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7),第31-36页;布莱萨其,《历史编纂史,古代,中世纪和现代》(Ernst Bre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Mode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第278-280页。)
兰克史学认识论不仅受到专业历史家的挑战,也遭到像狄尔泰这样的哲学家的深刻批判。狄尔泰提出历史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从内心上对过去的理解,而不是考察的结果。历史知识也就随着历史家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而变迁。历史知识的真理性因而是相对的。在狄尔泰眼中,历史家作为一个主体考察的并不是一个清楚地存在的现实,而是一个至少是在观察的过程中部分地、带历史家主观偏见地建立起来的历史现实。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贝克在后来的一篇关于历史事实的文章中较好地总结了当代西方历史家对历史事实的较为复杂的理解。贝克(Carl Becker)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存在所谓客观事实。历史家视野中的任何一个事实都是由许多小的事实组成的复合体。而这些事实的建立和表达都渗入了比较、概括和价值判断。历史家因而不能做到所谓不偏不倚。任何一个历史家对过去的看法都必不可避地体现了他所处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所具有的世界观、成见和其他观念。(注:卡丁纳尔编:《历史学理论》(Patrick Gardiner,ed.Theories of History),自由出版社,1959年版,第268页。)对兰克史学认识论核心观念,如历史事实的更为复杂的理解的出现,动摇了19世纪西方史学的认识论基础,以及那种认为历史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的盲目乐观情绪。这就是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以及分析历史哲学家们为什么要动力探索使历史学具有更坚实基础的方法的原因。
分析历史哲学的出现同20世纪哲学领域内对哲学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义也有密切关系。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哲学从探索现实,转向考察科学研究的方法、概念假设和语言基础。哲学思维从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移影响了历史哲学家。
历史解释的性质及其方式
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一个主要信念是历史家可以不偏不倚地、客观地、通过严密考察原始史料,发现事实,重建历史真相。这种观点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忽视了历史研究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史料的不完整和支离片断性及历史问题的复杂性。牛津历史学家吉佛利·巴勒克拉夫曾把历史研究概括为“试图根据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证据勾划过去的主要特征”(注:巴勒克拉夫:《变迁世界中的历史学》(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1955),第2页。)。这很简明地讲明了历史研究的性质。任何一个历史家如果不想仅把历史写作当做文献批判,不想仅停留在说明某些文献是怎样叙述某事件的,而试图较为全面地描绘和分析历史事件,都会由于史料的不完整性,而不得不借助于某种解释性的叙述,或推测性的研究结果来填补画面。另外,历史家在选择史料,或把考证后的史料组合在一起时,也不可避免地要运用某种解释性的理论框架。毫不奇怪,分析历史哲学家们在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批判考察时,对解释在历史研究中的性质及作用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20世纪分析历史哲学领域内最重要的两位哲学家是波普尔(Karl Popper)和亨佩尔(Carl Hemple)。他们是西方分析历史哲学两个重要流派之一,即同一论派的代表人物。同一论派认为历史知识同自然科学知识并无根本差异。因此历史解释应当而且必须采用自然科学中的解释模式。另一派即历史知识独特论派对上述观点持否定意见。波普尔、亨佩尔关于历史解释的性质及其形式的论点被称为“波普尔—亨佩尔命题”,或覆盖定律命题(Covering Law Thesis)。波普尔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主观的因素影响了对问题的选择,解释渗入了叙述。历史学成为二等科学。但是,如果关于个别、特殊的事件的叙述遵循一般科学发现的模式,历史研究会更接近自然科学水准。亨佩尔于1942年发表《一般定律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一文进一步发展了波普尔的思想。亨佩尔提出如果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统一体的一部分,那么历史理论也应遵循假设—演绎模式。在解释为什么某一事件以某种方式发生时借助于一般科学定律,即分析从一般定律演绎出。历史家不应满足于描述个别事件,而应分析对比相同的事件。历史家也不应当描绘某一事件,而应当指出其他先前的原因,及出现时伴随的条件。亨佩尔提出历史解释的理想模式应当是:(1)首先做出关于某类事件在某些特定时间、地点出现的陈述;(2)其次阐明关于某类现象的理论假设或一般定理。当这两项都有历史事实根据,当某一特定事件的出现能合乎逻辑地从(1)和(2)推导出,历史家便对该特殊事件进行解释了。(注:亨佩尔:《一般性定律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载于卡丁纳尔:《历史研究理论》(Carl Hempel,"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in Patrick Gardiner,ed.Theories of History),自由出版社1959年版。)
按照亨佩尔的理论,我们便可以对英国革命这样进行解释。(1)例举叙述关于资本主义农场、海外贸易的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生产技术的提高,上层建筑维持原状,同样的法律,课税制度,甚至限制某些工商业等等事件。(2)阐述一般定律或建立在对过去某些历史事件概括基础上得出的一套假设性理论,如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时,大规模的阶段斗争或革命便会发生。由(1)和(2)推导出英国17世纪内战出现的必然性、逻辑性。要大部分西方历史家承认他们在历史写作中经常采用亨佩尔所提示的这种解释途径是非常困难的。面对一系列的批评,波普尔和亨佩尔做出了进一步说明。波普尔争论说,历史家在进行解释时运用的大部分定律及原理是关于人性的一般真理。我们都信以为真,或过于熟悉,因此很少意识到他们属于一般定律。亨佩尔提出,在进行解释时,我们常模糊地提及或参照一般定律或原理。例如,当我们解释革命时,我们常指出普遍不满。但我们并没有现成的清楚明白的类似定律,例如关于不满的程度、方式及其与革命发生的可能性等等。因此,我们常不能清楚地说明这种解释后面的理论。历史家通常运用的是一种解释框架。该框架只是模糊地提及某定律和有关条件。(注:见卡丁纳尔:《历史研究理论》第351页,及波普尔:《公共社会及其敌人》(Karl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2),第264和265页。)
应当承认,历史写作与研究很难不使用抽象性的概念,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阶级、革命等。而在这些词语后面都含有某些我们可以称为一般定律的内容。此外,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复杂性又使历史研究同自然科学研究具有重大差别。自然科学家可以较容易地分离所要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家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首先面临的是从众多复杂的历史事件现象中选择他认为与此问题有关的事件或现象。因此实际上当历史家提出研究问题和选择那些他认为与此有关的事件或现象时,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与某种理论框架有联系的一般性假设。例如,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首先面临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定义的问题。这涉及到运用一般性理论。其次,历史研究者在选用或舍弃那些他认为与此定义有关或无关的现象和历史史料时,又进一步受到历史研究者本人的一些理论假设的影响。
另外,即使我们不使用规律一词,我们也无法否认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确存在某些规则性。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早在200多年前就对此有过著名论述:“生育、死亡、婚姻受到个人意志的强烈影响,显得似乎不受任何规则或计划的支配,但是每年的统计资料表明,人类生活的这些重要现象同气候的变化一样受不变自然规律的支配。”(注:康德:《关于世界通史的设想》(Immanuel Kant,"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in Hans Reiss,ed.Kant's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第41页。)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某些规则性的、群体性的、结构性的现象为其研究对象。一整套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抽象概念或亨佩尔意义上的一般性定律或理论已由这两门社会科学发展出来。这些概念、原理或理论已广泛地被运用于当代西方历史研究。任何历史家在构想、提出其研究问题和描述分析、解释历史现象时,如不参照有关的这些社会科学概念理论,或在相等水平上思维,其历史研究是会相当落伍的,并缺乏理论深度。
当然,历史解释并不是历史写作的主要的或唯一目的。历史作品的每一篇或历史家的每一步叙述也并不都涉及或必须运用一般定律。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忽视了历史著述的特征,把历史著述等同于抽象的、理论性的科学论文。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理论为我们认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提供了一有趣的观点。韦伯认为“理想类型”(假设理论框架)不是实际存在的历史现实的各种特征的复合体,而是历史家所认为的那些特征的试验性的组合体。历史家总是试图把这个观念性模式套用于个别历史现象。在该过程中会证明其是否能产生分析性效果。如其分析效用明显,它便存在于它所帮助获得的历史理解中。一旦不成功,历史家试验性地建立起来的历史现象的观念性框架便消失了。这样一种对理论的工具主义的观点也许有助于打破对历史规律的过于绝对论的迷信。
波普尔、亨佩尔命题在西方历史哲学家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亨佩尔在40年代和60年代又发表了另两篇论文讨论解释的性质及逻辑。(注:《解释逻辑的研究》(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taion)和《科学解释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对历史解释是否像亨佩尔所说那样总是需要和怎样运用一般性定律,西方史家争议很大。对波普尔、亨佩尔理论持强烈批判态度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知识独特论派的哲学家,如科林伍德、奥克夏特等。他们认为历史解释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解释。因此,试图使历史解释向自然科学解释看齐是无效的。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在其1948年再版的《历史哲学导论——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限度》所表明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温和的反对意见。阿隆认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点是以独特的时期、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对象。因此即使能从这些独特的事件和时期中抽象出定律性的理论,其运用的有效性是有限的。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定律则可适用于一切类似物理现象。(注:雷蒙·阿隆:《历史哲学导论——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限度》(Raymond Aron,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波士顿,1962年版。)
持基本赞成态度的有牛津历史哲学家卡尔丁纳,美国历史家曼德包姆(见曼德包姆:《历史知识分析》〔Mauriceu Mandelbaum,The Anatom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Boston,1997〕和沃尔什(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W.Walsh,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Hutchinoson,1958〕)。卡尔丁纳在其1952年发表的《历史解释的性质》一书中批评科林伍德和奥克夏特等人的历史知识独特论。他争论说,自然科学阐明规则的解释并不是解释的唯一类型。历史解释虽不同于自然科学解释,却在许多重要方面有共同点。(注:卡尔丁纳:《历史解释的性质》(Patrick Gardi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7,136页。)持相同观点的有著名的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埃尔顿。他的观点被认为是代表了一般历史家的看法。在他1967年出版的《历史学的实践》一书中,埃尔顿批评说那种认为叙述本身含有历史解释的观点低估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为了清楚叙述一个历史事件,需要大量的分析和讨论。历史解释如不依赖一般定律,并不意味它不遵守严格规则。埃尔顿认为,历史家常需要解释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可分为两类:直接原因和环境情势上的原因。前者解释为什么该事件实际发生了。后者解释为什么直接原因有效,为什么该事件在历史中占据一特殊位置。这两者既是结果也是后来事件的原因。(注: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G.R.Elton,The Practice of History,Fontana,1967),第136页。)埃尔顿的观点,遭到了历史家列夫的反驳。列夫不相信历史家能建立直接和环境情势上的原因。他强调历史事件的偶然,不相信存在一般定律或规律。列夫认为历史家最基本的抽象概括活动是历史分期。(注:列夫:《历史学和社会理论》(Gordon Leff,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Merlin,1969)。)
沿着波普尔、亨普尔思路探讨历史解释的性质及其方式的有历史家阿特金森。他区分了三种解释方式:(1)以规律、定律或规则的形式解释历史现象(Law explanation),如波普尔、亨佩尔所主张。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家一般运用这种方式;(2)认为历史事件主要是人类过去的行为,因而以人类行为后面的思想及动机来解释历史现象(Rational explanation);(3)以叙述的方式解释(Narrative explanation),如历史哲学家奥克夏特(Oakeshott)和盖利(Gallie)所主张。阿特金森认为历史解释可以是这三种方式的任何一种。(注:阿特金森:《历史知识及历史解释:历史哲学导论》(R.F.Atkinson,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Macmillan,1978),第138页。)在最近伦敦出版的一本历史哲学著作中,帕克区分了6种历史解释方式。在帕克看来“解释是一个通过提及相关的规律、原因和其他必要条件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的过程。”这6种解释方式是:(1)summary,列举造成某一事件的若干重要原因;(2)description of causes,陈述非原因性条件;(3)emerging causes,按先后陈述造成某一历史事件的诸多原因;(4)periodization,按时间顺序陈述集合的次要在因;(5)hierarchical typology of causes,列举造成某一事件的诸多同时发生的集合性次要原因,如以列举不能发展军用计算机、空间激光武器等来解释苏联军备竞赛失败;(6)narration of causes,按时间顺序叙述引起某一历史事件的条件。(注:帕克:《历史研究中的因果解释策略》,刊载于柯热金编著《现代历史编纂学新发展》(Adrus Park,"Strategies of Causal Explanation in History"in Herry Kozicki,ed.Developments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 ,London,Macmillan,1993),第182-192页。)这些理论为我们认识解释在历史写作中的性质及其方式提供了有趣的观点。
历史哲学家阿特金森区分了三种形式的历史解释,其中所谓Rationalexplanation是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出发来解释历史现象。那么,应怎样来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呢?这派历史家指出了一个重要概念"empathy",即历史家在历史研究中“移情”或设身处地地理解,深入历史人物内心去体验历史人物当时可能会出现的思想感情。巴特菲尔德宣称:“除非我们从历史人物内心像实际的历史行动者一样,设身处地地去体验而不是像一位观察者那样去体会历史人物的思想,历史叙述不可能正确”。(注:巴特菲尔德:《历史学与人类社会关系》(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London,1951)第146页。)我们知道,早在200多年前苏格兰哲学家体谟就提出从普遍人性出发,是历史理解的一重要原则。在休谟看来,人类行为具有相似性。如果历史家想了解古代希腊、罗马人的生活,情感倾向,他只需要仔细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脾气和行为就够了。(注:休谟:《人类理解力探讨》(D.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L.A.Selby-Bigge,ed.Clarendon Press,1975),第83页。)
这种观点代表了18世纪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即从人性论出发。维柯关于文明世界是人创造的,因而人能够理解自己(人类)的创造物(注:维柯:《新科学》(Giambattista Vico,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tr.T.Bergin and M.Fish,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第52页。)的观点出于同一思路。后来,狄尔泰发展了这种思想。狄尔泰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同自然现象有重大差别。在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动机、目的、意向及这些自由意志的后果。而在自然界则是有必然性联系的现象。因此历史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历史中发现规则、定律,而只能通过深入于历史人物内心去理解。比如我们要从文化心理去分析哥特式教堂,我们就必须重新体验历史人物设计和建造教堂的动机和观念。在狄尔泰看来,那些像实证主义者那样从外面去研究过去的历史家不会获得多大结果。他宣称:“我们解释自然现象。我们理解人类世界。该世界是心智的世界”。历史理解因而可以比喻为“从(过去的)你中重新发现我(历史家本人)”。(注:狄尔泰:《狄尔泰选集》(Wilhelm Dilthey,Selected Writings,ed.H.P.Rickm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第208页。)克罗齐更进一步声称历史知识是历史家直觉理解的结果,并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观点。
这些观点当然是可以商榷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尽管存在某些普遍的人性,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文化中具有差异性。因此,历史家往往很难正确地去体验不同时代社会人的思想感情。例如,今天生活在对在“非人”的状况下长途贩运肉牛都要举行抗议游行的时代的历史家、即使设身处地也很难理解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卫兵的思想感情。加拿大分析历史哲学家德雷在其牛津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另一途径。德雷认为历史家最好是从什么是较为合理的行为,而不是历史家本人会怎样做去寻找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为的解释。例如,对英国国王威廉为什么喜欢住到伦敦郊外的汉普敦行宫,而只在必要时才住在伦敦城中的肯辛顿宫中可以解释为是一个有肺病的人的合情合理的行为。(注:德雷:《历史解释与历史规律》(William Dray,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第134-135页。)对不合情理的行为,历史家可以从历史人物的性格、气质、倾向去寻求解释。德雷称为“性格倾向的逻辑”,即在某种情况下,由于性格倾向,历史人物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行动。按照这种理论,我们便可以以希特勒及其党卫队头目极为扭曲的性格心理来解释希特勒在部分德军高级幕僚和将领试图将其炸死于狼穴总部失败后在德国电台上对这批参与未遂政变者的指责及处以酷刑。
科林伍德以哲学的语言对深入历史人物内心去理解的解释方法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大多数的历史遗迹是历史著述,历史家因而必须发现历史著述词语后面的含义,即思想。为此历史家本人应当从头到尾地重新思想一遍。这就是所谓在历史家心中重演历史。在科林伍德看来,“人的肉体是自然过程的一个个别的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思想的潮流——历史人物及其他人的思想像海水流经一条沉船,在人类思维的无数个别框架中回旋流荡。”科林伍德因此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注: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R.Collingwood,The ldea of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第282-283页。)科林伍德关于历史家在自己心中重新发现历史人物的理性思维的观点受到了英国史学理论家斯坦福的批评。斯坦福提出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某一历史人物受到某种强烈感情的影响,我们才能理解该历史人物为什么不能以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是理智的方式行动。因此,认识驱使历史人物行动的情感,往往是非理智的,是解释历史人物行为的又一重要方向。在斯坦福看来,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已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人物、思想情感的方式和理论。(注:斯坦福:《历史研究手册》(Michael Stanford,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Oxford Blackwell,1994),第226页。)
这些关于历史理解的理论无疑是有趣的。当然其中也含有许多不可避免的缺点。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观点同一种关于历史知识性质的极端看法相联系。它认为不存在独立于历史家意识之外的现实。例如科林伍德就提出历史是历史家所构筑的。它开始于问题的提出,并不存在可供选择的历史事实。克罗齐也认为历史现实只存在于历史家头脑中。(注:克罗齐:《历史—关于自由的故事》(Benedetto Croce,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New York,1995)。)其次,应当看到尽管历史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或生活体验对历史人物的行为提出种种假设性解释或探讨途径,真正的解释和描述则必须建立在对文献或其他历史证据分析的基础上。正如亨佩尔指出的:“深入历史人物内心去体验其思想的方法仅仅提示了解释的方向,然而恰当的解释却必须依赖基本概括性的一般原理及可靠事实”。(注:亨普尔:《一般性定律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载于卡丁纳尔:《历史研究理论》,第325,353页。)历史家并不是凭自己的思想去凭空构造历史。
历史叙述的性质及其模式
60年代以来,分析历史哲学的重点从由逻辑和观念形态上研究历史家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到从逻辑观念形态上认识叙述在历史写作中的性质及其模式。区别于分析和横断性的描述,叙述以时间顺序来讲述人类事件。自西方史学在希腊开创,即是其主要形式。对叙述加以特别注意的这批分析历史哲学家认为叙述是融合和传递历史知识的特有理解形式。它注重人类的理性行为。(注:奥拉福森:《历史叙述与行为概念》(Frederick Olafson,"Narrativ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Action"),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1970年9月号,第265-289页。)奥克夏特宣称:“历史家通过对变化的全面叙述来对变化做出解释。”(注:奥克夏特:《经验及其模式》(Michael Oakeshott,Experience and its Mod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第143页。)盖利更提出历史家在缺乏证据因而不能做出流畅的历史叙述时,才去解释因果关系。“历史理解是我们运用我们追索一个故事的能力的结果。”(注:盖利:《哲学和历史理解》(W.B.Gallie,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Chatto and Windus.1964),第105页。)从语义学的角度,“历史的”这个词含有对某一事件从与其相关的过去的某些事件,或者说故事上加以理解或说明的意义。因此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批史学理论家们对叙述如此重视。如果说叙述或叙述的体系是我们理解历史的基本形式或这种理解的基本表现,那么历史著述中出现的这种叙述体系或结构源于何处呢?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两种基本观点:(1)历史事件本身以故事的形式存在。历史家只是发现这个故事的情节而已;(2)历史叙述中出现的故事情节或事件发展模式是历史家构筑的。
持第一种观点的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家,盖利(Gallie)和卡尔(E.H.Carr)。盖利认为历史本身已包括故事性情节发展。历史家在叙述时只是把构成该故事的事件连贯起来。(注:见盖利:《哲学和历史理解》,第105页。)第二种观点更为流行。这些史学理论家认为历史事件本身没有形态,也不构成一种能被连贯叙述的结构。历史叙述的故事框架是历史家给予的。法国历史家维恩(Paul Veyne)强有力地表述了这种观点。对维恩来说,历史的过去宛如未经开发整治的荒野,在这片荒野上的一切存在物真实地发生了。但是在叙述历史者赋予历史“事实”以秩序或情节结构前,历史事实并不成为历史著述的材料。维恩认为情节是历史家根据自己的意志从生活中分割下来的片断。其中的事件有其客观联系和重要的相关性。情节又可以被看作是历史家在历史事件的荒野上追循出的一条路径。每个历史家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穿越某片历史荒野的路径。所有路径都同等合法。然而没有哪一个历史家能描述历史荒野的全貌。因为路径即意味着选择。沿着路径也意味着不能走向各处。历史事件也不是历史原野上一个历史家可以选访的地方。它是那些可能形成的路径的交叉点。换句话说,是不同情节模式都可以利用的“事实”。(注:维恩:《历史写作:关于认识论问题》(Paul Veyne,Writing History:An Essay on Epistemology,tr.Mina MooreRinvoluci,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4),第15,32,36页。)
维恩的理论存在某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位旅行者(历史家)在一片原野上选择一条穿越路线时,他实际上对所要穿越的那部份原野的全貌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一定了解。美国历史家明克(Louis O.Mink)正是在这方面对维恩的观点进行挑战。明克提出历史著述中出现的历史叙述框架体现了历史家对有关历史事实的某种整体看法。历史家只有在从总体上对各相关事件进行考察、判断其意义,然后才能把它们连贯成一体系。历史著述中见到的叙述体系因而表现了历史家在试图把各相关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时如何理解和判断各相关事件的。如果维恩把历史家比喻为一位旅行探险者,费尽心力地在事件的原野上探寻一条路径,明克则把历史家想象为是站在那片事件荒野之上,试图观察琢磨出历史事件的某种模式。历史叙述的框架因而是一种鸟瞰观,或“概要性的判断”。(注:明克:《历史理解分析》,载于德雷:《哲学分析与历史学》(Louis O.Mink,"The Antomy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in Willam H.Dray,ed.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History,Harper and Row,1996),第178,191页。)
美国历史哲学家怀特(Hayden White)同样否认历史的过去是人类生活故事的堆集,而历史家只是把这些过去的活生生的故事写出来的观点。怀特宣称叙述为主的历史著作形同“文学虚构”,其内容半是创造出来的,半是发掘出来的。其体载与文学相似。在怀特看来,叙述结构的虚构性在于它是历史家创造出来,并加于某些早已过去了的,因而不能观察或通过实验加以研究的过程和结构的模式。换句话说,历史家虽未伪造事实,而且他力图发现历史事件“真相”,但他却构造故事情节。(注:怀特:《作为文学家的历史作品》,载于甘莱瑞和科茨基编辑:《历史写作:文学形式和历史理解》(Hayden Whit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in Robert Canary and Henry Kozicki.eds.The Wrting of History:Literary For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Univers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第42页。)怀特的这种观点在许多地方是颇为争议的。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曾提出我们所以理解故事情节的意义是因为通过我们的生活经验和三千年的文学传统,我们熟悉几个基本的故事情节:浪漫史、喜剧、悲剧和讽刺剧。(注:弗莱:《对批评的分析:四篇论文》(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62-163,206,223页。)怀特认为从许多重要的叙述性历史著述中都可以看到这4种情节的模式。怀特在19世纪西方历史家如米希勒(Michelete)、兰克、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布克哈特(Burckhard)等人的著作中发现了与这4种形式相当的叙述体。怀特认为这4种情节模式同不同的解释策略和意识形态含义相联系。它们不仅是同已建立的文学类型相符合,更直接地是来自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语这4种比喻形式,并激发不同的历史想象形态。怀特把这种按照情节模式来叙述历史,从而赋予历史以意义称为以情节化方式来解释历史。如果历史家在叙述历史故事时,按照悲剧情节模式,该历史家以一种方式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了解释。如果他以喜剧的模式进行叙述,他则又以另一种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了。(注:怀特:《历史形而上学: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Europ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第25和7页。)
怀特关于叙述体的历史著述形同虚构文学作品的观点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即使历史家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其著述同文学也有重大差别。历史家叙述历史必须依据所谓历史“事实”。而这些历史“事实”是经过对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献及其他物件进行考证以后建立的。这同文学作品可以随意虚构有根本差异。历史家在连接一个个事件或事实,从而构成一个叙述的体系时。该叙述的体系,或叙述的框架也并不是历史家可以随意构造的。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不论是叙述的逻辑或对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相关性的解释同历史事件的“真实结构”都有某种联系。美国历史哲学家奥拉夫森(Frederick.A.Olafson)和卡尔(David Carr)的理论可以说是对怀特历史叙述虚构性观点的某种反驳。
这种理论可被看作是一种折中的观点。它认为历史本身就呈现一种故事形态。虽然不只是一种故事形态。因此叙述的结构不完全是历史家构造的。奥拉夫森认为“叙述的结构性源于人类行为的理智性模式”。“历史家首先研究的事件是人的行动。历史叙述因而可以被理解为是重建人类行动的序列。其中一个行动及其后果成为后来一系列行动的前提”。因此历史人物的行为往往是伴随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理智性思考或推理:我想做成某件事,目前的处境,出现的机会或障碍,达到目标的手段,我因而只能怎样行动等等。正是这些伴随人类行为的思考推理连接那些历史家所要描述和解释的一系列事件。历史叙述的体系便源于对这些联系性的分析的结果。(注:奥拉夫森:《人类行为的辩证法:对历史学和其它人文科学的哲学解释》(Frederick A.Olafson,The Dialectic of Action: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第151和165页。)
在卡尔看来,“历史叙述体裁不仅是一种可能行之有效的描述事件的方式。叙述的结构实际上源于历史事件本身。历史叙述远不是对它所要讲述的事件的变形,而是对那些事件的首要特征的夸张。”许多历史事件也并不是因为它以时间先后出现所以构成一个历史故事。历史事件的故事性源于大部份历史事件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这一事实。人类行动具有结构性或故事性。我们处在某种环境条件下,想要达到某种目的,采取某些步骤去实现这些目标,在行动的过程中出现机遇、意外等等。换句话说,我们是怎样思考和行动的。这就等于一个故事的开始、进展和结尾。而且当我们在思考我们的行动时,往往把我们的思想投射到将来行动完成时的景况,并站在行动的终点上回顾我们是怎样在做的。这就等于我们给我们自己讲一个故事。因此,历史家叙述历史事件的结构皱形在人类行动过程中已出现。它并不是后来被加予的,尽管在行动后我们通常对这些行动的故事性加以提炼。(注:卡尔:《叙述与事实》(David Carr,"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载《历史与理论》第25卷,1986年,第125页。)丹尼特曾提出每个人实际上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断地给自己讲一个关于自己过去的生活的故事。这种行为就构成心理学家或哲学家称之为的自我观念。(注:丹尼特:《人类意识的解释》(Danniel Dennet.Consciousness Explained.Little Brown,1991),第410-418页。)与这种观点多少相似,卡尔也认为当一个历史家,如米希勒、马考莱或者班克罗夫特,在讲述有关一个民族的故事时,他也在帮助建立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或民族感。在卡尔看来,我们能够通过参与共同的集体的行动,分享共同的经验,并讲述有关这些行动和经验的故事,建立一种集体的自我认同。“当我们把一系列事件看做是时间上的不同形态,其现阶段从其与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将来获得意义,我们便获得一个共同的经验”。(注:卡尔:《叙述与事实》,第127页。)
毫无疑问,叙述是历史著述的一个重要形式。这是由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但是对历史过程的解释并不像赫克塞特所认为的那样只能以叙述的形式。在即使以叙述为主的历史著作中,我们看到对背景的描述,或对原因的分析解释都是不可缺少的。任何一本纯叙述形式的历史写作都会被看做是缺乏深度的。即使对人类意识的理解,也可以在对其社会存在的分析中更好地达到。历史事件可以在分析其出现的结构或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互作用中得到更好的理解。正如丹图所争辨的那样,历史事件只有在被某种形式的描述中才能得到说明。这种描述既可是非常具体的也可是非常抽象的。比如一个人的死亡,既可以从生理学上去描述,如医院报告,又可从政治上,从个人历史角度去描述,如国王的死亡。同样一个事件的描述则既可以借用一般科学定律或理论,也可以用叙述的形式。二者不可互代。(注:丹图:《分析历史哲学》(Athur 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第24页。)当代大部分历史学术著作,并不是以纯叙述的形式出现。历史不仅可以垂直地叙述而且可以在平面上描述。
结语
自分析历史哲学兴起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史学以兰克著述为代表的声称历史家能够通过严密考证史料,从而重建历史客观真实,以及运用诸如绝对精神、国家观念或神意等形而上学观念,或超验的庞大历史理论体系解释安排历史事件已不多见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已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当代历史写作。不论是在以叙述为主,或以结构分析为主的历史著述中,我们都看到一种对概念的更清楚的定义和注重语言的确定性,以及在做出一般性推论时的慎重性。西方史学的这种质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同分析历史哲学家们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历史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深刻批判有关。
亨佩尔的借用一般科学定理命题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历史研究的一个广泛而深入潮流的先声,即所谓历史跨学科研究。历史家们借用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及文学批评的概念,发掘和构想历史研究新课题,并运用这些学科的一般原理解释历史现象。不论是年鉴学派的整体史或全球历史,或以研究近现代初期国家政权、国民经济和宗教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的所谓微观史学都表现了历史家们试图使历史研究更为“科学”或向社会科学看齐的努力。
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西方史学新潮流、新特征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它同哲学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思潮有互为影响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了所谓语义学转向。这种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桑绪尔(Saussure)、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等人所发展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雅可布森以来的人类学的巨大成功所引起的。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法理论也受到雅可布森的影响。60年代语言学是社会人文科学中最充满生气、发展最大的学科。从中产生不少亨佩尔意义上的一般原理或原则。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对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叙事史的兴起、年鉴学派的结构主义史学和微观历史学的出现表现了西方史学的多样性。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关于历中知识性质问题的两派观点仍可在这种多样性中看到其影响。新叙事史同历中知识独特论有某种理论关系,而在整体史学、结构主义史学、微观史学和历史社会学著作中,我们则看到同一论的强大影响。可以看出,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在关于历史知识性质问题上的对立两派并未得到调合。本文所述及的那些问题并未有定论,尽管我们看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使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的性质及模式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注:70年代末,劳伦斯·斯通在其著名的题为《叙事史的复兴》论文中曾批评一度流行的以社会科学为模式的历史研究潮流。斯通宣称历史家们“试图对历史变化获得一种连贯科学解释的努力已终结”。而在1991年同样发表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的另一篇题为《历史和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中则描绘了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对历史研究的新的强的有力的影响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这些新潮流把政治的、制度的和社会的实践看做是推论的符号体系或符号,见斯通《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in Past and Present,131(August 1991),第217-218页),而在最近出版的另一本历史哲学著作中,作者则争论说社会进程同地球的历史演变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人类信念和理论的影响,客观地理解历史和以科学的方法认识历史并不是不可能的。见劳埃德:《历史的结构》(Christopher lloyd,The Structure of History,Oxford,Blackwell,1993.)。)同样清楚的是,本文所述及的大部分理论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唯心论的或相对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许多合理的、令人深思的论点。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上反思我们的历史研究,从而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在更高水平上进行。
标签:波普尔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物理定律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 history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