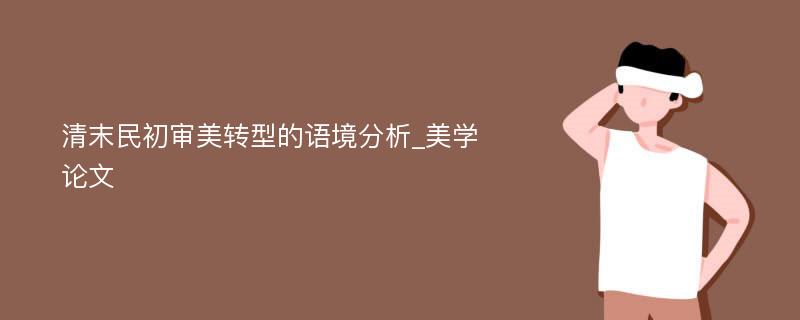
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语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语境论文,清末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5-0038-09 一 引言 “语境”(context)一词,是英国美学家和诗人、剑桥大学教授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80)创立的语义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1923年,瑞恰慈在与奥格登(C.K.Ogden,1889-1957)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中将语言分为“情感语言”和“符号语言”两个部分,他们认为,情感语言的意义有一个心理语境的问题,符号语言的意义则由上下文的结构语境决定。1936年,瑞恰慈在他的《修辞哲学》中将“语境”的概念扩大至由语言所指称的对象的历史环境。之后,专门从事意义的语境理论和韵律分析的英国语言学家、伦敦语言学派的创立者弗思(Firth,1890-1960)发展了瑞恰慈等人的理论,他提出从语言的内部结构和形式结构来反映外部语言环境的一般理论,把语境分为来自内部的“语言语境”和来自外部的“情景语境”。根据已有的研究,语境既指语言内部特定的言语片段和词语之间的关系,也指进行交际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前者可谓内部语境,后者可谓外部语境,相同的语言符号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也可以说就是语言交际的时空关系,研究语言时间关系的是历史语言学,研究语言空间关系的是地域语言学。 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李安宅将瑞恰慈的语义学和语境理论运用于他的《美学》专著中,开启了中国运用语境理论进行美学研究的先河①。李安宅说,作科学研究,“必在语言文字上发生自觉。有了自觉——即使不是充分的自觉,沉疴已去大半。所谓自觉,在消极方面,要觉到语言文字的障碍;在积极方面,要分析语言文字的运用。积极的功夫,可以建设意义的逻辑;消极的觉醒,可作这门学问的先驱——是一切清明思路的门限,是任何科学的始基”[1]3。而一个学科的转型必然受到语境的“规范性”制约。例如“美”的概念,先秦时期以“羊大为美”或“羊人为美”来规范;古希腊时期的“美”的概念则既涉及“美学”也涉及“伦理学”。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的概念,指的却是“女子和小孩”。之后,“美”被“广泛地用来指称一切种类的美”[2]140。再如,“崇高”审美范畴,从空间语境看,在中国先秦时期它带有自然崇拜的色彩,而在古希腊时期指的却是三大雄辩风格中最高级的一种风格。从历史语境看,伪朗吉努斯所作的讨论修辞学的《论崇高》论文在17世纪经布瓦洛的诠释则把它“当作讨论美学的论文来研读”[2]196。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前苏联时期,“崇高”的概念与“英雄”的概念相一致,“被理解为鼓舞人们、阶级、社会去进行创造性的、革命的活动的一种壮丽的和人道的理想。崇高表现的最光辉的典范就是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3]189。由此可以看出,特定的语境制约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这个性质在清末民初的美学转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清末民初美学概念的语境分析考察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某些特征,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二 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社会语境 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是在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向工业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资本经济结构、多元文化形态和以自由、民主、科学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变的社会语境中产生的,也是中国美学从古代理论形态向现代理论形态发生转换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曾指出,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的时候,“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因为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4]534-535。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民族意识都受到特定的“历史语境”的限制,并总是会产生本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普遍意识之间的矛盾。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也难逃此“精神的纠缠”,这种矛盾和纠缠在语言上的反映即是语境和语义上的差异,这在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美学因其先进生产力和世界贸易的裹挟,作为一种世界的“普遍意识”迅速传播至东方古国。西方话语体系凭借坚船利炮和先进的文化形态以及科学的文明意识一直占据着清末民初美学研究的主体地位和支配地位,致使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从一开始就受到代表西方价值体系的话语形态的制约。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和规律成为一种“幽灵”,无时不在清末民初的美学转型中游荡。另一方面,由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丧失了宝贵的历史发展机遇,奋起直追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同时却将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束之高阁,在西方文化东渐大潮中没有采取客观科学的价值取向对待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将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一刀斩断,致使中国美学转型失去“背景语境”,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因此,中国美学受到西学冲击和旧学衰颓的双重挤压,走上了极为艰难的转型之路。 当此之时,梁启超和王国维独具慧眼,看到了整个学术语境的变迁和否定消解传统文化带来的危害。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首先意识到中国旧有之学的痼疾,主张变法以取西学,但他对全盘西化的观点也不赞同。梁启超认为: 旧学之蠹中国,犹附骨之疽,疗疽甚易,而完骨为难。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藉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谓希腊、拉丁)英法之文,亦为上口,声光化电子学,亦为寓目,而徒“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据其五。若不思补救,则学者日伙,而此类日繁,十年以后,将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后,将十八九矣。呜呼!其不亡者几何哉?[5]《西学书目表后序》,126-127梁启超看到了打起西学的幌子而欲置传统文化于死地的“假洋鬼子”的祸害。他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主张,欲变法强国,必先翻译西方书籍,而“繙译之事,莫先于内典。繙译之本,亦莫善于内典。故今日言译例,当法内典。自鸠摩罗什、实义难陀皆深通华文,不著笔受。元奘之译《瑜伽师地论》等,先游身毒,学其语,受其义。归而记忆其所得从而笔之。言译者当以此义为最上”[5]《变法通议·论译书》,75。梁启超认为,译书者必须兼通中学与西学,亲身经历对方国家的文化和风俗,才能正确无误地翻译出西方学术专著的本来面目。尤其是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为西学书籍翻译的法式,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显然已经意识到魏晋文化转型时期外来的印度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相浃与化的历史经验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表现出对旧学有选择的尊重。 无独有偶,王国维也以汉魏之际印度佛教的传人为历史镜鉴,他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比作摄摩腾翻译的《四十二章经》,甚至称西洋思想为“第二之佛教”: 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繙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6]《论近年之学术界》,121 王国维一方面“惧邪说之横流”,担心因翻译等各种原因致使西方新学不得真传;另一方面又“恐国粹之丧失”,致中华五千年文化毁于一旦。面对这种双重压力,王国维在研究了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本土文化从“刺激—冲撞—融合”的历史规律后,指出建立“纯粹哲学”学科势在必行。王国维认为,西洋思想的传入犹如汉魏之际佛教的输入,必将对中国学术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他同时有远见的指出,西洋之思想与中国固有的思想并不相同,“风俗文物殊异”,“则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观乎三藏之书已束于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事之不忘,来者可知矣”[6]125。为了使中国美学的转型不至于失去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针对“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7]《国学从刊序》,131的现实,王国维大声疾呼学术的独立和设立“哲学”课程,力倡西来之“美学”为经学(理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之必修课程以奠定美学学科之基础,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对中国固有的美学概念、命题和范畴进行现代阐释。王国维的“以中解西”虽然还很难说已经是对西方美学的“综採”和“融冶”,但他注重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却成为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不二法门,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焦虑与担忧实际上反映了清末民初社会剧变给美学转型带来的双重挤压。一方面,中国美学要面对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被剥蚀——“三《传》束阁,《论语》当薪”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源源不断地随着洋枪洋炮的硝烟而东渐的西学,从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走向凤凰涅粲。这种双重挤压的社会语境,从一开始就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三 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翻译语境 中国美学有自己一套几乎完全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和规律,只有把中国美学放在它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情景语境中,才能追问到的它特殊性,才能对中国美学的转型给出合理的现代阐释。但美学又是一个泊来学科,惟有通过翻译才能获得这个学科的一般知识,而翻译中的“失真”往往带来学科知识的缺失。这个矛盾在清末民初的翻译语境中显得尤为突出。 自清顺治元年(1644)承继明代“四夷馆”而设立的“四译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8]2-3后,到咸丰十年(1861年)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8]6而创立的“同文馆”,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上海广方言馆为工业学堂,有清一代,翻译外国书籍文书等事务在清王朝中均有专门机构署理。随着翻译机构的设立和康有为、梁启超的鼓吹②,包括俄国、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书籍源源不断地被翻译进来。在这些图书中,虽然主要是化学、医学、“格物”、算学、地理、农田、兵学等西方科学技术一类的书籍,但也有艺术、法律、哲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一类的书籍,如1888年印行的法国学者钱德明著的《中国古代宗教舞蹈》、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由陈鹏翻译的介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三大哲学家说》、1903年由上海汇文学社出版的范迪吉等翻译的日本学者富山房著的《美术新书》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的周暹翻译的德国汉学家尉礼贤撰著的《康德人心能力论》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关于逻辑学的著作,如王国维翻译的英国随文的《辨学》(京师五道庙售书处1908年印行)、刘经庶翻译的杜威的《思维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印行)被翻译介绍进来,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旧有之概念、词汇等学术语境不能适应重思辨性的西洋之学的需要,“故欲通西学者,必道原于希腊罗马名理诸书,犹欲通中学者,必道原于三代古籍周秦诸子也”[5]71。而这些逻辑学专著的翻译以及新学用语的普及必将带来美学的逻辑体系的变化,与传统美学注重经验和体验的旧学形态形成明显的差别。 与此同时,因翻译而带来的美学理论的语义歧义也不断产生。“在晚清时期的翻译中,失真和独创常常是一对孪生姐妹”[9]10。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的词语一般都是通过日语翻译进来,而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的时候,由于日语总词汇的缺乏,大都使用日语中的古代汉语或和制汉字词来进行翻译,将西方概念中与古代汉语相近或相似的词语进行拼接。正如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1855-1944)所说: 当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对应词时,除了参考《佩文韵府》、《渊鉴类函》、《五车韵瑞》之外,还通过大规模参考儒家经典、佛教经典来进行遴选。[9]69 以日本著名学者西周(Nishi Amane)创造了诸如“哲学”、“观念”、“意识”、“抽象的”、“具体的”等787个词汇来翻译“philosophy”、“idea”、“consciousness”、“abstract”、“concrete”等西方哲学术语,而在这787个词汇中,有242个词汇来源于古代汉语[9]67-68。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西周的最大成就,是通过创生大量新词汇来翻译西方概念,进而丰富了日语。从长远来看,这也丰富了汉语。”[9]66 以“意识”为例看,西周很有可能参考了中国当年佛经的翻译来翻译西方的术语。日语的“ishik”(意识)来源于中国的古汉语。王充的《论衡·实知》篇就用了“意识”这个说法:“众人阔略,寡所意识,见贤圣之名物,则谓之神。”[10]401后来玄奘在翻译佛教唯识宗的经典《成唯识论》时用了“识”这个术语,而“识”的感知作用可以分为六个类别,其中五种符合感觉器官的五大功能,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而第六种感觉功能就被称作“意识”,也就是“识”思想上的感知作用。西周所首创的“ishiki”(意识)这个术语很快被作为英语“consciousness”的翻译得到认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前后以“意识”的符号形式进入汉语。日本学者Kawakami Hajime(河上肇)在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时,首先用“ishiki”(意识)来翻译德语“Bewusstsein”(意识)。之后,李大钊在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把相应的汉语词“意识”作为“Bewusstsein意识”的对等词,并一直持续至今日仍在使用。在这种中日古今语言双向交错、混合回归的语境下,“美学”一词的翻译自然成了清末民初美学转型中的焦点。 关于中国最早在学科上使用“美学”一词的现代意义,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据黄兴涛的考证,在英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1866年所编的《英华词典》中,翻译英语“Aesthetics”(美学)一词的汉语表述没有用“美学”这个词汇,而是用的“佳美之理”、“审美之理”。1875年,在由中国人谭达轩编辑出版、1884年再版的《英汉词典》里,“Aesthetics”(美学)则被翻译成“审辨美恶之法”,这种翻译基本上没有传译出德文美学的含义。同文馆的德文馆于同治十年(1871年)开设,当时翻译的重点在算学和天文学,没有“哲学”的位置,但毕竟开始有了德语的输入。最早在学科和现代意义上使用“美学”这个汉字词的则是德国著名来华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73年,花之安在他用中文编著的《大德国学校论略》(重版又称《泰西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中介绍到西方心理学和美学有关的内容,其中包括“绘事之美”和“乐奏之美”。1875年,花之安又编著了一本《教化议》,他在书中提出“经学”、“文字”、“格物”、“历算”、“地舆”、“丹青音乐”为“救时之用者”,而在“丹青音乐”后面特别加以括弧注解道:“二者皆美学。”[11]75-76 1902年,王国维在翻译日本文学博士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第二十节“自然之理想——宗教哲学及美学”时开始使用“美学”这个术语:“当解释自然之行程而加以目的之概念,则其本质亦生特别之意味,又其评价亦异即以自然之本质为神(向目的而发达之神)。或由理想之点观察之,前者宗教哲学之问题,后者美学之问题也。”[12]286同年,王国维在翻译日本文学士牧赖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时再次用到“美学”这个术语:“欲使教授时有生气,有兴味,而使生徒听之不倦,不可不依美学及修辞学之法则。”显然,这里的两个“美学”术语的含义有所区别,后者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美育”。这个情景语境的含混在日本学者那里就开始形成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竹内敏雄还说:“必须指出,在我国现在通行的‘美学’这个名称同样是不十分确切的,但是没有比它更好的词语,所以索性就作为Asthetik的译词通用这一说法(从前还有‘审美学’等其它译名,但还是‘美学’好一些)。”[13]116谭大轩、王国维与英国、德国传教士在翻译和使用“美学”一词上面的差别反映出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语境特征。 谭大轩把“美学”解释为辨别区分“美”与“恶”的概念和有关“美”“恶”知识运用的法则。简言之,美学为“审美(恶)之学”,这与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的“审美之理”相似而异于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所谓“丹青音乐皆美学”之说。花之安的翻译则与今天所谓的“艺术学”接近,而王国维的翻译则同于日本学者的翻译,在意思上接近谭大轩的译法。但无论是花之安还是罗存德,抑或是王国维和谭大轩,都没有完整的翻译出鲍姆加登(1714-1762)的“美学”的意思。花之安将本为“艺术学”的绘画(美术)和音乐学作为美学的内涵仅涉及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与鲍姆加登的“感性认识的科学”之说还有距离,但他代表了德国19世纪后期美学研究的转向,即将艺术纳入美学的研究范围。花之安的“美学”概念对宗白华有着深刻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后期,宗白华在一次有关艺术学的讲演中还提到:“艺术学本为美学之一,不过,其方法和内容,美学有时不能代表之,……美学的活动,包括艺术品的欣赏和创造,自然的欣赏,人类之交接礼仪等等。”[14]511-5121932年,宗白华在介绍两本中国画学著作的时候再次提到:“美学的研究,虽然应当以整个的美的世界为对象,包含着宇宙美、人生美与艺术美;但向来的美学总倾向于以艺术美为出发点,甚至以为是唯一研究的对象”[15]43。谭大轩、王国维和英国传教士罗存德将“Aesthetics”翻译成“审美学”或者“美学”,又很难从汉语词汇的概念上找到鲍姆加登关于“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的规定性。事实上,鲍姆加登当年在使用这个源于古希腊语的“Aesthetica”(感觉、知觉)时,也在不断地思考和完善,从1735年的《哲学的沉思》首次使用这个概念到1741年把“Aesthetica”命名为“感性认识的规律”,再到1742年在《形而上学》第2版里称其为“感官鉴别的科学”,从1757年在《形而上学》第4版里改称为“美的科学”到最后在1758年命名为“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加登始终以“感性认识”为美学研究的重点。正是在这种情景语境下,“美学”这个汉字词汇被日本学者用来翻译鲍姆嘉登的“Aesthetic”。时至今日,我们都还在为到底怎样翻译才算正确传达了鲍姆嘉登的“Aesthetic”的真正的学科内涵,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感性认识能力”还是“美”和“艺术”而争论。如果照汉语字面意义或日“符号外壳”来理解,“美学”显然是“研究美的科学”或“研究美的学问”的意思,这与鲍姆嘉登的初衷明显不同。 从1757年到1802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担任“纯粹哲学”讲席讲授《形而上学》、《逻辑学》、《自然地理学》等课程时,曾经选择鲍姆加登的著作作为教学参考书,称其“丰富和精确”[16]313,康德在前批判时期已经开始考虑到纯粹理性批判与鉴赏力批判即美学之间的关系,鲍姆加登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前批判期的经验主义美学影响很深。康德的贡献在于,他使鲍姆加登开创的“美学”从仅仅作为一门感性认识的科学向美学成为由感性认识向自由意志过渡的不可或缺的桥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的时候,主要以研究人们的感性经验和感性认识为主,或者说美学主要是一门“经验科学”。而无论是谭大轩、王国维还是和英国传教士罗存德、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翻译,都尚未完全传达出鲍姆加登的“美学”的原有之意,其原因在于“语言一般是不可译的”,任何一种语言被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词量的借用、扩充或者新造,借用、扩充和新造因语境的不同难免会出现语义“失真”的现象,“美学”术语的翻译正是这种“失真”的典型。 四 日源外来词美学概念的“重语”现象 除了因两种语言的历史语境不同而造成美学术语的“失真”外,翻译过程中还会出现“重语”的现象。如前所述,由于历史语境的限制,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很多关于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大都属于汉语的“日源外来词”,它们来自于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的日本,而日本又从德语、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翻译过来。据崔崟、丁文博的统计,在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著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有889个日源外来词,而在这889个日源外来词中,与美学学科相关的有131个,例如审美、美感、美化、情操、哲学、形而上学、唯心论、唯物论、表象、抽象、概念、范畴、原理、观念、批评、观照、知识、意识、直观、直觉、主观、主体、自由、文学、艺术、建筑、人格、思潮、思想、美术、悲剧、喜剧、作品、作者、想象、象征、内容、感性、理性、绝对、相对、客观、客体、类型、理论、理念、现实、现象、意匠、意义、印象等等,约占整个日源外来词的15%[17]173-177。这些词汇构成了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语言语境”(“内部语境”),制约着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和现代转型研究。当我们用现代汉语来翻译这些日语的时候,由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义差异具有双重语义特点,这就出现了翻译中的双重语义的重叠现象。我把这种双重语义的重叠现象称之为翻译中的“重语”现象。清末民初中日语言交流中所产生的借词——“汉语回归借词”和“原语借词”——的双重性质,致使中国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与西方美学相比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只有首先弄清楚它们之间的本义和借用义以及翻译中的回归义,我们才有可能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美学自身的术语、什么是日语来源词以及它们之间的同和异,从而清理出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语言语境。 例如“美化”一词,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加以装饰或点缀使其美观”。据《汉语外来词词典》,现代汉语的“美化”来自日语的“美化”(“bika”),而日语的“美化”(“bika”)则来自中国的古代汉语[18]234。早在南北朝时期,“美化”一词就开始流行。《宋书·武帝纪》就有“美化”一词,原文为“辩方正位,纳之轨度,蠲削烦苛,较若画一,淳风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绝域献琛,遐夷纳贡,王略所宣,九服率从”(《南史·宋武帝纪》“盈塞宇宙”作“盈塞区宇”)。“美化”在这里的本义是说在“宋公”刘裕平定桓玄和卢循后,东晋疆域内国泰民安,社会风气淳朴有序。“淳风美化”也就是“风化淳美”的意思,这是东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封赐刘裕为“宋公”的诏策中的话,自然有虚饰的成分在里面。现存《宋书》为南朝梁代的沈约所编,李延寿的《南史》编撰于唐代初年,“美化”一词很有可能是随着日本“遣隋僧”或“遣唐僧”的回国而传到日本,通过“汉语训读法”③,按日语的文法读汉文,并在日本传播开来。到了明治中期,即1885年前后,日本学者用源自古代汉语的“美化”来翻译英语的“beautification”。 依据日本汉学家铃木修次的研究,“新汉字词产生的截止期限定在明治中期,即1885年前后”[17]33,日本人创造的新汉字被广泛使用,也极有可能是“按照汉语的语素和语素意义,并按照汉语的构词法则去构造的”。从甲午战争(1894)到五四运动(1919),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流进入一个高峰期。“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间,日文版的中译本已经上升到译文书的第一位,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创造的汉字词(即和制汉字词)大量流入中国。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研究,1906年的中国留日学生已多达8000人。自此,日语中的和制汉字词就源源不断的通过留学生之口、留学生之手传入中国。自古以来,汉字、汉语词汇的单向流动(中国→日本)开始变为双向交流,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几乎变成由日语到汉语(日本→中国)的另一种单向流动”[17]24-25。与美学和艺术有关的词汇,诸如“美术”、“曲线美”、“演技”、“音符”、“画报”、“摄影”、“水彩画”、“裸体画”、“文学”、“艺术”、“叙事诗”、“抒情诗”、“旋律”等词汇大量进入中国。“美化”这个“重语”词汇也有可能从日本回流到中国,成为“同形异义”的汉语外来词。 但日本人在使用古代汉语翻译西方美学概念的时候,如果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则将古代汉语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新的西方概念。比如现代汉语的“美感”一词,意为“美的感觉”,源于日语的“美感”(“bikan”),日本学者用以翻译英语的“Sense of beauty”。而中国古代却没有双音词“美感”,只有单音词的“美”和“感”,这就造成了翻译中的“缺失”。 王国维当年在论新学术语的输入时说,如同当年翻译佛典苦其“周秦言语”之不足一样,“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但日本所造译之汉语则可利用。“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王国维认为,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术语时十分慎重,大都经过长时间的推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经日本这个翻译的“驿骑”,新学术语大量涌现,因此,使用日本翻译的新学术语,在行文的准确和概念的精确上要比自己创造的新词来翻译西方书籍好一些;但日本学者也有不甚精确之处,如用汉语的“观念”、“直观”、“概念”翻译“idea”、“intuition”、“conception”,他甚至觉得用《荀子·正名》的“共名”翻译“conception”亦可;而且在翻译时,“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9]128-130。最晚在8世纪后期,古代汉语的“感”字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学者在15世纪有意识、明确地将“感”作为一个审美概念来使用[19]。因此,“美感”这个双音词极有可能就是日本学者将“美”与“感”这两个“中国习用的单字(单音)”词合为一个双音词“美感”来翻译西方美学中的“sense of beauty”的结果。 崔崟、丁文博把汉语中的日源外来词分为“汉语回归借词”和“原语借词”两类,“即如果某词首先出现在中国的文献资料上,传到日本后词性及词义未发生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又原封不动地返回中国的,可判定该词是汉语回归借词。反之,如果某词在中国的文献资料上产生而首次出现在日本文献资料上的,或者词形虽然在中国文献资料上曾有记载,但是流入到日本后语义发生了改变,经日本语义改变后又回流到了中国的词语,可判定为原语借词”[17]41。按照这个分类,“美学”、“美化”、“审美”以及“美术”、“文学”、“文化”等都属于“原语借词”。“单从语言层面看,日源外来词具有双重性质。虽然同汉语一样构成要素是汉字,但是它在日语环境下产生,不可避免地带有日本语言、日本文化的特征,同时,它又是汉语外来词,汉语、汉文化的要素又不可泯灭”[17]92-93。按照日语构词法,源自日语的汉语新词,又可分成“单纯词、复合词、派生词”。依照这个分类,“美化”和“美感”都属于日本和制汉字词的“原语借形词④,“美化”可以说是单纯词中的借形词,“美感”则属于复合词中的借形词。 “审美”也是一个日源外来词中的“原语借词”,日语为“shinbi”,意思是“领会事物或艺术品的美”,由日本学者根据英语“aesthetic appreciation”意译而成[18]312。日语的“审美”一词,似由王国维开始将其运用于美学研究领域。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分析《红楼梦》的“壮美”特征时认为,如宝玉与黛玉最后相见的情景,“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凡稍有审美之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7]69。日本也曾经用“审美学”来翻译鲍姆加登的“美学”(Aesthetic)。而中国古代表达与“审美”同一个意思的词用的则是“课美”。“课美”源自王粲的《玛瑙勒赋》:“游大国以广观兮,览稀世之伟宝。总众材而课美,信莫臧于玛瑙。被文采之华饰,杂朱绿与苍皂。”[20]24“课”的本义为“试”和“第”,即“尝试、品第”之意,“课美”有“审美”的含义⑤。王粲这里所用的“课美”,实际上也就是对玛瑙之自然美的“审美”。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每一种语言,无论有多复杂,都处于一种由古老的呼声一劳永逸地设置的开启中。与其他语言的侧面相似——邻近的声音包含着类似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每一个语言与这些深层的、深埋的和几乎沉默的价值之间的纵向关系而被注意和记录”[21]305。通过日语翻译引进中国的美学的日源外来词中,无论是单纯词还是复合词中的借形词,抑或是回归借词和原语借词,它们与中国固有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显现出“重语”特征,这种翻译语境中出现的“重语”特征是清末民初美学转型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 五 结语 通过对清末民初社会语境、翻译语境和日源外来词的语义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惟有把中国美学放在它产生的情景语境(外部语境)和语言语境(内部语境)中才能追问到的它的本源性和特殊性,从而形成理论的规范性,才能对中国美学的转型给出合理的现代阐释。清末民初中国美学的转型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新民救国和洋务运动的需要,从西方输入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在这种时代思潮的冲击下,包括美学思想资源在内的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汉魏之际“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22]《仲长统传》,1646的历史现象再次重现,致使清末民初的美学转型失去历史语境,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此为梁启超和王国维大声疾呼保存旧学的原因所在。因此,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受到西学冲击和旧学衰颓的双重挤压。第二是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在理论术语和概念、范畴的语义规范上受到日本等外来词汇的制约。这些词汇中有些是中国古代传进日本的词汇,日本因自身词汇的贫乏借以翻译西方美学理论。但这种借用,无论是借形还是借音,日本学者都赋予了它们新的涵义。这种借用词又在清末民初回归中国,由留日学者从日语翻译进来,赋予它们时代的语用意义,这在美学概念上便造成了双重语境即“重语”的问题。因此,惟有从双重挤压和双重语境中解放出来,才能建成中国美学的“意义的逻辑”,建成中国美学的“科学的始基”。 收稿日期:2015-03-09 注释: ①李安宅(1900-1985),河北省迁安县人。1924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深造。1936年回国,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李安宅的《美学》,1934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后来编入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他的《语言·意义·美学》一书中,该书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再版。 ②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国家要富强,只有译书而已。梁启超说:“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 ③日本汉学家石川忠久说:“汉语训读法是公元八、九世纪在日本确立的,即在汉文字上注训点,按日语的文法读汉文。正因为有了训读法,即便在遣唐使被废止后,日本人也没有在阅读汉籍上产生困难。”参见:《日本的文化基础是汉文——访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石川忠久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4日第8版。 ④崔崟认为,和制汉字词的借形词“是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语言的过程中,按照汉字词的造词结构创造的新词语。它们数量最多,构成原语借词的主要部分。例如:‘辩证法’、‘传染病’、‘电话’、‘代表’、‘概念’、‘干部’、‘公仆’、‘美感’、‘内分泌’、‘无产阶级’等”。见:崔崟、丁文博《日源外来词探源》,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3页。 ⑤《说文解字》:“课,试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随部第十》云:“课,试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五上:‘课,第也。谓品第之也。’《逸周书·大匡解》云:‘程课物徵。’”审,古作“審”,有“观察鉴别”和“反复覈实”之意。《说文·采部》:“宷,悉也,知宷谛也。从宀、采。”又:“審,篆文宋,从番。”段玉裁注曰:“(徐)锴曰:‘宀,覆也。采,别也。能包覆而深别之也。’按此与‘覈’字从两、敫同意。”又《说文·襾部》曰:“覈,实也。考事而笮徼遮,其辞得实曰覈。”段玉裁注:“襾者,反复之。笮者,迫之;徼者,巡也;遮者,遏也。言考事者定于一是,必使其上下四方之辞,皆不得逞,而后得其实,是谓之覈,此所谓咨于故实也,所谓实事求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52、378页。标签: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读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王国维论文; 日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