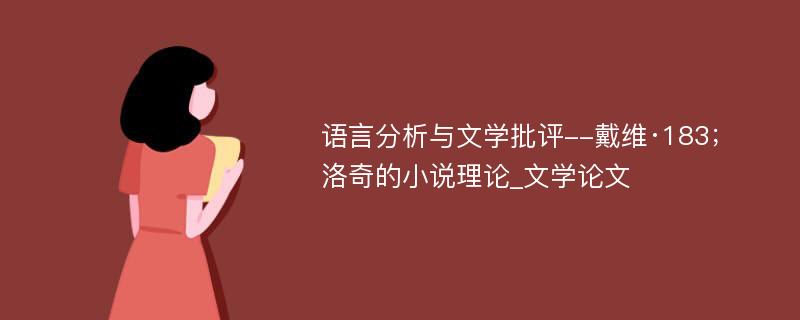
语言分析与文学批评——戴维#183;洛奇的小说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洛奇论文,理论论文,语言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文学评论家伯纳德·伯冈兹在谈戴维·洛奇的独特性时这样说道:在英国文学史上,诗人和批评家兼于一身者很多,而小说家与批评家二者兼于一身者却寥寥无几,除了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之外,就是洛奇了。(注:Bernard Bergonzi, David Lodge,Nothcote House,1955,p.48.)总的来看, 戴维·洛奇的文论带有大学教授的特色。自1960年至1987年,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任教二十七年之久。主要开设的课程,按他自己的话是“形式与小说”,(注:David Lodge,The Art of Fiction,Penguin Books,1992,p.ix.)他的文学批评论著也大多写于他执教期间。他的文论既有学术性,又颇有授业解惑之感。如讲解当代文论中的流派、术语,系统地分析评论英国现当代文学史和西方文学理论。具体地说,人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观点是他提出的“钟摆状说”,即近百年来英国文学主流的走向是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极间不同程度的来回摆动。(注: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Edward Arnold Ltd. London,reprinted,1979,p.52.ix,viii,94,110,245.)但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文论还表现出他对小说理论的偏爱,对现实主义小说美学分析的探求。
一、小说也是语言艺术——细节、意象及重复
在写于1966年的《小说的语言》中,戴维·洛奇开宗明义表明了他的写作宗旨:“小说家使用的媒体是语言,不论他写什么,就他而言,他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来写作。”(注: David Lodge,Language of Eiction,London,second edition,1984,p.ix,34.47,74,73.)这一观点他在其后的著作中反复声明,并强调“所有有关小说批评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注: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Writing,Edward Arnold Ltd.London,reprinted,1979,p.52.ix,viii,94,110,245.)
洛奇的这个观点是针对当时小说批评方面的状况而言。当时英美新批评理论在诗歌分析方面生气勃勃,而小说批评则显得苍白薄弱。他认为,这种状况最终根源于长期以来人们的偏见。自从浪漫主义以来,就有一种重诗歌轻小说的倾向。如雪莱曾经说过,诗歌表达的是“永恒的真理,”而小说则是把松散的事实连在一起,除了说明时间地点、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果关系之外别无意义。(注:Shelley,"A Defense of Poetry",see David Lodge,Language of Fiction,p.9.)另外, 人们认为语言有文学与非文学之分。如I.A 瑞查兹说:“一句话可以用作参考,从中得出是真或假,这是语言科学的用法。但这句话也可以显示结果,即这句话的意思对情感和态度所起的作用。这是语言情感的用法。”(注:I.A.Richards,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P.267,see David Lodge,Language of Fiction,p.7.)瑞查兹的话可以理解为语言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但也含有语言两分法的意思。按照瑞查兹的分类,“情感语言的最高形式是诗歌,”而介绍性语言的典型代表是科学论文。(注:I.A.Richards,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P.267,see David Lodge,Language of Fiction,p.8.)另外如艾默森的“歧义”说,布莱克默的“姿态”(gesture)说, 兰瑟姆的文本(texture)说,都是针对文学作品语言的独特性而言。虽然这些人都没有否认小说的文学性,但是在他们强调语言的艺术特性时,就多少显出一定的片面性。似乎小说的语言,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语言太贴近生活,不象抒情诗歌的语言讲究句子的长短、节奏和韵律,要求高度精炼,集中表现情感的力度——或似是而非、或含糊暧昧、或反讽、幽默、或比喻、象征等意义。
戴维·洛奇认为,把语言分成文学与非文学的观点容易引人误入歧途。在他看来,语言的文学与非文学之分,“不在于语言的作用,而在于作用的目的。”(注:David Lodge,Language of Eiction,London,second edition,1984,p.ix,34.47,74,73.)不同的目的决定不同的写作技巧。这并不是说,哲学家、历史学家不能使用表现情感的语言,更不是说看上去陈述性的文学作品的语言没有文学性。小说、诗歌的语言之所以与科学论著不同,是因为作者的写作目的是虚构。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但是由于人们把艺术模仿的方式与目的相混淆,导致了语言有文学与非文学之分的偏见,从而忽略了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语言的特点, 即它和诗歌一样“也是语言艺术。 ”(注:David Lodge,Language of Eiction,London,second edition,1984,p.ix,34,47,74,73.)
另外,50年代语言学和文体学运用于小说批评,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法国文体学家斯皮策(Leo Spitzer), 他的理论注意分析小说中违反常规的语言现象,从语言的变革来看历史的变化。洛奇认为,对于多数未经过语言学专门训练的人,他们看小说往往不是从语言是否符合常规的角度来阅读。而且“最普通、最正常的语言因素常常是文学结构的要素。”(注:Rene Wellek,Style in Language,ed.Seboek,p.418,see David Lodge,Language of fiction,p.55.)因而, 这种偏向语言学和社会历史学的方法显得学院气过浓而缺少了文学欣赏的味道。当时还有另一种文体学理论,主张研究作者遣词造句的有效性和恰当性。这种方法引起的问题是,批评家应尽量站在作家的位置来理解文字的意义。况且,这种方法难以对整部文学作品进行语言上的分析,因而难以作出超越文本的批评。一句话,文学批评需要谈价值判断的实现,而这是当时的语言学和文体学批评所无法达到的。
谈到作品的“价值判断的实现”,洛奇也表明了他与F.R.利维斯的不同:利维斯主张从欣赏小说的道德完善(the moral perfection)来研究作品的形式美,而他则倡导从欣赏小说的形式美来分析作品的道德完善。他说,在小说批评中否认道德价值判断是荒唐的,但是不能把“强烈的道德感”和“紧密地反映生活”作为小说批评的中心。他认为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1948)中按照这两个标准把英国小说家分成伟大和一般两类,说明长期以来英国小说批评偏重道德判断,甚至有以道德判断代替文学批评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以语言作为小说批评之基础的观点。
戴维·洛奇还强调了他的观点与“情节说”的不同。当时,芝加哥学派的克雷恩(Crane )根据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重要观点(“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注:亚理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23页。))按照作家组织情节的方式把小说分为三类:行动的情节、人物的情节和思想的情节。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属于行动情节小说,亨利·詹姆斯的《一幅女人的画像》属于以人物为主而组织情节的小说, 而佩特(Pater)的《亨乐主义者马留斯》(Marius the Epicurean )则属于通过表现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变化而组织情节的小说。(注:David Lodge,Language of Eiction,London,second edition,1984,p.ix,34,47,74.)洛奇指出,虽然克雷恩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语言对情节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他把情节置于语言因素之上,或者二者相互割裂。而洛奇的观点与“情节说”(也是他与亚氏理论的)不同之处是,他坚持语言是小说的根本。小说中的结构情节归根结底是“词句的组合”,“所有的情节都是语言的情节。”(注:David Lodge,Language of Eiction,London,second edition,1984,p.ix,34,47,74,73.)
那么如何从语言着手进行小说阅读和批评呢?戴维·洛奇用看织机织布这个比喻加以说明。在刚开始的时候,很难一下子看清布上的图案,而且图案越是复杂,要看出图形就越难,用的时间就越长。但是,根据线的颜色搭配和纹理交织方式的反复出现,就能够逐渐辨认出编织的规律,看出织布上的图案。这就是说,在开始阅读时,我们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在阅读中根据文字排列的顺序、句法结构的特点来分析文字意义之间的关系和语言的风格,根据已有的文学体验来感受并寻找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细节或意象,并根据所感受到的意象,从上下文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来预测小说的意义,然后再重新对那些细节、意象给以印证和解释。可以说,阅读的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是从寻找语言模式到观照小说的整体意义,又从对小说意义的整体观照回到对语言模式的阐释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对重复的语言细节和意象的发现是读懂作品的关键。
捕捉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洛奇认为应注意以下四个误区:首先,不能凭假想或根据作家的所谓创作意图来解释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因为这容易陷入“意图谬误”的困境,取代对作品本身的分析。其次,也不能先入为主,或让多数人有意或无意作出的批评来驾驭我们对作品语言的感受。再者,不能以对词语的统计概率来判断反复的语言模式,出现频率多的词语不一定最有意义。对反复的语言模式的判断主要依赖于批评的眼光和对文学的感悟,看语言模式与整个作品的关系及其意义。最后,对语言模式的解释不能生搬硬套,也就是说,在某个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的意义并不等于它在其他文本中也有相同的意义。对语言模式意义的分析应根据作品的上下文来阐释。
戴维·洛奇看到,运用语言分析去把握作品意义的方法在实践中并非易事。当着重分析小说的语言模式时,批评会显得琐碎枯燥,而谈到语言模式与其意义的关系时,会显出这一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当他接触了法国的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后,他感到犹如发现了新大陆,《现AI写作作方式》(1977)和《运用结构主义》(1981)就是他的收获。
二、小说的语言模式——隐喻和转喻
法国结构主义“把文学看成一个系统”,把一部作品看成是“对文学系统的一部分的体现。 ”(注: David Lodge, 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ARK edition,London,1981,p.4.)在文学研究方面注重寻找小说形式的规律,注重发现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挖掘文字符号的多重意义。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1953)中分析了法国1848年革命失败的影响,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标志是人们“对自由幻想的破灭”。在文学上突出表现为作家对文学反映生活真实的怀疑。他们认识到文学只是表现符号意义的相互联系,而无法表现作家所要表现的现实世界。因而,巴尔特认为,从那时候起,文学要么追求语言形式方面的实验,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要么试图达到一种自然明晰的风格。如福楼拜、左拉、莫伯桑的作品,他们在小说中试图“掩饰人为创作的痕迹”。然而实际上,他们的创作仍然不过是形式追求的一种,他们“最终成为自己创作神话的奴隶。”(注: Roland Barthes,Writing Degree Zero,see 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p.59—60.)
戴维·洛奇认为,巴尔特论著的意义在于,他分析了人们对语言的两种不同认识,从而深刻地分析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过去人们以为能指与所指相互对应,因而相信文学能够表现生活的真实,甚至认为文学能够改变生活,或者起码也可以帮助人们承受生活的痛苦。而现代主义者们看到了符号意义的复杂性,于是打破了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幻想。但他们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系统,看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的确深刻而有意义。洛奇指出,正是因为人们对语言和文学的两种看法各有道理,而且人们又往往是在不同的时期相信不同的观点并难以接受明显对立的观点,于是近百年来文学史上才出现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相互交替登场的现象。洛奇认为,虽然现实主义的理论看起来粗浅,但其创作比其理论要有趣得多。而巴尔特的理论虽然深刻,但他在理论上却明显地赞扬现代主义贬低现实主义。特别是他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中期后就被人们摒弃了,的确是失之客观和公允。
作为一个批评家,洛奇认为,面对多种多样的文学样式,“应该寻找一种描绘现代文学史的方法,把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放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带有任何偏见。”(注:David Lodge, 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ARK edition,London,1981,p.72.)而且作为一个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家,他也希望能够从美学的角度来解释现实主义小说有别于戏剧和诗歌的艺术独特性。 (注: 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Edward Arnold Ltd. London,reprinted,1979.p.52.ix,viii,94,110,245.)他认为可以堪当此任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特别是罗曼·雅克布逊关于隐喻和转喻的理论。
雅各布逊认为,说话的过程包括“选择”与“组合”两个层次。当人们表达一个意思时,首先需要选择一些词语,然后按照某种语法规则“组合成更高一级的复杂的语言统一体。”他后来提出隐喻和转喻是两种基本的语言表现形式, 而且“可能是两种诗的形式规则, ”(注:Roman Jackbson,"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Linguistic Disturbances",see David Lodge, 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p74.)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
一般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两种相似的修辞方法。隐喻指的是根据两个词语的相似性进行选择替换,而转喻是根据一事物的部分特征、原因、或结果指代另一事物。戴维·洛奇在《现AI写作作方式》中用“轮船横渡大海”(Ships crossed the sea.)为例,说明:用引喻的方法,此句就变成“轮船犁过大海”(Ships ploughed the sea.), 而用转喻方法,又可以说成“龙骨横渡海渊”(Keels crossed the deep)。可以看出,通过隐喻或转喻,造成了句子陌生化的效果,从而读来具有新鲜感。洛奇的小说《美好的工作》中,女主人公罗宾对路边的香烟广告“断绸”和万宝路“孤独的牛仔”的隐喻性和转喻性分析(注:戴维·洛奇:《美好的工作》,罗贻荣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210—214页。)更是妙趣横生。
洛奇指出,雅各布逊的标新立异之处在于提出隐喻和转喻是一组二项对立的概念,它们是根据不同的原则生成的表达方式,隐喻是按照相似性的原则进行选择与组合,转喻则是按照连续的原则进行选择和组合。(按照洛奇的分析,转喻是按照连续的原则进行删除和压缩。)由于词语意义之间的联系不外乎两种:或按相似的关系相连接,或按时空上的联系而延续在一起,由此可以说隐喻和转喻反映了两种基本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文学话语主要以平行、对称或对立、重复为特点,因而,隐喻和转喻又反映了两种基本的文学结构模式,也就是雅氏所说的“两种诗的形式规则。”作品的隐喻模式表现为“联系多重世界而产生联想”的艺术形式,(注:Roman Jackbson,"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Linguistic Disturbances",see 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p74.)如抒情诗歌,浪漫主义的想象、戏剧、超现实主义艺术、电影蒙太奇。转喻模式为“在单一的连续的话语世界移动而产生联想”的艺术形式(注:Roman Jackbson,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Linguistic Disturbances",see 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p74.),如史诗、散文、现实主义的诗歌、小说、立体主义、电影等。洛奇指出,隐喻模式由于不顾及词语或上下文之间的逻辑性,因而显示出事物连续性的混乱。而转喻模式在叙述上多采用线性结构,并通过选取个别的、典型的事件或人物,表现某一个时期的社会历史画面。特别是转喻本身的特点——部分表现整体——反映了世上事物本身存在的连续性,也反映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我们看到,作家的选择或删除会受到逻辑的或上下文的限制,但同时又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他(她)可以强调突出某些事物,又可以轻描淡写另一些事物。因而,洛奇认为,由于转喻形式含有未表现的(被删除的)部分,那么对转喻模式的文学批评不能忽略“恢复被删除的细节”,(注: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Edward Arnold Ltd.London,reprinted,1979.p.52.ix,viii,94,110,245 )也就是揭示作品中含有的但未表现的意义。
洛奇认为,雅各布逊对隐喻和转喻模式的分析,不仅从语言上揭示了现实主义文体的特点和意义,还可以帮助我们从语言的构成来划分现当代各种写作形式,具体分析作家的写作风格。一部作品如果从整体上看,语言上缺少关联词,采用很多意象的重叠,那么就是隐喻的、浪漫主义的或现代派的作品;如果语言流畅,虽突出某些侧面,但是却连贯一致,则是转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是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分析方法不是孤立的,而是以作品的相互比较为基础。如从总体上看,现代主义时期与维多利亚时期相比,前者的作品多是隐喻式的,后者的则表现为转喻式的;如果把维多利亚时期的狄更斯和萨克雷相比,狄更斯的作品是隐喻性的,萨克雷的则属于转喻式的;而如果比较狄更斯前后期的作品,可以说他早期的作品多是转喻式的,后期的作品是隐喻式的。总之,正如雷门·赛尔顿在谈洛奇的隐喻和转喻分析方法时所归纳的,“语境是至关重要的。”(注:Raman Selde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Harvester,1993,p.118.)
戴维·洛奇在《现AI写作作方式》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五篇关于死刑题材的文本,包括迈克尔·雷克在《卫报》上发表的描写断头台行刑的报导,乔治·奥威尔的短篇小说《绞刑》(1931),阿诺德·本涅特的现实主义长篇《一个老妇人的故事》(1908)中的第三章,威廉·巴勒斯的《裸露的午餐》(1959),和奥斯卡·王尔德的诗“里丁监狱之歌”(1896)。从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五篇作品在语言上的隐喻性依次越来越强。洛奇由此说明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揭示出文学性的所在。五篇作品中王尔德的诗歌显示出最强的隐喻性,也说明为什么在文学批评传统中,人们把隐喻性的诗歌看成文学的最高形式,而对现实主义作品却难以从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洛奇指出,即使雅各布逊,对如何评价现实主义作品也感到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在隐喻和转喻这二项对立的概念中,隐喻具有美学的特性,而转喻被认为是非美学的。但是洛奇指出,从总体意义上说,文学本身就是隐喻性的,而非文学是转喻性的。当人们谈论一部小说时,难免会问:“这部小说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可能把小说整个复述一篇,而往往只是简要归纳小说的内容和意义。这实际上就是点出“转喻性文本的隐喻意义。”(注: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Edward ArnoldLtd.London,reprinted,1979.p.52.ix,viii,94,110,245.)正如盖依·罗瑟拉托所说:“描述性最强的、或最现实主义的作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隐喻,但这隐喻暗含并贯穿在连续的叙述之中,在不同的地方显示出来,最明显的是在作品的结尾,显示出作品对生活的比喻、对现实的比喻”。 (注: Guy Rosolato."The Voice and
the Literary Myth",The Stucturalist Controversy,ed.Macksey and D onato,p.202,see 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p.110)
洛奇还提醒我们,没有单纯的隐喻或转喻式的作品,所谓隐喻或转喻式作品是指占主导倾向的形式而言。如果一篇作品中隐喻使用的越多,或比喻意义与上下文之间的意义相差得越远,那么作品的隐喻性就越强、越复杂。为了不破坏叙述意义的连贯性,作家往往多使用明喻,用关联词“象”、“如同”来连接不同的概念,但不论是用明喻还是隐喻,比喻意义与上下文之间的差距决定作品形式的特点。
比如乔治·奥威尔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绞刑》,其中形容监狱的牢房“如同关兽的笼子”,描写行刑的狱卒对付死刑犯人,“就象人们在收拾鱼,这些鱼还活着,可能挣脱跳到水里。”这些比喻用得贴切,与人们对生活的观察相似,因而读起来感到生动,具有真实感。而T.S.艾略特在《J.阿尔弗雷德·普卢弗若克的情歌》中这样写道:
那么让咱们走吧,你和我
当夜晚的天空四外伸展,
象病人被麻醉躺在手术台上(注:T.S.Eliot,"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ok",see 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p.116.)
显然,夜晚的天空与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两个概念从语言上和感情上都相差很大,也没有什么逻辑关系,而且全诗的上下文与医学也没有什么联系,可见作者所选用的比喻是极其主观的,造成解读的困难。当然,通过语言形式上的奇异,现代派作家力求打破传统的表达方法,突出表现个人的独特感受,在此得以充分体现。但是我们也看到,以隐喻性为主要形式的诗歌或小说,不能完全不考虑意思的连贯性,否则读者无从把握作品的意思。而对于转喻性为主的作品,需要借助隐喻性的符号,使文本具有隐喻意义;但是如果比喻使用的过多,那么文本的性质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对于60年代出现并流行的后现代文学,洛奇也用雅氏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后现代作家以一种更为激进的姿态表现出他们与传统的不同。他们继承了现代派追求形式创新的精神,同时又表明他们有别于现代派的创作。现代派作家如乔依斯、伍尔夫、康拉德,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很强的隐喻性,不容易读懂,但是由于他们追求作品形式的完美统一,人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作品的意义。而后现代作家在叙述上遵循荒诞的逻辑,他们把不同时空中的人物或事件放在一部作品中,形成对立矛盾,打乱或混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在结尾写出多种结尾,表现文本意义的不确定、现实的荒诞、世界的无序、以及对现实存在的怀疑。
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品,人们或认为它是反传统的、反人文主义的、反现代派的,或认为它是现代主义的继续。但是,洛奇指出,如果从语言模式的特点来看,如果雅各布逊有关隐喻和转喻是两种基本的写作方式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应该说,尽管后现代作家标新立意,其作品仍然不可能超脱隐喻和转喻两种模式。当然,从整体上来看,后现代作品难以确定是隐喻性或转喻性的,否则,它们就不是以不确定性为特点的后现代之作了。然而就具体作品而言,后现代作家的手法如:打破时空顺序,打破叙事的连续性,或者把现实与虚幻相连,混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等,实际上是把隐喻和转喻的手法放在一起,并发挥到极致,把它们各自的特点、局限性揭示出来,从而各个击破。洛奇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这一语言形式的特点决定了它最终走向自我消亡。如果说它有成功的一面,是因为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家具有“突破束缚的很高的艺术想象力”。但是,当后现代主义作家成功地揭露并打破传统的表现手法之时,也是暴露和否定他们自身之际,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是打破艺术规则的艺术,而问题是他们并没有让人们看到打破艺术规则的意义所在。(注: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Edward Arnold Ltd.London,reprinted,1979.p.52.ix,viii,94 , 110,245.)
三、小说的独特性——对话的复合性文体
隐喻和转喻的分析方法,从语言结构上梳理了多样的文学形式,从总体上认识不同时期、不同作家、或者同一作家的不同写作风格。然而,洛奇认为,隐喻转喻的分类方法并没有超越文体学的局限,它仍然把文学作品当作同一性的实体来看待。这就是说,为了确定文本的隐喻或转喻性结构,往往会忽略或淡化作品的一种倾向而突出另一种倾向。而任何一篇小说都不可能是单一性的语言结构方式,都会既有隐喻性的语言又有转喻性的语言。在90年代他写的《巴赫金之后》一书中,他分析了文体学方法的(包括他以前文论中的)局限性,认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更适于小说批评。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说:“在一篇作品中使用各种各样文体的可能性,完整地体现出所有的表现力,而不至于落入一个共同点——这是散文的最基本特点,也是散文与诗歌两种文体的最重要区别。”(注:Mikhail 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see David Lodge,After Bakhtin,London,1990,p.7.)巴赫金还说,小说家的创作天才就表现在“作家是知道如何用语言工作同时又身在其外的人, 他有使用间接引语的天赋。 (注: Mikhail 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see David Lodge,After Bakhtin,London,1990,p.7.)洛奇说,上面两段话犹如一盏明灯,使他顿时感悟到了“他为什么可以写关于学者的狂欢化型(carnivalesque)小说,同时自己又仍然是一位学者。”(注: David Lodge,After Bakhtin,p.24.)
他在《巴赫金之后》中分析了对话理论与索绪尔理论的联系与区别。索绪尔着重探讨语言在语言系统中的意义,认为语言意义的确定在于词语意义之间的区别,而语言本身没有确定意义。在索绪尔提出的语言/言语(langue/parole)这二项对立的关系中,隐含着一种倾向——偏重对语法规则、或偏重对反语法规则现象的探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则更偏重于后者、即对具体言说的研究。他在1929年就提出,语言是社会活动,“语言的意义在于社会。”他指出,在我们之前语言的使用者已经赋予了语言声音和意义,所以,我们说话时语言就已有一定的所指。人们在社会的、历史的、上下文等语境中进行交流,并判定语言的意义。 “在生活中的对话里语言会直接而明显地引出答案。 ”(注:Mikhail Bakhtin,The Dialogic Imagination,see David Lodge,After Bakhtin,p.21.)巴赫金指出的语言的社会性和对话性特点, 一方面不同于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者关于语言无确定意义的观点,从而肯定了人们阐释文本意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语言的对话性质,文学作品不可能是单纯性的文体,其表现的意义因而也是多重的,它们相互对立而存在。
洛奇认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对柏拉图“纯叙述”“纯模仿”说的发展。柏拉图在《共和国》第三章里把文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叙述(diegesis),如抒情诗,另一类是纯模仿(mimesis),如戏剧。 对于史诗,柏拉图虽然看到它是诗人语言和人物语言的混合体,但是没有看到史诗中的诗人语言并不是简单的纯叙述,而具有了二者相混合的性质。巴赫金看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杂语性(polyglossia)的文体, 如拉伯雷在小说中对多种语言包括拉丁语和各种方言的使用,“使语言更富有活力”(interanimation)。18世纪小说的叙述话语更为多样。有的采用了某种特殊的文体,有的使用第三人称叙述,包括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来讲述故事。19世纪和20世纪的小说叙述变得更为复杂。按巴赫金的理论,小说中的文体可以分为三类:
1.作家的直接讲述(the direct speech of the author), 类似柏拉图的“纯叙述”。
2.再现性的话语(represented speech),类似柏拉图的“纯模仿”,包括人物的直接引语和描述性的转述人物的话语。
3.双重声音或双向话语(doubly-oriented speech),不仅指世上的某件事,而且还指其他的说话行为。其表现样式为:(一)采用某种风格的文体(stylization),如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 卢梭的忏悔录式小说,歌德的日记体小说等。(二)戏仿(parody),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采用了中世纪骑士传奇的文体,嘲讽骑士文学的不真实,斯泰恩的《项狄传》用戏仿的手段嘲讽以前的文学话语,深刻触及了意识形态和文学方面的重要问题。(三)口头叙述(skaz),指作家用某种第一人称的口语形式讲述故事,如J.D.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用十几岁少年的口吻讲述故事。话语看似随意,但却是作者有意设置的,造成小说幽默活泼的风格和真实感。(四)对话(dialogue),这里所说的对话指的不是引用人物的对话,而是指另一方说话行为不在场的话语方式,含有文字上下文以外的含义。最突出的例子是文学作品中的互文性现象,有的还含有潜在的对立或矛盾。可以看出,以上四种双重或多重声音的话语方式是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充分体现。
洛奇在《巴赫金之后》中对奥斯丁、哈代、亨利·詹姆斯、吉卜林、劳伦斯、伍尔夫、乔依斯、伊夫林·沃、米兰·昆德拉等作家作品中的双向话语进行了分析后认为,由于小说中不仅有作者的语言、人物的语言,还有自由间接引语或双向话语,使得小说的文体变化多样,具有了杂语性或狂欢化的性质,造成小说意义的复杂和不确定,从而也显示出小说不同于诗歌戏剧的独特性。总之,小说的对话性揭示了小说的两个基本因素,“笑和杂语性”。(注:David Lodge,After Bakhtin,p.40.)笑,即传统民间欢庆活动里对所有话语形式的嘲笑,而杂语性,一方面指作家在小说中对不同阶层人物的语言包括各种方言俚语的模仿,另一方面指的是双向双重话语。小说的这两个因素不仅防止了作家强加给作品单一的观点,而且赋予小说本身不断创新的生命力。
洛奇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分析现当代小说的不同特点也很有意义。如现代派作家,力求避免表现人为创作的痕迹,显示出重模仿的倾向。然而乔依斯、伍尔夫、 福克纳等人常用的意识流, 即多瑞特·考恩(Dorrit Cohn)所说的“记忆独白”(memory monologue), 可以说是人物自己对自己讲故事。因而现代派的重模仿带有纯叙述的特点,或者说是叙述性的模仿。而后现代小说,则表现出重叙述的倾向,如小说中采用多种文体,像报刊杂志、11头叙述等形式,特别是在元小说中,作家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来谈自己写作中的问题。然而与意识流手法相对应,后现代作家又喜欢大段呈现人物的对话,而省略人物心理动机的描述,形成小说的“对话流”。(注:David Lodge,After Bakhtin,p.44.)可以说后现代小说是模仿性的叙述。不过后现代小说中的模仿不同于传统的那种栩栩如生式的模仿,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屈从于模仿的模仿”,而是揭示模仿的虚幻性的“反模仿”。(注:David Lodge,After Bakhtin,p.44.)
任何理论似乎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也有其矛盾之处。洛奇指出,如果说语言的本质是对话性的,那么怎么还可能有独白式话语(monologic discourse)和独白式文体的作品呢? 在巴赫金看来,理论上说文学作品不可能有纯粹的独白性文体。即使是表达某种强烈情感的抒情诗,也不应看成是独白性文体,更不应简单地说成是作家思想的表达。因为一首诗不是真正的语言行为,而是对语言行为的模仿;因为小说家有的就是把玩间接引语的功夫。洛奇认为,巴赫金的辩白说明他也意识到了其理论的矛盾之处,他的解释也不无道理,但是他过于突出强调了对话体,以至于取消了独白体的存在,从而取消了独白体和对话体的区别。
然而洛奇又指出,巴赫金的这种偏激并不意味着其对话理论失去了深刻性。实际上巴赫金告诉我们,从整体上来看,对话性在小说中占着主导地位,而不是独白和对话二者各分秋色。解读一部文学作品,应把它看成是作家对社会言行的模仿,应从文本与社会的关系、文本中的对话、文本间的对话、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入手,分析作品的意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当代文学理论也有很大的贡献。“对于那些倾向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人来说,巴赫金再次恢复了社会对语言和文学具有建设性作用的坚实信念;对于那些人文主义学者来说,他重新维护了以历史学和语言学为基础的文学研究的合法性;而对于那些形式主义者们来说, 他又为分析和归纳叙述话语开辟了新的领域。 ”(注: David Lodge,After Bakhtin,p.4.)
综上所述,揭示小说的诗学特征、语言模式规则和文体本质是戴维·洛奇对小说的三种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阅读和批评方法。贯穿其中的联系就是从语言着手来揭示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它们的不同点也反映出洛奇在文学批评道路上的变化,即在60、70年代他比较偏重新批评方法来分析小说意义的表达,到80年代他多用结构主义和雅各布逊的理论对小说的形式技巧进行分析,而到90年代他运用巴赫金的理论又重新偏重对小说意义的阐释。这些变化说明,洛奇在坚持以语言为小说批评之基础的同时,又试图从文本的语境、结构以及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小说研究。他既主张读者在阅读中相信自己的直觉,又提醒读者关注作品的上下文和整体意义。这也说明,文学批评中的语言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戴维·洛奇,“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方面不同意阿诺德式的文学具有宗教作用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注意避免用非人文主义的美学或狭隘的技巧分析来解释文学的问题。”(注: Bernard Bergonzi,David Lodge,Nothcote House,1955,p.50.)从洛奇的变化我们也似乎看到了西方当代小说批评理论发展史的一瞥。同时他的文论语言清晰晓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文学史发展的特点,阐释并充实了当代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特别是“他从语言上对小说的分析,成功地沟通了语言分析与文学欣赏、评价的分歧,”(注:雷.威莱克:“当代欧洲文学批评概念”,见《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5页。 )对于提高我们的文学阅读水平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洛奇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作品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