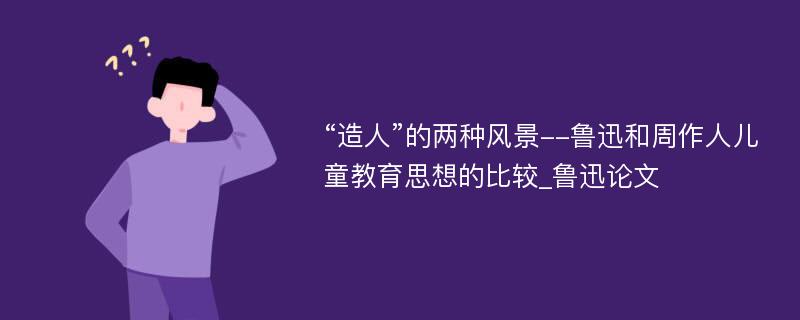
“立人”之路的两种风景——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两种论文,之路论文,儿童教育论文,风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4-0091-07 在中国近现代“儿童的发现”的历史进程中,周氏兄弟堪称双璧。早在留日时期,二周就开始留意童话以及儿童学的书籍。虽然鲁迅早在1907年就提出了“立人”概念,但在辛亥革命前后,二周还未明确从“人”的发现角度思考儿童问题,在话语形式上仍延续了晚清以来梁启超等人的思路,把儿童当作未来国民,重视教育是为“造成人民,为国柱石”[1](卷11P350)。然而,他们对于儿童学的翻译、研究和相关实践活动,已渐渐偏离了晚清以来强调培养公德意识、国家观念的思路,开始注意到儿童个性及美感的培育,发掘儿童内在的生命价值,为下一阶段也就是五四时期现代儿童观的确立做了很好的过渡。五四时期,周氏兄弟都从晚清以来把儿童看作未来国民的思路中走出,将儿童问题与“立人”思想紧密相连,在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背景下探讨儿童教育问题。当鲁迅发现中国历史“吃人”的真相,开始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时,周作人正是以其扎实的儿童学研究,以及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倡导呼应了这一口号。 如果通观他们二人对于儿童教育的看法,会发现很多观点如出一辙。他们都主张在教育上不应盲目追赶潮流,而应从对“人”的理解出发,确定教育宗旨。他们都强调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顺应孩子天性。强调游戏的重要性,特别重视玩具对于孩子的教育作用。并且都非常重视儿童读物,关注童话的翻译和研究,反对以科学的名义取消童话,并为神话辩护。他们都反对国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教育,反对给儿童讲些高文宏义,造成过重的压力和负担。他们都认为教育不仅仅是指学校教育,而是指广义教育。正是由于这种广义的大教育思想,使得鲁迅和周作人虽然都对旧学堂的弊病有过切身体会,对新式学校也时有批评,但却都不是从正面致力于学校教育改革的人物,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显示出更广阔的批评视野。虽然他们对儿童教育的思考中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但这其中又有不少看似细微,却又明显的不同之处,呈现出对“立人”之路探索的两种不同风景。 一、进化论与复演说 周氏兄弟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进化论为他们发现儿童提供了理论基础,却又使他们的儿童观朝着不同方向发展。鲁迅透过进化论思想看到了人类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基本趋势,并得出“后起的生命比前者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结论。而周作人则深受进化论中复演学说的影响。他认为“照进化论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蛮荒时期”[2](P75),所以他称儿童为“小野蛮”。他对儿童学的兴趣,也可以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虽然周作人曾先后涉猎过卢梭(Rousseau)、福禄培尔(Froebel)、蒙台梭利(Montessori)等教育家的著作,在日本时期就看过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史丹来霍耳(即G Stanley Hall,今译霍尔)的儿童学研究,这主要源于霍尔以复演说为基础的儿童心理发展研究与周作人对人类学、民俗学的兴趣之间的吻合与投契。 鲁迅也接触过复演学说,在《人之历史》中介绍过德国海克尔的学说,认为种族发生学与个体发生学是一致的。但这种学说却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他的儿童观。鲁迅对于儿童的理解更接近卢梭的自然人性说。在他与儿童相遇的思想基础里,《破恶声论》所提出的“白心”是尤为重要的。鲁迅认为当时的中国之所以恶声扰攘,是“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志士英雄,非不祥也,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1](卷8P29)。他赞美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卢梭等人的作品,心声洋溢,可以闻其“白心”。鲁迅在这里两次讲到的“白心”,无论是指自由表达心声,还是纯白素朴之心,都指向一种人性之“真”。他终生对“赤子之心”充满好感,一直关注儿童及其教育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源于对“白心”的渴望与珍视。《狂人日记》中认为孩子也会“吃人”是文化濡染、父母教育的结果,《补天》中女娲抟土造出的人本来都很可爱,然而经过文明的熏染之后却逐渐变成精神萎缩、面目可憎的东西。因此,在鲁迅看来,人生来应是好的,天真的,后来的“坏”是文化影响的结果。虽然鲁迅对此也产生过怀疑,比如《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的对话即可表明这一点。但对“白心”的渴望使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在30年代的《漫骂》一文中仍然认为有人说儿童会为吃的东西打起来,那是对儿童的谩骂,其实那不过是对成人的模仿。在《“小童挡驾”》中也极力为儿童的纯洁辩护。 而周作人对儿童的理解则截然不同。他认为儿童时代正相对于人类初民时代,其生活习性当中保留了相当多的野蛮思想,喜欢争斗并不能简单判定善恶。他翻译过日本新井道太郎的一篇《小儿争斗之研究》,介绍了儿童争斗的原因、方法,儿童争斗之价值、道德。在译者序里,周作人认为其实儿童是小野蛮,居于小天地中,以自己的力量解决一切;他们的斗争,就像野人之战,为了“自卫其权利,求胜于凡众,而其间自有法律自有道德为之调御”[3](卷5P591)。因此,凡儿童都好斗,这是出于一种求生、自卫、荣誉以及游戏本能,并非简单的恶事,自然也并非对大人的模仿。 鲁迅特别强调儿童的真,对儿童读物里的“诈”与“伪”都异常反感。认为儿童不会喜欢《二十四孝图》“老莱娱亲”中的“诈跌仆地”,因为“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1](卷2P262)。而周作人从人类学角度认为儿童实际上是喜欢说诳话的。这并非“作贼的始基”,而是“空想的表现”,“艺术的创造”[3](卷5P786)。在《“小大自休”》中也说,小孩子无论是对玩具还是童话,都喜欢“虚假的玩意儿”,但是等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便自然不玩了[3](卷5P743)。在周作人看来,儿童正处于幻想正盛的阶段,喜欢说诳话,喜欢玩一些虚假的玩意儿,这都是儿童心理很自然的现象。 鲁迅从线性进化论的思想出发,认为后起的生命更近完全,更可宝贵。他的白心论更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都希望在“绝假纯真”的真心、真人中寻求社会批判的主体[4](P221)。因而对儿童的“纯洁”有更高的期待,也就更容易失望。而以复演说为基础的周作人一开始就把儿童定位为“小野蛮”,因而对儿童的“争斗”、“说诳”等行为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二、“父范”与“母范” 鲁迅一直重视对于教育者的启蒙和培养,然而他却既没有专门论述过师范问题,也最反对“贤母良妻主义”,而认为“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1](卷1P312)。在中国近现代很多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认为母亲应该担当教育主体的情况下,鲁迅坚持认为父亲才是儿童教育最重要的主体,这在中国近现代思考教育问题的知识分子中间,是颇显特别的。他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中国第一篇关于“父范”问题的专论,是鲁迅论述儿童教育问题中最有创见的一个观点,也是最能显示鲁迅思想特色的一个命题。其中既包含着对传统夫父家长本位社会的反叛与对中国妇女现实地位的认识,也夹杂着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的生命体验。而周作人认为“母范”更重要。虽然他在谈论儿童教育的文章里常常以儿童的父兄身份来发表意见,有一些文章也声称是为“儿童及爱儿童的父师们而写的”[3]卷5(P824),但通过对西方儿童教育的了解和考察之后,周作人仍然认为承担儿童教育主体的应该是女性。在《女学一席话》中,他介绍英国和美国的儿童教育事业多由女士担任,认为中国要发展儿童教育,“男子如或太忙,可希望者自唯在女士耳。”[3](卷5P374)在谈到编辑儿童读物时,认为“对儿童有爱与理解的人都可以着手去做,但在特别富于这种性质而且少有个人的野心之女子们,我觉得最为适宜。本于温柔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与艺术的修养,便能比男子更为胜任”[3](卷5P711)。在《家庭教育一论》中也说“家庭教育以母为之主”[3](卷5P608)。然而在五四时期,当鲁迅提出“父范”问题之后,他其实也并未表示过异议,认为父范的实行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到50年代,他写的《何为父范》中引用齐公《何以怨爷》中的话:“凡私生子与孤儿都是有母无父的,大都有出息,能刻苦求进,奋发有为。但是我们很少说得出那个大人物没有了母亲,而是由他爸爸一个人苦苦造成的”。他引用齐公的话说“一般的父亲都比较自私”。他说这句话说得客气,也很深刻。“因为从动物的本性来讲,男性只顾传种,女性则管生育,家庭的意义在男性只是占领配偶,在女性乃是养育子女。人类文化虽然前进,可是男子至今未能克服或修改他的本性,结果养育儿童的责任也只有女子能够担当。五四前后有人说比师范要紧的是办父范学堂,可是这范哪里去找?”[3](卷5P657-658)所以,周作人还是回到了“母范”。 鲁迅对“父范”问题的独特思考,是针对父权和夫权重的中国传统社会而提出的,是“针对孔夫子的时代性的反命题”[5](P209),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而周作人通过对男女性别差异和人类本性的分析,认为担当儿童教育主体的应该是母亲。这不是刻意为男子应负的责任开脱,而是对男性的自私所进行的批判,包含着一种对男权社会的反省意识。 三、起点与目标 一般来说,儿童是教育的起点,成人是儿童教育的目标,教育的过程就是要使儿童顺利完成到成人的过程。周作人的儿童教育理念主要是把握儿童教育的起点和过程,至于效果或目标,他则认为是自然的“副产物”,而不是预先的“目的物”[3](卷5P683)。因此,他不仅坚决反对将成人世界的政治、经济、外交或者党派的意见教给儿童,而且也不主张在教育的过程中带有预先的偏见或者倾向性。他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出具有健全的身体,拥有基本的常识,保有完整童心的儿童,至于他将来长大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倾向于什么主义,教育者是不好代为选择和决定的,这是他们成人之后,有了自己的认识之后可以自由选择的。而鲁迅则不同,他的儿童教育目标是针对中国人的精神缺陷而提出的。所以,鲁迅的儿童教育观不仅注重儿童教育的起点,强调教育要符合儿童的天性、尊重儿童的心灵,更是为了实现将来的远大目标,那就是重塑国民灵魂,振奋国民精神,最终实现“立人”理想。因此,从教育的目标或者方向上说,周作人奉行的是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而鲁迅则一方面坚持个性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排除功利主义的思想。他反对把孩子培养成顺从的绵羊,而希望他们具有一点刚强勇猛的“狮虎”气质。在鲁迅看来,教育的内在理想就是培养未来的新人、真人、人的战士。 知识分子自身的个性气质也会影响其对教育目标的思考。胡适曾回忆他从小身体弱,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文绉绉的。他喜欢看书,绰号穈先生,所以不曾享受过儿童的游戏生活[6](卷2P393)。他对青年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勤、谨、和、缓[7](P391),即与他本人的气质相近。而陈独秀则崇尚兽性主义,希望儿童意志顽狠、好勇斗狠[8](P35),也和他本人的个性相关联。鲁迅与周作人同样是“从旧垒中来”,有着相同的家庭环境、相似的受教育经历,但他们的思想和气质从幼年起就略现轩轾。有学者把他们比喻为现代的“莱谟斯”和“罗谟鲁斯”[9](34-42)。周建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中也说过:“鲁迅待人以诚,却不像周作人那样好奴役,对不合理的事,他要反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10](P443)。这种气质反映在他们对于儿童教育的看法上,鲁迅认为儿童的教育既要顾及其天性,同时应注重人格的培养,特别是一种刚毅气质的培养。他主张儿童从小要养成强硬的性格,要有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的勇气,将来要有“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精神[1](卷3P59),这既内蕴着对中国人柔弱、卑怯的国民性格的改造意图,也和他本人的个性相关。虽然周作人也赞赏过陶渊明《读山海经》中流露出的慷慨激昂的情绪,对精卫、刑天与夸父等人物所包含的“猛志固常在”,“勇往直前的精神”有过注意[3](卷5P799),也关注过《西游记》中孙猴在大闹天宫时所体现出的反抗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大众和小孩们是很爱好的,在现代也有意义[3](卷5P796)。但是,在他大量的谈论儿童教育的文章中,很少关注这种反抗精神对于儿童人格的重要意义。 陈思和在论及周氏兄弟的个性风格时曾说,鲁迅对斯巴达精神是倾心喜欢的,他是从欧洲最古老的狂人的精神传统中,寻找到了一种与中国武侠传统、墨家传统相契合的东西。而周作人更偏于雅典精神,比较偏重于理性的、民主的、求知的传统[11](P32-36)。就儿童教育而言,二周也有这样的分野。鲁迅更倾向于斯巴达国民教育中培养勇毅精神的特点,而周作人则倾向于雅典式的偏重于理性,尊重个人的教育。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中,将周氏兄弟身边的青年文人进行了对比,其中也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鲁迅那里野气的、挑战气的人多,所以他能有萧军、萧红、瞿秋白、胡风、冯雪峰式的朋友是可以理解的。在周作人那里,必然会有废名、俞平伯式的学生”[12](P263-264)。 因此,一个人的教育思想,往往连带着他整体的思想文化理念,同时也和自身的个性气质相关联。鲁迅与周作人对于教育目标的思考,就投射着他们各自斗士与隐士的精神面影。 四、有趣与有益 鲁迅与周作人都特别重视儿童读物,并且身体力行地翻译童话、搜集儿歌。鲁迅强调“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1](卷5P295),周作人也希望供给儿童故事和画本,来“止那精神上的饥饿”[3](卷5P708)。不过,在考虑各年龄阶段儿童所适用的读物时周作人比鲁迅思考得更为细致。在《儿童的文学》中,他根据幼儿及少年期情感和心理发展的顺序,详细制定了各年龄段儿童应该阅读的文学种类。虽然并未经过实验,还如他自己所说“只是理论上的空谈”,但却是关于少儿语文教育的一份颇具建设性的计划书[3](卷5P682-690)。在儿童读物的选择方面,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态度显然比鲁迅宽容。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歌、传说、寓言、小说、故事,如《韩非子》《孔雀东南飞》《西游记》《今古奇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都可以择取一些适合孩子阅读的内容,而不像鲁迅那样决绝地认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1](卷11P369)。当然,从实践的角度上说,鲁迅并未反对儿童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作品,但他很少主动为儿童推荐传统的中国文学经典。他对青少年读中国书一向反感,对《三字经》、《二十四孝图》、《幼学琼林》等传统儿童读物更是深恶痛绝。在鲁迅看来,要养成儿童适应时代的新思想,就要阅读新作品。别说是儿童,就是他自己,也要多读新作品。鲁迅说:“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1](卷6P227-228)他引用《表》的日译者槙本楠郎在译本序言里的话说:“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1](卷10P436)他极力鼓励年轻作家创作并翻译新的儿童读物。他本人翻译的童话,除了《小约翰》创作于1887年,其余都属于20世纪的作品。《爱罗先珂童话集》《表》则是刚刚诞生的新作,被认为是“又新鲜,又有益”[13](P284)的。《小彼得》日译本1927年出版,鲁迅1929年就翻译过来,也可见他急于赶上世界潮流,给中国儿童输入新的精神食粮的迫切心情。 周氏兄弟在儿童读物方面分歧最大的当属对童话之于儿童教育意义的认识。周作人于1912年发表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的《童话研究》,用人类学方法解释童话中常见的现象,并探讨了童话用于儿童教育的意义。1913年鲁迅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也明确提出研究童话可以“辅翼教育”。因此,他们对童话的看法都是讲究既有趣又有益的,只不过他们对于有趣和有益的标准不同罢了。在《童话略论》中周作人认为童话对儿童教育的意义在于顺应儿童天性、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并使他们从中学得一些知识。而寄寓训诫,是不重要的[3](卷5P666)。也就是说,“童话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学的而不是道德的”[3](卷5P693)。他认为最理想的童话,在于“无意思之意思”[3](卷5P710),当然没有意思决不是没有意义,而是不含什么训诫的道理。因此,他反对给儿童的故事里有寓意,即使有也“须得如做果汁冰酪一样,要把果子味混透在酪里,决不可只把一块果子皮放在上面就算了事。”[3](卷5P710)在他看来,无论写得多么好,多么有意义,只要儿童不喜欢,没兴趣,那就不是好的教育童话。 鲁迅在翻译爱罗先珂童话之前,对于童话一直处于爱好、倡导,以及对周作人的童话翻译和研究给予支持的阶段。自1921年起,才正式开始翻译童话。他早年倾心《小约翰》那样具有浓厚哲学趣味的作品,20年代又翻译爱罗先珂的文学童话,后期选择的童话如《小彼得》则渗透着强烈的阶级反抗意识,而《俄罗斯的童话》则根本就不能称其为童话,更像是一种以夸张手法描写国民本相的讽刺文体。因此,鲁迅喜欢的童话几乎都是有“意思”的作品,都包含着比较正面的、积极的、反抗的甚至哲理的内涵,被认为是很有修养及教育意义的[14](P717)。我们会发现,从《域外小说集》与周作人一起关注王尔德和安徒生起,到飘荡着痛苦而忧郁情绪的爱罗先珂作品,再到翻译《小约翰》《小彼得》《表》和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鲁迅关注的童话越来越远离了“幻想”这一最基本的特征,从对“童心的,美的梦”的称颂,儿童精神的高扬,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和表现。充溢于童话中的“野蛮一般的思想”、童真的趣味和游戏精神越来越少。这一过程如赵景深在评论文学的童话时所说:“就文学的眼光看来,艺术是渐渐的进步。思想也渐渐进步了!但就儿童的眼光去看,总要觉得一个不如一个。”[15](P97)鲁迅的这一取向只能说是日益急迫的时代语境和“为人生”的现实焦虑所致。 可以说,周作人真正摆脱了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把儿童期的教育当成“成人生活的预备”的观念。他的童话观是牢牢把握儿童本位的,他之强调“无意思之意思”,就是把儿童的阅读趣味放在首位。虽然鲁迅也说过旧的教育者把儿童作为缩小的成人,或者成年的预备都是错误的看法,但他的儿童教育思想始终未能脱离“成人的预备”这一观念。在思考儿童教育的过程中,他始终用一只眼盯着儿童,另一只眼则眺望他的成年。因此,他的童话观一直在成人与儿童之间摆动。他所翻译的童话偏于教育的居多,而且并非都是给儿童看的,也是作为成人读物,供家长、儿童教育专家参考之用。 五、遗传与环境 周作人在题为《遗传与教育》的文章中指出,影响人格的主要因素是性别、种族、遗传和环境。实际上,这四个方面也是考虑教育问题必须关注的要素。 周作人特别关注教育上的性别差异问题。在《儿童研究导言》中认为儿童10岁以后两性差异渐渐明显。“男子率好斗,喜闻武勇之故事,女子则拟家事,弄人形。此时正教育之好机,但在善为迎导,各循其分以成全之而已。”[3](卷5P589)而鲁迅明确反对给女性以相差别的教育,尤其反对给女孩子以依附男子的教育。当然,他反对教育上的“贤母良妻主义”,并非要泯灭性别差异,而是包含着男女平等的现代观念,希望女性同样享受教育权,并养成独立的人格。不过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仍然需要考虑性别差异的实际存在,这一点上周作人的思考更为全面。 在关于种族的问题上,鲁迅经常把中国的儿童和外国的儿童放在一起对比。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他发现同样一个儿童,在中国相师和日本相师手里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表情,这反映出两种教育方式的差异。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他认为中国人与外国人相比之所以少了兽性,并非种族本身的问题,因为中国人从前也有过这种野性,只是由于长期受外族奴役,才慢慢地驯顺起来,从兽性变成了家畜性。因此,当他发现中国儿童驯顺、拘谨,外国儿童活泼好动之后,也认为这并非种族差异所致,而是教育的结果。周作人1913年即翻译过英国戈斯德《民种改良之教育》,将“善种学说”介绍到中国。在《遗传与教育》中则认为所谓“民种”,实际上是“远因之遗传”,再加以历史影响、社会风俗合力而成,在思考教育的过程中也应予以重视。 如果把性别、种族、遗传、环境这四个方面作为影响人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的话,鲁迅最重视的是环境,也就是社会、文化包括教育方式对人的影响。他毕生都在思索如何斩断吃人的罗网,从而救出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因此主张只有真正改革了社会,才能改革教育。周作人也接触过环境决定论的学说。1914年他翻译过英国加伐威尔的《外缘之影响》一文,以狼人为例,说明环境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不过,在以上四种因素当中,周作人认为遗传因素最为关键。在《遗传与教育》一文中,他认为教育应重点考虑遗传因素。因为遗传决定天性,而环境对人的影响之大小,也会根据遗传的天性而有所差别。他举例说,饮酒的人远离城市仍然饮酒,不饮酒的人酿酒为业也不饮。法拉第为药店洗瓶子而精化学,但并非人人洗瓶子都能成化学家。达尔文航海考察而发现进化之理,但并非人人航海而能成为自然科学家。所以教育的力量在于“顺其固有之性,而激厉助长之,又或束制之使就范围,不能变更其性,令至于一定之境界,如教育万能者之所想象也”[3](卷4P639)。以遗传学说应用于教育,也就是要使教育根据天性而进行扬抑,与法律、宗教等殊途同归,目的都是植善而去恶。他介绍了英国的优生学(当时称善种学),认为其“本天演之理,择种留良,以行淘汰,欲使凡智各群,各造其极,实为教育之基本事业,凡言教育者所不可不致意焉。”[3](卷4P639)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也论及遗传问题,他希望做父亲的要在道德上小心自爱,避免把体质上精神上的缺点遗传给孩子,但在其他谈论儿童教育的文章中,很少涉及遗传因素。对于中国孩子的苍白、斯文、钩头耸背,也认为是从小偏于静的教育造成的,并非遗传问题。 因此,在周作人那里,教育的效果如何,要根据天性对于教育的反应而定,而鲁迅却更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的决定性影响。这区别看似微小,其实重要。因为看重环境因素的鲁迅,激发出更强烈的批评意识和改造意图,而重视遗传因素的周作人,则显得平和冷静。随着年龄的增长,周作人越来越欣赏“小大自休”那句话。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教育的方法或者手段既重要,又不那么重要。在他看来,只要教育者不蓄意破坏,人的成长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康德说:“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人”[16](P5)。因此,教育是通向“立人”目标的必由之路。而儿童教育又是整个教育大厦的基础,这正是近现代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丰子恺、郭沫若、叶圣陶、郑振铎、夏丏尊等人何以如此关注儿童教育的原因之一。这其中,周氏兄弟是颇为耀眼的代表性人物。如论者所言,二周在思想根底上是一致的,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出发点与归宿——“立人思想”。但他们又有不同的关注点,有各自的领域,因而他们的思想具有极大的相渗性与互补性,可以互为发挥,在“参照”中彼此深化[17](P252)。就儿童教育问题而言,周氏兄弟都在其中投注了巨大热情,将其作为探索“立人”之路的实践起点。鲁迅不仅把儿童教育问题与儿童的发现、重新审视童年的意义联系起来,更与改造国民性的巨大工程,与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性转换结合起来,因此,儿童教育问题就成为将鲁迅思想中的两大命题“改造国民性”和“立人”思想联系起来的重要节点。周作人将儿童问题与妇女问题、人的发现紧密相连,共同构筑其人道主义思想的三大基石。因此,儿童教育思想对周氏兄弟来说,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是他们思想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鲁迅对进化论、遗传学、儿童心理学等虽有所涉猎,但他对儿童教育的思考更多源于自身的童年经验以及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深刻洞察。除了少量翻译作品,他大多是靠小说和杂文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因而显得更为感性,也更为忧愤深广。而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则倚重文化人类学、复演说、优生学、遗传学等较为系统的理论和科学思想,且较多以论文和随笔形式表达,因而显得较为平和理性。可以说,鲁迅是从战士和思想家的角度来思考儿童教育问题的,他提出的命题振聋发聩,影响深远。而周作人则更像一个学者,他通过扎实的儿童学翻译和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把鲁迅的思路具体化和深化了。”[12](P330)标签:鲁迅论文; 周作人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风景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小约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