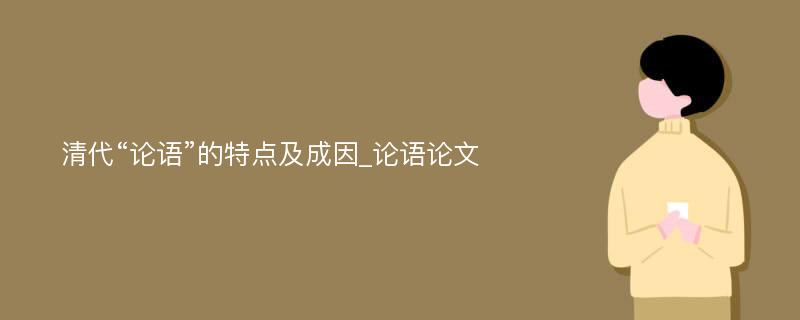
清代《论语》学的特点及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成因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7]11—0081—04
清代是《论语》研究的鼎盛期和总结期,不仅著述如林,而且名家辈出,气魄之博大。思想之开阔,考据之精审,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古代《论语》学史上,罕能出其右者。受统治者文化政策、社会思潮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论语》学呈现出注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汉宋兼采”的基本特征。
一、清代《论语》学的特点
《论语》学在经历了宋元明时期的复兴之后,及至清代,遂进入了鼎盛期。无论是《论语》研究的数量、质量,还是研究方式,都较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总结的态势。同时,清代的《论语》研究,在综合中也有创新,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历史特征。
其一,清代的《论语》学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文化是典型的入世哲学,“经世致用”是儒家学者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所谓经世,即治世,治理天下。[1](P41)这种经世思想往往在遇有国难民瘼时借助于对经典章句的释读生成。清初和嘉道以后的《论语》学著作中就有明显的经世思想。其主要代表作有颜元的《四书正误》、陆陇其的《松阳讲义》、孙奇逢的《四书近指》、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发微》、戴望的《论语注》、康有为的《论语注》等。如清初的颜元在注释《论语·尧曰》“何谓惠而不费”节时说:“看秦汉史尝说,汉高只行得‘惠则足以使人’一句,便定四百年统业。看韩淮阴那等大豪杰,所感激的只在‘解衣推食’,楚霸王只犯了‘出纳之吝’一句,便杀身败业。假使汉高能行四五句,便是三王。”[2](卷四)直接道出了《论语》的经世作用。又如清中期以后的公羊学者们力图贯通《论语》学和公羊学,发掘《论语》中的改制思想。其中刘逢禄“追述何氏之《解诂》义,参以董子之说”,[3] 作《论语述何》。在该书中,刘逢禄有鉴于当时的社会状况,着力利用公羊学的变易理论来解释《论语》。如《八佾》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下,刘氏解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如循环也。故王者必通三统。周监夏、殷,而变殷之质,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所谓从周也。乘殷之辂,从质也。服周之冕,从文也。”周朝处夏、商二朝之后,对前代制度有所改易,有所继承,故周朝得以强盛。可见,历史上的大一统的新王朝的兴起,必定改易前代制度以治天下,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在变易中求发展。不仅新王朝如此,旧王朝在力求复兴之时,也应革故鼎新。故刘氏在释读《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时指出,此条是孔子与弟子讨论改制之言。其时周政式微,但周命未改,周天子尚在,孔子告诉颜渊为邦不应再纯用周制了,而应时用夏制、辂用周制、服用周制、乐用舜舞,用四代综合之新制,以求周朝复兴。其时代意义不言而明。刘氏此书,虽然往往牵强附会,但却开清代以春秋公羊学释《论语》之风,对中国近代的托古改制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戴望撰《论语注》亦据《公羊》义注《论语》、以考见《论语》何休注之遗义。戴氏所注《论语》,一是宣究“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如其注“五十而知天命”曰:“性与天道,故知天命。命者,天所以教令,人所禀受,度命信也。殷继夏,周继殷,孔子当素王作,法五经以继周,治百世天所命也。”[4](《为政》),二是发挥今文“三统”说,言损益因革,言“若循连环”。如其注“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曰:“三王之道若循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成《春秋》,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兼三王之礼,以治百世。有王者起,取法《春秋》,拨乱致治,不于是见与?”[4](《为政》)戴氏的《论语注》,力言《春秋》与《论语》之相通,于《论语》中推演《春秋》“改制”、《公羊》“三世”之义,成为由清代经今文学运动向改良主义运动过渡的中介人物。最后康有为集其大成,著成《论语注》,将《论语》与《春秋》公羊学所阐发的“通三统”、“张三世”、“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结合在一起,改造成为维新变法服务的理论根据,在晚清的救亡图有的政治变革中,掀起了公羊议政、公羊改制的狂飚。
由上可见,《论语》学在清代生发出了强烈的经世色彩。
其二,清代的《论语》学具有浓厚的考据学色彩。考据学,也称考证,指对古籍文献的字音字义以及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等的考核和辨正。[5](P47),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由考经而考史,大家辈出。这一时期,有关儒家经典的笺注、古代制度的考订、文字训诂、音韵、史事考辨,以及校勘、辑佚、考异、辨伪等领域都有专著问世,学者们在考证工作上形成了一套很有特点的治学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6](P150)受此影响,重考证也成为清代《论语》学的重要特点,由此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校勘为主的《论语》研究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与《论语》有关的辑佚之作大量涌现。有清一代,《论语》古本、古注的辑佚之作层出不穷,惠栋、丁杰、王谟、袁钧、孔广林、宋翔凤、马国翰、黄奭、王仁俊等人先后来做这项工作,其中以《论语郑氏注》的辑本最多,以马国翰的功劳最大。马氏一人共辑《论语》古本、古注达四十种,其中汉代的有《古论语》、《齐论语》、《论语孔氏训解》、《安昌侯论语》、《论语包氏章句》、《论语周氏章句》、《论语马氏训说》、《论语郑氏注》、《论语弟子目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陈群、王朗、王肃、周生烈、王弼、谯周、卫瑾、缪播、缪协、郭象、乐肇、虞喜、庾翼、李充、范宁、梁觊、袁乔、江熙、殷仲堪、张凭、蔡谟、颜延之、释惠琳、沈麟士、顾欢、梁武帝、太史叔明、褚仲都、沈峭、熊埋三十一家《论语》注本。这些古本、古注的汇总成册,为后人研究该段《论语》学史乃至经学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二是有关《论语》的校勘、考异之作不断出现。如翟颢的《四书考异》(其中《论语考异》二十卷)、冯登府的《论语异文考证》、吴骞《皇侃论语义疏参订》、阮元的《论语校勘记》、叶德辉的《日本天文本论语校勘记》等。这些校勘、考异之作,多为作者多年研究之结晶,创获颇多。三是辨伪之作陆续问世。辨伪之作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孔安国《古文论语注》的真伪。陈健在其《论语古训》中认为,孔注《古论》据何晏叙“世既不传”,《集解》所采多不类,且与《说文解字》所称《论语》古文不合,反不如包氏章句之古,疑为后人假托。接着沈涛又在此基础上,以“《汉志》于《古论》下不云有孔氏说若干篇”等为据力证其为伪书,断言孔注出于何晏之伪托;而丁晏《论语孔注证伪》则从“汉儒无人提及”、“不讳汉高祖名”、安国早卒及《孔注》与《书传》、《家语》、《孔丛》说多相似,而断言为王肃所伪托;崔适《论语足征记》从《鲁》《古》异读,率《鲁》用假字,而《古》用本字为据,断言《古论》显然后出于《鲁论》,实为刘歆伪造,托之安国所传,并为作注以证之。一个是传世本《论语》的真伪问题。清代乾嘉年间,袁枚、赵翼、崔东壁三人,相继对《论语》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其中前两人只是提及而已,而后者则用力甚勤,写下了《洙泗考信录》、《论语余说》等专著,认为《论语》后五篇中,除“子张”篇外,“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四篇,可疑处甚多。而前十五篇中亦间有一二章不类者。四是专考《论语·乡党》篇名物制度的专著出现。如江永的《乡党图考》、黄守儛的《乡党考》、金鹗的《乡党正义》、胡薰的《乡党义考》、魏晋的《乡党典义》、谭孝达的《乡党类篡》等,这些著作对《乡党》篇涉及的内容多有考订,有的还附图以说明之。这些研究成果,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其中不乏考订精审之处,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论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其三,清代的《论语》学呈现出“汉宋兼采”的特点。所谓“汉宋兼采”,是指治学不讲门户之见,不论汉学宋学,一切以合于孔门义旨为标准。这里,汉学是指在治经方法上重训诂、辨名物的汉代经学和继承并发展这种学风的清代考据学,宋学是指在治经方法上注重阐发义理的程朱陆王之学。二者在治经方法上各有优长,汉学家强调实事求是,力求广稽博征,言必有据,事必有本,不穿凿附会,不驰骋议论,但这种“实事求是”,“只是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7](卷中之上)宋学讲求微言大义,好为新说,以义理见长,但“其所谓学,不求之于经而但求之于理,不求之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之于心”[8](卷三五),致使其学日益流于空疏。有鉴于此,有识之士乃主张兼采二者之长,考据义理并重。这在《论语》学方面也有体现。主要代表作有焦循的《论语补疏》和《论语通释》、戚学标的《四书偶谈》、刘宝楠父子的《论语正义》等。其中以刘氏父子的《论语正义》最具代表性,该书“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焦循《孟子正义》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9](P799-800),做到了训诂、考据、校勘、义理并重。由于该书网罗众家,引证博赡,集前人及清代各派整理研究成果之大成,所以成为古代《论语》学史上的抗鼎之作。
二、清代《论语》学特点之成因
清代《论语》学之所以具有上述特点,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明末和晚清的社会变迁,使清代《论语》研究具有了浓厚的经世色彩。明末和晚清的社会变迁,使经世致用思潮在清代两度勃兴,这两次勃兴,都影响到了《论语》学。经世思潮的兴起,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平稳,文化专制强有力,经世观念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口,国家民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部或外部的挑战,文化专制有所松动,士人的忧患意识便会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冲撞、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10](P179)在清初,伴随着王朝兴替、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学者们痛定思痛,纷纷把亡国之恨发泄到空淡心性的王学身上。许多学者认为:“明之天下不亡于盗寇,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11](卷二)经过反思,他们自觉地以匡济天下自命,力矫王学末流的空疏误国,不约而同地倡导学术必须“经世致用”。“他们的目标是要重构古典儒学,重估经典中治理现世的主张。”[12](P54)可以说,“众多思想家和学者从反思明亡教训,清算理学弊害中发出的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呼声,既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本质内容的反映,也是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精华的体现。它鲜明地表现了一代思想家和学者的觉醒与思考,并直接促成了明清之际学术风气的转换。”[13](P29)这种学术风气的转换,表现在《论语》学上就是在《论语》注释中出现了经世实学色彩。嘉道以降,清朝的统治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在政治层面,内则“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14](P78);外则西方殖民者挟着鸦片,带着炮舰,一次次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学术层面,内则烦琐的考证与注解经义,使乾嘉汉学亟亟于在故纸堆中讨生活,避而不谈现实问题;外则西学伴随着欧风美雨阵阵袭来,中华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受其影响,打破现状、革除积弊、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有识之士积极主动地追随时代变化,直面中国社会现实,他们“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异”[15](P119)。在“求变”、“图新”的追求中,他们纳入了西方的声光化电、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以求致用。“士林中遂形成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新思潮和讲求实学的新学风。”[16](P55)这种新学风也影响到了《论语》学。
其二,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学术的兴衰与统治者实施的文化政策息息相关。诚如经典作家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17](P52)可见,在王权支配一切的时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对学术具有支配作用。清朝亦可作如是观。
第一,清政府“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宋学和汉学的兴盛与结合。清朝建立后,为了长享国祚,依然祭起了理学的大纛,尊崇儒学正统。顺治三年(1646),规定科举考试内容采用程朱理学著作,《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颐《易传》和朱子《易本义》,《诗》主朱子《集传》,《书》主蔡沈的《书集传》,《春秋》主胡安国《春秋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康熙主政后,极力抬高朱子的地位,四十五年敕令李光地主持编纂《朱子全书》,并颁行全国。五十一年,将朱子陪享孔庙,升大成殿十哲之次。及至乾隆时,下令选录明清诸大家有关《四书》的时文,辑成《钦定四书文》,以为士子科考的程式。又通过追谥、褒奖明末死难忠臣之士和编写《贰臣传》、《逆臣传》,强化理学的纲常伦理观念,程朱理学遂成为清廷治国安邦的正统思想和官方学术。
在宋学蒸蒸日上的同时,顾炎武等在野学者则倡导“经学即理学”,清代学术走上了“回归原典”的不归路,儒学重心也从“四书”转向“五经”。这不仅一改明儒空谈性理、束书不观的积习,且在宋学之外另辟蹊径,形成考据儒经的趋向。而清廷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对汉学也予以了关注,如乾隆帝就明确规定“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细及名物象数”的汉学“有所发明”,“有裨实用”[18](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并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延揽了戴震、纪昀等一大批汉学家。同时还在科考中予以扶持,增加了经、史考据方面的内容,使汉学迅速加入到官方学术中。诚如马宗霍所言:“治经确守汉师家法,不入元明人谰言者,实始于乾隆时,分堋树帜,则有东吴、皖南两派。吴学惠栋主之,皖学戴震主之。……论者谓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19](P145)由于汉学、宋学治经方法迥异,所以二者同为官方学术时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如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撰成《国朝汉学师承记》,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诸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20](P6)而理学学者方东树则撰成了《汉学商兑》,与江藩针锋相对。他指斥江藩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又一一反驳江氏对宋学的批评,列举汉学弊端,并攻击其“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7](《序列》)集中体现了护宋斥汉的激烈态度。有鉴于此,乾隆帝采取了调和的方法,他在下发的征书谕中说:“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当备为甄择。”[18](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表明了政府的态度——汉宋学著作兼收。受其影响,如纪晓岚在《四库提要·经部总叙》中辨二学之关系时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抵,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擂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去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在谈到二学各自长短时说:“《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21](卷一)不难看出,纪氏辨二学之长短,未袒护任何一方,反对峻门户,固壁垒,此乃持平之论,门户之见,与此固殊。所以清人方濬师评论这段文字说:“此论出,虽起郑、孔、程、朱于九泉问之,当亦心折也。”[22](卷七)我们说,纪昀是乾隆帝钦定的《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之一,他的观点自然代表了皇帝的意志,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政府的文化政策是支持汉学、宋学兼采的。兼采汉宋遂成为乾隆帝中期以后清代学术的一大特点。《论语》学亦不能例外。
第二,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政策,是乾嘉考据学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政府在提倡宋学、汉学的同时,也对文化学术中的反清排满思想采取了强硬措施,钳制言论,大兴文字狱。如康熙时有《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时有汪景棋、查嗣庭、吕留良之狱等。乾隆时,文字狱达于极点,文网之严密,罗织之苛细,是康雍时所未有的。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文字狱几乎连年不断,一度呈冤滥酷烈之势。为了配合文字狱,乾隆帝还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大规模的禁书运动,这次禁书运动时间长,从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八年;危害大,据今存档案及有关资料统计,总共禁毁书籍3100余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0000块以上,这还不包括被文人学士和一般民众自行毁掉的书籍。[23](P72-78)这是中国文化的又一次大浩劫。“清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乾隆帝直接操纵的禁书运动,给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典籍带来了无可弥补的损失,也给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影响。”[13](P183)专门汉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诚如梁启超所言:“凡当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24](P21)清政府对汉学的提倡和大兴文字狱的做法,就把学者们赶向了纯学术的领域,萧捷父先生曾说:“政治上的强控制使独立的思想探索领域荆棘丛生,举步维艰。文字狱的惨祸使学者们对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的政治改革几乎不敢置一辞,惟有在远离政治的考据学领域和虽然远离政治,但却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感性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理欲、情理、义利诸哲学问题探讨中,学术文化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25](P628)学者们动辄得咎,终日惴惴不安,学术之触时讳者,皆不敢讲习,所谓经世之务,终不免成为空论。于是他们只能钻进故纸堆,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于世无患,与人无争。故乾嘉时期,治经学、史学、地理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