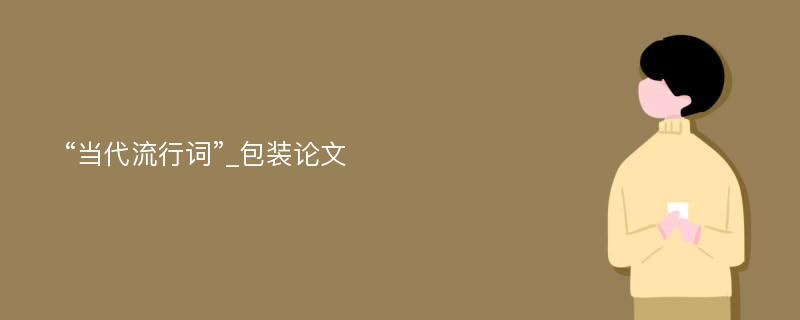
《当代流行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行语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畅销新书
包装
人类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视事物与自身的外观。从好的方面来说,可以看成是审美意识的提高,另外则也能视作伪饰。于是,包装大行其道,一种商品能否畅销,多半倒与此有关了,“酒好不怕巷子深”的纯朴民风,已荡然无存。所谓包装,也不仅指某种容器,含义正变得愈来愈丰富,包括品牌、广告形象,以自己的妙法得过什么大奖,等等。顾客也就以此来作选择时的参考乃至标准。至于到手后的货物,往往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概念,新近更扩展到“人体”,人的价值似乎也只有通过“包装”才能显示出来。于是名牌服装,甚至动辄多少万元一件的“极品”大氅,相继应市。而内中囊着的,不乏体态与品格都低劣之徒。但只要这么包装过一番,至少买卖乃至行骗均要容易得多。当然并不限于衣着,名车、别墅、印有某头衔的名片,内容也愈来愈丰富。
这种时候,真正富有创造力与操守的精英,常常倒像乞丐了。此辈或者无“力”,或者根本不屑于包装。他们仍然相信是金子就总会闪光的。
但金子之外,当代确实有了更多闪光的玩意儿。
剥离
这个流行词儿的背后,蕴藏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人被从他依附、固着固然并不一定如何愉快却久已熟悉的某物、某种关系,尤其是关乎存活的某岗位上离析出来,那是何等失魂落魄的经历!因为长久的附着,他甚至已失去选择的能力,焉知漂浮而来的命运是什么?
目下不少人在经历的这种考验事实上一些人早就经受过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改革便看作一场大规模的剥离,整个社会将转移运行轨道,要克服原有的惯性,它不能不经受震荡,甚至面临倾覆的危险。但当预定的前途无法通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更大的困难似乎在于,这种整体的处境还得让每个人独自面对与承受,体会上帝死去之后更加孤独、更加艰难,也可能更加幸福,却必然更加自由的生活。看看“先富起来的人”是颇有趣的。他们多为不情愿的最早剥离者:或婚姻失败、或久病失学,或无业即被社会弃绝于外,或……我不再写下去了。无可奈何使他们只好成为依靠自己的人,结果最早进入了新轨道,并逐渐如鱼得水。
剥离,这词儿许多人谈虎色变。就像在某个门坎上,孩子害怕成为大人。
但孩子终究要长大。
我们都将被“剥离”,而投入一种新的处境。这几乎无可选择,这将迫使我们选择:选择自己的道路与方向。
中国人将从此成熟起来。
不是万能与万万不能
这颇似绕口令的前言和后语都是有关金钱的。前者流行于五六十年代,全句为:金钱不是万能的。那时举国正在进行一种新的社会试验,企图以理想取代通货成为人际沟通与交往的媒介,最初还搞过供给制,至少在某个团体内部,金钱不但不是万能的,还几乎一无所能。然而理想过于空泛,具体操作过程中便以权力(那时设想它会永远是最公正的)逐渐填补了真空。权力易被腐蚀,但在那个年代,它尚清纯。所以金钱尽管可用于种种收买,却不能收买一切,它确实“不是万能”的。
后一句全文为: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它反映了后来的时代,当权力本身逐渐腐败,已难以体现公正的理想,这时来看金钱,似乎也不再那么罪恶,乃至只有资格去铸厕所,它至少在某个层面上还是公正的。而此时人们也不再那么注重公正了,比较之下,仿佛繁荣与富裕更能提高生活的质量。在那么一种共识之下,阮囊羞涩自然“万万不能”了。
但能守住清贫的人还是有的,他们仍看重精神价值甚于金钱,这些人或许是时代的落伍者,也可能是一个更新时代的先声。
不争论
过去我们都喜欢明辨是非,而众口纷纭一时难调之际,便往往借用别的手段,这有多种名目,或曰反右,或曰防修,效果相同,就是不让你说了,我的意见不容置疑。到这份上,“是非”就算“辨”出,随后便可统一行动了。偶尔严重起来,置对手入牢狱乃至死地的都有。这也不是国粹,且看法国大革命,一切争论不是都弄到断头台上去才解决吗?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理解“不争论”,真是绝顶聪明的做法。只要互不相扰,不妨各行其事,许多结论让事实来告诉大家,毕竟智商相差都不多,终究会弄明白的。其中实则是碍于私利的,逐渐也悟得以更好的方法去谋了。所以大体上的相安无事是可能的。说,尽可各自悄悄说去,不把公众注意都引到“争”上面来,有精力不妨去做。这也合于西谚“沉默是金”,少说点空话,钱就来了。而几十年来,我们被多少无益虚言所耗,祸害之深,谁能没有一点惨痛的教训呢?
BP机
已经几乎在任何场合,都能听见突然响起的嘟嘟声了,一些庄严或是融洽的气氛,因此被突然撕裂,最尴尬的大约在情人作爱的倾刻,生活中难以复得的若干瞬间,就这样破坏了。我并非复古主义者,也没有贬抑类似BP机等现代科技产品的意思。它们的问世,的确给大家带来了方便,普及之快,就可见出需求之盛。一机在身,等于在这世间树立了你的一个坐标,让希望与你对话者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你,而无意中,独处的自由也就丧失了。
法国作家费利普·穆莱说:“通讯手段乃是控制手段。”也许内心深处,人还是愿意受制于某个别的存在?强权消解之后,便寻别的来取代。目下腰上别个BP机是顶时髦的事情,似乎叫唤愈频繁,愈显出他在这世间的价值。无异不少人已成为自觉的奴隶——由金钱或别的意志驱遣着,因此得些忙碌的快活。
想起波德莱尔的一句老话,这位现代主义的先驱者,说他想在已被普遍认同的自由之上再加两个自由:自相矛盾的自由和消失的自由。而BP机的问世,使这后一个自由不复存在。也许只有哲人才作这样的冥想,俗子哪能耐住独处的寂寞呢?但凡是人,至少某些顷刻总不愿为他们所扰的。
至于思想家,也许一部电话机已是多余的。
我颇能理解钱钟书夫妇的闭门索居,远离尘扰并非因为他们如何谦虚,实在读书给了他们远比入世更多的快乐。既如此,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去应酬呢?
变通
这是在经济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统得还是太死,要求放宽而往往不可得。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出此下策。(或曰上策?)
某位“变通”专家的结论是:现有政策体系中,存在着足以利用的可能。一是国家那么大,一个政府要管11亿人,所以往往比较原则,而越原则的政策对解决具体情况灵活度越大,就看你怎么理解;二是“红头文件”本身前后有矛盾,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此一时彼一时,矛盾双方必有一方可以利用;三是政策出自多门,部门条条,区域块块,也存在各执一辞的可能,为我所用不难。
这实际上正在形成一门新的学问,或曰行当,专门研究政策的漏洞而加以利用,就像外国的律师深谙法律的薄弱环节来为当事人服务一样。那么,施展这种本领的余地越大,是否越显示出政策本身的不完善性乃至不合理性?这也显示出中国社会正趋于法制化,若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领导点头即合于政策,那时谁还去自己研究政策?
标签:包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