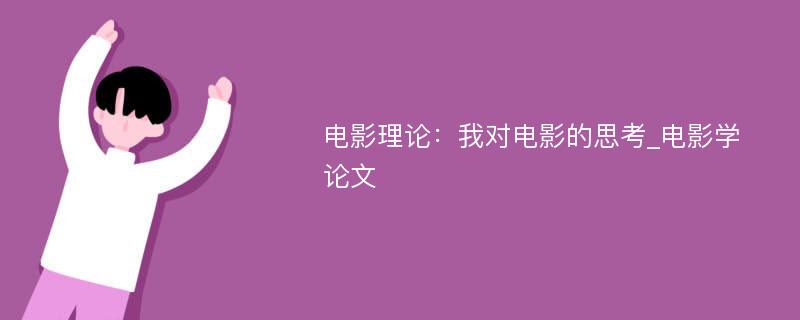
电影理论:面向电影的我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不是被物理的力量,而是被心理的力量,推动着走向电影院的。 ——麦茨 心之官则思。 ——孟子 电影的故事只是假象,是空的,关键是你个人怎么跟观众将心比心,心心相映,作为言语不能表达的沟通……把心交给观众…… ——李安 世界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的迅猛及强劲发展,一定会把电影理论问题郑重提出。前不久(2016年6月4-5日),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主办了“电影与媒介:理论新前沿和学术新领域大型国际研讨会”,特别是在会议的讨论互动环节,甚至提出了什么是理论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比较宏观地勾画出电影理论的历史演变、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的大致走向,少不了做一番回顾梳理、审视评估、展望憧憬的工作。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许多人来说,对电影的过去和现在做出判断,对电影的未来和发展进行想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冲破历史迷雾和时代围困,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德里达在宣布文字学诞生时说的那样,“未来已经在望,但是无法预知。展望未来,危险重重”。① 一、理论真的是灰色的吗? 提出这一问题,首当其冲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理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理论就是在不同知识领域运用概念进行陈述的组织化和集成化形式,陈述必须遵循逻辑原则;理论有三个要件,概念、观点,以及能够把一系列概念和观点整合起来的框架。理论作为对象的“逻辑素描”或“心灵戏剧”的价值和意义,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各种知识海量般涌现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突出了,尽管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随意贬损理论,并向理论泼脏水的思维惯性,几乎从未停止过。始作俑者大概可以追溯到德国诗人歌德,这里不提推波助澜者荣格、维特根斯坦等人。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从事或不从事理论工作的人,通过引用据说是德国诗人歌德说过的一句名言“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来表明自己同声誉不佳的理论的天然“劣根性”划清了界限。像巴拉兹这样敢于宣称“真正的理论绝不是灰色的,相反,它给一切艺术都开辟了广阔的自由前景”的电影学者,绝对是凤毛麟角。②这句话其实来自歌德《浮士德》(1808)中一段似乎并不重要的描述:有一天,一位青年学生前来向浮士德求教,想拜浮士德为师。浮士德并不想接待,于是,魔鬼便装扮成浮士德,来回答那位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说道:“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结果,这句话便阴差阳错地扣在了歌德的头上,成了一句流布甚广、贬低理论的说起来朗朗上口的俏皮话。尽管笔者认为,应当重新认识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恢复理论研究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③但并不意味着认为,所有领域(包括艺术门类)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拥有自身领域的理论。某一艺术门类理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不仅应取决于该艺术门类及对该艺术门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还应取决于该理论对于其他领域,比如哲学领域,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样,问题就变成了,电影究竟有多重要,电影理论又有多重要,它们的发展程度又如何的问题了。 二、电影在何种意义上定义人类? 巴拉兹说过:“电影是唯一可以让我们知道它的诞生日期的艺术,不像其他各种艺术的诞生日期已经无法稽考。”④笔者曾经这样说过: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电影看成是一种“神话故事”。如果说这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电影的诞生和它飞速发展的历史本身简直就是一个神话故事。⑤总之,电影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但是,笔者现在希望表达的是,虽然电影的历史发展相当短暂,但发展速度却异常神速;虽然电影已经向人们显示出它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利器的重要性,但是却仍然处在一个相当原始和初级的阶段。关于电影的历史和发展速度,这一点几乎不需要什么论证。关于电影的重要性,笔者曾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和前不久为上海大学举行的“电影与媒介:理论新前沿和学术新领域大型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理解电影——论思的延伸》中进行了一定的阐述。⑥此次会议受益良多,笔者论文观点可概括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一定要在人类之梦中大有作为,并且成为人类之梦进程中最引人入胜和光彩夺目的一个部分。人类之梦的要义是,实现一个伟大的转变,即语言及文字手段使可见的和可想的以抽象符号形式交互传输,电影及数字技术使可见的和可想的就以见和想自身的形式交互传输。”⑦一位国外学者,在发言中特别提出了电影如何定义,以及人如何定义的问题。正是她的这一把电影和人的定义同时提出来的提问,让笔者意识到,尽管电影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能够形成共识和像样的定义,但是,正如20世纪的哲学家们已经在用语言来给人下定义一样,21世纪的哲学家一定会走到用电影来定义人的一步。最近国内文学界在讨论中国网络小说“野蛮生长”的时候,提到了麦克卢汉关于人类由印刷文明向电子文明转化的问题,还提到了20世纪初期英国小说家伍尔夫在自己的书信里提到,“在新的条件下,人的概念要重新定义”的问题。⑧现在,我们也许更清楚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谈谈方法》中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论断究竟有多重要了:“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⑨笛卡尔把人的思和人的存在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论断,开启了“人如何思便如何存在”的想象空间,给后来的哲学家们带来了无尽的启发。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用语言来定义人,卡西尔用符号来定义人:“人是拥有符号的动物”,给后人用电影来定义人预留了拓展空间。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中的“我思”,是“语言的我思”:“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⑩伽达默尔则通过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拥有语言的存在,指出:“语言是人类存在的真正媒介”,把语言在人成为人和作为人过程中的意义提到了至关重要的程度,即人掌握语言的程度等于人成为人的程度。(11)海德格尔晚年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自己的早年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内在性批判”,提出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再转向”问题,主要体现在他196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面向思的事情》中。海德格尔承接其师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的提法,提出了“面向思的事情”,他指出,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之思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并把这种完成称之为“哲学终结”(他不像霍金那样,毫不留情地宣布“哲学已死”),但是,思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更重要的是,尽管这个任务是哲学从开端到终结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却是哲学和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科学从来都没有也不能完成的。这个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对此,海德格尔不仅显得相当谨慎,而且十分小心翼翼。在他看来,巴门尼德、柏拉图、黑格尔和胡塞尔都意识到了这一任务。他反复论证了实在与主体的一致性,“面向事情本身”和“面向思的事情”的一致性,即,“面向思的事情”,就是“面向事情本身”。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又是什么呢?他引证了胡塞尔的一段在他看来相当重要的话:“任何原本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性源泉;在‘直观’中原始地(可以说在具体现实性中)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一切,是可以直接如其给出自身那样被接受的,但也仅仅是在它给出自身的界限之内……”接下来,还提到了柏拉图早就认识到了的“没有光就没有外观”(这里我们必须提到,拍摄电影要有照明,电影撷取的不正是事物的外观吗?),然后他又引证了巴门尼德的一段哲理诗句,提出了“被思为澄明的那种充沛圆满的无蔽本身”。(12)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思与他之前所说的“语言之思”的不同在于,“语言是在本身既澄明又隐蔽着的到来”。(13)我们似乎能感觉到,海德格尔是在热切地期待着一种不同于“语言的我思”的新的我思。电影这个词在他的字里行间中,简直呼之欲出。如果海德格尔不是那么书斋气,对电影再多一些了解,就好了。遗憾的是,要等整整15年之后,德勒兹才在论述爱森斯坦的蒙太奇探索的理论与实践的表述中提出来“电影的我思”这一重要语段:“就是发生于皮质表层的和谐整体促使思维的诞生,即电影的我思:作为主体的全体。”(14)麦茨探讨故事片的特点时,也曾指出过电影作为知觉的主体性,即“电影的我思”特点:电影在人的精神装置内部完成,但却需要包含不是真实知觉素材的刺激材料,并具有可传递性和逻辑化特点。(15)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句式,就应该说:电影就是本身既澄明又无蔽的充沛圆满的到来。必须指出,意识到这一点的重大意义是,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电影的各个种类、类型、形式和规格的作品的规律性,都会因此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来加以认识和理解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才说,电影不是处在一个高度发达的阶段,而是处在一个相当原始和初级的阶段,当然,肯定会有人提出质疑。所以,这里一定要提到安德烈·巴赞的一篇重要文章《“完整电影”的神话》(1946),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绝对是一篇只有天才才能写出的文章。这位被人们称之为自己读那些最艰深的哲学著作,据说,多是现象学的著作,但却写出最通俗易懂的电影评论的评论家,为了解释电影的诞生与发展,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一个一般人很难认真对待的“完整电影神话”理论:“电影是一种幻想的现象。人们的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是完备的了,如同在柏拉图的天国中一样,与其说技术对研究者的想象有所启迪,莫若说物质条件对设想的实现颇有阻力,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16)他明确地把电影发明创造的第一位原因,归结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伟大理想,即“机械复现现实的神话”“完整的写实主义神话”“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即“完整电影的神话”(17)的实现,并把这个神话般的理想追溯到远古期造型艺术中的绘画与雕刻的“木乃伊情意结”。他还指出,在古代,“这曾经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在现代,仍然存在于那些伟大电影先驱者的想象中,“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在世界的幻景”。(18)也就是说,电影是从萦绕在那些少数先驱者头脑中的一个共同的念头之中,即从一个神话,即“完整电影”神话中诞生出来的。电影确实需要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冲破重重阻碍,一步一步地实现,电影的诞生却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貌似悖理的是,一切使电影臻于完美的做法都不过是使电影接近于它的起源。电影还没诞生出来呢!”(19)现在看来,只是给他的思想贴上纪实美学的标签,是绝对不够的。如果一定要贴,那就贴幻想/纪实美学好了。这样,我们才能从“完整电影神话”的高度,得出电影仍然处于相当原始和初级发展阶段的结论。更不用说,把电影同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字相比,电影正处在一种“仓颉造字”阶段。把电影同有数万年历史的语言相比,电影在制作、传播及检索等方面的局限性,更是显而易见。电影作为20世纪的重要产物,按照美国评论家三十多年前的看法,仍是电影发展的原始时代和古代。 这里须提及一个例子,这就是大卫·芬奇导演的影片《本杰明·巴顿奇事》(又名《返老还童》,2008)。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的拍摄,在美国乃至世界电影的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在电影艺术及技术表现的进程中应被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影片改编自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作家之一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的一篇同名短篇小说(1922)。这位被张爱玲称为“我最推崇的美国作家,他是个天才”的人,(20)有着疯狂而短暂的一生,当然,也写出了一篇疯狂的、值得拍成电影但是当时并不具备拍摄条件的小说。这篇小说,给电影人以及电影媒介技术发展水平都出了一道考题。根据小说拍成的电影,的确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巴赞关于电影发展水平的判断:“如果说电影在自己的摇篮期还没有未来‘完整电影’的一切特征,这也是出于无奈,只因为它的守护女神在技术上还力不从心。”(21) 把这篇小说拍成电影,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成了Digital Domain的一个项目,负责人是导演了影片《美丽的心灵》(2001)的朗·霍华德。由于技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2002年,又转到导演过影片《七宗罪》(1995)的大卫·芬奇手上。影片在人物形象的表现上难度极大,拍摄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精心打磨,六年之后终于面世。 影片通过垂暮之年的女主人公黛茜对女儿的断断续续的回忆,来表现她和男主人公本杰明·巴顿之间,既值得回味又令人揪心的一生情缘。本杰明·巴顿是一个一生都与自然规律相悖谬的怪人,他的降生,便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怪胎,对任何家庭的父母来说,都不啻晴天霹雳,因为,他虽然是婴儿之躯,但是,看起来却像80多岁行将就木的老人,接下来,他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其中不乏艰辛和苦难,也不乏喜悦的看起来越活越年轻的奇迹般的“逆生长”过程。他的遭遇也是极富戏剧性的:他11岁时,长的却像60多岁的老年人,和年仅6岁的小姑娘黛茜相遇,两人之间萌发了爱慕之情。十几年之后,“二战”爆发,他和许多其他美国人一样,远赴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斗,战后重返美国时,已由儿时的老态龙钟模样,长成为帅气逼人的小伙子,并与儿时的梦中情人、现已出落成风姿骄人的漂亮舞者的黛茜重逢。两人陷入热恋,并在年龄和外表都相当般配的情况下一同度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幸福美好时光。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本杰明却在所有人(包括黛茜)都不得不经历的苦于岁月带给他/她们衰老的忧虑中,继续年轻、英俊和阳光,马不停蹄地返老还童,逆行而进,不断加速两个人在外貌上的反差,使他与深爱着他的黛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令人揪心了。影片最让人感叹并唏嘘不已的是,巴顿选择离开,但最终还是回来了。回来时已经老年痴呆得认不出黛茜了,看起来还是一副儿童模样。影片结束时,观众看到,满脸皱纹的老年的黛茜,怀里面抱着一个看起来仿佛是刚刚出生的,但是却马上就要老得死去的婴儿,这个人,正是她一生中最爱的人。影片告诉我们,她发现巴顿在临死前的一瞬间认出了她,观看至此,每一位观众都能体会到她此刻正在经历一次怎样的撕心裂肺。 可以想象,拍摄这样一部在任何意义上都十分严肃的影片,不仅需要它的策划和拍摄者具有极大的艺术勇气,而且,还需要有好莱坞工业水平决定的制作团队巨大的技术支持。影片获2009年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三项大奖,绝对是名至实归。主演本杰明的布拉德·皮特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已有溢美之嫌。虽然他饰演男一号,但表演乏善可陈,剧情几乎没给他留下多少表演空间。必须指出,这部影片的观看,绝对是一个既感动同时又相当不满足的过程。影片暴露出剧情本身的惊心动魄和感人至深与对它的呈现匹配的巨大反差。能知道主创者们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正如导演所说,“尽管最后的影片还不完全令我满意,但也实在很难想象如何能把它做得更好”。影片表现主人公的体量,要从婴儿之躯开始,逐渐成长,长到停止生长时,再变成逆生长,直至回归婴儿之躯。与此同时,主人公的体貌,却要从老年开始一直不断地变得年轻,直至变成婴儿模样。要把这一过程呈现出来,必须充分运用迄今为止人们的认识尚不十分清楚,甚至羞于谈及的电影的相辅相成的两大本性:纪录本性和合成本性。对此,美国学者卡维尔(影片《生命之树》的导演泰伦斯·马利克在哈佛大学学习哲学时的老师)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电影能像描绘自然的东西一样得心应手地描绘幻想的东西。”(22)大卫·芬奇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本杰明其实是一个合成体,用电子成像捕捉布拉德·皮特的面容,然后安在其他人的身体上。”“这个合成体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在观众眼前出现的就是一个整体,丝毫看不出是一个合成体。……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无论做什么样的特技效果,必须让观众在第一时间认出那就是布拉德·皮特。”(23)影片最大的魅力和看点之一就是希望能够仔细地阶段性地端详一位现年四十出头,仍然相当帅气的皮特“饰演”的巴顿,究竟如何由婴儿体量老年样貌,一步一步地长大及衰老回缩同时经过一个年轻化的过程变回婴儿的。看这部影片笔者最大的感受是,极度感动和极度失望:让影片优雅地呈现小说所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曾反复地看过国产电视连续剧《甄嬛传》(2011),最大的感受就是视觉上过瘾,镜头中呈现的无论是人物景物、美轮美奂风流倜傥,还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都给观众留下了足够的端详时间。这种比较似乎不够恰当,但必须说的是,要使得现在看来显得相当青涩、窘迫、匆忙和力不从心的影片,在视觉观赏上达到《甄嬛传》的水平,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三、电影理论能够催生电影学吗? 回到电影理论,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仅仅从探讨电影概念入手,我们就能发现,虽然电影诞生以来经历了一个制作、存储、传播和观赏方式的不断扩展和延伸的过程,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定义。也没有发现哪一位电影研究者为此感到愧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电影始终处于一种“名实漂移和裂变”的“无名尴尬”中,无法掩饰地暴露出电影理论的发展,不管学者们为此写了多少文章和著作,电影理论仍然处于相当幼稚和粗糙的阶段。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电影理论研究中学理探究的惊人的缺位。这样说一点儿也不过分。就连被广泛使用的最重要的一个电影片种“纪录片”的译名,事实上都是错误的。但是,纪录片的研究者和创作者竟然能够默认和容忍这种错误。著名纪录片研究者尼科尔斯先是说,“每部电影都是一部纪录片”。接下来,他把纪录片分成两类:“达成心愿的纪录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片;“再现社会的纪录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纪录片。他很清楚这种做法的荒唐可笑性,于是,他在行文的括弧里这样写道:“在下文中,我们一律将达成心愿的纪录片简称为‘故事片’,将再现社会的纪录片简称为‘纪录片’。”(24)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敷衍了事,堂而皇之地大谈所谓的“纪录片”了。他还算是明白人,但是仍然不知道孔子关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道理很简单,“简称”,其实就是“误用”。我们为什么要容忍“误用”呢?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的误用,破坏了我们和事物本真的关系”,“语言的荒疏是由于人之本质之被戕害”。(25)有时仅仅是概念之争,可能就人命关天。我国“非典”时期关于“非典型肺炎”的病因是“衣原体”还是“冠状病毒”之争的教训还不惨痛吗?国内某些电视频道中播放的一些标明为纪录片的节目,有些简直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难道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在大量的以电影理论为名义的研究中,“语言大面积地荒疏”的严峻状况吗?电影理论忽视基础研究是很有传统的,加之电影理论研究的重镇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正是实用主义的故乡,美国大卫·波德维尔一派对欧洲大理论(grand theory),其实就是基础理论的极力攻击,对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的大力倡导,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并不是良性的。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在抨击之列,后果的严重性,可举一例说明。德勒兹的电影名著《电影1:运动—影像》(1983)、《电影2:时间—影像》(1985)有两个中文版。一个是台湾版,一个是大陆版。就说《电影2:时间—影像》中的最后一章,即第十章的第一句话,台湾版本是:“电影并非言语(langue),不论是通用言语,还是原始言语都不是,甚至不是语言(langage),它使得一种物质现世,就像一种先决性,条件,一种语言建构其专属‘对象’所必需的关联性元素(能指的单元与运作)。”(26)大陆版本是:“电影不是普适或原始语言,甚至不是一种言语行为。它展示一种心智质料,这种心智质料如同一种预含物,一个条件,一个必然对应物,言语行为通过它建构自己的‘对象’(意义单位和操作)。”(27)这两个版本,一般读者都是很难读懂,根本不知道讲什么,因为翻译有问题。估计翻译者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或者不了解,或者了解有限。索绪尔思想中有一个关于语言的公式:语言=语言系统+言语,是索绪尔的核心思想。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用的是法文,这个公式就变成了“Langage=langue+parol”,用英文来表示,就是“Language=Language system+speech”,也就是说,翻译者不知道语言系统、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区别,不知道langue应该翻译成语言系统。其实,德勒兹表述得并不那么复杂。他想说的是,电影没有(不是)一种语言系统,现行的和原始的都没有(不是),就算哪一天电影有(是)了,也绝对不是语言。因为,两者使用和运作的材料不同。那电影是什么呢?电影是语言试图描述,又描述不了,并仿佛先于语言而存在的东西。总之,在德勒兹看来,电影与语言之间存在着绝对不可通约项。再举一例,一位学生去台湾带回来一本介绍电影理论的书送给笔者。这是一部对电影理论的形态及历史的综述式汇集之作。作者是美国纽约大学电影学系教授,曾与克里斯蒂安·麦茨有过较深入交集。翻阅了一下这本书,笔者就明显地感到,电影理论研究在美国的困境和艰难处境。主要表现在,他不愿意,或许是不敢称自己是一位电影理论家:“我不认为自己是理论家,我只是阅读理论及使用理论的人,一个跟理论‘对话’的人。”在全书结尾部分,他似乎是以一种迷惘和近乎绝望的心情对电影理论的现状及前景做了描述:在各种五花八门的中层理论的挤压下,“电影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整合研究,如今蒙上了一层阴影,又好像把理论当成分析电影分析花园中的大毒蛇,……电影理论的多元性确实令人兴奋,不过,电影理论的多元性也带来了支离破碎的危险”。(28)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电影理论的发展正面临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任务,虽然形势严峻,但前景乐观。电影理论的目标就是催生电影学。由于电影的特殊重要性,建立电影学是必要和值得的。电影学概念于1948年首次提出,为此还专门造了一个新词“filmology”,日本的《美学百科辞典》(1961)中专门设有电影学(filmology)条目。(29)日本学者浅召圭司出版了一本内容简约的《电影学》(1964)一书,国内曾有学者译出此书,但并未出版。该书尝试建立电影学理论框架的意图十分明显,他把电影学的任务确定为:“十分留意电影所有的多个侧面,并志向于捕捉电影的全体。”“由这两个疑问的答案可以使它的内容产生天壤之别。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说,‘电影学’并未确立,它还处于黑暗之中的摸索阶段。”(30)克里斯蒂安·麦茨也曾认真地探讨过电影学的问题,(31)但这一努力却遭到了美国电影研究者的抵制,他们宁愿使用那个广泛使用、泛泛而论的“cinema studies”。(32) 笔者曾指出过:“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发现,几何学正在经历一种世界性的衰退,而物理学却正在经历着一个世界性的兴起。这一发现使我想到,一个时代可能有一个时代的占有优势地位的科学学科。它为该时代的各个研究领域或人文学科提供思想方法。就是说,古代的优势学科是几何学(欧几里德几何学)。据说,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建立的柏拉图学园的门口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道: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柏拉图令人佩服之处是,他抓住了那个时代思维方式的灵魂。让我们看一看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连其行文方式都采取几何学论证方式。……近现代的优势学科是物理学(细致的划分尚有待于研究)。马克思曾经称赞过的培根也是一位划时代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的方法论基础是物理学的(即实验的或归纳法的)。如果培根也建立了一个学园,而且门口也要挂一块牌子的话,我想,那上面一定会写着‘不懂物理学莫入’。他的体系性哲学著作的书名是《新工具》……按照这个思路,我认为,20世纪(即当代)的优势科学是语言学。语言学几乎成了所有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如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33) 必须承认,当时笔者还真的不知道,在语言学之后,引领时代的将会是什么学科,也不知道海德格尔后期发生了重要转变。在经过了整整20年之后,接下来笔者想要说的是,如果海德格尔(当然只是他的早期阶段)或者维特根斯坦,都要建立一个学园,他们的门口也要挂上一块牌子,我想,那上面一定会写着“不懂语言学莫入”。如果德勒兹也要建立一个学园,门口也要挂上一块牌子,那上面应当写着的就是“不懂电影学莫入”。因为电影学将可能成为21世纪的优势学科。如果22世纪的一位伟大哲学家也要建立一个学园,而且门口也要挂上一块牌子,我猜想,那上面应当写着“不懂生物学莫入”。也就是说,电影学是和过去的几何学、物理学、语言学和未来的生物学一样的,其形态能够对该时代哲学形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由于这个原因,笔者和赵斌博士主编了《电影学》(2015)一书。(34) 前不久,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大卫·查莫斯在《为什么在哲学中没有更大的进步》一文中,对人类哲学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对于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来说,哲学进步的水平只是达到了“还有半杯”水,或者“只剩半杯”水。作者预期的是,要使哲学进步的水平达到“一整杯”水的水平。(35)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指出,怎样才能使哲学达到这个水平。事实上,大约半个世纪之前,海德格尔已经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在一次题为《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的演讲中,论述了“哲学终结之际为思留下了何种任务”的问题(36);德里达的解决方案要更早两年:“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37)如果说德里达期待的是文字学,那么,海德格尔则似乎指向了电影学。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哲学早就并继续期待着电影学的诞生与发展。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或许我们过于麻木了,没有发现。 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世界文化及学术研究重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态势,同时,伴随着的是,世界性的由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过渡及两者此消彼长的均衡发展过程,这就给了中国电影研究者发挥智慧、贡献力量以难得的机遇。中国学者如能知难而进,先行一步,一定会对包括中国电影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德里达在宣布“文字学”的诞生时说:“经过几乎难以察觉其必然性的缓慢运动,至少延续了大约二十世纪之久并且最终汇聚到语言名义之下的一切,又开始转向文字的名下,或者至少统括在文字的名下。”“我们用‘文字’来表示所有产生一般铭文的东西,不管它是否是书面的东西,即使它在空间上的分布外在于言语顺序,也是如此:它不仅包括电影、舞蹈,而且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等‘文字’。”(38)德里达的表述,对于电影学来说,仍然适用,但是,必须像德里达所说的那样:“未来已经在望,但是无法预知。展望未来,危险重重。” 注释: ①[法]德里达《文字学》(1967),汪唐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②[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电影文化电影精神》,安利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③[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④[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⑤参见王志敏、崔晨编著《声音与光影的世界:影视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2012年的论文系《论电影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革命性意义》,载于《艺术百家》2012年第4期,上海会议提交论文题目是《理解电影——论思的延伸》。 ⑦参见惊秋呢的博客《理解电影——论“思的延伸”》,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d4bb30102w6sn.html。 ⑧见《北京青年报》(电子版)2016年6月14日,http://epaper.ynet.com/html/2016-06/14/content_202674.htm?div=-1。 ⑨[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27页。 ⑩[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11)[德]伽达默尔《人与语言》,张志扬等译,载《美的现实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28-140页。 (12)[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76页。 (13)[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4)[法]德勒兹《电影2:时间—影像》,黄建宏译,香港:远流(香港)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88页。 (15)[法]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82-117页。 (16)[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17)同(16),第21-22页。 (18)同(16),第19页。 (19)[法]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0)见[美]菲茨杰拉德《最后的大亨》,李庆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 (21)同(16),第21页。 (22)[美]斯坦利·卡维尔《看见的世界——关于电影本体论的思考》,齐宇、利芸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23)见时光网官网,http://movie.mtime.com/52414/behind_the_scene.html。 (24)[美]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25)同(13),第77、79页。 (26)同(14),第731页。 (27)[法]德勒兹《电影2:时间—影像》,谢强、蔡若明、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28)[美]罗伯特·斯坦《电影理论解读》,陈儒修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441-442页。 (29)[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1961),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373页。 (30)[日]浅召圭司《电影学》。此书未有中译本出版。国内一位曾经访学日本的学者译出此书,但未出版和发表。此处引自手稿。 (31)[法]麦茨《电影语言:电影符号学导论》,刘森尧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04-106页。 (32)[美]大卫·鲍德韦尔、诺埃尔·卡罗尔主编《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麦永雄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3)见拙作《我看“文化就是力量”说的依据》,《现代传播》1996年第3期。其中狄德罗的观点,见《狄德罗哲学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4页。 (34)王志敏、赵斌主编《电影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5)见[美]大卫·查莫斯《为什么在哲学中没有更大的进步》,王佳鑫、李大强译,《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1期。 (36)同(12),第58-62页。 (37)同①,第7页。 (38)同①,第8、11页。标签:电影学论文; 电影语言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电影理论论文; 文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神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