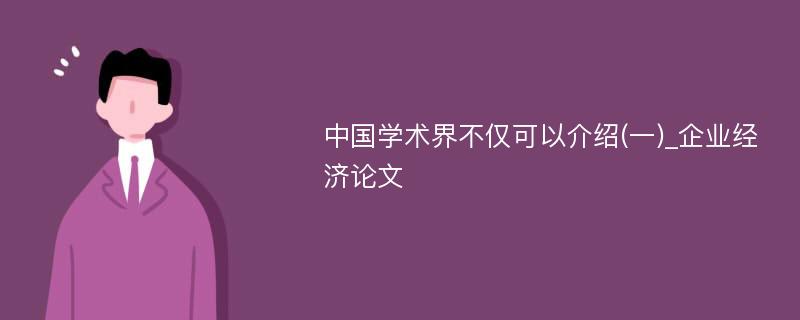
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7月5—6日在上海复旦召开的追思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主办方原定这是一个闭门会,不对外宣传,邀请经济学界的朋友坐下来一两天,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我认为这个倡议十分必要,就欣然应约前往,并根据即将发表于国外《经济政策改革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上的《反思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一文的内容,准备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的发言。主办方后来邀请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对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详细报道,我想这也是好事,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确实值得社会各界关注。 按会议安排,由黄有光、我和张维迎三位先做了主旨发言,发言完后进行相互评论。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溯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解释,并根据这种解释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供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作为决策的参考。每个学者的研究其实都是“瞎子摸象”,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有异,提出的解释和建议不同在所难免,学者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径。不过,争论要成为建设性的,而不仅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的口舌之争,则应该双方对争论对方的观点和逻辑有准确的把握,从内部逻辑的自洽和逻辑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来给予对方的观点进行评论。这次在复旦的会上由于时间的限制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事后的媒体报道中也未准确反映争论双方的逻辑、观点和实证经验的证据,许多评论就像有位媒体主编指出的“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具体可参见FT中文网徐瑾专栏《张维迎林毅夫在争论什么?》)。 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达到会议主办方原先所设想的“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想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二十年前的国企改革、十二年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 一、国企改革的争论 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我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于奏效,尤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我同时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如果是垄断,大型的民营企业也无法解决效率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此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中小型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大型的企业,则不管国有或民营,如果经营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至破产。在复旦的讨论会上,对我主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时,维迎据此认为我主张把大型企业都国有化,显然是一个误解。 维迎和我的观点就内部逻辑来说都是自洽的。从实践来讲,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中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基本都已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有不少还成为上市公司。到现在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并且,由于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装备、汽车等产业在中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因此,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建议应该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以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和市场垄断的方式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暗补,放开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在市场上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资本技术极端密集,仍然违反中国比较优势的国企,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补贴。 维迎的观点则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中得到实践,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按现代企业理论的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许多低价甩卖国有资产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的情形外,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20年前我和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目前从国家拿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期多而不是少了,效率是低了而不是高了。并且,就经济总体表现情形,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则都是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小凯是我在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之初就认识的朋友,自那时以后直至2004年他不幸病故,我们保持了20年深厚的友谊,他对推广以超边际分析来把斯密的分工理论模型化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思索所做的努力都是我所尊敬的。本着同样对中国学术发展和现代化的关心,我一向秉持2004年他病逝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悼念会上所说的“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精神,有不同的观点,就直接提出来和他切磋。 2002年12月,小凯在天则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在杨小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胡永泰2000年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他则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在改革后20多年经济发展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国虽然当时看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和小凯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先推行共和宪政,等宪政建立起来以后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不去模仿发达国家优秀制度的“后发劣势”的观点不同,我从1994年和蔡昉、李周一起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以来,就一直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固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对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做出改革,但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 我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我同时认为:由于过去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型中国家有许多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来改革,一方面保留些扭曲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一方面放开原来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经济转型期才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创造条件改革各种制度扭曲,最终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 在复旦的会上和其后的媒体报道中对我和小凯的争论有两个误读:1.认为我强调后发优势,所以,我主张只要发展经济不需要进行制度改革;2.中国现在出现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证明了小凯所主张的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 任何人只要细读我200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和从《中国的奇迹》以及以后出版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中国经济专题》、《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一系列著作和论述中,都可以了解我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把我的主张简化为不需制度改革是严重误解。 其次,中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就是因为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的结果?是否就证明了“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未必!原因是根据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发现,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一次性的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中国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同样存在,而且,和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些现象的产生不在于中国没有按“后发劣势”的观点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 在《中国的奇迹》和《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中,我分析、预测到,由于中国推行了双轨渐进改革,为了给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以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或是市场垄断的方式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那么就会创造制度租金,就会有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双轨制改革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前苏联、东欧国家,虽然,进行了“共和宪政”的改革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或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防安全和国家现代化所需不愿让其破产,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结果,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就比中国还严重。所以,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共和宪政改革,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我和小凯的核心争论其实是在于:1.共和宪政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2.是否应该采取休克疗法把各种制度扭曲都一次性消除掉,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后发劣势”,还是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边发展经济边改革完善制度? 对于前者,小凯和杰弗里·萨克斯等合作者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为了推行共和宪政,小凯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他也把日本在1990年代出现的金融危机作为是日本没有推行英美共和宪政的结果,但是,美国在2008年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同时,欧洲有许多国家没有采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政府清廉等高于英美,亚洲国家中唯一收入水平高于美国的新加坡也没有采行英美共和宪政体制。和中国同样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印度虽然有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绩效一直低于中国。而且,《国富论》中斯密记载了英国在18世纪时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哈佛大学Glaeser and Saks教授的研究也发现19、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普遍化的程度不比中国现在低。这些事实证明,小凯认为英美共和宪政是最优制度安排的看法只是理想条件下的臆想,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二点,小凯主张在转型过程中先难后易,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建设完理想的制度体制再来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否是这么样?现在回头来看,前苏联东欧的国家不仅没有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如前所述,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研究一再发现出现于中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中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休克疗法”最力,和小凯一起发表引发我与其商榷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杰弗里·萨克斯的观点显然是变了。今年3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接受了经济学家李稻葵的访谈,在访谈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的成绩,认为“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对于中国当前的挑战他则认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他则高度评价中国的减贫成绩,大力向非洲推荐中国的发展经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