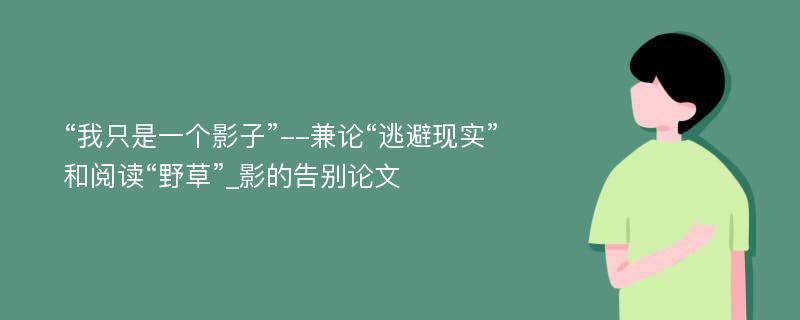
“我不过一个影”——兼论“避实就虚”读《野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避实就虚论文,野草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拙著《鲁迅的生命哲学》最后一章论《野草》,其中当然涉及《影的告别》。但以几百个字来“例解”一篇被不少学者视为“最难读”的名作,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专文申论之念很久,一拖至今。
认识鲁迅的精神特质,《影的告别》极具个案性。虽然,它与《过客》、《墓碣文》、《死火》等名篇一样,读者可借以直观其人,但是,倘要寻找鲁迅与中外各种精神遗产的复杂关联,《影的告别》要比诸篇更具可辨识性。
一
孙玉石先生曾经用“象征”说为《野草》研究打开一个缺口,尔后不断有人撕出更大的口子,但终敌不过无形的修复力。这与政治原因没有多大关系。正如诗学研究的一般情况一样,政治原因退场,社会学化① 却是一个尾大不掉的习惯。笔者曾尝试以“听梦”的姿势读《野草》,王吉鹏先生就此评论道:“在沿着哲学玄思,存在本体论的道路上一路飚扬的同时,研究者也过于‘避实就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野草》文本本身,而沉湎于哲学思考的高蹈境界,这又是一种矫枉过正。”②
笔者特别看好“避实就虚”这个用语。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中肯的概括:质疑“坐实”而“听梦”,这还不是“避实就虚”?
不过我同时要指出的是,“避实就虚”不是我的刻意为之,而首先是鲁迅本人的写作姿势。
根据有二:其一,鲁迅说野草是他的哲学。哲学就是形上,形上就是“虚”,就是“玄思”,这些词有时可以互训互换。其二,《野草》最诗化的几篇,多是“我梦见”,而梦就是“虚”而不是“实”。
也就是说,“虚”是“《野草》文本本身”的实情。如果这一点没有太大疑问,那么“听梦”就不是绕道走的“避实就虚”,而恰恰是直面文本的“如实”听来。因此我至今认为这是《野草》的一种读法。这里旧话重提,与其说是为旧作辩护,不如说是借此向读者交代本文的立论角度。这实出于不得已,因为《影的告别》是更典型的“避实就虚”,除了写作动机等知识性考据,我们无法将文本本身实证化和社会学化。③
比如劈头一句就是那样的谬悠不实: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谁能用逻辑界定,或者用经验性语言指明“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想无人可以做到。这是因为“不知道时候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实然判断的物理时刻(或社会学时间)。
“知道时候的时候”一定是在日常认知状态中。人在这个时候,大概是不会有形而上学的哲学沉思的,也是不会有诗的。“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姑称“超时候”。“超时候”将“时候”悬置,“超时候”说话,只能是超验语态。也就是说,《影的告别》之所诉,不是某种时刻的认知判断和心理现象,所以不能将其仅仅读作鲁迅某个阶段的“苦闷”、“灰暗”,而后来“克服了”的过去时。虽然某种机缘性偶在体验的确是作者的写作契机。
《影的告别》为什么难读?与其说是作者的晦涩造成,不如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学眼光遮蔽了读者。④ 它造成了一种大同小异的解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于是很难看到或想到:“影”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原型,是中西文化史上都曾有的一种形上隐喻,是东方与西方诗哲们都曾不约而同用过的一个经典寓象。虽然下面将证明,《影的告别》与一些历史之“影”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联,但我宁可强调,鲁迅写作时是否想到这些经典,是否有意为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之影与彼之影存在一种互文关系。一种原型无数次地被记忆和生成,不过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正如历史上难以计数的咏影之作和有关神话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类有同样的人生之谜。⑤
如果我们对所熟悉的认识图式稍加搁置,由此及彼地打开思路,应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可是习惯老是牵着鼻子走,于是一些简单的联想也成了不可能。
比如论者很难由此联想到老生常谈的柏拉图之“模仿”论。柏氏的学说被概括为理式论(通译理念论),其实理式论也可以叫模仿论、影子论。从另一个方向命名罢了。这个学说认为,不可见的理式世界才是真实的,可见的感官现象不过是这理式世界的影子。这样,肉身之人也不过是人的理式的一个模仿。模仿的名词化就是指人的理式派生出的影子。中国高校的文学理论课通常会批判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两层模仿即“模仿的模仿”理论,“模仿的模仿”其实也就是“影子的影子”。
又比如我们更难联想到《圣经》文化。
“影”在《圣经》中是与“光”相连的,可见“影”在《圣经》中是怎样一个重要的隐喻。根据《圣经》的说法,上帝是“真光”⑥,“真光”照亮世界,或者说万物反射或分有上帝的光,所以上帝是“众光之父”。这里的光绝不是物理世界的可见光,它是纯粹的,不可改变的:“众光之父……,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⑦ 上帝的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则是住在人间的真光,是“世上的光”⑧。那么人是什么呢?人是上帝的造物,人有上帝的赋予,尤其是人有灵魂,所以人虽然不是光,但也不是黑暗,人不过是上帝的影,所以《圣经》也以影喻人。比如:“耶和华阿!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⑨
《创世纪》讲上帝以言(word)造人,人就是上帝按自己的样子所造,所以人是上帝的相似物、影子。而在基督教历史上,柏拉图的理式论(模仿说)则通过新柏拉图主义神学影响到圣经文化的形成与传播。直到今天,这一传统朗然可辨。几千年的西方文化,正是在“理式—影子”说的土壤上发育生长出来的。
这一切难道与《影的告别》有什么关系吗?有的。探寻鲁迅的精神世界不能离开他所钟情过的“新神思宗”,尤其不能离开重估一切的尼采主义。而尼采主义不过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动,或者说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尼采要把两个世界的秩序给颠倒过来。在他那里,被柏拉图贬为影子的第二性的感性世界,是至上的,而那个被称为真实的理式世界却成了欺骗和幻影。他不承认理性主义的那个超感性的“物自体”。他要解放感性,并以神圣的认定。这种感性解放论可以看成尼采版的“影的告别”。他的所谓“重估一切”的价值翻转,可以看成“影子”对“理念人”和“上帝”的审判。
“苏鲁支如是说”究竟在“说”什么呢?其实就是告别,告别两千多年的那“真实的世界”:“真理”与“真光”的世界。宣布不再信任那些“侈谈超大地的希望的人”。
所以我们不妨把《苏鲁支语录》(或《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作影子的告别。《前言》开篇即预示出来了:苏鲁支“隐入山林”后,“独自怡悦心神,玩味寂寞,十年间未尝疲倦”,有一天突有所悟,在日光到来之前,向着太阳如是说:“伟大的星球!倘若不有为你所照耀之物,你的幸福何有?”于是改变了心意,下山布道,开始“降至深渊”。这就是告别,用今人言,即是向本质主义告别。因为本质离开了存在,一无所有。本质主义的上帝已死,老圣者似的“编制歌曲,自唱”、“颂赞上帝”或“在熊中为熊,在鸟中为鸟”,已经不可能和无意义。老圣者安于旧梦,是因为“在他的树林中还没有听到上帝已死”。上帝死了,而人生是不能没有神圣支撑的,所以苏鲁支不能听从老圣者的劝告留下,而是请“让我快离开”。他来到人间,教人以“超人道理”。这个道理与“死之说教”不同,它不“蔑视肉体”,而是给肉体以意义;超人不是“超地球的希望”,而是“给大地守忠实”,是“大地的意义”⑩。可见,《影的告别》与《苏鲁支语录》存在着同一取向的“互文本”关系。这是两个狂人站在各自的大地上,向各自传统的告别(11)。
那么我们再检视东方尤其是中土的“影”。
释读《影的告别》而疏忽本土古已有之的影子论,也是出于上述的眼障。如果不是从词典意义上看,不妨说,成语“形影不离”就是中国传统的影子论。“不离”或“不二”正是其精义。一者是形影“不离”,一者是影向形“告别”,即便从这两个词的对比中,也不难感到“影的告别”与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的张力关系。
经验语态中的“形”与“影”都是可视现象,形影之喻不过是一个通常的修辞。但在形上语境中,二者却是哲学、宗教的隐喻。道家和佛家经典中的“形”实指形骸,更喻指本体。后者相当于西方的“理式”,而“形”所生之“影”,则喻指本体所现之“象”。“影”在中国,其源头至少可推到《易》之“象”。为了不至把话题扯得太远,本文姑且把最早的“影子说”定于《庄子》。并且可以肯定地说,《影的告别》与庄子的影子论存在着因果关系:文中的“形”、“影”、“彷徨”、“随”、“走”等语词就脱于《庄子》的相关寓言和道论,而其取向,则是着意地反其“道”而行之(12)。这种着意,在鲁迅是一贯的,不独本篇为然。
鲁迅曾经在比较中这样表述过庄子的“一”:“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基‘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13) 老子虽然也倡合一,却同时讲对待;庄子可谓说“一”不二的绝对主义者。他的道论洋洋洒洒,其法式不过是“齐一”。庄子论道,寓言之多十之有九,其中之一,就有影子(景)的寓言。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14)
这个故事正是出于《齐物论》,影的态度即是形影不离:影本无所待,不要讲什么特操,不要分辨什么身体与影子。这个寓言之后接着就是著名的庄周梦蝴蝶,都是一个意思:齐一。
“影”与“形”达于合一之随了,也就是达生死,达逍遥。至人之行就是这样的:“子独不闻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现象状态的“影”只要“颂论形躯”便能“合乎大同”(15)。人只要“随”、“顺”,就能进入至人、真人的化境,否则就灾祸临头了。在庄子看来,孔子灾难之多就在他不知道人与影相随的道理,偏要“疾走不休,绝力而死”(16),《庄子》全书结尾所慨乎言之的,正是形影竞走:“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17)
在鲁迅看来,这种“齐一”、“无己”、“无心”、“刳心”、无“特操”的随顺是不可以的,因为活生生的现象之我被勾销,无异于“死之说教”。他宁可不要这样的“大同”、“大顺”。于是,影偏要与形告别:“你就是我不乐意的”,“我不想跟随你”。文章开始便是一连串的“我不”,其价值标准不是任何别的什么,而是我“乐意”。一切“有我所不乐意的”,我都“不愿去”。
庄子思考人的终极价值并没有错,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出色的一页。将人的终极本质实体化,从而求之若鹜,应该说这并不是庄子的精义所在,甚至是他所反对的。但是曲解也罢,末流化也罢,庄子因此成了“不谴是非”、“不辨生死”的道之祖师。鲁迅终生非周,也正在于这一层。在他看来,实体化地“悬设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18),是将“普遍”、“永久”、“完全”化为“棺材钉”,把人钉死。影向形(或“我”向“你”)所说的话,可以理解为活生生的感性之我向虚无的本质之我讨还存在理由,理解为精神的自我审判。
这种审判是一个自我的精神事件,同时也体现“我”与“他”(某种文化或某种生活态度)的批判关系。关于后一层,鲁迅还有不少篇章可以比照。
比如他发表于1918年的短诗《人与时》:“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19)
又比如稍后于《影的告别》的《杂感》:“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20)
顺便指出下面很容易搞混的两点似有必要。
其一,前面讲到的“超时候”,指的是一种思维向度,不是说人可以不在时间中。《苏鲁支语录》与《影的告别》一个共同的吊诡,是用一种超验的诗化语言为地上的意义辩护。其二,地上的意义不等于经验生活价值,不等于18世纪的感官主义。“感性解放”、“肉体”这些词容易给人错觉。他们强调现在时,用以打击的是抽象的本质主义和枯槁之道,而强调人的选择对本质的赋予,他们并没有忘情于天上,于是有超时之玄思。
二
影子是一个集合性具物。其微妙之处在于其不明不暗,亦明亦暗,就像一张黑白照片。照片被称为影,实为精当。影只能是光明与黑暗的中间状态(或中间物)。可能由于这奇妙的特点,尤其是影与人之间的一种最切己最难解的神秘关系,它成了人类理解自身的一个古老原型。原型不只是修辞学中说到的意象,所以不要只是在修辞学和社会学里打转,将影、形确指为某种象征。用荣格的理论说,原型是人类无数典型经验的“形式化”。他正确地指出:“原型这个词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形式”(21)。古往今来的各种影子说,常常是借此对人的本质作出的一种诠释,或者对人的生存状态发出的一种咏叹。
我们今天也不得不为这个原型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从科学上解释“光”、“物”、“影”的关系似乎已是常识,现代人大概不会像先民那样,把影子当作自己的灵魂来尊崇,也不会再有关于影子的禁忌。但科学无法让这个原型解魅,因为原型“形式化”了人的生存秘密,而生存秘密是认知理性无法进入的。这个原型的黑白二重性最能给人这样的启示:人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是灵与肉、圣与凡、无限与有限、空与色的交织物,影之谜不过是人之谜。影的两难处境就是人在生存论上的两难处境,就是人的定义,人的宿命。人生在世上不能不背负这个十字架,不能不在这两难处境中作出选择。这就是无数中外诗哲吟影、论影的原因。当然,这也是《影的告别》的原因。
“我不过一个影”,是鲁迅对人的本质的诠释,也是自我觉解。在这句之后一连几个“然而”,活画出的正是人的生存窘境与无奈:
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
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
不管这中间物愿意与否,都处于这种两难状态,拒绝任一方都会归于无,所以只能“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无人可以在这窘境之外,鲁迅异于常人,首先在于他有了这份觉解。
鲁迅以影释人,与中国玄学(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庄子与魏晋)有关,显然同时结胎于佛学。“影”在佛学中喻指从实体生但无实性的缘生之事物,或一切法相,当然包括众生相,包括人:“是身如影,从业缘生。”(22)“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23) 感慨释迦牟尼真是大哲的鲁迅当然明了,人因缘而生因缘而灭,人不过是因缘而合的假相,没有实相。众相无相,无地可栖,说到底人不过是“彷徨于无地”的“影”。不只是《影》,整本《野草》,都依稀可辨他对于这种智慧的承纳。
然而,如果只是承纳,也就不会有《野草》,不会有《影的告别》,他在北京营造的那个四合院,也就不过是一个“随园”或者“勿我斋”。在中国历史上,觉解到人生窘境的文化人,当然不只鲁迅。庄子之后,以文学家而论,最值一提的影子说(当然是由本文的论域来判定),不是李白、张先、马致远“花弄影”之类的人生感叹,而是陶渊明《形影神》诗三章:《形赠影》、《影答形》、《神释》。
前两首形与影一赠一答,说的就是人的二元冲突和苦恼。陶潜对付两难或窘境的方式正是老庄的自然大化之神。《神释》是这样说的:“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24) 同时值得一说的还有苏轼对陶的和诗三首。苏轼对形影之苦的描述和处理方式不同于陶潜之处,在于引禅入思。《和陶神释》云:“二子本无我,其初因物著。岂惟老变衰,念念不如故。”“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25) 在中国历史上,围绕着这样一种原型,还有很多的论说与歌唱,虽然千姿百态,其共同点都难逃“齐一”或“不二”。佛家与道家的形影论同样深刻,其解脱法虽然有别,但无我、无执,本体合一的基本套路则无大异。佛的究竟法门就是“不二法门”,所以佛学也讲“随”,随就是无执。
鲁迅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只是随之静之,忘之安之,也不只是“呜乎呜乎”,酹哭于江月。与无数中国诗文一样,《影的告别》也没有离开一个“酒”字,但不是以之浇愁解忧或遁入梦乡,而是“装作喝干一杯酒”独自远行,并且是向着黑暗,向着沉没:
“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鲁迅认可佛学之智,却在人生选择上另趣一途,这也是一例值得小心分辨和研究的个案。与对道家(尤其是流俗化后)“不谴是非”的“物化”哲学一样,他也不屑于“居士”、“信徒”之流“美其名曰大乘”的无特操。他“不乐意”通过“不二”的随缘以求解脱。即便是泡影,也宁可作一种毁灭性挣扎,在朽腐中“大欢喜”。与其同形偕行,不如“独自远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焚身以死,以绝望之“行”来见证人生。《过客》、《死火》、《墓碣文》等篇章都是这样的自白。
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思想类型。同是由有限而无限,道家通过“齐物”之玄门而逍遥,佛家通过“不二”之法门而解脱,鲁迅却是通过“分”——“告别”、“独自远行”、“沉没”——来亲证大自在。
“分”是合一的反动,反动意味着过客之“走”,意味着本质的“生成”。这就是《野草》从而也是《影的告别》有别于中国传统的隐微所在。对鲁迅来说,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反动不只是精神的“告别”、“独自远行”,甚至不止于尼采式的精神价值翻转,它同时是一种生活践行,这种践行意味着不恤弄脏自己,以“战士”的身份介入当下不无血污的历史,把自己烧在里边。
影向黑暗而沉没,不是走入没落的虚无,不是无可奈何的完结。《影的告别》通过一连串的“不”,虚无化了各种文明价值,但不因此就是无所肯定的“虚无主义”。正如海德格尔在批评一种流行意见时所说,“并非每一个思索虚无及其本质的人都是虚无主义者”(26),“虚无主义绝不只是一种堕落现象”,(27) 毋宁说,“影”这种虚无化正是反虚无,因为在这种虚无化中,一种新的肯定诞生了:“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这也便是尼采在“精神之三变”中所谓“失掉世界者要复得他自己的世界”(28)。这是一种“神圣的肯定”。
三
在自我毁灭中自我肯定,绝对的生命在此生或当下之行中绽放、无限回环,也是《野草》全书的悲剧美学:“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29)
“野草”、“过客”、“死火”是与“影”一样的中间物。这种中间物首先是生存论的而不是历史论的。与“根本不深,花叶不美”但终“无可朽腐”的野草一样,“影”的卑微与其伟大都在于它是一个中间物。它是卑微的,进退维谷,无论怎么选择都是危险的,正像系于两间的软索。然而它的伟大也在于此,这伟大不在于它能够致达永恒,而在于它用自己的“走”,生成化了永恒,于是在被黑暗沉没时它可以如此自信与昂扬地宣布:“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所谓“申论”,就此为止吧。最后,我想到“前后呼应”作文法,禁不住重提开首说到的问题:如果不“避实就虚”进入形上语境,这末尾的一句话也是不可解的死结。既是“沉没”,怎么又是“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推及《野草·题辞》,既然“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何又“无可朽腐”?“死亡而腐朽”却“坦然,欣然”是不是无可奈何与自欺?用“死而未悔”、“乐观主义”之类来解释也许不算太离谱,只是这样一来,《野草》就大失其旨,甚至不成其为《野草》。
注释:
① 文学、哲学等人文领域中的泛社会科学倾向,其突出的特点是思维模式的经验性和实用性。
② 王吉鹏等:《穿越伟大灵魂的隧道——鲁迅〈野草〉〈朝花夕拾〉研究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28页。
③ 即便能如此,这对一篇艺术作品的鉴赏也不重要。用形式主义理论看来,或许是有害的。
④ 这当然与传统的思维类型有关,但本文宁愿强调现代思维机制。
⑤ 生存体验与认知学不一样,一个人可以在不具备前人知识的条件下,与之进行生存论对话。反过来说,古人在知识学上也许无法与今人交流,但完全可能有相通于“后现代”的人生命题。
⑥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1:9)
⑦ 《雅各书》1:17,又见《诗篇》144:4。
⑧ 《约翰福音》8:12。耶稣也对信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14~16)
⑨ 《诗篇》144:3~4。
⑩ 参见《苏鲁支语录》前言一、二节,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1) 这种告别不管在言辞上如何激烈,都应该理解为对传统起死回生的改造而非勾销。
(12) 当然道家之道未必不可以生出另一种解释,所以鲁迅之行与老子之道在取向上并非无可通之处。这一思路也适于理解鲁迅与佛学的复杂关系。拙著《鲁迅的生命哲学》第二章有所论述,本文不涉及这一层。
(13) 《汉文学史纲要·老庄》,《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卷,第366页。
(14) 《庄子·齐物论》,又见《庄子·寓言》。
(15) 《庄子·在宥》。
(16) 《庄子·渔父》。
(17) 《庄子·天下》。这里说的是形与影竞走,似不必拘于字句。其要义在于齐一。
(18) 《“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卷,第428页。
(19) 《人与时》,《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卷,第33页。
(20) 《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49页。
(21) 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
(22) 《维摩诘经·方便品》。
(23) 《金刚经》。
(24) 《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65页。
(25) 《苏轼诗集合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056~2057页。
(26)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27) 同上,第229页。
(28) 《苏鲁支语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页。
(29) 《野草·题辞》,《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