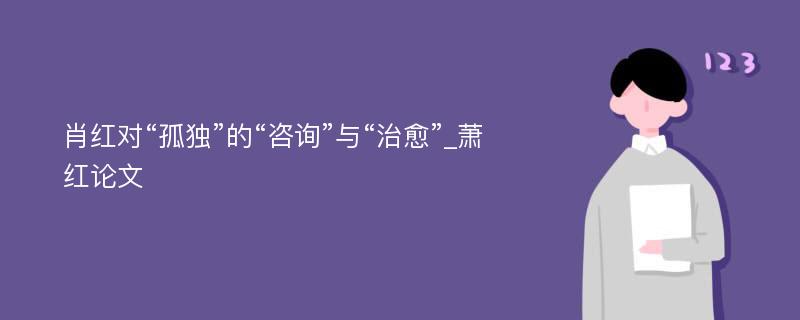
萧红“寂寞”的“问诊”和“疗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疗伤论文,寂寞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4)06-0172-08 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对萧红的身世和心境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种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① 我们读萧红的作品,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寂寞”的痛楚。茅盾从寂寞的角度透视萧红的创作,可谓“善解人意”;但萧红的寂寞到底从何而来?其“屡次幻灭”和“生活的苦酒”有多少成分是与她的个性和创作倾向有关的?对此茅盾并没有深究。按照茅盾的理解,萧红的“幻灭”和“苦闷”与她的个人生活道路选择有关,当“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的情况下,“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②在茅盾看来,萧红太局限于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了,如果她能把自己的生活与当时香港的“大环境”联系在一起,可能就不至于那么寂寞。然而,在我看来,事实可能并不这样简单,就萧红的个性和创作倾向而论,茅盾所谓的香港“大环境”,在萧红看来可能倒是一个“小环境”,她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远比这要“阔大”得多,虽然有时它以自身的情感样态呈现,但其意向所指却不是“香港”一时一地所能包容的,甚至也不是当时“中国问题”所能包容的。萧红在一篇文艺时评中曾认为,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屠格涅夫和罗曼罗兰为代表的,他们是“幽美的,宁静的”,“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与此相对应还有一种作家,“他们则不同,他们暴乱、邪狂、破碎,他们是先从本能出发——或者一切从本能出发——而后走到灵魂。”萧红钦佩和赞赏前一种类型的作家,认为优秀作家最终都要走向“灵魂”,③萧红“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她的个人生活境域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她创作时的一种“本能”,她的创作出发点是“灵魂”,而一旦涉及“灵魂”,几乎所有问题都可能要超出个人生活境域。正如曹禺所说,当作家进入到某一创作境界时,“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④不幸的是,萧红恰恰就跌落到了这口“宇宙”的井里,无论她怎样挣扎都难免不幻灭、不苦涩、不寂寞。 那么,萧红的“宇宙”到底什么样?它又如何与“寂寞”发生了关联呢?我们知道,萧红出生在一个境域相对优越的家庭,不论是蹲在马车上的调皮,还是在后花园摘花捕蝶,⑤在那个年代,有这种经历的儿童,都不是一般人家子弟,更不要说能到有暖气、铺着地板的摩登城市,上“第一女子中学”了——那里唯一出身于小康之家的孩子还会被人取笑。⑥《小城三月》里的翠姨是怎样羡慕“我”和其他一帮能在城市学堂里读书的年轻人的?她还不是为了这样一种希冀而抑郁成病、悄然离开了人世吗?从中可以反证“我”的生活真相到底什么样。一般人们都能记得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寂寞到只有一个老爷爷陪伴和千篇一律的后花园值得留恋;不要忘了,这些都是萧红成年以后的记忆性书写,也就是说它是萧红写这些作品时的“灵魂”反映,不是萧红幼年、少年生活的“实况直播”。萧红是从“灵魂”出发的作者,她的笔触时时都在超越“本能”,她所写的一切都与“临场发挥”的境遇相关——如果她后来幸福,童年也会跟着沾上一些喜气,如果后来痛苦,连带着童年也掉进了“井里”。萧红后来生活怎样呢?与家庭决裂、成为了无依无靠的“哈漂一族”,⑦原来的洋学生、阔小姐,一下子“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⑧。连“火也点不着,饭也烧不熟”,这个时候“我”才“向着窗子,心很酸,脚也冻得很痛,打算哭了。”可是眼泪还无法流出来,“因为已经不是娇子,哭什么?”⑨看到别人家的“女儿看电影,戴耳环,我家呢?”⑩“无家”的感觉与她曾经的小姐回忆相关,与失去看电影、戴耳环的条件、“已经不是娇子”的生活境域相关,被家庭放逐的结果,连带着把自己的童年也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童年的天地才变得狭窄了,否则也根本谈不上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更不要说小小年纪会感知到什么寂寞。 过去家庭生活优越、现在落寞,只是萧红与寂寞结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遭际和转变是萧红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萧红选择了一个“连有钱的丈夫都不愿嫁”的无家生活?(11)“陈义太高”是最贴切的解释。(12)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创作经验,萧红认为不论是“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就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3)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萧红的代表性作品关注的主要视点都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不应该”。“呼兰河这地方……到底太闭塞”,(14)“除了染缸房子在某年某月某日死了一个人外,其余的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动了一点。”(15)这里的人们“要吃的吃不到嘴,要穿的穿不上身”,可是他们“为什么活着,活得那么起劲!”(16)“是谁让人如此,把人生下来,并不给他一条路子,就不管他了。”(17)在别人都以为天经地义的行为中,她发现了诸多的不合理,家里人不让她读书,她软磨硬泡,非要上学不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不听,不顾一切地私奔了、自由恋爱……如果这些行为延后50年发生会怎样?现代青年女子哪一个不读书、哪一个不自由恋爱?可问题是这些都在1930年代的北方边陲小镇“呼兰河”发生了,这里和“现代”隔得很远、又很近——也就是说,有人隔得很远,有人隔得很近。只有极少数人如萧红者,提前告别了那个时代,从而留下了一段巨大的时空落差,它是为最先告别这个时代的人预备下的“一口残酷的井”,只要“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伤逝》是唱给最先走向光明者、自愿牺牲者的一首挽歌,萧红用自己的经历和创作再次奏响了同样的音符——子君所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萧红都遇到了,先是坚定地离家出走、自由恋爱;进而遇到生计问题、遭遇寒冷饥饿和别人的冷眼;最沉痛的打击还来自那个给自己带来希望和光明的化身的离去——“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这样一来,像曾经勇敢的子君一样,她变得孤立无助、谨小慎微起来:“近来时时想要哭了,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跑到厨房里去哭,怕是邻居看到;在街头哭,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18)这与子君最终去了一个连墓碑都没有的所在,其寂寞程度不是太相似了吗?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域环境里,想要“从灵魂出发”或“达到灵魂的所在”,多少都会有些“曲高和寡”的味道。 寂寞总与离群索居、特立独行有一些联系,茅盾也主要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萧红情感的。“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意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19)我们要指出的是,茅盾认定萧红与“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都有些不同,却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话题。如果说“劳苦大众”的生活,作为“知识分子”的萧红与其有些隔膜,应该不难理解;但对同样是“知识分子”的各种活动,也觉得是“扯淡”、“是无聊”,这对理解萧红的情感,认识萧红的寂寞,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萧红的个人生活而言,这样的处境称不上是好兆头,但对她的创作来讲,却大有裨益,“陈义太高”不容易“被人别人理解”,却绝对有利于“理解别人”,当然也就同时有利于理解自己。当萧红以这样的姿态从事创作时,既把自己融入到了她所描写的对象中,又让自己超脱于她所描写的对象之外,“问诊”人生是其创作的一大特色。 如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初期,在“为人生”的文学旗帜下,曾集聚了一批“问题小说”作者。一般人们认为,所谓“问题小说”就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20)这多少限制了他们的创作向更深广领域发展,30年代以后,这种过强社会参与意识的创作倾向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换句话说,作者的身份是“医生”还是“患者”?当然这两种因素在所谓的“问题小说”里都可能存在,但总体说,不管“问题小说”的作者怎样坚持“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从中还是流露出了自诩为江湖郎中的意向,他们潜意识是以社会医生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的。萧红的创作也有“问诊”社会的倾向,比如她写小团圆媳妇、写冯歪嘴子、写有二伯等等,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成为她作品的主要关注对象,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她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向。可是在我们获得这种认识的同时,还必须指出,这只是萧红创作的一个方面,而且是被人们谈得比较多的方面。与此相关,萧红创作还有一个方面,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方面,那就是她对自己人生困惑的描写——她自己意识不到,却在“灵魂”深处决定着她创作意识和描写对象的取舍。一般说来,萧红的创作素材有两类,一类是她童年、少年的生活记忆,一类是她自己现实生活的“写真”,往往是童年、少年的生活记忆从“我”的现实情感出发,我们上文分析过的萧红童年、少年的所谓“寂寞”就是例证;当她写自己现实生活的时候,更是处处流露着此时此地“我”的现场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红的作品常常在“问诊”社会,更时时在“问诊”自己。她的感觉、她的“灵魂”、她的自我体验,是她写作的第一出发点,这给她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个性化印记。寂寞的痛苦时时在折磨着她,无可名状,就像人在患病时的感觉一样,不舒服、不顺畅。萧红的创作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类似于“病”的感觉的书写,就像病人在谈自己的感受,目的是为了寻求解脱的方式和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萧红的创作倾向隐喻为“问诊”。 如果我们同意用“问诊”的比喻来看待萧红创作倾向的话,那么关于什么是萧红的“病”,人们却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一般人们意向中的所谓“病”,都与对病的诊断和医治相关,不知道病因的病没法医治,弄清楚了病因同时也就意味着有了可治和怎样治的下一步打算。这样一来,当人们把文学创作倾向与对“病”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时,其实已经告诉人们,描写对象是否“成病”,与观察者的意识相关。比如三从四德、女子贞洁等等观念,在祥林嫂们看来天经地义,是正常社会秩序的反映;可在“新青年”眼里,她却已病入膏肓。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对“社会病”的认识又不这样简单:一方面,在成病和不成病的意识之间,往往存在一些模糊的中间地带——意识本身的模糊和意识嬗变过程中的模糊二位一体;另一方面,上帝在造人时也留有缺陷,这种缺陷有时是无法克服和避免的,一旦人们意识到了这样的缺陷存在,那也就同时意味着要把自己抛向“宇宙的井里”,“病的感觉”和“病的意识”将如影随形。《庄子·列御寇》认为:“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其中“智者”就是一个患上了“灵魂”忧郁症的人。由于萧红“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因此萧红也是一个“智者”、一个“忧者”,同时也是一个“灵魂病”的患者。 上文我们谈过,萧红早年生活在一个相对有钱的人家,后来由于她自己的选择才“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在她走上创作道路的最初几年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自由是她的选择,贫困却不是她所需要的,当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时,虽然当她选择了前者就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后者,可当后者袭来时,她还是没有做好更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读萧红的作品,常常能从中发现和体会到一些“凤凰落配不如鸡”的感慨。比如我们前文已经举例谈过的,看到别人家的“女儿看电影,戴耳环”,抒情主人公便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家”,(21)在这样笔墨中,多少能让人感受到一些写作主体对曾经有过的那种身份和生活境遇的眷恋,同时也能体察到写作主体对自我现实处境的一种无奈。当“我”再次来到曾经求学的所在: “女子中学”的门前,那是三年前在里边读书的学校。和三年前一样,楼窗,窗前的树;短板墙,墙外的马路,每块石砖我踏过它。墙里墙外的每棵树,尚存着我温馨的记忆;附近的家屋,唤起我往日的情绪。 我记不了这一切啊!管它是温馨的,是痛苦的,我记不了这一切啊!我在那楼上,正是我有青春的时候。(22) 这与徐志摩写《再别康桥》时的感受不同,“温馨”是“我”曾经有过的“青春”,就是自己当小姐、有身份、有“家屋”的时候。“痛苦”是“我”已经从那个行列里被排挤出来,像一个校役,像一个下等人,被人拒之门外。萧红从家出走的时候,生活确实困苦,但像她所遭遇的那种饥寒交迫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有意味的是在萧红的创作中,有关这方面题材的描写更多集中在她走上创作道路的最初几年,而在这样的题材写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也往往不是生存本身受到的威胁,而是生存质量不高。同样是住在“欧罗巴旅馆”里,别人花天酒地,我的桌子上却只有“黑‘列巴’和白盐”,(23)主人公的生活意愿是按照住“欧罗巴旅馆”的人的条件来制订的,结果当然大不如意。我把这称为是作家所患的“富贵病”。一般说来得这种病的人,都是原来生活境遇较好,或者是自认为应该较好的人,可实际处境又不是那么回事,在二者的反差中,心理失衡了。这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这种“反差”加剧了自己的心理紧张,放大了困苦;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反差,放大了困苦,也让他们获得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社会和观察自己的视角。德国学者波兰特在《文学与疾病》一文中认为,病人在患病时,一般都努力“向社会谋取他在健康时得不到的权利”,反过来社会也往往因为病人的患病而免除他“在正常的健康情况下作为社会一员必须履行的义务。”(24)这里谈的虽然是生理病人的情形,但其道理同样可以移用来说明心理上的“富贵病”,只不过患上了“富贵病”的作家,“在健康时得不到的权利”不是有意谋取,而是生活的馈赠;免除他“在正常的健康情况下作为社会一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也不被社会觉察,而被认定从来就应该如此。这样一来,患上“富贵病”的作家就获得了某种常人所不容易获得的创作冲动,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自己的要求有什么不应该,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和不舒服说出来,只希望得到令自己满意的回答和同情而已,而别人也在作家的特定写作氛围里自然而然地接受和理解了作家的需求。 “富贵病”只是在“富贵”问题上引发的“病”,当作家转移自己的视线去看待其他问题时,因为病因并没有解除,发病机理还在,往往也会因此而患上其他的病。与“富贵病”同时存在于萧红创作倾向中的还有一种“怀乡病”,她的创作在“问诊”“富贵”的同时,也在“问诊”乡愁。(25)正如萧红自己所说,“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因为她是一个被家庭放逐的人,家的意识疏远了,家乡的意识当然也就同样被疏远了。但一个人能够忘掉家的感觉和遗弃家乡的记忆吗?并不。我们前文已经分析过,当《他的上唇挂霜了》的抒情主人公看到别人家女儿幸福生活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曾经有的家庭温暖和家庭庇护;而《失眠之夜》的作者听别人说到家乡的景况时,“我也就心慌了!”(26)为什么看到别人生活幸福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家”?为什么听别人说到家乡时自己会“心慌”?向往而不肯正视而已,这其实已经有些接近于病态了。萧红清醒意识到自己是无家的人,因此家乡观念“不甚切”,因为“甚切”也没有太多意义;但家乡观念又是无法割舍的,两种情感绞缠在一起,沉积日久,无法释怀,这就是萧红创作怀乡病的病源。萧红小说创作的主要素材就是有关自己家乡“呼兰河”的书写,其实她很想家,因为她被家庭放逐得太久了。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祥林嫂见谁都问灵魂的有无是因为她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一样;萧红的创作也是如此,她作品中充斥着那么多关于故乡的描写是因为她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创伤,因此也比别人更能理解家乡的含义。《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等最能体现萧红创作特色的一类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抒情气息充填其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出自一个患有“怀乡病”的作者之手,别人没有那样的条件,没有那种“病入膏肓”的深切体验。 当然,作为女作家,最让萧红跳不出来的,病情感觉最沉重的还是“妇女病”。萧红生活沦落、被家庭放逐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自由恋爱;而作为一个女性,她的几乎所有遭遇又都与她的女性身份脱离不了干系。自由恋爱是通往天堂之旅还是下地狱的诱惑?萧红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犹豫,进入了一个自己不能解答的人生怪圈。我们读萧红的作品有一个疑惑:恋爱对萧红的人生道路选择具有某种决定意义,对其创作也发生了根本性影响,可是通读萧红的作品,直接描写恋爱的作品少之又少,她小说里的恋爱情节远没有她人生实际的恋爱过程丰富,这是为什么?正像萧红在“家”的问题上受到了伤害,把对家乡的情感人为地掩藏起来一样,萧红也受到了“爱”的伤害,恋爱的甜蜜也被她有意无意地“冷冻”了起来。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她自己的选择也似乎没有逃脱“始乱终弃”的命运。在萧红的自我体验中,恋爱中的人与动物仿佛没有什么区别,“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27)萧红对异性爱似乎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她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一般很少直接袒露恋爱的实际感受。其实,这不是真实景况。在萧红短暂生命的后期,她还在不时地惋惜着自己,“我不是少女了,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她把自己倾尽全部身心之“爱”的破裂归结为自己性炫耀的缺失,其恐惧是可想而知的。由此带来的打击让她联想到了自己曾经有的遭遇,“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28)作为女性抒情主体,她清醒意识到了在人生舞台上,女人是弱者,是受到父亲和丈夫虐待的人,在萧红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大都带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色彩,而她们的受苦受难,无一不与女人的那点可怜的情感需求相关。在《生死场》里,在《呼兰河传》中,女人生育所遭受的痛苦让人触目惊心,“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29)萧红为什么把女人的生育写得这么恐怖?我以为这多少与她在实际生活中缺少必要的“生育关怀”、生育条件过于苛刻有关。这些类似于女人性自戕的描写,是受到女性欲望怂恿和压抑的双重折磨反映。面对着女人的爱欲问题,萧红感到有些绝望:“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30)对待“敌人”有办法,对待“他”没办法。在这个问题上,萧红再次进入了“人生的病房”。她申诉、她无奈、她痛苦,她渴望得到解脱而不能。在患上了“妇女病”的萧红眼里,两性关系描写退去了瑰丽的色彩,剩下的只有苦涩和无奈——而这又正是她作品特别魅力之所在。 萧红创作的“问诊”倾向,是其遭遇挫伤而心理郁结的下意识反映,创作对她来说首先是一种精神慰藉和情感满足。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就指出,人们在生活中遭遇的各种损害,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等方面,它们本身就蕴藏着相应的“希望”,比如“身体强壮与安全、自由和尊严、幸福与充实”等等。(31)在现实中遭遇挫折的萧红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呼兰河传》的结尾处,她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32)这里所说的“充满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等等,表面上看好像似一种被动选择,其实它们是萧红情感舒张的主动出击。“问诊”是着眼于对萧红所患之“病”的认识,可当作者把自己的“患病”感觉倾诉出来,向公众倾诉和“问询”的时候,其实也相当于情感“疗伤”。 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实践中经常遇到因遭遇生活压抑而要求书写和倾诉的案例。当某疗养院医师受“患者”的委托,帮她把自己一生的不幸遭遇写成“自传”时,“患者”“显得格外激动,在其连声地道谢之中”,让人“充分体会到她那一生苦楚终于得以尽诉、心中为之豁然开朗的”的情形。推而广之,“凡……精神受压抑者,均有将其胸臆、心境加以抒发、释放之愿望。”(33)没有写作能力的人还想方设法找人捉刀代笔,有写作能力的人,如才女萧红者,自己写不比让别人代劳更能发挥“抒发”和“释放”的功效吗?我们已说过,萧红主要以写自我生活为中心来从事创作,现在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萧红在写自我生活题材作品时,一般不大关心使用什么文类。她的小说往往类似于散文,比如《两个青蛙》、《离去》、《渺茫中》、《太太与西瓜》、《汾河的圆月》等是证明;她的散文也往往类似于小说,比如《两个朋友》、《花狗》等就是这样。从总体倾向上看,她的前期创作文类意识互侵更明显,后期的创作文类区别意识似乎稍有加强。为什么会如此?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同样可以从萧红创作动机上来透视,因为当你把她看作是一个“病人”时,创作对她来说就不仅仅是写作,还是一种舒缓和治疗的需要。因为“病人最初并非按艺术和美学的写作标准进行,他丝丝入扣地写下他的恐惧和感受”就会显露出一定的“艺术价值。”(34)萧红的创作恰恰是不大按固定“写作标准进行”而显示出了一定“艺术价值”的典范。坚持从“灵魂”出发的创作目的,使她像“患者”渴望写“自传”一样,是不是“自传”无所谓,只要能把自己的情感发泄出来就达到了目的,这应该是萧红创作一直不守“规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从整体倾向上看,她前期创作“问诊”倾向更明显,后期创作“疗伤”倾向更明显,这也多少可以解释一些她前后期创作文类意识嬗变的内在原因。 宣泄能够疗伤,是因为宣泄中含有希望获得同情和理解的成分,以此能够弥补一些情感的缺失。萧红作品中有关童年、少年时期生活的描写,比如《后花园》之类,弥补了她在家庭和母爱方面的缺失,显示的是作者对她们的渴望和怀念。她作品中有关自己生活困苦的描写,比如《孤独的生活》之类,起着弥补现实生活困窘的作用,宣示了作者对自己人生道路选择正确性的认定。而她对女人生产、生活罹难意识的过度张扬,弥补了作者一直缺少的性关爱,呼唤着那一份本应该属于自己却没有的温馨。萧红曾几次生育,孩子不是死了,就是送人了,作为母亲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她要创作小说《弃儿》,在作品中她申诉了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做出“弃儿”选择的艰难和无奈,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看作是萧红在为自己申诉,为自己辩解,为自己“正名”,弥补着自己失子的“过失”。“弥补”似乎已成萧红创作的一种习惯定式,不仅在以作家自我生活为素材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当她写别人、写故乡时,也不时能让我们看到这种倾向。“呼兰河这地方……竟不会办一张报纸。以至于把当地的奇闻妙事都没有记载,任它风散了。”(35)《呼兰河传》的写作不就起到了“办一张报纸”的作用,含有记载“奇闻妙事”、不“任它风散”的企图吗? 很显然,创作也给萧红带来的了一些生活的转机和希望,起着情感按摩和抚慰的作用。考察萧红的创作,从总体上说,她前期的作品宣泄倾向更明显,不论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抒情主人公,他们大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像动物,为本能驱遣,人间冷暖不胜唏嘘慨叹,《生死场》、《弃儿》、《桥》、《手》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一些系列散文创作都是这样。而她后期的一些作品,宣泄的成分减弱了,代之以更深沉的追思抚慰情绪上升。她写这些作品时的情境,有些像一个曾经有过创伤的人,在阴雨潮湿天气伤口会发痒一样,此时只有轻轻抚摩才能得到一些舒缓,重不得,也不能置之不理。《小城三月》、《后花园》、《呼兰河传》等作品都在这样的情境下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呼兰河传》与《生死场》做一对比,二者都以“北中国”的那个小城为描写对象,都用抒情笔调、散文笔法写作,但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情感和情绪还有一些细微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于作者的现实处境和现实的情感需要。前文我们举例谈过,萧红在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最后几年,曾经以“无题”的方式写下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和体验,她赞美的是“幽美”、“宁静”、“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36)这是萧红的创作经验谈,当作家从“幽美”、“宁静”的立场出发走向“灵魂”的时候,创作其实也相当于精神“按摩”,有不满、有宣泄、有补偿、有抚慰,对读者有这样的作用,对作者自己更是如此。我们还记得,当萧红对“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表示赞赏之后,并没有忘了告诉人们,还有一类作家,他们好像“暴乱、邪狂、破碎”,但最终也要走到“灵魂”的道路上——这,我以为应该是萧红对自己创作道路的总结。萧红前期的作品有一些“暴乱、邪狂、破碎”的成分,但那是就萧红创作自身相比较而言,并不说明她的前期作品真的就“暴乱、邪狂、破碎”,相反在这些作品中也同样含有“幽美”、“宁静”的倾向,而这正是萧红所谓从本能也能够走到“灵魂”的立论依据。对于萧红来说,创作首先是她的生命需要,她的“灵魂”只有在创作中才会感到一丝安慰,这是更深一层次的情感“疗伤”。 注释: ①②(13)(20)茅盾:《呼兰河传·序》,《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699、701、705~706、705~706页。 ③萧红:《无题》,《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087页。 ④曹禺:《雷雨·序》,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⑤⑨萧红散文《蹲在洋车上》记录了自己童年的这段一段趣事。萧红:《蹲在洋车上》,《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909、909页。 ⑥(17)萧红:《后花园》,《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647、647页。 ⑦萧红:《手》,《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⑧萧红离家以后,有一段时间住在哈尔滨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属于漂泊一族。萧红:《初冬》,《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⑩萧红:《最末的一块木》,《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994页。 (11)(22)萧红:《他的上唇挂霜了》,《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003、1003页。 (12)萧红:《弃儿》,《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14)萧红:《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记录》,上海:《七月》,第15期,1938年3月。 (15)(16)(18)(33)萧红:《呼兰河传》,《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822、719、730、878页。 (19)(29)(31)萧红:《苦杯》,《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173、1173、1173页。 (21)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页。 (23)萧红:《借》,《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006页。 (24)萧红:《欧罗巴旅馆》,《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972页。 (25)(35)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文学与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67、262页。 (26)袁国兴:《乡愁小说的“做旧故乡”和“城里想象”》,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4期。 (27)萧红:《失眠之夜》,《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059页。 (28)(30)萧红:《生死场》,《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99、97页。 (32)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34)余丰:《倾诉与转移》,《文学与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 (36)萧红:《无题》,《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0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