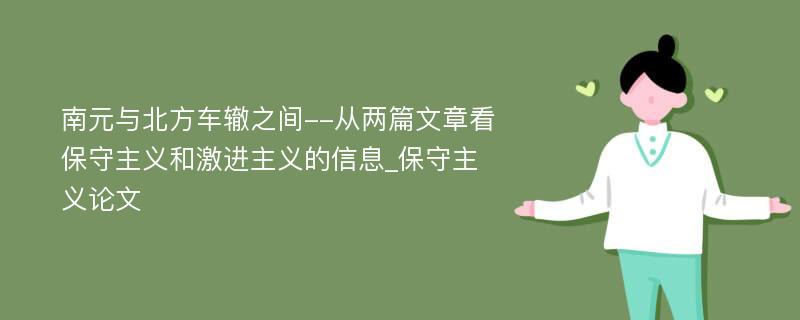
南辕与北辙之间——从两篇文章略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讯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保守主义论文,讯息论文,两篇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这两篇文章透露出来的讯息
捧读95年第2期《文艺争鸣》,其中的两篇文章让我着迷,其一是唐晓渡先生的《时间神话的终结》,其二是范钦林先生的《民族自尊的误区和现代文化选择——对一种东方怀古情结的批判》。这不仅是因为两篇文章写得有滋有味,而且因为它们从不同的方面透露出两种不同的文化讯息又一次开始相互撞击,这两种文化讯息近年来一直苦苦地纠缠着我们,在给予我们希望的同时使我们渺茫;在使我们渺茫时又时时露出希望的曙光。这就是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龃龉和对峙。
(二)为激进主义号脉
唐晓渡先生的文章高屋建瓴,笔意纵横,汪洋恣肆,酣畅淋漓。它不仅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范畴“时间神话”,而且对于时间神话的构成、其中孕育的价值观念、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突出表现,都作了精彩的分析,读来回肠荡气。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不再满足于从一般的社会政治学的角度,而是努力从哲学思想、时代思潮的角度,自觉运用观念史的方法探究文学史上非常复杂的精神现象问题。凭心而论,近百年来与我们生死攸关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现在看来是有些不正常之处,称之为病也好,称之为误区也好,反正我们不能再对它熟视无睹安之若素。中国文化与文学何以“大病缠身”,何以“走入误区”?唐晓渡先生的答案之一是:“时间神话”使然也。在唐晓渡先生那里,所谓“时间神话”“就是指通过先入为主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持之以故,言之成理。不过我觉得很有必要再挖一挖线性时间观的“祖坟”。应该说,这种线性时间观并非肇始于现代中国,亦非肇始于西方近代物理学;它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日常语言结构和由之命定的思维结构之中,并不知不觉地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近代以来,西方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取向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对这种线性时间观苦恼不尽,反思不已。这就是说,线性时间观并非科学主义的直接产物。但它与科学主义的关系不可小觑,它们可是有血缘关系的近亲,而且19世纪风靡全球的达尔文进化论毫不犹豫地强化了科学的权威性因而也强化了线性时间观的真理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本文这里或后面提出的科学主义、包括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在内的进步主义、线性时间观、片面地域观等范畴,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但愿以后有机会说清楚)。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句,科学是个好东西,让我们有衣穿有饭吃有五光十色的世界看有美妙动听的音乐听,但它一“主义”,原来的隐疾就成了显症。科学一“主义”就一口咬定科学(当然是自然科学)万能,而且也只有科学才万能;科学方法是解决一切自然问题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的灵丹妙药;认定科学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源泉和唯一尺度。在这方面,深受其害的不仅是我们中国人,西方人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忍受它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们有点冤:没有享受多少科技的成果,却不成比例地受到了科学主义的过渡伤害。外国人在吃肉的同时受伤害,我们啃窝头就萝卜条也受同样的伤害或更大的伤害,就显得有点天理不公。当然,不能把线性时间观当成一切问题的替罪羊,线性时间观在中国的确立也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给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披上华丽的外衣,用唐晓渡先生的话讲,“是近代中国深重的社会/文化危机产物。”但它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经形成并发挥影响,只不过近代中国深重的文化危机进一步确立了它的权威性与真理性罢了,正象它在西方近代形成以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强化了它的权威性与真理性一样。正如唐晓渡先生所言,线性时间观强调了时间的“前方”维度(正象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的“前几天”“第三天”一样),把时间理解为有着内在的目的性和线性运动,它体现了强力意志,歪曲了时间与空间的密不可分的性质。这些都是线性时间观不能逃脱的罪责。
我想进一步补充唐晓渡先生的是:“时间的神话”是一切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当然也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沃土(政治、经济的激进主义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线性时间观只是人们审视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才演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真理,可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它永远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假定,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一个符合经验的惯例,一个随时可以加以质疑的公理。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以线性的时间观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看待复杂的人类文化现象,当然也可以随时弃之如敝屣——至少从理论上讲可以如此。
在线性时间观大行于天下的时候,它的一母之同胞也大模大样地亮了相。那是一种让中国人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尊、咬牙切齿的同时又不得点头称是的一种(东、西方)地域观,我无以名之,姑且斗胆称之为“文化地域观”罢。这种建立在以成败论优劣、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基础上的地域观也有它自己的一连串未经任何证明的假定,那就是: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东方日出西方雨道是无缘也有缘;西方文化(至少是科技文化)比东方文化更优越,因为中国的四大发明毕竟没有抵挡住西洋的钢枪钢炮;西方对于东方的侵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上的侵略。于是文章满天乱飞,名词纷纷出场:先是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后是后殖民主义,后少数民族主义……不知文人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何所思何所忆,但它能满足一部分文人的精神需要,叫做悲剧情结也罢,称之自虐情结也罢。
这样畸形的线性时间观和文化地域观至少在中国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后果:第一是虚无主义(不仅是指民族虚无主义,而且也包括世界虚无主义),第二是进步主义(不仅包括逐渐进步主义——渐进主义,还包括激烈进步主义——激进主义),第三是唯“新”主义(当然也包括唯“后”主义)。这些都使我们深受其害而苦不堪言——全是我们自己找的。先说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已经成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似乎不来点虚无主义就不时髦不气派,就显着自己没水平没文化没有时代感没有现代感。特别是那些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认真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人,更是如此。在他们那里,不仅中国过去的一切,人类过去的一切都是垃圾,而他们之所以指控它们是垃圾,理由也只有一个:它们是“过去”的。在虚无主义者那里,过去的不足为凭毫无意义,过去的一钱不值。
再说进步主义。进步主义的假定是这样的: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它根本否认任何非变化的存在,即使承认静止的存在也要在“静止”的前面加上“相对”二字予以消解——这使我们想起了“右派”与“摘帽右派”的老故事);变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进化,进化就意味着进步。这一系列的假定能否成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努力,更需要现实的证实。不管怎样,它还是再用那个线性的时间观看社会,并把一种不言而喻的正面价值注入其中。它或者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或者是隐隐晦晦地暗示我们:未来的就是好的,过去的就是糟的;未来是一片光明,过去是一片黑暗。把它当成痛苦的镇静剂,比当成严肃的文化研究更明智、更能证明它的存在的合理性。
依据对于进步动力和进步速率在理解上的差异,进步主义把自己划分成两种,一种是渐进主义,它承认时间的线条性和未来的价值性,但认为获取那个价值必须有板有眼、有条不紊、按部就班、有理有节的,万万不能着急,一切都要慢慢来,这是一种慢性子的人所钟情的进步主义。一切改良主义者所信奉的进步观就是这样的进步观。另一种是激进主义,它相信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发达,文化的变化,不能老牛破车慢慢来,“俟黄河清,人寿几何”?孙中山先生1905年在伦敦对严复先生的这一句话,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这部分人的心态(当然这种心态具有不容否定的合理性——在当时)。在激进主义者看来,一切都要通过不断的革命来完成——也只有革命才能完成,这即是必要的,还是必然的,更是可欲的合理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一切激进主义称为“革命主义”。革命者生,不革命者死,反革命者十恶不赦罪该万死。政治上的改朝换代,经济上的激烈变革,文化上的扫荡决裂……革命成了口头禅,成了时尚,以至于象无徽不成商般地无处不革命,无人不革命,无事不革命,无时不革命,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思想、灵魂而且深处、脸蛋子脚丫子……都可以革一把命。一次革命不行,就来第二次革命,还可以第三次第四次……地革下去。这一切源于这样的假定:革命是进步动力,革命才使社会沿着一个时间的方向走向一个认定的目标,与此同时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无足挂齿。
线性时间观还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唯“新”主义。它认定只有新的才是好的,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值得追求的,才在历史的发展中有一席之地。有那么多的俊士才子不停地“新”来“新”去,唯新是从,唯新是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什么新时代、新国家、新时期、新纪元、新风尚、新一代、新人新事新气象……社会上比比皆是;新历史主义、新东方主义、新感觉、新体验、新写实、新状态……文坛上层出不穷。文人们马不停蹄、精神抖擞相互标谤着卖弄着,象打了鸡血,如吃了鸦片。唯“新”不足则唯“后”,后现代主义、后民族主义、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历史主义、后个人主义、后资本主义、后艺术、后美学,……张口尼采、海德格尔、德利达,闭嘴富科、德娄泽、杰姆逊,加之“话语”、“语境”、“文本”等半生不熟的概念绕来绕去漫天飞舞,让人不由得不想起威虎山上那著名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黑话,以至于无“新”不成文,无“后”难为人。结果,拉大旗做虎皮,牛皮上天文章落地,不仅把别人绕得晕头晕脑,也捎带着把自己弄得迷迷糊糊。文艺理论界、美学界虚假的繁荣与无聊的昌盛就是建立在这些文字游戏之中,什么“众声喧哗”呀,什么“走向多元”呀,全是空口说白话,哪时来的“众声”,何处去找那“多元”?
有两位造诣很深且我深深佩服的学者,在两篇写得不错的文章里写了这样两个句子,抄在这里,让大家费把子力气和我一道参一参,也趁着这个机会看看自己在“新”与“后”方面的功力如何。其一曰:“首先,开放的艺术,不是他律的艺术,不是受奴役、受控制、丧失了自我的异化的艺术。……其次,开放的艺术不是自律的艺术,不是孤立绝缘的、自我封闭的艺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这意思我明白了,可我参不透的是:开放的艺术既不是他律的艺术,也不是自律的艺术,那它可叫个啥呢?但凡有点逻辑常识的人,都明白:说既非A又非非A,那叫自相矛盾。其二曰:“传统审美文化以儒为尊,儒家审美文化也与整个儒家文化一样具有泛政治——伦理化倾向。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话语,被直接用作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而发挥功能。由此决定了它在道德伦理、学术思想、政治权力三个层面之间的直接同构,故被称作政治伦理哲学。它既是个体道德修养的经典,也是维护社会秩序与统治权力的‘法律’,是知识分子修身与官僚阶级治平的共同‘必修课’(所谓‘《春秋》断狱’、‘《论语》折案’)。这样,儒家文化,包括儒家审美文化,借助于它与政治权力话语的高度同构而占据了整个文化与知识系统的绝对中心,……不幸的是,包括审美文化在内的儒家文化的显赫地位是以其自身独立话语规范的丧失为代价而取得的……”那么,请问:儒家文化都已经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啦,已经是道德伦理、学术思想、政治权力三个层面上高度同构啦,已经借助于它与政治权力话语的高度同构占据了整个文化与知识系统的绝对的中心啦,怎么着又忽然不幸起来了呢?怎么又要丧失自身独立话语规范,并以此为代价来获得显赫地位呢?那自身的那个话语规范是什么?不就是在道德伦理、学术思想、政治权力三个层面之间的直接同构的“政治伦理哲学”吗?作者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家,如此为文,相信有他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写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无“新”不成文,无“后”难为人的危害有多么严重了吧?
虚无主义、激进主义、唯“新”主义、唯“后”主义……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文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也给社会的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文化的疲软,文化界的无聊,文化人的百无聊赖——为赋新诗强说愁……也都与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它既无需掩饰,也无需要抵赖。这里没有什么责任问题,或者说现在还谈不到究竟由谁来为此负责的问题——真有人负责也是负虚责,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指出激进主义的病根之后,我们开不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方。我们中国人都聪明过人,聪明就聪明在谁都能为中国,为中国人,为中国文化,找病根;但谁也开不出能治病的药方子来。在这里,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是:除了线性的时间观念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念可以更好地使我们审视这个世界?总不能完全抛弃时间的范畴吧?传统的“大道周天”、“无往而不复”、“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式的循环式时间观,唐诗宋词中巧妙的空间化的时间观,在今天恐怕都不足为凭。西方除了线性时间观恐怕也再难找到第二个有效的时间观为我所用。大伙说,这怎么办?人类及其文化是不是确实存在着发展和变化,除了进步的观念以外还有什么范畴、理念模式可以解释这种变化?人类的文化是不是需要一个价值判断上的尺度?如果需要,“新”还是不是人类文化一个主要的价值尺度?如果不是,那什么才是呢?激进主义不能逃脱线性时间观的限制,保守主义就做到这一点吗?
看来,严厉地批判了一通激进主义并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决心抛弃激进主义之后,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茫然不知所措了。看来,还是保守主义者说得有道理,破坏这个世界比建设这个世界要容易得多。尽管保守主义也有保守主义的难题。
(三)给保守主义透视
想必我们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想必我们不会忘记那里面让人欢喜让人发抖的名句:“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读到范钦林先生(如前述,《民族自尊的误区和现代文化选择——对一种东方怀古情结的批判》的作者)的感叹:“一个怀古主义的幽灵在京华大地徘徊”时,我忽然想到了它。虽然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不能否认二者之间共同的激愤情怀,那便是对一切保守主义的宣战。
保守主义远比激进主义更为复杂和多变。在这里,怀古主义只是保守主义之一种。如果说保守主义是一种对于往昔消逝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持有敬爱、崇尚的心态、激情与理念的话,那么怀古主义只不过是保守主义这个冰山的一角。它是保守主义中的一种情绪(还上升不到理念的层次)。当然,情绪的存在也需要寻求理论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使我们不能怀疑这样一种可能性:从怀古主义上升到保守主义,从保守主义变成复古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是复古主义者,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与盼望政治制度的复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可以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一样,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完全可能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保守主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温和的保守主义,一种是顽强的保守主义(这里说“顽强”也并非褒义,只不过怕说“顽固”有过分强烈的贬义色彩)。温和的保守主义又可叫做相对的保守主义,它强调珍惜历史,珍惜民族情感,珍惜文化遗产,但并不“愚忠”上述的一切;与其说它忠于过去的一切,倒不如说它试图保持现在与过去的血缘联系,而不致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迷失自己(在它看来,现实就是历史的延续,我们永远生活在历史之中);它强调与传统对话,适时地借鉴一些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解决自己的难题;这是一种“中体西用”式的洋务心态在文化研究和生活境界上的表现。顽强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绝对的保守主义,它只承认本民族及其传统、遗产才是唯一的价值源泉和尺度,这实际上是保清灭洋式的老义和团的心态在文化研究与生活境界上的表现。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年来保守主义的恶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清洗,现在说一个人保守并不象过去那样意味抱残守缺、不思进取、顽固守旧、死尸骨头、老顽固、老古董、跟不上时代潮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周公……。
坦率地讲,人类文化精神还需要保守,现在看来,传统不是守的太多,而是守得太少;我们现在不是受传统文化之累,恰恰是没有文化害苦了我们。20世纪以来,我们在一步一步地放弃自己的传统,同时又没有真正学到西方文化的精髓,甚至西方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我们现在都说不清道不明,西方文化的真相对于我们来说更是雾里看花朦朦胧胧。我们知识分子已经失去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社会大众已经不受任何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信心,更失去彼此间的相互信任——上街买东西,即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怕交了钱人家赖帐,仍有被诈骗的恐惧感。从这个角度说,怀古主义不能只是一个幽灵徘徊来徘徊去,应该快快显灵。
保守主义历史十分悠久。但悠久的历史,黄金般的过去并不是它永不衰落的保证。孔子可以作为保守主义的第一代宗师。那时保守主义作为社会意识的主流,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时代的潮流和社会走向,虽然不时也有各式各样的激进主义者(如王充、李贽)对其作出严峻挑战,但并不能对它们构成致命的威胁,相反使它一次又一次从危机走向新生。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甲午海战失败以来,保守主义改主动为被动,从中心走向了边缘,从台上走到了台下,从在朝派变成在野派,成为激进主义的补充、陪衬、润滑剂。它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绝迹,即使不再能以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也能通过其它方式保存自己:保守主义从此化作永远也发不完牢骚,永远泄不尽的怨气。从消极的方面说,作为一种情绪,作为一种发泄,它不满足于我们亦步亦趋地跟在洋人的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在国际交往中不能喊出自己的声音,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不满意于中国人得了失语症,不满意于激进主义的打倒旧文化埋藏古文学扼杀文言文,不满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沦丧,不满意于全盘西化或半盘西化,不满意于西方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统治。从积极的方面说,它要求弘扬祖国优秀文学遗产(什么才是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也说不清楚),要求清算五四新文化运动(怎么清算它也道不明白),反对白话文运动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厄运,要求挖掘东方的诗性般的智慧……不管能不能说清楚,这些要求、愿望何尝没有合理性,何尝不显示保守主义者的时代使命感(虽然永远活在传统之中)和民族正义感?不管其可能性和现实性是多么微不足道,保守主义者是多么自不量力、不识时务,它毕竟还是有那个心的(虽然无力)!忧国忧民的情怀,对生命智慧的执着追求,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坚定意志,这一切在今天是多么珍贵!
我们得承认,和激进主义一样,保守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这里所谓意识形态,并不是指我们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为了区别两者,台湾有人将前者译成“意谛牢结”,多么良苦的用心),即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各种社会意识的总和;而是指每个社会都无法脱离,包含了一定的情绪、情感、愿望、意志、价值、观念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在这里,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里面所包含的那些内在的东西,不管享有意识形态的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说到底,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工具,用来为一定的情绪、情感、愿望、意志、价值、观念来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辩护而已。保守主义,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的基本核心是一致的,那就是:强烈的民族自尊感(虽然有时这种自尊是一种盲目的妄自尊大,但把它与寡廉鲜耻放在一起时,我们选择什么),这正是民族主义的精髓之所在;对于人、人性、人道的关切(虽然失之于抽象,但又比一味推崇兽道好得多),这是一切人文精神的核心;对于过去遗产的珍惜(虽然有时不免盲目守旧但总比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要好些),这是社会进步的止痛剂……保守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这一点,激进主义者要么是看不到,要么是根本不愿意睁开眼睛看。
但保守主义的问题依然不少:既然是保守主义,那必然最终要有所守,可守什么呢?这是它最大的问题。守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种类繁多,并且具有极大的异质性。传统文化是指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还是佛家文化?即使儒家文化也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变迁,产生了先秦儒家、宋代理学、明代心学,守哪一种还是都守?况且文化还有其它的分类方式,是守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是守传统的风俗习惯,还是守传统的审美情趣?如果几者兼而有之的话,那又如何解释其中的对立与矛盾?关键的问题是:全守既没有可能性又没有必要性,还与保守主义者的主旨相矛盾(它也不得不承认传统中也有垃圾),那如何判断哪些东西值得守,哪些东西不值得守?即,哪些属于文化的精髓,哪些属于文化的糟粕?为什么要保守这些东西?又如何才能守得住这些东西呢?在我看来,回答上述的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证之于历史与现实,都需要一种强烈的现实感,需要现实作为参照架,不然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不论怎么评价“洋为中用”、“古之今用”,我们总是生活在此时此刻的现在而不是对过去的“诗意”的缅怀之中。而一谈到现实感,又毫无疑问地回到了那个令保守主义者都深恶痛绝的“线性时间观”之中,随后又为一切文化激进主义打开了方便的大门。从这个角度看,保守主义又何尝没有屈从于线性时间观念,只不过它认定的价值不在人类的未来而只是在人类的过去,过去的山水风俗人情,文化制度,典章礼仪……才是价值的源泉,才是价值的尺度。这从一个方面暴露出一切保守主义的天然弱点,它想在激进主义的轨道上开激进主义的倒车,无奈自己的牛车拉不过那电气化的火车。带着这样的天然弱点,保守主义具有更多的理论上的漏洞,不可能和激进主义争一日之短长。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保守主义越来越不是激进主义的对手,常常是让激进主义批得体无完肤伤痕累累,它也只能趁着激进主义受了来自其它方面的重创之后,重整旗鼓,“乘人之危”地发展一阵,一旦激进主义稍稍恢复元气,必欲迎头痛击而后快。到那时,保守主义就只能重新化作一股气,咬牙瞪眼强撑着,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过。悲壮固然也悲壮,只是悲壮中夹杂了过多的苦涩。
保守主义另外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它以十分明确的姿态,关心人文精神,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因此,保守主义者总是和人文精神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虽然严格说来决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说到人文精神,这几年也叫得很响。请问:什么是人文精神?什么是人本主义?什么是人道主义?什么是人文主义?人之“本”、人之“道”、人之“文”又是何所指?它(或它们)是一种客观存在吗?请指给我们看看,或从理论上证明一下它的客观性,让我们口服心服;它是主观的假定或愿望吗?那何以作这样的假定或愿望(如“人之初性本善”)而不是那样的假定或愿望(如“人之初性本恶”)?当两种假定或愿望一致时,一切都好办;可当两者相互矛盾时,那我们应该相信谁是谁非呢?有没有一个标准,一个有效的而不是一个想当然、信口胡诌的标准存在?
换句话说,当保守主义者在说“人应该是人”的时候,他不能彻底地令人信服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应该”来自于保处?为什么说应该呢?根据什么说“应该”不“应该”呢?
有人乞灵于形而上学(或称玄学、本体论),再三强调“重建形而上学”,以之为包括一切人文主义在内的哲学确立先验的前提。可困难的是,在经过了科学同时也经过了科学主义的洗礼之后,任何“自称”的“先验”都要屈从于“经验”,任何“先验”都必须经过理性和科学的证明才有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形而上学的神话早在二十年代科玄论战时就已破灭,现在请出其亡灵,很难奏效——任何形而上学的神话都已经破灭。
有人乞灵于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它承认形而上学已经失灵,只好说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不要说人是什么,也不要说人应该是什么,而是在做人的过程中认定自己。不过,不要说一般没有机会受教育的民众,就是我这样受过一定专业训练的人,也搞不清楚这种讲法与下列的情形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放任自流、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渴了抢水饿了抢饭,没钱砸银行,犯事就枪毙……一切都无所谓,反正存在先于本质。当然,萨特先生和敬仰萨特先生的人也不希望人都这样,就用类似于“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的大话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请问: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事后的被动承受还是主动的选择?如果是前者,存在主义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不足为训;如果是后者,又依据什么进行选择?……最后,萨特先生也只好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使新问题又变成了老问题:人之“道”何在?怎么证明它的确存在?如何证明“道”的合理性?所谓“心体呀性体呀自我呈现”之类的大话,不要说别人不相信,恐怕自己也不信。它充其量是诚则信不诚则不信之类的玩艺儿。
(四)激进主义:可信大于可爱保守主义:可爱大于可信我们生活在文化夹缝之中
文化激进主义经过近百年的突飞猛进之后,已经失去了它的光辉照人的魅力。再随随便便地以时间神话、地域神话来糊弄人,让人再点头如捣蒜,现在还行,再过几年难说。保守主义也不能把应该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依然不能服人。这使我们这些对什么“主义”都要打个问号的人生活在文化的夹缝之中,盲然不知所措。激进主义的可信大于它的可爱,保守主义的可爱大于它的可信。自王国维以来“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近代文化悲剧以另外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向我们逼来,所谓文化的危机,所谓文化的一重危机二重危机,也只有在这个方面演示得充分和彻底。我们当然不愿意陷入文化虚无主义之中,可又有什么办法使我们摆脱心灵的空虚,为我们的心灵寻找真正的家园呢?
其实,激进主义也好,保守主义也好,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共同性的,那个共同性就是民族主义精神,其目的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但达到这种目的的路径很不一样。比方说,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激进主义者要先给西方人当徒弟然后当师傅,来它个先苦后甜;保守主义者要自始至终地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这就象吃自己手里抓的花生,有的喜欢拣大的吃,始终都吃大的;有的喜欢拣小的吃,始终吃小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你说谁优谁劣?这个比喻或许是拙劣的,我这里只是竭力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性,以希望能通过某种方式,从根本上消解二者之间的对立和相互歧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或许根本不可能;或许可能,只是那一天离现在还过分遥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对唐晓渡先生和范钦林先生作派别上的划分,更无意于制造二人在理论上的对立,“挑斗群众斗群众”;只是从他们的文章中捕捉一些文化讯息,说明目前文坛上的混乱状况及其根源。甚至“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权作分析问题时的凭藉——在现实中,哪里有什么纯粹的保守主义,哪里又有什么绝对的激进主义?最激进的激进主义者(如鲁迅)也不能完全摆脱怀旧和恋古的情怀,最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如孔子)也不至于真的不食人间烟火地生活在他所谓的“传统”之中不能自拔。就连自称“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的,我们看起来时也要打些折扣,才不致于过分的天真和幼稚。更何况,除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参照系来审视人类的文化状况与处境。不过,无论用什么框架,用什么参照系,我们都希望对于我们现在的文化困境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只是一味地玩那些自己纳闷别人也糊涂的名词游戏,还自我陶醉其乐融融。那样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