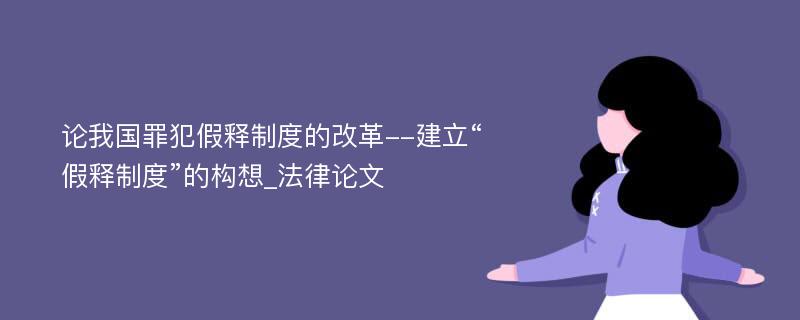
论我国罪犯减刑假释制度的变革——关于建立“预定假释制”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罪犯论文,制度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减刑与假释,均为在行刑过程中对罪犯良好在狱表现的奖励,但对罪犯而言,被假释4年的意义绝然不同于被减刑4年,前者是有条件的自由,而后者则完全脱离了监狱;前者的主体身份仍是罪犯,而后者的主体却已不再粘贴此标签。对行刑机关而言,两者的性质也同样有异:前者只是具体行刑方式的改变,是对罪犯在社会环境中的继续矫正,而后者则意味着余刑届满行刑过程终结。在以假释附加条件为法定假释监督内容的国家,假释者可能因非犯罪的原因而重新入狱,而后者在减刑余刑届满后,除因犯罪而入狱外,不可能因非犯罪的原因而重归监狱,同样是提前释放,两者各自的意义和后果截然不同。由此观之,作为狱内表现良好的奖励,被减刑者所获得的报偿要高于被假释者,相对于同一年数,减刑是比假释更为宽缓因而自然更受罪犯欢迎的制度。毫无疑问的结论是:被减刑的罪犯,其悔罪迁善及回归社会的程度应当高于被假释的罪犯,对减刑的运用相对于假释应更慎重、更严格。
但是,我们的法律与实践却与此相左,刑法对运用减刑所要求的主观条件只是“有悔改”或“有立功表现”,而对于假释则不仅要求罪犯“确有悔改”,而且要求该悔改必须以“不致再危害社会”为内蕴。我国的部分学者据此而顺水推舟地提出:对假释的运用应更慎重更严格于对减刑的运用,因而减刑率高于假释率是正常而合乎法律规定的。必须提出的是,科学的思维方式绝对不是:“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因此结论当是如此的”。我们当然可以引用现行的法律为依据而论理论是非,但这种引用必须以相应的法律本身合理科学为基础。我国的假释率远远低于减刑率的现状,究其根源,除涉及假释监督制度的法条规定和实际运作的缺欠外,根本在于假释制度运行的灵活与便利远逊于可以重复适用的减刑。
依我国刑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最高可减刑期可达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无期徒刑实际执行期满10年亦可减刑,但事实上,行刑部门很少对罪犯实行大幅度的减刑,我们一般认为,考虑减刑,既要鼓励罪犯积极改造,又要维护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和国家刑罚的严肃性,一次减刑太少,对于鼓励罪犯尤其是长刑犯就可能无效。同样,一次减刑过多,就有可能使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和国家刑罚的严肃性受到影响。一次减刑的幅度不能太大也不能过小。我国目前的减刑幅度一般一次为一年,二年以上者鲜见。1989年2月14 日最高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明确提出:对于有期徒刑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一般一次可减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一般一次可减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上述减刑幅度的限制。我国减刑幅度窄小的现状,使得我国的减刑制度在实际运用上反较假释更为宽松,幅度窄小但可重复适用的减刑制度,其灵活、心理刺激连续而代价甚微的效应,无疑使之成为行刑部门控制罪犯、维护监内秩序和纪律的应手工具。此外,根据罪犯的表现,根据其改造进步的程度,渐次相应减少其实际服刑,无疑可以更有效地持续地促使罪犯积极改造,而就长期自由刑假释而言,对罪犯过早地予以假释,使之生活于事实上缺乏有力的监督保护措施的社会,不仅为我国的具体环境所难以接受,而且也不利于保卫社会。实践中,行刑部门自然一般不愿意对罪犯过早地适用假释,而过晚地适用假释,在社会缺乏必要的监督的情况下,假释事实上在释后与减刑并无太大的区别,不如直接适用减刑。我国的减刑制度客观上无疑发挥着鼓励罪犯自新、控制监内秩序与纪律等功能,行刑机关青睐于减刑制度的运用并不令人奇怪,而存在缺陷,尚不完善,运作过程不乏实际问题的假释制度不能不因此而受到冷落。
减刑制度虽为行刑部门所重视,但该制度在实践中也存在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严重缺陷:缺乏预后性和过渡性。减刑,无疑具有促使罪犯改造的巨大动力,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预后保障,在罪犯获得减刑甚至获得几次减刑后故态复萌,行为不善然尚不够法律惩处的情况下,减刑不仅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有某些虽获得减刑但并未真正改造好的罪犯在放归社会后危害社会的弊病。减刑预后的保障的欠缺,使得行刑部门在未改造好的罪犯因减刑剩余刑期的届满而不得不提前释放的情况面前束手无策。原本为避免绝对罪刑相应主义僵硬死板的弊病,根据行刑个别化的要求而实行的有限度弹性化的行刑制度,反而成了自我限制的东西。减刑除原判刑期因减刑而直接届满外,一般情况下,获释的结果并不马上实现,被减刑的罪犯往往还要在狱内服一定时量的刑期,因而,行刑部门在考虑适用减刑时,一般无必要考虑罪犯将来获释后是否可能再次危害社会的问题。涉及罪犯在适当条件下能否重新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诸多因素如释后居所环境、释后生活能力、家庭关系及状况、同居亲友的品行及其生活状况等等亦可不在考虑之列,由减刑的性质所决定,即使对原判刑期将满的罪犯实施减刑,上述情况亦多无需考虑,被减刑的罪犯于减刑剩余刑期届满时并非因其“不会再危害社会”的预测而仅仅因其刑期届满而获释。刑法理论认为且行刑实践业已证明:受刑人出狱之初,是其最危险的时期。受刑人在狱内完全失去自由,一旦出狱,突获完全的自由,其间的强烈反差,往往使出狱者的心理甚至生理一时难以适应,如果缺乏适当的引导、调节,出狱者极易沦为再犯。因此,实有必要在不自由与自由间,介以半自由状态的制度,使受刑人在出狱出后仍受一定程度、一定期间的约束,以免其受不良的影响而重蹈覆辙。随着刑释者逐步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相应地逐渐减少约束,直至其完全恢复再生活的能力。而减刑制度,由于并不联系于罪犯的释后监督与保护,因而其对罪犯改造的促进与鼓励功能并不延伸至罪犯获释之后。如前所述,减刑获释者出狱是因其刑期届满,虽然其提前离狱是由于在狱内“确有悔改”或因“立功”,但“确有悔改”或“立功”并不等同于“不致再危害社会”。显然,就现行刑法及其指导下的实践而言,减刑获释者比因“确有悔改”并“不致再危害社会”而获释的假释者更需要一个逐渐过渡的时期。
我国目前所适用的假释和减刑制度实有因其各自的不足而进行改良的必要。其关键即在于改变现有减刑制度下所减刑期的性质,吸收假释制度可以预后的特性和释后保护监督的意蕴,将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合二为一,充分吸收彼此的优势,扬长弃短,建立更为完善的,效果更为明显的,集预后性、过渡性、释后可监督保护性、灵活性、重复适用性与连续刺激性于一体的“预定假释制”。
依现行的减刑制度,罪犯在其减刑后的剩余刑期届满后,即完全脱离了监狱,在此情况下,罪犯是以刑满的方式而跨出狱门的。预定假释制,首先就是要改变现有减刑制度下所减刑期的性质,即将现有制度下对所减刑期的绝对免除改为对所减刑期在监执行的免除,通过减少在监服刑期,改变执行的方式而不改变原判刑期长短本身。由于预定假释制下的“减刑”,其内涵仅仅只是减少罪犯的在监服刑期,改变行刑的方式,因此在预定假释制下,罪犯在监服刑期届满之日,只是跨出狱门而仍以罪犯的身份在狱外继续接受改造直至其原判刑期届满之时。对于在狱外服刑的罪犯,必须予以必要的监督,当罪犯违反承诺遵守的条件或又犯新罪时,应当撤销假释而回复至严厉的在监服刑。预定假释,实际上就是把在监服刑期的减少作为假释的依据,将在监服刑期届满之日视为适用假释的开始之时。具体内容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其实际服刑逾二分之一后,若其确有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经一定程序可减少其在监执行刑期,若该减刑未经一定程序予以撤销或其原减年数末予减少,则俟在监执行期满,罪犯即获附条件的释放。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如果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经一定程序可减为有期徒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10年,无期徒刑转为有期徒刑后,其假释适用上述规定,无期徒刑犯因确有悔改或有立功表现并不致再危害社会,经一定程序,在其实际服刑10年后可以假释,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如果没有违反假释条件或又犯新罪,即视其原判刑罚已执行完毕,如果违反假释条件,则可撤销假释,又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重新收监,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与后罪所处的刑罚,依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又犯新罪的,假释期间不计算在新决定的刑期内;因违反假释条件而被重新收监的,其假释期间也计算在原判刑期余刑之内,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为原判刑期没有在监执行的时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为10年,假释不影响附加刑的执行。
预定假释制是针对现行假释制度和减刑制度的缺陷与不足而提出的融合两者长处的制度,其实施的作用与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预定假释制对于已获减少在监服刑期的罪犯可能的故态复萌设置了预后保障。与我国目前现行的假释制度相比,预定假释制有其极为显著的特点:除无期徒刑直接适用假释或在监服刑期减少之数等于原判剩余刑期之数外,有关机关作出的假释决定并不表现为立即释放受刑人,此时的假释只是一种预定。依此制度,如果受刑人在监服刑期减少或几次减少后故态复萌、行为不善或经查明原系伪装迁善,行刑机关则可作出相应的反应,经一定的程序推迟或撤销假释预定,从而弥补在现行减刑制度下,减刑的运用缺乏预后保障,对获得减刑后又故态复萌的罪犯束手无策的不足,以保证从负刺激上督促已获在监服刑期减少,即已被预定假释的罪犯继续保持迁善,积极改造,维护行刑机关对于罪犯改造的积极可控状态,消除罪犯在获得减刑后所可能存在的松劲歇肩、退坡返恶与“大错不犯,小错不改,剩余刑期届满,照样释放回还”的表现或混刑心态,为行刑部门更主动、积极地运用减少在监服刑期的措施,充分发挥其正面激发与鼓舞作用,提供了切实的可能。同时预定假释制,对于投机取巧者,如对个别运用反衬手段,在故意表现恶劣成为抗改造尖子后又突然积极改善,由大会挨批者变为红榜有名者,以此利用行刑部门可能的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树立改造积极榜样的改造、管理需要而获取在监服刑减少者,显然亦具有明显的预后作用。
其次,预定假释制具有比现行减刑制度和假释制度更明显、更强烈的正向的刺激受刑人积极迁善的作用。行刑的实践说明,狱中服刑的罪犯,极为关心自己的在监服刑期的长短,无论他们各自内心的观念与需要的具体所向如何,服刑期间能缩减在监服刑期而早日跨离狱门,回归社会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直接的心理愿望,而这一愿望往往可以成为其行为良善的最直接的第一层次的动机。罪犯良好的服刑表现相当程度上直接联系于其早日恢复自由(即使是仍有限制但比监禁相对更宽缓的自由)。一方面对罪犯来讲,预定假释制不仅可以在预后方面,从负刺激上督促着罪犯,同时,其可以再次提早预定假释日使刑罚的执行向着更能满足罪犯前述愿望的方向可变的特性,具有比现行的单向可变的减刑制更加明显、有效地分化罪犯群体的功能,引导更多罪犯走改恶从善的道路,自觉接受改造,发挥着促进罪犯自我改造的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罪犯的刑期执行视为一种倒数递减的过程的话,那么很清楚,现行的假释制与预定假释制对于罪犯的正向激励作用也是有显著区别的。登月火箭的发射、原子武器的启爆等等采用分秒倒计时的准备法,祖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时日公告采用每日递减倒数计时的方法,无不以心理学的原理与科学的验证为依据。心理学原理表明:目标的远近与对人的激励作用成反比关系。当人们追求的目标越远,对其激励作用就越少,反之目标越近,对人的激励作用也就越大。当实现目标的时间是个定数时,时间愈趋减少与目标的日益接近的反比关系,最能使人产生激励与关注,时间愈是减少,目标愈是接近,该激励与关注越强烈。而预定假释制,由于是以减少罪犯在监服刑期为基础的事先预定的假释而有别于现行假释制度下实际假释时方才存在的假释,因此,假释预定日与假释日之间实际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先后之差。预定假释制,事实上是一种将假释程序通过预定的方式提前介入到监行刑程序的制度。而提前的介入,无疑是将现行假释制度下相对遥远的获得假释的目标更加现实具体化。通过在行刑过程中于罪犯服完法定的最低必要的在监服刑期与获得假释间,设置一个“获得假释预定”的中期目标,将相对较长的在监服刑过程分解为两个比较短小而后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更具有明确性、现实性与可期待性的倒计时过程,运用心理学原理与倒计时方法的结合,用长计划、短目标来实现大目标,通过这一手段连续不断地保持对于罪犯的刺激与鼓舞作用,促使预定假释制比现行假释制度具有更加明显而强烈的激发罪犯持续迁善的功能。
再次,预定假释制为建立以假释方法出狱的基本制度,迎接并战胜中国的社会现状对于传统的离狱方式及非强制性释后帮教所提出的严峻挑战提供了切实的可能。目前,我国所实行的以刑满释放为主的出狱制度是导致刑释人员社会化程度低,因而重新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罪犯,在其严格限制自由的监禁与完全自由状态之间有必要设置一个旨在使其逐渐适应后者的过渡环节。在传统观念面临挑战,社会环境更加复杂,诱发犯罪的各种因素日趋增多的今天,出狱者需要更多更经常且更有力的保护与帮助。对此,人们少有异言。但是,今天的出狱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接受非物质性、非利益性的帮助与保护。前述需要与出狱者普遍的主观欲求间的冲突,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中日益炽烈。同时,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今天,出狱人员经常性的人口流动所导致的人户分离、户口空挂现象不仅颇为严重而且呈日益扩大之势。理应人员到位接受帮助与保护而事实上人户分离,而这种现象又无法通过强制手段加以改变,这是社会向传统的离狱方法及非强制性的释后管理提出的严峻挑战。罪犯释后仍然需要帮助与保护,但必须以对象到位为前提,在刑释者缺乏自制力与自觉性,不愿接受劝化的情况下,对象到位必须以强制性措施为保证。但是,由此而产生的诸如国家对于刑满出狱的公民是否有权对其继续施以强制的问题,显然无法回避。人们坚信:帮助不等于管制,刑满释放,即意味着刑释者因服完既定的刑期而不再是罪犯,而是享有完全人身自由的公民,行刑机关与犯罪者之间改造与被改造的强制关系已告终结,即使对于释后行为不善有重犯之虞之人,对他们的必要帮助与保护也不能是强制的。释后帮助、保护的强制管理的必要与该强制“于法无据、于理欠妥”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而预定假释制为该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比现行假释更富功效的出路。变以刑满释放为主的出狱制度为以假释方式出狱为主的出狱制度,在假释制度下,对出狱者的帮助、保护在必要情况下与强制管理结合为一体并由后者予以保证,其管理至少在客观上可以更多地因此而强化。各种帮教措施与方案也因此而在保证相关人员受控、到位的前提下得到了实际的落实,从制度上为罪犯提供了完全监禁到完全自由之间显属必要的心理、行为过渡阶段。同时,以“监督”为标示的强制性管理,作为假释本身的内蕴,也更易被仍是服刑人的假释者在心理、情感上所接受。以减少在监服刑期为基础的预定假释制,吸取了现行减刑制度减幅窄小但可重复适用,具有稳妥灵活及心理刺激连续而代价甚微的特点,弥补了现行减刑制度缺乏预后保障,缺乏过渡性的弊病,集现行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各自的长处,远较两者更加完善、有效,为“逐步扩大目前的假释面,强化假释工作”,在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的情况下“逐步过渡到实行以假释为主的出狱基本制度”的构想(参见黑龙江省司法厅劳改局《劳改工作研究》1992年第1期第33页肖树林、 陈向阳《建立重新犯罪三大预防体系的战略构想》一文)提供了更为完善、更为可靠因而更可操作的基础和条件。
预定假释制,根据罪犯狱内表现的良好与否而可推迟、撤销或提前假释预定日的特点,更适应了行刑灵活化、个别化的要求,可以成为行刑部门引导、控制罪犯,维护监内秩序与纪律更为应手的工具。总之,预定假释制的建立与实行,无疑会有效地降低重新犯罪率,从而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标签: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