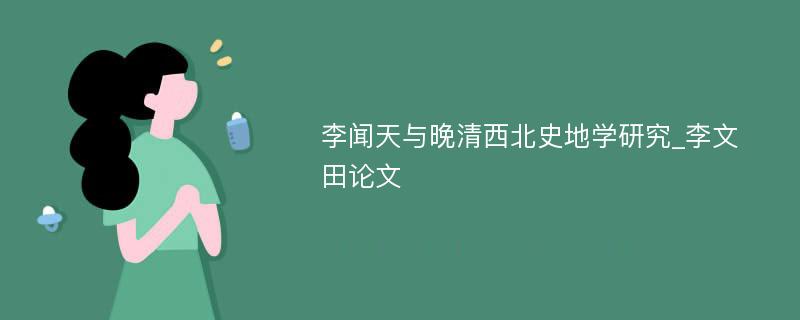
李文田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学论文,晚清论文,李文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5)01-0030-10 李文田(1834-1895),广东顺德均安上村人,小名胜儿,字畲光,号若农,又号仲约、仲若、药农,一痴道人等,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为咸丰九年(1859年)探花,历典文衔,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工部侍郎,殁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年六十一。民国三年(1914年)因梁鼎芬呈称而追谥“文诚”。 文田为官,敢于抗颜直言,所疏停修圆明园、停万寿景点、起用恭亲王均被采纳,为一时之名臣;甲午战争时负责京师防务,“查察三库遂感染寒疾喘病大作”,①卒于任上,操履端洁,更一时所瞩。文田“学识淹通,述作有体,尤谙究西北舆地”,②著有《元秘史注》、《双溪醉隐集笺》、《元史地名考》、《朔方备乘札记》及大量书画金石跋尾等,另有《宗伯诗文集》未刊。 回顾学界对李文田学术的研究,梁基永所撰《李文田》稍有系统,然为普及之作,学术分量自然较轻。③他如周清澍《张穆、李文田手迹考释》,④分写张穆与李文田,篇幅小,且多论其书法;梁基永《李文田泰华楼及其藏书初探》⑤、莫仲予《李文田与泰华楼》⑥论其藏书楼;朱伟《李文田及其篆书〈诠赋篇〉赏析》⑦论其篆书;李梦悦《康有为与李文田交往事迹考辨》⑧提出《我史》关于李文田的记载不合实情,但康、李二人书学思想相似,共同推进了岭南碑学的发展;胡亮松《李文田修堤》⑨则纯属文学作品;李骛哲《李文田与“清流”》顺应其师王维江思路,“把‘清流’看作政治现象,不是小集团,也没有共同的政治理念”,⑩认为李文田与“清流”“遵守着相同的游戏规则,也秉持着类似的价值观”,区别只在于“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于不同的政治问题。或许李文田要比多数‘清流’运气更好些、更聪明也更有心机,所以他的官做得更大,威望更高,名声也更好听”,(11)语甚谿刻。但是文所附《李文田年谱长编》颇有价值,引用了大量僻罕的档案、笔记、手札与日记,材料丰赡,(12)本文之研究,多资取于此。 概言之,学界对李文田之研究,成果较少,且多集中在其书法成就一隅。事实上,文田“其学靡不精综,书翰特其余事”;(13)政治方面多在考辨其与“清流”及康有为之关系;又因“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14)文田参预其中,故许多著作论述晚清边疆史地学时附议之。纵观全局,前人多聚一点,似少综合性研究,对其学术著作更是阐发不足。 李文田一生既与“清流”有离合,亦与“洋务”有往来,(15)为晚清典型的“政学之间”士大夫。因其学复杂善变,故支伟成修《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时曾致函章太炎,询“李文田学兼经、史、地理、校勘、金石之学,宜属何家?”太炎答曰:“李文田虽兼治诸学,然其所长在西北地理,宜入‘地理学家’,与徐松、张穆相次”,(16)可谓定评。李文田处于学术转型期,精熟边疆史地,间取西人著作,但方法及意识又决定了其为乾嘉殿军。本文尝试从李文田生平分析其学术理路,并藉此探讨传统舆地学的近代走向。 一、经世之讲求 李文田自幼颖悟,邻里以神童号之。十三岁时,其父李吉和去世,由其母徐夫人“悉索十指”,(17)供其读书。文田一度拟弃学从商,帮补家用,同乡塾师何铁桥得闻,即资以膏火,安排其与梁九图之子梁僧宝共读。又师从吴鞠通,得通岐黄;因“粤人笃信形家言,喜营佳兆,又重科名,往往建塔以镇风水”,(18)故亦旁采堪舆之术,有《撼龙经注》。尽管起自贫寒,但独特的成长环境使李文田既练达人情世故,亦怀有名士风度。 李文田咸丰九年(1859年)中探花,旋入值南书房,兼以编修衔加起注官。同治六年(1867年)获京察一等,出任四川乡试考官。仕途如此顺利,除文田自身博学多能外,更与前辈襄助密不可分。李文田座师郭汝成为祁寯藻门生、龙元僖为翁心存门生,且当时粤籍官员在朝廷“互为犄角”,(19)故文田甫一入仕即受广泛关注。翁心存“作寄龙兰簃书,八纸,托李若农去”,(20)翁同龢也来“订兄弟交”。(21)因精擅金石、书画、岐黄、卜算,(22)文田迅速结识大批京官,进入朝野交游核心圈子。 频繁雅集并不表示李文田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注。翁同龢记“晚李若农来,相与谈夷务,悲怀慷慨,莫能伸也”,(23)过后文田上奏《请饬广东督抚搜捕会匪以杜乱前事》,归乡后仍念念不忘剿匪,屡次建言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痛予创惩”。(24)又去函曾国藩,询军政吏治。同治十三年(1874年),朝廷重修圆明园,李文田趁星变陈言,博得美誉。此时的李文田,更多被当做是名士而非学人。 王维江指出,晚清存在“名利熏灼,驰骛势要,以学缘术,为上是从”(25)的现象,学术成了猎取利禄的工具,真学问衰落。刘师培也在《清儒得失论》中言“适潘祖荫、翁同龢、李文田皆通显,乐今文说瑰奇。士之趋赴时宜者,负策抵掌,或曲词以张其义,而闿运弟子廖平,遂用此以颠倒五经矣”。(26)翁同龢且不论,李文田与潘祖荫虽为莫逆之交,“而论学则异趣,盖潘固张今文之帜者也”,(27)故师培此语,不知何据。随后补充:“潘翁之学,涉猎书目,以博览相高,文田则兼治西北地理,由是逞博之士,说地之书递出而不穷。”(28)尽管语含贬斥,还是承认翁、潘、李三人学术著作发挥了一定作用。朱维铮根据对中国经学史的观察,提出:“经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学随术变’的,也就是说,学问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立场,而是根据政治形势、统治术的变化在不断地变化、适应。”(29)总体说来,晚清学风确实表现了“学随术变”的倾向,具体到李文田个人,之所以选择边疆史地学,则并非纯因利禄,而是经过理性权衡后的选择,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厥为两端,一是无征不信的乾嘉朴学,二是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传统。 李文田少时问学于南海何铁桥,“目辄十行,有神童之称”,(30)咸丰九年殿试传胪,中一甲第三名进士,赋诗《探花归第日马上口占》四首,有“壁里古文终日事,不应疎读尚书经”句,自注“拙著有古文冤词续二卷”。(31)《古文冤词》为毛奇龄驳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作,是书虽不足取,但文田既有续作,可证对经学颇有心得。渠同时熟稔校勘、版本之学,《翁同龢日记》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十二日赞“若农博览能文,丹铅不去手”,(32)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回忆文田书房:“长笺垂尺密于帘,插架堆床甲乙签”。(33)王拯亦在《药禅室随笔》里记载:“顺德李氏之学,自谓出于郑夹漈、王深宁,故于近人,最服膺俞理初。”(34)这大概为实录,王闿运到江西时,李文田专门“市我黔人俞正燮理卿癸巳类稿”。(35)郑樵、王应麟、俞正燮均是意存经世的博雅之士,文田仰慕他们,可见其志向。 长于粤省的李文田,对西洋文明并不陌生,同治八年(1869年)与翁同龢赏玩金石书画时,即“谋以洋镜取《华山碑》真影”,翁的态度是“不为然”;(36)其后文田侄骆选为翁同龢“写大像,用西法墨渲”,翁的态度是“不甚似”;(37)对比甚为鲜明。连一向与李文田不和的李鸿章,在推荐驻外公使人选时,也承认“侍读学士李文田,学识兼长,坚忍诚慤,生长粤东,熟谙洋情”。(38)张荫桓与李文田为亲家,二人曾不和,(39)但张驻外时曾“得李仲约书,论小吕宋设领事馆仰给华商之弊,又虑领事权力有限,威令不行,可谓见道之言”。(40)从疏谏今上,到中法战争与张之洞“商战守”,(41)再到修筑三水大路围,最后到卒于京师防务任上,李文田一生均秉持经世致用之传统。 李思纯曾纵论清代元史学发展大势: 盖斯学自康乾以来,如果树放花,初作蓓蕾。道咸之间,则嫩芽渐吐,新萼已成。至同光之间,千红万紫,烂熳盈目,及柯劭忞氏之著作成,而后繁花刊落,果实满枝矣。(42) 李文田真正全力研究边疆史地应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回京后,正处于于“千红万紫,烂熳盈目”的同光之朝,储备充分加上师友切磋,故收获丰硕。缪荃孙曾从李文田习版本和金石之学,因藏书丰富,文田也多次向他借书,《艺风老人日记》常见“顺德师”来“假书”(43)的记载。 同光时期边疆危机全面爆发,连科举考试也出现了相关题目。(44)许多学者纷纷究心朔方地形,以资政务。因西北为蒙古故址,故蒙元史研究亦同时勃兴。李文田不过为当时学者群体之一员,汪兆镛对此记载甚详: 顺德李文诚公讲求西北舆地,盖有感于中俄议界纠纷,发愤著书,非徒为矜奇炫博也。咸丰同治间,俄国乘我内乱,占据伊犁。……文诚因怵然於塞外山川形势险要,关系甚钜,而图籍多疏舛,乃萃二十年精力,考古证今,成书十余种,精博与何愿船秋涛、张石洲穆相埒。嘉兴沈子培中丞曾植与文诚书,商榷甚详。兆镛於哲嗣孔曼部郎斋头,见遗稿数十巨册,绳头细书,朱墨烂然,苦心孤诣,用意深远。(45) 既然“仲约之学,盖学通博”,(46)李文田具备良好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朴学训练,兼“元史在诸史中特为芜杂繁难,宜于施用此方法,故致力者独多”,(47)再加上时代风气的鼓荡,自然使文田从谈论钟鼎文字的京城名士过渡到讲求边疆史地的经世学者。 二、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 王桐龄云:“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48)论欧西部分不知确否,但中国往往如此。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同光时期的士大夫纷纷发挥经世精神,革新学术,其中以今文经学和边疆史地学势头最为强劲,前者思想资源多来自本土,后者则多取材异域。虽然“从某一角度上说,中国学术国际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波,似乎可以上溯到清代中叶对于西北地理和蒙元史的研究”,(49)但正因为受西学冲击最先最大,中国传统舆地学开始走向艰难的转型,并最终瓦解。在论述李文田标本意义之前,请允许笔者对清代边疆史地学作一回顾。 对于晚清边疆史地学,论者多认为乾嘉时发轫,道咸时兴盛,同光前期衰落,同光中后期复振,其演变既有学术内在理路的发展,也有现实外缘因素的需要。(50)王国维曾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写道: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51) 这段话用简明笔墨对清学进行鸟瞰,边疆史地学正为道咸以降的新学之一,而论其缘起,须溯源到“残明遗献思想”(52)乃至汉人“通经致用”。(53)要之,为经世思想在中西交冲(54)格局下渐次复活。 作为先驱的祁韵士在“羊肝下酒沙壶暖,牛乳烹茶木钵温”(55)的环境关注边陲史事与现实政治的沟通。魏源、龚自珍继任而起,“一反当时经学家媚古之习,而留情于当代之治教”,(56)到张穆《蒙古游牧记》、魏源《元史新编》、何秋涛《朔方备乘》三部代表作著成,标志边疆史地学达到全盛期。士大夫烹羊炊饼,剧谈西北,但当时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派,而只是因为共同关怀组成的兴趣圈子。再者,同光前期,学者们尽管“沉沉心事北南东”,(57)却极少有机会亲自到边疆考察游历。(58)最后,西方地理学系统介绍进中国,吸引部分学者转移研究方向。要之,人员的缺乏、资料的稀缺、西学的冲击驱使西北史地学者重回文献董理的旧范式,故斯学暂时处于衰落状态。 在短暂的沉寂后,同光中后期的边疆史地学重新焕发生机,涌现出沈曾植、李文田、柯劭忞、文廷式、洪钧、丁谦、屠寄等大批学者,陈寅恪“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59)可见其时盛况。 汪兆镛曾言李文田著书“数十巨册”,(60)若论其中最重要作品,则公推《元秘史注》。 《元朝秘史》又称《蒙古秘史》,本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蒙古族现存最早的史书,记载了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代远祖到窝阔台汗十二年,共五百余年历史,举凡蒙古族起源、生活、语言、风俗、军事、经济等,无所不包,具有极高史料价值,但一直藏之内府,冷僻无人知。乾隆时鲍廷博从《永乐大典》辑出十五卷,钱大昕为之作跋,称“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必于此书折其衷欤”,(61)后顾广圻据张祥云家藏“影元椠旧钞本”进行校勘,抄本辗转流传。(62)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张穆再次从《永乐大典》辑出全文,后来考释《元秘史》多以此为本。 李文田所据底本应为顾本,抄本借自盛昱,时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63)文廷式亦载此事:“此书为钱辛楣先生藏本,后归张石洲,辗转归宗室伯羲祭酒。余于乙酉冬借得,与顺德李侍郎各录写一部,于是海内始有三部。”(64)《元秘史注》“具有开拓性意义”,(65)对书中地理、种族、人物、习俗、年代等进行通盘考证,指出“击髀石”为蒙古旧俗,“罄身”义为光身,“势物”即“事物”(66)等,为后世研究蒙古史提供极大便利,故是书甫成即受到广泛称誉: 李先生所为《秘史注》,如发收梳,如玉就理,五百年来榛芜晦盲之径,乃豁然昭明矣。……顺德先生精于满、蒙、汉三合音之例,博综稗乘,旁摭金石,而一以声音通之。……钩心针棘之中,悬解希夷之表;辨方定位,确乎不易。以之订证《元史》,贯通邱长春、刘郁之《记》,无不迎刃而解者,斯真不朽盛业。大路椎轮,津导来学,匪徒忙豁仑氏之功臣者已。(67) 但李文田究竟不通外文,且抄本并非全译本,注释《元秘史》几乎纯用对音法,虽兼用金石材料,失误处亦开卷即见,如误认腾吉思海为里海,(68)擅改卷一“当初元朝的人祖”为“当初元朝人的祖”(69)等。总体而言,全书精当处为人物考辨,误考处则数地理方位最多。后来高宝铨撰《元秘史李注补正》及《元秘史补正续编》以正讹误,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翼辅之,丁谦则后来居上,驳正施著。沈曾植曾从文田问学,撰《元秘史补注》,补正疏失,并第一次提出“纽察脱察安”是蒙文“秘史”音译而非作者之名,纠正了从顾广圻、李文田到丁谦的错误,后王国维推定“脱察安”对音即“脱卜察颜”,证明曾植之论正确。张尔田校订《元秘史补注》,言“李书考订舆地,先生兼详史事,繁博不及李注而精审乃过之”。(70)可惜文田是时已去世,无缘见到此书了。 李文田最擅对音,如考证五端城为和阗:“《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忽炭’者,是也。《曷思麦里传》作‘斡端’,《拜延八都鲁传》亦作‘斡端’,《宪宗纪》则作‘扩端’,均此‘五端’二字之声转。今称‘和阗’者,是其地也。《明史》作‘阿端’,又沿古名作‘于阗’,均非两地”;(71)又言“铁勒”即“鞑靼”即“达达”(72)等。有《和林金石录》一卷,辑录自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释文精详,后经罗振玉校正。值得注意的是,李文田留意到了早期外来宗教入华情况,在《朔方备乘札记》“噉密莫末腻”条,称“噉密,即马哈默,亦即穆罕默德。末腻即牟尼,亦即末尼,此即天主教之祖也。末尼盖教主之称,犹曰和尚耳。《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二年(807年)正月,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设摩尼寺。摩尼即末腻对音”,(73)论摩尼教事甚确。在《论景教碑事》中直言“景教碑盖唐代之祆教”,(74)却属谬误。可见李文田虽熟悉金元故实,并在《至元译语》、《华夷译语》等书籍下了功夫,但总体而言,其治西北史地仍是“由通变假借以考见名物度数”,(75)未出朴学成规,且仅凭文献资料,没有祁韵士、徐松等实地目击的经验,故失误在所难免。 李文田注《西游录》“援据极博,引书几百种,备极殚洽”,(76)有范寿金补注本;《元圣武亲征录注》根据何秋涛稿本,经过沈曾植、文廷式、李文田、丁谦考释,王国维总其成。1940年香港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展出李文田手批书籍即有四十一种之多,其中三十余种为边疆史地著作,如《万里行程记》、《汉书西域本补注》、《俄国路程》、《宁古塔纪略》等,充分体现文田于斯学的深厚素养。(77) 昔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出,李鸿章即谓可“卑视仲约”,(78)在同光年间,李文田更多被认为是传统舆地学殿军。那文田是如何看待自身学术定位呢?孙雄在《李文诚公遗事》中追忆:“顺德李仲约侍郎师文田,辛亥后追谥文诚,师平日尝与门弟子言,他日得谥文敏,与董向光、张得天并传足矣,今追谥文诚,非师初愿所及也。”(79)早岁敬慕郑樵、王应麟、俞正燮的李文田,晚年愿望却是与董其昌、张照并传后世,可见其一生最大抱负实在金石书画方面。或曰中国文化的形成经过了反复的叠加与凝固,(80)其实个人历史的书写又何尝不是呢?“尤洽孰典章舆地,考索精详”(81)的是李文田;“书法唐贤,精严似信本”(82)的也是李文田,“屡典试事,类能识拔绩学”(83)的还是李文田。从学术史角度来讲,李文田应属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然而,此岂文田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文田哉?(84) 三、传统舆地学之终局 学术必有传承,传承首赖刻书,若无财力与势力相助,“盖棺有期,出版无日”(85)在中国古代并非罕见。 徐松算是幸运者,其门人缪焕章为缪荃孙之父,故艺风毕生致力刊布徐松著作;魏源撰写《元史新编》时,太平军兵锋至高邮,在祸乱不息的环境下,书稿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付印;连“通达时务,晓畅戎机”(86)的何秋涛,在咸丰十年(1860年)著成《朔方备乘》,却到光绪七年(1881年)才能刊行;至于李文田,若不是江标刻灵鹣阁丛书,《朔方备乘札记》、《和林金石考》亦不能付梓。当日有目无书者不知凡几,故对晚清西北史地学影响不可估计过高,虽然其标榜“经世”,但那时已风行“维新”矣。 既然当时士大夫喜谈史地,李文田又处于京师,必与当时胜流切磋学问。沈曾植在《译刻中亚俄属游记跋》提到:“曾植始于癸巳春见此书于顺德李侍郎斋中,侍郎以批本见示,属为详考,因签记数事于卷中,未能尽意也。”(87)后来曾植广治四裔诸夷史事,笺证《蒙古源流》,想必于文田著作启发甚多。叶昌炽求学心切,未通籍即由潘祖荫介绍,从文田学习碑版目录,“雅有知己之感”。(88)曾从总理衙门得和林石刻摄影本,正准备辑录全文,有所考释,后见文田《和林金石考》出,乃止。在《李文田仲约事实》中,叶昌炽回忆旧事,感叹文田奖掖后进,今也则亡。 晚清西北史地学者,对不通外文,只得拘囿于中文史籍一直耿耿于怀,文廷式即云:“他日中国文士能通西国语言,其考据必有出人意表者。”(89)沈曾植也认为边疆史地研究应“汇欧洲之精英罗诸几席……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90)洪钧于光绪十三年奉命出使俄、德、奥、荷,搜访各种西北史地资料,并组织人员进行翻译,苟有歧异,“乃复询之俄国诸通人,及各国驻俄之使臣,若英、若法、若德、若土耳其、若波斯,习其声音,聆其议论,然后译以中土文字”,(91)起草《元史译文证补》,回国后与李文田、沈曾植等参证商量,未料突然因病离世,稿本由陆润庠校对刊行。洪钧开创了引西人资料证补中土文献的先河,屠寄、柯劭忞接踵而上,继续推进边疆史地学的中西汇通。(92) 在同光士大夫倾力研究边疆史地时,历经明治维新的日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93)密切关注满、蒙、回、藏、鲜诸地。山县初男编著《西藏通览》,入民国仍不为国人所忽视;大谷光瑞、樱井好孝,根据新疆一手材料主成的《中亚探险》和《西域考古图谱》,又岂是局促于“本部十八省”的中国学者所能梦见?以至贺昌群也不得不叹息:“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相去远矣。”(94)西方学者更不待言,法人雷慕沙著有《于阗诚史》,沙畹、儒莲等翻译了《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探险家数不胜数,在库车发现的“鲍尔写本”更是轰动世界,李文田即批注过法国军官安邺的《柬埔寨以北探路记》。1902年,在德国汉堡成立了“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语言学和民俗学考察国际协会”,此时的中国学者,仅沈曾植尝试释读和林三唐碑,能与各国学者角力争先。(95) 葛兆光分析,晚清边疆史地学之所以未能转型为近代地理学,一是朝廷上下忙于救亡,忽视了这一重建中国的学术资源;二是与政治联系太紧密,缺乏国际交流,仅流传于少数精英。(96)最关键的还是学人本身,中国士大夫多被延续千年的经世传统笼罩,少有“古之学者为己”的精神。吴道镕撰《礼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铭》,言李文田忧国而死,“始终以文学结主知,始终不以文学掩大节,史传以淹雅称,未足概其生平也”,直豁地表明其“志在经世”。(97) 论者多强调晚清边疆史地学的经世色彩,谓其迫于事变,学者提倡“有意义之史学”,(98)但万不可忽视的是乾嘉朴学的影响,正是在学术惯性的推动下,西北史地学者才会逐渐把视野延伸到域外,逐渐突破前人窠臼。王国维称清学可分经世、经史两门,道咸以降之新学,“为此两派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99)所以晚清边疆史地学的辉煌,是经世和经史的融贯,是清代学术的逻辑发展,而非幡然一新的学问,是“乾嘉以来学术资源的一次能量绽放,是传统士人以传统学术来应对新问题的一声绝响”。(100) 尽管汉学巨擘伯希和也承认“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以惊吾欧洲之人”,(101)但在时人看来,边疆史地学早已是明日黄花。外国传教士联袂而至,近代地理学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相文在上海出版《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是“中国有地理教科书之嚆矢。两书流行达二百万余部,出于意料之外,由是海内谈地理者无不知之”。(102)出使异域的官员,也手持精良地图,腹藏地理知识,“在‘技’与‘用’的直接结合中,无需经由‘学’之中转”(103)了。到专注于“技”的学人出现时,政学之间的格局即被打破,传统舆地学宣告瓦解。当时像李文田这种博涉多方、难以归类的学人,遭遇到了“身份的焦虑”,以至于支伟成特去函章太炎,询其“宜属何家”。时代变了,问题也变了,“我心维新,我学守旧”(104)的屠寄也顺应世流,出版《中国地理教科书》。宣统二年(1910年)《地学杂志》创刊,其时李文田已去世十五年矣。 法国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105)晚清边疆史地学群体正是这样一个“艺术宗派”,李文田预身其中,全力发挥人生能量,著述宏富,时人嘉其为“经世之宗”。(106)然而时代呼唤的,不再是政学之间的经世之学,不再是松散业余的学术圈子,不再是“上以备谭边防奖王室者之用,下以为好古籍搜遗逸者之需”(107)的史地著作,而是规模齐整,“各怀集思广益之心,籍收增壤益流之效”(108)的近代地学会和专业研究人员。李文田有《咏万安宫遗址诗》:“阿尔台山白草肥,万安宫殿旧都畿。当年突厥兼回鹘,两代牙庭化夕晖。”(109)烜赫一时的传统舆地学,到了帝制末年,正如万安宫殿般,埋没春草,荒凉暮云。(110)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兴衰隆替原系自然之理,(111)李文田洵为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其谢世不久,中国近代地理学体系正式成型。只是传统舆地学的经世与经史精神并未随旧王朝一同覆亡,而是被后世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岑仲勉、顾颉刚、向达、冯承钧、方豪等承续,一次次地,随着时代脉动,魂兮归来。 注释: ①李渊硕:《顺德李文诚公行状》,民国十八年(1929年)铅印本。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17页。 ③梁基永:《李文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周清澍:《学史与史学:杂谈和回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9页。 ⑤梁基永:《李文田泰华楼及其藏书初探》,《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5期。 ⑥莫仲予:《李文田与泰华楼》,《岭南文史》1996年第1期。 ⑦朱伟:《李文田及其篆书〈诠赋篇〉赏析》,《书画艺术》2010年第5期。 ⑧李梦悦:《康有为与李文田交往事迹考辨》,《青春岁月》2013年第15期。可参阅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⑨胡亮松:《李文田修堤》,《江河文学》2013年第3期。 ⑩李骛哲:《李文田与“清流”》,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13年,第1-2页。 (11)李骛哲:《李文田与“清流”》,第36页。 (12)然而校勘不精,屡有失误。如第100页“野与仲约言前八仙后八仙之局,深以变更无惧”实为“夜与仲约言前八仙后八仙之局,深以变更为惧”;第262页“顺德李文诚公讲求西北兴地”实为“顺德李文诚公讲求西北舆地”;第262页“兆镛於哲嗣孔曼部郎齐头”实为“兆镛於哲嗣孔曼部郎斋头”等。 (13)马宗霍:《书林藻鉴》,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99页。 (1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15)在杨国强笔下,“清流”与“洋务”呈现出一种对立关系,见《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6-214页。 (16)章太炎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1页。 (17)李渊硕:《顺德李文诚公行状》。 (18)金梁辑录:《近世人物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54页。 (1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4页。 (20)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43页。 (21)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63页。 (22)晚清时北京盛行占卜,李文田既擅此道,自然受人关注。见孔祥吉《不问苍生问鬼神——清代北京的占卜风气》,《博览群书》2013年第3期。 (23)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0页。 (24)李骛哲:《李文田年谱长编》,见《李文田与“清流”》文末“附录”,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13年,第136页。 (25)王维江:《“清流”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26)章太炎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162页。 (27)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53页。又《孽海花》第十一回“潘尚书提倡公羊学,黎学士狂胪老鞑文”即影射其事,见曾朴著,宇文校注《孽海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28)章太炎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162页。 (29)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30)李渊硕:《顺德李文诚公行状》。 (31)李骛哲:《李文田年谱长编》,第57页。 (32)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82页。 (33)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540页。 (34)陶湘:《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小传》,明文书局,第751-752页。 (35)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90页。 (36)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738页。 (37)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2522页。 (38)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十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39)传李文田曾作《红棉诗》讥刺张荫桓:“尝闻槐棘誉三公,几见红棉位少农。百粤英雄标独色,一条光棍起平空。繁华毕竟归零落,衣被何曾及困穷。莫谓欲弹弹不得,二槌终日砍长弓。”见钱仲联《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63页。 (40)张荫桓著,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版,第180页。 (41)张之洞挽李文田:“士林奉公为师范,朝列推公为端人,独忧四海多艰,屡上青蒲陈谏疏;词馆与我相切磋,粤疆与我商战守,深痛十年不见,徒悬朱鸟耿文章。”见梁基永:《李文田》,第33-34页。 (42)李思纯:《元史学》,上海书店1974年版,第76页。 (43)李文田所借书目,计有《明稗史》、《永嘉召对录》、《甲乙纪事》、《行朝录》、《雍录》、《卫藏通志》、《法藏碎金录》、《地图综要》、《胡南志》、《破邪集》等。 (44)如光绪六年(1880年)会试第五策即以边疆史地为题,试后沈曾植“归家自熹”,李慈铭也自诩甚高。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77页。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会试,李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刺取自注《西游记》中语发策。举场莫知所自出,惟梁启超条对甚详”。梁落榜,李批其卷“还君明珠双泪垂”,后二人相见,“李闻其议论,乃大不喜。语人以此人必乱天下”。见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谭荟》,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96-97页。 (45)汪兆镛:《李文诚公遗书记略》,见《碑传集三编(一)》卷五,明文书局1985年版。 (46)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390页。 (47)李思纯:《元史学》,第52页。 (48)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49)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0页。 (50)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侯德仁:《清代边疆史地学》,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1)王国维著,黄爱梅校点:《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502页。 (5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页。伦明曾到泰华楼访书,言李文田“好搜明季野史”。见《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53)如皮锡瑞即言“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为万世教科书”,见《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页。 (54)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卷首。 (55)祁韵士著,李广洁整理:《万里行程记(外五种)》,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5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90页。 (57)钱仲联等:《元明清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5页。 (58)此时西方探险家联翩而至,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31-41页。 (59)陈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2页。 (60)汪兆镛:《李文诚公遗书记略》。 (61)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潜研堂文集·跋元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页。 (62)乌兰:《〈元朝秘史〉版本流传考》,《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63)同上。 (64)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65)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前言》,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页。 (66)张旭:《〈元朝秘史〉词汇探析》,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67)乔治忠,朱洪斌:《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88页。 (68)李文田注:《元朝秘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69)李文田注:《元朝秘史》,第1页。 (70)张尔田:《元秘史补注》校记,见北平古学院《敬跻堂丛书》。 (71)李文田:《西游录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72)李文田:《朔方备乘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73)李文田:《朔方备乘札记》,第13页。 (74)见杨荣鋕《景教碑文纪事考正》卷一,1895年。 (75)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53页。 (76)范寿金:《西游录略注·跋》,见《丛书集成续编》第244册《东北边防辑要》,新文丰出版公司,第249页。 (77)梁基永:《李文田泰华楼及其藏书初探》。 (78)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七》,第191页。 (79)孙雄:《李文诚公遗事》,见《碑传集三编(一)》卷五,明文书局。 (80)葛兆光:《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文史哲》2014年第2期。 (81)闵尔昌:《碑传集补(一)》,明文书局,第318页。 (82)闵尔昌:《碑传集补(一)》,第317页。 (83)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2417页。 (84)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感叹:“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见陈寅恪《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2页。 (85)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04页。 (86)何秋涛:《朔方备乘(一)》,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87)钱仲联:《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二)》,《文献》1991年第4期。 (88)郑伟章:《书林丛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30页。 (89)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第12卷,广陵书社1990版,第176页。 (90)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388页。是书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91)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92)马明达,李峻杰:《洪钧史迹述略》,《暨南史学》2013年。 (93)葛兆光:《宅兹中国》,第238页。 (94)贺昌群:《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47页。 (95)胡逢祥:《沈曾植与晚清西北史地学》,《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 (96)葛兆光:《宅兹中国》,第250页。 (97)吴道镕:《礼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铭》,见《碑传集三编(一)》卷五,明文书局。 (98)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页。 (99)王国维著,黄爱梅校点:《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第503页。 (100)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306页。 (101)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3页。 (102)张业修主编:《张相文: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版,第327页。 (103)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298页。 (104)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 (105)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2页。 (106)范寿金:《西游录略注·跋》。 (107)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7页。 (108)吴传钧,施雅风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109)李文田:《和林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页。 (110)温庭筠有句:“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见陈伯海《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3页。 (111)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读书》199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