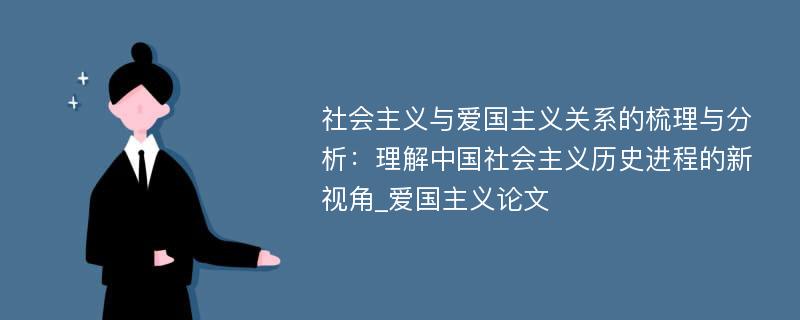
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关系的梳理与解析———个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历史进程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关系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整整80个年头。尽管时代变迁,风云变幻,党始终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伟大旗帜,领导中国人民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不断地推向新胜利。长历史、宽视域地梳理和把握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一个有意义的新视角。
一、中国古代历史上原始社会主义理想和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梳理
“建立一个消灭剥削制度,人人平等的社会的理想,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是一个古老的理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66页。)这一理想曾在“乌托邦”的荒野里徘徊了几个世纪。正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版,第724页。)亦即“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和“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304页。),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理论来源。这种“抨击”和“主张”是人类的应激本能和社会发展的潜在动力,并不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独有。在古代中国,也有一些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宝贵的思想萌芽,毛泽东称之为“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注: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版,第628页。),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原始社会主义思想。
由此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则原始社会主义理想的火花可谓丰富,传统可谓绵长。如《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尚书·大禹谟》中“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的太平盛世、陶渊明《桃花源记》中人人“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历代农民起义中“等贵贱”和“均贫富”的主张等等,无不折射着古人对“现存社会”的强烈批评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希冀。毋庸置疑,这种带有强烈平均和空幻色彩的思想,深深根植于小生产意识沃土之上,是对封建社会罪恶现象的本能反应和对新社会美好幻想的跳跃隐现,是潜意识的、肤浅幼稚的思想萌动,尚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而属于毛泽东、邓小平谴责的“农业社会主义”的范畴。另一方面,对旧社会的强烈批判和对新社会的积极主张,或说原始社会主义理想,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重要牵引力。以之为指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苦,丰衣足食。”(注: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版,第628页。)即说,在新生产力、先进阶级和科学理论没有出现前,此类思想对反对封建剥削压迫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是不可或缺和难能可贵的。此外,尽管它本身没有发展成为完善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其指导下的实践也避免不了失败的悲壮命运,但它幻明幻灭的存在却日渐内化为炎黄子孙的心理潜质和民族特质,最终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珍贵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注: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047页。)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新社会的憧憬外化为社会实践时,很大部分表现为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情操和行为。如“厚生重德”的民生主义、“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弘道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献身精神、“安无忘危,存无忘亡”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等等。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危急时刻,爱国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都是实现偌大中国协调整合、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特别由于封建王朝的忠君思想和狭隘民族主义,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思想,只能是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
由上观之,原始社会主义理想的牵引和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推动,在中国久远悠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价值取向和价值功用都有着一种不为先人觉察而又脉络清晰的“暗结”。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民族危难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蓬勃发展了80多年。但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误会”,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行程,造成了中国人民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救亡图存道路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基础。须知,“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111页。)
有明以降,封建体制再也解决不了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日益僵化堕落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惰性和桎梏。特别是“康乾盛世”后短短百年内,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造成了中国在世界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日渐边缘化。沉睡的中国在西方列强隆隆的炮声中开始了自己屈辱辛酸的近现代史。但是,中国近现代史更是中国人民一部伟大光荣艰辛悲壮的觉醒史、探索史和奋争史。“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富于爱国传统的中国人民在黑暗和血腥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救国救民道路的寻求,各阶级阶层的各种思想方案都登上了广阔的历史舞台,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一股强劲的流派。
单就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演进来看,近代中国先后出现了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大同书》中“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等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并部分地以此为纲领掀起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高潮,每次高潮之后还依次跟有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和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总体上看,其一,人们的探索异曲同工,即自从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却又殊途同归,即悲壮失败,于是人们产生了对向西方学习的怀疑;其二,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在传统朴素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因此,“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712页。);其三,中国无产阶级的潜滋暗长,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和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客观态势;其四,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方案,表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由“暗结”到“明合”的趋势。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469页。)相同的国情使中国人眼界豁然开朗,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人民爱国主义道路上的全新选择。一部分知识分子由激进民族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嬗变,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趋势的重要体现。他们敏感地把握住历史的客观趋势,并担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成为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由“暗结”到“明合”过渡的桥梁,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进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桥梁。
三、核心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选择马克思主义,只是找到了解放中国人民最好的武器,并不意味着找到了解决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并不意味着此后的发展一帆风顺。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明合”过程中又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现象,亦即“融合”与“偏颇”。关键就在于,作为拿着“最好的武器”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在依托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解读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一把熠熠生辉的钥匙。正是在毛泽东所做的两件大事上,即在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上,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融合”与“偏颇”。
毛泽东有着独立的人格和思维,他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眼睛”和“头脑”观察分析中国问题的同时,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在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他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交汇融合”(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2版,第163页。),亦即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有机融合,在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新中国。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信念渐渐扎根于中华大地,为自己赢得了生存发展的雄厚基础和广阔空间,日渐变成中国人民的共同信仰,并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但是,毛泽东在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民族解放到民族振兴的转换中,亦即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却犯了一系列错误,甚至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严重错误。其原因很多,根本的一条就是邓小平说的“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注:龚育之:《关于时代主题》(上),《学习时报》(北京)2000年11月27日。)。具体来说,就是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东西中国化、实践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东西抽象化、教条化。“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中。”(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当然,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爱国者的错误,但这些错误毕竟使中华民族丧失了几次大的历史发展机遇,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造成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顿挫失落。
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
“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实行,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渐步入正轨,也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20年来中国的发展,就内部条件而言,是一个历经百年磨难和20多年自身失误后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的探索式发展,起点低,任务重,困难大,风险多;就外部环境而言,是一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殊异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国际竞争剧烈,外在压力巨大。但中国的发展又是一个实现了年经济增长率低则百分之六、七,高则百分之八、九的高速度“膨胀式”、“赶超式”的发展,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复兴中华民族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和初步胜利。成绩和胜利的取得,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更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指引。
邓小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和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光辉典范,他的最大贡献就是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复兴中华民族的崭新局面。邓小平理论不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也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有机融合,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爱国就必须把祖国引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社会主义道路——两者在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上统一起来;第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强大则是当代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历史追求——两者在历史发展的根本任务上统一起来;第三,社会主义体现了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理想和实践,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又都是希望人民幸福富裕的——两者在社会实践的价值取向上实现了统一;第四,“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动中国发展的伟大精神动力”(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是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两面光辉旗帜——两者在牵引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作用上统一起来;第五,社会主义赋予爱国主义以崇高的理想和崭新的时代内容,爱国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广泛深厚的阶级基础——两者在相互为对方提供保证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总之,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具有“中国特色”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是爱国主义事业不断顺利发展的方向保证,“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注:江泽民:《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49页。)。从根本上讲,两者在本质上的统一是指两者有机融合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是这一伟大实践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既然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爱国就要爱社会主义。“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注: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051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五、新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复兴和民族复兴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巩固
“在新的世纪,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抓住机遇,只争朝夕,知难而进,开拓进取,坚定不移地实现我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2页。)新世纪中国发展将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严峻挑战,中国人民以什么样的精神姿态进入新世纪将直接关系着中国能否在民族复兴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
正当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复兴中华民族道路上奋勇前行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所谓“信仰危机”,二是民族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长期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但是苏东剧变的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封建遗毒的死灰复燃和西化思潮的泛滥流行,使少部分人包括少数党员干部信仰淡化、理想模糊,甚至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失望。但是,“我们的事业无比壮丽,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注:江泽民:《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浙江、北京代表团讨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3月15日。)。“信仰危机”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悲观失望更要不得。民族虚无主义,即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丧失信心;崇洋媚外,这更是极少数人的言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是中华民族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动力。鲁迅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就坚定地说:“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可以,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9页。)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先后豪壮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注: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太白》第1卷,第3期,1934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然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61页。)“人类在进步,中国在进步。在21世纪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定能够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3页。)这才是中国人民精神姿态的真实写照,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六、驳西方关于“中国共产党用民族主义代表社会主义”的谰言流语
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关于“中国共产党正在用民族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谰言流语缕缕不绝于耳。对这样的带有攻击性的猜疑议论要认真分析和严肃澄清。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西方有人挖苦说,苏东剧变使“卡尔·马克思成了人们打趣、讽刺和表达怀旧情绪的对象”(注:江泽民:《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香港代表团讨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3月9日。)。他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战斗力和吸引力,它将成为一种学术而不是信仰;20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在20世纪内灭亡。诬称“北京领导人目前正在努力以能引起大众共鸣的民族主义取代谁也不相信的马克思主义”(注:[美]詹姆斯·格拉斯曼:《卡尔·马克思无形的手》,《参考消息》1998年4月3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要利用社会主义以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作为“一种可供利用的‘追求富强’的工具”(注:[美]《华尔街日报》(纽约)1996年8月2日。)。这些议论的要害,一是认为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二是认为中国用民族主义填补了放弃社会主义后的信仰真空。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苏东剧变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注:[美]阿里夫·德里克:《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第11页。)。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并不讳言。但最大的失败不是完全彻底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不但经受住严峻考验,度过重重难关,而且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整个国家民族生机勃勃。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41页。)宣称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是西方反共势力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
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大发扬:第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气概之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因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而大大激发出来,民族自尊自信感空前高涨。第二,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打、压、封”和“西化”、“分化”政策,而“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5~346页。)。第三,苏东剧变后,西方反共势力几乎把意识形态的竞争压力全部倾泻于唯一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身上,而担心中国发展强大会对自己造成威胁的西方大国又把国家民族“零合博弈”的竞争压力覆盖于中国身上,中国发展遭受双重挤压。尽力消解和突破这种压力束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重要的是,“我们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而是尊重其他国家民族利益、借鉴其他国家民族发展经验,反对霸权强权、维护世界和平并以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为已任的爱国主义,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和弘扬爱国主义不仅并行不悖,而且是相得益彰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共产党用民族主义代替社会主义”。
标签:爱国主义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毛泽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