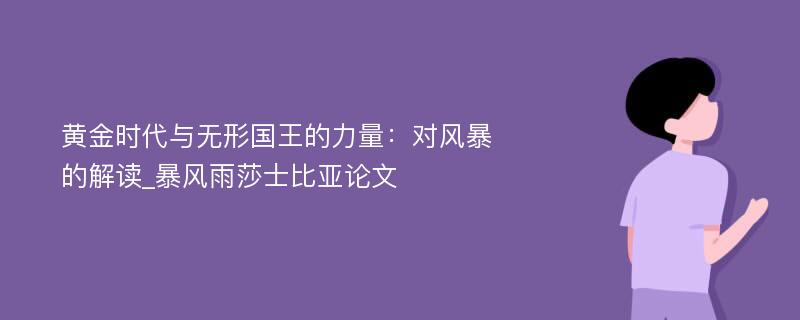
黄金时代与隐身的王权——《暴风雨》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权论文,黄金时代论文,暴风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暴风雨》一剧始于普洛斯彼罗通过魔法制造出来的一场海上风暴,这场风暴击散了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的船队,迫使阿隆佐本人及其近侍随从弃船逃上了附近的一座荒岛。第二幕第一场,这些人在荒岛上漫无目的地游荡。阿隆佐相信儿子腓迪南已经葬身海底,情绪十分低落,为此他的大臣贡扎罗尽力找出各种话题来转移他的思绪。贡扎罗看到这海岛似无人居住,便把话头扯到殖民地上来,下面这段关于乌托邦的遐想由此引出,本文的探讨也将从这段遐想与该剧主线情节和主题思想之间的关系开始:
贡扎罗 如果这一个岛归我所有,大王——
塞巴斯蒂安 他一定要把它种满了荨麻。
安东尼奥 或是酸模草,锦葵。
贡扎罗 而且我要是这岛上的王的话,您猜我将做些什么事?
塞巴斯蒂安 让自己很清醒,因为没酒可喝。
贡扎罗 在这个国家我要实行一种与众不同的制度;我要禁止一切贸易;不设地方官;没有文字;财富、贫困和雇佣都要消灭;契约、承袭、疆界、区域、耕种、葡萄园,这一切都不存在;也用不着金属、谷物、酒和油;职业也要废除,所有的人都不做事;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都天真而纯洁;也没有君主——
塞巴斯蒂安 但是他说他是这岛上的王。
安东尼奥 他这个国家的尾巴把开头给忘了。
贡扎罗 大自然的一切产物都不须用血汗劳力获得;叛逆、犯罪、剑、戟、刀、枪炮,以及一切武器的使用,一律杜绝,但是大自然会自己产出一切,应有尽有,来养育我那些淳朴的人民。
塞巴斯蒂安 他的人民中间没有结婚这回事吗?
安东尼奥 没有的,老兄;大家整天闲荡,尽是些娼妓和无赖。
贡扎罗 照着这样的理想统治,我的国家将足以媲美往古的黄金时代。
塞巴斯蒂安 上帝保佑吾王!
安东尼奥 贡扎罗万岁!①
在研究文献中,评论家在谈及这段小插曲时多会提到来自蒙田《随笔》第一卷第31章《话说食人部落》的影响。一般认为,莎士比亚不但从这篇文章的标题(“Of the Cannibals”)中化出了剧中重要人物凯列班(Caliban)的名字,②而且还从蒙田对西印度群岛土著部落的描绘中借来了贡扎罗理想国中的种种细节(下面引文中标出的英文词都曾出现在贡扎罗的话中):
他们[过去的诗人和哲学家]想象不到人性可以如此简单纯净,也想象不到社会的维系可以如此不依赖于人工和智巧。我要告诉柏拉图,那是一个没有任何贸易(traffic)的国家;那里不识文字(letters),不晓算术,没有官吏(magistrate),没有役使(service),不分贫富(poverty,riches),不订契约(contract)……人们不事劳作(occupation)而只享清闲(idle),一切共有,不讲亲疏……酒、谷物、金属(wine,corn,metal)一律不用,谎言、背叛、伪饰、贪吝、嫉妒、中伤,一概未闻。与这完美的社会比起来,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城邦(commonwealth)也不免相形见绌。③
不难看出,莎士比亚几乎把蒙田的整段文字都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贡扎罗口中。贡扎罗是个好心的老糊涂,作者让他说出这番话,再安排心性恶毒但眼光犀利的塞巴斯蒂安和安东尼奥不断从他的话中挑出滑稽可笑、自相矛盾的地方,其意图显然是要让观众对蒙田的观点产生一种“颠覆性的、冷嘲式的反应”④。蒙田相信自然状态下的人具有一种自然的美德,他们无须复杂的制度去规范,自然而然就能够和谐安宁地生活在一起;反倒是随着“人工和智巧”不断增加,人开始变得腐化,也就日益需要更多的人为手段去确保社会的维系和正义。莎士比亚对这一观点无疑是抱有深刻怀疑的。《暴风雨》中与自然最接近的人是凯列班,可在他身上我们却难见到自然美德的踪迹;相反,他是一个“不曾学一点好,坏的事情样样都来得”(《暴》:Ⅰ.2.351-353)的蠢物;而若要把一群像他这样的人聚集成一个社会,我们很难想象蒙田所描绘的那种秩序还能自然而然地生成。从这个角度看,本文开头提出的关于这段插曲与该剧主题思想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有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答案:在一部强调人性中的恶难以根除的作品中,贡扎罗的迂阔幻想让人回想起那使得一切乌托邦都难免成为空想的人性现实。
不过这个解释依然忽略了一个要紧的细节,因此有可能并不全面。贡扎罗的空想虽然大部分取自蒙田,但其中关于王权的一笔却是莎士比亚自己添加的。这一添加看似随意,其意义却很值得我们注意。王权(kingship)是《暴风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如果说凯列班身上展现出的人的“不可教性”(unteachability)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与之紧密相联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人性冥顽不灵的前提下(设想每个人内部都有一个凯列班)如何运用权力把美德“教”会给人——这个权力的最高形式当然就是王权。不过相对于王权的重要性而言,贡扎罗关于这个题目的言论却十分荒谬可笑,也是他现出的一个破绽:老人一开始想象自己是岛上的王,后来又称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王,但总结的时候又说自己要照着这样的理想来“统治”。这样的逻辑漏洞当然无法逃过塞巴斯蒂安和安东尼奥的眼睛,贡扎罗的乌托邦也就在众人的嘲笑中顷刻坍塌。
作为观众,我们也很容易被裹挟着加入到嘲讽者的行列中去,不过细想一下,贡扎罗的话或许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悖谬。事实上,我们只需稍稍行使一点阐释的自由,把他所说的“岛上没有国王”理解为“像是没有国王一样”,那么他的悖论就会立刻变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陈述。如果我们换一套语汇,这个悖论实际上可以表述为:作为一种使人向善的工具,王权在运用到极致时应当是一种化人于无形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最理想的王权统治下——即所谓“郅治”或“黄金时代”,被统治者在趋善的同时应当是感觉不到有外力在迫使他们趋善的;一切都会像自然发生的一样。⑤如此一来,贡扎罗就不再是犯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错误,他实际上在无意中说出了一个关于王权的深刻真理,而这个真理却被所有在场的人(包括他自己)忽略了。
但这真的是莎士比亚对王权的看法吗?这需待下文考察整剧后再做评估,但如果它确实是的话,那么上文得出的关于他对《话说食人部落》中自然状态(或“黄金时代”)的看法的结论就需要做大幅修正了。当然,即便在新的假设下,莎士比亚总体上仍旧会对蒙田所描绘的那种自然状态抱怀疑态度,但他会承认某种特殊的“人工和智巧”或许可以把已经被文明腐化了的人带回到一种接近于此的状态中去(因而他的态度又不同于塞巴斯蒂安和安东尼奥那种纯否定性的嘲讽)。如果我们用“技艺/自然”(art/nature)这对概念来做总结的话,莎士比亚的看法应该是:重回“黄金时代”归根结底要依靠“技艺”(即“the art of kingship”)而非“自然”来实现,但这须是一种特殊的、能够使自己看起来像“自然”一样不落痕迹的技艺。按照昆体良的说法,能让自身隐形的技艺是最高超的技艺(The height of art is to conceal art)⑥;而唯其具有自我隐身的特点,这种技艺也最易于被人熟视无睹甚至遗忘。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蒙田恰恰是忽略和遗忘了这一技艺,而莎士比亚则通过贡扎罗的一个“疏漏”把被忘记的东西再一次揭示了出来。
不过蒙田又是从什么“起点”上开始遗忘的呢?我们在此不妨以柏拉图关于黄金时代的一段描写来补足这逻辑上缺失的起始环节。
蒙田在《话说食人部落》中曾多次提到过柏拉图(见前面引文),但后者关于黄金时代的论述却出现在此文并未涉及的《政治家篇》中。在柏拉图那里,黄金时代指的是宙斯之父克洛诺斯(Kronos)统治宇宙的时期。那时,宇宙间所有的事物——动物、植物、星球——都被分配给它们的守护神专职照看。对于这其中的动物而言,“诸守护神就像牧者,依种、群对它们进行划分,每一个群都由一个守护神照料,专责满足它们所有的需求;在这样的照料下,动物们野性尽脱,牧群中不再有弱肉强食,也无战争和内讧。”作为动物世界中的一个种群——
人也有专门的神亲自照料,正如现在的人类作为一种更为神圣的动物也照料着比他低等的动物。在神牧的时代,没有任何政治制度的设置,人也不娶妻生子,因为所有人都是从大地获得生命的……(在那个时候)树上林中有食之不尽、品类繁多的水果,它们并非人工种植,而是从大地中自发生长的。人们大部分时候被放牧于野外,无衣无床,但由于那个时候四季不分,故不会有痛苦,大地生长的丰茂草原便是他们柔软的被褥。⑦
引文的后半段让人不禁会联想起蒙田和贡扎罗所描绘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同样,这个黄金时代里也是没有“政治制度的设置”的(因而也就“没有君主”),但柏拉图为这种情况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即当时的人类是由比其智慧高出许多的守护神悉心照料着的。也就是说,这种完美的无政府状态并非人类自然达至,而是一种超凡但不落痕迹的“神牧”的结果(彼时的人类并不一定知道他们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依赖于神的)。如果说即便在黄金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也都需仰赖守护神的照料,那么在人已然堕落的情况下,想要回复到近似于原初的状态中去,神一般的智慧和技艺的介入就更是必不可少了。从贡扎罗的话中透露出的信息看,莎士比亚并没有像蒙田那样“忘记”这一点。
贡扎罗无意中道出的真理并未引起任何一位在场者的注意,同样,这群人中也没有任何一人意识到,此时此刻,一种超凡的力量——亦即普洛斯彼罗的魔法——正密切注视和掌控着他们的行动并把他们的命运一步步地推向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结局。也就是说,在贡扎罗不经意间触碰到“看不见的王权”这一话题时,这样一种王权恰好正在他和他的同伴们身上发生着作用。
与贡扎罗想象中的君王不同,普洛斯彼罗并没有打算在荒岛上建立起一个堪比黄金时代的理想国度;相反,作为被篡夺权力的米兰公爵,他在剧中的一切行动都是着眼于恢复他在远方故国的合法权位的。要夺回权位,他面对的最大障碍当然是非法占据着米兰公爵宝座的亲弟安东尼奥及其同盟者、当年共谋驱逐他的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如今,命运的机缘将这两人送入了他魔法所及的范围,普洛斯彼罗的复国大业终于等来了难得的良机。安东尼奥和阿隆佐都是普洛斯彼罗的仇人,如果后者选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凭借其手中“狂暴的魔法”(《暴》:Ⅴ.1.50),他应当可以轻松夺回失去的公国并给予坏人应得的惩罚。不过,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普洛斯彼罗深知和解比暴力更有助于达成持久稳固的和平。和解的必要前提是罪人真诚地忏悔,因此对于普洛斯彼罗来说,最理想的行动方案莫过于迫使他的敌人先行悔罪,然后再由他本人适时地伸出橄榄枝并宣布两个仇家的子女米兰达与腓迪南已坠入爱河,即将成礼完婚的消息。这样一来,不但敌人交出权力将是理所当然之事,年轻一代的结合也将消弭积年的宿怨,巩固当下的和解并为未来两国间更紧密的联合提供契机。
不过这里的关键是普洛斯彼罗要让他的敌人悔罪。事实上,尽管莎士比亚让这一结果的达成看起来好像顺理成章,但仔细想来,这却远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莎学家保罗·康托尔曾提请我们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普洛斯彼罗没有按剧中那种方式行动,而仅仅是“对驶近海岸的王家船队挥挥手说,‘我是普洛斯彼罗,就是你们曾打算谋害的那位米兰公爵,我现在想要收回我的权力,你们不会反对吧’,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⑧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靠敌人自发地悔罪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如果普洛斯彼罗没有强大的魔法作支持来创造一个接一个的情境把这些人逐步引上忏悔之路的话,他是根本无法实现其回归米兰、重掌权力的目标的。而这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魔法在普洛斯彼罗的计划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它实质上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关于这个问题,剧中至少有两段情节给了我们明确的提示。在第一幕第二场,腓迪南拔剑意欲挑战粗暴对待他的普洛斯彼罗,但后者的魔法立刻使他感到“浑身无力,软弱得完全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暴》:Ⅰ.2.487)。在第五幕第一场,阿隆佐及其随行也都被魔法制服,成了普洛斯彼罗的囚徒。用爱丽儿的话来说:“在荫蔽着你的洞室的那株大菩提树底下聚集着这一群囚徒;你要是不把他们释放,他们便一步也不能移动。国王,他的弟弟和你的弟弟,三个人都疯了;其余的人在为他们悲泣,充满了忧伤和惊骇”(《暴》:Ⅴ.1.9-14)。这两个例子清楚地显示,普洛斯彼罗的魔法本质上是一种高效的强制力;通过它,魔法师能够轻易地使他的对手处于毫无还手之力的弱势。不过,它同时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强制力,其特殊性在于,尽管它可以让普洛斯彼罗控制其对象,但他的对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觉察不到自己实际上是处于某种人力的控制之中。换句话说,普洛斯彼罗的魔法是一种能够自我隐身的强制力。在第一幕第二场,普洛斯彼罗向米兰达讲完父女俩过去的遭遇以及眼下这场暴风雨的缘由之后,施魔法让女儿睡去:“别再多问了,你已经倦得要睡去;放心睡吧!我知道你身不由主。”(Thou art inclined to sleep; 'tis a good dullness,/And give it way.I know thou canst not choose.[《暴》:Ⅰ.2.185-186])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者让普洛斯彼罗说出这句台词只是为了告诉观众他对米兰达做了些什么,而米兰达本人是不知道父亲对她施加了催眠术的。她所能感到的只是有一种甜美的困倦(a good dullness)向她袭来,她没有选择,只能顺从。也就是说,虽然事实上米兰达是被“强制”入睡的,但这种强制力却是隐身在自然的倦意背后的。
广而言之,在剧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普洛斯彼罗的强制力都是躲藏在某种“自然”现象背后的:当他需要强迫仇人来到岛上时,他就制造出一场自然的暴风雨把船只掀翻;当他需要唤起沉睡中的贡扎罗以粉碎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的弑君阴谋时,他就施法让其被“一种很奇怪的蜜蜂似的声音”(《暴》:Ⅱ.1.317-318)惊醒;而当他需要让阿隆佐想起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并让他认识到当下发生的一切灾难都是对这一罪行的惩罚时,他就在后者的头脑中制造出一个恐怖的幻觉:
啊,那真是可怕!可怕!我觉得海潮在那儿这样告诉我;风在那儿把它唱进我的耳中;深沉而可怕的雷鸣在向我震出普洛斯彼罗的名字,它用洪亮的低音宣布了我的罪恶。这样看来,我的孩子一定是葬身在海底的软泥之下了;我要到深不可测的底极去寻找他,跟他睡在一起。(《暴》:Ⅲ.3.95-102)
对于意在迫使其敌人悔罪的普洛斯彼罗而言,这样一种自我隐身的强制力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工具。细究起来,所谓“迫使敌人悔罪”其实是一个颇有些自相矛盾的概念:真正的忏悔应该是一种油然发自内心的情感,而在外力强制下作出的忏悔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伪装,一种为了避免受到进一步伤害而摆出的姿态。但问题是,真正的忏悔在现实中是可能的吗?事实上,难道宗教所谈论的忏悔不也与畏惧密切相关,是人处于绝境(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绝境)中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心理反应?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主司报应、手握重权的神的存在,忏悔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在人心中“油然”而生呢?在剧中,莎士比亚并没有直接表现普洛斯彼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态度,但这些疑问所指向的结论却与普洛斯彼罗从凯列班身上得出的关于人性的看法高度一致。普洛斯彼罗起初希望教化巫婆之子、半人半兽的凯列班,但在屡屡遭遇挫折后终于认识到,“好心肠不能使你感恩,只有鞭打才能教训你”(《暴》:Ⅰ.2.344-345);“像你这样的下流胚子,即使受了教化,天性中的顽劣仍是改不过来,因此你才活该被禁锢在这堆岩石中间”(《暴》:Ⅰ.2.358-362);而凯列班也只有在面对这样的强力时才肯乖乖服从:“我不得不服从,因为他的法术有很大的力量,就是我老娘所礼拜的神明瑟底堡斯也得听他指挥。”(《暴》:Ⅰ.2.372-374)很多评论家认为凯列班这个角色代表了人性中某种冥顽不灵的因素。⑨如果这种理解是成立的话,那么从凯列班身上看清了人性真相的普洛斯彼罗在剧中采取一种以强制为主的策略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良心固然是“胸中的神明”,但不陷于绝境(necessity)之中,一个人的良心是很难自动发现的。⑩
不过仅仅采用强制远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完全依靠对象自发地悔罪与纯用暴力迫使对象就范之间还有一条折中路线,那就是,在运用强力将对象置于绝境的同时,发挥魔法自我隐身的特点,制造出一系列精心设计好的情境,藉此操控对象的情感,最终把他们身不由主地(就像米兰达“身不由主”地进入梦乡一样)引导到“忏悔”的心理状态中去,使一切看起来好像是自发完成的一样。因此,我们看到普洛斯彼罗先是用风暴切断阿隆佐的归家之路,让他和随从在荒岛上遭遇种种惊吓与磨难,再通过化成凶鸟的爱丽儿在风雷交加中当面历数他过去的罪孽并告之以腓迪南溺亡的假消息。这样,在经历了忧虑、焦急、悲伤、恐惧与惊愕之后,阿隆佐终于被逼入了绝望和疯狂的深渊。而当他的意识从疯迷中恢复过来时,他发现自己又与过去的敌人狭路相逢;不过这位强敌非但不思报仇雪恨,反而大度地向他的囚徒伸出了橄榄枝并用一件意外的礼物(腓迪南与米兰达即将成婚的喜讯)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忏悔与和解对于此时的阿隆佐来说恐怕就像瓜熟蒂落一样自然。事实上,他本人也会相信自己的忏悔是绝对真诚的,但观众不应该忘记,他眼下的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普洛斯彼罗精心操纵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即便他内心深处并无忏悔之意,敌强我弱的形势也会迫使他选择韬晦策略以避对手的锋芒。也就是说,即使魔法作为操控情感的工具在他那里没有见效,魔法作为粗暴的强制手段也足以迫使他接受普洛斯彼罗做出的安排。
最后这一点在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两人与阿隆佐同是普洛斯彼罗意在“改造”的对象,但直到终场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哪怕是假装的悔意。不过普洛斯彼罗对此早有准备,面对桀骜不驯的弟弟,他只是说:“我饶恕你最卑劣的罪恶,一切全不计较;我单单要向你讨还我的公国,我知道那是你不得不交还的”(《暴》:Ⅴ.1.131-134)。普洛斯彼罗确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让安东尼奥就范,而善于审时度势的安东尼奥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既然没有其他选择,他和塞巴斯蒂安于是便识趣地选择了沉默。
作为一种自我隐身的权力,魔法使普洛斯彼罗能够在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同时,让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某种自发产生(spontaneous)的道德复苏的自然结果。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善的复归的“自发性”。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普洛斯彼罗除依靠魔法之外,还巧妙地运用了“天意”观念对人心的强大影响力——要让一个人屈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他深感自己面对的是不可违的天意,抗拒和阻力就会大大减少。尽管两者都可以说是人在绝境下做出的选择,但在一般观念中,前者属于强制,而后者则算作一种内心自发的改变。
“天意”是莎士比亚晚期四部浪漫剧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但就天意在剧中彰显的方式而言,《暴风雨》与其他三部作品相比却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在其他三部戏中,天意都是由一位神明直接宣示给剧中人的(因此可算作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向主人公透露玄机的是黛安娜女神,她“在幻象中向配力克里斯显现”,指示他前往以弗所并按照她的话行事,“[这样做]你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幸福,否则你将要永远在悲哀中度日”(《配》:Ⅴ.1.240-249)。《辛白林》中托梦给普修默斯的是大神朱庇特,他在雷电中下凡,告诉受尽磨难的主人公命运的转折即将到来:“人世的事不用你们顾问,一切自有我们神明负责;哪一个人蒙到我们的恩眷,我一定先使他备历辛艰;你们的爱子他灾星将满,无限幸运展开在他眼前。”(《辛》:Ⅴ.4.100-107)出现在《冬天的故事》中的神是阿波罗,他虽未亲自登场,但却通过神谕直接说出了全剧的大纲:“赫米温妮洁白无辜;波力克希尼斯德行无缺;卡密罗忠诚不贰;里昂提斯者多疑之暴君;无罪之婴孩乃其亲生;倘已失者不能重得,王将绝嗣。”(《冬》:Ⅲ.2.132-136)但在《暴风雨》中我们却自始至终没有看到这样一位神明出场。诚然,普洛斯彼罗从一开始就提到“天命”、“神意”,宣称“慈惠的天意眷宠着我”(《暴》:Ⅰ.2.159),“福星正在临近我运命的顶点”(《暴》:Ⅰ.2.181-182),但在全剧高潮处,当阿隆佐等人以为自己分明从海潮、风声和雷鸣中听到了上天对自己过去罪孽的宣判时,我们观众却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听到的神明之声其实只是变作一只凶鸟的爱丽儿奉普洛斯彼罗之命发出的:
你们是三个有罪的人;操纵着下界一切的天命使得那怒海重又把你们吐了出来,把你们抛在这没有人居住的岛上……我和我的同伴们都是运命的使者……我来就是告诉你们这句话:你们三个人是在米兰把善良的普洛斯彼罗篡逐的恶人,你们把他和他的无辜的婴孩放逐在海上,如今你们也受到同样的报应了。为着这件恶事,上天虽然并不把惩罚立刻加在你们身上,却并没有轻轻放过,已经使海洋陆地,以及一切有生之伦,都来和你们作对了。你,阿隆佐,已经丧失了你的儿子;我再向你宣告;活地狱的无穷的痛苦将要一步步临到你生命的途程中;除非痛悔前非,以后洗心革面,做一个清白的人,否则在这荒岛上面,天谴已经迫在眼前了!(《暴》:Ⅲ.3.53-82)
普洛斯彼罗听完这段话后当即夸赞爱丽儿,“你把这怪鸟扮演得很好……我叫你说的话你一句也没有漏去……我的神通已经显出力量,我这些仇人们已经惊惶得不能动弹;他们都已经在我的权力之下了”(《暴》:Ⅲ.3.83-90)。普洛斯彼罗的夸奖再也明白不过地揭示了剧中所谓天意的实质,借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普洛斯彼罗其实是在“用人工模仿天意”(human imitation of providence)(11),其目的就是要让对手以为天罚已近从而因恐惧而甘心低头悔罪。“人工”在剧中就是指魔法,作为相辅相成的两个工具,魔法和天意共同发生作用,使得普洛斯彼罗能够一方面施加强制,另一方面又将强制力的源头深深地隐藏起来——他在对手灵魂中进行的改造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剧中另一处直接提及天意的地方在最后一幕。此时普洛斯彼罗与他的仇人已经和解,两家的下一代也已结为眷属。老臣贡扎罗在欣喜之余回顾遭遇暴风雨后三小时在岛上的种种奇异经历,进一步追想自普洛斯彼罗遭放逐以来十几年间所发生的一切,原来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逐渐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以“天意”为中心的有意义的序列:
天上的神明们,请俯视尘寰,把一顶幸福的冠冕降临在这一对少年的头上;因为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相聚的,完全是上天的主意!……米兰的主人被逐出米兰,就是为了让他的后裔成为那不勒斯的王族吗?啊,这是超乎寻常的喜事,应当用金字把它铭刻在柱上,好让它传至永远。在一次航程中,克拉莉贝尔在突尼斯获得了她的丈夫;她的兄弟腓迪南又在他迷失的岛上找到了一位妻子;普洛斯彼罗在一座荒岛上收回了他的公国;而我们大家呢,在每个人迷失了本性的时候,重新找着了各人自己。(《暴》:Ⅴ.1.205-213)
这段话在《暴风雨》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前引三位神明的话之于另三部浪漫剧,不过这只是贡扎罗对这些事件的“意义”的个人看法,作为观众我们不应该认为他是在代表莎士比亚直接说话。但这无疑会是普洛斯彼罗非常“欢迎”的一种看法。事实上,既然他在一开始设计岛上这幕和解大戏时就刻意把他的个人意图包裹在天意的外衣下,那么他所能期待的最佳效果恐怕就是当事人在经历了这番奇遇后当真把所有事件都归因于天意而非他个人通过魔法做出的安排。贡扎罗的总结中有很多地方是与真实情况明显不符的:他说所有迷失了本性的人都重新找到了自己,但我们看到塞巴斯蒂安和安东尼奥直到最后都没有表现出多少悔意——事实上如前文所言,连阿隆佐的忏悔我们都应当谨慎对待。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魔法在贡扎罗的叙事中根本没有被提及(当然他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好像所有事都是在天意彰显之下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发生似的,好像一个好人在逆境中只要坚忍沉毅、信心不坠,便最终会得到天意的眷顾,收获神的回报。当然,贡扎罗并没有故意掩盖任何事情,他只是记录了他有限视角内看到的东西以及他对这一切的真实感受,至于哪些是他能看到的,哪些是他无法看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普洛斯彼罗决定的。普洛斯彼罗明知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并无悔意,却不事声张,在最后一幕里把他们也当做“朋友”一起欢迎。关于魔法他也是守口如瓶,在整个过程中他只让爱丽儿一人与闻其事(但爱丽儿毕竟只是“空气”),而在他确信自己即将大功告成时,甚至把魔杖和魔书也都悄悄折断、扔弃。不了解这些情况的贡扎罗面对一系列奇迹般的事件当然只能把所有一切都归因于天意,但我们观众却可以看到故事的全貌;在这个更真实的版本里,起作用的始终都是魔法,而非所谓天意。
当然,“天意”这种工具也有一个弱点,即它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对象对超自然力量的易感程度。换句话说,如果对象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或唯物)主义者,那么这一招就很难奏效了。前文曾谈到普洛斯彼罗的道德改造计划在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那里并未取得理想效果,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与易感的阿隆佐相比,这两个人——尤其是安东尼奥——对普洛斯彼罗使出的超自然把戏几乎完全无动于衷。在第二幕第一场,爱丽儿施法让阿隆佐及其随从都昏然睡去,此时唯有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清醒着,后者惊讶地说,“真奇怪,大家一下都这样倦,好像着了魔似的”,但前者一句“那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暴》:Ⅱ.1.199-200),便立刻打消了他的狐疑。事实上,身处荒岛的现实和周围发生的奇异事件丝毫没有把安东尼奥的注意力引向内心,他关心的依然是如何从眼下的机会中攫取更大的权力:“他们一个一个倒下来,好像预先约定好似的,又像受了雷击一般,尊贵的塞巴斯蒂安……时机全然于你有利;我在强烈的想象里似乎看见一顶王冠降到你的头上。”(《暴》:Ⅱ.1.203-209)到第三幕,当化身为鸟的爱丽儿宣布对三个罪人的天谴近在眼前时,阿隆佐受内心悔恨和恐惧的折磨陷入疯狂急欲寻死,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却依然本能地把超自然的东西当做“自然”事物来对待,两人拔出剑来,准备和敌人(不管它是什么)拼个你死我活,一个说“要是这些鬼怪们一个一个地来,我可以打得过他们”,另一个喊了声“让我助你一臂之力”,便一起冲将过去(《暴》:Ⅲ.3.103-104)。
归根到底,天意观念是作用于人的迷信的。作为精明的马基雅维利式现实政治家,(12)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不会不明白宗教迷信在君主维持其统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马基雅维利在《罗马史论》(Discourses)中曾谈到罗马早期君主努玛(Numa)的治国策略:“他看到治下的人民野性难驯,便想运用平和的手段使他们变得顺从,于是他就想到了宗教的力量。”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努玛谎称自己与仙子有交通,把他自己想要制定的法律说成是仙子面授给他的。”从努玛的这种做法中马基雅维利得出了以下一般性结论:
从来没有哪位杰出的立法者会忽视神圣权威(divine authority)的重要功用;不诉诸这一权威,他的法律可能根本无法被人民所接受。有很多重要的法律,其好处只有少数眼光长远的立法者才能明白,而大众是根本无法参透其中奥妙的。由于立法者很难说服大家接受这样的法律,他便只能转而从神圣权威中寻求支持和帮助。(13)
用这样的认识武装起来的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当然会对所谓超自然事物抱有相当的警觉。如果由他们来总结岛上这番不寻常经历的话,其叙述肯定会与贡扎罗的大相径庭。最后一幕,当普洛斯彼罗奇迹般地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并在言谈中显示自己对他俩方才弑君夺权的阴谋了如指掌时,吃惊不已的塞巴斯蒂安不由得叫道:“魔鬼在他嘴里说话吗!”(《暴》:v.1.129)在莎士比亚时代的大众想象中马基雅维利就是魔鬼的代名词(14)——人们根据他的名字Niccoro给他起的绰号是Old Nick,意即魔鬼。塞巴斯蒂安此时虽然还未看透其中的玄机,但本能已经让他确信普洛斯彼罗就是岛上所有奇事的幕后推手。在他和安东尼奥眼中,普洛斯彼罗是同他们自己一样不折不扣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家。(15)双方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普洛斯彼罗手握强大的魔法,而另两个人目前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凭借手中强大的法力,普洛斯彼罗最终实现了自己定下的所有目标。早在第四幕,事态的发展就已经使老公爵对成功胸有成竹了。此时阿隆佐等人已内外交困,陷入疯狂,而另一方面腓迪南也已经受住“考验”,赢得了普洛斯彼罗对他与米兰达婚姻的首肯。为了见证这一重要时刻,普洛斯彼罗召来了爱丽儿等精灵,让他们装扮成朱诺(Juno)、刻瑞斯(Ceres)和埃利斯(Iris)为这对年轻的新人献上祝福。主管婚姻的朱诺在献歌中祝愿两人未来家庭幸福:“富贵尊荣,美满良姻,/百年偕老,子孙盈庭,/幸福朝朝,欢乐暮暮!”(《暴》:Ⅳ.1.106-109)刻瑞斯司掌农事和谷物,因而其献歌也着眼于更广阔意义上的“丰饶”:“大地增产,五谷丰获,/仓廪不空,粮库常足;/葡萄藤上结实累累;/果树枝子压得低垂;/春天来到你们的田园,/正好在收获完的时节!/贫匮穷乏永远轮不到你们,/刻瑞斯这样的祝福你们。”(《暴》:Ⅳ.1.110-116)(16)
从本文第一节的几段引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自然的丰饶是神话传说中黄金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就此而言,普洛斯彼罗通过刻瑞斯传达给新人的祝福是希望他们未来的生活像在黄金时代一样幸福美好。当然,在此地的语境中这一祝福还有另外一层涵义:米兰达和腓迪南都注定不是普通人(如田园作品中享受着自然慷慨馈赠的牧羊人),作为米兰公爵和那不勒斯国王的法定继承人,这两个年轻人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成为这两个合为一体的国家的君主,而君主的家就是他的国,因此祝福两人的生活堪比黄金时代实际上就是希望在其统治下他们的国家将“足以媲美往古的黄金时代”。当然,普洛斯彼罗不会天真到像贡扎罗那样相信乌托邦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但如果把标杆降低到人力所能企及的善政,那么以两人目前所表现出的德行,普洛斯彼罗确实有理由对未来抱有相当的期待。
不过,让与黄金时代相关联的意象在普洛斯彼罗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出现在他通过魔法创造出来的美妙幻景里,莎士比亚做出这样一种安排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用意。《暴风雨》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被颠覆的秩序如何得到恢复的故事,而黄金时代所代表的恰恰是社会与自然秩序尚未因人类的堕落而遭到毁损时的一种状态。秩序的恢复有程度、规模上的不同;它可能只涉及一家、一城或者一邦,但无论是多么有限的恢复,它最终趋向并奉为理想的却始终是那仅存在于黄金时代中的囊括整个社会与自然的宇宙性完美秩序。(17)这就是说,作为一部以恢复秩序为主题的作品,黄金时代的概念早已被深深地写入《暴风雨》的思想基因之中。在贡扎罗的乌托邦插曲中我们看到它曾以一种戏谑的方式露过头,现在它又出现在第四幕的田园幻景里,两者都指向该剧的主题,它们的意义也都只有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被真正理解。
黄金时代里是不存在僭越、侵夺、谋杀和战争的。当然,这些罪恶即便在其他时代也都能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获得有效遏阻,但黄金时代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在那里是看不到任何旨在防范僭越和侵夺发生的所谓“国家机器”的。按照奥维德在《变形记》第一章中的描写:
这个时代没有强迫,没有法律,人们却自动地保持了信义和正道(…of itself maintained/The truth and right of everything unforced and unconstrained)。这个时代里没有刑罚,没有恐惧;金牌上也没有刻出吓人的禁律。(18)
生活在堕落时代的人当然无法想象这样一种状态居然能在现实世界中存续,于是我们要么认定有一种宇宙性的变故也即“堕落”改变了人性,从而把我们的世界与黄金时代彻底隔绝开来,要么就干脆将一切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都斥为荒诞不经的幻想——就像第二幕中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对贡扎罗的乌托邦所做的那样。然而正如前文所示,贡扎罗的乌托邦想象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在它那自相矛盾的外表下甚至很有可能暗藏着一个关于王权的真理。这一点后来也在我们对普洛斯彼罗魔法所做的考察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证实。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暴风雨》实际上为我们重新认识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黄金时代的神话虽然从不提“王权”,但这个神话所描绘的情形却是王权运用到极致时社会所应呈现出的状态。
普洛斯彼罗对人自发向善的能力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便他早先曾有过),12年前突如其来的宫廷政变以及此后在荒岛上与冥顽不化的凯列班相处的经历也足以帮他打破这些幻想了。他在剧中的行动是严格建立在“只有把人置于绝境之中才能使他向善”这一预设之上的。与此预设对应的是他魔法中带有强制性的那一面——他运用这一强制力使敌人陷于无处可逃的绝境,同时也通过它阻止他们犯下新的罪行。但由于强制获得的善并不是真正的善,他便把强制力巧妙地隐藏在自然力(包括天意)背后,使对象感觉不到强制的存在,同时运用魔法制造幻象的能力,通过精确控制对象的情感让他们进入一种悔罪向善的精神状态。强制力依然存在着,但它却是完全隐身的。以这样一种方式,普洛斯彼罗成功地在荒岛的舞台上创造了一个“真理和正义不借任何外力、自动得到维持”的“传奇故事”(romance)。从这个传奇中评论家看到了世界秩序的重建。“普洛斯彼罗在戏剧中恢复了世界的秩序,”内维尔·考格希尔在《莎士比亚喜剧的基础》中写道,“新的亚当改正了旧的亚当;通过宽恕,通过汪洋大海,恢复天堂成为了可能。”(19)不知不觉之间,在其魔法所及的范围内,普洛斯彼罗使所有人都恍然回到了久已失落的黄金时代。当然,这并不真是传说中的那个黄金时代,考格希尔虽然用“黄金时代”这个名字来称呼它,但同时又给它加上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限定——“这是黄金时代的秋天,伊甸园的苹果树已经结果,果实已被人类吃过,罪恶与悲哀已侵入花园;当然,罪恶已受到控制,并仍在控制之中,下一代还要继续提防。”(20)
同第四幕中上演的那出“迷人而谐美”的假面剧一样,普洛斯彼罗通过魔法创造出来的黄金时代终究也是一种虚像:剧中罪人们的忏悔看起来像是真诚自发的——连他们自己或许都这么认为;但作为全知的观众,我们却清楚地知道,若是没有魔法的强制力,这一切其实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作为这出和解大戏的总导演,普洛斯彼罗对此当然是洞若观火的。换句话说,尽管他亲手编织出来的黄金时代幻景和谐而美妙,他本人却应保持清醒头脑,不让自己陶醉于其中。陶醉意味着放松对人性恶的必要警惕、忘记强制力的不可或缺,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暴风雨》第四幕中凯列班伙同屈林鸠罗与斯丹法诺试图谋杀普洛斯彼罗的情节显然就是专为警示这一危险而安排的。当这三个丑角式的阴谋家向普洛斯彼罗的洞室行进时,后者正在同米兰达、腓迪南一起观看精灵们上演的祝福假面剧。普洛斯彼罗本是这出假面剧的导演,但眼前美妙的乌托邦幻景显然把他也深深吸引住了,以至忘记了正在逼近的危险:
[普洛斯彼罗突然站起身来,在一阵奇异的,幽沉的,杂乱的声音中,众精灵悄然隐去]
普洛斯彼罗 (旁白)我已经忘记了那个畜生凯列班和他的同党想来谋取我生命的奸谋。他们所定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向众精灵们)现在完了,去吧!
腓迪南 这可奇怪了,你的父亲在发着很大的脾气。
米兰达 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他狂怒到这样子。
(《暴》:Ⅳ.1.139-145)
在这个时候让凯列班出现可谓恰到好处。黄金时代幻景中被刻意隐去的真相是人难以自发地向善,而凯列班在剧中所代表的恰恰是那使自发向善变得如此困难的东西,灵魂中不听理性管教的“感官欲望”(appetite)。凯列班常年来表现出的不驯让普洛斯彼罗懂得了道德教化中强制力的重要性;事实上,正是这一宝贵的经验教训帮助他在针对昔日敌人的道德改造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当胜利已然在望而他却再次险些忘掉这一关键事实时,凯列班又一次适时赶到,把他从善与美的虚像(illusion of goodness)中粗暴地唤醒,使他不至于再重复12年前因忽视权力而犯下的错误。
①语出该剧第二幕第一场144—170行。本文所用的全集版本为F.Kemode,et al.,eds.,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4。后文出自该剧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剧首字及幕次、场次、行数,不再另注。本文引文除特别标出外均使用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译文略有改动。
②See The Tempest(The Arden Shakespeare,3[rd] Series),Virginia Mason Vaughan and Alden T.Vaughan,eds.,London:Thomson Learning,1999,p.31.
③Michel de Montaigne,The Essayes of Montaigne,trans.John Florio,London:Modern Library,1933,p.164.
④G.F.Parker,"Shakespeare's Argument with Montaigne",in Cambridge Quarterly,28(1999),p.3.
⑤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可供参考。韩愈在《本政》中说:“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韩昌黎文集注释》[上],阎琦校注,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74页)。王安石在《原教》中也曾说:“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王文公文集》,唐武标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69页)。
⑥Qtd.in Edward William Tayler,Nature and Art in Renaissanc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p.34.
⑦柏拉图《政治家》,洪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31-32页。
⑧Paul A.Cantor,"Prospero's Republic",in John E.Alvis and Thomas G.West,eds.,Shakespeare as Political Thinker.Delaware:ISI Books,2000,p.249.
⑨关于把凯列班看做灵魂中非理性的“感官欲望”部分的化身的讨论,详见H.R.Coursen,The Tempest:A Guide to the Play,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0,p 20。
⑩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富有马基雅维利色彩的假设(See Leo Strauss,Thoughtson Machnavell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248-249)。
(11)J.H.Summers,Dreams of Love and Power,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50.
(12)有关两人身上马基雅维利特性的讨论,详见Frank Kermode,ed.,The Tempest,London:Methuen,1962,p.liv。
(13)以上几段文字均出自N.Machiavelli,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New York:Modern Library,1950,pp.146-147.
(14)Alessandra Petrina,Machiavelliin the British lsles,Farnham:Ashgate,2009,p.39.
(15)Nigel Smith把普洛斯彼罗——而非安东尼奥——看做剧中真正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家(See Nigel Smith,"The Italian Job:Magic and Machiavelli in The Tempest",in Linda Cookson and Bryan Loughrey,eds.,Critical Essays on The Tempest,Harlow:Longman,1988,pp.90-100)。
(16)此处采用了梁实秋的译本《暴风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远东图书公司,2002年,第135页。
(17)“宇宙性秩序”即指囊括整个“存在链条”(chain of being)的秩序。评论家注意到《暴风雨》是一部“着眼于整个存在链条”的作品,剧中的人物“被放置在宇宙性的大背景之下”,而“存在链条”的各个级别——从天意、物质自然,到人、精灵和兽——都一一在剧中出现了(See E.M.W.Tillyard,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London:Penguin,1966,p.47)。
(18)Ovid,Metamorphoses,trans.William Golding,M Forey,ed.,London:Penguin,2002,p.34.Jonathan Bate认为除了蒙田的《话说食人部落》以外,《变形记》中关于黄金时代的描述也为《暴风雨》第二幕中的乌托邦插曲提供了素材(See J.Bate,Shakespeare and Ovid,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255-256)。
(19)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9页。
(20)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第2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