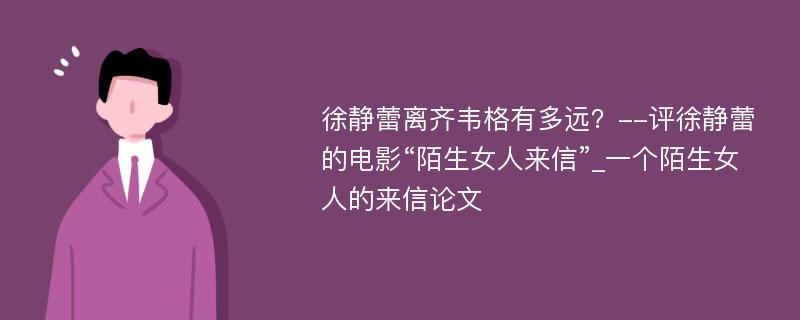
徐静蕾离茨威格有多远——谈徐静蕾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多远论文,一个陌生论文,来信论文,女人论文,茨威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静蕾借用了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用影像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意念中、精神上原初的“爱”的主题。这爱不同于人间烟火琐碎的爱,它是一个女性心灵充盈与生俱来的爱。这“爱”在形式上缥缈、孤独,这爱,纯粹得让人心疼。影片对爱情的诠释脱胎于原著,但又与原著有所不同。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离茨威格的原著还有多远?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揣摩人物心理、分析人物心理上有着独特的天份。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的24小时》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心理小说。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他的文本情有独钟。他认为,茨威格构筑了一个梦的世界。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分析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似乎验证了“恋父”情结。一个情窦初开又丧父的女孩,面对陌生男人的到来,由一开始的崇拜生发出好奇,又由好奇关注起这个陌生男子的一举一动。最终,在意念中毫无保留地爱上了他。其实这“爱”原本就是她一厢情愿的暗恋,其结局可想而知。世间会有男子能承受住这份纯净完美的“爱”吗?
小说中,茨威格的视点是一个男性的视角,他诉说了女性爱的无望与疯狂,是男人的阅读体验。他对陌生女人的叙述没有同情、他笔下的男性更为冷酷。在他第一次占有女孩的时候,他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将一支白玫瑰送给她,而是问她“想不想拿些花?”他对女孩远没有电影中表现得那么心细。他也没有像电影中,两次重逢追问女子问其是否曾经见过?
徐静蕾的电影中,她悄无声息地将叙事的视角转换成了一个女性的视点。镜头移动中,更多关注的是女性对爱、对性的心态。在女孩与作家相逢的一瞬间,原作更为注重的是男子的眼神,而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是林园那纯净而又惊恐的眼神。躲闪中,似乎暗示了爱情故事的开始。而后来成年女子徐静蕾身怀孩子时坚定的神色,更表达了一个女人的骄傲。她虽然没有从情感上征服爱人,但对于“爱情”本身来说,她是个胜利者,她一生都活在自己童话世界中。正如徐静蕾在匡正传媒运营人洪晃的“男人的一夜,女人的一生”的说法时所说的“女人的一夜,女人的一生”。女性对爱的主动性渗透着现代女性对于爱的执著与偏激。
飞翔的风筝VS腐烂的苹果——纯情的覆灭
电影用光影营造了昏暗、温暖的意境。所有的影仿佛静止,但在镜头的运动中,所有的影又仿佛有了生命力。它们宛如处子,外表的淡雅掩饰着内心激情。
故事在久保田修的配乐中开始,琵琶伴随着钢琴徐徐拉开序幕。车轮的飞转调和着匆匆的脚步,预示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封尘封了二十年的记忆在一个男子41岁生日当天缓缓铺展。他从未想到这样的一封来信是出自一位爱着他却永远离开他的女子的手,淡淡的独白融合琵琶的弹拨,那是一个临死的女子生命的啼血。
十三岁的女孩情窦初开,在没有来得及的时刻与作家狭路相逢,眼神的冲撞中决定了一生的命运。“没有一个女人象我这样死心塌地的爱过你,过去是这样,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察觉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热情奔放……从那一秒钟起,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这段旁白述说了一个宿命,一个孩子对爱情的直觉,当还没有弄清楚爱是什么的时候,已经坠入情网,网住了一生。镜头没有过分地渲染少女的喜悦,天空中飞舞的风筝取代了啰嗦的叙事。飞翔的风筝其实就是心灵欢畅的意想,一根线撑出一片风景。以为线在手就可以拥有男女,可是,不谙世事的少女哪里知道那撑出的一片风景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连续三夜的疯狂,男子决定离开。少女抱有一线生机,对“我一回来就去找你”这句话深记不忘,顺手让男子咬了一口手中的苹果,用目光为他送行。
“人是回来了,但什么都不记得了。”男子没有再去寻她。窗台上干枯的苹果,一半是他咬了一口的,一半是她吃剩下的。两条弧线勾勒的苹果孤独地倒在昏暗的窗前,失去光泽。
从空中的风筝到腐烂的苹果,传达的是一种心态。心从低谷中走出犹如放飞的风筝,它暗示新生命的升起,而干瘪孤零零的苹果则意味着纯情的凋零。对爱的绝望、对希望覆灭的失望,眼前的景色化为沦落异乡的漂泊。火车的行进中,一个陌生女子的旅途开始了。
温柔的滑动VS躁动的敲打——失衡的爱
影片中,当18岁的少女踏入男子房间的时候,镜头首先注视的是她的手,关注她的触觉。她温柔地抚摸刻花古董,随后,手背触摸满墙的书,手指翻转过来慢慢地在书上滑动。这是她从13岁就向往的地方,这样的抚摸穿越了记忆的空间,那一年的相逢在这样的触摸中慢慢融化。就这样,平静的心迎来了久违的感动。电影中,男子真的动情了,爱欲拥有了矜持……平静中舒展的玫瑰。
女孩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爱人,像完成了一桩心愿。影片中这种处理很好,但是,在这之前对前奏的交代有点草率。姜文除了从造型上像一个40年代北平的文化人,从行为举止上看,怎么也看不出儒雅,甚至有点笨拙。比如,在学生游行的时候,他作为报社的记者拍照时,神情中充满着呆滞。一个情场上的滑头怎么就对一个纯情的女孩显示出了一种痴迷?在这点上的处理,游离原作的行为逻辑。不免要怀疑是否导演有意这样设计,满足美丽女性的虚荣心。或者,徐静蕾没有茨威格残酷,她为女性留下了一件貌似华丽的外衣。
手在书中的滑动,这个创意很好,只是,由于这双手太美了,再加之滑动中有点做作,不免有刻意展示玉手的嫌疑。
有了孩子的女子再度回到北平。新生命的诞生是希望的绝处逢生。影片细腻地表现了女性的柔情与痴情,孩子这个新的生命仿佛是爱的福音。女子活在一个童话的世界中,童话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梦想的破灭。一个新的生命的出现是童心的复活,童话的主题依然延续,爱的等待就有意义。然而,剧院中的一幕彻底毁了她的平静。镜头以窥视的视角介入。从幕布摇到女子的脸上,朋友们坐在她身边讨论的也是有关男人、女人的故事。不经意的一瞥捣乱了女子的心。姜文的手和着鼓点的声音在腿上有节奏的敲打着,随着鼓点的密集,他的敲打也越来越急,每一下都打在女子的心上。终于,她无法忍受这种躁动,选择离席。外表看似平衡的心在这里彻底决堤。
门的开启VS门的关闭——死亡与新生
当女子在异乡生完孩子重新返回北平的时候,镜头从一扇开启的门缓缓进入,徐静蕾的背影成为流动的图画,交待了她新生活的开始。少女到贵妇的转变牵动价值观的改变。她对待街头受穷的孩子是一种自私与不屑,而且不允许他的孩子同情这些穷人,并把他们的生活比喻成垃圾堆。这是一种贵族视角,它与原作的精神相差甚远。在小说文本中,茨威格交待了她生孩子时医院的破旧,以及她在医院所受到的非人道的待遇。由于贫穷,她对金钱和地位有了重新地审视。我们可以理解为了生存,她被迫沦为妓女。而在电影中,徐静蕾的贵族意识有意把自己身份提高,少了普通人的情感。我不禁生发出疑问,一个出生于贫困人家的女孩子怎么会对穷人失去同情心?她的爱心哪去了?如果爱只是针对一个男子,这个女子的爱是狭隘的。这与她那么无私地爱着一个男子的真情又不相符,失去了人物行为的内在逻辑性。
生命的期待使她有了与男子的第二次缠绵,此时,女子退去了年少时的羞涩与被动,久压心底的爱燃烧成炽热的激情。影片中虚掩的两扇门遮掩着两个成年人的狂乱。白玫瑰的怒放是爱在等待中的娇艳。只是,女子的爱并没有勾起男子的记忆,她在男子的记忆中是空白的。当最后一朵玫瑰别在了女子的发髻,爱从此也随着玫瑰凋谢。孩子死了,希望没了,爱情走了,女子选择惨淡谢幕。
镜片在结尾处,姜文打开关闭的门,跟着镜头的移动,目光穿越一级一级的台阶,视线触摸微弱的灯火,灯火处一个女孩恬静的脸……
女子的死对于男子来讲也是一个顿悟,他似乎领悟了爱的美丽。而对她自己来讲也许是种解脱,她终于可以走出爱的阴影,等待她的将是彼岸温暖的阳光和孩子般纯净的笑。这比茨威格在文学文本中的结尾要温情。
小说文本结尾抛给男子的是反思,是惩罚。
茨威格以高傲的男性视角解剖一个陌生女人的心理,徐静蕾以小女人的视角圆满女人的童话。平淡的风格如同她的表演,电影好似她的一个心愿的完成。
一段爱情童话终结了,女子用一生等待着童话的实现。女子心中有爱的梦想,期待男子对信念的坚守,然而,徐静蕾用凄美的声音告诉人们真爱难求。摄像李屏宾先生流畅、缓慢、纯静的镜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位女性导演的女性情结。一切都是如此的矜持,一切都在等待……
影片在唯美中展示平庸,在平庸中展示唯美。
标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论文; 茨威格论文; 徐静蕾论文; 爱情论文; 苹果论文; 剧情片论文; 美国电影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