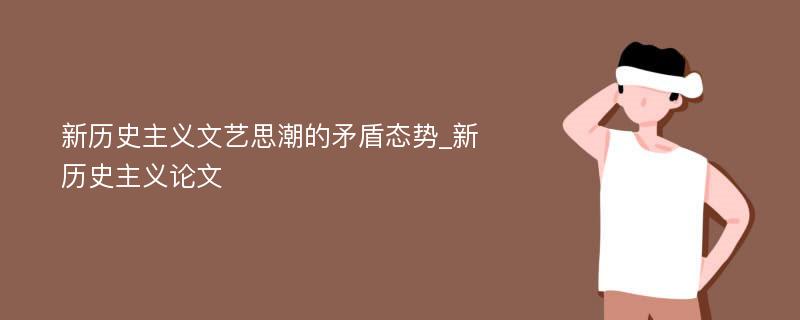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悖论性处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悖论论文,思潮论文,处境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1)04-0071-08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欧美思想界兴起的一种文化理论和批评方法。起初,它只表现为阐释文艺复兴文学的历史文化内涵的一种独特视角,后渐次演为声势浩大的文艺文化思潮。至80年代后期,这种思潮出现在新时期“方法论热”之后的中国文艺张力场。中国式的新历史主义从发生语境到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都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它既是“外生继起的”,又是“内生原发的”;既有欧美相关批评理论诱发的外在因素,又有国内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互激荡的内在动力;既有批评理论方面的思想内涵,又有创作实践方面的独特表现;既表现于小说、戏剧等纯文学样式中,也表现于电视、电影等综合性文艺样式中。
在创作实践中,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相当多的中国作家,特别是先锋派小说创作群体,都不约而同地进行“历史转向”:书写家族村落的故事、描绘残缺不全的传说、拼接支离破碎的历史瓦砾、勾勒零落颓败的历史图景。于是,通过书写各种“家族史”、“村落史”、“心史情史”和“野史秘史”来“重构”、“戏说”、“调侃”和“解构”历史的文学创作演为一时风尚,构成新时期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在理论批评领域,从1988年开始,一些文学研究者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性质和作家作品的价值定位进行质疑,进而展开了“重写(分)文学史”运动。这种创作趋势和批评取向与约略同时进入我国的国外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联袂而行,同气相求,颇可相互彰显和阐发。如上多种力量汇聚而成此期文学活动系统中的群体性思想倾向,可称之为“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之进行研究和评析是完全必要的。在命名上,批评家尚在“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等不同称谓间徘徊,也有人反对冠以“主义”和“思潮”(注:石恢.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J].小说评论,2000(2).)。但笔者认为,对于这种大规模、多层次的群体性文学倾向,不名以“主义”不足以尽其义,不谓之“思潮”又难以概其全。
本文拟通过揭示其悖论性处境对这种文艺思潮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效应做出整体评估。
(一)文学回归历史与沉沦历史
新历史主义基于新史观,将文学文本放回文化历史语境进行考察,以其文本间性理论和实践拆除了文学文本与历史修撰之间的传统藩篱,达到了对“诗具史笔”和“史蕴诗心”(注: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363.)的确认,走向了史文相济和文史互证,从而呈现出文学向文化全面伸展和历史向文学充分开放的文学景观。
从正面价值看,新历史主义此举命中了形式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的双重迷误,既对形式主义施行了学术纠偏,又对传统历史主义进行了改造更新,从而完成了对文史之间多重关联的揭示和确认。在它看来,历史与文学之间不再是“反映对象”与“反映者”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一种多重指涉、复杂交织和相互构成的交互关系。它认为,文本是一个“事件”,文学文本占据一定历史文化场所,在这里并通过这里,各种历史力量相互碰撞,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得以上演。“文本是历史变化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文本的确可以构成历史变化”(注:Brannigan J.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203.8.)。历史与文学之间“真实”与“虚构”的传统界限已经在其共有的“诗性”基础上被模糊和消除。传统历史主义的那种文学在历史“真实性”面前卑躬屈膝的仆从关系也被平等的互动关系所替代。这种新型关系不仅可以使文学创作进入更大的自由时空,从历史中汲取滋养、题材和方法从而创造出富有历史感和历史魅力的文学佳作,也可以使文学研究者在历史和文学之间自由出入,驰骋其批评才情。这种批评背后还有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生成着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也是当代人的共同诉求。
从负面效应言,新历史主义的这种做法,既未真正抵达那“非再现的”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又因沉溺于“历史”而使文学的审美本质问题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状态,而将“文学性”问题悬搁起来或消泯于批评操作过程的“文学”研究毕竟是令人生疑的。这事实上使文学研究沉沦和弥散于野史资料、档案记录、传说故事等历史碎片之中。从而,使新历史主义文学活动陷入回归历史与沉沦历史的悖论之中。
20世纪本世纪后半叶,各种形式主义沿着自己的批评逻辑最终走到了历史的“铁门限”前。这似乎是历史主义的“胜利”。可前来庆功志贺的已不是传统的那种客观的、非再现的历史,而是具有文本性的“历史”,是一种经过后结构主义锻造的新历史主义。这种“历史”,只是对历史的一种(再)阐释。当其亲近后结构主义“文外无物”的观念而面目一“新”时,他们实际上已被封闭在能指符号的转换链上,在“叙述的、再现的历史”层面穿梭。这无异于承认了他们已经不可能,也无意于再去企及那最终的所指,那本源的历史,那个“非叙述的、非再现的历史事实”(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而是通过对“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强调,将“解释与历史修撰、历史与历史书写”叠加起来而视为“同一回事”(注:Hamilton P.Historicism [M].London:Routledge,1996.21.)。因此,纵然新历史主义可以沉浸于历史阐释的欢愉之中,但它似乎只是在文本之中与历史文化相互赠答,终有一种“隔水问樵夫”的不实之感。
这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表现为作家以集体进入历史的方式颠覆了一切可能的历史,沉迷于历史瓦砾之中做碎片拼接游戏,从而将历史的精神性和神圣性消解殆尽,而作家则通过一个逻辑怪圈最终置身于历史之外。一些因追求文艺精神性而走向历史的作家却沉沦于历史废墟,忘却了文学的审美性。
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典型的新历史主义文本,小说回顾了当年发生在河南境内的大灾荒。作者以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又似乎无可辩驳的历史档案资料重构了那段灾荒史,并使其结论逸出了已有“讲坛历史”和“论坛历史”中广为人知的历史定论,从而重构了一部迷雾般的“民间历史”:两个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新闻记者成了灾民的救星,杀人如麻的日本侵略军放粮赈灾,“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作品中最高统治者的饫甘餍肥满不在乎与灾民的饿殍遍野嗷嗷待哺拼成富有张力的历史图景,达到了对当时“权力关系”的某种揭示,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统治阶级罪行的声讨和对蝼蚁般“与历史无缘”的下层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向来“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而“大而化之”的“历史”的控诉。但作品不厌其烦的资料征引和档案堆砌也有损作品的艺术完整性,“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不是写小说”,作品的审美震撼力也因之大打折扣。这种历史档案的翻检和书写与文学性失之交臂,使作品失去了审美依托。
在批评领域,批评家往往注重从政府文告、法律文本、野史传闻等档案资料中汲取材料而说明社会能量的“流通”和文学文本与它们之间的“交换”,常常表现出将文学混同于其中的趋势。
看来,当文学与历史文化相互开放之后,如何在历史文化大视野下寻求一条切中肯綮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方法,仍然是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当务之急,而如何从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结合部真正切实地出入历史文化,正是文学创作需要认真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二)文学颠覆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相对主义
新历史主义者由于对大写官修的“宏大叙事”的深刻置疑而普遍转向对“小写历史”的推崇,并通过对后者的书写而对大写历史进行有意识的颠覆。从其正面价值看,这打破了传统“正史”的叙述话语专制,确认了一般大众的历史话语权力,为历史修撰的多样性进行了合法性辩护。他们在历史阐释和历史话语方面的使命感和积极介入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新历史主义面临的困境也不容回避。他们实现了阉割大历史和重构小历史的双重快感,但大写历史的解构却使其文学创作和批评滑向了小历史相对主义。诚然,长期以来,“大历史”作为正史,经常只是一些关注江山社稷的改朝换代和政治权力归属的“宏大叙事”,普通百姓的小小悲欢远在这种历史书写的视野之外。新历史主义文学所精心构筑的心史情史、秘史野史和家族村落史将历史聚光点对准那些向来被大历史的强光照射得黯然失色的历史场景,这种做法本身是对大历史的颠覆和拆解。周梅森的小说《国殇》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了这一事实:“历史的进程是在密室中被大人物们决定的,芸芸众生们无法改变它”(注:周梅森.军歌[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83.)。这种感喟同时也就是对大历史合法性的盘诘。但小说对小历史进程的漫长追踪和书写最后也被轻轻抹去了:为保全所部袍泽弟兄性命而发出附逆投敌令又不愿蒙羞而自杀的军长,生死关头尚在争权夺利的副军长和率军突出日军重围的师长同时被戴上了“壮烈殉国”的花环,“历史只记住了这个结局”。这个结论使大历史的大厦摇摇欲坠,但如此建构起来的小历史却同样缺乏根基。它只是向正史的神圣性投去了疑团,却无法使自身成为神圣的历史。如此看来,作者正是在对小历史的书写中与真实历史擦肩而过。
从理论上说,新历史主义者并不公开否认那个“非叙述的历史”,但他们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态度暧昧。“历史事实这个概念在各个时代中似乎都是可疑的了”(注: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8.60.),巴尔特的这句话似可作为他们态度的写照。在小说创作中,他们从迷恋历史碎片到任意杜撰史料,总是在行动上对“非叙述的历史”进行回避。在《我的帝王生涯》、《风》等带有新历史主义特征的小说中,通过杜撰史料颠覆大历史是一种通用策略。在各种小历史中,恰如福柯将“差异”和“断裂”楔入历史所造成的效应一样,历史已丧失了其真正的起源性和连续性。格非的小说《青黄》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对“青黄”的词源学考证转化为一部关于“青黄”失踪的历史,即关于九姓渔户的残缺不全的历史。历史的源头消失在文本话语的书写过程,本来断裂残缺的历史被话语抹平而变成了一部“连续的历史”。这里,作品以对“历史”构成过程的揭示证明了历史起源的缺席和历史连续性的虚妄,从而也就取消了小历史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此,文学通过“转向”历史而“拒绝”了历史。
进而言之,各种小历史之间也相互取消和彼此解构。1991年10月号《上海文学》上的小说《撰史》暗示了这一点。几个老革命对往事的记忆与党史资料的记载彼此错位,文字的历史与人心的历史在相互矛盾中彼此消解,最终无法构筑起一段真正的历史,历史在各种小写历史的描述下变成了一团“迷雾”。这种对历史迷雾的专注消解了历史的价值。这意味着仅仅从小历史出发来撰写历史的悖谬性。这里,新历史主义“以一种无定性的整体观照来看待历史”(注:盛宁.新历史主义[M].台北:台湾扬智文化公司,1996.132.)的理论承诺与批评和创作实践中建构“整体历史”的不可能之间产生了悖反。
各种小写历史从取材到结论往往只是与既往大写历史进行的所谓“文本间性”创作,这势必使其自身的价值变得相对而有限。“重写革命史”的小说创作似乎并未达到被重写者当年所达到的历史和艺术水准。对巴金、杜鹏程、周立波等人的作品的戏拟,往往只是对模仿对象的线性反动,是严重受制于戏拟对象的“负模仿”(注: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从未实现对这些作品所达到境界的超越。“重写文学史”运动也有同样的弊端。小历史是由于与大历史之间的“差异性”而获得价值,也会因大历史大厦的轰然坍塌而丧失价值,这恰好落入了非历史的结构主义共时语言学的方法论陷阱。
新历史主义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达到对大历史的超越,而不仅仅是在“取代”大历史,或沦为大历史的“笺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新历史主义陷入自己所意识到的悖论:“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立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都是采用对方的手段,因此,有可能沦陷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注: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106.)。专意书写小历史的做法,不但使自身价值变得相对而有限,而且最终陷入历史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刺向大历史的同时,也使小历史受了致命伤。
(三)历史的心理情感化与历史不可知论
新历史主义竭力排除对历史的对象式单向涉入,而力图进入与过去和现在的“双向辩证对话”中,着意发掘人性重塑的心灵史。这种取向必然引导人们追求与过去和现在的双重心理情感共鸣,从而使心理情感成为人与历史和现实沟通的重要渠道。
这种多少与法国年鉴学派和新解释学相关的方法,对文学的效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从心灵和人性方面深化了对文学情感性的认识和把握;同时,对心理内蕴和一些经过心灵浸染的历史偶然因素的重视和运用,突出了文学的情感性和意识的自由流动,拓展了文学的思维空间。多数新历史主义小说都避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书写,更无意于通过重大历史事件的逻辑排列来印证历史发展的某些已成定论的必然性,而是通过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标准选择材料,通过对历史偶然事件的选择和渲染,来叙说自己对历史发展的内心感受——偶然无定。如在黎汝清的小说《皖南事变》中,偶然性因素对设置情节、烘托议论和作家笔触的自由跳跃的作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印证了作者自己“考察历史要从社会现象进入人的心态”的结论(注:黎汝清.皖南事变[Z].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144.)。总之,从其正面价值看,历史可能因为作家笔触真正伸入人的“心态”而变得活泼、丰盈和生动。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当知识分子密集涌入历史的时候,他们已不再相信历史是文学文本语义生成的客观基础,人们也无法进入或重建过去复杂的历史场景,甚至也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历史性。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属于相同的历史活动,“理解存在的活动本身被证明是一种历史的活动,是历史性的基本状态”(注:伽达默尔.伽达默尔集[C].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409.)。这种对历史客观性的摈弃可能使历史成为复杂多义的相对性的集积。面对这种困境,格林布拉特说,“我不会在这种混杂多义性面前后退,它们是全新研究方法的代价,甚至是其优点所在。我已经试图修正意义不定和缺乏完整之病,其方法是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情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和社会压力上去,并落实到一部分享有共鸣性的文本上”(注:Greenblatt S.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M].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80.5.)。尽管如此,人们却无法真正“回到”过去。格氏承认,当与死者对话时,“我竭尽全力所能倾听到的,只有我自己的声音”(注:Greenblatt S.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M].L.A.: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8.1.)。我们看到,新历史主义积极进入历史的方式表现为“返回”个人情境。进入历史与躲进心灵竟然是同一条道路!这样,新历史主义陷入了又一个悖论:通过心灵去穿透历史的确对文学具有重大意义,但心灵在尚未到达历史之前便已返回自我而沉溺于具有强烈非理性色彩的心造幻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格尔顿的批评不无道理,“极端历史主义把作品禁锢在作品的历史语境里,新历史主义把作品禁闭在我们自己的历史语境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家永远只会提一些伪问题”(注: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1.)。
以这种特殊处境与历史对话,势必使一些偶然性因素凸显出来,使历史不可知论和历史怀疑论的迷雾弥漫开来。新历史主义小说所表现的“历史”多是一些斗转蓬飞、偶然无定的漂浮物,具有令人不安但又无法破悉的神秘力量。因为,面对苍茫的历史,他们无心收集史料,也无意寻找历史的必然性,而是首先扪心自问:“我这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是否有能力完成一场既属于历史,又属于我个人的战争?”(注:周梅森.题外话[J].中篇小说选刊,1988(3).)这种心造的历史充满着偶然性和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这对于只相信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而无视任何偶然因素的人来说,或许不无纠偏作用。但这同时是以对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可知论的排除为代价的。阐释历史是人们占有自己当下生存意义的本体行为,新历史主义者对历史偶然性的迷恋,显示出他们深刻的历史焦虑和历史认同危机,折射出的是他们在现实面前的软弱无力。
李晓的小说《叔叔阿姨大舅和我》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本。其舒缓冷漠的叙述笔调似乎在让“历史自行上演”,但是,这种以回忆方式展开的“简单过去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造物主,这就是上帝或叙述人”(注:巴尔特.符号学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54.)。小说甚至有意暴露叙述人的存在,并时时以“我猜想”、“我想象”等轻佻的口吻裁断疑点和填补空白。小说中“讲述话语的年代”实施了对“话语讲述的年代”的全面入侵,造成了二者间“对话”链条的断裂。
因此,新历史主义进入历史的意义是可疑的。难道进入历史是为了印证历史的不可知性?难道对历史进步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反叛是为了向历史不可知论、历史怀疑论和历史偶然论妥协?由于对大历史的怀疑而走向历史的不可知论,使其能量几乎内耗殆尽。看来,新历史主义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这种困境进行克服。
(四)文学迷恋边缘意识形态与迷失于意识形态边缘
从理论到实践,从批评方法到创作姿态,新历史主义都坚守边缘:偏僻的村落、颓败的家族、散乱的历史瓦砾、被压抑的心理情感、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等边缘史料;被排挤的小人物、游离于正史之外的乡野村夫、匪帮流寇等边缘主人公;逸出正史的、有违于人们历史常识的边缘历史结论;甚至逍遥于任何一个理论流派之外的边缘的理论立场和观察视角等。怀特指出:“历史的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的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注: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106.)。
新历史主义确信自身的边缘化策略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反叛,因此追求边缘并安于边缘乐而忘返。这种做法把文学置于意识形态的边缘并通过对这种边缘潜能的发掘,突破了各种形式主义的文本界限,对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了相当深入的探索和说明。值得注意,它对文学意识形态性的强调采用两种形式:有时是通过对权力关系的直接叙述而从正面进行的;有时,特别是在创作中,是在二项对立关系语境中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而以否定方式曲折实现的。
从正面价值言,它突破了各种形式主义的束缚而确认了文学与社会风尚、心理特征、国家机构、宗教形式、家庭组织、权力结构、传统惯例等文化现象之间的广泛关联,将文学之根重新植入人类历史的沃野,有力矫正了传统文学理论在此问题上的简单化倾向。
从负面效应言,新历史主义过分强调社会权力结构对文学的支配而未能对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做出充分说明,因而造成了对文学审美娱乐作用的某种忽视。同时,也忽视了文学的科学性或认知性。这使新历史主义陷入悖论处境中。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其认知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等是辩证统一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孤立发挥作用。新历史主义沉沦于“历史”而对文学审美性强调不足,致使其诗学功能发挥缺乏审美依托。同时,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必然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新历史主义一味强调文学对于意识形态的巩固或破坏的价值功能而不重视文学的认知关系,这也使文学价值的实现失去了认知性根基。
文学也无法只从意识形态内部得到说明。新历史主义往往将文学禁锢在意识形态的狭小圈子里,只通过文学对意识形态的巩固、反叛或颠覆作用来确立文学的存在依据,致使文学失去了与社会生活的血肉关联。它吸取了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逆向思维方法,因此不重视历史本身的丰富内涵和文学文本的多样性,因而屡屡出现“意义短路”的险情。它对权力的最终关注使其以权力的宏大叙事替代其它种类的宏大叙事,也使其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日益丧失独特性和新颖性,这与文学的本质特征是相悖反的。
同时,这样做可能使自己成为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抑出来加以同化和顺化的对象,从而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牺牲品,甚至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流合污。诚如伊格尔顿在评价本亚明时指出的,“成为意识形态的颠倒的镜像,用理论上的和谐的散光来代替近视”(注: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34.)。这种为反抗而反抗的批评是没有力量的,通过对历史的批判来实现对当今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往往在批评操作中被释释甚至化为乌有。这种情况在小说创作中尤为明显,通过寻求文学精神性而进入历史的写作变成了对日常生活平庸性和琐碎性的认同。这暴露出作家在现实生活面前的无力状态和逃避态度。
另外,新历史主义发展到今天,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变得“媚俗、平庸、无意义”,而正是这些东西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重写文学史运动”的主将陈思和先生反思道:“当有些年轻作家自认为反对了原先宏大叙事里的崇高理想,就能还原人的自由本相时,却没有意识到你所放纵的轻薄、凡俗、卑琐的自由本相里,也同样认同了一种并不完全属于你的世俗‘主流文化’,你仍然是一个代言人或传声筒”(注:陈思和.碎片中的世界和碎片中的历史——90年代小说创作散论[A].李复威编.世纪之交的文论[C].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3~154.)。这也印证了新历史主义在冷峻的批评阅读中所意识到的文学颠覆活动的悲观前景:文学无法实现有效的抵抗,来自异己的颠覆为权力所需要和“包容”,因而颠覆的生产恰好变成了“权力的真正条件”(注:Brannigan J.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203.8.)。新历史主义的这一洞见用来评判其自身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倒是十分贴切。
总之,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以自身的方式将美学与史学相结合、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问题“问题化”了,而不是解决了。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这本身就是富有意义的。有批评家认为,“新历史主义面临的难题也是文学理论自身的难题”(注:Colebrook C.New Literary Histories [M].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1997,234.)。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不断高涨的“新历史主义之后”的呼声,不只是对它的否定批评,也是希望它尽快走出思维盲区的善意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