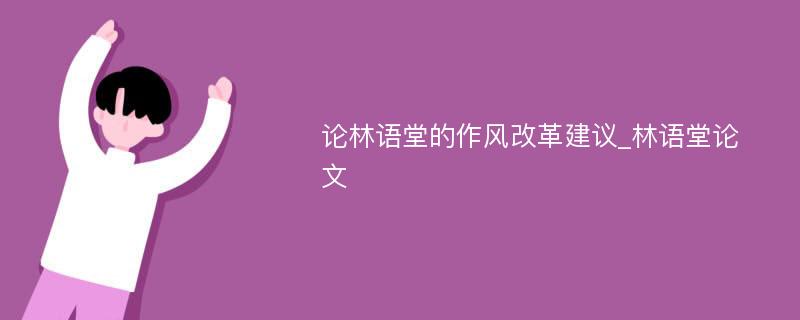
论林语堂笔调改革的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调论文,论林语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如今林语堂的书十分的畅销,他提倡的“幽默”再次被文化市场炒热,林语堂式“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的小品文已经一发不可收地从当代文人高谈戒烟戒酒发展到“小女人散文”和“小男人散文”种种畅销书。可笔者感兴趣的似乎还是他的另外一类文字,即关于“小品文笔调”的主张。林语堂在编《人间世》时直白地说过:余意此地所谓小品,仅系一种笔调而已,并说他之所以提倡这种文体,是为了“使其侵入通常议论文及报端社论之类,乃笔调上之一种解放,与白话文言之争为文字上之一种解放,同有意义”。为此,林语堂作了一生的努力。
所谓“小品文笔调”只是个总称,别号很多,诸如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幽默笔调、谈话笔调、娓话笔调、散文笔调、个人笔调等等,不胜繁复,却又不尽准确。但这些说法所表达的基本含义是清楚的,皆指取法于西洋ESSAY 又实证于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文体,并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论说文章相对立:“大体上,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小品文下笔随意,学理文起伏分明;小品文不妨夹入遐想及常谈琐碎,学理文则为题材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以一种轻松闲散、清新自然的文体来立志立言,在以抒情为主的现代白话散文之外,另创说理议论为主却又不威严、不拘泥、不端架子的现代散文,这就是“小品文笔调”的要义。林语堂甚至想把这种写作文体推广到更大的范围里去使用:“此种笔调已侵入社会及通常时论范围,尺牍,演讲,日记,更无论矣。除政社宣言,商人合同,及科学考据论文之外,几无不夹入个人笔调,而凡是称为‘文学’之作品,亦大都用个人娓语笔调。故可谓个人笔调,即系西洋现代文学之散文笔调”。
这种新的散文文体,无论在当时为纠正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中出现的文体缺点计,还是为以后的新文学散文创作的繁荣计,都是具有创意性的。三十年代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文体与鲁迅倡导的杂文文体并立于世,可以说是说理言志类的散文创作的两大潮流。而观今日散文创作之繁荣,杂文的战斗性与讽刺性难免受到现实的种种限制;小品文从积极的一面而言,用个人笔调与自己声音依然沉重地履行着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文化现象。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追根思源,重提林语堂在当年文学批评中的某些主张及其实践,是十分有趣的工作。
二
1918年,林语堂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入清华大学担任英语教员的第二年,陈独秀、胡适发动的文学革命运动已经进入了对历史传统的全面反省,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也成为当时文化界新旧两派争论的焦点。林语堂飘浮在中国思想解放,文学改革的潮流里,不免跃跃欲试。他最初加入《新青年》战斗行列的举动,是关于文字改革的设想方案,他从“汉字索引”说到西洋文体,转而对新文学提倡白话以来在文体上的毛病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先是从批评《新青年》上的理论文章未得“西文佳处”开始的,认为西方理论文章的特点是说理精密,立论确当,有规模有段落,逐层推进有序,分辨意义精细,正面反面兼顾,引事证实细慎,读来有义理畅达、学问阐明的愉快。而《新青年》所刊的文章虽然“皆是老实有理的话”,但离“西方论理细慎精深,长段推究,高格的标准”毕竟差得很远,而且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林语堂看来,当年作文最具有西方式逻辑力量的作者,恰恰是后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论敌章士钊。这个批评只是针对当时的白话说理文的文体缺点而言,还不涉及小品文体的提倡;但在当时提倡白话文的《新青年》诸子,显然是只顾着思想的革命和风俗的改良,文体改革还没有进入他们关注的视野,但林语堂因身在文坛纷争圈外,思想比较超脱,能见人所未见之处,从文体批评着手,一下子抓到了白话文的弱点,应该说是别开生面的一局。可惜当时新旧文学两派文白之争正处在白热化状态,《新青年》诸子为确立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地位,正竭尽全力苦争,所以并未重视林语堂的批评。钱玄同在附本文后面的复信中对林语堂的议论有赞成也有解释,认为新文学家固然应该“效法”西文佳处,但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当前第一步必须将文言全盘推倒,让白话文立稳了正宗的地位,把旧文学里的那些“死腔套”删除,然后再走第二步,把西文佳处输入到白话文里去,否则虽有别国良好的模范也是枉然。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其实说来也奇怪,《新青年》诸子中除李大钊、高一涵是从写逻辑文体的“甲寅”派转化而来但又很少作文、胡适虽是留美学生却为了提倡白话必须以身作则用口语写作以外,其他几位主将级的人物都是从旧学分化过来,从未受过严格逻辑的思维的训练,即使在后来白话取得了胜利,他们依然是用散漫的文体在写作,仍未写出过严密的有逻辑的西方式的理论文章。
但是,林语堂在同一文章中的另一个建议显然是对他们胃口的,那就是他在文章中深感《新青年》文体单调,建议“凡文不必皆是讲义理的深奥”,因为“文生于情,须要与情感题目相配才好”,不妨因其应用不同,采用多种文体:如书信体、说话体、讲学体、科学记事等,特别举例了ESSAY STYLE“应格外注意”。 这大约是新文学的文体建设中第一次提到了西方文学中以说理议论、自由发挥为主要特征的“随笔体”。说来也是巧合,就在刊发林语堂这篇通信(1918年3月2日作)和钱玄同复信的4卷4号(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上, 编辑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一期上首次推出了“随感录”专栏,发表陈独秀、陶孟和、刘半农三人七篇谈话体杂感文。虽然对于《新青年》“随感录”的出现,究竟是由于林语堂的建议,还是出于纯粹的偶然,现在已经无法作出确切的回答,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林语堂与《新青年》诸子在提倡自由散漫的西方随笔体方面,确有相通之处的。事实上也正是《新青年》中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议论性散文大家。
此后不久,林语堂远渡重洋,留学哈佛大学,继之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与新文坛中断联系达四年之久。当他于1923年秋回国之时,尽管《新青年》已不复存在,然而白话为文学正宗地位已经确立,林语堂自然兴奋不已。据林语堂推断,白话代替文言,既然以说话方式行文成为文学正宗,自然会演变出以闲谈说理,在谈话中夹入个人感情及个人思想,即所谓“小品文笔调”一派来。当年钱玄同所说的第二步,正是到该兑现的时候了,行文笔调上的大解放似乎就在眼前。然而,现状令他大失所望。白话文倡导者陶醉在“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的喜悦之中,而对于白话文所需要的笔调改革似乎并无热心。对此,林语堂不失书生本色,他当仁不让,再次提出笔调改革的主张。
1924年5、6月间,《晨报副刊》刊出林语堂《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两文,虽然打出了“幽默”的旗号,但重点是在呼吁“笔调”的改革。他认为中国旧文学在“礼教蝉化”之下生成了“板面孔文学”。一旦扯下面孔来便失去了“身格的尊严”,所以总是以庄重、严正的笔调喋喋不休地叙述着仁义道德或“天经地义”的道理,令人有寒气逼人之感。新文学虽然文体变了,但行文笔调变化不大,白话文学中“板面孔”训话式的笔调并不鲜见。林语堂的笔调改革主张就是专门用来医此顽症的,他开出的第一个医方为西式的幽默,试图通过寓庄于谐,打破庄谐界限,以“会心的微笑”,变“板面孔”训话式笔调为谈话式笔调,希望不仅散文家用它写散文,而且大学教授用它写学术论文,大主笔用它来写社论的。
中国本无“幽默”二字,HUMOUR一词来自西方,是林语堂首创“幽默”的译法,以愈幽愈默而愈妙的说法,战胜了其他的各种中译名而成为“定译本”。幽默本来是含有一种人生态度的,但在林语堂最初的介绍里,首先突出的写作方式的改变。大约“五四”文学是启蒙文学,知识分子站在广场上负有唤起民众,传播真理的使命,习惯了充当大众导师(或在当时的说法是青年导师)的职能,文章写着写着就要忧国忧民,脸孔也不自由主地“板”起来了。只有你自觉跳出传播真理、以启蒙导师自居的精英立场,站到普通人的立场上去发表自己的看法,才有可能真正说出自己对生活拥有的感受,使自己脸孔上的肌肉放松下来。这在当时,已有周作人提倡“美文”和“个性的文学”在前,林语堂当然是站在周作人的一边。他批评陈独秀的文章“大肆其锐利之笔锋痛诋几个老先生们,从一方面看起来,我也以为是他欠幽默。我们只须笑,何必焦急?”而他更提倡的是“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来替社会开点雅致的玩笑。”这显然不是对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社会种种旧习陋习的分歧,而在于如何批判旧习陋习的具体战法方面,是急吼吼的组织并指挥大兵团作战呢?还是散漫地学学堂·吉诃德先生,以个人战斗的立场展示骑士战风车的风度?而这一分歧,却形成新文学以来知识分子的两大分流。
三
平心而论,林语堂最初提倡“幽默”,鼓吹笔调改革的主张,全无反对新文化战斗传统的意思,也不似后来文学史所划分的左右翼之分。相反,他所反对的“板面孔”文体,正是与知识分子因袭的旧文化传统相关的。这有他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为证。就在他发表两篇提倡幽默的文章约半年之后,《语丝》和《现代评论》两种白话周刊几乎同时诞生。虽然它们都承袭了《新青年》自由议论、批评时事的余脉,但思想倾向和学术个性却不相同。《现代评论》支柱人物均为留欧归国学生,若以门户而言,林语堂理应参加《现代评论》,可是他却偏偏成为以《新青年》老人马为主体的《语丝》的一员,个中原委恐怕与他的文学主张不无关系。
林语堂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中尽管坦白批评白话文“板面孔”训话式笔调,但对于《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上的随感录和杂感文体却表示相当的好感,认为“板面孔”训话式笔调的这种毛病,在“做杂感栏的几位先生”那里“好的多”。而正是这批写杂感的知识分子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参与了《语丝》的创办,标举“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只说自己的话,不说别人的话”。作者们心有所感便秉笔直书,古今并谈,庄谐杂出,此种“放逸”的笔调深得林语堂的欢心。《现代评论》虽不乏小品高手,可是就其多数成员而言,则都擅长做政论文,而且他们对政治有较多的热心,适宜于做官,言行举止文雅,彬彬有礼,不失绅士风度,文章都似大学教授的演讲,这显然与林语堂生性不相近。后来林语堂曾从笔调上比较这两家刊物的异同,指出:“《现代评论》与《语丝》文体之别,亦甚显然易辨,虽然现代评论派看来比语丝派多正人君子,关心世道,而语丝派多说苍蝇。然能‘说别人的话’已难得,而其陶冶性情处反深,两派文不同,故行亦不同,明眼人自会辨别的。”接着他又说,《语丝》之文,人多以小品文称之。可见在当时以《语丝》派为代表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在林语堂看来正是他所中意的小品文体。林语堂舍《现代评论》而投身《语丝》的缘故大致可见一斑了。
林语堂加入《语丝》是由于“性之所近”,但他主要佩服的是周作人。这位以提倡“人的文学”而著名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艺评论家,从1921年起反思了先前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转而提倡“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由此自觉在民间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他连着发表《个性的文学》、《美文》,树立起小品文写作的大旗。林语堂虽未直接参加《新青年》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但他与周作人的心是相通的,从反思启蒙立场到《语丝》文体建设再到小品文的提倡,他对周作人思想主张几乎是亦步亦趋。就在周作人反思五四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同时,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反思了留学生中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流风。他自我反省说:当时留学生都患有一种“哈佛病”,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一般说,此种病症就读哈佛四年而养成,离开哈佛四年才会消失,当然也有一辈子不治的。这是留学生刚回国时的通病。林语堂坦白承认曾患过此病。其表现在文章上就是所作之文“文调太高”,“言过其行,视文章如画符”。其实“文调愈高,而文学离人生愈远,理论愈阔,眼前做人道理愈不懂”。他承认与《语丝》诸子相处若干年后,才悟出其中道理,渐渐摆脱“哈佛俗气”。
其中一例就是1925年末关于《语丝》文体的讨论。这次讨论是由林语堂的一番意见引起的。在某次座谈会上林语堂主张《语丝》应扩大范围,连政治社会种种大小问题一概都要评论,这就很有一点“哈佛”气,或说是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精英气。但在孙伏园把他的意见捅出去后,受到了周作人的批评。周作人的意见十分平淡,认为《语丝》没有什么文体,只是“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不伦不类是《语丝》的总评”。这无疑向“视文章如画符”的“阔理论”、“高文调”泼了点冷水。林语堂一下子被点悟过来,对此感触颇深,认为周作人把《语丝》宗旨表白得“剀切详尽”,不仅“使一班读者借此可以明白《语丝》的性质,并且使《语丝》自己的朋友也自己知道《语丝》之所以为贵”。自此之后,他的笔调理论更为激烈。他写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直率地说《语丝》文体的二大条件,一是敢承认自己说的是“偏见”而不是所谓“公理”;二是敢于打破“学者尊严”,可以骂人。他引用周作人的话说,唯一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所谓“真诚”也就是“不说别人的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讲真话。为了不失真诚,宁可发表“私论”、“私见”,乃至“偏论”、“偏见”;同时,由于反对“板面孔”训话式的笔调,主张打破“学者尊严”,而为了打破“学者尊严”,甚至要提倡“骂人”。这就成了林语堂的笔调改革的第一阶段的理论。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林语堂承认他的笔调理论核心是反对文以载道的“板面孔”训话式笔调,那么,他所鼓吹的“骂人”,又怎么能体现不是“板面孔”笔调呢?林语堂是有所防备的,他所谓的骂人,并不是那种自以为握着真理,或者代表着某种意识形态的训话式骂人,而是一种率性的撒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敢怒敢骂的文人脾性,但光是这样地认为还不够味,还应有另一帖药来限制,那就是费厄泼赖。这个名词也是由周作人首先提倡的,林语堂加以发挥。周作人认为这样具备了费厄泼赖的精神,便有了言论自由的资格。林语堂进而作解释:“骂的人却不可以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这种能骂人而不“板面孔”的雅量和戏谑,就是林语堂所鼓吹的小品文笔调。这里似乎已经隐藏了他的笔调理论在第二阶段的某些特征,但在当时林语堂的文章里,骂人还是主旋律,不久他的“费厄泼赖”说受到鲁迅的批评,他也十分费厄泼赖地接受,并在《讨狗檄文》里号召北京知识界进行打狗运动。但平心而论,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判是有针对性的,即“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并没有一概而论地否定费厄泼赖,更没有把林语堂当作批判对象,而林语堂的费厄泼赖说也不是专对章士钊、陈西滢之辈的,而是针对那些以放暗箭造谣言来背后整人的鬼祟陋习而提倡的。他说:“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与暗放冷箭的魑魅伎俩完全不同,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这是林语堂终生身体力行的一种人格和文格的追求。
四
1930年《语丝》终刊。这对林语堂来说,既是不幸又是大幸。《语丝》停刊之后,他那种笔调的文字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发表阵地,而那些“鸟瞰”、“展望”、“检讨”、“动向”之类的长篇阔论又不会写,也讨厌写,岂不是不幸。所谓大幸,自1932年起,他终于脱颖而出,自己抗起“幽默”大旗,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从此,不仅用不着为寻找一个适合自己胃口的同人刊物去犯愁,而且还有了提倡和实践小品文文体的阵地。他的笔调改革理论在实践中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论语》等杂志以“幽默”文学相号召,其宗旨仍不离十年前《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中的主张,以“会心的微笑”来医治那“板面孔”训话式笔调的毛病,一时响应者甚多。但是客观上的形势有所改变,十年前是五四文学革命时代,新文化思潮如交响乐轰轰长鸣,启蒙的黄钟大吕淹没了其他的不协调的音符,林语堂虽倡幽默和笔调改革,并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但到了三十年代初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是国内外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激化;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文化理论与文艺政策旨在否定和消除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传统和左翼文化思潮,而后两者则是在反压迫和反专制的斗争中各自丰满着自己的羽毛,文化界由多角纷争进入相对多元发展的“无名”状态,个人性的文学容易生长;另一方面是都市大众消费文化迅速发展,刺激着新文学不得不改变原先的启蒙姿态来考虑如何适应大众文化口味的问题。而林语堂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幽默”,响应者趋之若鹜,一时赶时髦者瞎模仿者蜂起蚁涌,于是在偏重于批判现实一方的文学立场而言,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难免有“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之象。但就林语堂自己所写的鼓吹文字来看,他所强调的幽默和小品文笔调,仍侧重在一贯反对的“板面孔”式的训话笔调,也就是重在提倡一种轻松、闲适、自由的议论散文的文体,于思想上的非斗争性和非现实批判性倒还是其次的要求。如他所作的《今人八弊》:“方巾作祟,猪肉熏人”,“随得随失,狗逐尾巴”,“卖洋铁罐,西崽口吻”,“文化膏药,袍笏文章”,“宽己责人,言过其行”,“烂调连篇,辞浮于理”,“桃李门墙,丫头醋劲”,“破落富户,数伪家珍”,其中文体批评过其半。
林语堂好辩。他所作的辩白文章中长文《论幽默》最具代表性。他重提“板面孔文学”,以及“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丧期之期限年月”,铸成了廓庙文学的传统,并且延续在白话文学中,某些新文学家担心幽默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其严肃。在他看来这种担心完全多余的:“现代西洋幽默小品极多”,“文字极清淡的,正如闲谈一样”,“大半笔调皆极轻快,以清新自然为主”,“既无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可见,林语堂播种幽默,其希望所得的主要还是在文体的改革上。所论的八弊中,有不少正是新文学运动初期“八不主义”中的内容。譬如他倡导过一种娓语式笔调,建议“使用此种笔调,去论谈世间之一切,或抒发见解,切磋学问,或记述思感,描绘人情”,无所不可,这必能解放小品文笔调。所谓娓语,大约是指一种娓娓道来的谈话式笔调,他曾回顾说,白话提倡时,林琴南斥为引车卖浆者流之语,文学革命家大斥其谬,而作出文来,却仍然满纸头巾气,学究气,不敢将引车卖浆之口吻语法放进去。”可见其所追求的,依然是五四新文学未竟之业。
在林语堂所倡的小品文笔调诸种别名中,“个人笔调”、“闲适笔调”使用频率最高。虽然其它别名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小品文笔调的特性,可是这两种笔调却最能传达小品文笔调的精神。所谓“个人笔调”,林语堂又称“言志”笔调。“载道”、“言志”对立说取自周作人,而林语堂却把它解释成两种笔调的对立。他在《小品文之遗绪》里说:言志与载道,“此中关键,全在笔调”。“言志文系主观的,个人的,所言系个人思想;载道文系客观的,非个人的,所系‘天经地义’。故西人称小品笔调为‘个人笔调’”。笔调当然是个人的,五四新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发现“个人”,散文不再为圣人立言,代天宣教了,应该充分表现作者的独立思想,个人情趣爱好。小品文的产生和发展真是适逢其时,它的笔调讲究个性色彩,可以幽默,可以感伤,可以豪放,可以奇峭,可以辛辣,可以温润,不拘形式,不再要求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上耗尽气力,可以说是白话文体上的一大解放。所谓“闲适笔调”,又称娓语体、闲谈体,都是不拘形式的家常闲谈式的意思。林语堂认为此种笔调发展已成世界的趋势。自从18世纪末叶至19世纪初叶,浪漫主义勃兴之后,古典的礼仪传统崩溃,人们对于人类心理有了更多的关注,因此追求闲适不再被看作是不道德的行为。随着休闲心理的发展,日常生活日趋休闲化。此种社会风气影响到文学写作,于是闲适格调便应运而生。作者撰文时如到友话旧,良朋交谈,推心置腹,诉说衷肠,读者读来有一种亲切、自由和平易的感觉。在此潮流下,假若作者仍摆八字脚,“板面孔”,用满篇训话式的口吻,读者势必只能“似太守冠帽膜拜恭读上谕一般样式”聆听教训,未免与现代潮流格格不入。
为了使他的小品文笔调被人接受,林语堂又认上了一个中国祖宗。林语堂本来是从西洋文学那儿学来的笔调理论,他在二十年AI写作的文章里,不提小品文则已,若提则言必称“西文佳处”,不是英国现代散文始祖乔叟,就是小品文鼻祖爱迪生。可是在三十年代办《论语》等刊物后,他承认笔调改革除了需要西洋祖宗之外,有再认一个中国祖宗之必要。其实这也是来自周作人的影响,周作人早在《〈燕知草〉跋》、《致俞平伯》等文中,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以为现代散文虽然“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格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周作人的创作实绩摆在那儿,周作人散文不仅接受了西洋散文笔调的影响,更是得力于明代小品文。林语堂是一向佩服周作人的,甚至认为鲁迅说点笑话不算稀奇,只有堂堂北大教授周作人也来说笑话,才算是幽默。所以他也开始承认,中国最发达最有成绩的笔记小品之类,在性质和趣味上与英国小品文气脉很有相通的地方,而且觉得提倡小品文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小品文,也须寻出中国的祖宗来。于是,苏东坡、袁中郎、徐文长、李笠翁、袁子才、金圣叹、郑板桥、章学诚等人的一些反对儒学教条,主张性灵自由的散文,都被尊为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先驱了。
当然,林语堂虽把现代小品文的源头上溯到古代,但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在林语堂看来,古代小品与西洋小品文固然时代不同,毕竟血脉相通。消闲、清淡小品原本为中国小品正宗,未尝不可追随时代而进步;但古代小品取材范围狭窄,今天需要扩充,“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取材,关键之点在于摆脱“板面孔”训话式的笔调,充分“扩充此娓语笔调之用途,使谈情说理叙事纪实皆足以当之”。其实,再往深一层说,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笔调的两个祖宗之说,可分作“正宗”、“偏宗”之说。林语堂说过,他理想的文学乃英国的文学,所以凡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大致不离西洋文学,所举小品文模范也是如此,他对于西洋杂志文更是推崇备致。这才是他的小品文笔调的正宗。至于中国古代小品文,其较为系统的见解不出周作人范围,其它大多只言片语,提到的作家作品以引作例证为限。但周作人谈明代小品,自有其生活理想和处世态度的寄托,而林语堂更多的是看中了那些潇洒古人的优雅的文笔而已,所以只能算作偏宗。林语堂说过“在提倡小品文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这可以作为“正宗”“偏宗”之说佐证吧。
五
如果说,林语堂的小品文笔调理论在《新青年》时期萌芽,《语丝》时期成长,那么,《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时期则进入成熟期,其主张的阐述更加周到,根据这笔调理论而实践的小品文文体更加圆熟,为五四以来追求个性发展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新品种。
林语堂提倡的反对“板面孔”式的训话式笔调,推崇个人性、娓语性的小品文笔调,其旨虽不仅仅为一种小品文的文体创造而是为了改革五四来整个新文学的叙事传统,但最后成就的却只是小品文创作。林语堂坚信这种笔调改革是五四新文学终将完成的任务,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以后,个人声调代替传达圣旨,必然会演进出小品文笔调一派的诞生和繁荣。所以,他坚信“谈话(娓语)笔调可以发展而未发展之前途甚为远大,并且衷心相信,将来有一天中国文体必比今日通行文较近谈话意味,以此笔调可以写传记,述轶事,撰社论,作自传,此则专在当代散文家有此眼光者之努力”。或许当时人囿于时事,浮躁于事功,未必都能看清这一点。但当我们把眼光移向六十年后的今天,对林语堂的预言就不难理解了。
六十多年来新文学历史上对林语堂毁誉不定,但批评者更多的是出于对新文学于社会现实功利效益的考虑,而非对小品文文体本身的批评;再者,林语堂在三十年代提倡闲适笔调、个人笔调时,有意无意地迎合了当时的都市大众文化消费的趣味,回避了他在二十年代提倡《语丝》文体、笔调理论时所包括的现实批判因素,这给当时知识分子既要抗衡来自国民党官方的文化专制政策又要经受大众消费文化在世俗层面上的腐蚀,多少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即使在今天,这种影响也并非完全可以漠视。
标签:林语堂论文; 周作人论文; 小品文论文; 现代评论论文; 文学论文; 语丝论文; 人间世论文; 散文论文; 白话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