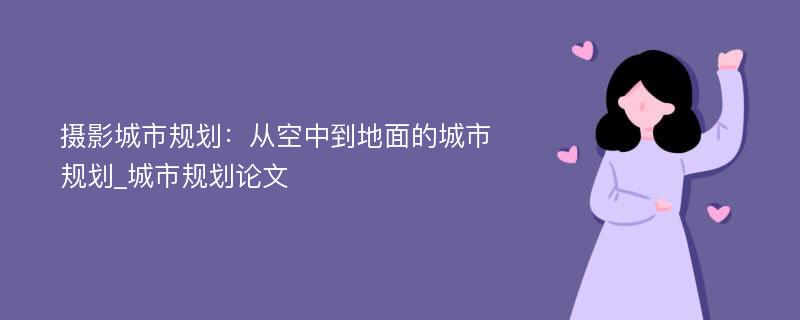
摄影城市规划:从空中到地面规划城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规划论文,地面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摄影术利用空中摄影展现城市,把哥特式教堂顶端的凸雕和塑像带到人们面前。所有的空间布局都以不寻常的组合收录入主要档案,使人类再也难以接近。
——塞弗雷德·克拉考 《摄影术》①
空中摄影始创于巴黎,由于它成型于从18世纪80年代的首次热气球航行到摄影师纳达乘热气球俯拍城市期间,可被视为传统“空中鸟瞰”的延展。空中摄影从一开始就既是“真实”的工具,也是超现实的载体;它越来越成为满足规划者的空想与现实双重理想的特有手段。② 正如克拉考所说,这种视角完全脱离地面,势必增加摄影媒介固有的“距离感”,因而增加了其假想的客观性,当然还有由于缺乏难以处理的个人或社会对象而固有的可操控性。
然而,具有真实效果的照相机也是抵制空中鸟瞰视角的一个主要工具。基于街景照片的传统,照相机在20世纪20年代阿特格特的重新发现之后,越来越成为反对空中视角规划者的工具,它为激进者和怀旧者们提供“站在地面”的视角,倡导城市规划艺术应顾及历史及社会情境。从这种意义上说,关于摄影术在城市规划中的辩论和应用重新提出了早在巴隆·奥斯曼之前就开始的拆除与重建之争。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场论战(仍在进行中)在现代历史中的两个时刻:一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勒科尔比西埃确立了空中视角的规划作用,二是五六十年代对这种观点的不完全成功的抵制。
众所周知,勒科尔比西埃对飞机有着偏爱:《走向建筑学》(G·克雷和西,巴黎,1923)的插图和内容,他对拉丁美洲的空中素描,以及他的摄影集《飞机》(摄影室,伦敦,1935)仅是部分例子。在此他的圣埃克苏佩里情结得到了明确体现。③ 他于1935年回忆道,他对飞行的热情最初是被1909年在圣米歇尔码头经过他学生宿舍的兰伯特伯爵的飞机轰鸣声激发的:“我听到一种噪音,它第一次充满了巴黎的整个天空。在那之前人们只熟知一种来自天空的声音,就是雷霆风暴之声。”后来,在为皮瑞特工作时他回忆道“奥古斯汀·皮瑞特……猛冲进了工作室……‘布莱里奥已经越过了英吉利海峡!战争结束了:不会再有战争了!不再有什么前线了!’”④ 从那时起空中景观,即使还不是实际上的鸟瞰视野,也已经成为勒科尔比西埃表现性以及概念性技术的一部分。的确,他对飞机的迷恋迅速取代了对汽车的热情。如果在《走向建筑学》中德拉奇大体育场足以和帕台农神庙媲美,那么飞机则成为新式住房理念的模型——“从建筑学角度讲,我把自己置于飞机发明者的精神状态中。”⑤ 书中邻近房屋的展现即由此而来。(它不是如Maison Citrohan般像汽车的房子,而是飞机制造者制作的与飞机原理相同的房子)就帕台农神庙而言,一张来源于《光辉城市》(樊尚,弗雷艾尔和西,巴黎,1933)的照片显示的是从神庙柱子之间看到两架飞机的景象,这证明到1932年,汽车的确已被飞机取而代之了。
勒科尔比西埃把飞机作为建筑模型以及规划工具,我们也可从中看出他清晰的思维进程。因此在《走向建筑学》中,第四章第二部分以“不寻常的眼睛”为标题,用插图展示了飞机在地面上的细节和飞行中的样子。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班轮”着力解释关于“组织”的问题,即按照机器运行特有的不可变更的规则来组织小型城市——“班轮是在这种新思想下组织一个世界的第一步。”⑥ 书的最后一部分“汽车”则讨论标准与类型的出现,讨论在希腊建筑从Paestum到帕台农神庙的完美化进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准达尔文进化规则,以及从亨伯特到德拉奇的汽车设计。与此形成反差的第二部分“飞机”则是关于问题解决方法的:
“飞机给我们的启示不仅是它的外形,首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飞机不是一只鸟或蜻蜓,而是一架飞行器;飞机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主宰提出并成功解决问题的逻辑。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一个问题被提出就一定能得到解决。而关于房子的问题并没有被提出。”⑦
这一章的其余部分都着力于如何提出以及解决房子的问题,对引入原则性论点的飞机却只字不提了。正如比阿特里兹·克罗米那所指出的那样,勒科尔比西埃的目的是“把建筑嵌入当代生产状况”,这种状况包括对消费必要的广告。⑧ 以“不寻常的眼睛”为一章没有提到飞机上的景观——作者本人还不曾乘坐过飞机——也未提及飞机视野的特别,只有第二部分的题图阐述了这个主题,这幅题图由勒科尔比西埃取自法曼·歌利亚广告册。⑨ 飞机对于建筑学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设计须屈从于飞行强大的功能决定因素。
但如果勒科尔比西埃对建筑的理解如上述,他发展中的城市规划理论却与此大相径庭。《创新精神》中描述的“邻近的房子”是连续生产的范例,房子乃静止的飞机,飞机是飞行的房子。在这里,飞机作为生产方式的同义词,不像它作为规划的技术性视觉工具那样显得非同小可。如同照相机、望远镜和显微镜一样,飞机也成为一种视觉工具,它所揭示的面貌使它对城市规划尤为重要。如果正如克罗米那所说的那样,对勒科尔比西埃来说照片不仅是对建筑的“记录”,它还可以起到如镜头般的作用让人们观察周围地形,那么规划者眼中的航拍照片则是城市形态的关键。组成《城市规划》卷(G·克雷和西,巴黎,1925)的插图和《创新精神》一组文章无不印证了这一点。在这里,飞机已经不再在功用性和精确性方面是房屋设计的同义词,而成为了承载认识,分析,概念及设计的中心工具。
在所有展现当代城市的手法中,微型立体布景作为展现19世纪大都会的重要手段受到了空中鸟瞰视角的挑战,后者在大城市规划中受到青睐,飞机场首次作为城市中心出现在罗马圣彼得城的规划图中。城市新规模的摄影证据同样是采取航空拍摄的:“同样范围和相同角度下的纽约城和‘现代城’,对比非常强烈。”⑩ 勒科尔比西埃选择了一张1909年热气球航行拍摄的埃菲尔铁塔照片作为《今日装饰艺术》的封面,这张照片已于1922年帮助罗伯特·德劳内完成了画作《埃菲尔铁塔》,在《城市规划》中这种鸟瞰视角的以及办公楼窗户视角下的埃菲尔铁塔照片同时出现——“从这些写字楼窗户望出去,我们有从瞭望台主宰世界秩序的感觉。”(11) 另外一些鸟瞰图片又被用来做规模比较:威尼斯和圣马可露天广场的景致是与“宏伟广场”形成对比的“普通大小,整齐划一的城区”;廷盖与凯万传统居住地的鸟瞰图;芝加哥经济公寓和“小块地花园房”的对比;以及巴黎旺多姆广场的照片。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选自法国航空公司的两张照片,分别拍摄档案馆区和香榭丽舍区,它们之间的比较揭示了城市状况。照片的说明如下:“这是但丁笔下第七层地狱的写照吗?不是啊,这是成千上万居民令人恐怖的栖身之所。巴黎城不拥有这些揭丑的摄影文件。这种全貌就像一记重锤。”勒科尔比西埃讽刺了以历史浪漫来吸引游客的做法,“漫步者游荡在迷宫似的街道上,眼睛享受着一幅幅图画般的破败景象,历史感油然而生”,并把这种感伤情绪与“肺结核、道德败坏、贫困、羞耻”的猖獗相提并论,而“巴黎景观委员会”却对此袖手旁观,只怀旧地收集罗列古旧铁器标本。(12)
航拍照片(巴黎还未拥有的指控文件)已成为战事工具,或审判中反映城市面貌的证据。对勒科尔比西埃来说,一张航拍照片就能揭示一切真相,展现从地面无法看到的东西,清晰展露时间本质。勒科尔比西埃的最后一记重锤,就是把需重新开发的马赫地区的航拍景象与同一范围的重新规划方案放在一起对比。(13)《城市规划》的末尾是一幅17世纪路易十四设计巴黎残老军人院的版画,图中Fama在巴黎上空翱翔,勒科尔比西埃干脆用飞机之眼取代了绝对的王权。
战争的比喻是恰当的,因为从1914到1918年空中拍摄的照片完全成为了侦察工具。随着战事的发展,空袭和空中侦察被紧密联系起来了。1935年,勒科尔比西埃回忆道,“飞机可以是鸽子,也可以是老鹰。结果它成了老鹰。这是一个多么出乎意料的礼物,它能在夜幕中起飞,在夜色的掩护下飞向沉睡的城镇并用炸弹播散死亡……它能用从喙状头部伸出的机枪进行扇面扫射,把死亡射向蜷缩在洞中的人群。”(14) 对抗初期,德国飞艇残骸上发现的一架照相机给了法国人灵感,在巴黎大学的前摄影学教授路易斯·菲力普·克拉克的协作下,法国空军组建了摄影队。直到1920年,这支部队与布尔茹瓦将军领导下的地理情报机构并列空中情报来源之首。战争即将结束时,军事情报又帮助了考古研究的发展。在叙利亚,熟悉空中侦察技术的法国和英国考古学家们用“空中探索照片”来进行研究。
从奥斯曼开始,巴黎重建政策中就已经把军事和城市相结合,而在1933年勒科尔比西埃在结束莫斯科之行后所著的《光辉城市》一书中,这种结合被巩固了。勒科尔比西埃在《飞机》中写道,他在这次旅行中已经从实用和概念两方面发现了飞机的潜力;“我想乘坐飞机能使旅行变短。我在勒布热、科隆和柏林都发现了机场。我认识到人们凭借信仰和决心的力量,一点一点,不讲章法地配置了飞机库,仪器,建筑物和员工。飞机场同火车站一样。瞧,人们在规定时刻出发,又在同样精确的时刻抵达。”(15)
《光辉城市》一书更对新的空中经验饶有兴趣。此书以一张1930年10月科斯特穿越大西洋的照片为开头,就如同工程师莫班建筑悬臂梁钢筋混凝土飞机库的例子一样。(17) 为了使这个计划与战时理想同步,这座“光辉城市”的构思不光依赖空中视角,而且也考虑到了接受空袭下生存能力的考验,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危险愈演愈烈。勒科尔比西埃援引了法国和德国军事战略家的证据,即陆军中校保罗·沃蒂埃的《空袭威胁及国家未来》(巴黎,1930)以及外交家、工程师汉斯·肖茨伯格的《建筑技术的对空防御》(柏林,1934),来证明这座城市具有防卫能力,可以抵御空袭。针对空中武器带来的“顶级罪恶”,勒科尔比西埃认为光辉城市将是唯一“能从空袭中成功幸免”的城市,因为它的建筑带狭窄,中弹目标小;混凝土屋顶能提供保护,空调以及自动电梯能对抗毒气,而炸弹若落在公园内则是无害的。(18)
对于新型的沿高速公路,海岸线或山脉而建的区域城市来说,空中鸟瞰照片能提供更大的帮助。勒科尔比西埃在南美的经历是决定性的。他在1929年乘坐了梅尔莫兹和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的由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巴拉圭的木质飞机,这是两个地区之间首次载客航行,也是勒科尔比西埃的第二个主要飞行经验,他的回忆充满诗情。勒科尔比西埃从空中观测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地貌,包括殖民拓居地,森林,河流,草原等等。(19) 他写道这种奇观是“无垠的”。这种景象引起了有趣的联想:“地球就像一个熟鸡蛋,是一个皱巴巴外壳包裹着的一团液体混沌,”还有“像熟鸡蛋一样,地球表面有饱和的水,并不断进行蒸发和冷凝。”(20) 作者还以崇敬的心情从地平线观察了薄雾散去,晨露挥发的乌拉圭清晨,这种景象是“令人眩晕”的。但在这种奇观之下还存在另一种现象——在丛林和水源的覆盖之下,土地正在蜕变。这恰恰与之前形成对比,“这个熟鸡蛋让我们忧伤和绝望;甚至让人神经衰弱。地球到处都是腐烂的痕迹。”(21)
1964年,勒科尔比西埃回忆圣埃克苏佩里曾经告诫过他:“勒科尔比西埃先生,您得准备好,飞机已经赋予了人类从12,000甚至30,000英尺高度俯瞰地面的眼睛。”勒科尔比西埃回应道:“我已经应用30,000英尺俯瞰的眼睛好几年了!”建筑师又拥有了一种新的眼睛:这是一种新的视物方式,鸟类的眼睛被移植到人类头上了;这就是空中鸟瞰视角。理性智慧过去通过分析、比较和演绎才能得到的知识,突然成为了眼睛的直接经验,而直接观看显然是比用大脑思考更有力度的认识方式。(22)
在1000米的高空旅行所带来的平静和净化效果,支持了勒科尔比西埃提出的与“地狱景象”相对立的“人文景象”,前者是在火车或汽车里观看到的景象。与事物的距离可以使人获得平静的思考,他总结说,“我只有在观看时才存在于生活中。”(23)
勒科尔比西埃在描述巴拉那三角洲时得出的熟鸡蛋哲学和“迂回法则”势必对他规划里约热内卢,以及后来规划北非产生影响。空中视角使殖民地的占领作为技术空间的一种无限制神化得以实现。曼弗雷多·塔夫里描述阿尔及尔规划时说,空间环境被“潮涌般的”占领了:“技术,或者它的形象像岩浆一样扩散入现实,并包含了现实。”飞机创造了新式的雅典卫城,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与自然之战”也带着“些许迷惘”。(24)
在拉丁美洲,更在阿尔及利亚,勒科尔比西埃不光把空中俯瞰视角作为普查方式,更作为监测方式。人种学家马赛尔·格里奥尔曾领导了1936年研究多贡的探险,他向巴黎地理协会赞扬了航拍照片的优越:“很明显,它确立的文件构成了官方行政管理的首要工具:统治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它……出于同样理由,人种学研究可以帮助殖民政府执行涉及不同方面的艰巨任务。”(25) 这无疑是了解土著民族的一种方式,但同时也是殖民地监督。在航空部和Gao空军的协助下,利用航拍摄影技术,格里奥尔仅用了陆地观测时间的三分之一就完成了对尼日尔和多贡领地的探索。在1935和1945年之间,从《光辉城市》到《四条路线》,勒科尔比西埃不断地扩展这种殖民地/领地/空中的视角来促成欧洲以及世界的规划,在这一过程中他创建了“魔术地理”,这一术语来源于政治社会学家汉斯·斯皮尔在1941年的《社会研究》中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26) 如果我们把勒科尔比西埃的《四条路线》中的欧洲航线地图和斯皮尔对德军利用地图作战争宣传的解释做个比较,就足以证明这点。
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1941到1945年间军事侦察所带来的显著技术进步,航拍视角成为了一种主要规划工具。在法国,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保罗·尚巴特·德·洛维的努力实现的,此人是一名地理兼人种学家,在人类博物馆附属的CNRS工作,1936年曾乘飞机穿越了撒哈拉沙漠,帮助格里奥尔完成其“人种学任务”,1942到1945年在法国自由军作战期间获得“人种学家飞行员”称号。(27) 1948年在他编著的《世界航空发现》(法兰西地平线,巴黎,1948)中,尚巴特宣称“鸟瞰视角下的世界”是现代性的新视野。(28) 在同一本书中,立体地形图博物馆的馆长米歇尔·巴航撰文,把“城市规划者对航拍摄影技术的利用”既作为对奥斯曼式改建的批判,又作为对勒科尔比西埃规划马约港的三维现代性的颂扬。他认为,勒科尔比西埃的空间口号以及表现都来源于航拍摄影技术。(29) 他这样写道:“空中视角下的巴黎中心显示了奥斯曼改造旧区以及有时改变被百年历史逐渐和谐化的遗址的程度。”(30) 这并未阻止他赞颂勒科尔比西埃的工程,他认为,他实现了“鸟瞰视角和三维城市规划”的完美结合,抵制了采取离地面太近的视角的“鼹鼠城市规划”:
“勒科尔比西埃是伟大的建筑和未来城市规划的先知,过去二十年来他已经引导我们走向这种研究。他的所有关于三维建筑和融会主要艺术的想法都表现在源于航空摄影的图纸中。从行政管理大厦的露台到任何一种建筑,都呼吁鸟瞰视角作为一个城市的日常视角,而且无论如何,这种视角都不会让人失望。”(31)
两年后,尚巴特又出版了一本关于航空摄影的技术手册,认为这可以给“地球上人的研究”,以及人文地理学,人种学,考古学,还有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各方面带来新的理解。(32) 他对法国西南部小村庄厄特作了个案研究,通过空间追踪分析了巴斯克和加松居民间的关系。他系统研究了地区和区域的空间监测,以及摄影在各角度的作用。但他最关注的是每种成像规格的不同技术和几何形状——特殊的滤色镜,彩色屏幕,快速摄影,红外线摄影,以及首要的多角度视角。为了满足各种不同的拍摄要求,他详细展示了角度、飞行方式以及不规则地形的走样,然后从几何学角度分析了纠正技巧、立体成像视角及检测。
尚巴特的另一著作把视野从广阔的地域转移到了巴黎城,极大地影响了1958年后的环境主义者。在此他发现了空中监测不光可以记载物理地形,也是记录社会变化的最好方式:“在研究社会空间时,关于它的大部分重要解释都与空中视角的图形记载有关。空中观测对比图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社会空间,还有某些过程。”(33)
的确,用尚巴特的话来说,空中鸟瞰视角是开启城市社会空间综合视野的唯一方式。“社会空间”是他巴黎研究第一部分的主题,这部著作深受莫里斯·哈尔伯瓦克斯的影响。勒科尔比西埃为巴黎所著的《邻国地图》即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对尚巴特来说它“虽然在某些方面稍嫌夸张”,却还是让人佩服的,他也第一次拉开了关于规划的“真正论战”,尤其重要的是它考虑到了“基本象征性纪念物”的价值以及全体民众对此的接受力。1949年以后,尚巴特在研究住房问题及社会后果时,仍对勒科尔比西埃保持着相当兴趣。
我所正在谈及的这位尚巴特·德·洛维先生是飞行员,人类学家以及航拍视角的社会学家,有趣的是,他也是1958年到1968年之间环境主义者批判城市规划,尤其是批判勒科尔比西埃所引用证据的来源。1958年6月《国际环境主义者》的第一期重载了吉尔·伊文思的《新式城市规划汇编》,插图是大幅的巴黎东南部鸟瞰照片(pp.6-17)以及一幅展示典型地理特征的“地图”(p20)。紧随其后的是题为《威尼斯战胜了拉尔夫·拉姆尼》(p28)的文章,此人原本的目的是绘制一幅威尼斯的心理地图,结果却(由于厌倦)只完成了“纯静态方位”,迷失在威尼斯的“丛林”中。插图也直接来源于尚巴特,表现了生活在十六区的一个女学生的所有行动,(PAP,I,106)空间限定通过她的房子,钢琴课以及科学政治课程表现出来。当然,环境主义者在此强烈声援打破这种空间以及心理界限,创造新的城市“心理地图”,这种地图被打破成相联系的四部分,各部分以箭头连接,以显示更迅速和随意的运动。居伊·德鲍尔推荐了出租车。德鲍尔的地图描绘了巴黎一部分的社会组成,这种灵感似乎又一次来源于尚巴特。
正如彼得·伍伦在和我的一次对话中提到的那样,环境主义者们正在用一种极其相似的方式拥护从上方规划城市以及规划整体性的概念,这与他们的对头勒高布泽其实是相似的。直到1961年,在刊登在《国际环境主义者》第六期(1961)33至37页的《反对城市规划的言论》一文中,罗尔·瓦尼热才最终详细阐释了环境主义者对尚巴特的批评。在1961到1968年之间,IS(国际环境主义者)不断避免提到实体性的主张(康斯坦由于把环境主义者观点应用进了建筑工程的实际术语中,而于1960年遭到驱逐),而提出一种创所未想的城市规划——一种集街道,心理和政治需求以及人口需要为一体的“一元规划”。这时的照片主要表现“未铺砌的街道”——“街道下即是海滩”——以及1968年的涂鸦革命。
可以这么说,摄影革命的另一面在此显现出来——即其内在的对鸟瞰视角的批判:就像超现实主义者所演示的那样,摄影术是同样有力的批判工具,因为它利用了“陌生化”的现代技巧,尤其依赖照相机的“真实效果”。相机日益突出的便携性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瞬间被作为事实真相捕捉下来。1930年,皮埃尔·麦克奥兰在阿特格特著作的再版绪言中说,这种照片揭示了一个城市的私密,而不是它的“正式性格”:“城市并不是通过官方建筑来显示个性,而是通过一些外表模糊的热闹街道,它们就像小曲,蕴涵着微妙的爱国主义。”从30年代开始,在左右两个阵营中,流行小曲,小巷,熟悉的叫卖声就已同正统文化对立起来,迥异于怀旧的音乐厅和摄影杂志。阿德里昂·里文坎在他的《街道喧闹声》中把这种情结与莫里斯·谢瓦利埃联系起来;勒内·克莱尔和罗伯特·德瓦诺分别利用电影和摄影确立了这种体裁。
这场运动势头强大,右边有布热德主义的支援,左边有流行前沿精神撑腰,并且无疑得到了二战后向往和平生活的怀旧情怀的支持,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会把鸟瞰视角拉向地面。从某种角度来说的确如此,尤其对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许多1968年运动的领导者和《国际环境主义者》的读者都被亨利·莱弗沃呼吁的居民“对城市的权力”以及他对日常生活微妙而重要的结构的强调所影响,背离了传统艺术学校。受环境主义者影响,这种意识被越来越多地借鉴,以改造曾严重破坏市中心以及造成郊区荒废的建筑原则。安东尼·格拉穆巴,罗兰·卡斯乔和克里斯蒂安·德·伯桑巴克等建筑师和理论家们开始修正他们的观念,发展了与“单纯”的传统现代主义相对的“不纯”理论,认为城市应该建立在几世纪以来连续变化过程的基础上,而不是现代发展所造成的理想决裂。
这代人虽然反对城区整体拆除,却不能免除19世纪的勒阿尔市场被拆除以发展现代商业的厄运。而围绕这种“故意破坏文化的行为”的争论并未阻止政府兴建蓬皮杜中心,它由英国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和意大利的伦佐·皮埃诺共同设计,时至今日仍对法国现代主义有着影响。这项高科技洁净完成于1977年,它的内部管道构成了外部五颜六色的构架,建筑的一面是有着透明扶梯的银行,可以观看城市景色。这栋建筑定义了一代建筑家的基调,指导了密特朗总统的宏伟计划的风格和方式。
因此,从二十世纪末的角度来看,勒科尔比西埃的鸟瞰视野和荣于身后的“效果”一直影响着法国现代主义。由伯纳德·楚密实施的密特朗的“宏伟计划”包括了对十九世纪法国角斗场原址上的维莱特公园的开发——作为卢浮宫新入口的由贝津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国防部的立体拱门以及巴士底广场的剧院和图书馆——这一计划似乎是受了这样一种理念的控制,即从空中看来,这些棱柱形的新建筑应该是现代建筑的代表。密特朗亲自挑选了这些工程,它们都是法国几世纪以来理性主义的代表,拥有高科技建筑与服务、几何纯粹主义和追求透明的完美结合。就卢浮宫金字塔来说,它强调了透明的材质,发明了一种不反射的玻璃;就图书馆来说,则背叛了保护图书不受阳光直射的原则建造了透明的塔楼。宏伟工程吸纳了众多前人的智慧,包括路易十四宏大的建筑计划、克鲁德·尼古拉·勒杜斯和雅克·路易·大卫对几何图形的革命性崇拜、亨利·拉布鲁斯特维克多·巴尔德的玻璃和钢铁建筑物、奥斯曼的大规模规划项目、最后是勒科尔比西埃把所有这些传统吸纳进抽象的现代主义。因此它所吸收的是三个多世纪以来国家集中支持的现代主义和它的建筑表现。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空中鸟瞰视角与地面视角的对立,例如,可以应用拉莫里斯的经典电影《红气球》中的观点。一方面,电影中的静物与德瓦诺学派相呼应;在表现“环境”以及小事件时可以发现肮脏又熟悉的角落,“地带”遍布的sine Apollinaire浪漫,生活的常规被不经意打破;“微小”与“宏大”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帕斯卡尔的视线方向,就会发现他总是望向天空,看着漂浮的气球。当他最后逃离了他的折磨者——母亲,学校和地痞——他最终奔向了天空,紧抓着能让他俯视已逃离的世界的气球。这又回到了纳达的出发点。我们完全可以做此设想,帕斯卡尔成为了一名职业建筑家或规划者,或许在报复曾经压迫过他的小角落,因此总以宽敞的大地方来消灭和代替狭窄的巷子。当然,1968年以后人们不再怀疑无处不在的鸟瞰视角以及勒科尔比西埃视角的复兴了。多米尼克·佩罗的照片拼贴画《法兰西图书馆》赢得的视觉争论印证了这一点。
(本文译自A Companion to the City,Ed.Gary Bridge and Sophie Watson,USA:Blackwell Publishers,ltd,2003,pp.35-45)
注释:
①塞弗雷德·克拉考,《大规模饰物:魏玛组文》,托马斯·Y·列文翻译、编辑并作序(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95),p.62。
②关于空中摄影史常有著述,博蒙·纽霍尔的优雅作品《飞行中的相机:从天上和太空俯瞰地球》(黑斯廷斯,纽约,1969)也许是最精练的一部。该书以纳达摄于1856年的首帧热气球照为开篇,结尾是1968年从双子星座四号航天器上拍摄的一组照片。
③参见布律诺·佩德莱提的重要总结" Il volo dell' etica," Casabella,531-2(一月至二月刊,1987),pp.74-80。
④勒科尔比西埃,《飞机》(摄影室,伦敦,1935),pp.6-7。没发表的法语原文“空中史诗题图影象”刊印于Casabella,531-2,pp.111-13。
⑤《走向建筑学》,p.85。
⑥同上,p.80。
⑦同上,p.86。
⑧比阿特里兹·克罗米那,《隐私与宣传:作为大众传媒的现代建筑学》(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94),p.159。
⑨《走向建筑学》,p.81。参见斯坦尼斯劳·冯·穆斯编著的《创新精神:勒科尔比西埃与工业1920-1925》(恩斯特及索恩,苏黎世,1987),pp.248-9。
⑩勒科尔比西埃,《城市规划》,p.164。
(11)同上,p.177。
(12)同上,p.268。
(13)同上,p.274。
(14)《飞机》,pp.8-9。
(15)同上,p.10。
(16)勒科尔比西埃,《光辉城市》,p.15。
(17)同上,p.20。
(18)同上,pp.60-1。
(19)勒科尔比西埃,《精确细节:关于建筑和城区规划的现状》(樊尚,弗雷艾尔和西,巴黎,1930),pp.4-7。
(20)同上,p.5。
(21)同上,pp.6-7。
(22)同上,p.83。
(23)同上,p.8。
(24)曼弗雷多·塔夫里,《“机器与记忆”:勒科尔比西埃著作中的城市》,收入H.艾伦·布鲁克斯编辑的《勒科尔比西埃》(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1987),p.210(203-18)。这是现有的分析勒科尔比西埃的城市规划及其与19和20世纪的思想渊源最深入和最有启发性的文章。
(25)“很明显,它确立的文件构成了官方行政管理的首要工具:统治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它……出于同样理由,人种学研究可以帮助殖民政府执行涉及不同方面的艰巨任务。”(马赛尔·格里奥尔,《航空摄影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收入《人类学》1937),pp.474-5。地理学家P.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普通地理》一书中,航拍照片比比皆是,这就是1935-1939年间“航拍地图绘制术”发展的结果。
(26)汉斯·斯皮尔,《魔术地理》,发表于《社会研究》,8(1941),310-30。
(27)埃马纽埃尔·德·马东,《航空地理》(巴黎,1948),p.15。
(28)保罗-亨利·尚巴特·德·洛维编《世界航空发现》(法兰西地平线,巴黎,1948),pp.19-56。
(29)米歇尔·巴航,《城市设计师对航空摄影的利用》,收入《世界航空发现》,pp.316-26。
(30)同上,p.316。
(31)同上,p.325。
(32)保罗-亨利·尚巴特·德·洛维《航空摄影》、《方法-过程-诠释》、《地球上的人之研究》(阿尔芒·科兰,巴黎,1951)。
(33)尚巴特·德·洛维,《巴黎与巴黎居民点》,共2卷(皮甫:巴黎,1952),第二卷,p.5。在他的文献目录中,尚巴特列举了勒科尔比西埃的文章《现代民居》(收入《人口》,巴黎,1948),以及《光辉城市》(1935)和《巴黎的命运》(索尔洛,巴黎,1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