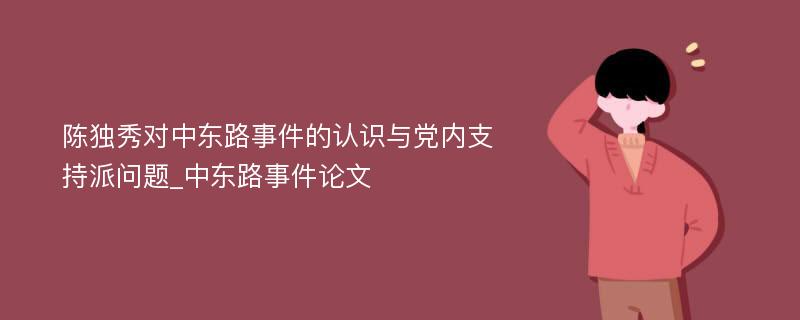
陈独秀对中东路事件之认识与中共党内托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派论文,东路论文,党内论文,对中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中东路事件”是伴随中共党内“托派”问题形成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指出:中东路事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产生的“契机”,围绕中东路事件产生的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与苏联共产党内的“托派”问题,在实质上有很大区别;中共党内“托派”问题的产生,是中共党内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所产生的不同意见,渗入了苏联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后产生的。明确地说,陈独秀对中东路事件的正确认识,影响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志在中共党内的体现,特别是影响了苏联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实现,这是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
中共党内托派问题最先酝酿和产生于20年代中期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间。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苏联共产党内展开两派间的大辩论时,许多留苏的中国学生卷入其中。1927年底,苏联国内开始“肃托”后,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被遣送回国。随着这些人的回国,“托派”的影响才日益渗入到中共党内。陈独秀等通过这些留学生,在1929年5月前后接触到托洛茨基的有关文件资料,在有关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上,与托洛茨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并在其后7月开始发生的中东路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与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苏联发生分歧,最后被打成“托派”,中共党内托派问题真正形成并公开化。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都普遍认为“陈独秀完全接受托派有关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而“堕落为托派”;“陈独秀接受托派的观点,欲以托派面目改造党,则是酝酿已久的必然事件,是他与党中央争论的主旋律”,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他与党的决裂”;“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不发生‘中东路事件’,他也是要与党决裂的”。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因犯有“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而离开领导岗位。一段时期内,陈独秀很少对中央现行的路线发表议论,直到各地武装起义,他才给中央写信,指出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绝不会象中共中央所估计的那样快,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象中央所估计的那样高昂。现在群众虽有斗争,但拿它当作革命高潮来到的象征还不太够。应该说,这有一定的正确性。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的不同意见遭到“左”倾的中央领导人的攻击,被说成是“超等机会主义者论调”,是“政客式、落后的、不信群众力量,不见群众力量”,“简直是没有群众的估计”,是“虚伪老成的机会主义余毒”①。对那些“超过事实的指摘”,陈独秀“默不答辩”,但内心深处却极不平静,对中央“左”倾的不满和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产生新的中央的厚望交织在一起,他一方面拒绝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邀请,一方面期待“新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能够自己醒悟过来”②。对“左”倾盲动主义以及“革命高潮”论“加以相当的矫正”。
1929年春,彭述之从回国的留学生中,获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个重要文稿:《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1928年6月5日)、《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彭述之认为托氏分析极为精辟,并请陈独秀研究。5月,陈独秀又通过尹宽看到了“我们的话派”③印发的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件、文章和书信,发现托氏的某些观点,特别是他指责斯大林文过饰非,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个人的做法,与陈独秀一段时期以来反省的结果,即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指导上的错误完全一致时,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托氏的这一“基本观点”,他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意见反映出来。
5月27日,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当局因中东路问题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事件,苏联政府向中国方面表示抗议,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中共中央在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指出了“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这种一切以苏联为中心的口号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引起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人的不满,陈独秀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苏联是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担负者,现在却要在新的中苏民族冲突中去“拥护”它,这从情理上讲是通不过的,更何况中东路问题是很复杂的,而中苏间的纠纷也不仅仅是阶级间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民族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中共中央觉察到陈独秀的变化以及托洛茨基主义的传入。6月底,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强调: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④。“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⑤这一切表明从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有关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观点开始,“左”倾中央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陈独秀指斥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中国的反对派”了。
二
1927年7月10月,南京国民政府以武力收回中东铁路局管理权,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指责中方行为是“非法行为”,17日,又宣布断绝对华外交关系,中苏冲突不断升级直至发生武装冲突。
“中东路问题发生后,中央曾得到国际一个短电的指示”,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加紧中心城市工作特别是哈尔滨工作及拥护苏联的宣传”,同时中共还“得到国际代表团的帮助”⑥。这样,中共中央在7月1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号召全国的劳苦群众,在国际反帝赤色日——8月1日举行示威”,“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并表示“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就是苏联的失败”这些观点。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一般原则和意义上说,这是对的、无可厚非的,但把它放在中东路事件这一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上,显然就太简单化、太幼稚了。接着,《红旗》等中共中央党刊又发表了《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第一系列过于“左”倾和幼稚的文章,有的文章甚至提出:“中东路系俄国国家出资,在中国境内建筑,所以规定为中国与苏联共管,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主权。”⑦“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根据地”⑧。很明显,这种旨在证明苏联应当在中国享有权利的理由,是很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
7月17日,中共中央第41号通告更进一步指出:“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应尽可能的号召群众起来,作特殊抗议中东路事件的行动”,“务使反帝国主义战争保护苏联的口号成为农民群众中通常了解的口号”⑨。共产国际执委会十次会议决议指出:“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进攻是主要的危险”⑩,并强调:“不粉碎右和‘左’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分子,不坚决克服调和主义态度,就不能完成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在新高潮的条件下所面临的任务,就不能完成防止战争的危险和保卫苏联的任务。”(11)决议要求“采取一切必要的准备措施,使国际无产阶级在8月1日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的行动具有对革命无产阶级力量实行战斗检阅的性质”(12)。18日,共产国际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书》,要求各国共产党“为保卫苏联而前进”,其中特别要求中共“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
一系列“左”的口号,最终改变了陈独秀自大革命失败后在政治问题上长期沉默的态度。其中包含了陈独秀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中“苏联”因素的连续性思考:中共领导人缺乏独立性,过分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乃至过分迁就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使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一些错误的思想及策略在中共党内畅行无阻,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和托洛茨基有某种“共识”。陈独秀觉得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7月28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了第一封信。他强调:中东路事件“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因此,对于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方法”,“不能象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越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割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他认为,“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因此,宣传苏联不放弃在中东路的权利“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军事根据地”,这种说法不能服人。从信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批评和建议中央不要把中东路问题简单化,目的是为了让群众“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13)。但信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政策的内容,事实上这也是对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上所持立场的一种挑战。这是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偏面的“国际主义”的一次修正。
8月7日,中共中央在《红旗》杂志上公开了陈独秀的这封信,同时发表了《中央答复撒翁的信》。中央坚持“中东路问题很明显的反映着现在世界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帝国主义有计划的进攻苏联的表现”;“中东路问题既然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所以这一事变发展的前途,将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的爆发”;“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中央的信还指责陈独秀的意见是“离开了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实际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陈独秀所提倡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信中表示陈独秀和中央的分歧,不只是“策略的讨论,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陈独秀是“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当然信中也表示“希望同志公开的发表对于政治的意见”,并准备接受陈独秀“对于重要问题的意见”(14)。
8月5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他认为中国革命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盲动主义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这是必须注意并加以纠正的,“我们若有正确的估量(非夸大的),群众斗争是能够逐渐开展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也能逐渐恢复”(15)。信中虽然没有直接谈到中东路问题,但其中所蕴含的对中共中央、苏联和共产国际有关政策的批评和第一封信是有相通和相同之处的。中央回避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诸如基本路线的争议,没有对陈独秀这封信直接作出反应。
8月11日,陈独秀第三次致信中央。他指出:“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们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接着陈独秀话锋一转,把深层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至于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并不是说对群众解释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险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之后,而不归结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说必须对中东路问题本身有了正确的详细的解析,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们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较大的效力。”他表示:“拥护苏联的口号”,“不是在原则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在策略上够不够的问题”,“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即“(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中东路问题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二)‘只是’拥护苏联的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16)。
但是,陈独秀的正确意见并没有被放在党内“极诚意的来讨论”。共产国际再次号召中共“组织最坚固的防御战线反抗进攻苏联”。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六大又根据苏共“十五大”的决定,明确宣布:“凡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都不能留在布尔塞维克党内”,并表示:“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对反对派的观点一再提出最坚决的谴责的情况下,跟共产国际的敌人就托派的反革命政纲的内容进行辩论,是多余的。”(17)
8月20日,《红旗》杂志公布了陈独秀8月11日的信,同时发表了《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最新精神和指示的影响下,中共中央指责陈独秀的观点是“极有害于革命的斗争,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的路线,必须给以严厉的批评,使全党同志得到正确的了解”,同时还指责陈独秀“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缺乏阶级的观点”,“不仅是18世纪的机械的唯物论的观点,而且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群众运动和党内概况”问题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封信,目的是通过代表团把有关情况反馈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表明中共对中东路事件的立场以及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在中东路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信中表示,“党正在以中东路问题为中心”,“开展武装保护苏联的宣传”和“动员”,并且把“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和“独秀同志之不同的政治意见的发表”等同起来,指斥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之宣传策略的讨论”,“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陈独秀“对于中东路问题,是将帝国主义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平列着看,并将战争灾祸统笼的反对,……显然是没有一点阶级观念,并给群众以极不正确的暗示,而成为资产阶级左派和平主义的宣传”。信中还明确结论:“这些见解已证明他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显然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观念无二致”(18)。很显然,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原则,都是围绕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苏共中央及苏联国家的方针、政策、利益为轴心而转动的。只要影响到苏联的基本利益,一切正确的意见和见解,都被视作异端,列入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列。这样,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托派问题的结论在所难免了。
三
8月中旬,中苏间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纠纷最终以诉诸武力的方式升级。中东路事件进一步发展,中苏两国矛盾进一步加剧。在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由于苏联方面的影响和压力,陈独秀的问题被看得更加严重。28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责他不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并表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中央也“不能公布党内不同的意见”(19)。据陈独秀《答国际的信》反映,“驻中国的国际代表曾以开除党籍当面威吓我,禁止我发表政治意见”(20)。
9月2日,《红旗》又公布了中央44号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的问题》。通告指出:“中国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与各国一样地是与党站在两条战线上,站在对立的路线上来进行分裂党之反革命的工作的。”“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借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与他一无二样地来反对现时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因此,“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自发活动,党除掉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无留恋地开除出去”。显而易见,中共党内托派问题的产生和苏共党内托派问题产生的思路是一致的,只是在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产生的表象后面,有着更深层的,但又无法明说的原因,即对苏联的中东路利益问题的态度。通告在关键处还是明确强调,“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斗争,必须从半殖民地的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相互联系上来认识苏联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好友,苏联是全世界工人的国家,而主张保护苏联”(21)。9月18日的中央第49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更明确地指示全党,要注意“扩大我们的宣传,号召群众的反抗行为,同时要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拥护苏联的一切工作”。这样“武装拥护苏联”在“左”倾中央领导人眼中成了中共一切工作的中心,谁违背了这个中心工作,谁为此而影响了苏联在中东路的利益的实现,谁就是异端,就是“与统治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一样”,“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应毫不犹豫地以组织上的制裁”(22)。
10月5日后,中央政治局在有关决议中对陈独秀的批判也步步升级。政治局的决议开始系统地批判陈独秀给中央的几封信的观点,指责他“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陈独秀“不去正确地认识历史的教训,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而诬共产国际的根本践线为机会主义!”从而“与托洛茨基主义同样的走入更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的观点”。决议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明确的认识,只有坚决的肃清党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和小组织行动,才能顺利执行党在目前紧张形势中之‘拥护苏联’与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同时必须坚决的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推进革命的发展,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思想”(23)。6日,中央又书面“警告”陈独秀,要他“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10日,陈独秀再次致信中央回绝了“最后警告”,表示要“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他认为,中央“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并表示“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指中共中央——著者注)负责的”!陈独秀谴责“左”倾中央领导人用官僚政治的“革命主义”,用“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然而,当时“左”倾中央领导人,在思想、策略甚至原则上,都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已经不可能和陈独秀等人去“公开”地、心平气和地讨论了。10月2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给中共中央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不认真了解中共党内分歧的情况下,就急于把预先设计好的处理党内分歧的套路强加给了中共中央。信中强调,“反苏联的冒险政策(中东路事变)引起一切矛盾的剧烈和全部局势的复杂化”,“共产党的根本主要任务,就是争取革命运动里的领导作用,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现在不要重复这种错误;现在要以全力鼓动并加紧阶级的冲突,领导群众的愤怒情绪,按照阶级冲突的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斗争,日益推到更高的阶段上去。”为了能够“直接拥护”苏联,“加紧阶级的冲突”,就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排除一切影响“直接拥护”苏联的因素,特别是党内不同意见分歧带来的干扰。共产国际进一步强调,“现在比较任何时候,党都应当更加保证自己思想上布尔什维克的统一,党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政纲”,“必须继续加紧暴露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的真相”,“肃清自己的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取消派”(24)。形势的发展已很难逆转,在共产国际、苏联和“左”倾中央的双重作用下,中共党内“托派”问题最终形成。
四
11月13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继续强调“保护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是“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下”“日益加重了……的二大任务”。对于陈独秀及其“反对派”,公开信指责他们“更明显地来阻挠党同敌人的斗争,站在完全与共产国际和党的六次大会及中央现在所执行的正确路线相反地位,积极的进行破坏党的一致和分裂党的活动,以公开的攻击现在的党,是卖阶级的无耻语句以献媚敌人,以极端民主化来鼓励同志反对上级指示机关之指导讨论党的政策,提出与六次大会完全相反的路线,以‘不了解’‘怀疑’的掩饰来攻击党的六次大会的路线,以捣乱式来反对讨论问题的范围与每一问题的结束而使每个会议都没有结果,绝不接受任何会议的决议,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组织内公开宣传的活动,坐在家里不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以空谈来攻击党现在的策略与行动。”公开信表示“党应坚决地予以组织上最高原则的裁制,以巩固党的一致,决不能有半点动摇”(25)。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强调陈独秀等“提议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观点和阶级观点绝对不相容的”。决议进一步指责陈独秀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表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进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26)。这样,陈独秀被开除了党藉,并最终被踹入“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的行列。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和苏联要求中共“武装保护苏联”在中共党内的障碍已经消除。12月8日,中央第60号通知指出:“取消派已经从党内反对派走上阶级的敌人”,如果“不肃清取消主义的思想和小组织,必然要使党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工作受着莫大的阻碍”(27)。
对中共党内“托派”这一顶帽子,陈独秀是不愿戴的,他还在努力为自己的政治意见和见解申辩,特别是围绕中东路事件的意见和见解,他也深知这一牵涉苏联利益的问题,是他落入“托派”误区的关键所在。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表示面对中央和共产国际、苏联的种种批判和指责,自己“不但不愿掩护”“过去的错误”,“即现在或将来”“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同样不愿掩护,同样希望同志们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加以无情批评”,当然,“只要不是附会造谣”,“都虚心接受”。他一再重申,“我说要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使还有民族偏见的‘广大民众能够同情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口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这正是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28)。此外,他还对中央把他的“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的提法作为“开除”他的“理由之一”和因为“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便说他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尽力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申辩。然而,“左”倾中央对陈独秀的问题的定性,已使陈独秀的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了。
随着中苏武装冲突的逐步平息,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一个决议,以“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形式,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问题作了系统的总结,“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并重申:“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目前主要危险”,“只有取消主义者陈独秀们,才在极明显的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中东路问题上把帝国主义战争与进攻苏联的危险平列起来;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这样的观点只是替帝国主义在群众中散播和平欺骗的空气,来松懈广大群众武装拥护苏联的决心”。“中国取消派与调和派在各方面的表现,正是与国际取消派调和派的思想,一条路线,一个系统。”(29)为接受共产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1月11日再次表示“断然排斥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将帝国主义相互冲突与其对苏联的冲突平列来看之非阶级的观点”,“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拥护苏联”(30)。至此,因中东路事件而引起的中共党内的分歧,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不同意见者被划入“托洛茨基反对派”后而暂告一段落。
五
以中东路事件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托派”问题同步产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托派”问题的产生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化,必须透过事情的表象而深入发掘更深层的东西,才能找到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产生的真正的全部的动因。
第一,中东路事件问题是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产生的“契机”。在对待中东路事件的问题上,“左”倾中央是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指导和影响的。“左”倾中央、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的立足点就是“苏联”,就是苏联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任何不同意见和分歧,都被视作异端,都被视作“民族主义”,最后都被归入“托洛茨基主义”。尽管陈独秀在对待中东路事件问题上持极为谨慎的态度,希望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不要用那种“太说教式”、“太超越群众”、“太单调”的宣传来对待复杂的“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代替“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更易于为群众所接受。但是,陈独秀这种带有明显国际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立场,从开始就和苏联的通过共产国际影响逐步实施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发生冲突,特别是影响到中共党内“左”倾领导层对苏联政策在中共党内的推行。从中东路事件发生起,陈独秀和“左”倾中央、共产国际的分歧,就已经预示了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产生的不可避免性。而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在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推行则是潜在的最深层的原因。早在1928年8月,共产国际“六大”时,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就特别强调,“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政权,没有从剥削者手中夺得生产资料的时候,它没有祖国之可言。”(31)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理论的最后落足点却是要各国共产党不惜一切地保卫苏联,而不顾其它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用苏联的民族利益代替各国自己的民族利益。共产国际在执行其政策过程中,常常把苏联的民族利益,直接等同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陈独秀和中共党内“托派”问题的产生,原因就在于此,这是值得深思的。
第二,围绕中东路事件产生的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与苏联共产党内的“托派”问题,在实质上并不是一回事。1929年5月,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接受并“完全同意”的是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的观点,这也是陈独秀本着“亲历的经验”,在“完全个人反省”的基础上而得出的“必然应有的结果”(32)。
在中东路问题上,托洛茨基本人的立场和陈独秀等人的立场也完全不同,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也要求苏联和各国“托派”,包括中国的“托派”,“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33)。托洛茨基还批判了德法等国的“托派”中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34)托氏在《保卫苏联和左翼反对派》中,还提出了激进的“保卫苏联”的方法,即“在国际范围内发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不论这些国家是不是苏联的‘同盟者’”,来“保卫苏联。”(35)这些观点与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完全不同,相反却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立场完全一致,进一步说,托洛茨基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在牵涉到苏联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的,在理论表现上可以说是两极对立。如果说陈独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右,则托洛茨基完全属于极“左”,这一点在中东路事件发展过程中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分歧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29年11月,托洛茨基致函中国托派刘仁静,不赞成他与陈独秀合作,“如果太性急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们之间,在过去的歧见(1924-1927)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能统一起来”。“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36)。刘仁静也认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和中央的分歧,并不能表明他是“左派反对派”,他认为陈独秀是“右派反对派”,是“假藉反对派的招牌”,实质是“旧货贴了新商标”。与托洛茨基有直接联系的中国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直到12月份,还称陈独秀是“斯大林主义者”要“象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37)。实际上,陈独秀从“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抵抗得最长久”(38)。这样,实际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托派”,但很快又脱离这一现象了。
第三,中共党内“托派”问题的产生,是中共党内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所产生的不同意见渗入了苏联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后而产生的。大革命失败后,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重新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历史赋予中共的重任,其间产生分歧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陈独秀在反省中即使产生错误或失误,是可以开展正常的党内批评的。但是,由于中东路事件是牵涉到苏联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因而在中东路事件上的分歧,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左”倾中央领导层看来就不同了,处理的方式与以往中共党内历次分歧都不同。对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一概冠以“托派反对派”,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处理是“坚决”、“彻底”的。这实质上是在维护“苏联民族利益”和“苏联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将苏共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问题无原则地、随意地加以扩大化和国际化的表现,是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推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的表现。同时,这也是当时中共党内“左”倾领导层无视中国革命的实际,一味迁就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片面强调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结果。事实上,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39)。相反,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着眼于争取广大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统治和拥护苏联、维护中国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宣传和努力,却显示出其很大程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也体现了其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一致性。
注释:
①《布尔什维克》第一卷,第19期,1928年2月27日。
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二),第129页。
③1929年1月由原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中的中国留学生在上海组织的托派组织。
④⑤⑥⑨(14)(18)(21)(22)(23)(24)(25)(26)(27)(2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10-211页、第228页、第412页、第382-384页、第389-393页、第413-418页、第405-411页、第461-471页、第495-496页、第791-799页、第543-544页、第550-553页、第561-573页、第593-600页。
⑦《红旗》第33期,1929年7月24日。
⑧《红旗》第31期,1929年7月18日。
⑩(11)(12)(17)(31)《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46页、第157页、第187页、第140-141页、第41页。
(13)(15)(16)《陈独秀书信集》,第432-434页、第447-449页、第454-461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
(19)(20)《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三),第124页;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2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上),第318-336页,中国人民大学。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3页。
(32)(38)《郑超麟回忆录》,第381页、第27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
(33)(34)《中国革命问题》,第313页、第319页。
(35)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第23页。
(36)(37)《陈独秀年谱》,第302页、第305页。
(39)《苏共历史问题》,1987年第10期。
标签:中东路事件论文; 陈独秀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托洛茨基主义论文; 中国托派论文; 历史论文; 红旗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