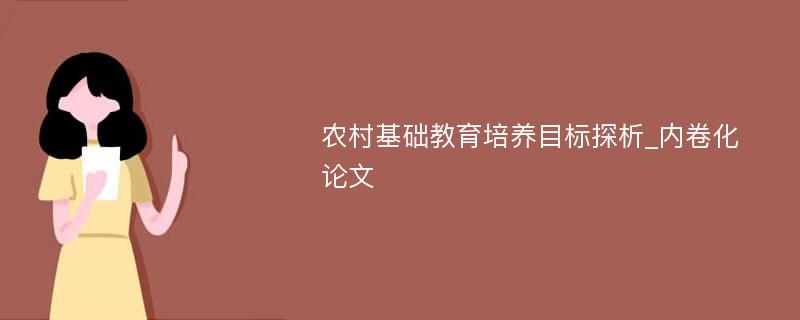
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内卷化”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培养目标论文,农村论文,内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0)03-0050-04
如果把整个农村基础教育喻为一幅画,那么“为农”和“离农”悖论就是两端的画轴,一个“内卷化”(农村劣势文化圈),一个“反向内卷化”(城市优势文化圈),这种倒戈相向的内缠一度屏蔽了人们的视野,打破“内卷化”的根本廓清画面,而由果循因以求解的内在逻辑正是打开农村基础教育这幅画的潜在线索。
一、“内卷化”概念简述
“内卷化”(involution)既可以指一种机理,也可以指一种现象,“它源于拉丁语involutum,原意是‘转或卷起来’”[1]。有学者考辨,“involution是由involute一词抽象而来,指内卷、内缠、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事物,复杂的事物,以及退化和复旧等涵义”[2]。
这个概念随着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问世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名声大噪。近年来,已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运用广泛、影响深远的一个概念。然而,也就是“内卷化”在对其周延的跨越过程中也招致了诸如“概念定义失真”和“分析导向模糊”等批评。
为了暂避争论,本文在综合各类文献的基础上,从“内卷化”的词源,即“卷起来”加以引申,并将此概念引入教育领域,解读农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两难困境。“内卷化”是指一种“转或卷起来”的现象,一个系统或模式如果表征出这种现象,便陷入积重难返的“自我锁定”状态,并对原有的路径僵化循环,不断的在自身内部精细化、复杂化,从而日渐丧失其内部制度创新和根本变革的可能性。
当下,对于农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内卷化”表现为“离农”和“为农”两种悖论的自我复制,这种停滞并封闭的延续又反过来使“内卷化”问题不断被固化和加强,使得原本就左右摇摆的教育目标越发无从抉择,只好沿着旧有的轨迹机械运作,两种僵持的文化圈进一步加固,导致农村教育目标最终囿限于这种“离农”与“为农”的正反“内卷化”当中,无以超越。
二、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内卷化”表征
目前,我国农村教育培养目标的“内卷化”与反向“内卷化”只是相互强化,不能相消解(各自都有内在的刚性),“内卷化”加剧强化反向“内卷化”自缠,反向“内卷化”自缠又强化“内卷化”加剧,这主要表现在为农教育和离农教育的向度摇摆和意愿冲突。
(一)“内卷化”:为农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政策对农村基础教育目标的定位逐渐明细化,在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驱使下,百般重视农村教育发展的教育政策中潜藏着“为农”的暗流。通过对教育政策发展脉络高屋建瓴的把握,不难发现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整体走向的“内卷化”轨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教育为本地经济服务,因而城乡发展教育的目标定向不一样,于是便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农村教育主要为当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适用人才。而且这些教育大致可以归为两点:一是教育要与农村经济相适应,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并使学生掌握服务农村的基本技能;二是在精神层面培养学生热爱农村、扎根农村。
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报告为农村教育服务农村指明了方向,时至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的深化“农科教相结合”和“三教统筹”等项改革,并于2003年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对服务“三农”进行了重申和强化。
农村教育目标如此定位宗旨是服务农村,纠正教育脱离生活实际、远离农民生活等偏颇。这种愿景固然是好的,但却不自觉陷入了“内卷化”陷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把教育看作是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具有维护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功能。“如果农村教育只面向农村劣势文化圈,那么只能导致农村孩子的低地位的社会再生产,农民永远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3]
(二)“反向内卷化”:离农教育
国家级的教育政策和理论界的学者的“为农”情结,并没有改变农村教育在实践中的“应试取向”,“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价值观在实践中悄然取代了农村教育本质目标,在为“内卷化”奔走呼号的同时,“反向内卷化”悄然破壳而出。
“实际上,‘留农’教育和‘离农’教育反映了政府的教育意愿和民间教育意图的两种不同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框架内是不可调和的。”[4]对农民而言,改变农民身份、过上城市生活、得到社会认可,是最体面的、最完满的生活状态。而“应试”是逃离农村的唯一途径,所以一代代的农村教师和家长竭才尽智的让孩子争夺这个社会升迁的机会,这就加剧了农村教育的离农性和城市性。
离农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得益彰”使“内卷化”分化出“反向内卷化”。受各方面因素制约,农村孩子只能通过应试流入城市,而这些孩子进入城市后,无论学得好还是坏,都不大可能流回农村,这就进一步壮大、巩固了城市优势文化圈,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依靠教育真正走出去的农村孩子毕竟寥若晨星,所以苦读的一大部分学子将被城市拒之门外,这些“失败者”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不禁感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现实境遇,从心理上对自身生长的农村心生怨恨,对教育开始抵触。本来质量就不乐观的农村基础教育,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和力不从心的绝望中被再次边缘化。长此以往,固化了农民的心态,而且使原本就画地为牢的农村教育的外围进一步萎缩,不知不觉中便进入了与为农教育殊途同归的样态:“内卷化”—“反向内卷化”,这种“内卷化”的直接结果是人才外流,其最显著影响是加剧了“内卷化”,对原本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村教育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内卷化”归因
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内卷化”,很大程度缘于我们预设农村可以脱离城市孤立发展的假设所致,这种二元思维背离了基础教育的内在品性,抹杀了农村教育向前发展的可能性。
(一)基础教育内涵的情境背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机会。”在基础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农村孩子不断的因教育权利被剥夺而难以享有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从本义上背离了基础教育的神圣内涵。
社会现代化特别是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狭隘的把农村基础教育目标定位于服务农村,使农民处于不利的地位,加剧城乡二元结构关系推向敌对。“强调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服务’实质上强调的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工具性功能,赋予农村基础教育阶段过重的工具性功能是一种功利色彩太浓的做法”。[5]将农村基础教育画地自限为“留农”性质,明显削弱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
(二)农村基础教育的静态理解
城乡一体化的构建所孕育勃勃生机的气息正是在于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双向流动。“我国现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2.3%,到2050年,农村人口会降到20%以下,城市人口则增加到80%以上”。[6]以农村人口状况考察农村基础教育思维方式的静态化处理,令我们难以把握农村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症结。
很多为农教育的辩护者以“脱离生活实际”为托词,提出农村教育培养目标应满足农村生活需要、致力于农村生活改造。这种声音基本脱胎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诚然,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梁漱溟等一代学人,开创了农村教育改革的先声,但是他们在农村教育改革实验中的失败也留给我们深刻的教训。“简单地斩断乡村教育与城市的联系,实现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的自我循环,通过对农村既有生活的发扬与改造,在农村与农业现状基础上是否可以‘催生’出农村的现代化呢?”[7]中国的现代化若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面对浩浩荡荡的全球化浪潮,可以说选择了孤立就等于被淘汰出局。
(三)城乡二元割裂的思维模式
城乡二元对立结构①是我国多年存在的社会特征。在二元化的映衬下,农民生活苦、收入低的双重困境压迫让更多人滋生了“离农离乡”的价值取向。“当我们言说农村教育之时,实际上也是在用一种心中默许的标尺来言说一种区别于城市教育或允许落后于城市教育的教育。”[8]
从家长的角度出发“望子成龙”是无可指责的选择,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作祟在人们心目中,城市代表着先进、富裕,改变农民身份,像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一直是多少代农村人的夙愿。实践中的“离农”渊源正是始于这种心态,然而,众所周知,农村的升学率本来就比不了城市,大部分被高考淘汰下来的学生对乡村教育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坚定地确立了下一代人“跳农门”的教育信念,而且由于自身学校教育的城市化标准使这一批批不得以而留下的学生对农村只剩下深深的消极和厌烦,一旦陷入这种无奈循环,农村教育的培养目标只能是因循守旧的路径依赖。
四、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内卷化”正解
对教育目标的思考必须兼顾现实和未来两个维度,并且求得两者的统一。“在现实与未来这两个维度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往往是后者。教育改革倘若缺乏国际与未来的‘教育视界’,因而缺失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思考,那就只能拘泥于技术性问题的就事论事的范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化解现有矛盾的目标、动力、机制也将丧失殆尽。”[9]
(一)全局性:基础教育质量
既然是基础教育,就不应该存在地域性、区域性的差异,无论在哪里基础教育都是为儿童全面发展打基础的教育,根本不可能有打折扣的道理,也没有“为农”抑或“离农”的偏差。数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差距不仅没有消解,反而越来越大,难道不说明问题吗?由于条件、师资不到位,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一直难以实现。
消除教育目标定位的悖论,基础教育的质量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关隘,教育视界的全局性是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全面发展的教育,也许在教育内容上带有为农或离农的倾向,但培养目标上和质量标准是绝不可以分化出两种尺度。虽说教育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但只有同质量的教育才会打造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诚然,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不仅仅是硬件的改造和资金的拨入,但这些都是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可能性前提。高质量的教育培养既可“为农”亦可“离农”的人才,它没有具体的指向,而是以提高全体人的素质为旨归,着眼全局,发展整体。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为农村教育培养目标的正反“内卷化”找到一种可能性的解脱。
(二)前瞻性:主体性教育
“我国城市化过程就其实旨而言乃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对抗过程。这种过程也决定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城市取向和农村取向的共时性,而绝非两者相继发生”。[10]农村城市化进程固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城市的界线不断的向农村蔓延,也许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或者消失,或者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但农村人口永远不会消失,所以农村基础教育问题也不会不了了之。
长期以来,由于功利主义观念的影响,农村教育的培养目标要么为农,要么只想离农,教育总是作为一种达到手段的工具被利用。而与此同时,其对人身心发展的内在品质被工具性所遮蔽,一味的追求“实用价值”,最终成为制约农民发展的瓶颈,仅仅作为一种工具的农村教育不可能成功,只能失败。所以农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关键是变工具性教育为主体性教育,因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本质上是自主的、自觉的、能动的主体性活动,这种主体性是与动物区别的根本特征。
教育中主体性的缺失,导致农民中较多的只是“臣民”,而非“公民”,加之农村天然的封闭性、孤立性和保守性使教育体制和教育目标更易依赖定势,形成农村劣势文化圈的刚性外延,农民缺乏能动性和冒险精神,抵制改革。难怪19世纪二、三十年代改革先驱们发出如此感叹,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主导,而我们“造势”的运动,事与愿违的是,他们不仅不想当“领导者”,反而和我们采取“不合作的日常抵抗”。
(三)战略性:“城市包围农村”
根据布东的“顶点效应”(ceiling effect)和MMI假设②的饱和定律,当基础教育推广到一定程度,若优势阶层子弟在这个既定教育层次上机会达到了饱和状态,教育不平等将出现一定的下降。
由此推之,基础教育扩展到饱和程度后,人才外流便不再有明显的负效应了,也进入不了“内卷化”状态,因为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城市具备了精力和财力反哺农村。而且从“推拉理论”中,容易得出农村人口外流是流出农村的推力(实然状态)和流入城市的拉力(应然追求)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是合力作用下的人口流动。若一味固守为农教育而淡忘农村城市化的大趋势,便会导致一种褊狭的文化实用主义,造成低社会对位的文化再生产,制约和阻碍了农村人口的代际流动。“到2020年有约1.2-2.3亿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过程。”[11]这种巨大的城乡结构变化,标志着农村人口在未来的几年内会急剧下降,而且在这庞大的转移人口中,当下农村基础教育适龄儿童占据着相当比重。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动态的眼光和复杂性思维去考虑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在提高质量和关注主体的前提下,切实施行新式的“燎原计划”,即以城带乡共同发展,力图使农村基础教育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农村教育的“内卷化”与“反向内卷化”双向“强化”,为农与离农二维冲突,在现代化与全球化并驾齐驱的冲击下,已到了不得不重新考虑的关口,挑战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麦克拉伦(McLaren)所说的,“要不断的突破边界线,尽管它们会不断地卷土重来或愈加的顽强”[12]。
注释:
①城乡二元对立与城乡二元结构不同。城乡二元结构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是在经济超越过程中形成的,而城乡二元对立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极端形式,不再只是一个城乡发展差距的概念而是城乡间的割裂与分化。
②MMI假设即“不平等最大化维持”,该假设认为伴随着教育机会的扩展,不平等将最大程度的维持。具体见:刘精明.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2008,(5):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