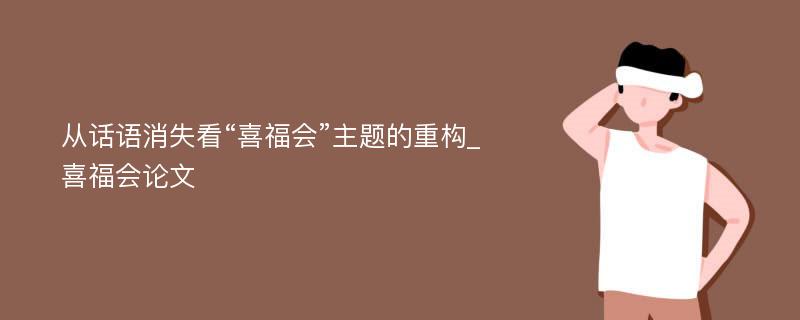
从话语的消失看《喜福会》中主体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话语论文,喜福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3831(2000)04—0018—05
随着全球范围的文化研究在英语文学界的不断升温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对经典、主流文化的冲击,目前在对美国文学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先前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与作品,投向了第三世界作家、少数民族作家(相对于白人作家而言)和女性作家。了解主流文化以外的“亚文化”正日益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而作为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地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们也在这股潮流之中被冲到了文学研究的前沿。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反映的既独特又普遍的问题和美国评论界对它们的反应是我们这些在中国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人(尤其是女性)无论从哪个角度也不能不了解、不介入、不发表看法的。本文就试图以此为背景,从一个侧面来对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 )的成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作一番重读。
《喜福会》是生长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市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于1989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同《女斗士》(Woman Warrior )的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一样,她也是根据自身的经历,选取移民的母亲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写作素材,并一炮打响。小说出版之后很长时间内都名列美国畅销书榜首,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至后来又被搬上银幕,赢得了更多的赞誉。这可以说是华裔女性文学继《女斗士》之后的又一个热点。那么这本描写美国“少数民族”女性生活的小说何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呢?评论界对此意见不一,大部分人认为首先是它那带有全球性的主题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母女间的冲突、移民自身的传统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等;也有人认为谭恩美的写作风格幽默风趣,正对美国人的胃口;被认为是一部为适应美国人口味而写的中国故事,一部文字风趣、节奏轻快、态度俏皮的“小点心式”的作品;更有人认为《喜福会》的成功是因为它充分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古老、神秘、浪漫、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的好奇心。故事中心狠手辣的男人和温柔善良、对男性与长辈言听计从的女性无不迎合了西方人民族主义的口味。毫无疑问,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 )在他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反复批评的对东方狭隘、肤浅的认识。 本文无意从正面反驳这些观点,而是要在一个更深的层面——非语言的层面——去挖掘作品的内涵,揭示沉默的喻义。
沉默在文学作品中犹如在口头交流中一样,表达着一种非语言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又是超出语言所能表达的思想。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他著名的《性与传入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Introduction )一书中曾为沉默作过这样的定义:“沉默本身是那些人们不愿提及或被禁止提及的事情,是不同的谈话者应学会采用的谨慎的态度。沉默并不是话语的绝对终结。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话语与沉默截然分开,然而沉默却是伴随话语而来、相对于话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强调符号为本文作者所加)。的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话语力量。正如康拉德在《黑暗的中心》中的一句名言所说,“人以声音证实自己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失去了话语的人就犹如自身消失了一般,不复存在了。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沉默不仅仅是语言的沉默,还有思想的沉默和自我意识的沉默。当话语代表的是主流文化、是溶进去就意味着彻底推翻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的文化时,沉默就是对话语所代表的社会意识与规范的无声反抗了。沉默是武器,它可以用来抵抗外来的侵略,但它也在不知不觉中自我伤害、相互伤害,使女性在潜移默化之中渐渐为自己所欲抵抗的文化和观念所同化,以至于完全丧失了自我之后还浑然不觉。借用福柯的话说,“沉默是人们表达思想的方式之一,它构成了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一部分,又渗透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中”,它是话语世界不可或缺也不容忽视的延伸。
《喜福会》所讲述的是四位华人移民妇女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儿女各自之间的故事。小说的题目《喜福会》原是母亲们打麻将的聚会。这些妇女移居美国已有几十年,但她们仍念念不忘从小受过的传统教育,恪守着中国几千年来渗透于妇女血液之中、几乎已成为天性的封建男权的思想。她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严格教育、管束自己的女儿,使她们能逃脱自己这一辈女人的命运,成为她们眼中幸福的女人。然而,对于母亲的管束,女儿们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一味反抗,在这个种族、阶级、性别不平等的美国社会里,两代女性上演了一出由相互争斗到殊途同归、相互认同的悲喜剧。在这出悲喜剧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人物口中道出的事情,而是那些她们无法启口、无法触及、讳莫如深的事情,是沉默背后的东西。在这里,沉默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它那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摧毁着女性赖以生存的自尊、自信和勇气,使她们在沉重的压抑之中丧失生存的能力。然而一旦打破沉默,这毁灭性的力量就会立刻消失,被压抑已久的人性就将得到复苏,平衡和谐的关系就会得到恢复。《喜福会》中母女们的悲欢故事大部分都是以沉默和打破沉默这条主线编织起来的。
例如在吴苏圆和吴晶梅这对母女之间,许多年的时间就是在沉默中度过的。母亲在女儿童年时曾坚决而“狠心”地以做清洁工为代价让女儿有机会去学习钢琴,希望把她塑造成一个有别于自己、能为白人社会所接受的高雅女性。而女儿却“不懂事”地一味反抗母亲的意志、母权的统治。在一次华人社区举办的少年天才表演比赛上,女儿演奏得一塌糊涂,让争强好胜的母亲当着亲朋好友丢尽了脸面。回到家里,女儿满以为母亲要朝她大发雷霆。然而,这时的母亲却一反常态地平静如水,缄口不语,脸上一副“毫无内容”的麻木表情,沉默得令人恐惧。没有受到训斥的女儿的表现同样令人吃惊:面对母亲的沉默她的反应既不是吃惊,也不是轻松,更不是害怕,而是“失望”!因为这样她就没有办法“也朝她(母亲)大喊大叫,把心中的痛苦哭出来,摔回到她身上去”。在这里,沉默就像长在母女心中的一块恶性肿瘤,把双方都折磨得痛苦不堪。这件事情过去之后的很多年里,它一直是母女之间不敢提及的禁忌话题。女儿再也不弹琴了,母亲也不坚持让她弹了。琴盖锁住了女儿的痛苦,同时也锁住了母亲的希望。沉默中女儿长大了,母亲也衰老了。沉默的结果是“母亲和我(晶梅)从未互相理解过。我们相互翻译对方的意思,我听到的内容似乎总比她说的少,而母亲听到的却总比我说的多”。相互间的沉默和误解持续了很多年。在女儿过三十岁生日之时,母亲把这架闲置了多年的钢琴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女儿,但这已经是母亲临终的愿望了。当女儿再次打开琴盖,弹起往日觉得很难的一支曲子时,她竟惊奇地发现这首曲子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难了。母女之间的这些无言的行动象征着沉默的被打破和两代人之间最终的理解与谅解。然而,代价毕竟太大了。它牺牲掉了母亲一生对女儿的期望和女儿半生的欢乐,并在女儿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沉默所蕴藏的巨大的破坏力。
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个例子是莹映·圣克莱尔和莉娜·圣克莱尔这对母女之间的故事。她们的沉默已经不仅仅是话语的消失,而是整个人的消失,是对自我的不断贬低和最终的抹杀。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终极的悲哀。可叹的是当母亲的一代已经失去了自我之后,女儿又在不知不觉中重复着母亲的故事,尽管她曾经是那么激烈地反抗过母亲的意志。故事的一开始作者就以母亲的口吻写道:
许多年来我总是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让自己的愿望流露出来。因为我沉默得太久,女儿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她坐在她那豪华的游泳池旁,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她那索尼牌随身听中发出的声音和她那身材高大无比的丈夫(的声音)……
这么多年来我总是把自己隐蔽起来,像个小小的影子般跑来跑去,这样就没有人能抓得到我。我的动作是那么的隐蔽,以至于女儿对我都熟视无睹。她所看到的就是她的购物单,她的记帐本和她那张整齐的桌子上摆着的扭曲的烟灰缸。
我想告诉她(女儿)的只有这句话:我们俩人都已经消失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别人;没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没有人认识我们。(Tan,1993:64)
正如这位母亲的这段内心独白所描述的,她为了掩饰自己屈辱而辛酸的过去——无情的丈夫另觅新欢,腹内的婴儿被她为报复丈夫而狠心地杀掉,独自逃出家庭,寻找生路——在受尽了生活的折磨之后她变成了一只“老虎”,一个“看不见的幽灵”,一个能未卜先知、看穿一切、预测一切灾难的女巫般的人物。(这样的女预言家或女巫般的人物在美国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作品中也常见,如托尼·莫瑞森、爱丽斯·沃克等人的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这一点也非常耐人寻味)。尽管她后来碰到并嫁给了善待她但却不了解她的美国丈夫,随他移居美国,离开了恶梦般萦绕在她心中的故乡和过去发生的一切,但此时的她已经沉默得太久,失去了生命力:
我怎能不爱这个人呢(她的美国丈夫)?但这是一种幽灵般的爱。明明双手紧紧地搂住了他,却根本没有碰到他;明明一碗满满的米饭摆在眼前,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是饿,也不晓得什么是饱。(Tan,1993:286)
而正是这样一个沉默了半生,感情、精神上几近麻木、死亡的母亲在看到女儿面对的不幸婚姻时,却出于母爱的本能果断地打破了自己的沉默:
我要用这尖锐的痛去穿透女儿厚厚的皮,把她体内的“虎气”也释放出来。她必定会反抗。因为这是老虎的天性。但我终究会战胜她,把我的精神输入她的体内。这就是母亲爱女儿的爱法。(Tan,1993:286)
母亲为了拯救女儿准备采取行动了,那么女儿呢?这位听着索尼牌随身听,喝着可口可乐,在母亲眼中只知道物质享受的新一代华人妇女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她的故事远没有母亲的那么一清二楚、黑白分明。她自认为在学业、智力、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能与丈夫平分秋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胜他一筹:是她出主意协助丈夫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因此她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她都“应该得到这样一个丈夫”。而事实上她的婚姻,以至于她的整个生活都在美国式的“帐目均摊”的貌似平等的游戏规则下悄无声息地松动着、瓦解着。她在游戏之中竟渐渐忘记了游戏最初的目的,失去了是非观念和自我意识,到最后甚至幻想以经济上的忍让与多付出来换取丈夫的感情。失败的结果使她完全丧失了自尊和自信。面对男权的威慑,她深深地感到了自身的嬴弱和无助,变得束手无策,哑口无言:
我开始哭泣,我知道这是哈罗德一贯讨厌的。我一哭他就会不舒服,发脾气。他认为我这是在耍手腕儿。可我真的忍不住,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清楚这场争吵最初的起因了。我是想让哈罗德站在我一边吗?是想少付一些那一人一半的费用吗?我真是想结束俩人之间这种凡事都算得一清二楚的生活方式吗?即使真的那样,我们不还是会照样在心里算这些帐吗?那样我不就会觉得更糟糕,更不公平吗?……
这些想法全不对头,全讲不通,我一样也说不准,整个人都陷入了绝望。(Tan,1993:180)
莉娜提出的实在是个令人困惑而又发人深思的问题。的确,女权主义最初的目的是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争取男女平等。用在我国流行了很长时间的一句话来说,女性的解放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男女同工同酬”。我们姑且不谈这个理想是否已经实现。就算是真的已经实现,女性就真的从此能与男性平分秋色了吗?莉娜的故事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锱铢必究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更隐藏、更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维定式和人们早已习焉不察的男权观念。莉娜对这令她有苦难言的男权观念的沉默与忍让把她推入了一个无言、无奈、无望的境地。一段婚姻葬送在“男女平等”的生活方式之下,这难道不是对某些人头脑中的“平等”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新阐释吗?可以断言,女性的这种沉默才是女权主义者和全社会更应备加关注的现象。在这里,“分摊帐目”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一个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具有实际意义的暗喻。
在《喜福会》中,沉默的主题似乎无处不在,但又仿佛是作者在漫不经心中流露出来的。书中的女性不仅是沉默的受害者,也是将沉默锻造成一把锋利无比的剑去互相伤害的杀手。小说中的琳多和魏芙丽这对母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女儿魏芙丽少年时代很有下棋的天赋,每逢与人对弈都犹如有神人在暗中相助,无往而不胜。她在学校和市、州级的比赛中都捧回过奖杯,这令做母亲的颇为自豪。她走在街上,逢人便拿出登有女儿照片的杂志封面向人炫耀。这引起了女儿的反感。争吵之后,母亲一连几天缄口不语,对女儿下棋的事情不闻不问。最后,女儿沉不住气了,主动与母亲讲和,又继续参加比赛。然而,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她身上的那股神奇的力量不见了。她一输再输,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下棋,从一个天才的棋手变成了个“普通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现实的描写。女儿身上神奇的力量自然是母亲所赋予的,而母亲的沉默竟永远地夺去了她的天赋。在母亲的眼中,女儿的生活是透明的,一切都逃不出她的眼睛。但是,当女儿带着她参观自己新布置的住所,希望间接地告诉她自己已再婚的消息,并迫切希望得到她的首肯与祝福时,母亲却作出一副充耳不闻、事不关己的样子,或者顾左右而言它,或者干脆不予理睬,把女儿悬在了沉默的半空中,使她受到了比来自话语更加深重的伤害。对这一点女儿有着切肤的体会:“我妈妈懂得怎样让人痛苦,这种痛苦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痛苦都更加深重”。这位母亲能让“白色变成黑色,黑色变成白色”,让女儿经过精心调整、自以为满不错的新生活——包括新婚的丈夫、自己的女儿与新继父之间和谐的关系、丈夫送她的贵重礼物裘皮大衣、精心布置的家;一切的一切都变得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可言。母亲利用沉默这把利剑把女儿戳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而更可悲的是女儿从母亲身上继承来的那不可救药的心理情结(非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才能生活得心安理得)。一个非要不可,一个执意不给,这场不见硝烟的沉默战争使母亲和女儿都身心交瘁,伤痕累累,在双方感情上造成了本不该有的深深的伤害。一天,当女儿下定决心要去找母亲说个清楚时,她才在母亲睡熟的时候霍然发现,自己那强大的“敌人”原来不过是一个毫无攻击力,甚至是不堪一击的老妇人,这是多少年来她第一次发现母亲的真实面孔。经过一番母女间推心置腹的交谈。女儿终于认识到:
真的,我终于懂了,不是懂了她刚才所说的话,而是那些原本就是真实的事情。
我明白了自己一直是为何而战的:是为自己,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一个老早以前就逃到了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的孩子。我躲在这看不见的掩体后边,心里很清楚对面藏着的是什么:是她从侧面可能发起的攻击、她的那些秘密武器,还有她那洞察我一切弱点的高超本领。然而,就在我把头伸出掩体,向外窥视的那一瞬间,我终于发现了那里的一切:那是一个用铁锅当盔甲,用毛衣针作利剑的老妇人,一个因久等女儿的邀请而不得,正在变得脾气暴躁的老妇人。(Tan,1993:204)
这是一段多么形象、生动的描述!母女间多年感情、心灵上相互间的沉默给对方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而这沉默一经打破,战争的阴影也随之散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代女性之间可贵的重新认识和相互理解,是女性的觉醒。她们终于认识到,在一个“种族、性别歧视的世界里,女性之间应该成为朋友,成为同盟”。对于书中的两代女性来讲,要想相互破译对方的真实思想——那些掩盖在各种形式的沉默之下的真实思想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无论怎样,她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年轻一代的女性从母亲身上汲取了精神的营养与力量,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新的生活。这正是小说的结尾处吴晶梅在母亲去世之后代表母亲去大陆寻找她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姐一幕所象征的。三姐妹在母亲的故土上终于搂在一起,多年的归乡之梦、母女和姐妹团圆之梦都随着沉默的打破而实现了。这是让人多么欣喜的一幕!
谭恩美是华裔女作家中的第二代,她与王玉雪(Jade Snow Wang)和汤婷婷这些年长于她的华人女作家一样,沿袭了母女关系这一写作题材。她们都各自从自己母亲的身上汲取了写作灵感和素材。这正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她们的作品中,“母亲的苛求所代表的就是男性的苛求”,是男权社会渗透于她们意识深层的自我贬低、自我排斥、自我抹杀的传统观念,是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她们自然永远无法达到母亲的要求,也无法正视原本的自我。无论她们怎样努力改变自己,以何种标准改变自己,其结果却总是更多的失败和更大的痛苦。这是一些华人女性最大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喜福会》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多元文化,也就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的新格局,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把戏,是对亚文化的同化和心理侵略的掩盖。那么,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女性一样,华裔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文化的沉默和性别的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对生活,才能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最后,再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一个问题:在看到了作者通过她的16位女性人物一一讲述的那些埋在她们心底的故事,了解了她们深深的沉默背后的心曲,对那些我们曾经那么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问题作出了新的思考之后,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身处西方还是东方,你还能把这部小说当作一块轻松可口的小点心来消化吗?这里,我们不禁又想起了海明威那著名的冰山理论,我想它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如果人的话语世界占他整个世界的十分之三,那么有谁因此就能忽视那冰面之下十分之七的沉默世界的力量呢?收稿日期:1999—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