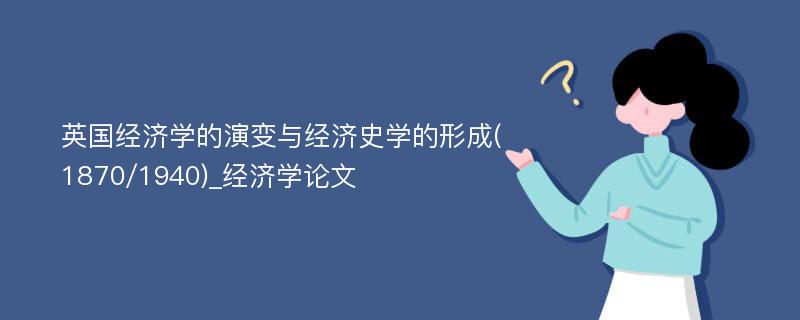
英国经济学的演变与经济史学的形成(1870-194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英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对它的批评也与日俱增,其中绝大部分批评集中在其过于追求形式化和普适性,而忽视各国经济现实的特殊性方面。①对此,包括索洛和诺斯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建议,应当通过经济史学对于历史和制度特殊性的关注,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不足;②这种观点在我国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形成了对于经济史和经济学关系的“源流之辩”。③ 从已有文献来看,无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还是对经济史学与经济学关系的探讨,基本都是规范性的评论,而很少实证地考察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与经济史学的关系在过去究竟是怎样的。④本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探讨这一问题,在第一部分介绍理论渊源后,分三个阶段回顾1870-1940年英国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从观点分歧到学科分裂的演变历程,并结合英国经济社会变迁和大学、学科演变的历史和制度环境,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一、早期渊源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那么在诞生以后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这门学科的性质及其所适用的研究方法,就引起了当时最重要的两位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的意见分歧。⑤ 李嘉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像数学那样严密的科学。⑥他为此创立了后来被称之为模型分析的纯粹演绎方法:首先以劳动价值论、地租理论、自然工资率、工资基金说和比较优势论为基础,构建起一套理论体系;然后从现实经济问题中抽象出基本要素,运用上述理论,通过纯逻辑推理,探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最后得出一系列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政策建议。 马尔萨斯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比较类似于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不近似数学”,应当面向现实,更重视经验材料的搜集和历史归纳法。他批评李嘉图“轻率地力求简单化和一般化……使人们不愿意承认,在一些特定结果的形成中,有不止一种原因在发挥作用”。⑦其继任者理查德·琼斯更直斥李嘉图学说是“妄想的假设”,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只有在充分了解经济发展历史和考虑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因素之后,才可能真正地分析、研究和彻底了解经济问题。⑧ 马尔萨斯和琼斯的观点,揭示出李嘉图思想因过度抽象演绎,导致重要因素遗漏和政策建议脱离现实的潜在危险,也得到了后来众多学者的认同,⑨但却并未能阻止李嘉图思想成为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这不仅是因为李嘉图的演绎和模型分析逻辑严谨,极具说服力,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便于学习者接受;更重要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契合了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英国在世界市场的霸权地位。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曾以晚餐会的方式成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⑩邀集学者、政治家和商人探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理查德·科布登等曼彻斯特学派和自由党人也都接受了李嘉图的学说并组织“反谷物法同盟”,传播自由贸易理论,最终促使国会废除了谷物法。李嘉图还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来传播其思想。(11)其中最著名的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分别是当时两份重要学术期刊《威斯敏斯特评论》和《爱丁堡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他们撰写了大量论文,介绍李嘉图的理论,使其深入人心。麦克库洛赫还在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中,为李嘉图学说营造了权威形象。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李嘉图学派在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界取得了支配地位。 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与演绎学派 (一)英国历史学派的形成 1860年代,英国虽然仍处于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但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济波动日趋增加,贫富差距则不断扩大,李嘉图的自然工资率和劳动价值论越来越不能解释现实。同时,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工会地位的加强,社会上对于自由放任政策和工资基金理论的反对声音也在不断增多。 然而,仍有一些政客把李嘉图学说尊为教旨,用来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做背书。1868年,英国政府计划出台一项土地补偿和改革法案,对之前因大饥荒而失去土地的爱尔兰佃农进行补偿,以缓和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而那些代表土地利益的议员们就援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予以反对,声称“虽然我们已经将自己的后背靠在了政治经济学上,但科学似乎已经被打破了”。(12)尤其是时任财政大臣的自由党人罗伯特·洛,异常教条地复述李嘉图的理论,反对任何救济和土地制度变革,宣称政治经济学“在英吉利海峡的这边和那边应当没有什么不同”,“一项在英国完全令人满意的法律,在爱尔兰是不可能存在根本的不公正性的”。(13) 针对于此,出生于爱尔兰的经济学家克利夫·莱斯利撰写了多篇论文予以抨击,同时积极支持国会改革爱尔兰的土地制度。他首先以工资基金理论为例,指出李嘉图学说并不符合现实的情况,原因就在于其脱离实际的纯粹演绎方法。(14)随后,莱斯利采取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回顾了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社会变迁,同时参考欧陆国家的土地制度,指出爱尔兰落后的原因就在于英格兰以自由贸易和普适理论的名义,把自己的法律和土地制度强加给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完全不同的爱尔兰,从而在实质上把爱尔兰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15) 莱斯利批评了罗伯特·洛等人,他写道:“在国会里的那一群抱负不小而且势力很大的经济学家,自以为拥有了包含所有经济学知识、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处方”;(16)然而,“恰恰相反,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体系,或者某种具有普适性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由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推理和学说所组成的”,“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即使是在同样的国家和同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对它的解释也有所不同”。(17) 莱斯利还从哲学层面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针对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现象,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这种调查必须覆盖所有影响到研究对象的力量和制度因素”,“我们可以把诸如劳动分工、国民财富……经济现象单列出来进行研究,但绝不是因为这种做法会更合理或更科学,而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无法进行总体研究,而且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能够把影响这些现象的所有因素都纳入到研究当中去。如果隔离出某一种因素来推导其对于国民财富的影响,即使这个因素是真实而非纯粹抽象的,也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种做法也是极其不科学的。”(18) 尽管莱斯利没有建立起一个历史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但他对于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阐释,奠定了英国历史学派的基石,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共鸣,也由此形成了与演绎学派相抗衡的英国历史学派。 作为莱斯利最主要的同盟者,约翰·英格拉姆在1878年担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科学与统计学组(19)主席时,发表了题为“政治经济学的现状与前景”的演讲。(20)他批评演绎学派过于重视“经济人”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把经济方面孤立于其他社会现象之外进行抽象研究,从而脱离了现实,也败坏了政治经济学的声誉。 在《政治经济学史》一书中,英格拉姆还指出,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制度环境中产生的,强调“政治经济学应当永远被视为较大的社会学之一部分,它是与其他部分紧相连接的,而且与道德的总合相联结”,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包括道德因素和价值判断,而不是一门干枯冷酷的科学。(21)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杰斯,他的代表作《英国农业与价格史:1259-1793》和《六个世纪的劳动与工资》,(22)就是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历史归纳研究的典范,通过对农产品价格和地租的长期统计,他指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当时任教于牛津大学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也是如此。他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课程,直接启发了牛津学生采用历史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他将政治经济学思想与社会经济改革现实相结合、积极投身于社会改良运动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牛津政治经济学面向现实的研究风格,并由此带动了以威廉·阿什利、兰福德·普赖斯和威廉·休因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历史学派思想因而在牛津大学繁荣发展起来。 而在剑桥大学,尽管以马歇尔为核心的演绎学派一直主导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但也出现了威廉·坎宁安和赫伯特·福克斯韦尔等重要的历史学派学者。(23) (二)英国演绎学派的发展 莱斯利1868年的论文引发了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界对李嘉图学说的反思和批评,紧随其后,弗莱明·詹金(Fleeming Jenkin)和威廉·桑顿(William Thornton)也发表了对工资基金学说的批评论文,到1870年时,连李嘉图学说最重要的继承者约翰·穆勒也已经明确放弃了工资基金学说。穆勒热情赞扬莱斯利的文章,并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上站在莱斯利一边,公开批评罗伯特·洛,指出不弄清具体情况,没有人能断言什么才是一个国家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穆勒增加了很多历史和现实资料作为理论的补充,并尝试把政治经济学分为两个部分:生产部分是静态的,适用于演绎法;而分配规律是动态的,受制于社会的习俗和制度因素,适用于历史归纳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穆勒放弃了抽象演绎法。《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大部分内容在实质上依然是李嘉图理论的重新表述和延伸。更为重要的是,在另一篇专论政治经济学性质和研究方法的论文中,穆勒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使用先验方法的抽象科学。它可以像数学那样,根据某种没有事实依据的假说,进行纯逻辑推理;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众多干扰因素,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只需理论正确,或者说在某种假设的前提下正确就可以了。(24) 穆勒的弟子凯尔恩斯(John E.Cairnes)对此作了更清晰的阐述。他把政治经济学分为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就理论部分而言,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所有理论都只能源于逻辑思考,是“在不存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根据假设推导出的结论,或者说,它并不是客观发生的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25)而当政治经济学理论被应用于实际时,才把那些影响“趋势”实现的历史和制度性扰动因素考虑进来,但不能就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批评和排斥理论。因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就其根本而言,并不是根据具体事实而建立的,而是直接源自于我们的意识和理性思考,因而不会受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现象的影响”。(26) 通过这种“两分法”,凯尔恩斯把历史和制度因素归入了政治经济学的应用部分,而将理论部分的对错完全交给演绎推理来评判。在他看来,历史学派只是强调了应用部分的重要性,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部分的批评则是没有意义的。(27) 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因此而恢复平静,就在1871年,它的理论部分也正在迎来了一场由斯坦利·杰文斯发起的边际革命。 杰文斯和莱斯利有着很多相似之处,(28)他同样致力于“摆脱工资基金学说、生产费价值学说、自然工资率学说及其他种谬误的李嘉图学派的学说”,企图“把这种被束缚的科学的断片拾起来,重新再开始”。(29)但杰文斯把李嘉图学派的错误归咎于李嘉图和穆勒个人,而不认为演绎法存在问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而莱斯利的历史主义方法会使得政治经济学“成为纷杂的不连贯的事实之结合”,或者“沦为斯宾塞社会学的一支”;(30)并进而指出,要想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仅靠逻辑推理还不够,还必须从数学的基础出发,才能进行圆满的探究。(31)为此,杰文斯建议把“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学科名称改为“经济学”(Economics),去除其中附着有历史和制度因素的修饰词“政治”,同时加上象征普适科学的“-ics”后缀;他还撰写论文和编制数理经济学书目,积极推动当时对经济学家们还十分新颖的微积分方法在经济学中的普及。(32) 杰文斯理论的核心,就是他称为“拱心石”的边际效用理论。通过以边际效用决定价格来取代劳动价值论,他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生产和分配转移到对交换和消费的分析,同时把人口问题剔除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建立了新的研究框架。通过强调主观效用和心理动机的决定性作用,杰文斯进一步强化了演绎学派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把个人效用最大化和欲望满足变成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而把历史学派所强调的个人与周围的社会关系(制度因素)全部排除在外。 对此,莱斯利曾批评说,“人口理论以及所有那些被杰文斯先生划进经济社会学的内容,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都应拥有合理的位置”;莱斯利指出,国民财富的很多组成部分都不体现为货币,很多经济问题也都不适合用数学进行度量和验证。(33)但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杰文斯的框架和微积分方法作为理论平台和研究工具,无疑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881年,埃奇沃思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契约曲线;1889年,J.B.克拉克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1890年,马歇尔阐述了消费者剩余概念;1906年,帕累托发展了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1930年代,希克斯提出了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替代弹性等概念,建立了完整的消费者理论。 除了同李嘉图体系一样的逻辑严密外,杰文斯理论和边际分析法的成功,还与19世纪后半期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正值英国的新大学扩展运动,一批新的城市大学纷纷成立并不断扩张,使大学逐渐成为知识的主要传播者。(34)如果说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家们还来自于社会各个部门,那么,到19世纪末,无论是演绎学派还是历史学派,基本上都是大学以讲授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为职业的专职学者了。早期的非专业学术人员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兴趣在于它的政策含义方面,而大学教授们则更关注那些比较根本和具有持久性的知识。(35)通过数学化的模型,杰文斯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知识的可累积性,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套逻辑自洽、具有持久性的庞大理论体系,更加适应大学这种知识传播载体的需要。 与之相比,历史学派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击中了政治经济学的要害,它的很多观点也颇具合理性,但主要依靠统计和归纳的方法,很难建立起一个足以与演绎派抗衡的理论体系,而且不同学者的研究也会显得彼此独立而无法相互累积;在教学中,历史学派要求讲授者既要清楚阐述事件的制度背景,又要突出研究对象本身的经济发展逻辑,才能保证学生不至于误入歧途。(36)这些都限制了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学在大学中的发展,使之更像一个在野的批评者,而不是这个学科的主人。 三、英国历史学派与演绎学派的竞争 (一)思想观点的交锋 在1882年莱斯利和杰文斯相继辞世之后,以牛津大学为中心的一些学者继承和发展了莱斯利的思想,形成了以重视历史、制度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现实面向为特点的历史学派;而以剑桥大学尤其是马歇尔为核心的另一群学者则采用了杰文斯提出的“经济学”这个新的学科名称,在吸收李嘉图、杰文斯等经济理论和借鉴历史学派部分观点的基础上,以边际效用论为核心,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派。 与之前的演绎派学者相比,马歇尔以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接纳了很多历史学派的思想。他承认,经济学研究的应该是一个实在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在经济研究中,包括道德在内的制度因素都必须被考虑进来。(37)在1885年的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就职演讲中,马歇尔明确指出,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习俗、规则和制度上的差异及其不断变化,任何经济理论都不能被看做是普适不变的真理。 但马歇尔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紧接着又提出,尽管经济理论本身不具有普适性,但是它作为我们从事经济研究的工具(Economic Organon),是具有普适性的。在分析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问题时,经济学理论都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搜集资料、建立研究框架;只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再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选择适合的具体方法。通过“工具论”的提出,马歇尔不仅在被凯尔恩斯等学者以“两分法”分开的经济学理论部分和应用部分之间,架起了一座具有普适性的桥梁,而且把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都纳入了他的“工具”之列。 马歇尔进一步提出,单纯依靠历史学者的方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观察历史不能直接发现事件的原因,而只能找到它们在时间上的发生顺序;即使发现了某个或某组事件发生的先后或共时性,也还不足以给我们以指导,除非同样的事件还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而这种重复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是不会出现的”。(38)不仅如此,马歇尔还论证说,“过往的学术争论告诉我们,如果不经过检验和逻辑思考,就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信息;最粗疏和不诚实的理论家们,就是那些宣称让事实和数字自己说话的人,他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选择和组织资料的方法藏在身后,而告诉人们‘在此之后,所以是因此而发生的’”。(39) 与马歇尔有力的批评相比,历史学派的还击则显得相对无力。1889年,坎宁安撰文批评马歇尔把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应用于古代英国和印度的做法是错误的,指责马歇尔“自称对历史抱有无比浓厚的兴趣”并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但实际上还是认为不同历史时期有着类似的经济动因,这些历史资料在本质上仅仅是作为他由演绎法所得出结论的佐证而已。(40)在回复中,马歇尔辩称,坎宁安批评的问题主要是他在撰写《经济学原理》时压缩篇幅而造成的,而对李嘉图地租理论应用的批评则完全属于误读,自己多年来一直在为一部计划中的经济史著作做准备;他还详细举例说明,自己在研究中充分考虑到了历史和制度因素,逐项回复了坎宁安指出的具体问题,并在文末对其他历史学派学者对其著作的评论和意见表达了谢意。(41) 应当说,坎宁安的批评确实有些牵强,即使是同属历史学派的阿什利和普赖斯也都承认,马歇尔对历史和制度有着深入的理解,马歇尔后来用历史方法撰写的《工业与贸易》也验证了这一点。因此,尽管坎宁安撰写了多篇后续论文对马歇尔进行批评,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读者。 历史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在政策观点上的一次集体交锋,出现在1903年。 当时,由于新式设备投资不足和产业升级滞后等原因,英国工业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不断衰落,很多工业部门逐渐被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德国和美国所赶超,英国国内的失业、低工资和贫困问题也更趋严峻。以约瑟夫·张伯伦为代表的自由党统一派意识到了“英国病”的严重性,主张改善下层人民的经济状况,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脱离自由党,与保守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03年5月,张伯伦发表公开演讲,批评英国一直以来的自由贸易政策,提倡建立帝国特惠制,加强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联系,对内实行关税优惠,对外执行高关税壁垒。 同年8月,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等14位著名经济学家联名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宣言,措辞严厉地批评张伯伦,坚持自由贸易政策,认为自由贸易不仅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也是符合英国具体国情的最佳政策,实行保护关税会降低效率、抬高物价,从而降低英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历史学派的学者们则立即结成了另一个联盟,坚决支持张伯伦改革,公开指责马歇尔等人的宣言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观点,不能代表政治经济学专家的集体意见。坎宁安专门为此撰写了《自由贸易运动的兴衰》,(42)指出自由贸易政策只是英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此时已经不再适应英国的经济状况了;阿什利不仅以其著作《关税问题》(43)为张伯伦的意见提供依据,通过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统计资料,表明保护关税政策的必要性,而且正式加入了张伯伦的自由党统一派,参与了一系列政策辩论。原本与马歇尔关系良好的普赖斯(44)也在拒绝签署批评张伯伦的宣言之后,公开与马歇尔进行辩论,阐述帝国特惠制能为英国带来的好处。福克斯韦尔在批评自由贸易理论的同时,还指责马歇尔等学者的态度带来了政治经济学的倒退及其在公众心目中地位的下降。休因斯则辞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职务,从政参与了关税委员会的工作。 从英国历史来看,张伯伦和历史学派的主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的趋势,(45)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但在当时,各殖民地国家从本国工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对张伯伦的提议反应冷淡,并要求英国提高从非殖民地国家进口农产品的关税,而这将导致英国国内食品价格的上涨并威胁普通民众的生活,从而使张伯伦陷入政策的两难境地。再加上自由党人对马歇尔和庇古自由贸易主张的大力宣传,以及1904年英国经济的短暂复苏,使大批民众相信,张伯伦的主张言过其实。这导致自由党统一派与保守党联盟的分裂,及其在1906年大选中的失败,张伯伦随后也因中风而退出政坛,历史学派再次遭受挫折。尽管如此,张伯伦和历史学派学者们掀起的贸易保护运动仍然有力冲击了自由主义思想,动摇了自由党的阶级和思想基础,并加剧了自由党此后的分裂与衰落;而保守党则接受了张伯伦的贸易保护主张,进而扩大了在工商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中的影响力和自己的选民队伍,并于1932年最终实现了帝国特惠制。 (二)关于经济学科发展方向的竞争 19世纪后半期,英国大学的迅速发展和政治经济学学科专业化的不断深入,使得政治经济学教授作为学科权威的影响力,以及学术组织对于学术规范的控制力大大加强。为了影响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教授职位和学术组织成为历史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竞争的重要目标。 在1884年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竞争中,马歇尔取得了对坎宁安的胜利。事实上,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已经没有人堪与马歇尔比肩了,“英国几乎一半的经济学讲席获得者都是他的学生,而由这些学者所控制的经济学教学资源,在英国的比例还要更大”。(46)当1890年《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各大报纸杂志都认为,这本书即将开启经济思想的新纪元,(47)马歇尔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在这一年,马歇尔担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科学与统计学组的主席时,向参会人员发出一封公开信,倡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专门的经济协会和经济学期刊,并被众人所接受。同年11月,英国经济协会(British Economic Association)正式成立,(48)马歇尔的这封信奠定了学会成立后实际遵循的总路线。次年,英国经济协会创办会刊《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由数理经济学家埃奇沃思担任主编。 牛津学者们立刻意识到这对经济学科规范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于是赶在《经济学杂志》出刊之前,另外创办了《经济评论》杂志(Economic Review)。早期的《经济评论》确实发表了一些与新古典学派针锋相对的高水平文章,强调历史和制度因素,尤其是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意义,倡导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现实的社会改革中去,只是其辐射范围不及作为英国经济协会会刊的《经济学杂志》。马歇尔虽然也曾对《经济评论》有过敌意的批评,(49)但在应对挑战时,《经济学杂志》还是体现出作为协会会刊应有的公共性和多元性,(50)不仅为历史学派保留了一定的空间,甚至对阿什利等批评马歇尔思想的文章也予以刊发。 只是这种竞争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1891年,因詹姆斯·罗杰斯逝世而空出来的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讲席,引发了阿什利、埃奇沃思和另外两位学者之间的激烈竞争,结果仍然是演绎学派获胜。埃奇沃思的当选固然主要源自他本人的学识和影响力,但马歇尔也的确通过时任牛津巴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好友本杰明·乔伊特,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51)而且,埃奇沃思在任期内的无所作为(52)似乎也表明,他并不是担任牛津经济学领导人的最佳人选。竞选失败的阿什利于是转赴哈佛大学,就任那里新设立的英语世界的第一个经济史教授(1892-1901)。189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立后,威廉·休因斯(William A.S.Hewins)就任院长,也离开了牛津。 他们的相继离开,不仅导致《经济评论》质量的下降,就连历史学派先前组织的另一个团体牛津经济学社,也逐渐变成了业余经济研究者的论坛。(53)而英国经济协会及其《经济学杂志》,则真正成了促进英国经济学者自律化的平台,全国的职业经济学家们在这里相互交流,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和基础的专业语言和习惯。这不仅意味着相似的方法论和价值判断,也暗含了为拒绝其他人员进入而设置的学科范畴与方法的界限。(54) 除了倡办经济学专业组织和期刊外,马歇尔还成功地从制度上实现了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立化。在19世纪末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仅是道德科学和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从属性科目。(55)马歇尔对这一状况非常不满,认为道德科学学位考试的课程过于追求形而上学,不能吸引那些“适合从事最尖端和最繁难经济学研究的学生”,也不利于培养学生们“保持头脑冷静和清晰,以追踪和分析由多种原因而造成的复杂现象的能力”。(56)因此,在就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之后的近二十年中,马歇尔撰写了多篇文章,(57)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吁请剑桥大学设立独立的经济学科。直到1903年,独立的经济学荣誉学位考试的设立终于获得批准。(58) 当马歇尔退休时,当然不会允许这门由他创立的新学科回到历史和制度主义者的手中。在1908年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选举中,尽管历史学派的福克斯韦尔和阿什利的资历更深,马歇尔还是不遗余力地支持了资历最浅,但方法论与自己一致的弟子庇古,帮助他成功当选。(59) 职位之争的连续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历史学派学者们彻底放弃了对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追求,转而寻求在马歇尔的影响范围之外,设立另一个独立的新讲席。 四、经济史学的产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演变 (一)经济史学的产生 1895年,威廉·休因斯接受费边社核心人物韦伯夫妇的邀请,就任新成立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院长后,立即把牛津历史学派的风格带到了这里。除了亲自教授英国贸易与金融史外,休因斯还把坎宁安、福克斯韦尔、阿什利和霍布森等历史学派的主要学者都邀请到这里担任兼职教师,开设了很多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应用经济学的课程,要求学生必须从事应用领域的研究。LSE迅速成为英国历史学派新的中心。 1903年年底,休因斯辞职从政,兼职教师的方式无法继续满足LSE的教学需要。校方在次年设立了英国第一个全职的经济史讲师职位,由坎宁安的得意弟子莉莲·诺尔斯(Lilian Knowles)担任。1907年,牛津的普赖斯也获得了专职的经济史讲师职位,并在两年后升任准教授(Reader)。1910年,曾就学于牛津的乔治·昂温(George Unwin)获聘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史教授,这也是英国的第一个经济史教授。1921年,莉莲·诺尔斯升任LSE的经济史教授。1928年,剑桥大学终于也设立了经济史教授,由马歇尔的另一个学生约翰·克拉潘担任。1931年,牛津大学设立了齐切利经济史讲座教授职位,由乔治·克拉克(George N.Clark)担任。诺尔斯逝世后,LSE又于1931年同时聘任了两位经济史教授,分别是毕业于剑桥的艾琳·鲍尔(Eileen Power)和毕业于牛津的理查德·托尼(Richard H.Tawney)。 这样,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历史学派已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范围之外,逐渐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学科。尤其是在1926年,艾琳·鲍尔等学者借英美史学会议在伦敦召开之际,倡议组建一个经济史专业的学术团体,并获热烈响应。同年7月14日,“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正式成立,大会选举阿什利任主席,鲍尔任学会秘书;半年后,又创办了学会的期刊《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由牛津大学的经济史讲师伊弗列姆·李普森(Ephraim Lipson)和理查德·托尼任编辑。 在成立大会上的主席演讲中,阿什利不无感伤地说:“理论经济学家们认为,只要给我们一小块属于我们自己的田地,就可以让我们保持沉默了;而我们这些谦卑的历史学家们也应当为这一小块没有争议的领地而感激庆幸,以至于听任那些经济学家们自行其是。在彼此都拥有自己学会和期刊的今天,这两个学科存在着渐行渐远的危险……(但)如果我们彼此都能多了解一些对方田地里的作物和种植方式,我想,一定会对双方的成长都有好处的。”(60) 然而,阿什利的期望并没能成为现实。为了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和赢得历史学者的支持,新学科采用了“经济史”这一名称。它源自于剑桥大学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中的一门科目(政治经济学也是科目之一),其研究对象是过去的经济或者历史中的经济方面。以此作为与“经济学”相抗衡的新学科的名称,看似合理,但实质上却与历史学派的旨趣大异。因为自莱斯利以来的历史学派学者们都是经济学家,他们主要是把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而研究的对象和目标仍然是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因此,与历史学派更加贴切的学科名称,应该是历史经济学(Historical Economy),而不是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后者颠倒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间的相对位置,使之看上去更像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结果正如阿什利所担心的,此后的经济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把研究视野投向历史领域,而把现实问题留给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听其自行其是。 从英国历任经济史学讲师和教授的就职演讲词中可以看出,阿什利、普赖斯和昂温等早期经济史学者,无一例外地都会回顾历史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及其与演绎学派的竞争,甚至抱怨经济史学者没能在经济学科中得到应有的职位。阿什利和昂温还特别指出,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更注重个人和心理分析,后者则强调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61)然而从克拉潘开始,在回顾经济史渊源时,所开列的历史学书目越来越多,演讲的内容也越来越历史学化。尽管克拉潘也曾用“空匣子”的比喻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脱离现实,(62)但在1937年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经济史词条时,他不仅通篇以历史学著作来介绍本学科的发展历程,而且承认历史学派取代演绎派的尝试已经失败,经济史作为制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正与社会史和人文地理学日益联系紧密。(63)在克拉潘以后,英国经济史学界日益默认自己的历史学性质,淡化了历史学派面向现实的研究风格。(64) 1930年代,如果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艾琳·鲍尔和理查德·托尼,仍然保留着对经济理论的批判观点和对现实经济的强烈关注;(65)那么在牛津大学的乔治·克拉克那里,虽然意识到历史资料总是不那么支持纯粹演绎所得出的经济学结论,但仍然从一个历史学者的立场出发,认为经济学理论可以在经济史的研究中“简化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摆脱考古癖和迷失于资料中的危险”。(66) 到1940年代,不仅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史只是过去时代的经济学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历史资料,(67)而且经济史学家也默认了这一点。当托马斯·阿什顿1944年接任LSE经济史教授时,不仅放弃了历史学派一直以来在方法论上的挑战,而且承认“即便是有经验的历史学家,也需用一套大致自成体系的原则作为取舍选择的标准……正如渔民需用一张渔网……但这张网必须成于专门网工之手,而不是随意编制的织物,编织(经济史学)这个行业专用渔网的人就是经济学家”。(68)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演变 在英国历史学派向经济史学转变的同时,新古典经济学也在发生着变化。 经过与历史学派的多次交锋,剑桥的新古典经济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历史学派的一些思想方法和政策主张。通过前述“工具论”的提出,马歇尔在方法论上超越了以往的“两分法”,把归纳和演绎作为经济学的方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他明确指出,“一般性推理是重要的,但对事实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同样重要”,“只有结合了这两者的经济学才是唯一正确的经济学”。(69)马歇尔对于数学的应用也极为审慎,认为数学只是推理的快捷工具,在完成推理后,应该把数学转化为文字和现实案例,并“烧掉数学”。(70)如果过度依赖数学,就“会使我们沉迷于这种智力游戏以及那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虚幻问题,甚至还会进而扰乱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那些不能被数字化的因素,往往会因此而被我们所忽略”。(71)在他晚年撰写的《国际贸易的财政政策备忘录》中,马歇尔也指出,他并不反对欠发达国家的幼稚工业保护,之所以赞同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只是因为英国的成熟产业不必继续得到保护;他也意识到,在自由贸易政策下,英国的一些新产业已经落到了其他国家的后面。(72) 在马歇尔工具论的基础上,庇古进一步把经济学家的研究分为两类:埃奇沃思是典型的工具制造者,“对一个设计精巧而没什么用处的探针的钟爱,要远甚于一把实用然而笨拙的刀”;而马歇尔则更多表现为工具的使用者,“在使用各种工具解决问题后,就把用过的工具隐藏在繁冗复杂的文字之下”。(73)在这两者之间,庇古认为,“只有实用经济学而不是纯经济学才是我们研究的目标”;(74)经济学“所关注的并不是应该怎样,而是实际会怎样”。(75)他还接受了更多历史学派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改良主义政策主张,指出“经济学家努力进行的复杂分析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们是改善人们生活的工具”,“对陋巷的厌恶以及对衰弱生命哀愁的社会热情,才是经济科学的起点”。(76) 世纪之交的英国,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蔓延的失业不断激起工人运动的爆发。1920年,在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中,庇古采用了更加体现道德关怀的“福利”(welfare)概念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广义的社会福利不仅包括经济福利,还包括从其他社会文化等因素中获得的福利,非经济因素也会对经济福利产生影响,只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经济福利。他又把经济福利分为个人经济福利和社会经济福利两种,其中个人经济福利可以用效用来表示,社会经济福利由个人的效用加总而成的,可以用国民所得来表示。这样,庇古就把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民财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并进而提出,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从而在不破坏个人主义传统的情况下,修正和拓展了“经济人”的研究框架。(77) 由此出发,庇古指出,通过增加国民所得,当然可以提高社会经济福利;而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通过政府的力量,从富人向穷人转移支付,缩小收入差距,也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庇古还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指出私人净边际产品与社会净边际产品往往并不一致,厂商出于自利心,只会关心私人净边际产品,因此需要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通过税收、财政补贴或立法等手段,纠正市场配置资源的失效,实现私人净边际产品与社会净边际产品的一致。(78) 在这里,庇古彻底地改变了李嘉图以来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修正了片面强调机会均等的经济公平观,更加关注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同时从理论上证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倡导通过政府的力量来矫正市场之不足。他也反对李嘉图等学者认为贫困源自懒惰、应由个人而不是由社会负责的观点,认为某些地区和职业的工人工资少于他们给企业所带来净边际产品的价值,应当通过政府介入来提高工资,消灭剥削。庇古还认为,罢工会导致劳动力和设备闲置,进而使经济福利受损,因此他主张建立和加强劳资协调机制,使劳资双方和谐共处,实现“产业和平”(industrial peace)。所有这些,正如经济思想史学家塞利格曼所评论的那样,“极少有经济理论像庇古的理论那样,既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又有强烈的伦理关怀”。(79) 凯恩斯更对历史归纳法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马尔萨斯的方法被完全抹杀,而李嘉图的方法则取得完全支配地位,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可谓一场灾难”。(80)他还指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也就是说,它有赖于自省和价值判断”。(81)凯恩斯甚至还对计量经济学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用理论模型进行思考的科学”,如果像自然科学那样把模型变成定量化的方程,“那等于是毁了它作为思想工具的价值”。(82)他进一步推动了新古典经济学从自由放任向积极发挥国家干预经济作用的重要转型,其政策主张也在此后欧美各国抑制经济波动和调节社会矛盾的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可以说,庇古和凯恩斯这种从传统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转型,集中体现了剑桥新古典经济学派面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矛盾,积极吸纳有益思想方法进行理论创新和改良的努力。而这些在回应社会需要上所取得的积极进展,也是1920年代以后在英国自由贸易政策遭遇失败、自由党趋于衰落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仍然能够占据英国经济学主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与此同时,新古典学者所致力推动的经济学专业化进程与历史学派的退出,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模型演绎法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垄断和对历史与制度因素的日益忽视。随着20世纪前30年英国经济学科的专业化及其迅速扩张,(83)一种过度抽象演绎和忽视现实的态度,逐渐在剑桥大学以外的青年经济学者中蔓延开来,特别是1930年代莱昂内尔·罗宾斯和约翰·希克斯的登场,更大大加剧了这种状况。 在1931年和1932年,罗宾斯激烈地批评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中立的科学,不应该涉及道德哲学或价值判断问题,个人之间的效用并不具备可比性,庇古福利经济学所依赖的基数效用论是不成立的。(84)凯恩斯的政策在罗宾斯看来,也只是在重弹历史学派的老调,(85)从而在方法论层面,退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的“两分法”,在政策主张上,也从现代自由主义退回到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罗宾斯还赋予经济学以新的定义:“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做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86)用以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国民收入的性质、来源和分配问题,从而进一步清除了与国民收入相关的历史和制度因素。 两年之后,希克斯运用埃奇沃思的无差异曲线,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进而在帕累托最优思想和罗宾斯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福利经济学。他还提出了替代弹性和边际替代率概念,在消费者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一般均衡理论,大大推动了微观经济学作为一套不依赖历史和制度的纯逻辑体系的成熟化。在一般均衡的基础上,希克斯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简化成了国民收入核算模型和IS-LM模型,尤其是后者仅用利率这个单一指标,连接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抽象掉了非常重要的动态因素和不确定性预期,把一般均衡变成了经济常态,而把凯恩斯思想中的非充分就业作为特例,在很大程度上颠倒了凯恩斯的原意。(87) 194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新霸主地位的确立,经济学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美国。罗宾斯对经济学的新定义在被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采用后,广泛传播,成为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标准定义。尽管希克斯的IS-LM模型存在着很多问题,但经过汉森等学者的发展和推广,也以其高度简洁和直观的表述形式,迅速被美国经济学界所接受并用于计量模型,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88) 回顾以上历程,我们发现,经济史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分别源自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和演绎学派,新古典取代古典并发展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也正是历史学派在经济学科内部被边缘化,并最终独立成为经济史学的过程。 早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初,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就在学科的属性和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前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应当面向现实,采取历史和归纳的研究方法。后者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可以像数学那样严密,并建立了强调逻辑演绎的模型分析法。但在二者的经济思想中,分歧要远远小于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观点的差异性和方法的多元性,反而促进了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1870年代以后,随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规模和影响力的增加,这种方法论上的分歧也日益扩大。以莱斯利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李嘉图思想脱离了实际,其根源就在于演绎法的错误,他们强调历史归纳的方法和问题导向的研究,重视政治、社会和价值判断等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反对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逐渐形成了英国历史学派。凯尔恩斯等演绎派学者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理论层面和自然科学一样,提供的是一种趋势性的结论,不依赖于现实,只能源自逻辑思考,但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理论在应用时可能会因为现实条件差异而出现问题,历史学派以此来攻击其理论错误是没有道理的。杰文斯更发起了边际革命,以数学方法代替逻辑推理,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经济学框架。这一新框架更易于实现不同学者研究成果的累积,以及建立逻辑自洽的持久性理论体系。因此,相对于历史学派,后者更能适应19世纪后半期英国大学作为知识主要载体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化的发展潮流,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由此发展为新古典经济学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历史学派和演绎学派在理论观点、政策建议和学科主导权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工具论”思想的指导下,将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看做是经济研究中同样重要的工具,吸纳了历史学派很多正确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历史学派虽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和更为切合英国国情的政策建议,但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可以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的体系,并在竞争中连续败北以致被边缘化,最终在1920年代选择了组建新的经济史学科。 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分裂,对二者的发展均造成了负面影响。正如阿什利所担心的,这两个学科出现了渐行渐远的趋势。1930年代以后,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过度依赖抽象演绎和忽视现实的倾向,并因此而备受批评;而经济史学的研究也逐渐淡化了历史学派面向现实的研究风格,日益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历史领域,忽视了运用历史和制度的方法贯通古今、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的传统。 温故而知新,在厘清上述发展历程之后,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经济史学的方法意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存在问题的根源,进而实事求是地找到可行的办法,使经济史学不要偏离运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和面向现实的传统,进而发挥自身的特点,弥补理论经济学的不足,推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良好互动和健康发展。 作者感谢彭慕兰教授推荐的重要文献资料,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典型的批评如D.Seers,"The Limitations of the Special Case," Bulletin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vol.25,no.2,1963,pp.77-98;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方福前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R.Solow,"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5,no.2,1985,pp.328-331;D.North," Cliometrics:40 Years Late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7,no.2,1997,pp.412-414. ③参见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董志凯:《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之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④大部分经济思想史著作的回溯始自新古典范式,并因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而对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关系避而不谈,或仅作为思想流派加以介绍,很少分析二者长期演变的过程和原因。 ⑤相比之下,《国富论》则被熊彼特看作是历史与演绎相结合的典范。(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1页) ⑥参见1821年1月1日李嘉图致穆勒信。(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寿进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1页) ⑦参见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2卷《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14页。 ⑧理查德·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说明”、“序言”、第11—12、15页。 ⑨例如,马歇尔曾批评李嘉图这种过度抽象的思维方式并不属于英国文化,而是来自他的犹太渊源(A.Marshall,"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An Inaugural Lecture," in A.C.Pigou,ed.,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London:Macmillan,1925,pp.152-174);熊彼特更直斥其为“李嘉图恶习”。(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2页) ⑩这也是英国第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交流组织,详见K.Tribe,"Economic Societies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in M.Augello and M.Guidi,eds.,The Spread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Economists,London:Routledge,2001,pp.32-52. (1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第146页;A.W.Coats,"The Role of Author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7,1964,pp.85-106. (12)转引自杭聪:《土地所有权观念与近代爱尔兰土地改革》,《历史教学》2009年第1期。 (13)转引自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乔吉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John Maloney,"Robert Lowe,the Times,and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27,no.1,2005,pp.41-58. (14)T.Leslie,"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ate of Wages," Fraser's Magazine,vol.LXXVⅢ,July 1868,pp.81-95. (15)T.Leslie,Land Systems and Industrial Economy of Ireland,England and Continental Countries,London:Longmans,Green & Co.,1870. (16)T.Leslie,Land Systems and Industrial Economy of Ireland,England and Continental Countries,p.89. (17)T.Lesli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dam Smith,"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London:Longmans,Green & Co.,1888,p.21. (18)T.Leslie,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p.212. (19)1831年,旨在推动科学普及与发展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成立,每年举行一次会议;1833年,在理查德·琼斯的倡议下,由马尔萨斯主持成立了科学促进协会的统计学组(F组),1856年更名为“经济科学与统计学组”,成为当时英国政治经济学者交流讨论最主要的组织和平台。 (20)John K.Ingram,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Political Economy,Charleston:Nabu Press,2010. (21)因格拉门:《经济学史》第4册,胡泽、许炳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序言”,第71页。 (22)J.E.T.Rogers,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1259)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1793),Oxford:Clarendon Press,1866,1882,1887,1902;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bour,London:Swan Sonnenschein & Co.,1884. (23)历史学派的主要学者还包括毕业于牛津的约翰·A.霍布森、乔治·昂温和毕业于剑桥的约翰·S.尼科尔森;关于他们的介绍,详见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和A.Kadish,The Oxford Economis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 (24)J.Mill,"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 in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Rockville:Arc Manor LLC,2008,pp.105-139. (25)John E.Cairnes,The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Longman,Brown,Green,Longmans,& Roberts,1857,pp.65,69.这种“不存在干扰因素”或者“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表述,被马克·布劳格比喻为某种“期票”,它并不意味着兑现本身,而只是兑现的前提条件,“只要公众能够保持对它最终能够按其票面价格得以兑现的信心,它就可以一直在科学世界里自由循环”。参见M.Blaug,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61. (26)John E.Cairnes,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pp.152-153. (27)这一思想并非凯尔恩斯所独有,而是此后演绎派学者的共识,参见Carl Menger,Collected Works of Carl Menger,vol.Ⅲ,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1935,p.279;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28)在两人的著作和书信中,常以“吾友”(my friend)相称。杰文斯曾使用历史统计的方法撰写过数篇关于经济周期和物价波动等问题的论文,并因此而获得了教授职位;莱斯利在为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撰写的书评中,也对效用理论的意义和边际效用递减思想赞赏有加。 (29)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4、27页。 (30)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7页。 (31)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5、30页。 (32)尽管微积分学早已创立,但直到1821年柯西明确阐述了极限概念和1861年魏尔斯特拉斯给出了极限的严格定义之后,微积分才真正趋于严密并成为了一项可以被广泛应用的工具。杰文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这些调整与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本文对此不再展开讨论。 (33)T.Leslie,"Jevons′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pp.66-72. (34)Joseph Ben-David,"Universities," in David L.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vol.16,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1968,p.194. (35)G.Stigler,"The Adoption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no.2,1972,pp.571-586. (36)A.Usher et al.,"Round Table Discussions on Economic Hist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8,no.1,1928,p.91. (37)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原著第一版序言”。 (38)(56)A.Marshall,"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An Inaugural Lecture." (39)A.Marshall,"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An Inaugural Lecture."这与门格尔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批评非常相似,参见Carl Menger,Collected Works of Carl Menger,vol.II,p.260. (40)W.Cunningham,"The Perversion of Economic History,"The Economic Journal,vol.2,no.7,1892,pp.491-506.马歇尔学生的一些评论似乎印证了这一批评。(彼得·格罗尼维根:《翱翔的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丁永健、鄢雯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29、246页) (41)A.Marshall,"A Reply," The Economic Journal,vol.2,no.7,1892,pp.507-519. (42)W.Cunningham,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ree Trade Movement,London:C.J.Clays & Sons,1904. (43)W.Ashley,The Tariff Problem,London:P.S.King & Sons,1903. (44)兰福德·普赖斯(Langford Price)是马歇尔在牛津贝利奥尔学院任教时的学生,在马歇尔的帮助下,获得汤因比信托基金的讲师职位,但在学术观点上,普赖斯完全支持历史学派。 (45)高岱:《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46)H.S.Foxwell,"The Economic Movement in England,"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no.1,1887,pp.84-103; A.W.Coats,"The Role of Author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Economics." (47)这本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水岭,参见D.Milonakis and B.Fine,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Method,the Social and the Historical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9,p.119. (48)1902年以后,该协会改称“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 (49)A.W.Coats,"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The Economic Journal,vol.78,no.310,1968,pp.349-371;A.Kadish,The Oxford Economis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p.191. (50)N.Jha,The Age of Marshall:Aspects of British Economic Thought,1890-1915,London:F.Cass,1973,pp.201-203. (51)A.Kadish,The Oxford Economis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pp.198-199. (52)A.W.Coats,"Sociological Aspects of British Economic Thought(ca.1880-1930)," Journal o f Political Economy,vol.75,no.5,1967,pp.706-729. (53)A.Kadish,The Oxford Economis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pp.204-205. (54)A.W.Coats and S.E.Coats,"The Changing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890-1960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British Economic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4,no.2,1973,pp.165-18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83—84页。 (55)D.E.Moggridge,"Method and Marshall," in P.Koslowski,ed.,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Eth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Newer Historical School,Berlin:Springer,1997,pp.342-369. (57)A.Marshall,"The Old Generation of Economists and the New,"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no.2,1897,pp.115-135; A.Marshall,A Plea for the Creation of a Curriculum in Economics and Associated Branches of Political Science,Cambridge:J.and C.F.Clay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02. (58)牛津大学1920年设立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学位(PPE),保留了关注历史、制度和面向现实的牛津传统。 (59)竞争者中还有埃德温·坎南;庇古的成功当然不能仅仅归功于马歇尔的支持,他自己的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关于这次竞选的详细情况,参见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86-206页。 (60)W.Ashley,"The Place of Economic History in University Studie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no.1,1927,pp.1-11. (61)N.B.Harte,ed.,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Collected Inaugural Lectures,1893-1970,London:Routledge,2001,pp.3,7,23,40,50,58. (62)J.H.Clapham,"Of Empty Economic Boxes," The Economic Journal,vol.32,no.127,1922,pp.305-314; J.H.Clapham,"The Economic Boxes," The Economic Journal,vol.32,no.128,1922,pp.560-563. (63)J.H.Clapham,"Economic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in E.Seligman,ed.,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5,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7,p.329. (64)R.M.Hartwell,"Good Old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3,no.1,1973,pp.28-40. (65)N.B.Harte,ed.,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Collected Inaugural Lectures,1893-1970,pp.87-126.作为费边社和英国工党的重要成员,托尼带有历史学派风格的改良主义思想,对当时的英国学界和社会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66)N.B.Harte,ed.,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Collected Inaugural Lectures,1893-1970,p.83. (67)J.R.Hicks and A.G.Hart,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American Economy: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pp.10-11. (68)N.B.Harte,ed.,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Collected Inaugural Lectures,1893-1970,p.170.在196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福格尔等学者曾试图通过计量回归的方法,实现经济史和经济学的再统一,但遭到了经济学家索洛和经济史学家陈振汉等的严厉批评。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对此进行考察,有兴趣的读者也可参阅R.W.Fogel,"The Reunific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with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5,no.1/2,1965,pp.92-98; R.Solow,“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陈振汉:《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69)A.C.Pigou,ed.,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p.437. (70)A.Marshall,"Letter to Arthur Bowley," February 27,1906,in A.C.Pigou,ed.,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pp.427-428. (71)A.C.Pigou,ed.,Memorials o f Alfred Marshall,p.84. (72)A.Marshall,"Memorandum on the Fiscal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J.M.Keynes,ed.,Official Papers by Alfred Marshall,London:Macmillan and Co.,1926,pp.365-420. (73)A.C.Pigou,The Func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9,pp.4-5. (74)庇古:《福利经济学》,朱泱、张胜纪、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页。 (75)A.C.Pigou,Economic Science in Relation to Practice,London:Macmillan,1908,p.13. (76)庇古:《福利经济学》,第2、9页。 (77)庇古:《福利经济学》,第16—28页;A.C.Pigou,"Some Aspects of Welfare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1,no.3,1951,pp.287-302. (78)庇古:《福利经济学》,第185—209页。 (79)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488页。 (80)凯恩斯:《经济学家的生活》,吴贵根、杨玉成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81)J.M.Keynes,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4,London:Macmillan,1973,p.297. (82)J.M.Keynes,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4,p.296. (83)A.W.Coats,"The Role of Author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Economics." (84)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1—122页。 (85)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第234页。 (86)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第20页。 (87)希克斯后来也承认这一模型存在很多不足,因而只是一个教学的工具。详见John Hicks,"′IS-LM′:An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3,no.2,1980-1981,pp.139-154. (88)在美国政府和考尔斯委员会等的支持下,美国新古典经济学家迅速实现了包括凯恩斯理论模型化、线性规划、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等一系列的经济学新发展,与历史学派持类似观点的美国制度学派则被边缘化。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对此进行考察,有兴趣的读者也可参阅Y.Yonay,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Institutionalist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in America between the W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高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